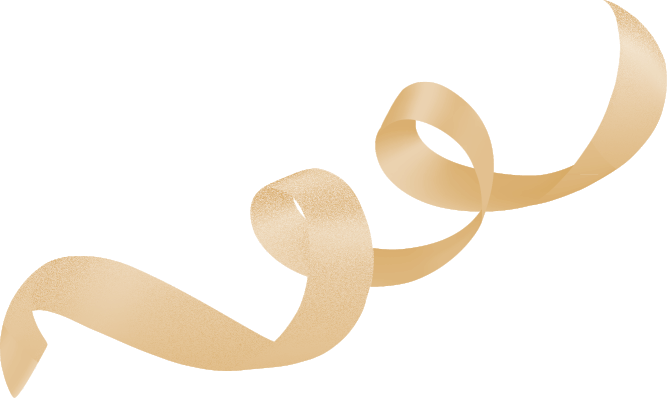段义孚 著
宋秀葵 陈金凤 译
作为具体存在的社会性的人,我们需要一些赖以养育和支撑并感到亲切的地方,如家和四邻,社区和亲属。作为政治性的人,我们需要寻找一种归属感,它不仅存在于家或四邻,还存在于更大的实体——城市或州之中,其中的大多数人是熟人和因客观的市场运作、政府机构以及共同的公民身份联系在一起的陌生人。人具有思考能力,因此属于更大的世界。顽皮的孩子把地球当作其完整住址的一部分,大人迟迟才意识到这种观念的真谛。但是地球之外的天体呢?一个人有可能喜欢太阳系本身吗?我曾经一度以为这个问题遥不可及,但现在不这么认为了,因为近期发生的事拓宽了我的思维。1990年2月13日,宇宙飞船“旅行者1号”离开太阳系,并同时在它的上面拍摄了太阳、地球及其他六个行星的照片。一张关于太阳系的快照被刊登在《科学》杂志上,如今我可以剪裁下这张照片,把它贴在家庭相册上。而至于宇宙,我相信弗朗西斯·培根首先提到的,宇宙正如它本身足够大,大到恰好可以作为人类心灵的栖息地。是的,我们同时拥有灵魂与肉体。对于脆弱的身体来说,一个舒适的家和社区大小恰好;而对于灵魂来说,如古印度哲学家和现代天文学家所想象的那样,任何小于这个世界甚至宇宙的东西,都似乎能令人感到幽闭恐惧。
现在有大量关于“地方感”的文学作品,并且其数量还在继续增多,这些作品压倒性地致力于再现那些小的明确的地区。这些微小地区的至关重要性是十分明显的。然而,我想从孩子那里得到一些线索:我想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探索“地方”——它与身体、思想和精神的关系,以及它的馈赠和义务。我先从壁炉这一微观角度入手,因为它满足了人的基本需求——避难与呵护。
一、避难与呵护
从狭义上讲,壁炉就是炉边。随着对火的使用,我们的祖先大概在五十万年前第一次明白庇护所和家真正意味着什么。在使用火之前,早期原始人在黑夜里因捕食动物的存在而无法感到安全;在使用火之后,他们可以在洞口生起火,驱走捕食动物,由此感到安全。洞里的火同时也带来了温暖和光明,还有木头燃烧的噼啪声和肉烧烤飘出的香气。火在墙上投下摇曳的阴影,赋予其一丝神秘的气息。跳动的火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大家都围聚在火旁。作为封闭的空间,洞穴也有类似的功能:不仅使人类与自然隔开,同时也凝聚了居住者的精神能量,加强了他们彼此间的认识。因此,世世代代,人类每建立一个封闭空间,也就建造了一个亲密的人类保护圈。尽管各地和每个时代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是基本经历大致是一样的,“温暖”和“壁炉”这两个词分别体现了其字面及比喻意义。
家意味着“呵护”。我们对“呵护”记忆最深刻的时间段,一是很长一段时间需要依赖的童年,二是任何生病期间。所有的动物都会照顾自己的后代,物种的生存正是依赖于这样的照顾。但照顾病者则是另外一回事,愿意把其他工作放在一边来专门守护照顾病人,直至病人康复,这是人类独有的。狒狒以及其他猴子、猿类群体里都不存在这种护理的家庭基础。人类学家告诉我们,当“群体每日例行出发的时候,所有成员必须跟随一起行动,否则就会被遗弃。对于狒狒来说,唯一获得保护的方式就是与群体呆在一起,不论受伤或病得多么严重,它都不能掉队……对于野生灵长类动物来说,与群体分离便是致命的疾病;而对于人类来讲,致命的疾病是即使在家庭人员的守护和照顾之下仍无法痊愈的病”。我们会很自然地从那些在背后照料我们恢复健康的人身上感受到温暖,也很自然地对我们赖以痊愈的地方本身产生深深的情结。随着病者身体慢慢恢复,鸟儿在身旁歌唱,树荫下的凉爽带来如母亲般的关怀。奇怪而相当悲哀的是,狒狒却享受不到这种待遇。
二、亲密关系的纽带
众所周知,血缘使人类关系密切,特别体现在父母与孩子之间以及兄弟姐妹之间。这一部分要归因于人类本能,在母亲和孩子间体现得最为明显;另一部分则归因于亲密关系的早期体验:从婴儿时期的吃奶,到由哥哥姐姐看护,再到与其他年幼的亲属一起玩耍。身体的亲近在加强关系方面,至少跟血缘起到了同样的作用。跟我们住得最近的人,不管是否与我们有血缘关系,我们都管他们叫“叔叔”“阿姨”或“哥哥 (弟弟) ”“姐姐 (妹妹) ”。这些礼貌的称呼可能在整个近代社会都普遍使用。
维持大众生计的共同工作加强了人们之间的联系。《诗经》是一部中国文学名著,其中的诗歌可追溯到公元前八世纪,里面有干农活时温馨感人的场面。“千对”劳工在其头领、雇主及其儿子的监管之下,清除杂草和树木,犁地耕田。午休期间,妻子们送来的篮子里盛满饭,丈夫们都在那吃,“离他们的妻子很近”。在与《诗经》几乎是同时期的史诗《伊利亚特》中,荷马描绘了这样的情形:农夫牵着他们的牛走在松软肥沃的土地上,在田地边,主人双手持一杯浓酒迎接他们。传统农业可以使人们体会到深深的情谊。农民的劳作节奏不仅与自然周期相关,还跟其劳作伙伴的行动及日程安排有关,这些劳作伙伴可能是他的亲戚。田纳西州一位妇女指出,她的四个兄弟间关系密切,因为他们四个拥有相邻的农场。她说:“他们终日一起劳作,一起吃饭,并且在回家之前总是闲坐聊天。”
三、自然与神灵
与自然的亲密关系是人类满足感的最深来源之一。人们极其渴望生活在农场或小的社区,这里有那些记忆模糊的触感、香气、景象和声音,那些在户外工作时围绕着他们的东西。自然的爱抚能使人得到安慰并获得生机,甚至她的“斥责” (如莎士比亚所说)也能提升人的幸福感和生命力。同时,自然也哺育着我们,因此也可以称之为我们的母亲和最亲近的家人。从广泛意义上来讲,这仍是对的。虽然如此,这种比喻在现代人听来却很奇怪,因为餐桌上的食物可能来自于世界各地——那些地图册上的抽象地名,而非像过去那样,来自于自己村庄周围的田地,那些自己每天可以看到、嗅到、照料到的不变的田地。
对于每一种生物而言,地球既是其孕育的摇篮,也是其死亡的坟墓。据此,对地球的虔诚也就自然产生,这也引发了宗教信仰及宗教活动,尽管这其中存在文化之间的细微差别,但仍有许多共同之处。因此,世界各地的人们找出诸如高山、河流和丛林等具有这种自然特征的神灵,以便他们祈祷和供奉。同一家族的人可能会强调家族的重要性,家族即一个家庭或宗族随着时间流逝的延续性,对血统的重视势必使得人们尊敬祖先。延伸至依稀记得的过去,祖先首先成为文化英雄,不论创造出什么奇迹,他们始终承载着人类的印记,然后就成为与自然的神灵不可区分的灵与神。
四、标准模式与其他模式
我曾提出“地方感”的一个标准模式,把它作为评判其他模式的标准,不论是否意识到自己这么做。当“地方感”用于表述大于所有感官能察觉到的单位时,这意味着我们打了个比方,从直接而具体的经验中推测出间接且抽象的认识。如此说来,一个完整的民族国家可被称作祖国,配有主神或图腾;又或者,整个地球可被称作人类的家园,并被赋予盖亚这一神圣的名字。是思想包含了更广大的实体,但情感也绝不示弱。实际上,情感参与的力度更大。在国外待一段时间返回美国时,我们会对它产生一种特殊的情感;同样地,当我们坐宇宙飞船在太空待一段时间再重返地球的时候,会对地球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地方感”的标准模式,强调经过一段时间后获取直接而复杂的体验,诉诸常识,但是它无法解释这样一种奇异的现象,即:尽管没有复杂的体验,我们也可能会对一个地方产生强烈的感觉,对它不仅仅是一种视觉的欣赏或者抽象的理解。这种现象令人感到奇怪,不是因为地方的范围太大,而是因为人没有一段时间的体验。设想一下沙漠。居住在沙漠里的游牧民以标准模式的复杂方式了解沙漠,但对游客来讲,可能因为第一次见到沙漠,体验会更神秘而深刻,这种体验的成分包括认可、精神上的亲切感、兴奋感甚至是安全感。认可无关熟悉,因为沙漠并非如家一般,也几乎没有居所和养育的明显标志。亲切感基于精神层面而非感官层面——更多的是周围景观的和谐感,而不是对其特殊的标志建筑和神灵的尊崇。至于安全感,这种“家”的标志,并非来自任何可能的物质养育(因为沙漠对陌生人来说是有敌意的),而是来自于精神上的肯定——来自于沙漠带来的几何线条的清晰感。
五、神圣的空间与神圣的地方
“地方感”的标准模式代表了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随着物质文化的进步而逐渐消失,由此增强了人们应对自然力量的信心。拥有了更强大的自信,人们倾向赋予空间和地方越来越多的正面价值。人们对抽象与客观的事物产生了兴趣,比如天文学上确定的空间坐标系,辉煌壮丽,赋予它独具特色的神秘色彩。我以一个中国的例子来阐释这种观念。传统的中国社会是等级社会,权力与教育集中在上层人士手中。这些上层人士跟普通百姓一样,都拥有住宅和宗祠,普通百姓指拥有一些土地的工匠、小商贩和农民。尽管他们二者的地产大小和职位性质存在明显的差别,但是这两个社会阶层的住宅都能唤起人们与标准模式相一致的复杂情感。
在“家”的范围之外,出现了不一致的现象:上层人士把注意力放在神圣的空间上,而普通百姓则关注神圣的地方。上层人士的神圣空间依据天体的周期性变化和运动来界定,尤其与太阳相关,这与宇宙密切相连。首都北京本身就是一张宇宙图,是个神圣空间,其设计体现了宇宙秩序。在宇宙空间的活动是庄严的、可预测的:二分日和二至日是农历的开端与结束,人们会举行仪式来纪念这些极重要的时刻,皇帝和上层人士会来参加。然而对于神圣的空间和在此举行的仪式,地位和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很少感兴趣。他们的关注点集中于城市神圣空间的某些特殊地方——一棵树、一口井、墙的一角、一座建筑——那些确实发生过异常事件的地方,或者在那些反复讲述和润色的故事里,人们认为发生过异常事件的地方。事件本身可能是关于自然或人类的,但不论怎样,都被罩上超自然的光环。神圣的空间和神圣的地方都能使人产生敬畏感:对神圣空间的敬畏感来自于其规模和时空秩序,对神圣地方的敬畏感来自于其不可预测性和奇异性。上层人士认为,他们能够强加于现实一种秩序,当然这种秩序以前还不存在。相比之下,普通人拥有更少的权力去调整自己的生活,他们认为现实主要是由变幻莫测的力量和偶发事件组成的,这些力量和事件需要被确定,需凭借故事使人熟悉,并通过神奇的方式加以抚平或控制。
宇宙空间,作为一个具有丰富共振基本点和中心的概念性坐标,为世界上很多地方所认可,一个人可以在其中轻松地找到共同点。不过,它们也存在不同之处,其中较为显著的是在建筑上体现的程度不同。在一些社会中,宇宙空间基本上依然是理念和姿态;在另外一些社会中,它也是建筑和人造空间,可能是整座城市。建造名胜和城市需要知识、技术和组织结构,简而言之即力量。中华文明已拥有这种力量。在运用这种力量去建造几何形的城市——一项人们认为拥有天堂之令的事业时,地球上不规则的自然特征及其主要神力,以及农场、村庄这些人类卑微的作品都会被迁移或彻底改变。从这种程度上说,随着人们对天堂的尊敬加深,对于地球及其神灵的敬重却减少了;或者换而言之,随着空间感意识的增强,对于地方感即地区独特性的认识却减弱了。
六、抽象和地方感的丧失
现代文明越来越偏好抽象笼统,否则,先进的物质文化几乎无法存在。在中国,早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周朝君主渴望把国家分成精确的方格状,并把国都定于国家中心。当然他无法实施如此宏伟的计划,但是跟后来的许多继承者一样,他的确认识到,高效地发挥政府的作用需要清晰化和规范化 。正规的城市建有长方形模式的街道,这受天堂秩序的启发,这种城市在任何地方都可建立,却很少考虑该地的地理特征。因此,帝国城市便呈现出某种单调统一的面貌,但是高效弥补了这一缺陷。一位钦差大臣为了把工作做好,应该在被派遣工作的任何地方都感到轻松自如——如果他的新居建筑和所管辖城市的设计保持相似,他就能更快地进入这种状态。
在中国的封建体制之下,没有人可以在自己的家乡做地方长官,因为人们认为这会牵涉太多当地责任和私人情感而使其无法公平执政。因此,官员会被送至另外一个城市,即便在另一个城市,他也不能呆很久,避免其发展当地势力,影响他保持公平正义。一位官员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会在多个城市任命,如果幸运的话,在其职业巅峰时期会在京城任职。这种无根的到处移动,其影响之一就是空间感——对空间范围及其宏伟的感受。官员成为了一个世界公民,在帝国的很多地方都能感觉自如。但也并非完全如此。成为世界公民所带来的体面,可能会使其精神振奋,但同时也会使其身体感到疲惫,人会渴望家的稳定。因此,一直四处奔波的官员饱受着乡愁的折磨。毫无疑问,驻扎在边疆的士兵和为了寻求更高利润市场不断移动的商人,也同样饱受思乡之苦。官员也是文人诗人,与其他人相比,他们通常更多地把思乡之情记录在哀伤的诗文之中。
封建中国对于矩形网格的渴望,可能会使我们联想到美国类似的网格设计。城镇及其范围内的土地测量体系,将国家的三分之二划分成方格,使得美国的大部分地貌呈现严格的传统特征。此外,一些聚居区有垂直的街道和大路。当然,这些网格的目的与中国的完全不同。在美国,宇宙的特殊意义其实是微弱的,然而经济目的——土地的有效利用及开发——很重要。但细细想来,二者依然存有相似点,即使仅仅因为任何大规模的几何设计都将天堂而非地球作为参考标准。中国的天文学更接近于美国现代天文学,而非注重那份抚慰幽灵出没之地的心境。还有另一个相似之处。不论在帝国管理还是土地规模方面,几何网格设计都能提高效率,这一点在中国和美国都被认可。然后就是流动性的问题,即无论身在何方人的心灵归属问题。美国为移动中的人提供方向的便利。简单的几何图样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可能略显乏味,但对于陌生人和过客却十分有利。
在西方文明中,天空是陌生人的指挥神灵,在古希腊(至少从荷马时期)就已经如此了。城隍照料他们的子民,那么谁来照顾进入该管辖范围的旅客呢?答案是:众神中至高无上的主神——宙斯。基督教的神就承担着宙斯的职责,因为它对陌生人和无家可归之人也很友好。繁华城市中的移民群体乐于接受新的宗教,然而传统的罗马家庭,植根于他们的宗祠,乡下人依旧深受自然神灵的束缚影响,它们二者都抵制新的宗教。基督教的神是极为公正的,他的脸如太阳一般,同样照耀正义之人和不义之人;他可以被依赖,对那些无家可归之人,即那些没有享受当地神灵庇护的人们,显现恻隐之心。这样一位神,在美国深受欢迎是合乎情理的,但很奇怪的是,美国不像边界以南的那些地方,即使在其罗马天主教群体中也没有宗教圣地和朝拜中心。在历史上,美国人拥有空间感而非地方感。只有在20世纪下半叶数十年里,人们对于地方及根脉、血统和守护神的渴望才真正凸显出来,而且这存在于那些其祖先在开放的场景——边疆及天城中寻求灵感的民族中。
七、超脱:地方感丧失
民间社会的宗教具有特定的地方特点,每一片树林、每一个洞穴、每一条河流以及每一户家庭都有其内在的精神。民间社会制定的宗教仪式增强了责任感和依恋感。而宗教和哲学则恰恰相反,它们宣扬超然尘世。比如佛教,它将其存在归因于大胆的分离行为。乔达摩·悉达多决定离开家,什么样的家呢?是一个完美的家庭,家里有一位慈爱的父亲,父亲是一个小王国的统治者。这个家拥有感官和情感渴望的所有东西,但缺乏满足精神渴求的东西。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佛教是极其严苛的。与其他主要信仰相比,佛教更不允许人性的弱点和需求,包括从具体和有限的事物上寻求安慰和保护。佛陀在哪里?这样一个合理的问题却会引发令人困惑的答案。有个故事讲的是,一个禅僧因把唾沫吐在佛陀的雕像上而受到训斥。他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说,佛陀无处不在,这一点禅师们教导过,所以他很难把唾沫吐或不吐在佛陀身上。他的回答显示出对于神圣地方的彻底否定,更概括地说,是对某个地方有着特殊依恋和尊重的人类需求的否定。
耶稣缺少一个可以退避的地方。“狐狸有它们的洞穴,鸟有自己的巢穴,但圣子耶稣却无处安放他的头颅”。在作出该抱怨后不久,耶稣提出的一个观点挑战了基本的孝道,即他提出要埋葬逝去的父亲。“离开死者并埋葬他;你必须要将之告知天国”(《路加福音》第9章:57—60节)。对于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埋葬的地方是具有深刻意义的,且这种埋葬行为是有关尊重、急切的渴望及抚慰的原始行为。耶稣似乎对这二者都不以为然,他认为不存在神圣的地方,即没有能敬拜上帝的地方。一位撒玛利亚妇人说:“先生,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位先知。我们的祖先在这座山上进行敬拜,但你却说敬奉上帝的庙宇应在耶路撒冷。”耶稣回答说:“相信我, 敬拜上帝既不在这座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这个时刻就要来临了……这个时刻接近了,实际上当那些真正的信徒以心灵和忠诚朝拜圣父的时候,这个时刻已经到来了。”(《约翰福音》第4章:19—23节)。
亚里士多德曾说,无家可归是哲学家的自然条件。真理即哲学家的家。因此,他们的家不可能是山上的居所或者庙宇里的一个地方。阿那克萨哥拉被问道:“你不爱你的国家吗?”他指着天空回答道:“我深爱着我的国家。”古典学者卢斯认为,该“轶事使其成为首个明确的‘世界主义者’,即忠诚于科学真理而非属于雅典或克拉佐美纳伊的‘宇宙公民’”。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强调自由是人的纯粹的内在品性,从而否定了地方的重要性。马可·奥勒留在其著名的《沉思录》中写道:“就我是安东尼来说,我的城市与国家是罗马;但就我是一个人来说,我的国家就是这个世界。” (卷4, 第44节) 并且,“你要始终清楚,这片土地与其他地方无异;这里的一切跟山上、海边或者你愿去的地方的一切一模一样。因为你会发觉,正像柏拉图所说的,居于一个城墙之内就跟居于山上一个牧人的草棚中一样” (卷10, 第23节) 。
我们的家在哪呢?如果不是城市或山脉的话,那它是整个地球吗?然而,对于马可·奥勒留来说,整个地球也只是一个点而已。在他的脑海里,他有足够的想象力将地球视为一点,而我们在大约一千八百年之后,在从宇宙飞船上拍摄的太阳系照片中,才真正地将地球视为一个点。提倡心灵的栖息地为宇宙,而非一些特定的地方,这令人振奋,但这种想法也会导致对身边触手可及的事物视而不见和不负责任,并最终导致不真实感,因为我们毕竟是人类。斯多葛的世界因其一切都以朴素为美,是苍白无色的,最终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甚至因此可能是悲哀的,因为它缺乏生命的热烈绚丽,而这只能由特定的人、文化及地方才能彰显出来。
八、生物与灵魂
我们是与大地紧密相联的生物,同时具有渴求自由的灵魂。我们需要对大地万物有更强烈的情感,这是支撑现代环境生态运动的理念、热情和规划的基本认识之一。环境保护主义者已重新发现了这种由来已久、为全世界人所共享的智慧。就肉体性的存在而言,我们需要在我们自己的地方感到心满意足,这个地方要具有独特的个性和氛围,具有自身的文化印记,以及由动植物组成的它自己的生物群落,我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而我们要给予其关爱和尊重。然而,就思想和灵魂而言,我们经常会不由自主地向往其他地方,这也是很自然的。向往别处是我们的天性使然。小孩一边依偎在母亲臂弯里听故事,另一边却想象着另一个世界。既在“这里”又在“那里”,这种人特有的能力从小就会显现出来,幸运的年轻人在富足的社会可以持续接受这种能力的培养,这是通识教育所提供的最好的东西。不幸的是,即使在富足的社会,也并不是每个孩子都能从中受益;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个孩子都能以一种玩笑却严肃的方式,告诉你她的地址,这个地址不仅包括她自己的社区,还包括地球甚至宇宙,或者不仅把她的文化家园定位于一种特定的遗产,同时还是人类的遗产。
九、瓦茨拉夫·哈维尔的家
瓦茨拉夫·哈维尔是一位剧作家,同时也是捷克共和国的总统及捷克斯洛伐克的前任总统,让我以他的“地方感”结束全文。他写道:
我的家就是我居住的房间……我已经习惯居住、而且从某种程度上布满我自己无形踪迹的地方……我的家就是我的居所,我出生或者度过大部分时光的村庄或小镇。我的家就是我的家庭,我的世界,我朋友的世界,我的职业,我的公司,我的工作场所。很显然,我的家也是我居住的国家,是那里的语言所表达的智慧及精神氛围……因此我的家就是我的捷克,我的国籍,我认为我根本没有理由不去接纳它,因为它如我的男子气概一般是组成我的基本成分,我的男子气概是我另一个层次上的家。当然,我的家不仅是我的捷克,也是我的捷克斯洛伐克,这是我的公民身份。此外,我的家也是欧洲和我的欧洲身份。归根结底,家即整个世界和它现在的文明,就此而言,家即宇宙。
本文原载《鄱阳湖学刊 》2017(04)。注释、引用请参考原文及出处。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