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福清(Борис Львович Pифтин, 1932—2012)是俄罗斯当代杰出的汉学家、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他出生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一个犹太职员家庭,从小就对文学感兴趣,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学激发了他更大的兴趣,之后他一直致力于汉学研究。2003年,李福清获得中国教育部授予的“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这是中国政府授予国外最为杰出的汉语教育工作者和汉语语言文化研究者的专门奖项,李福清是俄罗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汉学家。
李福清学识渊博,汉学研究范围极广,中国神话是他最早进入也始终钟情的汉学研究领域之一。北京大学俄罗斯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张冰主编的《神话与民间文学——李福清汉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是李福清教授汉学研究论集,收录了李福清关于中国神话和民间文学研究的一些重要论文,内容涉及中国神话、中国古代人物外貌特征的描写原则和人物形象观念及艺术思维的发展演变、东蒙古民间说唱艺术以及中国中世纪文学的体裁等,几乎涵盖了李福清汉学研究的所有领域。《神话与民间文学》中的“中国神话总论”和包括一百余条具体条目的“中国神话” 均选自李福清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化大典·神话、宗教卷》(《Духов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 Мифология. Религия》,2007),而《原始与发达的神话系统》则是李福清本人提供的手稿,无疑更具研究价值。

李福清教授全面梳理了海内外中国神话的研究现状,对中国神话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阐释了中国神话的体系构成和历史流变。从他对中国神话的阐释中,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一个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是以他独特的国际视野和眼光来展开中国神话研究的。他的中国神话研究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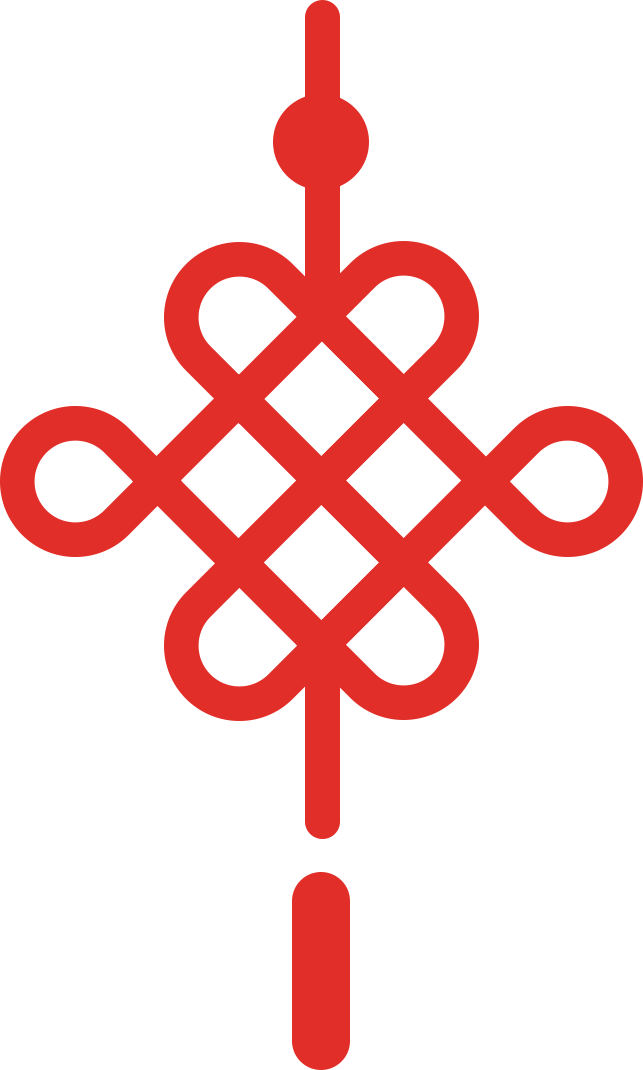
第一,系统梳理中国神话的海内外研究现状,从纵向维度探讨中国神话研究的历史进程。
李福清教授认为:“无论做什么新的研究,都需要知道前人搜集的材料及他们的研究成果,了解国际学术研究动态,与世界接轨。”他调研了海内外中国古代神话研究状况,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梳理研究俄罗斯、日本、欧洲以及中国本土对中国古代神话的研究成果,将20世纪各国对中国古代神话的研究分为20年代、30—40年代、50—60年代、 60—70年代及20世纪末进行全面剖析,整理并评析了60多位不同学者的研究观点,为我们了解20世纪中国古代神话研究状况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李福清认为,世界上第一本关于中国古代神话的专著1892年出现在俄罗斯,即格奥尔基耶夫斯基(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1851—1893)的《中国人的神话观和神话》(《Мифические возрения и мифы китайцев》, 1892)。在该书中,格奥尔基耶夫斯基首次提出了神话和神话观的区别,他认为神话观是“被所有民众所接受的”某种世界观的基础,它先于神话而出现。之后,日本学者井上圆了(1858—1919)、白鸟库吉(1865—1942)力图从新的视角研究中国古代神话,认为尧、舜、禹这些品德高尚的模范君主并非真实的历史,而是传说。20世纪20年代,欧洲出现中国神话热,欧洲汉学界开始探讨中国神话,出现了一些臆测,如把大禹界定为太阳神,把他的太太定义为月亮神等。1936年,法国首先翻译了《山海经》,并发表了第一篇关于中国神话研究的论文。30年代欧洲中国神话研究依然处于起步阶段,50年代中国神话研究的力作《〈山海经〉与造型艺术的关系》(Das Verhältnis des Schan-hai-djing zur bildenden Kunst,1952)面世。1963年,日本学者贝冢茂树(1904—1987)的《神的诞生》(神々の誕生,1963)从史学和考古学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神话,发现了中日神话某些形象的同一性,对中日神话比较研究颇具启发意义。
国内最早研究神话的是鲁迅先生,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小说的起源问题、中国原始神话的消亡问题以及中国古代神话研究的资料问题。在鲁迅之后,中国文学史开始给予神话以一定的地位。中国学界50—60年代在神话研究方面着力颇多,195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袁珂的《中国古代神话》这部神话研究力作。但是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研究过于强调神话艺术对社会生活的直线式反应,或过于强调神话的浪漫主义特征,违背了客观事实。“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神话研究陷于停顿,直至袁珂的《古代神话选释》和《山海经校注》分别于1979年、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国内的中国神话研究才掀开新的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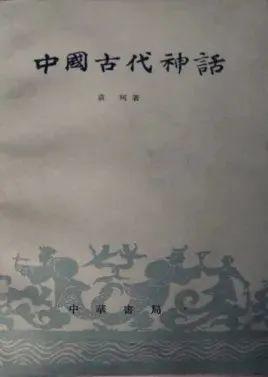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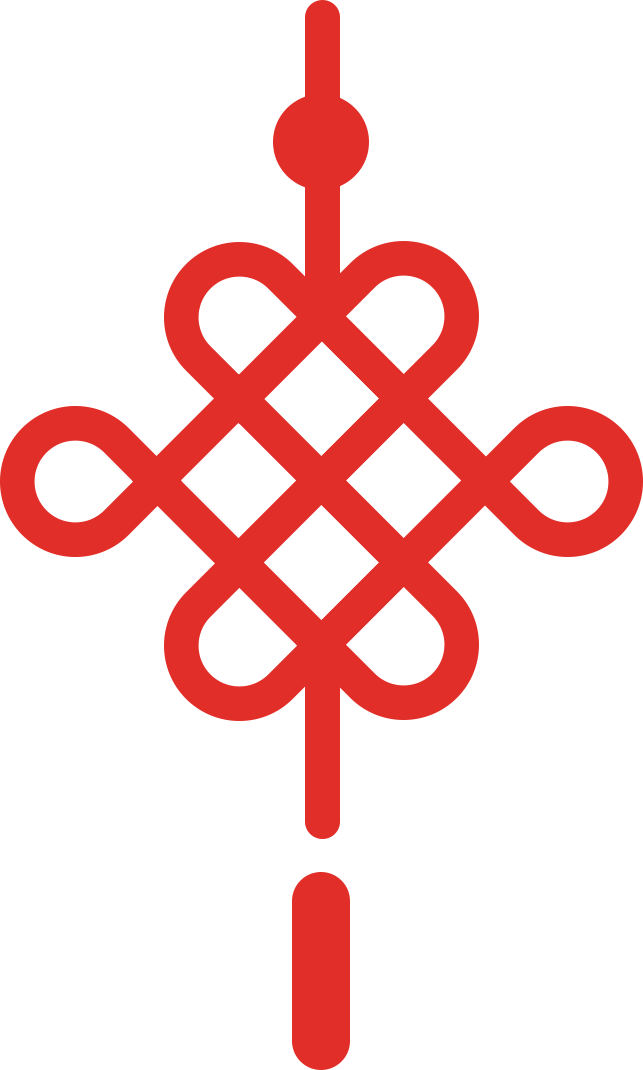
第二,用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中国神话,从广义的角度揭示中国神话的本质和特点。
李福清将中国神话划分为四个体系,即远古神话、道教神话、佛教神话和晚期民间神话。中国古代的神话观念以及与之相应的神话本身只保留在简略的、零碎的残篇中,只有借助于《尚书》《易经》《庄子》《列子》《淮南子》《论衡》等古代历史哲学典籍的记载,我们才能更好地对中国古代神话进行复原。而在儒家理性主义的影响下,神话人物很早就被解释为远古的历史人物;因此,神话的历史化,尤其是神话英雄始祖历史化是中国古代神话的鲜明特色之一。中国古代神话的主人公基本都是文化英雄,他们当中最厉害的往往被历史化为君王,重要性稍微差一些的则被历史化为官吏等。李福清指出:“这表明,文化活动同一定人物的关联不是一下子就确定的,不同的民族都把发明记在自己的英雄的名下。”例如夷部落始祖伏羲被认为是渔网和八卦的发明者,而黄帝和燧人氏都曾被记载过发现火。在研究古代神话时,李福清还着重分析了中国古代的神话观。他认为在自然哲学观念和分类体系发展的推动下,古代中国不同部落和部落联盟分散的神话形象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体系,五行观念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起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在五行观念的影响下,宇宙由四方体系变成了四方与中央的五元模式,而中央之神则是天上的最高统治者,这一变化直接导致了中国神话五帝观念的产生。神话五帝观念其实是一种较为复杂的观点体系:五帝各占一方,有一定的助手,代表不同的季节,有各自的颜色与元素,又与五行相对应。他认为,从这个思想体系中,我们可以推测出人和宇宙最初是如何产生的。

李福清认为道教神话源于中国古代神话,其神话形象是从远古神话形象观念中转变而来的,而在转变的过程中,古代神话的主人公们逐渐失去其远古文化英雄的特点,变为不死的仙人,因此道教神话又可称作“仙话”。比如黄帝和西王母,黄帝在道教神话中已不是古代的文化英雄,而是第一位神仙,是道教的始祖和保护神,而西王母在道教神话中则由实行惩罚的西方女性统治者变为不死之药的拥有者。
关于佛教神话,李福清认为“是公元初年同印度佛教一同自中亚传入”中国的,因此中国的佛教神话带有浓厚的外来佛教气息。但为了适应中国本土条件,佛教逐渐吸收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学说中的某些思想,比如孝的观念,佛教的各个人物的诞生也逐渐与中国历史人物产生了关联。在佛教的影响下,中国神话也出现并发展了地狱观念,而这在中国古代神话中一直处于非常含混的状态。
在李福清看来,与远古神话英雄始祖人物历史化相反,晚期民间神话出现了一种历史人物神话化的现象。人们把各行各业的祖师爷或做出突出历史贡献的真实的历史人物变为护佑神灵,或赐予历史人物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比如关羽因为忠诚英勇,先被尊为寺庙的保护神,又在6世纪被尊为战神,秦叔宝和尉迟敬德则在12—14世纪被神话化为门神。在中世纪,一个以玉帝为首的众神家族出现了,玉帝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道教的黄帝,而他的众神形成了固定分组。李福清教授也指出:“中国神话人物,尤其是晚近的,常常以现实中的人物充任神话主人公,拥有纪念日,在中国纪念日是按照阴历的日期来举行的。”

我国神话专家袁珂在他的《中国神话的源与流》中提出广义神话观,认为研究中国神话应 “源”“流”兼顾:“源”主要是上古活物论时期的神话,而“流”则可分为历史人物神话、仙话中的神话、中国化的佛经人物神话、民间流传的神话、后世产生的带有地方志色彩的神话和神话小说六类。实际上,李福清的神话四体系说也是从广义的角度研究中国神话,但与袁珂不同的是,他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划分中国神话的,这就使他的神话分类更具系统性、逻辑性和科学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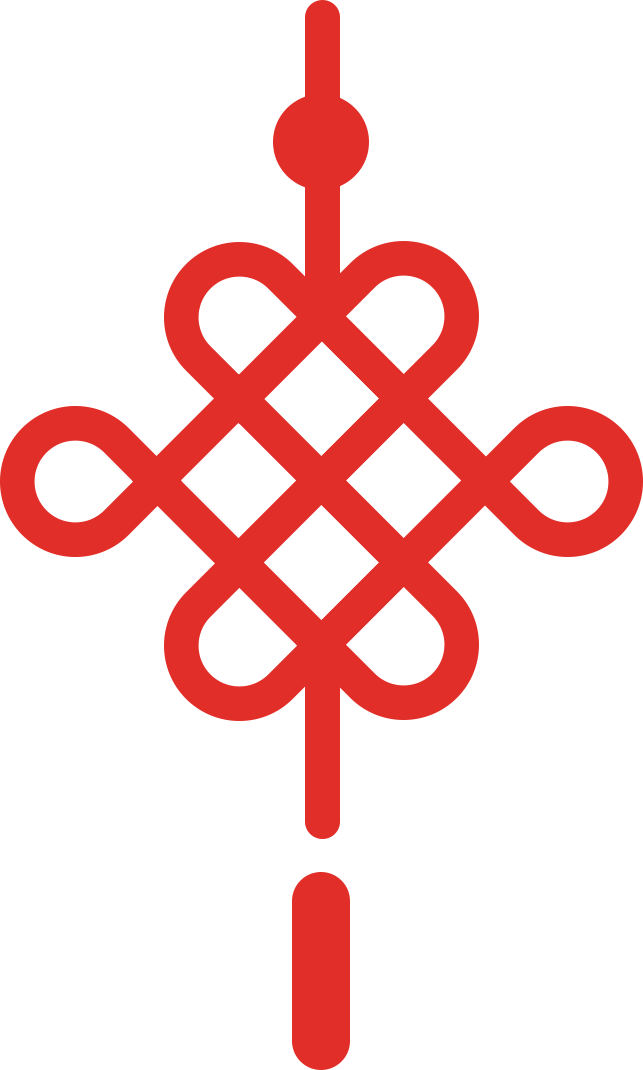
第三,李福清学术视野十分开阔,在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的过程中,他搜集并使用多个国家与民族的多语种、多形态的资料,坚持在国际视野下构筑中国神话体系,把中国神话放在世界神话概念体系中去把握。
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本来没有“神话”这一学科概念,直至1903年蒋观云在《新民丛报》第36号上发表《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神话”这一从日语中移植过来的术语才首次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正因为如此,作为一门国际学科,神话应该使用国际共有的概念,中国神话研究自然应该在世界神话概念体系的大框架下展开,进而揭示中国神话的特点与本质。一方面,中国神话自成体系;另一方面,中国神话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许多形象所赖以产生的神话观念是东亚、东南亚、中亚等诸民族所共有的,同一主题在这一区域的各民族神话中以不同的形象发展演变着,但是隐含在背后的神话观念则是一致的。李福清在搜集整理资料时发现,在与汉族相邻的民族的神话中,虽然没有后羿这样的形象,但他们也都在纪念和后羿类似的射掉“多余的”太阳的射手,这些民族也同样有多个太阳的观念:在壮族人民的颂歌中,射掉太阳的是射手特康;在瑶族人民的故事中,射手是杨雅;蒙古族则赞扬射手额日亥或乌恩。在中国台湾的几个南岛民族、菲律宾吕宋岛上的三个民族、印度尼西亚的达雅人、东印度的几个民族中,也都流传着射太阳的传说。在不同民族或地区的神话传说中,英雄有着不同名字,行为也不尽相同,但射太阳这一母题则是一致的,这充分表明中国古代的神话人物和神话观念与其他相邻民族的神话人物和神话观念具有同一性。这就凸显了中国神话研究中国际视野的重要性。

李福清认为,在研究中国神话时,无论是典籍神话还是活神话,只要利于研究,文献的、民间的,书面的、口头的,文学的(小说、讲史、演义、平话、说唱文学等)、艺术的(墓滩、石刻、壁画、年画、插图等),这些资料我们就应该合理利用。李福清教授十分注重资料的搜集,其所运用整理的史料之丰富令人叹服。在对中国神话进行剖析时,他经常引用多方面的例子,除了书面记载的典籍文学资料,还经常引用民间的神话传说和少数民族的口头文学。在谈到文化英雄伏羲和人类始祖女娲时,李福清指出伏羲是夷部落的始祖,因为夷人的图腾是鸟,所以伏羲大概是半人半鸟的形象。直到在中国神话体系形成时,伏羲与女娲才开始被描绘成夫妻。山东、江苏、四川等省份考古发现的古代石棺画像中,伏羲和女娲都被描绘成身体相连的一对,尾巴也纠缠在一起,这就证明了他们的亲密关系。20世纪60年代初在四川汉族人代代口口相传的神话传说中,伏羲和女娲是兄妹,他们的结合是为了恢复被毁的人类。而公元2世纪的书面文献只偶然提到女娲是伏羲的妹妹,“但只有9世纪时,诗人卢仝的诗中有‘女娲本是伏羲妇’之句”。在女娲词条中,他指出,屈原的《天问》中第一次提到女娲,而女娲造人的故事则在《淮南子》和《风俗通》中都曾提及,《淮南子》中还提到过女娲补天的相关故事。此外,李冗在《独异志》中谈到伏羲和女娲在昆仑山结为夫妻。李福清借助石刻、书籍和传说的资料,细致而全面地研究伏羲和女娲神话,勾勒逐步发展的、生动形象的伏羲和女娲神话人物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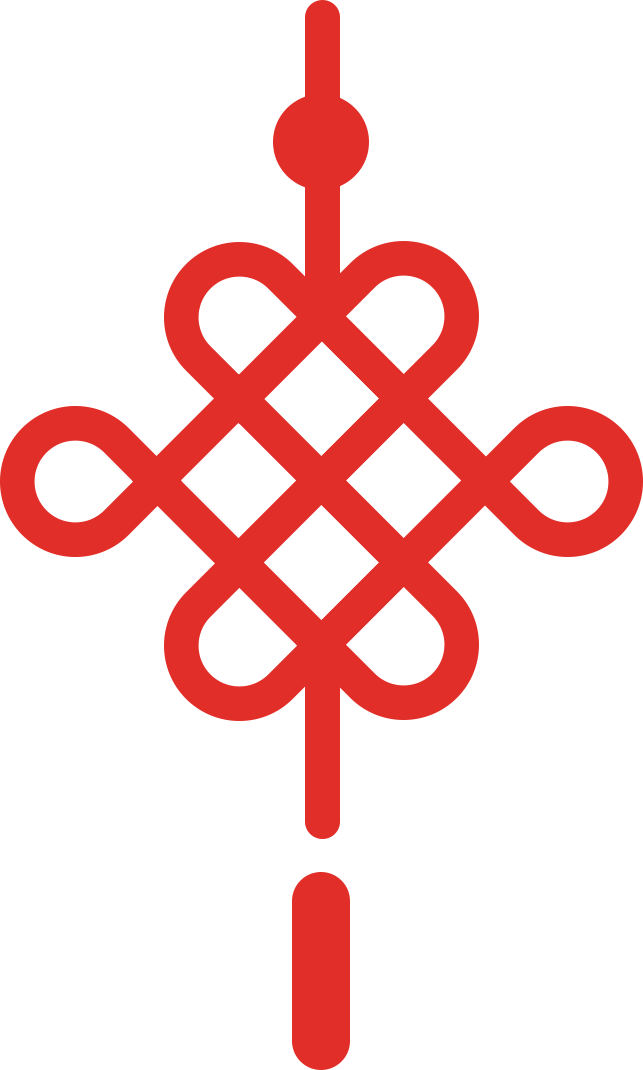
第四,在研究中国神话时,李福清教授十分注重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方法的运用。
作为俄罗斯汉学家,在神话理论方面,李福清深受普罗普(Владимир Яковлевич Пропп, 1895—1970)等苏联学者的影响,师承苏联历史诗学传统,注重用俄罗斯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神话。李福清教授提出,进行中国神话研究不能步障自蔽,必须认识到国别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强调文学的相互影响。“如我的老师阿列克谢耶夫一再强调,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他也谨遵老师的教诲,在研究中国神话时,十分注意钩沉其他民族类似的神话,并将它们加以比较研究。这一点在讨论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中国神话新采录,探讨汉族和相邻民族神话的共同特点时表现得特别突出。
在“中国神话的新采录”中,李福清指出,对于同一个传说故事,不同省份和地域的表述并不一样,必须进行比较研究才能真正勾勒出神话与传说的轨迹。关于“大洪水”神话传说,在四川省采录的故事中,大洪水不是偶然的灾祸,而是玉皇大帝为了惩罚人类而降临的灾祸;在苗族、瑶族和其他西南少数民族的传说中,洪水是雷公造成的;而在汉族的传说中,制造大洪水的则是风伯和雨师。关于“伏羲和女娲造人”传说,在苗族、瑶族和其他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传说中,伏羲和女娲的结合是由于大洪水,因为大洪水毁灭了人类,为了人类的繁衍,伏羲和女娲只好兄妹婚配。而在唐代汉族人的民间故事中也记录了类似情节,只是故事中并没有洪水,只保留了乱伦的主题,故事中也只提到了妹妹的名字,并未提及哥哥的名字。除此之外,唐代的民间故事中,兄妹婚配发生在宇宙初开之日,但苗族、瑶族和其他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传说中,兄妹结合则发生在“世界终结”之后。“伏羲和女娲造人”故事中提出婚配念头的人也不尽相同。在唐代李冗的笔记中,女娲和伏羲都是孤零零的,于是伏羲便提出婚配以延续人类,该事件发生在“宇宙初开之日”。在苗族的神话中,兄妹二人婚配以延续人类的念头则来自妹妹女娲。而在其他的记录伏羲女娲兄妹婚配的文本中,提出结合建议的却是一个神,而且是第三方的神。由此可见,即使是同一个母题,不同民族演化的情节也不一定相同,这为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过程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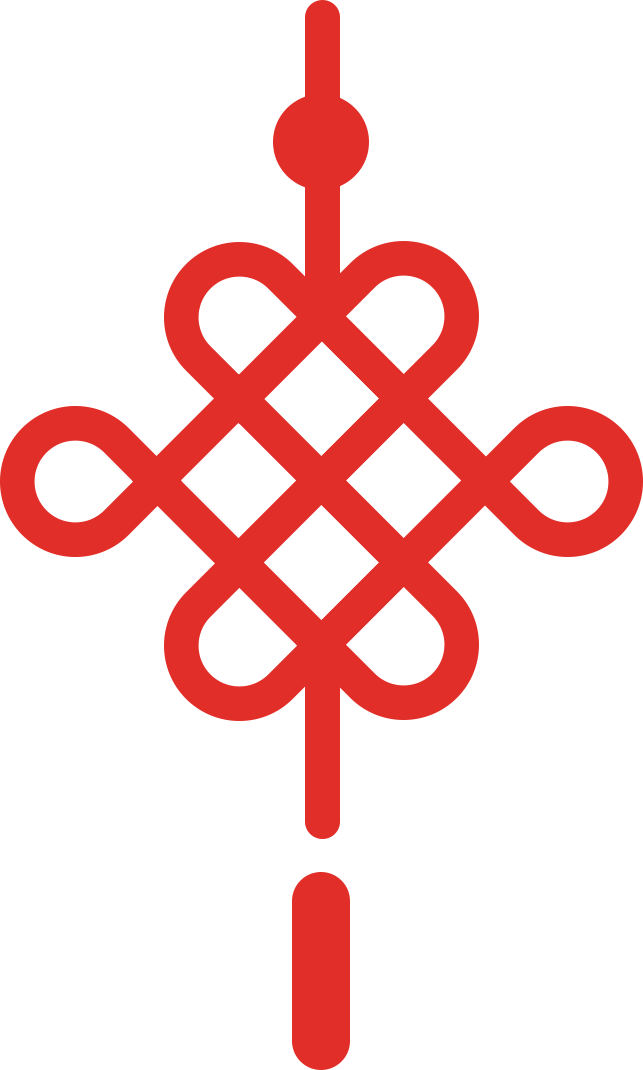
作为俄罗斯当代杰出的汉学家,李福清教授对中国神话的研究可谓独树一帜。他以国际视野将中国神话放到世界神话体系中去研究。他不仅整理了俄罗斯本土研究中国神话的资料,还整理了中国、日本乃至欧洲各国研究中国神话的资料,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神话研究的原典史料。在研究过程中,他很好地继承了自己作为俄罗斯学者的优良传统,有着鲜明的比较意识,不仅注重探析中国神话的根源,也注重比较中国神话与其他国家与民族同类型神话的情节、母题等方面的异同,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李福清开阔的国际视野,严谨而又具探索性的学术态度值得我们学习。总的来说,李福清对中国神话的阐释为中国神话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角度和大量丰富而有意义的史料。李福清的中国神话研究为解读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特别是俄罗斯汉学提供了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样本。

文章来源:《国际汉学》总第23期,2020年第2期,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详见原文
图片来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
王立群,工作单位:北京科技大学人文素质教育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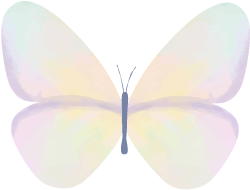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 神话工作坊 2021-02-05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