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乔健先生
乔健先生生于1935年,著名华裔人类学家。早年毕业于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后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人类学系并获得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东华大学教授、台湾世新大学讲座教授。乔先生于1979年创立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并担任系主任达十一年,于1978年创立了“香港人类学会”并担任创会会长,1986年创立了“国际瑶族研究协会”并担任首届会长。还为家乡的山西大学创建了华北文化研究中心并担任荣誉主任至今,为台湾东华大学创建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所并担任创所所长,并担任中国民族学会(台北)第十九届理事长。
乔健先生曾获多项学术荣誉,包括中央民族大学荣誉教授,首届人类学高级论坛新世纪“人类学终身成就奖”等。乔健先生长期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包括中国南岛语诸民族、中国大陆的传统底边社会、美国印第安人中的拿瓦侯传统及美亚文化关联等领域,撰写和编辑的学术论著包括《拿瓦侯传统的延续》《飘泊中的永恒:人类学田野调查笔记》《山西乐户研究》《中国的族群关系与族群》《东亚社会研究》《人在江湖:略说赛场概念在研究中国人计策行为中的功能》《中国人的观念与行为》等。主要学术论文主要有:《传统的传承:藏族<萨格尔>史诗诵唱者与拿瓦祭祀诵唱者的比较研究》《香港地区的“打小人”仪式》《惠东的常住娘家婚俗:解释与再解释》《关系刍议》《传统中国的底边社会管窥》《多元族群、多元文化与文化咨询》等近百篇。
2018年10月7日下午,乔健先生在台北过世。民俗学论坛特转载数年前徐杰舜教授对乔健先生的访谈,以表达我们深切的悼念。
【作者简介】乔健,山西介休人,美国康奈尔大学人类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人类学系创系系主任,人类学高级论坛顾问、学术委员会主席;徐杰舜,浙江余姚人,广西民族大学汉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摘 要】乔健先生50年的人类学学术生涯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研究台湾的高山族,第二个阶段研究美国的印第安人、香港的民间风俗和中国大陆的少数民族,第三个阶段是研究汉族社会至今。乔先生十分重视田野调查,认为做田野是人类学工作者的基本功和成年礼。同时,他也强调理论学习和本土研究。
【关键词】学术生涯;田野调查;本土化
【来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1:62-69.
徐杰舜(以下简称徐):乔先生,您是我们中国人类学的一位前辈,从事人类学研究已有五十多年了吧?
乔健(以下简称乔):我是1954年进台湾大学的,1955年从历史系转入了考古人类学系(1982年后改称人类学系),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人类学的研究。
徐:那就是将近五十年了。今天是正月初九,在猴年开始之际,有机会采访先生,十分荣幸。我想首先请乔先生对自己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做一个学术的回顾。
乔:好!我是1954年进到台湾大学历史系。我自己比较喜欢旅游,我想,学人类学可以到许多地方去走走,就这一点吸引了我,我就干脆去念人类学吧!于是就决定了从历史系转到人类学系。结果转过去的时候,本来系里头有九个学生,除了有一位,就是王松兴因生病休学外,其他的全部转走,我进到人类学系后,便成了唯一的学生。第一届是两个人,就是唐美君、李亦园先生他们两个人。唐美君已经过世了。第二届就是张光直他们,共三位。那么中间就是两个、三个这样子,我是第六届,是最少的,只有我一个。但在我之后,人就多起来了。所以我常说我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因为我以后下一届就是八个人,以后人就越来越多了,就不再是那么冷的一个系。
我的第一个阶段。先在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毕业以后,接着又考入研究所,进了研究所三年。我一方面是做研究,另一方面又当助教,所以可以说在台湾我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从1955年开始。记得1955年的冬天我第一次做田野调查,从那时开始到1961年7月出国,到康乃尔大学攻读人类学的博士,就算是第一阶段。
在这个阶段,我做的工作主要是研究台湾高山族,那个时候,这也是台大考古人类学系的重点,大家知道那时人类学还是比较流行研究所谓异文化。台湾高山族,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宝藏,所以当时在台大考古人类学系的一些教授都可以说是中国人类学界的精英,李济、凌纯声、芮逸夫等都是大师,但他们几乎没有一个没有尝试过去研究台湾高山族的,可见这是当时系上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也是这样。我大学的毕业论文可以说是一半对一半,一部分是民族学的,一部分是考古学的。题目是《中国境内的屈肢葬》,大陆的部分完全是根据考古报告,这个论文是李济先生指导的,但是,台湾的部分是民族学的调查,所以可以说我的论文是考古学和民族学的一个结合。当时台湾的高山族还有屈肢葬,我的运气不错,就是1958年过年的时候,我没有在台北过年,我去屏东县调查排湾族,正好在一个部落里头看到一个老年人过世的全部过程,正好是屈肢葬。据我所知道的,恐怕也是唯一一个关于台湾屈肢葬的民族学报告,而且有照片的记录。不过我自己的兴趣,那个时候在弄文化人类学。在台大也好,后来到了美国也好,人类学一定包括四种:文化人类学或者民族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还有语言学,就是说任何一个人类学家,这四样东西都要会。不过在大学念完了之后,我的兴趣主要在民族学,也就是文化人类学。所以我到了研究所以后,还是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在研究所的硕士论文我集中研究卑南族,就是我最早研究过的一个民族。卑南族当时已经开始受到人类学界的注意,就是说它有所谓的一种非单系社会亲属组织。因为我们平常观念里面看到,这种单系的社会,像我们中国是父系社会,纳西族是母系社会,都是单系,但是像美国、英国他们这种就是双边,因为他们不往上追,说亲属关系的时候只是到三四代,到曾祖父嗣这一代为止,这种叫做双边,英文叫bilateral。所以,早期的人类学家他们在讨论这种世嗣制度的时候,主要是这三种。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晚期的时候,特别是在太平洋地区,他们就发现一种非单系,有一种制度叫ambilineal,就是两可,可以父系,也可以母系,很复杂的一种情况。这种情况正好是在太平洋地区,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我们人类学方面研究亲属制度最有名的经典著作,就是G.P.Murdock的《社会结构》。这本书是1949年出版。在这本书里,他只看到主要是这三种:父系、母系、双边。最后一种叫做double descent,就是双系,非洲有些地方有的人是同时从父系和从母系的,他相信他自己的这个灵魂是从父亲这边来的,肉体是从母亲这边来的,不动产是从母亲这边继承的,动产是从父亲这边继承的。有时候从父系,有时候从母系。这种情况G.P.Murdock在1949年他都没有发现。到了50年代晚期60年代初才有人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对卑南族我自己感觉到很特别,很多日本的人类学家也说它是两可型的,所以我特别选了卑南族。卑南族又叫八社番,一个是知本社,就是我第一次去的,这个系统是很清楚的两可型。另外一个是南王,这个就很难说了,它也可以说是母系的,但至少知本是很标准的两可型,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知本系统里头的一个大社,叫做吕家,我就是做这个卑南族吕家社的社会组织,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台东县卑南乡利嘉村。在这个地方住了半年,写硕士论文,所以在台湾我主要做的一些研究工作是台湾高山族。
我是1961年出国,离开台湾,到美国去念博士学位。到了美国以后,选择去康乃尔。那时我对美国的大学了解也不多,正好认识一些美国的留学生,我大学时有两个地方给我奖学金。哥伦比亚给我奖学金,康乃尔也给我,但是康乃尔大学是属于助教的奖学金,那些美国朋友都说,你不要去哥伦比亚,那个地方太乱了,康乃尔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方,你去康乃尔。我就听他们的意见,到康乃尔去。康乃尔是在美国东部常春藤盟校中最年轻的一个学校,我们早期的一些中国学生,像赵元任啊,都去过那所学校。胡适也是,到康乃尔之后他是研究苹果,读苹果系,后来他对哲学有兴趣就转到哥伦比亚哲学系去了。康乃尔那一带环境很漂亮,不过就是比较偏僻了。到了那里之后,康乃尔也还是维持一个传统,人类学的四个领域你都要修,不可以只专修一种,比如说现在可以专修文化人类学了,那时候不可以,就是都要懂,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是遵守这个传统。不过那个时候,大部分中国人到了美国去念书,他们都是选中国研究做博士论文的题目。我自己总觉得,人类学应该是研究所谓异文化、不同的文化,不应该研究自己的文化,而且到了美国反而来研究中国文化,所以心理上有一种抗拒感觉。在当时有一位非常出名的研究中国的人类学家,就是威廉姆·斯金纳(William Skinner),他研究中国的市场。威廉姆·斯金纳就是我的导师,但是我觉得不太对劲,一方面我觉得我不应该研究自己的文化,另一方面我对他对中国的一些解释不太同意,所以搞了一年以后,我毅然就决定不跟他。正好有一位先生,在我修的课里面,作了一个演讲,我对他的东西很有兴趣,他对我也很有兴趣。他是研究美国印第安人的,叫约翰·罗伯茨(John M.Roberts),他就是我刚才说的Murdock的学生,我就想:去跟他一年也不错。所以想了半天以后,我就去跟罗伯茨讲,说想跟他学,他说当然很欢迎我。于是我就去跟斯金纳讲,说我想换导师。斯金纳当时就非常吃惊,然后他很不高兴地说:“你决定了?”我说:“我决定了。”他就很不高兴。结果第二天,他就给系里一个公开信,就是任何人接收我做学生,当我的导师的话,必须再给我一次资格考试。我那时候已经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我已经是博士候选人了,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不合法的要求,因为你已经通过了,不可能把你的通过撤回。当时,罗伯茨说他既然坚持,那只好形式上给我一个,但是不能向学校报,因为学校是绝对不接受的。所以第二天,因为斯金纳的这个通知,我到了系里,老师们看到,都说这是第一次学生主动地要求换导师,只有老师要求换学生,没有学生要求换导师的,学生把导师给辞掉了。不过我想我这个决定还是对的。
这样我的第二个阶段就从跟罗伯茨开始。那时候他正好拿到美国的叫做NIMH,即国家精神卫生部的研究经费,那个时候NIMH大概是支援人类学最多的一个,很多人类学的计划是它支援的。那时候罗伯茨有一个相当大的计划叫models of culture,就是文化的模式。他准备在美国的西南部调查比较四个族群,一个就是拿瓦候人(Navajo),一个是住在美国境内的墨西哥人,还有一个就是摩门教徒,然后就是他自己研究过的Zuni印第安人。我就负责关于拿瓦候人的研究。从1964年开始,我们两个人首先去拿瓦候,短暂的去过一次,秋天去了一次,然后1965年的春天,又是我跟他两个人去新墨西哥州。在那里有一个人类学实验室,这个实验室里保存了很多前辈对拿瓦候的研究,早期的很多前辈都在这里研究过。我们就在这里查,查完以后,就先去到新墨西哥一个叫雷玛(Ramah)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有名的美国人类学家Kluckhohn,这个人本来是研究心理学的,早期因为他身体不好,在这个地方休养,因为这个地方,他有一个舅母叫Vogt太太,在那里经营一个家庭旅馆,专门给那些游客,特别是人类学家住宿。很多有名的人类学家像克鲁伯(A·L·Kroeber)都在他那里住过。Kluckhohn在那里住下来以后,他就开始接触拿瓦候。由于与拿瓦候的接触,他开始对人类学产生了兴趣,慢慢就转到人类学方面去了。我也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后来慢慢开始进行这些研究,最后我们选定在拿瓦候比较偏僻落后的地方,当然也是传统文化保留最好的,就是在阿里桑纳(Arizona)的东北部,美国在地理上叫做四角地区(Four coner area)。为什么叫四角呢?因为它正好是四个州交汇处。我就在那里住了下来,自己买了一部福斯车,这种车的底盘特别高。拿瓦候保留区山多,都是土路,普通汽车无法开。我就在那里住下来,专门研究拿瓦候的祭仪。他们的祭仪有三十多种,每一种祭仪主要是治病。这些仪式,至少唱一个晚上,最多是唱九个晚上。我就是研究这个东西,看怎么样一代一代传下去。我这次来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要把我的论文,原来是由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出版的,翻译成中文出版。这个时候,我的兴趣,主要是在美国研究印第安人。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封面学者
在康乃尔念完博士以后我就去教书。我第一个教职是在印第安纳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是研究美国印第安人的重镇,有两位大师在那里,一位就是Hargold E.Driver,他是克鲁伯(A.L.Kroeber)的学生,是专门研究印第安人的,他有一本很有名的、很流行的一本著作,就是《北美的印第人》,是研究美国印第安人的经典著作。另外一位就是研究语言学的Voge Carl,就是Edward Spear的学生,他是李方桂的同学。印第安人的课程,主要是Driver来教,如果他不在,我也开这个课程。因为我是中国人,所以也要开始教关于中国方面的课。我开了两个课程,一个是中国文化,一个是现代中国文化的变迁,这个是第一学期的课。这样,我一方面研究美国印第安人,另一方面因为那时候中国大陆正在开始“文化大革命”,我也因为教课的关系,开始注意中国方面的一些变化,也写一些关于中国方面的文章,不过这个是根据文献来写的,后来发表了。在那里我呆了七年,但是实际上是只有六年,因为有一年我回到台湾。就是1970年到1971年,我回到中央研究院去作访问。在这一年内,我又回到了卑南族去进行调查。到了1973年,香港中文大学要成立人类学系,他们邀请我,说是希望我过去,我就答应了。我从来没去过香港。原来的计划是只呆两年,但是第一年1974年碰到了石油危机,这是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所以成立一个新的系是不可能的,于是成立新系的计划就搁了下来,我们只能在社会学系里成立了一个人类学组。社会学系里本来已经有一个组了,是心理学组。我原来还是希望两年后就回到印第安大学,所以就向大学请了假。到了两年以后,1975年我应该回去了。可是我太太和我小孩他们喜欢香港,而且我太太在香港有很好的事情,他们两个人不肯回去。这样我们在香港又呆了一年,到了1976年是一定要回去了,印第安大学把我的课也排好了,但是他们两个到了最后关头还是怎么也不肯回去。印第安大学一到7月份课程都已经排好了,我都不好意思向印第安大学辞职,我只好请我们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他认识印第安大学的校长,直接写了一封信给校长,说中大确实需要这个人留下来,你们那里人才多,希望你们再找人,他写了一封信替我辞职。辞掉以后,从此就在香港呆下来了,这可以说是我的第二个阶段。
1976年,我们决定在香港呆下来,夏天就回到美国,把家搬了过来。所以实际上,1966年到1976年,我是在印第安大学。1976年以后,我就在香港中文大学正式住下来。到了1980年,香港中文大学就正式成立了人类学系。
香港是一个相当商业化的社会,而且对整个中国社会来讲,人类学都是一个冷门,大学不大愿意投资,所以要让社会认识它,让社会认识以后,你才能走下去。所以我在1978年的时候,就和一些当地的学者,主要是西方的人类学家,办了一个香港人类学会。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对我们人类学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香港电视台最大的一个无线电视,他们有一个连续剧,好像是叫《香港82》,它是每年有一集,每一集是一小时,讲一个故事,《香港82》就是1982年的香港出现一些什么。有一集里头,讲一家发生的事情,那一家的一个男孩,他考上了大学。他的哥哥是一个比较实际、势利的人,他哥哥问他你考了哪个大学,他说我考了香港中文大学,哪个系呀,考上人类学系,哥哥便说:“你怎么去考什么人类学系,那是专门研究猴子的系!”他弟弟的话更让人生气,他说你看我这个成绩能进到别的系吗?所以我们学生就向他们抗议。香港无线电视台向我们道歉。但是这件事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所以就请我们人类学系的老师去上节目向他们解释什么是人类学系。可见当时人类学系还是很冷门的一个系,直到现在人类学系在香港也不是一个热门的系。不过成立这个系可以说,就整个中国来讲,除了台大的考古人类学系以外,我们还是第一家。我们是1980年成立的,中山大学是1981年,厦门大学是1982年成立人类学系的。
人类学系成立后,我们必须找地方给学生实习,那时我还是坚持这个观念,要找一个异文化。香港周围最近的就是瑶族,所以我们就选定了瑶族,就是连南的排瑶。我自己也就开始做瑶族的研究。在1986年召开了第一次国际人类学的瑶族研究会,也成立了国际瑶族协会。那个会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国际会议。我们得到广东的支持,同时国家民委也给了一些支持。当时费孝通先生也来参加了,但他只参加在广州举行的会。我们的会从香港开到广州,然后从广州,我记得当时是有六部车,浩浩荡荡,警车开路,一直开到连南去,所以这个声势是很大的,一下子把瑶族研究给炒热起来了。从那时起,我们每隔一年举行一次国际瑶族会议,中间还做一个小型的讨论会,开始那一段就弄得很热闹了。到了1990年,那是第三届,我们在法国图鲁兹开会。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感觉到,我必须做一个决定,因为我发现瑶族的研究,过去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有很多文献,如果我要继续做下去,我必须放弃其他东西,集中专门研究瑶族,当然要学习瑶语了。但是这时我就开始想,我过去都是在研究所谓异文化,到晚年了,我觉得应该开始研究一下自己的文化。所以到差不多90年代初期,这可以说是第二个阶段,就是对中国的少数民族,主要是瑶族的研究,我还去过一次西藏,对藏族做了一些研究,中国西南部的少数民族地区都去过不少。在90年代初期,我就开始逐渐结束了对异文化的研究,退出了瑶族学会,开始把我的精力放回汉人社区,到了晚年,我自己想研究一下我自己的社会。
正好这时候,山西一位老先生,就是原来山西社会科学院的院长刘贯文先生,经过香港,来看我,他跟我提到关于山西的乐户。我对这个很感兴趣,所以在1993年我特地跟他去了一次,到了山西晋东地区看了一下,确实是很有意思,从1994年开始便研究山西的乐户。我还邀请了另一位李天生先生,我们三个人一起做。到1997年三年弄完,这个书已经出来了,这本书好像是2001年出来,江西人民出版社的那本2003年才出来。这两本书出来了以后,我就开始对乐户所代表的那个社会作进一步的研究。我觉得,那个社会与我们所接触到的一般的社会不一样。我把他们叫做底边阶级,因为他们是最底层的,也是边缘的。他们自认为是下九流,上九流最低的一层就是农民,农民是上九流最低的,下九流中最底的是“七优、八娼、九吹手”,吹鼓手是下九流中最低的。我做完乐户以后,就想做整个底边阶级和底边社会的。我觉得他们的一些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社会的组织都是与主流社会不一样的,唯一具体能够表现它的是《水浒传》里的描写,他们特别讲究义气。所以我说我是研究底边阶级和底边社会。
我第二个计划,是从1999年开始做的,已经做完了。它包括以下几种:首先是山西的乐户,但是跟乐户共存的另一种社会阶级,比乐户地位高一点,叫做红衣行,他们不是贱民,山西也有。另外就是剃头匠,在山西的长子县那个地方专门出剃头匠。然后还有就是河北吴桥的杂技,北京天桥的说唱艺人,这些都做了。没有到南方,因为钱不够。台湾的国科会给钱太少,而且限制在大陆,每年只能有十五万新台币。蒋经国基金会那一次钱是三百万新台币,那时候台币很值钱,就等于是一百万人民币。这次钱只有六十万新台币,那怎么够呢?不够。现在做是做完了,报告也交了,但是我觉得离出版还有一段距离。现在正在想办法,怎么样把这个研究再做一做,而且我觉得这个研究还是很有意义的,它还没有人弄过。虽然说现在有些人在研究边缘社会,但我这个绝对不是边缘社会,我想就叫底边阶级、底边社会。有一些文章出来,总的田野报告交给国科会了。田野报告还没到能够出版的程度,所以我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我这个计划对国科会是交代完了,但是我自己是想找一点时间把它写出来。这学期我在东华大学新开了一门课,这门课也是关于中国的,叫做《中国社会的深度分析》,我就想把我这几年来对中国社会所做的一些研究总结一下,这里头最近的研究就是底边阶级的研究。
我到香港以后,除了做少数民族研究以外,也做汉族的研究。当时我到香港的时候,正好碰到“文化大革命”。1973年,林彪已经死了。林彪死了以后,中国大陆出了很多批林批孔的文章,就是揭露林彪的黑材料,黑材料就是讲林彪怎么用阴谋诡计。我就发现这个,确实是一批很有意思的材料。接下来的,批林批孔完了以后,“四人帮”垮了。“四人帮”垮了以后,又批“四人帮”,又有黑材料。这些资料我收集了很多。这里我做了一些研究,第一个研究是关于样板戏,只有一篇文章写了出来,书没有写出来。接着就是“中国人的计策行为”,比如三十六计,这个原本想写一本书,也没有写完,但是最后文章写了不少,有十几篇,都发表了,有一大半是英文,那时候还是写英文比较多。还有一个我也做过有关中国人的关系的研究,我最早的一篇文章是1980年在台湾发表的。这个问题,那时候还没有人注意,还有很多人说这没有什么好研究的,但是现在已经成了热门了。从1975年开始,先研究样板戏,接着是计策行为,断断续续地一直研究了十几年,是没有做过实地的调查,但是那时候访问过不少从大陆去到香港的干部,所以,可以说是有一些田野资料。
我现在教这一门课,就是叫做《中国社会的深度分析》,我希望将来写本书把它总结一下。我想这里比较强调的几点,第一点是需要有一个理论,第二个就是要根据田野的资料,不像过去主要是文献的资料。第三点就是本土性的,有很多观念是从我们自己对中国人的理解得出来的,不是说模仿抄袭外国人的。所以我希望能够综合我这几年来对计策行为啦、关系啦,然后从1994年开始的对汉族的一些田野调查,乐户啦、底边阶级啦,用这些调查的一些资料,希望能够写一本书,就用我现在开的这个课的名字——《中国社会的深度分析》。
所以总的来说,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个是从1955年开始,一直到1961年,这是第一个阶段,主要做高山族的研究;1961年去了美国,最先是念书,后来是做印第安人的研究,然后1973年到了香港以后,就是在研究香港的民间风俗、中国的少数民族,这是第二阶段;差不多从90年代开始,我回归到汉族社会。三个阶段大概就是这样。
徐:您从事人类学的研究将近五十年了,当然如果从1954年算起,2004年就是50年,如果从1955年算起,2005年就是50年,到时候我们要给您开一个讨论会了。但是现在,乔先生您也感觉到,人类学在中国的新的崛起这个大的背景下,我觉得现在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都在和人类学互动,发生跨学科的这种形式的交流。在这里,有很多人都对人类学开始感兴趣,本来没学过人类学的现在对人类学感兴趣了,其他学科的人都在学人类学,人类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应该相当于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您在对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当中有些什么好的体验和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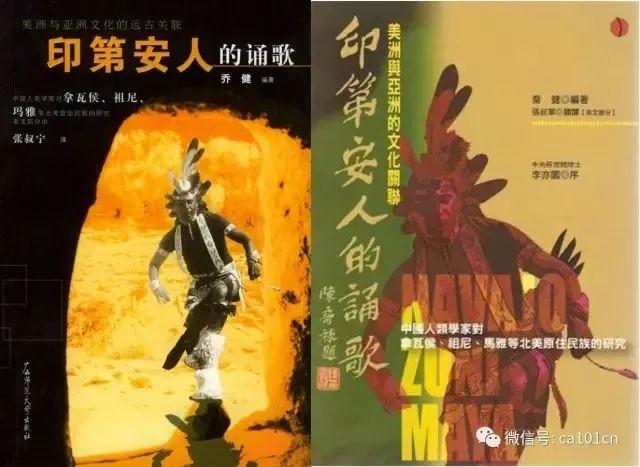
乔健:《印第安人的诵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5.
乔:你讲到了这个互动的问题。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sord Geertz),在他的《Local knowledge》,即《地方知识》,那本书里就有一篇文章叫《文类的混淆》,他就提到了学科相互之间的新界线,已经没有以前那么清楚了,以前人类学就是人类学,社会学就是社会学,文学就是文学,哲学就是哲学,现在这个界线没有了,这是整个学术界的新的现象。第二点就是在过去,人类学主要模仿的对象是自然科学,像早期的人类学所举的例子都是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来的,人类学受生物学的影响也特别深。但是新的一种情况,是在接近人文学科,如文学、哲学这些东西,所以说人类学本身就在变,它受到外界一些学科的影响,当然外界的学科也受到人类学的影响,比如早期跟人类学最接近的,第一是社会学,然后是心理学。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文学、历史学这些人文科学它们受人类学的影响很多,人类学受它们的影响也很多。比如说现在文化的研究本来是人类学的东西,但是在文学方面也兴起了一个新的学科就是文化研究,透过这个文化研究,人类学就在文学、哲学方面对它们造成一定的影响。同时,因为人类学研究的是关于人类最基本的一些问题,所有人类社会上的一些基本的观念,比如说什么叫婚姻,什么叫家庭,什么叫氏族,都是人类社会的一些基本构成单位,这些都是由人类学来界定,所以人类学本来是整个社会科学,现在包括人文科学中的一些基本观念的最早也是最清楚的界定者,所以说人类学是社会科学、人文学科里头最基础的一个学科,就像你说的,它等于是自然科学里的数学。
徐:现在大家对人类学感兴趣,在学习人类学。在学习人类学理论的问题上,乔先生您有什么好的体会、好的建议,我们现在在学习人类学的人要注意什么问题?
乔: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中国学者把理论的观念好像看得太神秘了一点,好像是万能钥匙。但是理论只是对一些事实的解释,所以我想,我们在学习人类学的时候,最重要的还是把事实弄清楚,就是要做田野。现在建设中国人类学最要紧的还是一个彻底的、长期的、详细的田野工作,这是最要紧的。没有田野工作,没有充分的田野工作,理论是没有用的,而且理论必须受到田野资料的检验。理论到现在为止基本上还是西方的东西,理论本身一定是受到它所发生的社会的文化的影响,所以它不是凭空造出来的,它有很深的文化背景,现在所谓的理论都有很深的西方文化背景。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了解这些西方的理论,但是另一方面最要紧的是怎么样用中国的实际资料、田野资料来检验这些理论是不是对的。人类学经过一百多年的进展,是一个基础科学,就像很多其他的科学,它的进展是累积型的。现在有很多人,喜欢搞什么后现代,后现代的东西一定是建立在现代上,现代的一定是建立在古典上,你对古典的、现代的不懂,而你要讨论什么后现代,那完全是空中楼阁,而且会误己误人,因为你完全没有基础。所以我们现在,要搞人类学的理论,必须从头搞起,就是从古典到现代到后现代的理论全部吃透,因为它们是一脉相承的,你不懂前面的,就完全没有办法了解后面的东西。所以我说,要弄理论一定要从头做起,同时必须要与中国的现实,说得具体点就是要和田野资料结合在一起,这些理论才能够发生作用,千万不要搞空的理论,这是很重要的。
徐:乔先生,您先后创建过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又创建过东华大学的族群文化与族群关系研究所,后来又创建了台湾第一所原住民民族学院,在学科建设上,您一定有很多很好的体验吧?我觉得现在大陆的人类学学科建设正处在重要的发展时期。您刚才讲了,中山大学一个人类学系,厦门大学一个人类学系,但是现在厦门大学的人类学系又取消了,变成只有一个研究所,现在云南大学有一个人类学系,据我现在了解来讲,中央民族大学也在积极的想筹办一个人类学系,清华大学他们现在还没有成立,但是人类学已经作为一个重要的学科在那里了。据我了解,南京大学和上海大学都有这种想法,有的甚至已经在物色人类学者,就好像70年代香港中文大学到美国找您来创办人类学系一样,有些大学正在物色人类学的博士。还有中国社科院的民族研究所,已改名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总之我觉得已经开始进入这个重要时期。那么您创建过一个人类学系,创建过研究所,又创建过一个民族学院,对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有经验,您能不能谈一下对我们大陆现在的人类学学科建设有什么评论,有什么好的建议?
乔:我想我们自己还是认为自己属于第三世界的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事实上,尤其是最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快。我希望它很快能够结束发展中国家这个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对这个学科的建设最要紧的就是不要过急,因为当初我在香港创办人类学系的时候,每个人都问学生的出路怎么办,都要问这个。我说我当初作为整个学年唯一的一个学生,也没有人质问我的出路怎么办。因为人类学系是一个基本学科,一个基本学科是每一个大学,像样的大学都必须有的,就像你刚才说的,没有一个学校能没有数学系的,数学本身是基础学科,它不可能一出来马上就能找到工作,但是它是别的学科的基础,在任何一个有规模的大学、综合性的大学,都应该有。所以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是要纠正这种政府、社会对一种新的学科的态度,就是说不要用一种功利的眼光来看待一个基础学科,它不像工商管理这些学科,它不是一个实用的,立刻就可以用的学科,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因为人类学包括非常广,就像我刚才讲的,它包括四个或者是五个分支,现在就说四个,五个的话就再加一个应用人类学,它包括很广,往往不是一个大学,尤其是在创办一个新的人类学系的时候可以全部照顾的。因为中国太大了,在一个地区最好是能够由几个学校分工合作。比如说在广西这个地方,广西的几个大学像广西民族学院,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大学,大家来看看,哪一个负责哪个部分?而且理想的是能够让学生互相跨校选课。同时有一些课程,比如我在台湾,我就有一种很深刻的感觉,人类学的研究必须和田野调查结合。我们说田野调查是人类学者的成年礼,你没有经过一个长期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你就没有成年,你就不是一个人类学家。但是这个东西需要时间,需要一种训练。我在台湾常常感觉到这种情况。我在台湾就提倡,应该大家合起来办,要做田野调查的研究。我想在中国大陆也是一样,比如说北京,人类学发展最多的是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也在发展,我知道中央民族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合作比较多一点,但是我想清华大学、人民大学也想发展。那么,比如像北师大,北师大由于有钟敬文先生的基础,民俗学比较强,所以他们正好和北京大学、中央民大可以互补,民俗学也是人类学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应该提倡跨校和校际合作,跨校学科合作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人类学内容太广泛,不太可能由一个学校来完成全面性的学习,所以它比别的学科更需要一个校际间的合作。
此外,就是我觉得定期的人类学家的聚会是必要的。但是这一点,不知道为什么在中国很难实行。国外的人类学会,比如说美国人类学会,他们每次开会至少有四千人,是很庞大的。但是我们的会就不行,比如说在大陆的中国民族学会开会人数就比较少,台湾也有中国民族学会,我也当过他们的会长,都是只有几十个人来,就是说这种互相交流的机会还是很少。不晓得什么道理,中国人习惯各自为政,交流合作的机会不多。应该一方面由政府,一方面由民间共同想办法,去提倡大家多一点交流。现在我们争取到了2008年在中国召开世界人类学大会,在这之前我想应该多举行一些这种定期的聚会。能够有些定期的人类学家的聚会,中国人类学才能够有发展,就像美国人类学会那样,有很多外国学者参加。我们的学科也希望将来能够这样做,因为现在华语也是世界语里的一种。我希望我们中国人类学会能够也像美国人类学会那样,有权威性的刊物,有很多人参加,至少每个大学都会有一些人参加,包括学生在里面。你去年组织的人类学高级论坛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徐:谢谢乔先生的鼓励。我只是想推动中国人类学者之间的交流,没想到受到大家的认同和欢迎。乔先生,我们学报发表了您的那篇著名的《中国人类学的困境和前景》之后,对大陆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发展起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中国人类学本土化始终是您关注的一个问题,在香港您推动了瑶学的研究,后来您到了台湾又推动了汉人社会的研究,这些我觉得是我们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的两个范例。比如瑶学的研究,那真是使它成为国际上学术重视的一个热点。您对底边社会的一个研究也是一个很好的范例,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我想趁这个机会请您给我们谈一下您对人类学本土化的体会,最重要的是想请您谈一下您在这个本土化研究中有什么概括?有些什么提升?有些什么升华?因为您在那篇文章中讲得非常的好,特别是对前景。我觉得印象很深的一句话,您说:“通过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的洗礼,使得国际人类学得到升华。”
乔:我觉得这里面,就像我刚才强调的,要做到本土化,必须要从事田野工作,没有田野工作我们谈不到本土化。我们人类学跟别的社会科学不一样,它是建立在田野工作上的。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进化论派在20世纪30年代一度被批判得很厉害,尤其是博厄斯他们这一代,他并没有说它完全不对,博厄斯是最注重田野调查的,他完全是用田野资料来驳倒它的。那么事实上,早期的进化论,经过由博厄斯他们所提出的理论检验以后,到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进化论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它已经受到了田野的洗礼。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今天要建立真正的本土化的话,就是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理论,就必须做很彻底的工作,也就是做很彻底的田野调查。可惜这一点我们现在做得不够。做得不够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好像比较忙,不但是中国人类学家,就是在世界上来讲,现在像马林诺夫斯基那样做长期的田野工作的都比较少,主要是大家都比较忙,而且有很多是世俗的要求,要求你早点拿出作品,要升职等等,所以大家都没有时间。但是这种工作必须坚持做下去,才能谈得上我们说的真正的本土化。所以我在那篇文章中就讲到,第一点,整个中国来说是一个人类学宝藏,少数民族文化少有人研究,中国民间文化少有人研究,我最近研究的乐户也没有人彻底研究过,确实我觉得是一个宝藏。我记得我在做这个乐户的研究之前,我在北大做过一次演讲,好像叫《漫游归来近乡情怀》。我讲完了以后,就有一位同事,好像是张海洋,他说山西的民间文化就像山西的煤矿一样深,我觉得他说得确实对。
我做了一个初步的研究之后,我觉得我们对中国民间文化的研究还是不多,它是那么丰富,又那么深厚。因为它深厚,所以在研究中国文化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特别理解到时间或者是历史的因素。我有一篇文章讲到乐户的社会地位,它的社会地位你就没有办法用现代的理论去解释,因为现在所说的社会地位主要是根据个人的经济收入啦、教育背景啦等等。乐户收入实际上比一般农民高,它的教育不见得比较差,但是为什么他的社会地位会那么低,而且受到很多的歧视?这个原因你必须要从历史里头去找,历史是原因,所以当时我就引了费先生的话。他是马林诺斯基的学生,是功能学派的一个主要传人,他对功能学派,特别是对涂尔干系统的一个批评,就是说他们把这个社会组织看成平面,他认为还应该把它直立起来,也就是说要了解它的历史深度。乐户正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引了费先生的话,就是说必须从历史里去找,因为早期的乐户一种角色是巫觋,所以他现在还扮演一些巫的角色,比如说抓凶。乐户虽然社会地位很低,但是他可以给有钱人的儿子当干爹,以及许多很神秘的角色。因为他过去是罪犯,至少从南北朝开始,强盗等首罪犯处死,如果牵涉到有强暴杀人的话,首从都被斩首,他们的家属则变为乐户,凡是乐户都是一个犯罪的人。到了明朝以后,政治犯的家属变成乐户,所以它是一种刑罚。整个历史的原因就造成了乐户角色的多重性,所以乐户社会地位的复杂化只能从历史上找。研究中国社会,如果完全用功能学派的观点来看的话,解释不了,因为功能学派过分地忽略历史的因素,研究中国社会,历史或者时间的向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向度。同时我研究乐户时真正地感觉到,中国文化或者我们广义地说华夏文明,是唯一的一个世界文明,能够持续几千年,至少从新石器时代,从仰韶开始,一直到现在没有断掉。你到华北地区去看,就是从仰韶一直下来,从尧、舜、禹下来,这三代之前的传说人物,好像都还活着,那个地方的人,拜伏羲,拜女娲,拜后羿,这些神都还活在那个地方。我常开玩笑说,你到黄河中下游去看,最年轻的神是关公,他之前的神都还是远古传说中的。你去看一下希腊、埃及的神老早就死掉了,都在博物馆里头,没有人再崇拜他了。希腊神话里那么多神都已经死掉了。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真的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的话,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悠久的传统的延续,这个存在对整个人类有怎样的一种作用,为什么中国传统能够这样存在下去?为什么其他的传统不能延续下去?比如说张光直先生在过世前的一些研究里,他比较殷商文化和玛雅文化,他觉得很像,但为什么殷商文化可以一直延续下来?玛雅文化发达得很,但是到了差不多12世纪的时候就没有了。没有了并不是被哥伦布他们带来的西方文化消灭掉,哥伦布来之前就已经没有了,所以这不是外来的力量把它消灭掉的。比如希腊、罗马的文化不是被基督教文明消灭掉了,或者说不是被阿拉伯的文明消灭掉了,它本身在后者出现之前就已经没有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中国文化又可以传下去呢?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人类文化至少在这个地方延续了这么长的时间,至少四五千年了,那么这里面就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研究,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去做的。这些资料,以乐户为例,在文献上的资料是非常缺乏的,必须要自己详细地实地去找,只要深入现在还可以找到,再过几年就完全丢了。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必须做很彻底的田野工作,在做田野工作的过程中,很自然地就会发现历史的深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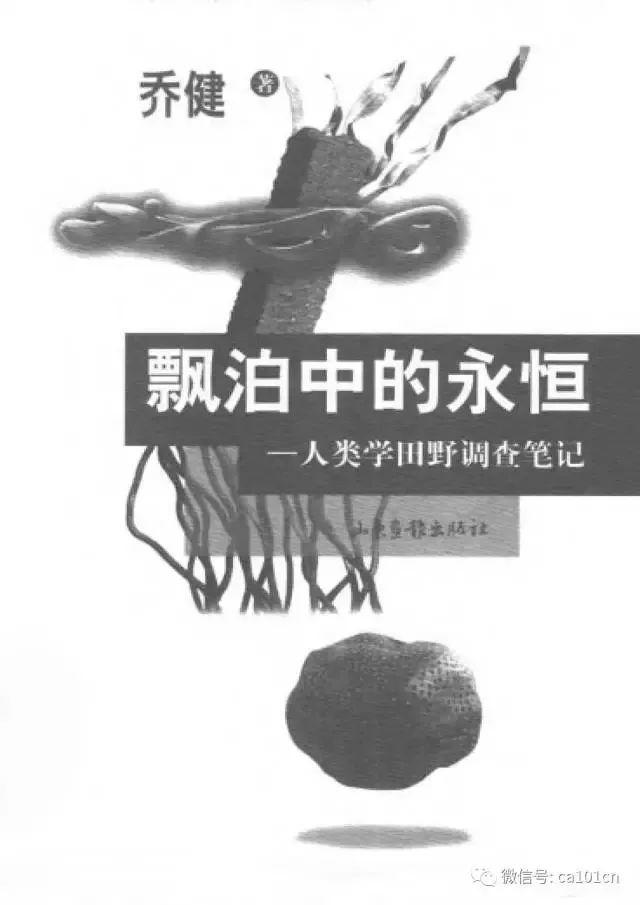
乔健:《飘泊中的永恒——人类学田野调查笔记》,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
徐:乔先生您写了一本书《漂泊中的永恒》,那么从您刚刚讲的,无论是学科建设也好,或是讲人类学的理论也好,都非常强调田野调查,做田野是人类学者的基本功,也是他的成年礼,所以我觉得,可不可以把您这个书名反过来称“永恒的漂泊”?
乔:“漂泊中的永恒”跟“永恒的漂泊”不是同一个意义,因为“漂泊中的永恒”我是指瑶族。我现在发现不但是人类,动物也是这样,它有一些永恒的东西,比如有鲑鱼,它在出生后不久就走了,当它生命结束的时候又回到出生的地方产卵,这是生物的一种常态,就像瑶人虽然他漂泊到别的地方,死后他还是要把自己的灵魂送回到原来的地方去。
徐:借用这样一个词,好比讲你做田野,现在因为有很多的人在学人类学,他们不习惯于去流动,到田野去会比较辛苦,要跋山涉水,到下面去,吃的住的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我们就是把田野象征为一种漂泊,但是你做人类学的就一定要坚持做下去。
乔:当然,人类学不可能要做永恒的漂泊,但是一定程度的漂泊是必须的。我始终都相信王国维讲的学问的三个境界,第一就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所以你必须多看,对人类学者来讲,要多看几个文化,回头才能更看清自己的文化。如果别的文化你都没去过,便不太容易客观,所以这第一个境界你必须要做到。这个漂泊的意思,我想在这里解释一下,就是比如你这辈子没有漂泊的命,你也不需要漂泊,但是为了人类学的训练,你应该暂时漂泊一下,当然永恒的漂泊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你看现在所谓的后现代大师萨依德,他的一本自传叫做《Out of Place》,中国人把它翻成《相关何处》。可以说漂泊就是后现代人的特征,这个对人类学家也很有用,因为漂泊到一个不同的地方去,往往会有新的认识。
徐:现代社会,人住的地方都是一个公寓式的房子,公寓式就是比较稳定,有些人就是不太想动了,很安逸了。但是你作为一个人类学者真的不能太安逸,不能太安份了,你必须不断地到田野去,别说异文化,你就是研究本文化,你也要迈出双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是漂泊的,而且作为一个人类学者可能一辈子都要这样。根据你年纪大小,当然你可以做多做少,但是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借用您这个“漂泊中的永恒”把它反过来,可以强调田野的重要性。
乔:像费孝通先生他到了晚年,都在走,他一辈子都在走,他后来虽然因为身体的关系,到了一个地方他不太能够东奔西跑到乡下去,但是他还是去听人们谈谈当地的情况。
徐:对,年年都下去。所以像您一样也是到处跑。
乔:对,我现在还能跑得动。
徐:是呀,所以他们说乔先生真是不辞辛苦,哪里有活动,哪里有事,就是转几趟车,您都下去,都得去看看。所以我觉得,做田野真是一个人类学者的成年礼,这也是人类学家的一个看家本领。
乔:确实是一个成年礼。不经过这个洗礼,真的不知道什么是人类学,只是关在家里头做一些文献的研究工作。过去的人类学者就不接受。但是现在开始,慢慢开始接受了,过去要求必须一到两年在一个地方做田野调查。这一个部分是要相当长的。
徐:乔先生,您1994年给我们的文章《中国人类学的困境和前景》是我们人类学界的骄傲,1994年底给我们,1995年第一期发表,使我们《广西民院学报》能够迅速的进入到了人类学的前沿。从此以后我们就能够在这方面一直得到您的关怀,召开的一些学术讨论会您都到会参加,大力支持。最近我们学报获得了第二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所以我想请乔先生谈一谈您对我们学报今后的发展还有什么好的建议?
乔:我觉得《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在最近十几年来,确实是在中国人类学界起了很大的作用,一方面是把比较重要的文章发表出来了,另外一方面是把一些人类学家团结在一起了。我希望这个作用能够继续发挥下去。最近你们的学报已经得到了政府权威的期刊奖,我很高兴,这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希望能够在这个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继续成为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的刊物。
徐:谢谢乔先生的鼓励,我想您有机会的话请您能光临我们学报指导。我一直在找机会,希望真的能有这个荣幸。同时,我也要祝贺您获得台湾教育界的最高奖励——讲座教授。可不可以谈谈这个奖励对您的意义?
乔:获得这一个奖对我而言是很大的鼓励,实质上也带给我很多协助。这个奖项让我有更充裕的经费与时间来从事与规划一些想做的研究。我可以说是一个很标准的人类学家,对异文化的研究始终是我的方向,但后来我认为也该回过头来研究自己的文化,于是就回到了我的家乡山西,经过当时山西社会科学学院的院长的告知,知道当地遗留了一个特殊的族群也就是乐户。因此在1994年与他及另一位山西学者一起到当地访查,找到一百五十几户的居民,发现了很多以前史书上从未记载的数据。
经过这个研究之后,我又兴起研究底边阶级与社会的念头,例如剃头匠、杂技、说唱艺人等,因此获得这个奖后,我计划锁定台湾几个行业群进行研究,其中一个就是高雄县内门乡的“总铺师”(专门办理外烩餐饮的行业)。这是我第一次研究台湾的民间社会,发现台湾民间真的保存了很多珍贵的文化。虽然比不上大陆的古老,但保存得很好,不像大陆地区遭受到“文革”的破坏。
另一个是阵头文化,我还有学生正在研究台北的公娼,这是中国最古老的一个行业,台湾一直到几年前才废掉,这个行业在中国已经维持了几千年,是真正的底层也是边缘的阶级。正好也可以利用这些经费来实现这些研究,因此我感到相当的高兴。
徐:为了庆祝您得到“讲座教授”的荣誉,同时也为了庆祝您荣退及七十岁生日,东华大学准备在明年三月召开一个研讨会,主题是“族群与社会”,我已收到邀请函,届时一定会出席。
乔:谢谢!这是东华大学族群关系与文化研究所现任所长吴天泰教授的一番好意。她和别的几位同事正在积极筹备。到时候能和多位老朋友团聚一次,也是一件美事。
文章来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1:62-69.
原文标题:《漂泊中的永恒与永恒的漂泊———人类学学者访谈之三十二 徐杰舜/问, 乔健/答》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