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记录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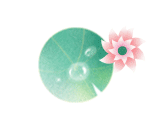
位于“世界屋脊”的西藏,因独特的地理位置、浓重的宗教色彩、多元的民族造就了深厚多样的文化传统,缔造了丰富多姿的民间文学。西藏民间文学体裁多样、内容丰富,映射着生活在这块壮美大地上各族人民的生活实践和审美体验,是西藏儿女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呈现,传递着人们的日常经验和艺术追求。由于民间文学口头性和变异性特征,在现代民俗学等社科类学科未成熟前,大量民间文学作品没有得到记录,资料的匮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西藏文化传统的深入研究,因此,搜集和整理成为研究西藏民间文学、民俗的关键问题。
西藏有深厚的民间文学讲述和记录传统。1949年后,尤其是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以来,在国家统一领导下,伴随几次全国性民间文学采集工作的进行,西藏丰富的民间文学资源得到挖掘,搜集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越以往,并且针对西藏民间文学建立起一套系统、科学的搜集整理方法。1949年来,大量藏文和汉文民间文学作品不断得到编辑、出版,留下了丰硕的文字记录成果,为西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累积了大量经验。但是,对于民间文学在政治话语中的定位,以及在学科体系中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搜集整理的方法论的建设和实践,不同时期的搜集整理理路、观念直接影响着民间文学文本的呈现。本文以已出版的西藏相关汉文民间文学文本为基础,梳理西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的历程,分析西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实践经验与方法论追求。
一、西藏民间文学记录传统的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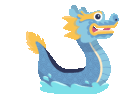

二、20世纪以来西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体系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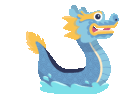
20世纪50年代,西藏民间文学正式开始“科学地、系统地、全面地搜集、采录、出版,并翻译成汉文和其他种文字加以传播”。1951年西藏实现和平解放,一批文艺工作者和爱好者进入西藏地区,他们中绝大部分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军入藏,随即就被西藏多彩的民间文学所吸引,开始了自觉搜集和整理的过程,如冀文正、李刚夫等。李刚夫在修建康藏公路的途中对藏族民间歌谣进行搜集,后于1958整理成《康藏人民的声音》并出版,他代表了这时期文艺工作者对民间文学自觉意识的兴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家制定并实施大量民族政策,开启民族识别与民族考察工作,之后中共中央于1956年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关于西藏的调查在首批8个调查小组计划之中。1958年,时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提出书写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建议并得到中央的肯定,搜集整理少数民族文学的工作在小范围开展起来,1961年编写工程正式启动,文学研究所制定相应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编选和出版计划,提出有计划地在全国搜集和整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是编写文学史和研究文学的中心问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民间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化调查工作在文学领域出现交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与整理围绕国家话语与意识形态迅速开展”,中央政府、学术机构、各类高校纷纷组织社会历史调查组、民间文学调查组,带动一批训练有素的学者进入西藏,如佟锦华、耿予方、王尧、陈践践、祁连休、段宝林等,开启了西藏通过田野调查进行民间文学采集的时代。他们从民众口头采集到大量民间故事、传说、谚语和歌谣,为西藏各族民间文学累积了大量资料,并整理出版了一批民间文学资料本和选编本,如中央民族学院藏族民间故事编译小组的《藏族民间故事》(1959)、肖崇素编著的《奴隶与龙女》(1957)、田海燕编著的《金玉凤凰》(1957)、王尧编译的《说不完的故事》(1962)等,西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迎来第一个高潮。这时期的搜集整理在政治话语的指导下展开,调动了学者的广泛参与,多种视域下进行的采集工作勾连起全区民间文学脉络,成为西藏后来自上而下搜集整理体系的基础。
三、西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范式的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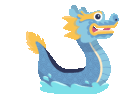
四、西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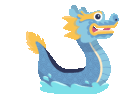
西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展现出多层次、多元化特色,同时受到国家意识形态和文化建设的影响,体现了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科学理念的进步。然而,在搜集整理实践中,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完善和深入。
西藏境内的藏族、门巴族、珞巴族、汉族、回族、夏尔巴人、僜人等共同缔造了西藏灿烂的民间文学,但是西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较少关注藏族以外的其他民族。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组织编辑出版了《西藏歌谣》,其中只收录了藏族民间歌谣。西藏自治区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出现其他民族的民间故事、民间歌谣和民间谚语的比例较低,这与西藏多民族丰富的民间文学流传的现实不相符。在搜集整理方面,尽管冀文正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搜集和整理门巴族、珞巴族民间文学,但是,直到1979年,为编写门巴族、珞巴族文学史,西藏民族学院组织民间文学调查组才对门巴族和珞巴族进行第一次科学、系统的调查搜集,这就是后来的《门巴族珞巴族民间文学概况》,这一工作比起藏族晚了将近二十年。至于夏尔巴人、僜人的民间文学资料被搜集整理的就更少了。这种状况对于全面、系统地呈现、认识和理解西藏民间文学是极为不利的。
民间文学因其口头性,与其他民间知识具有互文性关系,因此在搜集民间文学过程中,理应对与之相关的民间知识进行采集,比如与民间文学有关的音乐、舞蹈、戏剧以及图像等都应搜集和整理。然而,20世纪50年代,西藏民间歌谣搜集只注重搜集歌词,而忽略音韵、节奏、曲调等相关知识。随着西藏民间歌谣搜集整理逐步成熟,人们提出记录民间歌谣的相关标准,但是依然缺乏对于民间歌谣演唱场景的记录。到了《中国歌谣集成·西藏卷》中,不仅记录了民间歌谣的歌词,而且出现以乐谱形式对部分民歌韵律的记录,这才出现了民间歌谣较为科学的记录。然而,笔者以为,许多民间歌谣是在仪式之中演唱,伴随舞蹈进行,有特定讲述情境,这些内容的缺失对于民间文学的研究和理解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对于西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应该将其相关的民间知识采集起来,以此实现在民间知识谱系之中进行互文性的科学阐释。
由于语言、文字差异,翻译是西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过程中的难题,翻译的精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影响民间文学价值。西藏民间文学调查常常采取现场口译的形式,从口头经过翻译再到书面,是对藏族民间文学的藏语讲述、演唱的双重“翻译”,口译者的藏语、汉语水平影响研究者的判断。不少民间文学资料本都提到翻译带来的困难,“在翻译整理中,我们力求保持原文的思想性和艺术美,但由于藏、汉两种语言的差异,不少本来很精炼优美的句子,译出后大减其色”从事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工作,使我们最感困难的,是语言的隔阂,这也是我们几年来没能解决的问题。当口述者眉飞色舞谈笑风生的时候,我们只能瞠目相对。虽然我们的翻译岗青同志经验丰富,并且随时在小本子上作笔记,但是经过他的翻译,也只能保证故事情节的正确和完整,并不能把口述者的生动的语言,完美无缺地传达出来。我们所记录的材料也只能是翻译者的语气,而不是口述者的语气了。”在规范化搜集整理体系后,现在西藏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基本都采取藏文记录再翻译的方式,三套集成就“先用藏文直接记录和整理,然后进行分类,编选出《藏文卷》,最后再通过严格地复查、鉴别和筛选的基础上译成汉文”,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翻译带来的困扰。但是,藏文、汉文资料数量不对等影响了目前西藏民间文学相关研究,西藏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搜集到的大部分资料没有翻译成汉文。因此,西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需要对翻译问题更加重视,以推进和提升西藏民间文学资料的科学性、整体性研究。


个人简介
林继富,汉族,湖北麻城人,1986年至1994年在西藏农牧学院工作八年。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学科负责人,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亚细亚民间叙事文学学会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西藏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个人简介
杨之海,纳西族,云南丽江人,中央民族大学民俗学专业2018级博土研究生。

本文来源:《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图文来源:微信公众号“民族文学学会”2020-06-16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