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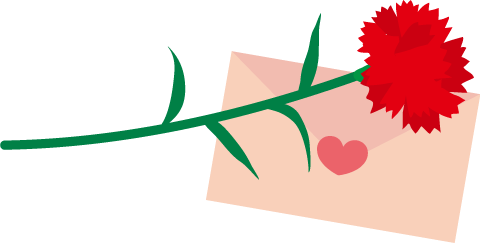
摘 要:以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代表,民俗传统上世纪后半叶在全球范围内经历了文化遗产化的历程。在探索民俗保护到公约形成的历史过程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有关“文化遗产”的几个文件,在相关概念的界定和阐释中表现出对民俗传统时间界定上的微妙变化:民俗从具绵延性的历史产生的文化产品变成了与历史以某种方式关联的当下实践。文章通过辨析这些文件形成的社会历史和政治文化背景,探求其演变背后的知识生产及知识/话语相关的权力过程,并指出这一演变与现代化到后现代的历史进程中,时间、空间和时空关系变化的深刻关联。
关键词:时间;空间;当下性;民俗传统;遗产化
作者简介:彭牧,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认同、身份政治与美国民俗学知识生产研究”(项目编号:17BZW172)阶段性成果
一 遗产界定:历史悠久与当下实践
2003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32届大会上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2003《公约》”)。至2017年9月5日,加入的国家已达175个。2017年12月9日在韩国济州岛闭幕的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十二届常会,共有117个国家的470个项目列入了“2003《公约》”的三类名录/名册,其中我国共有38个项目列入。作为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我国入选的项目皆有悠久的历史。对我们来说,能称得上遗产的,时间是否悠久显然很关键,这正如《现代汉语词典》对“遗产”的定义:“泛指人类历史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或物质财富。”但是在“2003《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界定中,时间是否悠久其实并未做要求。“2003《公约》”第2条给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定义:
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在这里,非遗的时间性仅仅通过“世代相传”来限定,整句的重点其实在“不断地再创造”,也即其当下的功能和意义而言。如果说在“2003《公约》”的文本中,这种弱化历史而强化当下的时间观还只是一句话的凝练表述,那么在公约2006年生效之后的评审中,它就得到了明确的阐释和实践。

事实上,至少从2009年的第四届常会的评审报告开始,在如何理解非遗的定义这一关键问题,也即对公约第2条的阐释和评审上,项目在当下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与项目的历史维度的关系、比重就是一个屡次论及的问题。评审机构多次对各缔约国明确指出,在申请表的填写中,对项目的历史信息无需过多赘言,需要重点阐述的是非遗项目的当下功能和意义。如在2012年和2013年咨询机构提出的评审中出现的横向问题(transversal issues)和2014年的申报表填写备忘中,淡化历史和突出现状都是反复强调的问题。九届(2014)和十届(2015)常会的评审报告均提及缔约国对于“项目的描述不应该着重于历史性的方面,而应该着重于其当下对于相关社区的社会功能与实际意义。”十届的评审报告还明确阐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当代实践和历史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毕竟总是一种活的实践……虽然可以围绕社区与其历史的互动而展开。”
显然,“2003《公约》”界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向一种当下的实践,虽然它有历史的维度,但这种历史维度在时间的跨度上可以是非常短暂的。如2015年列入的代表作项目“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传统绘画技巧Filete porteno”,是20世纪初意大利移民面对新的社会文化环境,在城市空间中形成的民俗实践。而2016年列入的孟加拉国“庆祝Pahela Baishakh(新年)的Mangal Shobhajatra节习俗”,作为传统新年庆祝的一部分,则是从1989年才开始的,也就是说只有不到30年的历史!以此而言;“2003《公约》”定义中虽然有“世代相传”的限定,但是其所指涉的时间其实并没有具体的纵深程度的要求。与其说这里是表述时间性,不如说是强调传承的方式。在这样的界定中,真正强调的是,这些遗产在当下的状况是处于“不断地再创造”之中。显而易见,非遗界定与考量的关键并非强调某个文化实践是否具有悠久的历史,并非其在时间上的绵延程度,而是其在当下存在的意义及其再创造的实践。
如果我们比较“2003《公约》”体现出的这种时间观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个有关文化遗产的公约,也即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1972《公约》”),以及“2003《公约》”通过之前与非遗有关的几个文件,即1989年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下简称《建议案》)、1998年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以下简称《代表作条例》),我们会看到,在文化遗产从物质文化扩展到非物质文化的三十多年的历程中,教科文组织在对“文化遗产”相关的几个概念的界定和阐释中,体现出时间性的微妙变化:遗产从具绵延性的历史产生的文化产品(product)变成了与历史以某种方式关联的当下实践(practice)。这样的转变何以可能?其历史和社会的原因何在?本文以“2003《公约》”形成过程中教科文组织的几个关键文件为对象,通过探讨文件形成的社会历史和政治文化背景,辨析民俗传统在遗产化过程中对其时间性界定的演变,探求其背后的知识生产及知识/话语相关的权力过程。
教科文组织的“1972《公约》”是这样界定文化遗产的:
在本公约中,以下各项为“文化遗产”
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成份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
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
遗址: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
而《建议案》这样界定民俗:
民俗(或传统的大众文化)是文化团体基于传统创造的全部,通过群体或个人表达出来,被认为是就文化和社会特性反映团体期望的方式;其标准和价值是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流传的。其中,其形式包括语言、文学作品、音乐、舞蹈、游戏、神话、仪式、习俗、手工艺品、建筑及其他艺术。
《代表作条例》把民俗换成了“口头和非物质遗产”,整体上沿用了《建议案》的界定:
根据上述《建议案》,“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一词的定义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其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除了这些例子以外,还将考虑传播与信息的传统形式。
在上述三个文件和“2003《公约》”的历时展开中,我们不仅看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形成的轨迹,也看到文化遗产概念与时间、历史关系的变化,看到民俗传统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实践而遗产化的历史过程。

二 现在与过去:遗产保护的时间性
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遗产概念及其实践体现出一种特殊的时间性,即其作为当下实践但在本质上又与过去时间相关联,这也是现代化过程中对过去和现代的时间划分的结果。正如美国民俗学家芭芭拉·科尔申布拉特-基布列特(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所言,“遗产是当下一种求助于过去的新的文化生产方式”。受约翰内斯·费边(Johannes Fabian)批判反思人类学学术史时提出的否认同时性(the denial of coevalness)启发,科尔申布拉特-基布列特把时间性看成文化遗产的关键特性,指出遗产实践中体现着时间上过去与现在的特殊关联,呈现出现代化构建出的当代时间中的多重并置:
遗产的超文化属性(metacultural nature of heritage)的核心就是时间。历史、遗产和惯习之钟的非同时性(asynchrony)和事物、人和事件不同的暂时性在当代性和同时代性之间产生了一种张力(a tension between the contemporary and the contemporaneous),正如上文所论,产生了一种逐渐消失和消失殆尽的混乱(a confusion of evanescence and disappearance),以及一种悖论,也即:拥有遗产作为现代性的标志。这正是全球遗产事业得以可能的条件。

众所周知,民俗学作为学科起源于现代化进程,起源于现在与过去在时间上看似连续实则是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构建。而遗产的概念及其相关实践亦产生于同样的历史过程,带有现代性的烙印。阿斯特丽德·斯温森(Astrid Swenson)用详实的史料展示、比较了遗产的概念及相关实践于十八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叶在法国、德国和英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形成与发展的历程。它表现为各民族国家身分形成时对民族文化起源的探求,也与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世俗化过程中宗教的位置相关,更体现为19世纪中叶开始的各种世界博览会与展览中的历史性展品的流行。在这样的过程中,遗产成为民族文化身分的体现,但其展示与保护实践又始终与资本主义在全球兴起阶段中各国之间的交流对话和国际竞争相关,显示出国际性的背景,这也成为战后国际联盟和联合国推动的国际性遗产保护的先声。
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文化遗产概念,与同时期形成的人类学和民俗学一样,对全球历史和文化持有单线进化的观点。欧洲文明被置于历史的顶点,其他文化的成就被从其各自的脉络中抽离出来,分门别类地列入线性的历史排序中。文化被条目化(itemized),被按照某种超越其具体语境的分类方式归类、排列,构成一种超文化的清单(list)。任何的排序都需要一个分类与编排的标准,在这里,时间,启蒙以后被普遍化和抽象化的时间,成为最基本的分类线索。费边指出,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时间是线性的,是神圣历史的媒介,而异教的时间是循环的。在现代化过程中,并不是发明一种新的线性的时间,而是把犹太-基督教的宗教时间世俗化,把这种时间泛化和普遍化。线性的普遍时间在文艺复兴时期已出现,到启蒙时代得以迅速发展,这也成为人类学的基础。民俗学也一样,这是学科起源时期历史起源研究占主流的根本原因。
以这种线性的时间观为基础的全球文化历史的排列在时间上具有两个颇有意味的特点。首先是民俗学和人类学研究中的遗留物的概念。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umett Tylor)的遗留物概念深受英国民俗学早期的古物概念(antiquity)的影响,而无论是表述为古物还是遗留物其基本的特点就是认为这些现象虽然当下存在,但是其意义和价值从本质而言并不属于当下,它们是“污损了的历史,或者是逃离了时间沉船的一些历史遗迹”,它们“只能处于毁坏的状态,它们象征着缺席、衰退与损失,构建并强调着过去与现在的鸿沟。”遗留物是过去生活留下的破碎残片,其价值在于构建过去的历史。它们作为现在和过去相关联的物化呈现,展示出一种特殊的时间性,也即它们是过去与现在时间的混合与中介。在民俗学学科上世纪中后期转向研究当代实践之前,可以说,民俗学整个的学术对象就是这种看似当下存在但本质属于过去传统的遗留物,所以民俗学才是一门面向过去的历史学科。第二个特点,就是费边所指出的在全球文化线性排序的体系中表现出的非同时性特质。费边认为,从人类学学科伊始,其话语实践就使学者和他们的学科对象——那些在田野中和他们身处同一时代的人———被界定为原始人、野蛮人这样的文化他者,因而处于不同的时间之中,后者的同时代性被学科话语从根本上否定了:“这是一种持续和系统化的倾向,即把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置于与当代的人类学话语生产者相异的时间中。”正是这种非同时性的本质,使民俗学和人类学在很长时间内对世界文化的分析排序本身成为一种不平等的权力话语体系的话语实践。
其实,这两个特点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费边的批判指出了:遗留物概念背后人为的非同时性及其体现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遗留物被赋予的特殊历史价值正源自其被话语构建出的非同时性和被遮蔽而模糊的当下性。
整体而言,从欧洲开始的文化遗产概念及其保护实践也处于同样的线性时间观为基础的知识话语体系中,体现着现在与过去交织的复杂的时间性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文化遗产的完整价值在于过去的历史之中,我们今天面对的存在是历史过程已然结束的结果,所能做的只是保持原样或者说尽量减缓时间流逝侵蚀的烙印。从对象的时间和当下的关系来看,“1972《公约》”至《建议案》无疑体现出这种非同时性和遗留物的观念。
三 本真性、历史产品与文化遗产的线性时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层面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始于20世纪60年代埃及与苏丹就努比亚遗址向联合国的求助。为使遗址免遭修建阿斯旺大坝导致的人工湖淹没,众多国家参与了保护行动,这一国际合作性保护得到了价值4千万美元的国际资源。原本被看作是各国国内事务的遗产及其保护,第一次被理解为超越国界的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得到国际社会和教科文组织的关注。作为这一行动的发展,“1972《公约》”所指向的显然是这种全人类的遗产:文化遗产开始在超越国界的层面上被审视。那么,这种审视的标准是什么?上文引述的“1972《公约》”对文化遗产的界定中,“突出的普遍价值”无疑是最核心的评判标准,而历史性就是这种充满模糊性与可能性的“突出的普遍价值”的第一个限定性维度。具体到文化遗产的评审原则上,就是体现出时间和历史烙印的本真性(authenticity)问题。
1994年版的《世界遗产公约行动指南》(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明确指出,要具备公约所说的“杰出的普遍价值”,从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财产(property),必须符合下面的一条或多条标准以及通过本真性的检测。而后面所列的几条标准皆或明确或隐含地体现着时间的标准,如“一段历史时期”、“已消失的文明或文化传统”、“人类历史的特别阶段”等等。而本真性则是“要满足在设计、材料、工艺或背景环境方面的本真性检验,如果是文化景观则是其独特个性和构成要素方面的本真性检验。而委员会强调重建只有在完整和细致的记录原貌并且没有任何程度的臆测的基础上才可以接受”。在本真性的判定上,这里显然继承了1964年《关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宪章(威尼斯宪章)》的精神,强调:
保护与修复古迹的目的旨在把它们既作为历史见证,又作为艺术品予以保护……古迹不能与其所见证的历史和其产生的环境分离。除非出于保护古迹之需要,或因国家或国际之极为重要利益而证明有其必要,否则不得全部或局部搬迁古迹……修复过程是一个高度专业性的工作,其目的旨在保存和展示古迹的美学与历史价值,并以尊重原始材料和确凿文献为依据。一旦出现臆测,必须立即予以停止。此外,即使如此,任何不可避免的添加都必须与该建筑的构成有所区别,并且必须要有现代标记。
可以看出,“1972《公约》”界定的文化遗产的本真性就在于其原初材料的物质性中凝结的久远的历史,也即线性的普遍时间中所绵延的程度。在全球文化创造物在统一的、以单一的线性时间观进行的重新分类、比较与排序中,物质文化遗产所谓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就在于它们具有的历史悠久性。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在今日时空中依然存在,更在于它见证着时间的流逝,是可见的历史本身,是过去在今天遗留的残片,其价值的大小可以用时间的跨度来精确测量因而也就可以把突出与非突出区别开来。
这样一种线性时间观自然青睐那些长于抵御时间侵蚀性的文化创造物。“1972《公约》”因此被非西方国家认为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纪念碑式遗产观的代言人,其实质是欧洲启蒙哲学理念的体现,是用欧洲中心的文化遗产观、时间观来评判全球多样的文化。如何评判包含着完全不同时间观的历史见证物?例如日本的建筑以木结构为主,但是体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时间观。虽然有法隆寺这样类似欧洲的尽量保护原材料的建筑,但也有一种通过不断重建来延续的传统,如始建于7世纪的伊势神宫。伊势神宫的本殿每20年就会依照传统重建,称为式年迁宫,迄今已有62次。这一方面是绵延上千年的传统,另一方面真实存在的建筑却只有最多20年的历史,是在不断创造中力图保持不变的传统,是一种循环的时间。

正是出于对这种欧洲中心主义文化遗产观的不满,1994年11月的奈良会议对“1972《公约》”的本真性进行了重新阐释,采用了更为宽泛的本真性的界定,不仅考虑纪念物的材料,而且考虑其设计、形式、用途、功能、技术等因素,特别是衍生出来的精神和感觉,并最终承认每种文化对价值和本真性的界定都不同,不能采用单一标准。本真性界定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样一种单一的线性时间观,承认了遗产不是过去历史过程的终点与结束,而仍然具有不断创造的可能,也正是本真性界定的这种变化,使包含着不同时间维度的非物质文化传统得以进入遗产化进程。
“1972《公约》”生效以后很快就遭到非西方国家的质疑,主要因为不符合欧洲观念的文化遗产无法得到承认与保护。1982年,教科文组织设立了民俗保护的专家委员会,同年夏天,在墨西哥举办的“世界文化政策会议”(World Conference on Cultural Policies)才正式扩展了文化遗产的定义,整合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包括它的艺术家、建筑家、音乐家、作家和科学家的成果,也包括匿名艺术家的成果、民族精神的表达以及赋予生活以意义的价值体系。它同时包括民族创造性得以表达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成果(both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works):语言、仪式、信仰、历史地点和纪念碑(historic places and monuments)、文学、艺术作品、档案馆与图书馆。
会议肯定了民俗(folklore)构建民族文化身分(cultural identity)的价值和意义。但正是因为把遗产看成历史过程的终点和成果,也就是一种业已完成的产品(product),教科文组织对民俗的保护是从知识产权的角度开始的。玻利维亚政府在1973年向教科文提出建议,希望从知识产权的角度保护民俗。其动因是20世纪70年代初南美安第斯山区的民歌《山鹰之歌》(El Condor Pasa)被美国流行歌手保罗·西蒙填词重唱,全球流行,取得了巨大的商业利润;而其专辑上并没有给出任何来源的标注。虽然从知识产权角度保护民俗的动机是抵抗民俗成果在商业化过程中遭受的国内外剥削,但是实践证明,从知识产权的角度来保护民俗传统并不可行。教科文文化遗产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处的专家萨曼塔·谢尔金(Samantha Sherkin)曾撰文,详细地追溯了教科文组织从1952年《世界版权公约》通过到1989年《建议案》形成之间探索立法保护民俗的漫长历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教科文联合召开了多次专家会探讨合作保护民俗的可能,但是其分歧在于,从知识产权法的角度采取措施,是保护个别的民俗成果,还是关注民俗实践整体的保护?换言之,知识产权的保护角度必然把民俗看成是已完成的具体产品,看成是过去历史的结果,那么如何看待民俗在现实中不断的创造?这种根本性分歧导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终在1985年从合作探讨中退出。
《建议案》的民俗保护是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框架之外由教科文组织独自展开的,标志着教科文组织在民俗保护过程里程碑式的进展,但是《建议案》依然体现出从知识产权角度与从文化角度进行保护的矛盾,知识产权思路的影响并未消除。虽然劳里·杭柯(Lori Honko)从1982年开始就参与教科文组织的专家委员会,并直接参与了《建议案》文本的撰写,但从上文引述的定义来看,《建议案》基本上还是把民俗界定为已完成的历史产品。民俗作为历史过程结果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差别只是在于,《建议案》力图从整体上保护已形成的民俗传统。
《建议案》虽然承认民俗传统在时间上兼具过去与现在的双重性:“强调民间创作作为文化遗产和现代文化之组成部分所具有的特殊性和重要意义”,但是其重点在于从国家层面从上到下地依赖专家对民俗进行整理和研究性保护。首先提出的保护措施是鉴别(identification),旨在完成“民间创作标准化分类法:即(i)编制民间创作分类总表,以指导全世界这方面的工作,(ii)编制民间创作细目汇编,(iii)对民间创作进行地区分类,特别是通过实地试办项目进行。”之后就是民俗在博物馆、档案馆等机构中的保存(conservation)。后面的三项措施保护(preservation)、传播(dissemination)与维护(protection)虽然涉及到了民俗传统的传承者及其当下传承与创造,但其具体列出的措施和支持的重点还是在民俗传统的研究者身上。换言之,《建议案》保护的重点是民俗专家的学术研究和资料搜集、整理,希望能从专家角度,在全球范围内完成一个民俗事项的学术研究性保护体系,其核心是借助教科文组织的国际平台,从超越具体国家的层面对全球民俗进行记录、整理、分类和排序,构建一种全球性的标准类型学体系(typology)。这也是当时制定《建议案》的指导思想之一。从某种程度而言,这和民俗学早期阶段努力完成的各种母题、类型索引并无二致,只不过此时的类型学体系的范围从口头文学扩大到了民俗生活整体。这里的民俗传统从本质上而言是已完成的民俗事项,是可以抽象为学术对象的民俗,而不是作为生活本身的民俗,其保护的对象并不是作为民俗传承主体的民众,而是事项本身。在这里,民俗依然被看成是历史性的业已完成的创造物,这种全球体系必然是一种线性时间观指导下的分类与排序。
虽然《建议案》的出台历经曲折,但是它并没有带来成功。实际上,它甚至是非常失败的。由于该文件采取“建议案”的形式,直接针对各成员国,但并未赋予教科文组织任何权力,所以也就无法采取什么行动。1999年,在《建议案》十周年之后的华盛顿评估会议上,时任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部主任的爱川纪子(Noriko Aikawa)坦承:《建议案》生效之后,教科文组织成员国反应很消极,对要求提交的行动进展汇报,只有区区6个国家回应。但是90年代初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发展,却使各国认识到其民族文化资源的重要现实意义:冷战结束之后,东欧各国在重塑民族身分,拉美国家正在重新思考融合多元的文化身分,而市场扩张造成的全球化又促进了各国对本土文化多样性的重视。在这样的国际社会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成员国向教科文提出民俗传统保护的需求。90年代初,教科文组织开始寻求从新的角度保护民俗传统的可能,关注民俗传统的当下传承与实践、关注传承主体和社区成为民俗保护的指导思想之一。“2003《公约》”即是这种努力的结果,它体现出和《建议案》的专家型、研究性保护完全不同的框架思路。
四 民俗传统的遗产化与当下性
从1982年墨西哥会议民俗传统被认可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到“2003《公约》”通过,民俗完成了其在国际层面上遗产化的历程。凭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身分,民俗传统多少摆脱了“folklore”概念的负面含义,成为当代生活中重要的文化资源。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会议对民俗主要功能的理解还在于其构建文化身分的价值,那么到2002年的里约会议,它就与对抗全球化的文化多样性联系了起来,具有了更多、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整个历史过程,只关注其中关键性的两个转折点。一个是1997年的摩洛哥会议,另一个是1999年的华盛顿会议。前者直接促成了《代表作条例》的出台,为“2003《公约》”的形成铺平了道路;而后者对《建议案》的民俗保护思路进行了彻底反思,实现了遗产保护的框架思路从作为历史产品的民俗到作为当下实践过程的民俗之转变,也完成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俗从历史到当下的转变。虽然这两次会议之后乃至代表作项目宣布之后都还有不少不同的声音,“2003《公约》”起草过程中的每一个会议也充满着这种产品与过程的激烈斗争,但最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当下的创造与过程占了上风。
1997年6月,教科文组织在摩洛哥马拉喀什(Marrakech)召开了名为“保护大众文化空间国际磋商会”(International Consultation on the Preservation of Popular Cultural Spaces)的小型会议。会议是在旅居马拉喀什的西班牙著名作家胡安·戈伊蒂索洛(Juan Goytisolo)的动议下召开的,其最初的直接目的在于使马拉喀什的吉马·埃尔弗纳广场(Jemaa el Fna Square)免遭当地城市改造计划的破坏。至少从17世纪开始,这个广场就是民间音乐家、故事家、占卜看相、杂耍等各色民间艺人汇聚、表演的空间。戈伊蒂索洛等人组织了保护协会,并利用他和当时的西班牙籍联合国教科文总干事费德里科·马约尔(Federico Mayor)的关系,进入了教科文组织的议程,最终使地方性的危机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人文地理学家托马斯·施密特(Thomas M.Schmitt)撰文详细回顾了摩洛哥会议如何使多少偶然的具体文化空间的保护成为全球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的转折点。
这中间一个具有连接性的概念就是此次会议的议题所在:“文化空间(cultural space)”。1992年,“1972《公约》”的文化遗产概念增加了新的一类: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希望能包括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文化空间”这一概念就基于与文化景观概念的直接关联。实际上,摩洛哥会议最初的目的,是以吉马·埃尔弗纳广场这个文化空间为代表,探讨在具体的物理空间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能性。也就是能否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放入类似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物理空间(site)中,从而具有更好的确定性与更强的可操作性。这次会议专家讨论的结论是,吉马·埃尔弗纳广场在全球是个特殊的个案,非物质文化遗产充满了流动性,很难被有限的具体空间所局限。因为会议由具体的空间危机急迫性所引发,会议最终依然颇有成效,乃至具有里程碑式成果:也就是建议使用人类口头遗产(oral heritage of humanity)的概念,拟照“1972《公约》”的名录(list)形式,建立一套简化的体系。此后经过1998年教科文组织第154次、第155次两次执行局会议讨论,将概念扩展修订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于1998年联合国大会最终确认通过《教科文组织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并启动计划,戈伊蒂索洛担任最初的评审委员会(jury)主席。

但正是由于摩洛哥会议的原初动机是保护具体文化空间的现实危机,在会议之后形成的《代表作条例》中,文化空间不仅成为着重界定的概念,也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初的两大遗产领域(domain)之一,不仅和另一大领域民间或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forms of popular or traditional cultural expression)并列,而且位列第一。但是把具体物理空间作为界定和分类非遗的标准并不具有很强的操作性,非遗保护中的这种空间性关注并没有维持很久。巴莫曲布嫫最近也注意到非遗名录中“文化空间”类遗产的减少。限于篇幅,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中的空间维度,将另文专述。
代表作计划从草拟到实施的过程中引发了激烈争议,特别是发达国家反对在“1972《公约》”之外,另外再通过一个新的非遗公约,而正是1999年的华盛顿会议使这种可能性变得较为清晰。1999年6月,教科文组织与美国史密森协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合作,召开了“全球评估1989年《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在地赋权与国际合作”(A Global Assessment of the 1989 Recommendation on the Safeguarding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Folklore:Local Empowerment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的会议,主旨就是对已通过十年的《建议案》在全球范围内的效果进行评估,探讨民俗保护的有效框架。这次评估的结论非常清楚明确:《建议案》所体现的概念和保护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中已经完全过时,需要创造一个全新的模式。大会的最后报告指出,《建议案》最大的问题是“过于僵化地局限于记录和档案机构中,反应出保护的目的是产品而不是传统文化和民俗的生产者。必须在两种需求中寻求某种平衡,一种是记录的需求,一种是保护创造、培育以后能被记录的产品的相关实践的需求。因此保护的重心必须转移到社区。”报告还指出大部分与会者认为《建议案》所使用的folklore一词带有负面意味而颇有问题,建议以后吸收当下民俗学界关于民俗定义的根本变化,不再把民俗看成具体单一的事项,而是理解为一种社会行为,是创造或重新创造的事件,是促成这种行为的知识和价值以及这种行为存在的社会交换模式,并进而关注行动的主体。
以华盛顿会议的结论而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欧美民俗学界学术转型带来的对民俗的全新阐释已体现在教科文组织的保护理念之中。以此次会议为标志,通过史密森学会的几位美国民俗学者的参与,已完成了从历史到当下转型的美国民俗学理论对教科文组织国际层面的保护实践产生了根本性影响。在这次会议上,民俗作为一个概念被明确取消,与稍前召开的摩洛哥会议相呼应,民俗传统转换身分以“非物质遗产”的面目出现,由此完成了概念上的遗产化过程,在新的框架下,获得了新的可能性。非物质遗产的当下性从理论上得以根本确认,其核心是民众即民俗主体的当下实践。当绵延的时间和具体的物理空间都无法成为外在的分类、排序民俗实践的基本范畴与准则时,教科文组织的非遗保护最终选择了从民俗实践的内部寻找界定的维度,这就是在后来的评审和保护中实践者/社区成为中心的根本原因。从实践者角度界定非物质遗产,这最终体现在2015年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十届常会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其中有这样的明确表述:“每一社区、群体或个人应评定其所持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而这种遗产不应受制于外部的价值或意义评判。”当然,这些根本性的变化从学者提出建议到最终体现在公约的文本和实践中,充满波折,学界的观念也总是和国际政治的角力既纠缠又抗争。从1993年起担任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部主任的爱川纪子曾详细回顾了教科文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到“2003《公约》”出台的历史过程。在一些会议的激烈讨论中,不同国家特别是那些得益于“1972《公约》”的发达国家,曾经强烈质疑已经通过的相关决议,甚至几乎危及《代表作条例》计划的实施,其焦点就是产品与过程行为之争。2003年10月非遗《公约》最终通过时,“无反对票,但有八票弃权,它们分别来自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丹麦、俄罗斯联邦、美国、加拿大和瑞士。”
五 从历史到当下:时间的浓缩化与空间
饶有兴味的是,民俗传统在上个世纪后半叶以来的遗产化进程中,从具有历史纵深度的遗留物式文化产品变成了当下的行动过程,呈现出瑞吉娜·本迪克斯(Regina Bendix)所说时间上的浓缩化(temporal thickening),即跻身遗产行列所需时间跨度的缩短。在科尔申布拉特-基布列特探讨文化遗产时间性的基础上,本迪克斯进一步指出,“在我们关注于荣耀文化过去时,我们碰到越来越新生的现象。有人甚至会说,对一些文化创新来说,其遗产化与它们在日常生活的逐渐发展是同时进行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电子文化遗产,”因为技术的迅速革新,已威胁到第一代的电子文化和知识。
文化遗产化过程中的时间浓缩化的过程其实并不特殊。事实上,这从根本上是从现代化到后现代的历史进程中,时间、空间和时空关系变化的体现。正如美国理论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所指出的,“我把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视为空间对时间取得了绝对的优势。现代主义经典在某种深刻和生产性意义上沉迷于对时间的本质的关注,它迷恋深度时间、记忆、绵延(柏格森主义的duree)、甚至是乔伊斯的布卢姆日里的点滴瞬间。”现代性从根本上是关乎时间性的。民俗学肇始于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与划分,源于对于过去的怀旧,从根本上而言亦是对于时间的关注与迷恋:“我想,不仅是柏格森,还有托马斯·曼和普鲁斯特,这些现代主义者都迷恋深度时间。这种迷恋实际根源于现代化进程的不平衡,于是造成了迟缓的乡村时间和令人眼花缭乱的都市及工业化节奏共存的情况。”关注乡村时间的民俗学兴起时对起源分析、历史脉络的热衷与执着,对古老习俗、传统消失产生的抢救、记录与保护的紧迫感,都深刻地体现出当时历史语境中时间焦点的特质。民俗实践的完整意义被界定为指向过去时代,现代生活中带传统色彩的民俗实践是碎片化的,是遗留物,民俗就是现在中的过去。

而从1980年代开始,在当下后现代、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生产中,空间已经取代时间成为更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杰姆逊称之为时间性的终结,它表现为对身体和此刻的关注:“我将这称之为时间性的终结,一切终止于身体和此刻。值得寻找的只是一个强化的现在,它的前后时刻都不再存在。我们的历史观也受到影响。从前的社会没有一个像我们现在的社会这样,有着如此少的功能性记忆和可怜的历史感。”福柯、列斐伏尔、德·塞托等理论家们对空间的大量论述与探讨,亦反映出学界对社会生活变迁的崭新认识。
在很大程度上,民俗传统从现代化过程中被关注、建构到在全球层面遗产化过程中其时间维度的变化和时间跨度的浓缩化,正是这一历史过程中时间性变化的体现。民俗传统在遗产化进程中的种种曲折,反映出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化的过程中,当时间性的标准变化之后,相较于多少固定于具体时空、具有边界性的文化遗产,民俗传统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更加难以操纵与控制,因为它充满了流动性,往往是越界的、不断变化的。正因为民俗传统所具有的复杂的时空特点与关系,其遗产化最终是通过指向当下社区主体来实现的,通过社区主体来把握,也即聚焦身体和此刻。
但是另一方面,从宏观而言,“2003《公约》”的评审和名录列入实际表现为一种面向当下、此刻的空间性并置。因为所列入的各个项目彼此之间并无一种时间线索的序列,强调的都是它们当下在其具体社区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也即它们在各自存在空间的意义与价值。由此“2003《公约》”名录体系呈现出一种空间的关系,具体的文化空间从根本上决定了项目的意义,这也是非遗评审与保护实践中反对去语境化,反复强调再语境化的根本原因所在。
虽然非遗项目的根本意义取决于其社区文化空间内原有的意义,但是列入名录(代表作、优秀实践、急需保护)这一举措本身赋予了项目得以超越自身文化空间内部意义的可能性。由于其所获得的“人类非遗”的名号,从而与其他文化空间的实践产生了关联,在全球空间的层级性并置中(世界级、国家级等),获得一种重新的理解与阐释。这样“2003《公约》”本身所强调的文化多样性,亦是一种空间关系,因为不同文化在时间上是同时的,所谓的多元实际上是一种空间上的分布,这也体现为名录希望包括更多的国家,以获得更广泛的地域分布的努力。以此而言,“2003《公约》”及其评审和名录体系体现为一种超越具体地域文化空间的超越性的空间关系,这无疑正是当下全球化时代时空关系的缩影。地方性的民俗传统因其地方性而列入名录体系,却由此获得了超越地方性的能力,显示出地方性与全球性的深刻关联。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4期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