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上方“民俗学论坛”可订阅哦!
摘 要
由于研究对象的交叉,“神话/历史”成为国内文学人类学与历史人类学的共同对话场域。不同于古典时期的“神话历史化”与近代以来的“神话-历史”二元划分,后现代语境下文学人类学与历史人类学的“神话/历史”理念,更加注重两个范畴之间的互渗与通约。从具体学术实践来看,二者因立场的差异又体现出不同的学术旨趣:前者由大、小传统论出发,视神话为中国文化的“原型编码”,在强调历史叙事之神话性质的同时,试图发掘神话叙事背后的历史质素;后者则是对美国史学家海登·怀特思想的进一步延伸,将神话与历史均视作一种“社会记忆”,强调两个范畴基于族群认同的“建构”性质。两种人类学从不同角度丰富了“神话/历史”的内涵,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神话是一种历史,历史也是一种神话。
关键词
文学人类学;历史人类学;
神话历史;社会记忆
神话与历史的关系,是东西方学术史上一个十分恒久的话题。早在古希腊时代,西方世界对于神话与历史关系的思考已经萌生。公元前4世纪,西西里哲学家尤希玛拉斯(Euhemerus)在其《神的历史》一书中提出,神话中的神灵乃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神话即历史。上述观点首开“神话历史化”的端绪。在中国,儒家对于上古“圣王”体系的建构,《韩非子》《尸子》等先秦典籍关于“夔一足”“黄帝四面”等的解释,根据后世学者的解读,与西方“神话历史化”观念几无二致。“古史辨”运动兴起后,神话与历史的关系更是引发激烈论争,受欧洲近代客观主义史学的影响,顾颉刚等学者试图将神话从历史中剥离出来,引发斯后“神话”与“历史”的对峙。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以来,在后现代史学的推动下,国内历史人类学与文学人类学界均对“神话/历史”问题再度给予关注,其着眼点均在于二者之间的交融与互通。自然,由于学术立场与理论视野的不同,两派学者在研究实践中亦呈现出一定差异。本文以海峡两岸历史人类学与文学人类学代表性学人的有关论述为案例,通过相关学术史的梳理,对上述问题做一考辨。
一、“神话”与“历史”
与众多源自欧美的概念一样,“神话”一词亦是近代以来伴随西学东渐的大潮经由日本传播而来。学界通常认为,国内最早使用“神话”概念的是梁启超1902年发表的《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一文。不过就笔者所见,这一时间还可以往前追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二月,王国维在为徐有成等翻译的《欧罗巴通史》所作《序言》中已论及“神话”:
分类之法,以系统而异,有人种学上之分类,有地理学上之分类,有历史上之分类,三者畫然不相谋已。比较言语,钩稽神话,考其同异之故,跡其迁徙之实,或山河悠隔而初乃兄弟,或疆土相望而元为异族,是以合匈牙利于蒙古,入印度、波斯于额利亚,是为人种学上之分类。
当然,这段文字并非关于神话的专论。在王国维看来,各个民族的神话与言语一样,是进行人种划分的重要依据。据陈鸿祥所著《王国维传》,王氏1898年已在罗振玉所办的“东文学社”学习日文并协助教务,其间还结识日本教习藤田剑峰,从而与日本文化有了直接接触。考虑到上述因素,可以推断王国维有关神话学、人种学的观点,很可能来自日本。
王国维之后,较早对神话进行专门阐述的,是蒋观云《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这篇文章1903年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发表,虽然题目中出现“神话历史”,其实将神话与历史分而论述,与前文所说的“神话历史”并非一回事。综观此文,主要论述神话与历史对一个民族的性格所起到的塑造作用。文章第一句话,即是“一国之神话与一国之历史,皆于人心上有莫大之影响”,其出发点在于民族性格的改造与思想启蒙。
既然神话概念在中国迟至20世纪初才出现,中国古代亦缺乏汇录神话的专书,由此引出的问题是:今天所说的中国古代“神话”,借助于哪些古籍得以保存?总体来看,在经史子集中均可发现神话的蛛丝马迹。载录最多的,自然是“语怪之祖”《山海经》;此外在《楚辞》《淮南子》等典籍中,亦可发现许多神话“碎片”。比较成体系的神话,则见于史部典籍。《史记》首篇《五帝本纪》,依次讲述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上古帝王的事迹,不过今天看来,这些人物多半属神话形象;《后汉书》所载盘瓠、竹王、廪君等的事迹,《魏书》所载朱蒙故事,今天看来亦属神话性质。上述神话的特点,都是讲述一个族群的起源,只不过古代史家将之作为过去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载入史书,并且置于历史叙事的开端位置——此位置恰与神话叙事中的“创世纪”相当。如前所述,由学术史的视野观之,这是一种典型的“神话历史化”。这种现象在前现代社会具有普遍性,在各个文明中均可发现。直至清末民初,许多学者的学术著作中,还将今天视作神话的事迹看成是远古真实发生过的历史。比如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二书对于中国历史的叙述,均从三皇五帝说起。用冯友兰的话说,上述诸人属“信古”一派,即对古籍中所载有关上古圣王的事迹深信不疑。
现代学人中,最早致力于将神话叙事从历史叙事中剥离出来的当属顾颉刚。1926年,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第一册出版,随即在学界掀起轩然大波。在《古史辨·自序》中,顾颉刚对“层累地造成的历史说”进行了系统阐述,其方法是,将典籍中所载华夏始祖的先后次序,与这些典籍的成书次序作了比较。结果发现,二者的序列恰好相反,越是后出的典籍,对华夏始祖的追溯越是久远。比如在顾颉刚看来,西周时代文献中已有“禹”的记载,“尧”“舜”则迟至春秋时期才见诸典籍。问题是,在当时的历史叙述中,后起的“尧”“舜”反倒位于“禹”之前。顾颉刚由此得出结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换句话说,这历史不是真实的,而是出于种种原因如积木一样层层叠加起来的。顾颉刚援引传入不久的“神话”概念进一步认为,三皇五帝等所谓的早期历史人物,都是神话传说。由于当时安阳殷墟尚未发掘,因而“古史辨”派对中国信史的判断非常保守。同属“疑古”派的胡适,其常遭诟病的一个观点便是“东周以上无信史”。顾颉刚只所以将神话当作“伪古史”从历史中剔除出去,除受“重估一切价值”的“五四”思潮影响外,也有近代德国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为代表的科学史观的影响,认为历史意味着客观、真实,与之相对的神话则意味着虚构。
顾颉刚的上述思想,在学界引发巨大争议。一方面,在顾颉刚生前及身后,不断有学者提出批评,认为其矫枉过正。早在1925年4月,张荫麟在《学衡》杂志发表书评文章《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从“默证”法的使用原则及界限出发指出顾颉刚“根本方法之谬误”:“凡欲证明某时代无某某历史观念,贵能指出其时代中有与此历史观念相反之证据。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陈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Argument from silence)。默证之应用及其适用之限制,西方史家早有定论。吾观顾氏之论证法,几尽用默证,而什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古史辨》第二册问世后,梁园东又发表《古史辨的史学方法商榷》,对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历史”说提出了批评:“古代的历史,多一半是聪明人制造的,是伪的,这何用说!若有方法,尽管可以指出那时所记的历史,不尽合乎那时的事实,完全是虚构的、是伪的,这都可以。但却绝不应只因为他所说的某时历史,不见于某时记载,就都认为是他的假造,是骗人,这个‘辨伪的方法’,就离开历史的研究十万八千里了!”直至上世纪90年代,李学勤出版论文集《走出疑古时代》,仅从题目可以看出,其出发点是对“疑古”的反拨。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学者对顾颉刚的“疑古辨伪”评价甚高,认为其研究开一代范式。神话学者吕微就曾撰文《顾颉刚:作为现象学者的神话学家》,其中谈到:“如果海登·怀特对顾颉刚当年的假说有所知晓,他一定要奉顾氏为后现代史学的一代宗师,因为海登同样认为,历史所呈现给我们的只是叙事的话语,至于历史的本来面目其实已经过历史学家以及无数的历史叙述者们的过滤,从而不再是客观的事实。”其问题意识在于,顾颉刚看待“历史/神话”如同海登·怀特看待历史一样,均悬置了“历史/神话”的真实性问题;顾氏研究神话的出发点是“不立一真,惟穷流变”,本质上是一种观念史、思想史的研究。
不过细究起来,顾颉刚和海登·怀特还是有很大差异。海登·怀特认为:“只要史学家继续使用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他们对于过去现象的表现以及对这些现象所做的思考就仍然会是‘文学性的’,即‘诗性的’和‘修辞性的’,其方式完全不同于任何公认的明显是‘科学的’话语。”言下之意,在“文学话语”和“科学话语”之间,历史叙述更接近前者,因而与事实、真理有很大距离。而在顾颉刚看来,历史中固然掺杂着神话,可如果把神话剔除了,剩下的就是“真古史”。所以他认为真正的历史还是对过去的真实记述,只不过“真历史”让神话给搅混了。因而“疑古辨伪”仅是其设想中的第一步工作;第二步工作,便是重建中国上古史,尽管这项工作因种种原因并未完成。
二、“历史”的多重面相
顾颉刚本着“真实”与“虚构”之间的二元对立,将历史与神话截然分开。本文所要讨论的“神话/历史”,则是强调二者之间的互渗与交融。在这一范式转换过程中,前文谈到的海登·怀特及其所代表的后现代史学,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海登·怀特看来,虽然自19世纪以兰克为代表的史学家以来,西方史学界极力倡导“科学史学”,但在本质上,这个时期的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一样,仍是一种叙述,也要遵循叙述法则,采用修辞手段,因而具有“诗性”品格与文学色彩:“19世纪历史学的科学化,历史编纂中大多数常用的方法假定,史学研究已经消解了它们与修辞性和文学性作品之间千余年来的联系。但是,就历史写作继续以基于日常经验的言说和写作为首选媒介来传达人们发现的过去而论,它仍然保留了修辞和文学的色彩。”
为了说明历史著作是“以叙事性散文话语为形式的一种文辞结构”,在出版于1973年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一书中,海登·怀特以19世纪欧洲(亦即科学史观确立之后)的几部经典史学著作为对象,借用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斯蒂芬·佩珀《世界的构想》、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等著作的分析框架,对隐含在上述史学著作中的“情节化模式”、修辞方法与意识形态蕴含进行了发掘。

需要指出的是,海登·怀特的讨论对象,是对历史的叙述,或者说书写下来的历史;而书写下来的历史,只是历史的诸多面相之一。今天的研究者已经指出,所谓历史,至少包括以下层面:真实发生的历史、史料中的历史、历史学家写就的历史。“真实发生的历史”亦即呈现为过去时态的历史事件。这些事件当然是一些客观存在,不以书写者的意志为转移。可问题是,时间是线性的、单向的,历史事件发生之后,再也不会重现。这些历史本事究竟如何,后人永远无从得知,因而在后现代史学家看来,这个问题可以悬置。“史料中的历史”其实说的就是史料,作为历史事件的残存形态,“史料”表面看来是客观的,但正如彭刚所言,试图借助史料来“重建过去”,许多情况下可能捉襟见肘。一方面,“史料的形成和流传保存,都有太多的制约因素和偶然性。很多重要的东西留存下来,实在是非常侥幸的事情”;另一方面,留存至今的史料很可能是权力与等级的产物。对此,彭刚以考古资料为例来说明:“墓葬是我们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材料,而能够在墓葬中保留大量反映当时制度、文化等因素的墓主,只是社会中处于优势的极少数人,就‘沉默的大多数’而言,我们往往缺乏足够的凭借,来推断相关的情况。”“历史学家所写就的历史”即历史文本。这是书写下来的历史,也是后人所能看到的历史。前文已述及,海登·怀特发现,任何一个历史书写者,都会受特定意识形态与诗学观念的制约,在历史著述中往往采用一些文学性手法。因而从根本上说,历史与文学一样,也是一种叙述。
这种看待历史的视角,解构意味非常明显。如果进一步追问:既然历史也是一种“叙述”,既然所谓“历史真相”可以被无限度悬置,那么历史学究竟有何意义?如此一来,整个历史书写传统可能会被消解。起码除思想史这一传统领域外,其它各种以“求真”为诉求的历史研究会面临危机。因而从学术影响来看,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其在文学界的影响恐怕大于史学界。
当然,对于海登·怀特及其史学思想的评价并非本文重点。笔者想指出的是,海登·怀特的这一套思路,对于当下神话与历史的再度融合,起了很大的辅助作用。如果沿着海登·怀特的思路往前推进,便可得出如下结论:既然历史也是一种叙述,与文学叙述无本质差别,那么历史更应该是神话。因为海登·怀特主要是从结构主义、修辞学等形式论的视角来看待历史与文学的亲缘性,却悬置了历史的功能,在将历史归结为文学叙述的同时,也忽略了一个问题:与文学相比,历史书写在一个社会中往往发挥更大的效力,更受群体的重视。如果历史是一种文学叙述,且这种文学叙述在一个社会中发挥着强大的意识形态功能,在笔者看来,要给其寻找一个对应物的话,最恰当的莫过于神话。广义而言,神话也是一种文学叙述,但它又不是普通的文学叙述,而是一种“神圣叙述”,用马林诺夫斯基的话说,“神话不只是多使我们知道一点东西的评论,乃是关乎实际活动的保状、证书,而且常是向导”。如此一来,历史和神话之间的壁垒便彻底打通了。
三、作为“社会记忆”的神话/历史
沿着海登·怀特的路径,将历史视为文学叙述,更进一步视为神话,从而弥合神话与历史之间的裂隙,这一取向,海峡对岸的王明珂颇具代表性。
在当下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界,王明珂是一位颇有建树的学者。这位出生于中国台湾,初在台湾师范大学学习历史,后又远度重洋师从著名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的历史人类学者,近年来以其《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文本与表征分析》等一系列著作,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理解,将神话和历史视为二元对立的两极,神话意味着“虚构”,历史意味着“真实”,那么王明珂的“神话历史”理念,可以概括为“化历史为神话”。在王明珂看来,“‘历史’不一定比神话传说更‘真实’”,历史和神话一样,往往不是基于事实的表述,而是种种意识形态观念制约下的特定言说。为此,王明珂从人类学立场出发,将历史表述区分为“典范”与“边缘”两种形态,他所要解构的,正是我们所习见的、借助于文字书写形塑而成的“典范历史”:“我们生活在历史知识构成的社会现实之中,社会现实塑造我们对‘历史’的想象与建构。因此,当现实成为一种为社会权力支持的正统、典范,与之相应和的‘历史’也成为典范知识。”更需要警惕的是,我们遵循传统的成见,习惯于把“典范历史”视作客观的“信史”,而在王明珂看来,“典范历史知识不一定是最真实的过去;它成为典范乃因其最符合当前之社会现实,或最能反映人们对未来社会现实的期盼。更进一步说,一人群共同信赖的典范历史与传统文化只是掌握知识权力的个人或群体所主张的‘历史’与‘文化’”。不难看出,王明珂的思路是从后现代史学延伸出来的,只不过他比海登·怀特走得更远,在解构历史真实性的同时,消解了历史叙述与神话传说的界限:“当各方‘神话’与‘历史’在人们的社会记忆交流中接触,产生配合政治、经济活动的知识权力冲突与交锋时,经常是‘神话’成为‘历史’,或‘历史’成为‘神话’。”如此一来,“历史真实”便向“神话虚构”的一边倾斜,历史也被化约为神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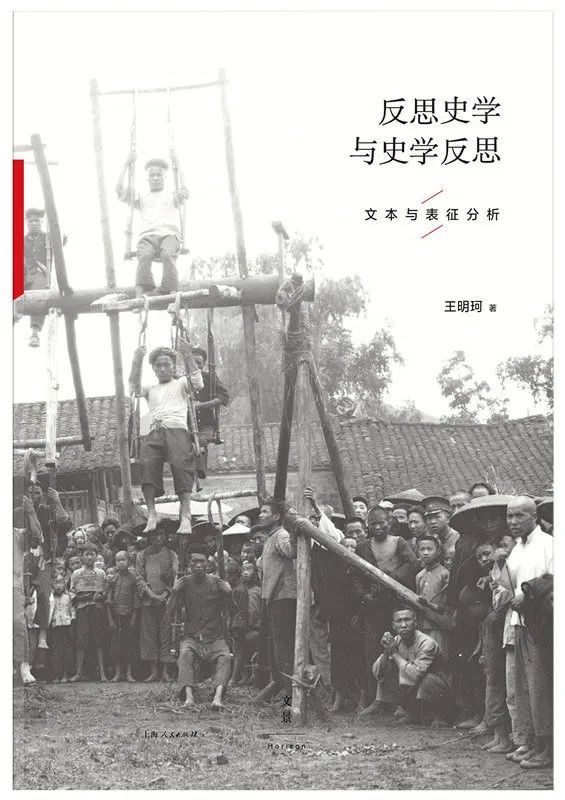
当然,王明珂并没有停留在解构真实历史的层面,在《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一书中,他将自己所倡导的“反思性历史研究”与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历史解构”进行了区分:虽然二者都将“历史”当作人们在现实情境中的建构物,但不同的是,“解构论者大多否定我们有探触真实历史的能力,或将造成‘现在’的历史限缩在‘近代’,而反思性历史研究之目的仍在探索真实的过去,并希望因此让人们对‘现实’有更深入透彻的了解”。不过,生活在后现代历史语境下的王明珂,对“真实过去”的探索不再拘泥于所谓“历史真实”,而是“历史心性”;在对“历史事实”的摒弃上,他和后现代史学仍然是一致的。在他看来,“‘历史’或‘神话’的内容都不一定真实,但它们都真实地流露、反映述说者或书写者的情感与意图”。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王明珂的研究更多呈现出“心态史学”的特点:悬置了所谓“历史事实”,而去探究过去人们建构“历史事实”的潜在心态,因而他要追问的是:如果历史本质上是一种“建构”,为什么过去的人们要“建构”历史?说到此,有必要提及王明珂的一个重要研究方法——在文献中作田野。
传统上所说的田野研究,由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奠定,是指人类学者前往某个部落或社区,在一定时间周期内参与当地族群的生活,设身处地观察他们的文化并最终形成民族志文本。作为科班出身的人类学者,王明珂对传统的田野调查自然了如指掌,不过在他看来,历史叙述和田野调查点报道人的陈述没有本质的区别。在田野现场,人类学者面对报道人的表述,会思考对方为什么如此“言说”;同样,在历史文献面前,研究者同样可以思考历史记录者为什么如此“书写”。因而所谓“在文献中作田野”,其要义“便是将历史记载当作田野报告人的陈述,以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态度进入史料世界之中”。比如《史记》中所载“太伯奔吴”一事,由传统观念出发自然会信以为真,认为吴地确系太伯所开辟。但王明珂否定了这种观点,他利用自己的考古学训练,考证出太伯所奔之“吴”当在渭水中游,而非长江下游。从情理来说,吴地远在关中千里之外,太伯不必跑到当时尚有“断发纹身”习俗的蛮荒之地。既然如此,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有“太伯奔吴”的历史记载?王明珂结合人类学知识,认为这是一种“攀附”现象。处于华夏边缘的族群,为了维系与中原王朝的密切关联,需要构拟一个想象的“共祖”。如果他们的祖先是周王室族裔,他们身上有周王室的血统,便可名正言顺地享有中原王朝才具有的正统地位,连带地也可以分享其经济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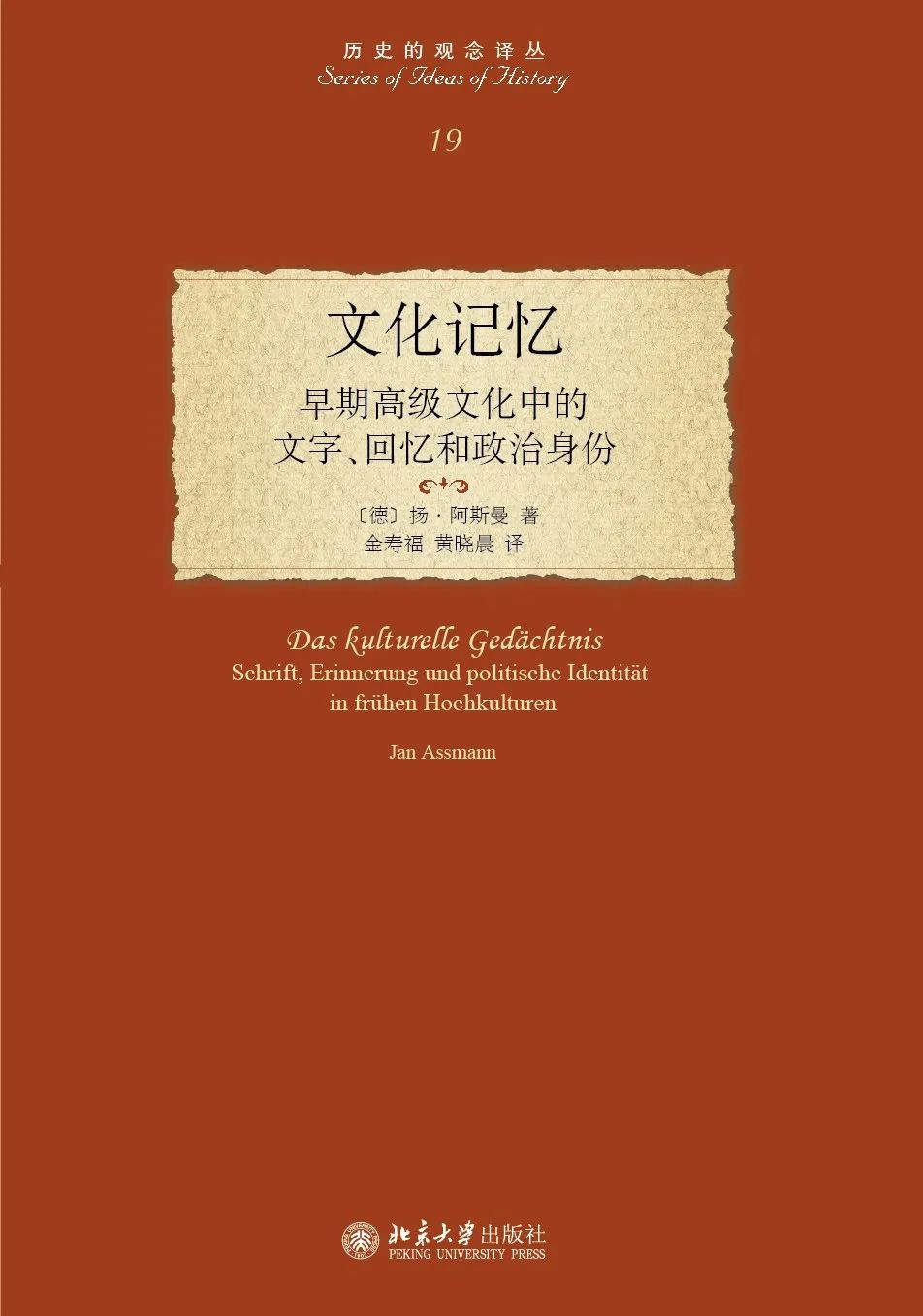
回到历史的建构性问题,如果说海登·怀特在历史和文学之间找到的共性是“叙述”的话,那么王明珂在历史和神话之间找到的共性是“社会记忆”。从社会记忆的角度看待历史,国外也不乏其人,德国学者扬·阿斯曼、阿莱达·阿斯曼夫妇,在其《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等著作中,已谈及神话、历史与记忆之间的关联。不过,由于作者过多强调书写文化之于“文化记忆”的意义,因而其所说神话、历史,主要指“文献化”的神话、历史。王明珂的“神话/历史”观,则涵盖了书写形态与口传形态;其研究对象,既包括历代“正史”中的记载,又包括来自田野的“活态”资料。在王明珂看来,无论过去信以为真的历史,还是被视为荒诞不经的神话,本质上都是一种“社会记忆”:“我们所熟知、深信的‘历史’只是一种‘社会记忆’,‘神话’则是另一种形式的社会记忆。”这些记忆有两个特点:第一,都与某个远古的“共祖”有关,都是围绕远古时代的某个共同祖先来展开叙述;第二,既然是“记忆”,便不等同于真实的历史事件,而是一种人为的选择性建构;在“不断地强调某些集体记忆,以及遗忘另一些记忆”的同时,“甚至假借、创造新的集体记忆”。总体来看,王明珂认为历史与神话一样,在本质上都是一种集体记忆,均受特定的“历史心性”制约。王明珂的研究,便是探寻集体记忆背后的社会心性与动因。
四、神话的历史性与历史的神话性
在中国大陆,以叶舒宪为代表的文学人类学界近年来亦对“神话/历史”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2009年,受以色列学者约瑟夫·马里(Joseph Mali)《神话历史:一种现代史学的生成》一书中“mythistory”概念的影响,叶舒宪在汉语世界率先提出“神话历史”命题。自2010年始,叶舒宪主编《神话历史丛书》,以此彰显“神话历史”理念的本土化改造与实践。参照学界有关文学人类学“元话语”的界定,“神话历史”无疑已成为中国文学人类学的主要“元话语”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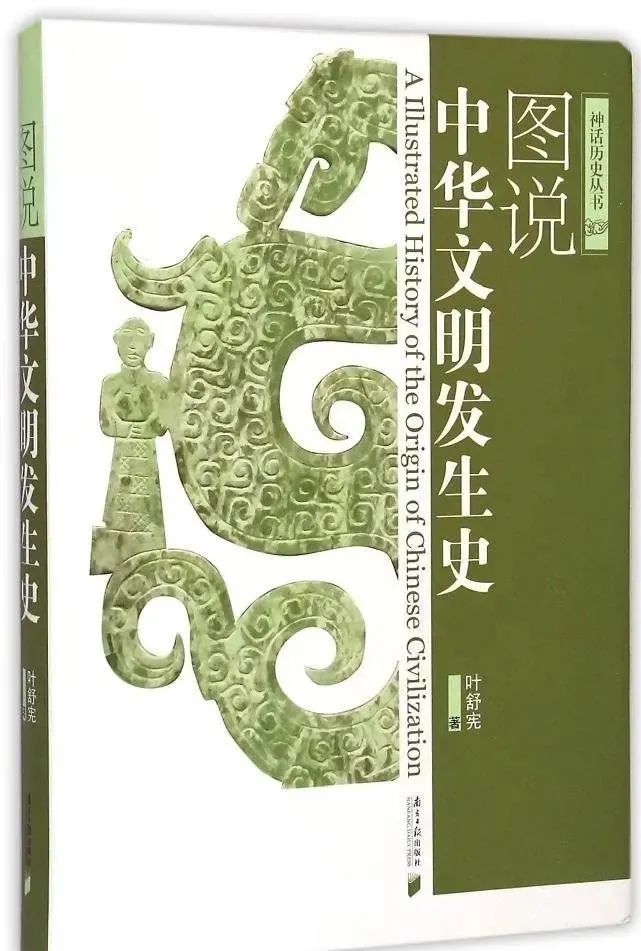
与王明珂一样,叶舒宪也认为神话与历史之间不可截然分开,二者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互渗关系:“神话的内容和神话讲述活动本身都显露出充分的历史性, 历史叙事中也显露出充分的神话性。”对于王明珂的“集体记忆”说,叶舒宪也有一定程度的共鸣:“对于大多数无文字社会,神话几乎是社会精神和群体记忆的同义词。”不过细究起来,二者的“神话/历史”观仍有着比较清晰的分野。这种分野首先在二人的理论背景上有所体现,虽然二者均受文化人类学、后现代史学的深刻影响。王明珂的理论来源比较多元,举凡挪威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的“族群与边界”思想,以及生态学理论、考古学知识,均对他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不过总体来看,王明珂是对海登·怀特历史观的延伸,在“真实”与“建构”的两极之间,他更倾向于后者,视历史为一种社会记忆。叶舒宪的理论来源也十分丰富,比如以詹姆斯·弗雷泽为代表的古典人类学、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以诺思罗普·弗莱为代表的原型批评,均可在其研究中发现踪迹。不过从“神话/历史”理念来看,对他影响较为显著的,除前述以色列学者约瑟夫·马里外,还有美国考古学家玛丽加·金芭塔斯的神话考古学研究,尤其是美国人类学家芮德菲尔德的“大、小传统”说。
1956年,芮德菲尔德出版《农民社会与文化》一书,其主要内容是对各种类型的“农民社会”(尤其是所谓“原始形态的小型社会”)及其文化进行探讨,从而为以这些社会为对象的人类学研究者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论模型。按照传统的社会人类学观点,包括农民社会在内的“小型社会”,通常是一个相对孤立的单元,与都市文化、精英文化的交流有限。不过芮德菲尔德在此书中试图阐明的是,“所谓小型社区实际上在社会结构上和文化传统上都和比它们大的社区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外,芮德菲尔德在此书中呼应社会学家吉迪恩·斯伯格(Gideon Sjoberg)的观点,认为让处在较低社会地位上的农民与处在较高社会地位上的精英之间建立起一定联系是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由此出发,芮德菲尔德在书中提出“大传统”与“小传统”这对概念作为新的解释模型:
在某一种文明里面,总会存在着两个传统;其一是一个由为数很少的一些善于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大传统(a great tradition),其二是一个由为数很大的、但基本上是不会思考的人们创造出的一种小传统(a little traditon)。大传统是在学堂或庙堂之内培育出来的,而小传统则是自发萌发出来的,然后它就在它诞生的那些乡村社区的无知的群众的生活里摸爬滚打挣扎着持续下去。
需要注意的是,芮德费尔德还使用了一系列与上述模型相对应的概念,可以加深我们对这对模型的理解:“高文化”与“低文化”;“古典文化”与“民俗文化”;“上流社会传统”与“通俗传统”。这几组概念中,属于“大传统”一极的主要有“哲学家”“神学家”“文人”等精英集团,属于“小传统”一极的则主要是以“老百姓”为主体的社会群体。综合作者使用大、小传统的语境,大致可以说,“大传统”主要指社会精英阶层所创制的传统,其主要载体是文字与典籍;“小传统”则是在下层民众中间传承的一套传统,主要以惯习或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的形式代代传承。从前述来看,这对概念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其一是对“下层社会”的明显偏见;其二是潜藏在其中的二元对立思维。尽管如此,由于这组概念为文化史的分析提供了全新的解释范型,因而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反响。中国文化研究领域,自上世纪80年代起,余英时、李亦园、王元化、王学泰、葛兆光等学者已对这组概念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与引申,不过总体来看,仍未跳脱其中的等级划分与精英主义偏见。正因为此,近几年来叶舒宪基于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省察,对芮德菲尔德的大、小传统概念进行了反向改造:“针对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和多层叠加、融合变化的复杂情况,倘若既剔除孔子上智下愚二分法的价值判断色彩,也不拘泥于西方人类学家的雅俗二分结构观,可以把由汉字编码的文化传统叫做小传统,将前文字时代的文化传统视为大传统。”二者之间的主要界限,便是汉字书写系统的建立。就其关系来看,“大传统对于小传统来说,是孕育、催生与被孕育、被催生的关系,或者说是原生与派生的关系。大传统铸塑而成的文化基因和模式,成为小传统发生的母胎,对小传统必然形成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反过来讲,小传统之于大传统,除了有继承和拓展的关系,同时也兼有取代、遮蔽与被取代、被遮蔽的关系。”即以“神话/历史”这对范畴而言,神话产生于人类史前的口传时代,是文化大传统的主要载体,具有“原型编码”的作用;历史书写产生于文字出现之后,自然代表后起的小传统。正因为此,神话对于历史有着强大的辐射力和制约作用。不仅神话题材不断转化为历史书写的重要资料,更重要的是,整个历史书写都受神话思维的制约。如此一来,貌似理性的历史与貌似荒诞不经的神话,便互相粘附在一起而难分彼此。更为重要的是,在叶舒宪看来,这种二分法“有助于清醒地看到文字符号出现后被割裂的神话历史大传统的存在,将神话—文学研究的目光引向无文字时代的历史纵深处。”受上述思想的促动,叶舒宪主编《神话历史丛书》,致力于探究历史编纂与神话思维之间的关联,进而揭示历代正史中的神话质素及其与前文字时代文化“大传统”的关联。
另一方面,当王明珂用社会记忆理论来阐释“神话/历史”时,神话、历史同时成为社会建构的产物。叶舒宪则不然,在解构历史知识之“科学性”的同时,也解构了神话叙述的“虚构性”,试图在神话背后发掘真实的历史质素:“神话被认为是跟历史有重大区别。历史都是真实的,神话都是传说的,靠不住的。现在看来,神话中有靠得住的,历史中也有神话虚构的东西。”这种取向貌似回到了前现代时期的“神话/历史”观,其实不然。与早期学者的索隐臆测、主观比附不同,叶舒宪等文学人类学者借助传世文献、出土文献、民俗学与民族学资料、考古实物与图像相互参证的“四重证据法”,通过抽丝剥茧般的细致分析,使得神话叙事里面的历史碎片与信息得以呈现。比如出土于西晋太康年间的《穆天子传》一书,记述周穆王四海巡游之事,其中卷三讲述周穆王“执白圭玄璧”远赴西土“宾于”西王母。因西王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女神,因而近代以来以茅盾为代表的学者,多将上述叙事视作无可稽考的神话。叶舒宪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发现,《穆天子传》一书讲述周穆王西征的各卷,其叙事主要围绕玉石神话与玉石礼仪展开:第一卷为西征的序曲,始于以玉璧献祭河神的礼仪;第二卷为西征的主体,包括四个情节单元,每个单元都围绕穆天子获得美玉的中心事件展开叙事;第三卷为西征的高潮,穆天子手捧白色玉圭和黑色玉璧晋见西王母。结合中国境内有关玉料、玉礼器的考古发现与华夏先民的玉石崇拜,叶舒宪得出结论:“《穆天子传》所讲述的穆王西游故事,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巡狩、封禅,也不是寻常的旅游、探险,而是西周帝王对华夏版图以西的边地所特有的神玉源头的一种朝圣之旅。”换言之,《穆天子传》中对于周穆王与西王母赠歌互答的描述,可能出自文人的虚构与想象,因而西王母身份及事件真实性问题可以悬置。不过在这种颇具文学色彩的神话叙事背后,仍透露出些许历史的信息,即中原王朝对于昆仑美玉的追求与“玉石之路”的开辟。与叶舒宪观点形成互文性关系的,还有方艳《玉石之寻——论〈穆天子传〉的历史文化意义》一文,其中梳理了《穆天子传》所述周穆王的巡行路线,发现这一线路与上古华夏的“玉石之路”恰相吻合,从而揭示出《穆天子传》一书与华夏玉石文化传统之间的关联。上述文学人类学者对于《穆天子传》的研究,将穆王西巡的神话叙事置于中国玉石文化传统与西周大一统思想这种宏大的文化文本之中,体现出对于传统研究的超越。
要而言之,文学人类学所说的“神话历史”,其所指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神话作为“原型编码”,对历史书写、历史编纂起着深层的制约作用;二是神话并非全然虚幻的言说,在其貌似荒诞的叙事中潜藏着历史遗痕。
结语
自从詹姆斯·弗雷泽至今,神话一直是文学人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对于历史人类学而言,其主要研究领域自然属于历史。不过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要在神话与历史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殊非易事。许多情况下,二者之间相互浑融、难分彼此。正因为此,“神话/历史”成为文学人类学与历史人类学的共同对话场域。美国史学家唐纳德·R·凯利曾说:“不管承认与否,历史在许多时期产生自身的神话,而神话时常被当作高级诗歌真理或者甚至宗教真理。当今,一些学者一直在努力重新联合这些争论的兄弟,断言神话有其历史面目,而历史并不完全像它经常所宣称的那样是真理的推动者。”本文以国内文学人类学与历史人类学的相关研究为个案进行讨论,正是试图呈现上述努力在国内的进展。从研究取向来看,文学人类学在强调历史叙事之神话性质的同时,试图发掘神话叙事背后的历史质素;历史人类学则将神话叙事与历史叙事均视作一种“社会记忆”,强调两个范畴基于族群认同的“建构”性质。两种人类学互为补充,从不同角度为我们审视神话、历史之本质及其关联提供了新的思路。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图文来源:微信公众号“文学人类学” 2021-09-20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