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上方“民俗学论坛”可订阅哦!
多民族戏剧交融及其中华文化认同功能论析——以云南为例
董秀团
原文刊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一、问题的提出
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国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精准论断,是对我国各民族长期交流互动、共同创造丰富灿烂的中华文化这一过程及其结果的生动描述。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化,从精神层面有力地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艺术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表征,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长河和当代实践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研究艺术的文化认同功能及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同体意识中的作用,戏剧是不可忽视的资源。原因主要有二:其一,作为综合性艺术,戏剧是多种文学艺术因子融合互动所形成的复杂整体,承载着丰厚的族际交往信息,是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其二,多民族在戏剧领域的长期交流、互鉴,反映了中华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各民族共创共荣、相互认同的基本事实,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云南蕴含着丰富的戏剧资源,除了滇剧、花灯等汉族戏剧,还拥有形态多样、剧种丰富、剧目富集的少数民族戏剧。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少数民族有近30个戏剧剧种,主要分布在广西和云南。要研究多民族戏剧的互动和认同,云南是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云南各民族戏剧是文化交融的产物和见证,其形成、发展、剧目、母题、艺术特色等方面都充分体现了各族文化的交融互鉴。此种族际交融,既体现于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也体现于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汉文化的输入和影响是云南少数民族戏剧产生、成熟的重要动因,作为云南汉族戏剧代表的滇剧和花灯,也在很多少数民族当中生根发芽,绽放异彩。云南各民族毗邻而居、交错杂处、往来密切,有的还具有相同的族源,此种天然的亲缘关系让戏剧的交融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在一些相邻或交错杂居的民族中,常流传着同一种戏剧形式。如吹吹腔在大理白族和彝族中均有流传;傣剧也传播到周围其他少数民族中,户撒阿昌族就深受傣族之影响,其剧本用傣文抄写,傣语演唱;保山香童戏除汉族外,还流传于傣族、彝族和傈僳族中。云南的多民族戏剧交融蕴含着突出的文化认同意识,这其中,既有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也有对汉文化和中华文化的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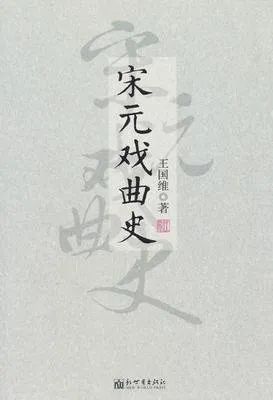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开启了古典戏曲研究的先河。百余年来,我国戏剧艺术的起源流变、剧种剧目、艺术特征、功能价值、传承保护等诸多方面皆引起学者关注并取得了丰富成果。对少数民族戏剧艺术的关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伴随着民族识别、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等工作而得以展开的。20世纪60年代,《少数民族戏剧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戏剧》等著作被视为奠基之作。此后,研究的视角趋向多元。总体而言,我国少数民族戏剧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第一,对少数民族戏剧的整体观照和历史梳理。曲六乙《中国少数民族戏剧通史》是系统研究我国少数民族戏剧、梳理其历史发展过程的力作,纵向时间上从周代至当下,横向内容上几乎涵盖了所有少数民族代表性戏剧形式。王文章《中国少数民族戏曲剧种发展史》则从剧种角度出发,同样对少数民族剧种发展史进行了全面梳理。李强、柯琳的《民族戏剧学》以跨学科的视野力图构建起民族戏剧学的分支学科。第二,对某一少数民族具体剧种、戏剧形态的考察。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戏剧丛书》既收录了各省区少数民族代表性剧目,也有关于当地少数民族戏剧的研究论文。不少民族有了自己的戏剧志,如《傣剧志》《彝剧志》《白剧志》等。第三,对少数民族戏剧源流发展、艺术特征、仪式表演的探讨,也有大量结合田野调查切入上述角度的研究成果。对民族地区傩戏、傩文化的研究成为20世纪80、90年代的学术热点。与此相呼应,呼吁对现代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戏剧进行传承保护、发扬少数民族戏剧的民族特性等方面的成果也比较多见。
云南民族戏剧的相关研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前述整体观照中国少数民族戏剧的丛书论著中,云南民族戏剧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专注于云南民族戏剧自身的研究成果也不少。曲六乙、杨明、金重、郭思九、顾峰、黎方等学者从不同角度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此外,云南民族戏剧的“活态”性为理论反思提供了支撑,王胜华的《云南民族戏剧论》从云南戏剧个案出发,但在某种意义上却构成了对戏剧艺术发生学和传统戏剧本质的重新思考。吴戈的《云南少数民族戏剧生存现状的思考》从题材内容、生存发展的角度对云南民族戏剧的现状进行了反思。
在民族戏剧的研究中,已有学者关注到并讨论了各民族戏剧文化的交流问题,如曲六乙的《少数民族与汉族戏剧文化的双向交流》一文,从纵向脉络中截取少数民族与汉族交流的典型例证进行论述;朱恒夫在《论中国少数民族戏剧的特征》中也谈到了少数民族对汉族戏剧的自觉接受;黎方的《彝汉文化的交流和云南彝族戏剧的发生、发展》论述了彝汉文化交流对云南彝族戏剧的影响;田同旭的《论古代戏曲的形成与民族文化融合》分析民族文化交融对中国古代戏曲形成的影响;此外,以元杂剧为切入点分析民族文化交融的成果也比较多。曲六乙还倡导确立“中华民族戏剧史观”,给予少数民族戏剧应有的价值认定。也有学者讨论传统戏曲或少数民族戏剧的认同问题,但以身份认同、接受与认同、传播与认同等为讨论热点,涉及民族文化认同的相对较少。
总体来看,以往的研究中,对我国传统戏曲和汉族戏剧的关注要多于少数民族戏剧。在少数民族戏剧的研究中,又存在或偏重整体把握,或专于某一少数民族剧种、某具体案例的情况。学界对多民族戏剧间的交流、互鉴关系研究不足,还未能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多民族戏剧交融及其中华文化认同功能。云南是多民族戏剧交融的典型地区,以往学界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戏剧起源发展、早期形态和传承保护等方面,对多民族戏剧交融历程、表征及其中华文化认同功能,尚未展开探讨。本文通过梳理云南多民族戏剧交融的历程、表征,发掘其中的中华文化认同意识和达成路径,为研究我国多民族戏剧交融及其中华文化认同功能提供范式,以期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创新发展。
二、文化交流与戏剧发展:
云南多民族戏剧交融的发生学表达
戏剧是综合民间歌舞乐、劳动、祭祀、仪式等多种因素后形成的艺术形态。此种综合性是戏剧艺术吸附、整合能力的一种反映。文化交流及其所带来的多种文化艺术因子的融合是刺激戏剧艺术形成发展的重要原因。
云南虽地处边疆,却很早就拉开了与汉地交流的历史序幕。《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关于公元前三世纪楚人庄蹻入滇的叙事是最早有关内地与云南交流的汉文史料。云南民族发展史是一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廖国强指出,“以汉化夷”将少数民族纳入华夏文化圈的同时,“因俗而治”加强了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整合互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新形态。长期、持续的文化交流必然会带来乐舞、戏剧等各种艺术形式的双向交融互动。一方面,云南各民族的乐舞等戏剧元素被带入中原汉地的文化系统;另一方面,汉族地区的戏剧艺术也不断输入云南,极大地影响了云南各民族戏剧的产生、发展和完善。
先看云南地区戏剧元素对中原汉地的影响。《新唐书·礼乐志》载:“贞元中,南诏异牟寻遣使诣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言欲献夷中歌曲,且令骠国进乐。”异牟寻派遣使节率歌舞乐团到成都向韦皋敬献“夷中歌曲”,经韦皋加工整理后定名为《南诏奉圣乐》进京献演。《南诏奉圣乐》吸收了中原汉族、西域以及印度、骠国等地乐舞而成,又被唐朝宫廷乐舞吸收,在原有“十部乐”的基础上增加了“南诏部”。这是云南少数民族乐舞融入中原的典型例子。北宋徽州时,入献中原的乐舞“五花爨弄”对宋元杂剧产生了重要影响。《白古通浅述·大理国纪》载:“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遣使李紫琮等贡马三百八十匹及麝香、牛黄、细毡、碧圩山诸物,又有乐人,善幻戏,即大秦、犛轩之遗,即‘五花爨弄’,徽宗爱之,以供饭宴,赏赐不赀。”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说:“院本则五人:一曰副净,古谓之参军;一曰副末,古谓之苍鹘……;一曰引戏;一曰末泥;一曰装孤;又谓之五花爨弄。或曰,宋徽宗见爨国人来朝,衣装鞋履巾裹,傅粉墨,举动如此,使优人效之以为戏。”王国维认为“丑”之角色也与五花爨弄有关:“余疑丑或由五花爨弄出。”《辍耕录》中载院本名目960多个,其中有“诸杂院爨”107个,107个中又有21个名目明确冠以“爨”名,如《讲百果爨》《讲百花爨》《打王枢密爨》等。《武林旧事》载南宋官本杂剧名目280个,其中以“爨”名之者43个,如《孝经借衣爨》《黄河赋爨》《门子打三教爨》等。上述史实说明,云南地区这些与戏剧相关的乐舞元素进入到中原汉地后,被汉族戏剧所接纳。汉少戏剧交融的过程中,少数民族并非只是单向度接受。
再看汉族戏剧对云南少数民族戏剧发生发展的影响。由于较早发生交流、汉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历程中的主导性地位、移民屯田强化了杂居共处格局等诸多原因,汉族戏剧对云南少数民族发生影响似乎是自然而然的过程。云南各少数民族的文化本体中也生发出对汉文化的高度仿照和认同,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将自己的根脉追溯到中原汉地,主动攀附为汉族移民后裔。云南弥勒彝族阿哲人、腾冲佤族、大理白族都有祖籍南京应天府的说法,阿昌族、佤族、景颇族则说自己的祖先是诸葛亮。傣族戏剧《布屯腊》开头有一段汉傣夹杂的开场白,述很久以前傣族先民从南京应天府出发,跋山涉水来到当地开荒。艺人谓此开场白不能随意更改。王胜华认为这段戏极有可能由明代进入麓川的军队和军屯之人带入。此类说法,虽有一定的历史可能性,但更多体现的却是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向慕之心。云南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高度认同,为汉族戏剧艺术的输入奠定了坚实基础。据载,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南诏攻陷成都,曾大掠子女百工,李德裕上任西川节度使后即进行调查,说南诏所掠并不像传言那么多,“成都郭下、华阳两县,只有八十人,其中一人是子女锦锦,杂剧丈夫两人,医眼大秦僧一人,余并是寻常百姓,并非工巧”。任半塘认为:“所指出之男女四人,宜皆确切为‘音乐伎巧’无疑……其次‘杂剧丈夫两人’,为‘音乐伎巧’,无问题”。此处,“子女锦锦”和两名“杂剧丈夫”被李德裕单独列举,说他们非“寻常百姓”,这些人到南诏后极有可能对当地戏剧产生了影响。汉地戏剧的传入,或直接促成了云南一些少数民族剧种的产生和发展,或将汉地剧目移植传播到少数民族之中,或是在唱腔、音乐、伴奏等方面影响了云南少数民族戏剧。此种艺术交融是云南民族戏剧得以产生、成熟并形成自我风貌的重要动因。
云南民族戏剧形态丰富,为了更好地厘清其发生学意义上的文化交融特质,可将其大致划分为原生型、次生型和再生型。3种类型的发展形态、成熟程度、艺术特征不尽相同,但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却都渗透着文化交融的影响。
原生型戏剧指与各民族祭祀、信仰、巫术、仪式、乐舞等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交织共生的戏剧样态,通常具有驱邪除疫、祈福纳吉等特殊功能。此种戏剧形式,保留了仪式性、混融性等特征,体现出与各民族民俗生活和文化系统的黏合。如果用成熟形态戏剧的标准去衡量,或认为它们还不能称之为戏剧,但从模仿、扮演等要素来看,它们无疑又具有戏剧的基本特质。如玉溪花腰傣的“猫猫舞”,由三四名强壮男子戴虎头面具、身披虎皮,装扮成老虎,追赶驱逐同样戴着面具装扮而成的魔鬼夫妻。玉溪、大理等多地彝族中流传的“跳哑巴”,大理白族“耳子歌”和拉祜族苦聪人“哑巴舞”,都是比较类似的仪式戏剧。傣族《布屯腊》在开春前演出,先由巫师带领到寨神勐神处祭拜,邀请四方神灵看戏,演出过程贯穿着各种祭祀仪式。与之相似的是插秧季节演出的大理白族田家乐,以戏娱神、祈求丰产。云南各地的原生型戏剧很多具有“傩”的特质,楚雄彝族“小豹子笙”用孩童扮演豹子并挨家挨户打闹追逐的形式无疑与驱傩仪式是吻合的,康保成指出“民间驱傩亦多用小儿”。此外,楚雄彝族“老虎笙”,从广义角度也可纳入“傩戏”的范畴。此种傩及傩戏,在中原汉地同样具有久远历史和广泛流传。原生型戏剧中表现出的这些类同和相似,虽还缺乏族际交流和相互影响的直接证据,但从某种程度上却体现了更高层次和更普泛意义上的融通。
次生型戏剧是云南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民族戏剧形式,或是中原汉地戏剧的传入,又或是汉族滇剧、花灯在少数民族中的流传。相较于原生型戏剧,其产生时间较晚,艺术形态更完善,更接近戏剧之“标准”。次生型戏剧通常是本民族歌舞乐传统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受汉族戏剧影响所形成,从产生就被打上族际交融的印记。比如白族吹吹腔,以打歌、白族调、绕三灵、打秧官、田家乐等白族传统歌舞戏曲活动为基础,又接受了汉族戏剧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其受明清高腔、乱弹之影响;也有学者认为吹吹腔源出弋阳腔系统,明洪武年间随浙江、江苏、江西等地屯田、移民到云南的汉民传入大理;或又认为吹吹腔由大西军于明末清初带到云南,吸收本地民俗文化艺术及其他剧种元素而成。再如腾冲佤族的清戏,清咸丰年间已有演出,音乐属弋阳腔,表演形式为“佤族村民着汉族服饰,运用汉语演唱汉族故事”“与汉族移民、中原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扎根有关”。曲六乙也指出,傣剧在初期受京剧、滇剧的影响,后逐渐加入象脚鼓、葫芦丝等民族乐器,将外来影响和民族特色相融合,壮族师公戏受到汉族傩舞和粤剧的影响。云南各民族中的傩戏,同样是本土巫傩传统与外来汉文化相融合的产物。如保山香童戏,“除与古代傩歌傩舞及巫的祀神驱鬼活动有直接关系外,同时也与大量来自中原、江南各地的移民即从军者、从商者涌入带来中原文化和许多神仙道化剧目的渗透有关”。民间传说香童戏所祀之神是诸葛亮南征凯旋回蜀所封,这当中自然也有汉地文化的印记。昭通端公戏和文山梓潼戏都是从省外传入云南。但端公面具中,又出现了彝族“八蛮将军”、苗族“苗老三”“娘差”等少数民族形象。澄江关索戏的起源虽无定论,有当地产生、外县传入、外省到云南戍边的军队带入诸说,但从该戏只演三国故事的特点来看,该戏种必然也无法与汉地文化分割开来。滇剧、花灯等汉族戏剧形式在少数民族中得以流传后,通常亦会发生民族化的改变,体现出汉少族际文化的交融互构。如彝族花灯,虽由汉地传入,但彝族民众也将彝族民歌、彝族乐器等自身艺术传统赋予了花灯,让花灯具有了彝族味道。甚至戏中的人物形象也具有了彝族民众的性格气质,《打花鼓》《打鱼》《老贾休妻》中的女性角色豪爽率真,有的甚至把男人打倒在地,这在汉族花灯中是极其少见的。
再生型戏剧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云南各民族中的新创剧种,如白剧、壮剧、彝剧、撒尼剧、章哈剧等,它们往往与本民族的次生型戏剧有密切关系,但又不能等同。如云南壮剧的三大分支富宁土戏、广南沙戏、乐西土戏都具有较悠久的历史,但以壮剧统一命名则是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白剧在吹吹腔和大本曲基础上发展而来,但作为一个剧种是20世纪50年代才产生的。再生型戏剧身上族际交融的影响更加明显。首先,再生型戏剧多在本民族次生型戏剧的基础上发展形成,次生型戏剧本身就是汉、少文化交融的产物,再生型戏剧自然也具有此种特点。其次,再生型戏剧对于族际文化交融的实践更加自觉。这些新创剧种既肩负着凸显民族特色的任务,又面对着戏剧文化发展相对成熟的当代背景,还要适应现代化和新媒介系统的要求,民族特色、现代标准、新的需求都是“规制”新创剧种的重要元素。民族的和外来的、传统的和现代的这样的多面向协调平衡在此类戏剧中显得尤为重要。很多少数民族新创剧种将汉、少两种语言结合使用便是一例,如壮剧“唱词用汉语,念白则半壮半汉,有时丑、旦说白还夹用粤语。”白剧、彝剧均采用“汉语别音”的语言形式,即用本民族语言口音讲汉语。
三、剧目互鉴与母题共享:
云南多民族戏剧交融的本体表征
剧目互鉴和母题共享从本体层面搭建起云南多民族戏剧交融的核心和要旨。剧目互鉴是云南民族戏剧内容和题材上的突出表征,也是多民族戏剧深度交融的反映。云南民族戏剧中还存在大量共享母题,体现了各民族共同的心理基础和价值追求,也映射着多民族的艺术交融。
1、剧目互鉴
相对稳定的剧目是判断和评价戏剧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云南多民族剧目互鉴主要表现为:
首先,云南各民族都有从汉族移植而来的剧目,形成与汉地剧目的互鉴呼应。傣剧中此类剧目有《陶禾生》《汉光武》《庄子试妻》《八仙过海》等。傣剧《十二马》据说也是明洪武年间由南京应天府传入。实际上,兴盛时期的傣剧剧目多源自汉地,故江应樑称之为“汉化的傣族戏”。壮剧有大量取材于汉族历史演义、小说唱本的剧目,《三官堂》《八仙图》《火钉床》《薛仁贵》《征西》《张四姐》等均存有清代抄本。白剧400多个剧目中移植自汉族的传统吹吹腔剧目占据主体。彝剧中也有不少移植自汉地的剧目,《大头和尚戏青柳》的源头便是中原地区的《大头和尚戏柳翠》。甚至在戏剧历史比较悠久、形态比较成熟的民族中,源自汉族的题材剧目往往占据着更大的比重,说明在少数民族戏剧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向汉族学习、从汉族剧目中进行移植改编往往是一条通用的路径。有些剧目,表面上似乎看不出与汉族的关系,甚至被归入民族传统题材,但实际上却来自汉地。如傣剧《布屯腊》述爷爷和孙子犁田、奶奶送饭的故事,类似的是大理白族田家乐,演五月农忙,十二三岁的来兴在爷爷犁田时帮忙干些轻活,来兴奶送饭来迟,受来兴爷责备,来兴奶于是细数在家的忙碌苦楚。两剧又与汉族地区的《大舜耕田》相似,甚至也有傣族群众认为《布屯腊》与《大舜耕田》是同一个剧目。
其次,一些源自汉地的剧目进入云南多个民族,各民族中流传着相似或相同的剧目,形成多民族、多向度的剧目互鉴。这方面,梁祝故事即是代表。该故事在汉地的经典性和流传度都毋庸置疑,杂剧、传奇、宝卷及汉族地区各种地方戏中皆有此剧。在云南,除滇剧、花灯外,梁祝故事还被移植到壮剧、傣剧、白族吹吹腔和大本曲、昭通唱书、姚安莲花落中。一些少数民族戏剧中还有梁祝死后事迹的敷演。富宁土戏中,化成彩虹的梁祝被神仙搭救,习得武艺,再生还阳。山伯中状元,且于英台外又娶路凤鸣。白族大本曲中,梁祝化蝶后分别被洞宾老祖和尼山老母搭救并授予武艺。英台杀死黑店店主和田总兵,自立朝阳王。山伯中状元,娶英台、凤鸣、公主三妻。剧中曲折的梁祝后记,实非少数民族的创造,而是源自汉族宝卷《后梁山伯祝英台还魂团圆记》,“梁山伯、祝英台死后还魂,成为带兵的将官。后来功高名就,山伯被封为定国王,且于英台外,复娶二女为妻。故亦名《三美图》。”大本曲中,山伯助太子登基,定国安邦有功,也是被封为定国王。再如流传于云南壮剧、白剧中的蓝季子故事,有《双贵图》《血汗衫》《蓝季子会大哥》《磨房记》等名。该剧目与汉文化的联系十分紧密,当移自汉地。一方面,该剧所述内容与明代沐英、蓝玉平定云南的历史事件有关,传说剧中主角蓝季子是蓝玉之弟,或谓兰中林是沐英、蓝玉的部将。湖北土家族柳子戏《边关投军》中,兰纪昌在边关立功,被封为平西侯。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疆,此处的“平西”或许就指云南。闽西汉剧《蓝继子》亦说投军出征边关。这些都说明该剧目与明代进取云南、移民入滇之间有所关联。另一方面,我们可在汉族戏剧中找到相同剧目或类似情节。秦腔传统剧目《血汗衫》,述明时兰仲礼、兰仲信投军,继母张氏虐待仲礼妻李氏,张氏亲子兰吉子外出寻兄前李氏杀鸡以飨,鸡血染吉子汗衫。张氏诬李氏杀子,李氏被判死刑。仲礼、仲信立功封官,救出李氏。豫剧《血汗衫》述蓝芳草赴山东讨债,其子忠岫、忠岭进京赶考,继妻郑氏让儿媳尹氏到刁庄推磨。郑氏亲生子蓝季子替嫂推磨,尹氏杀鸡酬弟,鸡血污衣,季子换衣寻兄。郑氏诬尹氏杀子,尹氏被判死刑。季子遇已做官的两兄长,尹氏获救。这些剧目内容大同小异且都具备“血染汗衫”的核心母题。
再次,汉族的剧目先传入某个少数民族,又从此民族传入另一个少数民族当中,构成了戏剧传播中多元参与、多向流动的状态。比如傣剧《牡丹》,又名《鲤鱼》,原为明清传奇剧本,全名《鲤鱼精鱼篮记》《观世音鱼篮记》,该剧先随汉族剧种传入户撒阿昌族地区,后又为傣剧所吸收。
最后,中原汉地剧目先进入到滇剧、花灯等云南汉族戏剧,进而再传播到少数民族中。《蟒蛇记》《董永卖身》《滴血珠》《金铃记》等当属此种情况。彝剧《大王操兵》也是20世纪40年代花灯班社时常在土主庙中扮演的剧目,其唱腔“阿苏找”是彝族代表性曲调。或认为这是汉族花灯剧目在彝族地区的流传,或认为此乃汉族花灯剧目但吸收了彝族某些传统艺术,或认为这是彝族原有戏剧形态吸收融合了花灯的艺术形式之产物。该剧取材于三国陈泰搬兵的民间传说,其中的大王角色,有说是彝族土主,有说是孟获。还有一些地方在剧中增加了杨宗保和穆桂英的角色,但又认为二人是彝族。无论如何,该剧都鲜明地体现出彝汉融合的特点。
2、母题共享
母题是对固定的情节叙事单元的凝练概括,该术语在民间文学、文艺学、叙事学等领域有着广泛运用。“无论是何种艺术形态,其最基本的元素就是母题,没有母题的艺术是不存在的。”汤普森将母题界定为“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在传统中的成分”,并划分出3类母题:一个故事中的角色、涉及情节的某种背景、那些单一的事件。戏剧研究中引入母题概念,可为族际比较提供直观视角和可操作的工具。王政指出戏曲母题是戏曲作品中稳定承传、具有共同属性及特点的最小情节单元或单一叙事单位,类型化的形象,象征化的喻象或原型。综合学者们的观点,我们在云南民族戏剧的角色类、背景类、事件类共享母题中分别选择拟兽、孝感、冥游进行论述。
拟兽。云南少数民族戏剧中,有很多扮演动物的仪式剧,王胜华称之为“拟兽戏剧”,展现的便是拟兽这一共享性戏剧母题。如楚雄彝族祭龙仪式中由专人扮演的“龙”,“老虎笙”中扮成老虎表演交尾、护儿、开路、盖房、烧荒、耕田、春播、秋收等内容,“小豹子笙”由男孩扮成小豹子并模仿其一举一动。大理白族有演“牛马剧”酬神的传统,据民国《乔后井历史杂志》记载,演马剧者脚踩高跷、头戴金盔、背插红旗,腰间系纸扎之马,演牛首者头戴牛首,演牛尾者身披牛衣。傣族则有扮演孔雀的戏剧。此类拟兽母题,在一些少数民族中与傩仪、傩戏相关,而傩戏曾经在中原地区同样广泛流行,云南现存的一些傩戏就是从中原传入的。云南少数民族戏剧中的拟兽母题,是各民族传统文化底色中尊崇动物、亲近自然生态观的反映。云南一些少数民族视动物为人类的兄弟、家人,认为二者本就应该和平共处。在有的民族那里,一些动物被视为始祖、图腾,是神圣性的存在。因而,拟兽戏剧母题的仪式性必然要高于娱乐性,扮演的目的在于践行仪式,通过仪式,建构起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和谐。

孝感。在云南民族戏剧中,有不少改编自二十四孝的剧目。佤族清戏《三孝记》又称《安安送米》,源自明传奇《跃鲤记》,情节围绕“孝”字展开,姜林广因孝遵母命休妻,其妻离家仍不忘孝敬婆母,其子安安虽年幼却深谙孝理送米接济母亲。腾冲花灯中也有此剧目。白族大本曲《赵五娘寻夫》源自《琵琶记》,描绘五娘吃糠割股孝养双亲的至孝行为。彝剧《董永大孝记》讲述七仙女因董永之孝而下凡搭救他。白族吹吹腔、傣剧、壮剧和彝族汉文古籍中都有的剧目《摇钱树》,述七仙女中的四姐感文瑞砍柴孝母之举而下凡与之结亲的故事。流传于花灯和傣、彝、白等民族中讲述目连故事的《目连大孝记》《傅罗白寻母》等剧目,将行孝与敬佛置于同等地位。总体上看,孝感母题的相关剧目多从汉地移植而来,但也要看到,孝道伦理在云南各民族中也有坚实的存在基础,此种社会人伦的共同情感在各民族戏剧中传播的时候最易引起共鸣。
冥游。该母题出现于云南民族的多个剧种剧目。前述的目连救母剧目,目连为救母亲“上穷碧落下黄泉”,游历地狱各殿。源自汉地又在傣族、白族、彝族中流传的《唐王游地府》,都描绘了唐王阴魂游历地狱的经过。富宁土戏《阴阳扇》中,冤死的翠英到了阴间向包公告状申冤,包公赐宝扇救她起死回生。白族大本曲《王素珍观灯》和《黄氏女对经》均涉及冥游母题。还有一些民族传统题材剧目亦出现此母题。取材于“两兄弟型”民间故事的彝剧《阿佐分家》,述阿佐兄弟二人游历阴间,看到惩恶扬善的种种情形,哥哥悔悟,两兄弟和好如初。此类母题总的功能是劝善教化,正如彝文《唐王记》引子所言:“皇帝唐天子,魂魄游地府,返回阳世来,心灵受洗涤。地府走一趟,阴间理和规,清楚又明了,呈现世人前。”
云南民族戏剧中的共享母题,既有源自少数民族传统的,也有来源于汉族地区的,不论哪种情况,置于整个中华文化的背景下,则可发现这些母题在各民族中具有一种通约性。那些与少数民族传统相关的母题,在汉族文化的原初底色中同样存在共通基础,而汉地传入的母题看似汉文化的影响比较突出,然实际上在少数民族中也存在接受基础和共同情感。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共享母题不仅体现着具体的族际交融,更体现着各民族共通的文化心理和情感根基。“各民族共有的本性,正是艺术跨族界交融的根源。”戏剧共享母题从文化深层和本源印证着多民族的艺术交融。
四、认同逻辑与达成路径:
云南多民族戏剧交融的中华文化认同功能
云南民族戏剧的交融是多层面、多维度、立体状的,既有族际“少数民族吸收汉族艺术、汉族吸收少数民族艺术、各少数民族艺术相互交融”这三大维度,也有族内族际贯通的复合式交融,即跨越纵向大小传统交融的族内界限,将交融延伸至族际。此种深度的交融,是各民族达成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
1、云南多民族戏剧交融的认同逻辑
云南多民族戏剧交融何以能够产生文化的认同和整合功能?或者说,认同的基础和逻辑是什么?这首先得要回到戏剧本身的功能当中去寻找。戏剧具有教化之功能,教化以认同为基础,戏剧在传导教化的同时,实现了文化的理解、凝聚和融通。云南多民族戏剧的交融则是对传统戏剧教化融通功能的实践、扩展和放大,让文化系统内部的大小传统融通跨越族际界限,延伸至更广阔的层面,搭建起多民族共享的知识谱系与文化传统。在中国的传统视野中,戏曲小说乃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是被排除在主流正统之外的。然而这样的戏曲,却深受民众喜爱,乃至上层主流亦不能忽略其存在,又或是主动地去运用和实现其教化之功能。因而戏曲逐渐成为一个特殊的中介符号,“中国戏曲总是处于‘雅的嫌俗,俗的嫌雅’的中间层次……是一种雅俗都可以接受的艺术”。学者在为戏曲正名、提升其文体地位的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宣扬戏曲的教化功能,让“曲关风化”“剧以载道”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教化的另一面就是认同,教化要真正实现,还需要得到民众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化和认同实为一体两面。各民族的戏剧与此类似。由此,戏剧自身的特点让其成为沟通大小传统的绝佳中介。
戏剧对大小传统分野的弥合,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其一是勾连口头与文字,使得分别代表社会文化系统中小传统和大传统的两端得以交融整合。以云南而言,各少数民族过去大多没有文字,有些虽有文字,但文字掌握在少数文化精英手中,使用范围狭窄,相对而言各民族中口头传统更为发达。而民间戏剧的剧目移植、创编多依赖掌握了文字的民间艺人,他们有的不仅通晓本民族文字,还掌握着汉字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字,故能运用汉字或者本民族文字来移植、书写剧本,又能从本民族丰厚的口头传统中汲取营养并纳入戏剧创作,戏剧交融的过程恰好让两种传统得以勾连。傣剧的剧本一般用傣文写作,剧目或从汉文作品移植,或从佛经、本族民间文学中改编,在口头与文字的结合中创造出自身的特色,如德宏傣剧中常出现的阿暖形象,既有佛教文化的影响,也有傣族传统文化的塑造,既有文字力量的积淀,也有口头传统的滋养,“当阿暖遇难时,步入观众席中,人们会自动为他捐钱捐物,把准备好的食物恭敬的送给他,以帮助他脱离困境”。这是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有机融合、文字形式和口头传统互渗传播的典型例证。彝文书写的彝剧传统剧目中同样融入了口头文学的内容,如楚雄彝族《大刀舞》里黑脸孟获的吞口有三只眼且中间一只是直眼,这显然是艺人们在创作时吸收了彝族创世史诗中直眼与横眼的传统母题。
其二是连接社会规训与民众理想,让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融通整合。戏剧有教化功能,而教化一词更多承载的是大传统对小传统的规训,然戏剧的教化与别的教化方式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戏剧自身的中间属性,它就像粘合剂或是润滑剂,让社会规训和民众理想之间有了契合的可能。戏剧的教化劝世并非空洞说教,而是融入具体的故事情节,融入鲜活的生活,由此,戏剧的教化劝世中也承载起民众的理想和愿望,寄托着民众的审美和期待。围绕戏剧生成了编剧、演剧、观剧、拟剧之间的共识,其中既有精英的观念,也有民间的情感,原本各属阵营的大小传统在戏剧构建的奇特时空中交织穿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彼此。
戏剧弥合大小传统的重要作用,其价值应予重估。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分野,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并举,都暗示着区隔的存在。此种区隔和互斥维持在一定范围内时,社会文化系统仍可稳定发展,但当这样的区隔超出了可控范围的时候,就会对社会文化的常规化运转和整体性发展带来冲击与破坏。戏剧让各以自我标准为标榜的两种文化形态间有了迂回、缓冲,让冲突和趋异的两端之间变得柔和,也具备了回归趋同的可能。精英文化和上层社会需要戏剧这样的形式来传导自己的规训标准,民间文化和下层社会也需要戏剧这样的中介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诉求。戏剧对大小传统的弥合,原本更多局限于同一文化系统内部,而云南戏剧因为增加了多民族交融这一维度,能够让大小传统的对话融通跨越族际,极大地拓展了此种交融的深度和广度,进而在族际的交融中凝聚并强化着共同体的意识。前述云南少数民族的民间艺人运用戏剧勾连口头和文字的时候,不仅借助本民族文字,也常常使用汉字,这实际上就是口头与文字的交融跨越族际界限的具体例证。再比如白族的吹吹腔和大本曲艺人,不光借用汉字来记录和书写剧本,甚至还自创出增删偏旁部首、重新组合汉字的“白文”,艺人们用此种汉白夹杂的文字或移植或改编汉地剧目,或将火烧松明楼、望夫云等传统故事纳入戏剧表演。傣族地区干崖土司衙门每年腊月十五封装土司大印,表示公务结束,来年正月二十再取出。开印时,要举行重大仪式并上演傣剧,《八仙过海》和《封侯挂印》是必演剧目。此中既有傣族地区大小传统的互渗,也可看到汉傣文化的交融,是上述两个面向的文化交融交叉共存的典型例证。
2、云南多民族戏剧交融的认同路径
在中华文化的长期发展历程中,汉文化作为主导力量,发挥了重要的凝聚整合作用。汉族文化在对少数民族施以影响的同时,也被少数民族主动接受和吸纳,成为更广阔的时空范围中各民族自觉靠拢的共享标准。久而久之,一种更具普泛性的认同标准在各民族之间得以构建,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基底。少数民族之间发生交流通常也会有主导的一方。从云南民族戏剧的角度而言,其族际交融和认同建构是从多个维度展开的,不论是给汉族戏剧输入新鲜血液,还是受汉族影响产生民族戏剧形式,或者是源自汉地的戏剧形式传播到少数民族当中并在时间的洗礼后逐渐被染上本土和民族的印记,又或是剧目、题材、母题、情节在不同民族中的互鉴和共享,都可让我们感受到流淌于其间的文化共性和认同意识。在这些多元的维度中,剧目移植、本土化、再经典化是一条比较突出和常用的路径。
剧目移植是第一步。排除一些偶然因素,移植更多基于选择和认同的逻辑。选择大多聚焦于经典剧目。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其本身已经历并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在多数人的选择和认同中所达成的,所以经典往往最契合人们的认同意识。输出一方将本族文化中的经典输出给另一民族,自然是基于对自我经典的强烈认同。接受一方主动将外来经典剧目移植进入自己的文化中,无疑更体现出对外来文化的高度认同。
移植后还要面对融入的考验。输出型移植中,接受一方对移植什么似乎没有选择的主动权,但剧目能否真正被接受,本土的力量就会显现出来。如果是接受一方的主动移植,则在选择移植对象之时业已为后来的融入铺垫了道路,当然,接受一方主动移植剧目的往往是民间艺人或地方精英,为了让剧目得到更广大民众的认可,作品同样要经受融入的考验。融入的有效方式是本土化,这又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在地化,将故事背景、时空等与本土的地理相联系,如本地地名的引入、将故事情节的发生地点具体化到当地某处之类;二是民族化,即在故事的情节内容中融入本族风俗,让剧目打上民族的烙印。很多时候,这两者也会结合在一起。融入和本土化最终又成就了云南民族戏剧的再经典化。再经典化指的是外来经典流传到某一民族之后融入了本土内容并成为当地民众公认的本族经典的过程。这是将移植的剧目本土化并且最终与本文化融通的结果,是对经典的接受和再次升华。这一过程本身充满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融,是在更高层面对外来经典和本我传统双重认同的整合贯通。如果说移植还只是源起于表层的认同,那么,融入和再经典化则已成为建构深层认同的途径和方式。以云南民族戏剧的汉少交融为例,那些首先被选择并充当着交流媒介的往往是汉地经典之作,而作品被移植到少数民族剧目中之后,借助本土化的改造,在剧目中加入具有当地民族特征的文化元素,并最终为民众接受认可,成为少数民族文化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标志性剧目,外来的经典终成本土之经典,这便是再经典化的结果。这方面梁祝剧目堪为典范。故事进入云南少数民族戏剧中后,通过本土化的改变,最终完成再经典化的形塑,成为各民族认可的自我之经典。傣剧里梁祝坐在芭蕉树下谈恋爱,这是本土地理风物的展现。白族戏剧中,梁祝同游苍山、本主庙中结拜、对歌唱曲,祝家的“三坊一照壁”式住宅,马家办喜事迎娶的风俗画面,无一不表现出强烈的白族特色。英台吊孝一节,融入了白族民间丧礼中流传至今的作祭文习俗。英台开药方是最具吸引力的情节之一,川剧、花鼓戏、鼓词、木鱼书等地方民间艺术中也有此情节,但白族民众对之进行了本土化的处理,药方的具体内容中加入了当地艺人的再创作。这些都表明,梁祝故事通过白族民众的改造,已经成为具有白族民众体温、情感的个性化叙事。广南沙戏中,把壮族喜爱对歌的特点移植到剧中人物身上,英台是一个壮家养鸭女,她与山伯对唱壮族山歌,充满壮乡风情。云南壮剧《梁祝》也有不少异于汉族的情节,如山伯去追赶英台,一路上遇见很多动物,山伯询问它们英台的情况,并根据动物是否配合为其命名或赋予习性特征,山伯碰见一只鸟,鸟回答他能撵上英台,山伯便高兴地给此鸟取名为“红嘴鸟”,现在云南还有这种鸟。山伯、英台死后,两人的坟被挖,墓碑变成两扇磨滚到山下仍合在一起,两扇磨被砸碎变出了一对对蝴蝶。富宁土戏中,梁祝死后变成一道彩虹或两扇石磨,石磨被马家砸烂后变成一个石碓嘴、一个石碓窝,意为永不分开。这里,墓碑变成两扇磨盘滚下来仍合在一起的情节,当吸取了云南少数民族洪水后兄妹婚神话里经典的滚磨盘母题,是颇具地方民族特色的新创造。
有关蓝季子的剧目同样是再经典化的典型。由于本土化色彩突出,再经典化的过程非常成功,以至于该剧目常被视为民族传统剧目。前面已述该剧目的汉地来源,当然,在进入云南少数民族戏剧中后,该剧也进行了大量本土化的改变,最终又成为独具各民族特色的少数民族剧目。比如,白族戏剧中增加了大量其他地区没有的独特情节,吹吹腔和大本曲将投军情节与平定白王之乱联系在一起,述中林、中秀打败白王,中秀还娶了白王之女白鹤公主为妻。除了常见的鸡血染衣、兄弟立功、救出嫂嫂等情节,白族戏剧中对火烧磨房情节描绘尤细,还加入了乔氏骂媳、季子羞母等精彩内容。剧中还借季子之口对大理地区的山水地理、风物景致进行了细致描绘,剧中的蓝季子、蓝中林甚至被一些白族村寨奉为本主,全剧融入了大量白族特有的生活和风俗。该剧目之所以一直被视为白族本土题材的代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再经典化的成功之处。
上述的移植、本土化和再经典化,既可以理解为是对外来文化的认可,也可以看作是对本土民族性的彰显,但更应被视为是外来与本土的族际融通。李世武指出,文化交流并非仅以“同化”方式存在,“交融”才是更合乎实际的描述,各民族在交流中存在“选择性接受、吸取外来文化中的部分元素并结合本土文化元素,开展文化创新,形成交融型新文化的大量案例”。云南民族戏剧的移植吸纳、本土化和再经典化诠释的就是文化交融的事实。
五、结 语
多民族戏剧交融及其中华文化认同功能研究,是我国戏剧界必须回答的重要理论问题。中国戏剧艺术发展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各民族戏剧交流、交融并共创、共享中华文化的历史。对其交融历程和文化认同功能的回答,有赖于宏观视野和个案深描的有机统一。围绕此议题,以云南为例展开讨论,可推动相关研究的范式创新。多民族戏剧交融及其中华文化认同功能研究,应从三大维度入手:从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语境出发,整体观照多民族戏剧交融的发生;从剧目互鉴与母题共享出发阐释多民族戏剧交融的本体;从认同逻辑和达成路径出发,分析多民族戏剧交融现象所具有的中华文化认同功能。
云南戏剧是在多民族戏剧交融过程中形成的地方戏剧,是我国多民族戏剧交融的区域性案例。多民族戏剧交融促进了多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并加强了多民族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云南多民族戏剧的交融特性,是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戏剧、中华艺术、中华文化的有力见证。云南戏剧中蕴含着多民族相互认同的理念和意识,具备心意相通的基础和事实,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各民族通过艺术交融“走向‘艺通族心’的美妙境界,在艺术世界中共筑共有精神家园,有力地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多民族统一的中华文化认同观,不能仅强调强势文化的地位,必须平等地看待各民族对中华文化形成和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云南多民族戏剧交融现象表明,各民族人民有能力、有信心创造出为各民族所共享的文化艺术。各民族戏剧界应加强交流、取长补短、互鉴融通,创造出更多的优秀戏剧作品,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力量。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图文来源:微信公众号“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21-12-05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