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上方“民俗学论坛”可订阅哦!

周作人的民俗书写
张伯存
原文载于《民俗研究》2022年第2期

摘 要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者,他一生的民俗书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普通民俗学,风土志、节令诗和竹枝词,民间文学,有关译介工作等的考察、研究和写作。他以现代思想者的眼光观照民俗、民间文学,其不少观点新颖独到,他的民俗书写中的人民性思想和对民俗文化三重功能的观点尤其值得关注。他的研究和书写具有一种高远的历史意识、宏阔的世界视野和清明的比较眼光。周作人对中国古代民间文学和现代民俗学的历史梳理体现出一种敏锐的史家眼光,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我国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关键词
周作人;民俗学;民间文学;学术史

现代思想家、散文家周作人(号“知堂”)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研究的先行者、开拓者,他一生写了300余篇民俗和民间文艺方面的文章,成果蔚为大观。1922年,周作人公开表示:“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在晚年总结其一生写作和研究的长文《我的杂学》中,周作人专辟一节谈他的民俗研究。1951年,周作人发表《风俗调查》一文,公开呼吁风俗调查“不可或缓”。他在一篇介绍风土志著作的文章中这样谈到写作意图:“我的本意实在是想引诱他们(引注:指青年读者),是的,我老实的说引诱,进到民俗研究方面去……从事于国民生活之史的研究,虽是寂寞的学问,却于中国有重大的意义。”由此可见他对民俗研究的重视和对后来者的期望。
本文分五节,前四节分别从通常意义上的一般性的民俗学、专题性的民俗学(风土志、节令诗和竹枝词)、民间文学、有关译介工作四个方面论述周作人在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和写作等领域所做的诸多学术贡献,第五节对前四节内容进行总结。


一
周作人从小就对民俗感兴趣:“最初见到一本不全的《岁时广记》,时常翻看,几乎有点不忍释手。后来得到日本翻刻本顾禄的《清嘉录》,这其间已有十多年之隔了,但是我的兴趣不但是依然如故,而且还可以说是有点儿增加。”早在1913年,周作人就在绍兴公开发表了名为《风俗调查二》的文章,叙录了五个越地风俗。1926年,周作人为其弟子江绍原的新著《发须爪》作序。1931年,周作人再为江绍原翻译的《英吉利谣俗》(即《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作序,他认为民俗学具有跨学科的价值和意义,将民俗学“归结到一种学说的时候,便侵入别的学科的范围,如信仰之于宗教学,习惯之于社会学,歌谣故事之于文学史等是也。民俗学的长处在于总集这些东西而同样地治理之,比各别的隔离的研究当更合理而且有效……民俗学的价值是无可疑的”。周作人在《<中国新年风俗志>序》中提到英国彭女士(Charlotte Sophia Burne)的《民俗学概论》(The Hand-book of Folklore)中有讲历及斋日、祭日的内容,他在该序言中褒扬娄子匡的书是“集录各地方的风俗以便比较的书物……可以说是空前的工作,这在荒地里下了一铲子了”。
周作人对送灶、爆竹、七夕、扫墓等民俗均作过考察。其《关于送灶》一文征引冯应京《月令广义》、刘侗《帝京景物略》、英廉等《钦定日下旧闻考》、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震钧《天咫偶闻》、让廉《京都风俗志》等关于明清时北京送灶习俗的记载;引用《武林新年杂咏》、顾禄《清嘉录》、厉秀芳《真州竹枝词》、无名氏《韵鹤轩杂著》《笔谈》中记录的苏州、杭州、绍兴等地送灶风俗,比较与北京的异同。他又引顾张思《土风录》、苏东坡《纵笔》、范石湖《祭灶》中关于送灶所供食物的说法,还以《通俗编》《五经通义》《酉阳杂俎》来考证灶神姓氏。关于灶的制式,他先从明器考证,在罗氏《明器图录》、滨田氏《古明器图说》中检索到所载汉代样式,又在汪辉祖《善俗书》、李光庭《乡言解颐》中翻检到炊灶样式的记载。
对于放爆竹(花炮、鞭炮、炮仗)这一民俗,周作人尤其感兴趣,他数十年里写过6篇这一题材的文章,在感情、认识上也有变化、变迁。《七夕》一文是关于七夕风俗的,通篇以引文连缀成篇,所引古籍有:《订讹类编》《淮南子》《荆楚岁时记》《风土记》《岁时广记》《学林》《艺苑雌黄》《拟天问》《越谚》《复堂日记补录》及杜甫诗句,他通过研究古书得出以下观点:“略阅所征引杂书,似七夕之祭以唐宋时为最盛,以后则行事渐微而以传说为主矣。”而他对故乡七夕风俗的观察是:“吾乡无七夕之称,只云七月七,是日妇女取木槿叶揉汁洗发,儿童汲井水置露天,次日投针水面,映日视其影以为占卜,曰丢巧针。”
其文《扫墓》引张岱《陶庵梦忆》、刘侗《帝京景物略》、顾禄《清嘉录》、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所录之明清扫墓习俗。《结缘豆》一文引范寅《越谚》、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刘玉书《长谈》谈结缘的风俗。周作人《记嫁鼠词》以《天花乱坠》二集卷五中的一条小引谈“鼠嫁”:“《虞城志》正月十七夜民间禁灯,以便鼠嫁。”作者情动于衷地写道:“鼠嫁女也是有趣的民间俗信,小时候曾见有花纸画此情景,很受小儿女的欢迎,不知现今还有否也。”
在写于1950年的《看笔记》一文中,周作人自云很喜欢看古人笔记,但“总觉得有一种不满意的地方,即是关于名物与风俗这两部门,古今来注意纪录的人实在太少了”。因此,他发出呼吁:“此后写笔记的人希望能各尽所能,把自己所最了解,最有兴趣的东西,不论雅俗巨细,详加记述,保留其真相,目下虽若无聊,百十年后便是难得的资料……若关于已将遗忘的习俗事物,则随时记录,自属更是要紧了。”他的《关于祭规》全文基本抄录萧山汪氏嘉庆七年(1802)刊《大宗祠祭规》和山阴平氏约光绪十六年(1890)手写稿本《瀫祭值年祭簿》中关于除夕、元旦、清明扫墓时家族祭祀的祭规,就是有意识地辑录民俗学史料,是研究清代浙江祭祀风俗的上佳材料。他留意到乾隆年间金德舆编、方兰坻绘《太平欢乐图》,“自太平箫以至年画,凡一百种职业。金方二人都是浙西人,所以可以看见百七十年前江浙民间的风俗一斑,也是很有意思的事”。周作人谈风俗的文章还有《风俗的记录》《风俗的记载》《风俗调查》《闲话风俗》《占验与风俗》等30余篇,此不赘述。
下面论述周作人关于民间信仰和鬼怪精灵的文章。他有如下一种总的看法:“我们可以看出野蛮思想怎样根深蒂固地隐伏在现代生活里……海面的波浪是在走动,海底的水却千年如故。把这底下的情形调查一番,看中国民间信仰思想到底是怎样,我想这倒不是一件徒然的事。”周作人在《关于祭神迎会》中认为,从“祭神迎会的习俗,可以明了中国民众对神明的态度,这或可以说礼有余而情不足的……中国人民之于鬼神正以官长相待,供张迎送,尽其恭敬,终各别去,洒然无复关系,故祭祀迎赛之事亦只是一种礼节,与别国的宗教仪式盖迥不相同”,“中国人是人间主义者,以为神亦是为人生而存在者”。此为不刊之论,后来者多沿袭其说。
周作人还有一个重要观点,他认为以张天师为教主、以道士们做祭司的民间道教对中国老百姓影响很大。《张天翁》《关于雷公》《乡村与道教思想》等篇目尤为关注作为民间宗教的道教,这也是周作人在思想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洞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长文《无生老母的信息》,此文先是对总称“道教”的民间宗教内各种分支教派的名称、立教传道的源流年代以及传教书的刊刻情况等方面加以梳理、考订、引证,然后将考察重点转向立教最早的红阳教,引出它的“八字真言”:“真空家乡,无生父母”。他由此展开以下论述:“大概人类根本的信仰是母神崇拜,无论她是土神谷神,或是水神山神,以至转为人间的母子神,古今来一直为民众的信仰的对象。客观的说,母性的神秘是永远的,在主观的一面人们对于母亲的爱总有一种追慕,虽然是非意识的也常以早离母怀为遗恨,隐约有回去的愿望随时表现……也可以说即是归乡或云还元。”他体察、理解了劳苦大众寻找安生之地的悲悯情怀和非理性背后的人性人情,文章最后,作者又四方搜索,几番抄引,研究民间宗教与戏曲的关系。
他认为民间信仰习俗是一种野蛮时代的遗留,反映了人类共通的情感:“民间的习俗大抵本于精灵信仰(Animism),在事实上于文化发展颇有障害,但从艺术上平心静气的看去,我们能够于怪异的传说的里面瞥见人类共通的悲哀或恐怖,不是无意义的事情。”周作人写了不少谈鬼的文章,因为他有个观点:“我常觉得中国人民的感情与思想集中于鬼,日本则集中于神,故欲了解中国须得研究礼俗,了解日本须得研究宗教。”他在《谈鬼论》中说对鬼故事的兴趣着眼于两方面原因:一是文学的,是简洁有力的好文章;二是民俗学上的兴味。其《水里的东西》说的是水乡的“河水鬼”信仰和禁忌,文末道:“河水鬼大可不谈,但是河水鬼的信仰以及有这信仰的人却是值得注意的……社会人类学与民俗学是这一角落的明灯,不过在中国自然还不发达,也还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发达。我愿意使河水鬼来做个先锋,引起大家对于这方面的调查与研究之兴趣。”周作人《说鬼》一文有如下观点:“我们喜欢知道鬼的情状与生活,从文献从风俗上各方面去搜求,为的可以了解一点平常不易知道的人情,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鬼里边的人。反过来说,则人间的鬼怪伎俩也值得注意,为的可以认识人里边的鬼吧。”“鬼里边的人”,是人情人性;“人里边的鬼”,是人的丑恶、阴暗一面,二者有种辩证关系存焉。他的《读<鬼神论>》专门从清代钱绮所著的《钝砚卮言》中挑出一篇《鬼神论》,认为其“娓娓千三百言,情理两备,为不可多得之作”。他认为对鬼神问题须留意考察,“因其中盖有人心的机微存在也”。其《鬼的生长》从古籍中检索、考据关于鬼生长的材料,先后征引了纪昀《如是我闻》、邵伯温《闻见录》、俞樾《茶香室三钞》和钱鹤岑《望杏楼志痛编补》等古籍中的若干记载。《刘青园<常谈>》一篇,对清代阮元《广陵诗事》和刘玉书《常谈》中写鬼的内容褒贬分明,认为前者迂腐,后者明达。此外,周作人谈鬼的文章还有《说鬼》《溺鬼》《虐鬼》《变鬼人》《花煞》等10余篇。作者坦言其实说鬼的文章并不好写,“问题固然是不好搞,但是主要的原因却也是因为材料实在是难得,这些材料全都是散在古今的杂书里,第一要有闲工夫来杂乱的看书,才能一点点的聚集起来,第二是要有这许多书籍,这却是一件难事”。周作人写此类文章甘苦自知。


二
在中国古代记某地风土志、岁时节令风物的著述中,周作人看重晋代《南方草木状》、唐代《北户录》《岭表录异》,以及关于《诗经》《楚辞》《尔雅》的名物笺注;还有逸民遗老追怀往昔光景的笔记,他推崇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的《梦粱录》、明代张岱《陶庵梦忆》以及不知撰者的《如梦录》等;此外是本地人写本地的各类著述,如明代《帝京景物略》,清代《日下旧闻考》《天咫偶闻》《燕京岁时记》以及近代的《旧京琐记》,他都非常欣赏。
清人富察敦崇(号“铁狮道人”)的《燕京岁时记》,是周作人一直喜欢的书籍之一。他对之评价颇高,认为该书“文颇质朴”,且“其风俗与物产两门颇多出色的纪述,而其佳处大抵在不经意的地方”。该书1935年有英译本,随后不久有日文译本,名《北京年中行事记》,周作人以《关于<燕京岁时记>译本》为题著文评价。周作人对清末抄本闲园鞠农的《一岁货声》赞赏有加,该书记录北京一年里各种叫卖的词句和声音,他曾“手录一过”并撰文推荐:“著者自序称可以辨乡味,知勤苦,纪风土,存节令,此言真实不虚,若更为补充一句,则当云可以察知民间生活之一斑……我读这本小书,深深的感到北京生活的风趣,因为这是平民生活所以当然没有什么富丽,但是却也不寒伧,自有其一种丰厚温润的空气。”1950年,他在《诗里的市声》一文中,再次评价该书“是民俗研究上很有价值的书”。他在评文昭的诗集《紫幢轩诗》的末尾写道:“昔日读闲园鞠农之《一岁货声》,铁狮道人之《燕京岁时记》,心正喜之,其爱景光识名物之意有相同者,今在紫幢轩亦得见一斑,此数人者可谓不俗者矣。”他的脍炙人口的散文随笔《北京的茶食》《北平的春天》《北平的好坏》《立春以前》等可看作是在前人基础上对北京岁时风物的续写。
关于两广风物的著述,周作人最欣赏明遗民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他从中读出了明遗民的郁愤不平之气:“就是在这记风物的书中,著者也时时露出感愤之气。”他还著文评价了陈坤的《岭南杂事诗抄》,他认为上述两部书加上李调元辑《南越笔记》和古代《南方草木状》《北户录》《岭表录异》,表明两广乡土风物之书“著述不绝”,源流有序,而闽、蜀次之。
下面重点评述周作人对绍兴风俗的考察和他的《儿童杂事诗》对绍兴岁时节令风俗的表现。
周作人因“乡曲之见”搜集了不少同乡人写山阴会稽的诗文集,如陶元藻的《广会稽风俗赋》、李寿朋的《越中名胜赋》、周晋铢的《越中百咏》、周调梅的《越咏》、张桂臣的《越中名胜百咏》、孔延之的《会稽掇英集》、王十朋的《会稽三赋》各注本、陈祖昭的《鉴湖棹歌》等。他以《三部乡土诗》为题评价了《娱园诗存》《鞍村杂咏》《墟中十八图图咏》。同乡、清末胡梅仙著诗集《洗斋病学草》带有乡土色彩,周作人撰文推介。他尤其看重同乡先贤范寅编著的《越谚》,它是一部关于越地(绍兴)方言俚语、风俗名物、民歌童谣等内容的书,成书于光绪四年(1878),在民俗学、语言学方面有重要研究价值。1932年,《越谚》重刊,周作人作《<越谚>跋》一文附后,推崇备至。
周作人用心寻觅清人的儿童诗。清代蔡云诗集《吴歈百绝》共收诗作26首,内容是关于苏州四时的,周作人文中引用一首关于压岁钱的诗,并评点道:“写新年风俗,兼及儿童生活,殊有情致。”清代高凤翰的《南阜诗集》里有数首儿童诗,他觉得“很难得”,《宾退录》卷六有路德延的《孩儿诗五十韵》也获得他的首肯,他从寅半生编《天花乱坠二集》中找到一首儿童诗,推崇说是“百年内难得见的佳作”。他还从陈授衣著《孟晋斋诗集》中翻检出几首表现儿童生活主题的诗。可以看出,周作人遍翻藏书,孜孜以求前朝诗人骚客的儿童诗,从中撷取养分,周作人撰《儿童杂事诗》72首有个长期的准备过程,受到上述诸家的启发和影响,是一种文脉的赓续。
1933年,他在《<谈岁时风俗的记载>前言》中写道:“这篇东西,是在二十一年的初秋写成的,本打算是作儿童的论文的,后来,在写的时候,却忘了把儿童二字加进;自然,在外表面看起来,这并不是儿童的论文,其实,岁时风俗的记载,与儿童本身问题,也有极大的关系,儿童们也应当注意岁时与风俗。”这对理解他的《儿童杂事诗》不无裨益。周作人《儿童杂事诗》是儿童诗,但又不是单纯的儿童诗,它们是儿童诗、岁时节令诗和故乡风土诗的综合体。下面就结合有关资料对他的《儿童杂事诗》中涉及的清末民初绍兴一带的民风民俗作一番研究考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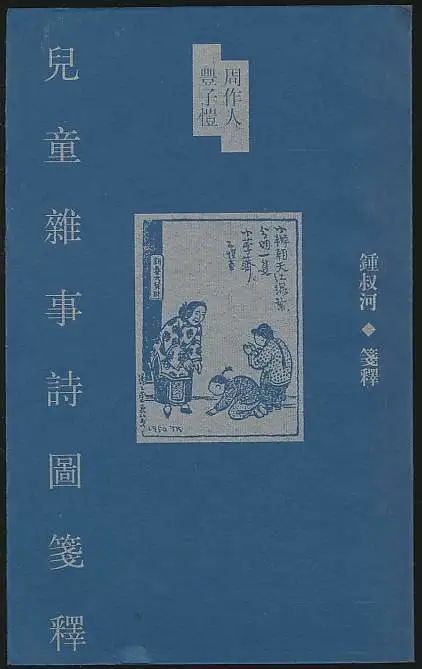
丰子恺插图版《儿童杂事诗》
周作人的《儿童杂事诗》共三卷,分为甲编儿童生活诗,乙编儿童故事诗,丙编儿童生活诗补,各24首,共计72首,写于20世纪40年代末,连载发表于1950年上海《亦报》。周作人在《儿童杂事诗·序》中表明“甲编以岁时为纲”,而乙编以历史人物为题材。本文以甲编为主,兼及丙编论之。周作人在“甲编附记”中说:“儿童生活诗,实亦即是竹枝词,须有岁时及地方作背景,今就平生最熟习的民俗中取材,自多偏于越地,亦正是不得已也。”甲编儿童诗以岁时为序,写到春节、上元、清明、端午、立夏、中元、中秋等时节绍兴一带的民风习俗,下面分述之。

第一首《新年》:“新年拜岁换新衣,白袜花鞋样样齐。小辫朝天红线扎,分明一只小荸荠。”“拜岁”(拜年)是我国古老的风俗,大概在南北朝时就有了,而越地拜岁与别处又有不同,据鲁迅堂叔周冠五对绍兴民俗的记载:“先向天地神祃行过礼,次财神,次张神,再次灶神,最后拜祖宗的悬像,依次拜毕,家庭间自长辈起由大而小地分别拜岁。”周作人此诗通过儿童向长辈跪拜贺新年时的情景及独特发式写出了儿童的天真可爱,“小辫朝天”发式,北方称“朝天杆”,绍兴称“小荸荠”,取江南水乡名物比拟,似更形象有趣。
《新年二》是关于“压岁钱”的:“昨夜新收压岁钱,板方一百枕头边。大街玩具商量买,先要金鱼三脚蟾。”金鱼、三脚蟾是用火漆做成的玩具,后者是一种传说中的动物。鲁迅在散文《阿长与<山海经>》中也写到少时拿到压岁钱的情景和憧憬。
《新年三》诗如下:“下乡作客拜新年,半日猴儿着小冠。待得归舟双桨动,打开帽盒吃桃缠。”周作人《拜年看游记》可为“猴儿着小冠”作注解:“小时候往亲戚家拜年……照例要戴胡人的红缨帽,装在皮帽盒里。”“胡人的红缨帽”指的是清朝时流行的带红缨的礼帽,即诗中的“小冠”,“猴儿”则是对顽皮好动的小孩的谑称,此诗句可想象小孩端坐的窘态,令人联想到“沐猴而冠”。诗中所言“帽盒”是一种点心盒,“桃缠”是核桃缠的简称,为当地的一种点心,其他如松仁缠等。
《上元》诗曰:“上元设供蜡高烧,堂屋光明胜早朝。买得鸡灯无用处,厨房去看煮元宵。”农历正月十五为上元,通称元宵节,以赏灯观灯吃元宵为主题。所谓“鸡灯”,以竹篾扎成,外糊彩纸,中置蜡烛,酷似鸡的形状。绍兴的上元灯火自古有名,宋朝《嘉泰会稽志》就有记载,《陶庵梦忆》中对“为海内所夸”的绍兴灯景和放灯盛事亦有极尽渲染之描绘。
甲之六《上学》诗:“龙灯蟹鹞去迢迢,关进书房耐寂寥。盼到清明三月节,上坟船里看姣姣。”作者诗后注曰:“儿童歌云:正月灯,二月鹞,三月上坟船里看姣姣。”此诗写出小孩对清明节去郊外上坟,自由亲近大自然的期盼,它其实和下面的三首《扫墓》是一个主题。周作人在《上坟船》《山头的花木》《看姣姣的来源》等文中一再写到绍兴上坟习俗和这首儿歌。
诗《扫墓一》:“扫墓归来日未迟,南门门外雨如丝。烧鹅吃过闲无事,绕遍坟头数百狮。”此诗写坐船去城外扫墓归来,中途停泊吃上坟酒的情形,这是绍兴水乡独特的风俗。《扫墓二》歌咏牛郎花、草紫(即紫云英)、映山红(即杜鹃花)这三种野花,诗末句“船头满载映山红”是“上坟船”的证据。周作人《故乡的野菜》中也写到当地扫墓习俗:“浙东扫墓用鼓吹,所以少年常随了乐音去看‘上坟船里的姣姣’;没有钱的人家虽没有鼓吹,但是船头上篷窗下总露出些紫云英和杜鹃的花束,这也就是上坟船的确实的证据了。”《扫墓三》诗中提到绍兴当地一种代步的交通工具“兜子轿”。
《立夏》诗如下:“新装扛秤好秤人,却喜今年重几斤。吃过一株健脚笋,更加蹦跳有精神。”周作人注曰:“立夏日秤人,以防蛀夏。是日以淡笋纳柴火中烧熟,去壳食尽一株,名曰健脚笋。”而“蛀夏”一说,概因酷暑炎热,胃口不佳,身体不健,精神不旺,如树木之为虫蛀,通常有“苦夏”的说法,但“蛀夏”更形象。吃“健脚笋”来“防蛀夏”,大略是绍兴人对身体安康的美好祈愿吧。
《端午》诗曰:“端午须当吃五黄,枇杷石首得新尝。黄瓜好配黄梅子,更有雄黄烧酒香。”这首诗专咏绍兴端午吃食,“端午须当吃五黄”是绍兴人的风俗,“五黄”指五种名字或颜色带黄的食品,从诗中看是枇杷、石首(即黄鱼、黄花鱼)、黄瓜、黄梅、雄黄酒。周冠五记忆中的“五黄”,则由黄鳝取代枇杷。《端午二》:“蒲剑艾旗忙半日,分来香袋与香球。雄黄额上书王字,喜听人称老虎头。”周冠五《绍兴的风俗习尚》关于端午习俗记载较详,节录以作注解:“用雄黄在每个小孩头上写一‘王’字,并涂耳孔,门窗、床铺遍插艾叶、菖蒲,用苍术、白芷等药物做气味浓厚的蚊烟堆,门上贴张天师和道士送来的符,另外还在黄纸上用雄黄写‘姜太公神位在此诸邪回避’。”小孩额头写上“王”字象征“老虎头”,寓意威猛无比,并用以辟邪。
《中元》诗如下:“中元鬼节款精灵,莲叶莲华幻作灯。明日虽扔今日点,满街望去碧澄澄。”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为民间祭祀先人的节日,周作人《丁亥暑中杂诗》中的一首五言古诗也题作《中元》,细腻描绘了“款精灵”和点“莲花灯”的情景。
甲编最后一首诗《中秋》:“红烛高香供月华,如盘月饼配南瓜。虽然惯吃红绫饼,却爱神前素夹沙。”“素夹沙”即是素油制作的豆沙月饼。周作人文章《中秋的月亮》描述拜月风俗及传说较详。绍兴中秋拜月,女拜男不拜。
此卷《儿童生活诗》的内容,以节日为节点“歌咏岁时一段落”,如新年、上元、清明、端午、立夏、中秋等;或描写“年中行事”如上学、扫墓、驱蚊、捉蟋蟀等,取材于作者儿时在绍兴的生活记忆,其情可感,正是:“语及旧风俗,情意多能喻。怀念乡村人,东望徒延伫。”
《儿童杂事诗》甲编《儿童生活诗》有数首是关于名物的,如:麻花粥、茯苓糕、虾壳笋头汤、乌皮香瓜、蒲瓜、呃杀瓜、驼背白(一种四角菱)。丙编写名物甚多,有6首写果饵,如糕团、夜糖、石花等,2首写玩具,5首写虫鸟,3首写花纸(年画)。还有3首写故事,3首写歌谣,兹不赘述。
周作人《儿童生活诗》里所歌咏的民间风俗距今已百余年,有的已消逝无踪,有的发生变化,有的依然流行着,当然,有的风俗也不仅限于“越地”,但它们无疑在民俗史和文化史意义上是有价值的资料。周作人1950年发表的文章《儿童诗与补遗》(手稿题为《儿童杂事诗代跋》)末尾写道:“文化建设的高潮中,民俗学自然也占一个地位,这种资料都是必要的而且有价值的。”
但是,周作人《儿童杂事诗》的价值不仅是提供了民俗学的材料,它的独特价值在于是以诗的形式写风俗,是一种“风土诗”。诚如上文周作人在“甲编附记”中说:“儿童生活诗,实亦即是竹枝词。”他为何有这种说法?他在竹枝词的搜集、整理、编辑、研究上花过大力气,曾编辑一部竹枝词集,可惜没有出版,关于编辑动机,他说:“散文的地理杂记太多了,暂且从缓,今先从韵文部分下手,将竹枝词等分类编订成册,所记是风土,而又是诗,或者以此二重原因,可以多得读者,但此亦未可必,姑以是为编者之一向情愿的希望可也。”他写的序文性质的《关于竹枝词》其实可当作这方面的论文来看。他认为竹枝词古已有之,唐朝诗人刘禹锡拟巴蜀俗歌作竹枝词11首,收在诗集乐府类内,才广为人知。“七言四句,歌咏风俗人情,稍涉俳调者,乃是竹枝正宗。”后来引申开来,题材渐广,宋元明历代诗人均有歌咏,清初朱彝尊的《鸳鸯湖棹歌》开始使竹枝词盛行于世,此后作者甚多,有谭舟石、陆和仲、张芑堂、纪晓岚、蔡铁耕、厉惕斋、黄公度等。他们这一类的诗集,“其性质则专咏古迹名胜,风俗方物,或年中行事,亦或有歌咏岁时之一段落如新年,社会之一方面如市肆或乐户情事者,但总而言之可合称之为风土诗,其以诗为乘,以史地民俗的资料为载,则固无不同”。周作人此文将竹枝词的历史流变、诗体性质和文化历史价值提纲挈领地概括出来。清人李于潢的两卷《汴宋竹枝词》录诗百首,周作人在评该诗集的文章中写道:“竹枝词以志民俗风物,又事属汴京,作者对于风土之变不能无深恫。”他还编订了《北京竹枝词集》,其文《北京的风俗诗》大概是该集子的序文,不过换一个角度从它的诗体风格、艺术特色方面立论,谈竹枝词的艺术性。他认为,风俗诗须“加点滑稽味,即漫画法是也……须得有诙谐的风趣贯串其中,这才辛辣而仍有点蜜味”。其《儿童杂事诗》庶几近之。
由此看来,周作人将《儿童杂事诗》看作是竹枝词,是有明确的、自觉的诗体意识的,他赓续了中国源远流长的竹枝词传统。不仅如此,他还借鉴英国诗人利亚(Lear)的诙谐诗和日本一种特有的兼具讽刺和风俗的十七字短诗体“川柳”,写出“别有一种味道”的《儿童杂事诗》。他的《儿童杂事诗》蕴涵博大的人情、浓郁的乡情以及对儿童深情的爱意,充满谐趣、童趣、意趣,是一种谐诗的风格,妙语天成,生意盎然,有如天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无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是民俗学史上,能写出既具有不俗的民俗学价值又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的现代竹枝词(风俗诗)的,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人吧。周作人《儿童杂事诗》的价值就在这里。



三
周作人于1911年从日本回到绍兴,他最初的计划是从鲁迅购买的《古谣谚》中抄录所有古来关于童谣的言论,编为一卷集说,作为参考资料,但这项工作繁重、繁琐,实施起来难度很大,他便调整计划,只就范寅的《越谚》里所收的歌谣辑录下来,作为参考资料。同时,他开始独自收集当地儿歌,共收集儿歌200首左右,1913年1月着手编辑整理,将所编集子定名为《越中儿歌集》。1914年1月,周作人在绍兴公开刊登征集儿歌、童话启事,拟“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但到年底只收到一件投稿。鲁迅特别支持周作人收集歌谣,时任职于北京教育部的他从友人处听了些地方儿歌,抄录下来寄给周作人作参考。1936年,周作人将早年搜集的绍兴儿歌整理出来,题名《绍兴儿歌述略》准备出版,并将写好的序言先行公开发表,但“七七事变”爆发使之功亏一篑。
1958年4月,周作人将旧稿本重新整理,定名《绍兴儿歌集》,他在写就的《小引》里说:“前年有友人劝我,乘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把它编出来,也可以做一种纪念,因为里边的歌谣都是鲁迅所熟知的,有的是他儿时所唱过的,这是很值得做的工作……现在只能因陋就简的加以整理,姑且把它编印出来,以供读者的参考,此外也别无奢望了。”改写的《绍兴儿歌集》“于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五日卒业,民间文学研究会友虽颇见赏识,唯因其时正在大搞新民歌,此种旧儿歌暂不能出版,有同乡友人问过东海出版社,亦是同样结果,以是原稿尚高搁架上也”。周作人数十年念兹在兹,此集命运多舛,惜生前身后均未正式出版,只是在20世纪50年代抄录两首在《民间文学》发表,直至2004年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影印出版毛笔手写稿本。该稿本收录的大量童谣不仅具有资料文献价值,而且,其“集说”部分,辑录《左转》《正义》《列子》《晋书》《三国志》《论衡》《魏书》《抱朴子》《全唐文》等典籍中有关童谣的各家各说;“集释”部分从《孟子》中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起首,历朝历代下来,直到清末民初童谣。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中国童谣(儿歌)史”的框架结构。
1914年,周作人撰写《儿歌之研究》,或许是现代中国最早的研究儿歌、童谣的论文。该文立意高远,气象阔大,征引历代典籍,梳理童谣文脉,认为“依民俗学,以童歌与民歌比量,而得探知诗之起源,与艺术之在人生相维若何,犹从童话而知小说原始,为文史家所不废”;在教育方面,“幼稚教育务在顺应自然,助其发达,歌谣游戏为之主课……儿歌之用,亦无非应儿童身心发达之度,以满足其喜音多语之性而已”。1923年,他在《读<童谣大观>》一文中指出,童谣研究者大致可分为“民俗学的”“教育的”“文艺的”这三派。他认为时人编辑出版的《童谣大观》观念陈旧,编辑粗糙。周作人多次在文章中表达了童谣(歌谣)须本真、自然、质朴的特质,反对文人进行雅化、删改等处理。清代郑扶羲的《天籁集》一集收录儿歌48首,二集23首,是周作人在东京留学时买到的,他后来撰文评价:“集中所录皆是江浙间通行童谣,什九与现今相同,可知是诚实的集录,未经文人加点,故可贵也。”以“天籁”为题,编者的态度和倾向不言自明。时隔七年后,周作人又以《小孩的歌》为题再次撰文褒扬,他认为“儿童的诗,也即是诗的祖宗”,“从旧的那边说,岂不是很有《国风》《乐府》杜子美白乐天之风么?从新的那边来看,新诗有没有这样的力量,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评价不可谓不高。周作人写童谣的文章另外还有《螺蛳经》《吕坤的<演小儿语>》《读<各省童谣集>》等。周作人认为:“歌谣的研究与神话传说一样有好几方面。这都是有长远的历史而现在流传于民间的,所以具有一种特异的性质,即是,他可以说是原始文学的遗迹,也是现代民众文学的一部分;我们可以从那里去考查余留着的蛮风古俗,一面也可看出民间儿女的心情,家庭社会中种种情状,作风俗调查的资料。”他在为刘半农编译的《海外民歌》作的序中表示:“我平常颇喜欢读民歌。这是代表民族的心情的,有一种浑融清澈的地方。”
1918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论歌谣事———致半农》,考证一首庚子歌谣,文末云:“考查此类歌谣变迁之迹,足为研究历史上童谣起源者添一例证,甚可喜也。”1919年,周作人为刘半农搜集的民歌《江阴船歌》写序,题为《中国民歌的价值》,他在概论中国民歌类型、特质、题材和中心思想之后,指出:“我们所要的是‘民歌’,是民俗研究的资料,不是纯粹的抒情或教训诗,所以无论如何粗鄙,都要收集保存。半农这一卷的《江阴船歌》,分量虽少,却是中国民歌的学术的采集上第一次的成绩。我们欣幸他的成功,还要希望此后多有这种撰述发表,使我们能够知道‘社会之柱’的民众的心情,这益处是溥遍的,不限于研究室的一角的。”这一认识在当时是超前与高远的。
1918年2月,周作人与刘半农、沈尹默等一起征集歌谣,至1919年底,已征集1700余首。1920年,周作人与沈兼士、钱玄同等在北京大学发起歌谣研究会,征求会员,由他执笔撰写《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启事》。周作人1922年发表的《歌谣》一文可看作一篇歌谣(民歌)研究论纲,他首先对“歌谣”作了界说,认为要从文艺和历史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历史的研究一方面,大抵是属于民俗学的,便是从民歌里去考见国民的思想,风俗与迷信等”,并进一步将民歌按照体裁内容分为六个大类:情歌、生活歌、滑稽歌、叙事歌、仪式歌、儿歌,儿歌又分为事物歌和游戏歌。1922年,周作人和同仁创办《歌谣》周刊,他在《<歌谣>发刊词》中写道:“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他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因此我们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别,尽量的录寄,因为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这种工作不仅是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
周作人在民歌搜集方面考虑既全面又长远,并透露出他开放、现代的歌谣观,他次年在《猥亵的歌谣》一文中又专门阐述他对“卑猥”“粗鄙”“猥亵”一类歌谣的看法。1925年,他在《征求猥亵的歌谣启》一文中再次发表新观点:“我们相信这实在是后来优美的情诗的根苗……从这些歌谣变为情歌,再加纯化而为美人香草的文词,这个痕迹大略还可以看出来。其次,我们想从这里窥测中国民众的性的心理,看他们(也就是咱们)对于两性关系有怎样的意见与趣味。”至1924年,歌谣研究会已搜集到八千多首各种歌谣,但限于经费和人力不足,无法进行研究;研究会还议定另行征集神话、传说、童话等。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成员刘经庵采集、编辑的《歌谣与妇女》出版,周作人为之写序时指出:“这是一部歌谣选集,但也是一部妇女生活诗史。”他还为林培庐编的《潮州畲歌集》作序,为刘半农翻译的《海外民歌》作序。顾颉刚、钟敬文、常维钧、白启明等都各自完成了个人辑录的地方歌谣集。1936年,歌谣研究会改称“歌谣整理会”,编辑者改为北大女毕业生徐芳。
20世纪30年代,朱瑞轩重刊明代冯梦龙编《山歌》,周作人题写书名,并作长跋,他在跋中写道:“《山歌》十卷中所收的全是民间俗歌,虽然长短略有不同,这在俗文学与民俗学的研究上是极有价值的。中国歌谣研究的历史还不到二十年,搜集资料常有已经晚了之惧,前代不曾有一总集遗传下来,甚是恨事,现在得到这部天崇时代的民歌集,真是望外之喜了。”周作人《歌谣与名物》一文,起首引用日本人北原白秋著《日本童谣讲话》中的一章,然后从《本草纲目》、扬子云的《方言》、小野兰山著《本草纲目启蒙》、川口孙治郎著《日本鸟类生态学资料》抄录有关资料,考察一种叫“水胡卢”的鸟的名称、特征、习性。他此文的主要观点是:“辑录歌谣似是容易事,其实有好些处要别的帮助,如方言调查、名物考证等皆是,盖此数者本是民俗学范围内的东西,相互的有不可分的关系者也。”周作人有关歌谣的文章还有《河南民歌》《从猥亵的歌谣谈起》等,兹不赘述。
周作人对另一民间文学形式———笑话也很关注。1924年,周作人写了《徐文长的故事》一文,共8个小故事。他在《小引》中提道:“儿时听乡人讲徐文长故事,觉得颇有趣味,久想记录下来。”在文后“说明”中,他又道:“我的意思是在‘正经地’介绍老百姓的笑话,我不好替他们代为‘斧政’。他们的粗俗不雅至少还是壮健的,与早熟或老衰的那种病的佻荡不同……这是我所以觉得还有价值的地方。”虽说此文是“来料加工”,保留了原初的故事情节,但周作人以他独具面目的语言、腔调、用词叙述出来。1933年,周作人从《笑府》《笑倒》《笑得好》三部古代笑话集中取材,编辑出版了《苦茶庵笑话选》,他的序言《笑话论》是一篇关于笑话的论文,就中国笑话历史演变、价值、内容等方面展开论述,是这一领域不可多得的研究成果,他指出:“与歌谣故事谚语相同,笑话是人民所感的表示,凡生活情形,风土习惯,性情好恶,皆自然流露,而尤为直截彻透,此正是民俗学中第三类的好资料也。”他还两次著文评价明代赵南星的笑话集《笑赞》。周作人1956年编订的《明清笑话四种》,195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除上文三种外还收入了《笑赞》。他的《引言》其实是一篇中国笑话史论,他认为先秦《孟子》《韩非子》、汉魏《百喻经》、《隋书·经籍志》、唐李商隐《杂纂》、宋王君玉《杂纂续》、苏东坡《杂纂二续》,以及明清的三续、四续、新续和顾禄《广杂纂》中有大量的笑话,可谓涉猎颇广,用功甚深,独具只眼。
早在1913年,周作人就发表《童话略论》,从童话起源、分类、解释、变迁、应用、评骘等方面立论,他在结论部分指出:“治教育童话,一当证诸民俗学,否则不成为童话,二当证诸儿童学,否则不合于教育。”同年,作《童话研究》,收录、注解绍兴当地童话数则,他认为:“依人类学法研究童话,其用在探讨民俗,阐章史事,而传说本谊亦得发明,若更以文史家言治童话者,当于文章原起亦得会益。”他在文尾表达了收集国内童话的迫切心情。这两篇论文是国内较早的童话研究论文,它们及数十年后周作人写就的《童话的翻译问题》一文都表达了一个意思:童话是民间传说故事,不是通常所认为的儿童读物,“童话”是外来的新名词,是从日本传入的,故有“那时日本只想利用于儿童教育,因此规定了这名称与其性质,中国就因袭了”之说。其实日本的“童话”和欧洲本源意义上的“童话”有所变异,周作人取原义。民国初年国内才有小本童话在上海出版。1914年,他作《古童话释义》,针对有人认为中国没有童话这种说法,他加以辩驳,认为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童话之名,但有些篇目实则是童话,他引《支诺皋》中两例、《玄中记》中一例,进行释义、辨析。同年,他又在题为《童话释义》的文章中,对他认为的中国古代童话《蛇郎》释义、解读。1958年,周作人又用白话改写《蛇郎》发表在《新民晚报》上。他1917年发表的《一蒉轩杂录》辟专节论童话。1922年,他以致赵景深公开信的形式在《晨报副刊》上连发3篇《童话的讨论》,引起很大反响。
无论是儿歌、民歌、笑话、童话,还是民间戏曲、民间传说等民间文学文类,周作人都立意从民俗学研究和民俗学史的视野加以考察,注重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考察国民心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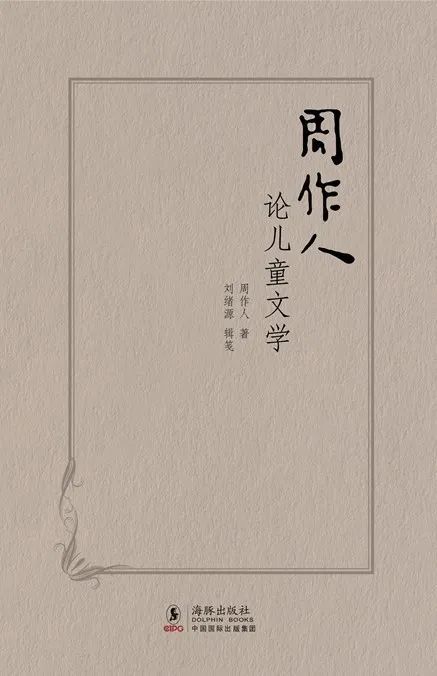
上述部分文章见辑录《周作人论儿童文学》


四
周作人走上民俗学、文化人类学、民间文艺研究的学术道路,是与他在日本留学时接触到西方新知识新思想密不可分的。他1926年回忆:“我在东京的书店买到了‘银丛书’(The Silver Li-brary)中的《习俗与神话》(Custom and Myth)《神话仪式与宗教》(Myth,Ritual and Religion)等书,略知道人类学派的神话解释,对于神话感得很深的趣味,二十年来没有改变。”他由阅读英国人类学家安得路·朗(Andrew Lang)的几本关于神话的书开始,继而对传说、童话也十分注意,自然地又留意儿歌。安得路·朗编辑的10余册童话和一种《儿歌之书》,他都设法买到。他于1906年在上海买到英国人类学家泰勒的《人类学》译本,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金枝》作者、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还有威思忒玛克教授(E.Westermarck)的两册《道德观念起源发达史》(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ral Ideas)也对他影响很深。
周作人对神话一直很钟爱:“有一样东西,我总是喜欢,没有厌弃过,而且似乎足以统一我的凌乱的趣味的,那便是神话。我最初所译的小说是哈葛德与安度阑合著的 《 红 星 佚 史 》 (The World’s Desire by H. R. Haggard and Andrew Lang),一半是受了林译‘哈氏丛书’的影响,一半是阑氏著作的影响。”《红星佚史》是他1907年留学日本期间翻译的,后交付商务印书馆出版。周作人1922年发表《神话与传说》一文主要介绍安特路朗的人类学思想,指出人类学关于一切神话的起源在于习俗的观点已为现代民俗学家所采用,他从科学和文学两方面阐述神话的价值,他强调,他所说的“神话”包括神话、传说、故事、童话四个文类。1924年,他以“神话的趣味”为题在中国大学演讲,演讲记录稿公开发表,内容和上文基本相同。周作人翻译出版了劳斯(W. H. D. Rouse)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他一生写了30篇左右与希腊神话有关的文章。《金枝上的叶子》是弗雷泽夫人所编的一本书,周作人在介绍该书的同题文章中先介绍了弗雷泽的《金枝》,然后介绍《金枝上的叶子》,最后选译了其中较短的一篇。
周作人在《童话的翻译问题》中认为:“童话正当的说是民间故事,一面是民俗学的资料,一面是民间文艺,可以称为原始的小说,它的性质是兼有学术与文艺这两重的。”1909年,鲁迅、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在日本东京出版,其中收入了周作人执笔翻译的安徒生(他译作“安兑尔然”)童话《皇帝之新衣》。1910年,周作人作《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介绍安徒生行状,当时中国鲜有知之者。1917年,周作人以文言写作《外国之童话》介绍西方童话,言简意赅。1918年,他著文评介安徒生的童话集《十之九》。1919年翻译《卖火柴的女儿》,作译记一篇。1936年,他以《安徒生的四篇童话》为题,再次著文推介。周作人对安徒生的译介功不可没。他还以《土之盘筵》为总题目翻译外国童话10篇,为李小峰童话译本《两条腿》作序,介绍《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王尔德童话》等。1916年,周作人在《一蒉轩杂录》中专辟一节介绍英国俗歌。
周作人受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影响很大,他在《我的杂学》中说:“柳田氏的学识与文章我很是钦佩,从他的许多著书里得到不少的利益与悦乐。”他表示:“《日本之祭事》一书,给我很多的益处,此外诸书亦均多可作参证。”他对柳田氏的《远野物语》评价极高,认为是“独一无二之作”,使他知晓“民俗学里的丰富的趣味”,故而他购买了柳田国男10种书,可见喜欢之至。周作人主张:“要了解一国民的文化,特别是外国的……须得着眼于其情感生活,能够了解几分对于自然与人生态度,这才可以稍有所得……非从民俗学入手不可。……如以礼仪风俗为中心,求得其自然与人生观,更进而了解其宗教情绪,那么这便有了六七分光,对于这国的事情可以有懂得的希望了。”
周作人对日本民俗和民俗学研究很关注,写了不少文章。1926年,他在《汉译<古事记·神代卷>引言》提到《古事记》的上卷“讲神代的部分,也可以说是日本史册中所记述的最有系统的民族神话”,“我只想介绍日本古代神话给中国爱好神话的人,研究宗教史或民俗学的人看看罢了”。早在1916年,他在《一蒉轩杂录》中用一节介绍日本的祭祖风俗歌谣“盆踊”,次年,另一节介绍描绘时代风俗的日本浮世绘画风的创制、演变和工艺特点。他著文介绍《绘本隅田川两岸一览》,主要是因为该书“仔细描画人间四时的行乐,所以亦可当作一种江户年中行事绘卷看,当时风习跃然现于纸上”。其文《两国烟火》征引黄公度《日本国志》中的《礼俗志》、藤月岑《东都岁时记》、寺门静轩《江户繁昌记》、寺田寅彦《柿子的种子》、若月紫兰《东京年中行事》等著作,介绍历史悠久的两国桥烟火盛况。其文《撒豆》话题是流传日本数百年的立春前夜撒豆打鬼的习俗,继而谈到“追傩”,联想到“傩”在中国古已有之,遂引《论语》《后汉书》《吕氏春秋》《南部新书》《东京梦华录》等典籍说明先秦至唐宋时期“大傩”都在除夕,与日本殊异,这已涉足“比较民俗学”范畴了。其《鬼念佛》写的是日本的鬼故事鬼观念,并和中国的做了比较。《缘日》谈的是日本诸神佛诞日参拜仪式的风俗。其《日本之雏祭》介绍江户时代初期形成,然后普及到民间的一种儿童成长仪式习俗。其《五月人形之说明》解释端午节前后日本随处可见的人形陈设,其寓意是为男儿祝福,兼具尚武之意。《谈混堂》是关于日本洗澡的风俗。周作人还著文介绍日本早川孝太郎的《猪鹿狸》,将它与中国古籍《太平广记》《幽明录》《集异记》中记载的狸妖狸怪作比较。他以同名标题为文介绍佐佐木喜善的著作《听耳草纸》。其《<如梦记>译记》二至九是对所译的《如梦记》一书第二章至第九章出现的日本民间风俗和传说的解释。《果子与茶食》《陆奥地方的粗点心》和译文《普茶料理》三篇是关于日本的点心、吃食的。《江都二色》是介绍日本各种关于玩具的图书。
他的《日本的落语》介绍日本的笑话,同时和我国古籍《东京梦华录》《梦粱录》《古杭梦游录》《武林旧事记》《都城纪胜》中的有关记载相比较。二十八年后,他又写了一篇《关于日本的落语》,表达的意思是,日本的落语是民间文学的一种,是描写日本民间风俗的,搜集的有关材料不少,但写好很难。他的《和尚与小僧》一文基本上是抄译柳田国男的一篇文章,介绍日本一种民间故事类型和主题。译文《儿歌里的萤火》,译自日本北原白秋著《日本童谣讲话》中的一章。1921年,他翻译《日本俗歌五首》并作译序发表;同年,他翻译《日本俗歌六十首》并作译序,先公开发表,后于1925年,收入其译诗集《陀螺》。1958年,周作人发表了《日本民间故事》,选译了4篇东瀛民间故事。1963年,他发表《反映日本民情的笑话》,选译6则。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周作人翻译的《古事记》,他专门撰写了《<古事记>引言》介绍日本这部重要古籍的编撰经过、主要内容(神话传说)和艺术特色。他还著文介绍了日本乌有子的《艳歌选》。
另外,1914年,周作人写有《斯拉夫民歌》《苏格兰民歌》等文。他为刘半农的女儿刘育厚翻译的《朝鲜童话集》作序,翻译《朝鲜传说》,作《<蒙古故事集>序》。1952年,周作人翻译《乌克兰民间故事》《俄罗斯民间故事》,均为12篇,每篇有译者按语,一般是一段,个别像一篇文章,他在前者序言中介绍乌克兰地理、历史、文化、宗教,指出乌克兰是果戈里的故乡,特别强调他的小说受到乌克兰民间传说故事的影响,后者也有序言。


五
综上所述,周作人在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考察、研究、写作、译介等方面均做出了骄人的成绩。他在民俗学研究与书写方面,既有洋洋洒洒的宏论,又有精微切实、论证严谨的考证,还有清新可诵的随笔以及独具一格的韵文。难能可贵的是,他的研究和写作具有一种高远的历史意识、宏阔的世界视野和清明的比较眼光。他的《绍兴儿歌集》含有童谣史纲架构,《<明清笑话四种>引言》《论笑话》是笑话简史,《古童话释义》《童话释义》可看作中国童话史略。他研究竹枝词史,其《儿童杂事诗》是这一文体传统的自觉赓续。《送灶》《七夕》等文不啻为具体的民俗事象“小史”。他遍览古籍,披沙拣金,集腋成裘,博闻强记,特别是征引大量清人笔记,如果不是他孜孜以求,将有关风俗记载的文字翻检出来,公诸于众,后人很难发现。虽然现代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源自西方,周作人自涉足这一领域始直至晚年他都有一种阔大、平等的世界视野,他不仅译介古希腊神话,对西方民俗学理论著作以及朝鲜、蒙古、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的民间故事传说,也译介甚勤。他在译介、研究中不乏清晰明达的比较眼光,这尤其体现在他的中日民俗和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上。
周作人以现代思想者的眼光观照民俗,其观点往往能推陈出新,独树一帜,发人所未发。最突出的是他的民俗书写中的人民性思想。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的“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的主张流布甚广,深入人心,他从理论上论证的平民文学,当然包括民间文学,为新文学形成人民性特征迈出了关键一步,对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人民方向论的形成具有积极作用。可以说,“平民论”是“人民性”理论演进逻辑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链环,也体现、践行于他的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中。他对民间文学中的人情人性作了深入探究、对民俗中所表现的劳苦大众生活的悲欢和情感心理的寄托体察入微。对于北京寒冷的夜晚街头小贩的叫卖声,他言道:“在寒夜深更,常闻此种悲凉之声,令人怃然,有百感交集之概。”这体现出一位人道主义者的悲悯情怀。周作人认为民俗是“国民生活之史”,是人民生活原初、本真、自然的记录,反映了历代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从民俗学着手考察能够看出人民大众对自然与人生的态度、情感心理以及民间信仰。周作人认为歌谣是“国民心声”,是“‘社会之柱’的民众的心情”的自然流露,从民俗学视域观照民歌,能够考察人民大众的思想、风俗与情感,歌谣、故事、笑话等均是“人民所感的表示”。这样的思想观点是难能可贵的。无论是中国传统士大夫还是现代知识分子往往是高高在上,对普通百姓的民俗、民歌采取俯视态度,不屑于关注它们,更谈不上亲自收集、整理与研究了,而周作人的平民思想和“劳工神圣”意识使他对普罗大众抱有“同情之理解”,取平视态度。他的上述关于民俗的观点透露出,民众是社会生产生活的主体,民俗民歌是劳动人民充满烟火气、接地气的生活百态的浓缩形式,它忠实地记录社会生活习尚,表达人民真诚感情,表现人民大众的愿望和精神诉求,具有鲜明的民族感情和民族特色。这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现代民俗思想。
周作人还提出民俗文化的学术、教育与艺术三重功能。他1913年就认为研究童话(传说故事)可以从人类学、民俗学或者说学术的、历史的角度研究,探讨其本源;第二种研究路径是文学视域,他认为童话是“原人之文学”,有感而发,出乎自然,含有“艺文真谛”,足以“探文章之源”。正如民歌是诗之本源,而童话是“小说之胚胎”。周作人非常看重童话的教育功能,他从三个方面阐述其理由:一是童话和儿童心理感情趣味相近,儿童喜欢听读,“顺应自然,助长发达,使各期之儿童得保其自然之本相,按程而进,正蒙养之最要义也”;二是“小儿最富空想,童话内容正与相合,用以长养其想像,使即于繁富,感受之力亦渐敏疾,为后日问学之基”;三是“童话叙社会生活,大致略具,而悉化为单纯,儿童闻之,能了知人事大概,为将来入世之资”。但周作人不强调道德说教,主张“意会”。他标举艺术上适用于教育的优秀童话的特征是:“优美”“新奇”“单纯”“匀齐”。周作人在1914年的《儿歌之研究》中也从民俗学、文艺、教育三个层面论述其功能,重点落脚在教育方面,这是其启蒙思想使然,他是个儿童本位主义者,儿童是民族的未来,他希望儿童在心智方面能健康、自然地成长、成熟。对于儿歌、民歌,周作人指出其民俗学价值在于“是民族心理的表现,含蓄着许多古代制度仪式的遗迹”,可作为考证的资料;而其文艺功能,可考察诗的变迁或作为新诗创作的参考。周作人在民国初年以及民俗学开创期提出的民俗文化的民俗、文学、教育三重功能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民俗研究的三个路径、三个走向,周作人的现代民俗观是其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文化运动的开启民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920年代起,民俗学界的童谣、歌谣、童话研究也是大致按照他指出的研究路径开展的,因此具有较高的历史意义。而周作人的民俗文化三重价值的观点置于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来看,依然不失其现实意义。
周作人还在民俗学研究组织工作和培养学术队伍方面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他1920年任新成立的北大歌谣研究会主任,是1922年创办的《歌谣》周刊主编之一。一份珍贵的史料———1924年1月31日“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歌谣研究会常会并欢迎新会员会纪事”———真实还原了中国第一代民俗学家们开会研讨的热烈情形。周作人作为会议主席主持会议并作主要发言,钱玄同、林语堂、沈兼士、常惠等出席,新吸纳会员二三十位,其中有后来成为知名民俗学家的容希白、容肇祖、刘经庵等,可见周作人等很重视民俗学学术队伍的培养。周作人在会上介绍了已印行的《歌谣》周刊十八期。会议有两个主要议题,一是与国学门方言调查会合作,解决收集各地歌谣的注音、音标难题;二是商议扩大歌谣收集范围,收集神话故事、传说及童话,考虑将歌谣会改成“民俗学会”。周作人认为:“现在一时,民俗学学者国内尚属缺乏,很该合方言、风俗、歌谣、故事、神话……各种,成为一个大学。”从1920年代至1930年代,周作人为刘半农父女、江绍原、林培庐、娄子匡、李小峰、刘经庵、柏烈伟、翟显亭、张次溪等人有关民俗学、民间文学的著作写序,1951年再为张次溪所著《天桥志》作序,俨然民俗学界“盟主”。除刘半农和他是同侪外,其余基本是他的学生、晚辈,他奖掖后学,提携后浪,精神可嘉。
周作人自清末留学日本,1907年翻译民俗学著作,到民国初年在家乡绍兴收集儿歌,做民俗调查,筚路蓝缕,“但开风气”,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者,“1913年是他首先从日本引进了‘民俗学’这一名词”。周作人以主要组织者、身体力行者、积极倡导者的身份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展脉络有以下观察:“五四以后,风俗研究与方言调查的运动连带而起,可是没有底力,只算起了一个头,虽然有了做起讲之意,也总是很好的,后人就可以来接续下去了。”1933年,周作人总结了民俗学研究的成绩:“中国民俗学的运动渐渐发达,特别在广东浙江两省,因了钟敬文、娄子匡、林培庐诸同志的努力,有好些研究机关与刊物,这是很可乐观的事。研究的初步重在搜集资料,中国地大物博,这种工作也就颇烦重,不是现今少数同志所能办好,在这样困难之下却总能有那些成绩,风俗和歌谣故事方面有了不少记录,不能不说是很好的成绩了。”但他同时敏锐地意识到民俗学研究的问题和不足:“资料搜集固然多多益善,而搜集的得法不得法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其中最要注意的是其记录的方法……歌谣故事之为民间文学须以保有原来的色相为条件,所以记录故事也当同歌谣一样,最好是照原样逐字抄录,如不可能则用翻译法以国语述之,再其次则节录梗概,也只可节而不可改,末后二法已是搜集故事者的特许自由,为搜集歌谣者所不能援引者也。大凡愈用科学的记录方法,愈能保存故事的民间文学与民俗学资料之价值。”他在同年底的另一篇文章中又一次表达了民俗学研究科学方法的重要性:“近年来中国研究民俗的风气渐渐发达,特别是在南方一带,搜集歌谣故事纪录风俗的书出来的很不少了,可是在方法上大抵还缺少讲究。”他警告应避免“失了科学的精严,又未能达到文艺的独创”的危险。
1930年代,周作人对收集、整理歌谣的看法同样发生变化,他反思20世纪20年代同仁们热心整理歌谣,“特别感着一种浪漫的珍重”,是“浪漫主义的发挥”,认为“大家当时大为民众民族等观念所陶醉,故对于这一面的东西以感情作用而竭力表扬,或因反抗旧说而反拨地发挥,一切估价就自然难免有些过当,不过这在过程上恐怕也是不得已的事,或者可以说是当然的初步,到了现在却似乎应该更进一步,多少加重一点客观的态度,冷静地来探讨或赏玩这些事情了”。1920年代是歌谣收集、整理研究的开创期,也即他所谓的“初步”阶段,大家热情高涨,为引起广泛注意,不妨“热闹”“浪漫”,动作频频。1930年代是发展阶段,可谓“下沉期”,需要客观的态度,冷静的探讨,扎实的成果。周作人的当事人、圈内人身份决定了他以上观察是清晰、客观、切实的,集中到一起看,就是一部简要的中国现代民俗学学术史,而周作人在相关学术史上的地位无疑是很高的。王文宝在《中国民俗学史》中“重要的民俗学家”一节,以生年先后为序将周作人排在第一位,并作出公允评价,认为周作人“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创始者之一,重视和提倡民间文化,提出了‘平民文学’的口号,对我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但因全书体例和篇幅限制,他对周作人的评价稍欠详尽。
从本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这半个多世纪里,周作人对民俗学、民间文学的研究和写作几乎贯穿其一生的笔耕时期,影响者众,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创建和发展可谓贡献重大。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22年第2期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