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推介

本期新青年惠嘉,女,陕西榆林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俗学、民间文学理论。本文说明了民俗学者们开始将语境理解为一种特定的阐释框架,从对穷举式语境研究的反思转而关注框架内文本的生成过程。框架式语境观凸显了民俗之“民”的主体性,进而昭示了民俗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应有的价值关怀。
民俗学“框架式”语境观的双重向度
惠嘉
原文发表于《民俗研究》
2018年第5期
摘要
随着对穷举式语境研究的反思,民俗学者们开始将语境理解为一种特定的阐释框架,转而关注框架内文本的生成过程。框架式语境观虽然仍有时空条件决定论的客观向度,但也具有主观赋义的向度。单纯取径前者,俗“民”可能成为被时空条件决定的他律者,缺失自由的维度;取径后者,则使“民”有望以赋义者的姿态开显其作为主体的主体性,这也是民俗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不能放弃的价值关怀。
关键词
民俗学语境;框架;时空性;主体性
就民俗学而言,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欧美,学科研究的主流转向“语境中的民俗”已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不过,作为学科范式的关键词,“语境”的意涵在学界既非一成不变,亦非已有定论。如果说早期的民俗学者倾向于将“语境”理解为先于和外在于民俗文本、且能决定文本生成的诸多客观性时空因素,多采取“穷举法”来诠释这一概念*;那么,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反思穷举式语境观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民俗学家们已经不再试图穷举语境的构成要素,以便客观呈现“语境中的文本”,而是将“语境”视为一种特定的阐释性框架,转而研究该框架中的文本生成过程,亦即“语境化(Contextualize)”的实践。这一极富张力的语境观虽仍有沿袭自穷举式语境观的“时空坐落”*的客观维度,但是,受诠释学的影响,亦在内涵上呈现出了不同于传统的主观向度,这在上个世纪90年代欧美民俗学界的一些成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对语境本质的思考不仅仅意味着研究方法的革新,更在某种程度上,凸显了民俗之“民”的主体性,进而昭示了民俗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应有的价值关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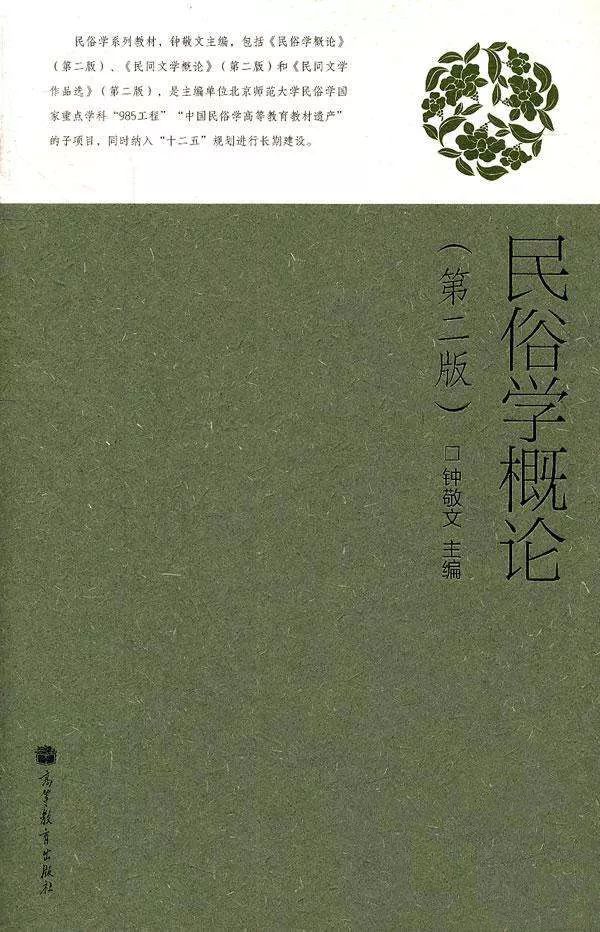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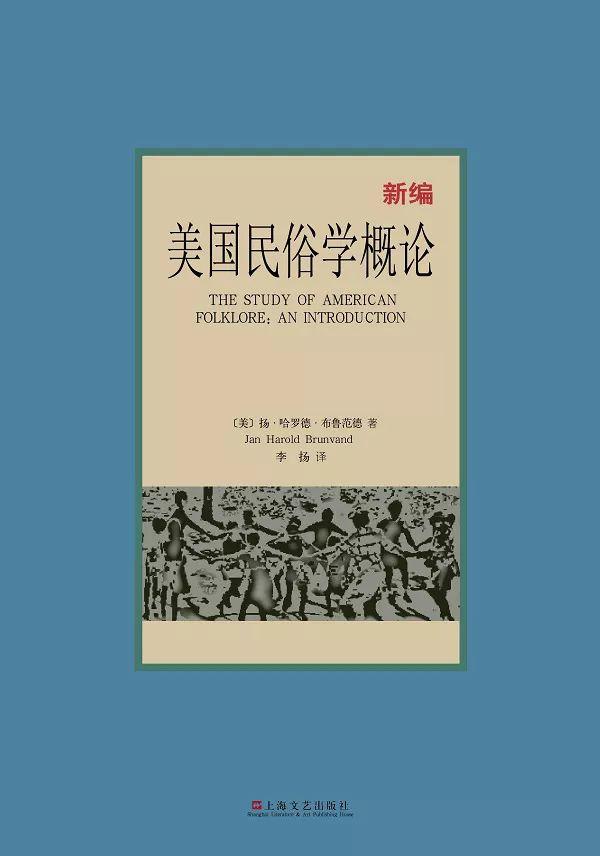
一、作为时空框架的语境
(一)语境的时空性
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在《表演中的文本与语境:文本化与语境化》一文中曾有过这样的表述:“当全面描述上面提到的每周一次的露天集市时,我们也许很想了解推销员在其中兜售药品的这个集市的地点、布局、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其他方面的事宜……从‘交流性实践’(communicative practice)这一更有利的视角来看,上述方法有一个重大缺点:它并未将围绕表演者的无数语境要素中那些对其影响最为显著的部分,作为正在形塑其表演的定位要点(points of orientation)而纳入直接的思考之中。”[注]就此而言,我们不难发现,如果说包括鲍曼在内的语境主义者早期尚希求罗列一切语境性的要素,那么此时他们已经放弃了“穷举一切”的野心,转而试图捕捉诸要素中“影响最为显著”亦即最具效力的部分。
在这一思路下,鲍曼于其名文《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中进一步指出:“表演表现了对语言基本指称用法(basic referential uses of language,用奥斯汀的话说,即‘严肃的’‘正常的’语言使用)的转变。换句话说,在这类艺术表演的交流互换过程中,正发生着某种事情,它对听众表明:‘要用特殊的理解来阐释我所说的话,不要只依据字面的意思去理解。’这进一步引导出这样的观点:表演建立了一个阐释性框架(an interpretative frame),被交流的信息将在此框架之中得到理解,这一框架至少与另一框架——字面意义的框架(literal frame)——形成对照。”[注]并且补充道:“这里我使用的‘框架’(frame)一词,并非采自奥斯汀,而是采自格列高里·贝特森的深富影响力的见解,以及时间上更为晚近但同样具有激发力的欧文·戈夫曼的著作。贝特森在他的富有开创性的论文《关于戏剧与幻想的理论》(A Theory of Play and Fantasy,1972[1956]:177-193)中,首次系统地发展了“框架”的观念,认为框架是一个有限定的、阐释性的语境(defined interpretive context),它为分辨信息顺序提供了指导(1972[1956]:222)。”[注]
也就是说,语境就是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和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所谓的“框架”(frame)。当然,除表演之外,还有暗示、开玩笑、模仿、翻译、引用等多种框架[注],但表演无疑是关注口头交流的民俗学者鲍曼眼中,最为重要的一种。以表演为例,进一步言之,框架是表演的边界,“如同围绕图画的文字框架一样,约定俗成的框架维持了图形和背景之间的必要区分,这样就更加便于我们找到界线,如果界线不存在,那么表演也就不存在了”[注];它是将表演事件同周围其他事件区别开来的特定条件——“在表演研究中,语境属于一个基础概念。‘表演’一词意指一种‘上台’行为,也就是说,是被加框(framed)的一类事件,具有不同于框架外行为的表达秩序。我们通过语境化(contextualizing)或加框式(framing)实践来创造这类事件……”[注]

明确了这一点之后,鲍曼试图将这种语境框架更为清晰地呈现出来,他强调道:“谈到构成‘表演作为框架’概念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主要因素,即框架实现的方式,或者,用戈夫曼对于框架被使用和转换的过程的称法,是表演如何被‘标定’(keyed)的……包括表演在内的所有框架,都是通过使用在文化上已经成为惯例的(culturally conventionalized)元交流来实现的。用经验性的语言来讲,这意味着每一个言语共同体都会从其各种资源中,通过那些已经成为文化惯例和具有文化特殊性的方式,使用一套结构化的特殊交流方法,来标定表演的框架,以便使该框架中发生的所有交流,都能在该社区中被理解为表演。”[注]类似的观点亦见于1992年出版的《民俗、文化表演与大众娱乐:以交流为中心的手册》[注]所录鲍曼的《表演》[注]一文。在对“标定”的具体阐释中,鲍曼列举了“特殊的符码、比喻性的语言、平行关系、特殊的辅助语言特征、特殊的套语、求诸传统、对表演的否认”等几种手段,并称之为可见诸各种不同文化的一般性标定手段。[注]在鲍曼而言,捕捉到这些标定手段,便可以勾勒出作为框架的表演语境其轮廓和边界,并使之显明出来;与此同时,他告诫我们,把握这些手段的途径或曰“更正确的做法”[注],只能是立足于特定社区的经验考察,亦即民族志的方法:
“必须强调的是,无论如何尽可能地明确和努力,也不可能有一个标定表演手段的世界性的清单。更正确的做法是,在特定社区中可能被用作标定表演手段的特殊清单,需要通过民族志方法去发现,而无法事先假定。”[注]
“这里我想说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我们必须要经验地确定在一个特定的社区中,哪些是特殊的、惯常被用以标定表演的手段。尽管这些手段也许会具有地区的和类型的模式以及普遍性的倾向,但是它们常常会由于社区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注]
现在,我们不妨尝试做这样的推论:如果标定表演框架的手段必须立足于特定社区的民族志考察才能加以把握,那么这些标定手段本身一定能够显现在时间和空间当中;如果这些标定手段本身可以为我们在时空中所直观,那么,它们一定是一些经验性的标定手段——我们可以看到,在上文的引述中,鲍曼本人甚至直接就使用了“经验”这一表述。进一步言之,鲍曼将表演的标定手段视为“框架实现的方式”[注],如果作为框架的语境必须经由经验性的手段才能得以实现,或者只能被经验性的手段所标定,那么,这种框架式语境也一定是一种可以显现在时间和空间之中的经验现象,换言之,它一定具有时空性,这一点,我们可援引鲍曼的相关论述以为佐证:
“在一个社区中,文化表演一般是最为显著的表演语境,而且具有一套特有的特点……它们在时间上是有限定的(temporally bounded)……它们在空间上也是有限定的(spatially bounded)……在这些时间和空间界限之中的文化表演还是用结构性的计划说明书或者行动节目表规划的(programmed)……”[注]
“我们将表演行为看做情境性的行为(situated behavior),它在相关的语境(contexts)中发生,并传达着与该语境相关的意义。这些语境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确认,比如场景(setting),它是由文化所界定的表演发生的场所。再比如制度(institutions,如宗教、教育、政治等),从它们表现或者没有表现社区中的表演语境的角度来看,也是一种语境。”[注]
“对于表演取向的民俗学者来说,其语境观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注意力聚焦于“实践的情境性语境”(situational contexts of use),即由地方性所规定的情境、事件、现场(scenes)……”[注]
“时间”“空间”“时间和空间界限”“场景”“场所”“地方性”“现场”,细查上述引文,我们不难从这些表述语境的关键词中看出鲍曼对语境所具时空性的着意强调。至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告别了穷举式语境观的鲍曼,仍然部分地保留了穷举式语境观中以时间和空间来定位语境的思路,在他而言,作为框架的语境很大程度上(此处有关程度的表述是因为框架式语境观并非单纯立足于时空范畴,还有另一种阐释的向度,这一点本文稍后再行讨论)仍然是一种时空性的语境,尽管它对于文本的理解来说不可或缺,但它还是一种可以随时进入或抽离的外在于文本的时空场,以此,民族志方法才有其必要性。就此而言,鲍曼依旧秉承了语境、文本二元论的思路和物化的文本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鲍曼所言的文本一体两面的“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注]。而无论“去再语境化”还是“文本化”,“化”的过程本身都是在强调语境变化于文本生成进程中的决定作用,这一点,也是此一表述本身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缺席的“主体性”
正如本文开篇所言,伴随着对穷举式语境研究的反思,民俗学家们逐渐放弃了对语境构成要素的穷尽式枚举,不再只研究“语境中的文本”,转而开始关注“语境中文本的生成”,亦即文本的语境化过程。换言之,学者们不再致力于通过考察语境更为客观地呈现那个先在的乃至固化的文本,而是将注意力放在了特定语境框架之下各种因素共同作用形塑“这一个”新生文本的过程。因为框架式语境观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立足于时空范畴的语境理解,这就意味着于方法论而言,无论是摹写表演策略还是深描互动过程,学者关注的多还是特定的时空条件和具体的现象、事实。也就是说,这一维度下的框架式语境研究实际是在考察表演现象中的时空条件之“因”决定物化文本之“果”的动态过程,以此来解释表演文本形成的现象原因;其本质仍然是一种以认识自然因果关系为目的的时空条件决定论。故此,尽管较之穷举式语境研究,框架式语境观似乎提炼出了“无数语境要素中对其影响最为显著的部分”[注],可单单从这一本质来说,它与穷举式语境研究并无二致。[注]
胡塞尔曾经感叹,“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唯一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且唯一被科学所造成的‘繁荣’所迷惑,这种唯一性意味着人们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对真正的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造就单纯注重事实的人”[注],实证科学“从原则上排除的正是对于我们这个不幸时代听由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支配的人们来说十分紧迫的问题:即关于这整个的人的生存有意义与无意义的问题”[注]。

如果语境仅仅是一种时间和空间的框架,如果框架式语境研究仅仅是特定时空中的动态事实描述和因果现象说明,那么,我们不免遗憾地发现:人的一切表演和创造都不过是特定时间和空间条件之下必然如此的产物而已。倘若我们将民俗理解为以人为主体的“生活”,倘若这种以人为主体的“生活”完全取决于外在的时空性条件亦即语境条件,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人的主体性何在?人的自由何在?换句话说,当我们研究视野之内以人为主体的“生活”仅仅是自然原因作用的结果,民俗之“民”仅仅是被自然因果律规定的他律者,重读胡塞尔对于实证科学的反思,或许我们也会无可回避地面临同样的问题:这样的民俗研究对于整个的人的生存有无意义?
彭牧曾经十分敏锐地指出,鲍曼认为,在民俗学与人类学界,“表演”一词至少有三种有所重合又各有侧重的意义:第一,将表演理解为实践,亦即特定情境的日常实践;第二,将表演理解为文化表演或扮演;第三,将表演理解为口头诗学,即出于特定情境中口头互动交流的艺术实践;鲍曼本人以及大部分运用表演理论的民俗学家都主要持第三种表演观,但这种意义上的表演具有局限性,其局限性之一便是可能因为对民俗艺术性的格外强调而导致表演理论背离“它最初的对民众真实的社会生活的关注与参与”。[注]出于对表演理论价值初衷的强调,彭牧认为表演应当理解成实践,并指出,“就人类学与民俗学而言,在个人、历史、人类文化的关系上,实践理论提出了不同于结构主义的理解框架”——如果说结构主义认为“文化、语言等的结构完全支配了人类文化的历史过程,人面对结构束手无策,毫无能动性”,那么实践理论虽然也强调某种结构性的制约,但它更“强调人的能动性、历史、事件的意义”。[注]这是否意味着为表演理论之方法论建基的语境观自身也孕育着开显俗民主体性的理论因子呢?
对于框架式语境观,凯瑟琳·扬(Katharine Young)曾做过这样的说明:“框架可以是界线,用来从空间和时间上对事件进行划分,同时,框架也可能以信息的形式出现,以帮助参与者理解 ……” 这或许为我们从另一种向度理解语境提供了某种可能。
二、主观赋义的语境
玛丽·赫夫德(Mary Hufford)曾经论述道:“在我们所构想的各种整体中,对于这个在文化层面界定的事件而言,什么才是它的情境呢?表达这些整体的术语有许多:世界观、文化、体系、文化框架及话语等。此外,还有很多用于表达其应用的词,例如范围、世界、学术圈、思想领域的词汇,他们勾勒出了学者们进行研究时为其敞开的空间。考虑到最近有不少批评认为,民俗学不过是一个关于意义的学术领域而已,我们的确可以在其间增补上‘语境’的术语。”[注]在她看来,民俗学研究是一个指向意义的领域,而这意义与“语境”有着密切的关联。
丹·本-阿莫斯(Dan Ben-Amos)则更为明确地指出,语境研究使得民俗学从既往的因果说明(explanation)转向了意义的阐释(interpretation)。语境分析并不解释或说明(explain)民俗,而是通过考量文本和民俗在社会中的整体经验来阐释(interpret)民俗,它探求的是意义(meanings)而非原因(causes)。[注]
事实上,本-阿莫斯关于“说明”和“阐释”的讨论呼应了狄尔泰在哲学史上的一个著名界分,这里稍作解析。狄尔泰有一句名言“我们说明自然,我们理解精神”[注],并以此作为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或曰人文科学之间的方法论分野。他认为,“自然科学同精神科学的区别,是由于自然科学以事实为自己的对象,而这些事实是从外部作为现象和一个个给定的东西出现在意识中的。在精神科学中,这些事实则是从内部作为实在和作为活的联系更原本地出现。”[注]以此,对于自然科学,我们可以“说明”,即通过观察和实证把一个个事实纳入普遍的自然因果律当中;而对于精神科学或曰人文科学,我们只能去“理解”和“阐释”,亦即“通过自身内在的体验去进入他人内在的生命,从而进入人类精神世界”[注],“从事物本身出发进行阐发性和揭示性的本体解释”[注]。也就是说,于方法论而言,“说明”面对的是现象世界,一个我们可观可感的外部世界,它具有普遍而必然的自然因果法则,我们可以遵循自然法则,经由观察、实证来解释、说明个体的事实,将其摄入因果规律之中;而“阐释”面对的则是精神世界,是我们无法直观的内部世界,且因人存在的自由意志,并不完全受制于普遍必然的自然法则,故而不能单纯依靠实证研究进行自然因果推论,而应诉诸一种旨在领会他人精神的内在体验。[注]我们在“说明”中主要使用因果范畴,在“阐释”中则主要使用意义、价值、目的等范畴。[注]
明确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回到本—阿莫斯的论述。本—阿莫斯极具慧眼地指出,语境研究使得民俗学从既往的因果说明(explanation)转向了意义的阐释(interpretation)[注];据上文讨论可知,因果说明意在解释现象世界中民俗事实发生的时空性条件(也是现象条件);意义阐释则旨在开显民俗主体自身主观世界中的意蕴空间。取径前者,“民俗”是“俗民”役于外在时空条件的被动使然,无以体现“民”的自由创造;取径后者,“民俗”不是研究的目的,而是理解“俗民”的进路,导向意义世界的研究本身就强调和凸显了“民”作为“赋义者”的主体性。这不仅意味着民俗学研究方法的转变和学科研究任务的转换,意味着民俗学关注的领域较之以往发生了重大的转向,更意味着语境研究对于学科价值目标的潜在自觉。就“语境”概念自身的意涵而言,因果说明指向的是民俗坐落其间的外在的时空场域、客观语境(这里的“客观”是牛顿物理学意义上的客观),而意义阐释指向的则是民俗主体自身展开和建构的内在的意义世界、主观语境,本—阿莫斯的论断无疑为我们理解这一概念开启了另一种新的可能。
尽管本—阿莫斯向我们开示的新的语境向度并未得到表演理论的充分解读,甚至很大程度上为其所忽略,但是,表演理论推动民俗学由传统的关心“事象”(item)——民俗材料(the things of folklore),转而关注“事件”(event)——民俗实践(the doing of folklore)[注],让曾经隐于民俗背后的人作为行为、事件的主体凸显出来,进而使我们有可能经由行为或事件介入民俗主体的主观语境。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出版的论文集《重新思考语境:作为交互现象的语言》便是这一思路的集中体现,对此,胥志强博士亦有关注[注]。

在《重新思考语境:作为交互现象的语言》的导言中,编者亚历山德罗·杜兰特(Alessandro Duranti)和查尔斯·古德温(Charles Goodwin)援引了贝特森以持杖行走的盲人为喻探讨语境边界的例子,认为贝特森的例子阐明了对语境分析而言至关重要的两个核心问题:“其一,语境分析的起点应该是那个行为被分析的参与者的视角。研究者力图描述的不是他们认为的语境,比如他们手中可以供盲人自我定位的城市地图,而是主体自身在行走过程中如何参与和组织他对于事件与情境的视角。其二,这个比喻生动地说明了一个参与者如何根据当时开展的特定活动来塑造自己认为的相关语境。比如,在走路的行为中,城市环境、一段走廊、它的限制条件,它特别突出的障碍物,都会成为显著相关的语境,而这些在吃三明治的行为中则是无关的。”[注]这是一段极富现象学意味的表述——在现象学家胡塞尔看来,“所有的世界之物,所有的空间-时间的存在对我来说存在着,这是因为我经验它们、感知它们、回忆它们、思考它们、判断它们、评价它们、欲求它们等等。众所周知,笛卡尔将所有这些都冠之以‘我思’(cogito)的标题。世界对我来说无非就是在这些思维(cogitationes)中被意识到存在着的、并对我有效的世界。世界的整个意义以及它的存在有效性都完全是从这些思维中获取的。”[注]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世界”不是牛顿意义上时-空扩展的物理世界,而是由我们的主观意向所建构的意义世界。正如赫夫德所做的梳理,这一思想通过现象学的社会学家舒茨和戈夫曼,在民俗学中的框架式语境观中产生了回响。[注]
赫夫德曾经强调:“‘加框’是民俗学家们改编而来的变形词,它出自欧文·戈夫曼对两门学科的综合研究,包括格雷戈里·贝特森的元交流理论和阿弗莱德·舒茨现象学的社会学理论。从这一角度出发,意识是有意向性的(intentional);也就是说,必须有一个对象(object),意识才可能构成现实(reality)。反过来,现实只有在成为被关注的对象时才存在(only exists as an object of attention),当关注不存在了,现实也就不在了。就像意识一样,语境也需要一个对象(object),实际上,语境就是集中关注的一种结果(effect)。”[注]
语境是一种意向投射所建构的现实,当投射其间的对象性意向亦即“关注”消失时,语境也将不复存在。赫夫德对框架式语境的理解与胡塞尔的思想十分接近,至此,语境已经超越了外在的时空场域,而成为一种“主观赋义”的意义空间。戈夫曼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译本译者冯钢,在译序中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来解释这种“主观赋义”的“情景”(语境框架)。冯钢写道:
“‘情景定义’也许是读者在形象互动理论著作中感到最陌生、最难以把握的一个常见概念。这个概念是由另一位形象互动论奠基者,威廉·托马斯(1863-1947)创造的。用托马斯自己的话说‘情景定义,即对于条件、状况和态度意识的比较清楚的概念’。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条件、状况和态度意识,既可以是客观存在的对象;也可以是不客观、不存在的对象,重要的是人赋于它的意义。因为人在行动时,总是根据他对外界的解释和意义而采取行动的;所以尽管对象可能是不客观、不存在的,但只要人们赋于它某种意义,行动就会产生客观的效果,‘杯弓蛇影’这个典故便是讲的这个道理。托马斯的一句名言是说:‘如果人们把某种情景定义为真实的话,那么这一情景就具有真实的效果。’(‘If men define situation as real they are real in their Consequences.’)”[注]
也就是说,意义是完全主观的东西,并不能因为其所关涉的对象(比如“蛇影”)不是“客观存在”,我们就判定它是假的,只要我们“赋予”了意义、“接受”了意义,那意义就是“真的”。只不过这种“真”不是无关意志的客观实体性的“真”,而是开启了我们生存处境的一种内在的“真”。

当然,类似的语境观在鲍曼的著述中亦有体现,比如他曾经谈到:“推销员通过自己的推销方式,创造了一个特定的情境性语境……语境化过程不必限定于眼前即见的场景。事实上,语境化的动态性向我们揭示了表演超越单个表演事件界限的方式。当我们的推销员在为其推销制造情境性语境并将自己置于舞台中心时,他也在尽力将自己与圣米格尔的周二集市相分离,并将自己放置在外在于此时此地的表演的世界中予以定位……”[注]其间,鲍曼明确强调,“语境化过程不必限定于眼前即见的场景”,“语境化的动态性向我们揭示了表演超越单个表演事件界限的方式”,并指出,彼时的推销员“创造”了“情境性语境”,“并将自己放置在外在于此时此地的表演的世界中”。这实际表明,在鲍曼看来,语境不应仅限于随意进出的自然场景,更是主体(推销员)基于主观目的(推销)创造的情境性语境,亦即是一种主观意向所建构的意义世界。
不过,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鲍曼并没有将语境的两种向度进行清晰的界分,所以他才会有时强调“使用‘民族志’一词来标定我们研究表演的方法”[注],将表演视为一种经验性的行为框架;有时则认为表演的“本质在于承担向听众展示交流技巧的责任”[注],它可以脱语境交由观众进行品评[注];呈现出了一种杂糅甚至矛盾的语境观。
赫夫德曾指出:语境化的工作就是复原意义。[注]既然语境不仅仅是外在于主体的时空场域,还是主体内部的主观赋义,那么我们田野作业要做的就不仅仅是客观的民族志描述,还需要“‘以意逆志’,以研究者的主观去‘会’被研究者”[注]的主观,去理解主体主观意向中的意义世界。正如刘宗迪所言:
“每一个地方都有与其独特的地理景观相映照的地方风物传说,在自然地理学意义上,一个地方只是一片自然形成和人工造就的地形、地貌而已,而正是因为有了地方风物传说,这些地形、地貌才获得了意义,那些庙宇、水泉、坟茔、山丘、河川才成为龙脉所系的福地、恬然可居的家园、野鬼出没的古墟,那些与这些地理景观相关的神仙下凡的神话、先祖卜居的传说、风水堪舆的故事,就赋予了这些景观以不同的意义,也让这些景观在地方空间中具有了不同的地位和重要性,从而在当地土著的心目中勾勒、建构了一幅乡土地图,这幅地图和地理学家或者任何一个外来人居高临下鸟瞰的地图迥然不同,是两个风情各异的地理世界。”[注]
“这些故事和歌唱宣示着民众对于其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的理解,也引导着民俗学者对民间社会和民俗生活的解释,它们其实就是解释学意义上的“前理解”,海德格尔把“前理解”称为“先行看到”,也就是说,在研究者把一个对象当作考察和研究的主题之前,前理解已经预先为研究者展现了一个通向对象的视野,它决定了你在这个对象(比如说一片“田野”)中看见什么、关注什么、把你看到的东西看作什么、理解为什么。正是这种“前理解”开辟的视野,为研究者展现了通向对象或田野内在奥妙的幽径。”[注]
事实上,刘宗迪的“乡土地图”就是当地居民经由民间叙事所建构的主观语境,也是研究应当指向的意义世界,其所述的“解释学意义上的‘前理解’”与框架式语境观实际上别无二致。如其所言,前理解不但决定了你“把你看到的东西看作什么、理解为什么”,更决定了你“看见什么、关注什么”,而戈夫曼的框架,或者更具体地说,民俗学中的框架式语境也是如此——以表演为例,我们通过框设作为民俗实践的表演事件,将它同别的事件区别开来,使之进入我们关注的视野,让我们“看到”,进而在这一框架内理解表演行为的意义,即所谓“语境就是一个框架(frame),环绕着被考察事件,并为恰当的理解提供资源”[注]。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研究表演时不应只着眼于外在时空条件对表演的影响,更应从参与者的主观视角出发,理解参与其间的多元主体对表演的主观体验与所赋意义,这是框架式语境观为我们开启的语境概念的主观向度。
这一向度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论的变革,它通过关注“民”的主观意向,使得俗民以赋义者的姿态从幕后走到了台前,由抽象、模糊甚至匿名的传统承受者转而成为可以自由创造和享用传统、并对传统进行自由赋义的主体,进而将“民”作为主体应当受到尊重的权利和尊严呈现于我们的视域——这是民俗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不能放弃的价值关怀,也是学科由以获得温度的路径。
(注释及参考文献见原文)

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18年第5期
图片来源:网络
专栏连载
拓展阅读
99.新青年 | 苗露:百年二人台:幕课、史料与民间小戏传承实践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