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母题是故事学的重要术语,影响广泛却众说纷纭。母题术语界定的模糊、功能与母题等术语未能有效勾连、故事学术语体系不完整,这些均限制了民间故事研究空间的拓展。汤普森的母题界定及分类影响最广,但逻辑混淆。邓迪斯借用普罗普的形态学理论和派克的语言学理论分析民间故事的形态结构,明晰了功能(母题位)和母题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有理论套用的瑕疵,且并未解决母题界定逻辑混淆问题。要解决上述问题,应将故事类型学和故事形态学视角相结合重新界定母题,厘清母题位、母题和母题变体三者间的层级关系。在此基础上,以母题为基础单元搭建故事学的多层级术语体系。故事学的多层级术语体系让民间故事的形态结构研究和文化意蕴研究有了勾连和转换的学理基础,这有助于开启民间故事研究的新空间。
关键词:母题;母题位;母题变体;故事类型;术语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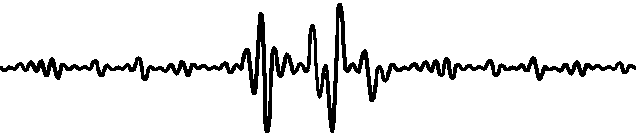
在故事学领域,母题是使用最为广泛的术语,却又是未能达成共识的概念。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学术史梳理,但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仍未解决:母题在民间故事中是形式还是内容?如何定义母题?母题位(motifeme)、母题(motif)、母题变体(allomotif)之间的关系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是学界深入探析民间故事形态结构特征及文化意蕴的基础。
一、母题:影响广泛却众说纷纭的术语
母题术语常用于艺术学、书面文学、民间文学、叙事学等领域,因研究对象不同,各学科对母题的界定不尽一致,本文集中在民间故事学领域讨论母题的定义。母题成为民间文艺学的核心术语,汤普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汤普森的母题界定影响最大,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的争议。
(一)汤普森对“母题”的定义与争议
美国著名故事学家斯蒂·汤普森在《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中对母题做了这样的界定:
一个母题是一个故事中最小的、能够持续在传统中的成分。要如此它就必须具有某种不寻常和动人的力量。绝大多数母题分为三类。其一是一个故事中的角色——众神,或非凡的动物,或巫婆、妖魔、神仙之类的生灵,要么甚至是传统的人物角色,如像受人怜爱的最年幼的孩子,或残忍的后母。第二类母题涉及情节的某种背景——魔术器物,不寻常的习俗,奇特的信仰,如此等等。第三类母题是那些单一的事件——它们囊括了绝大多数母题。正是这一类母题可以单独存在,因此也可以用于真正的故事类型。显然,为数最多的传统故事类型是由这些单一的母题构成的。
汤普森不是第一个将母题与民间故事联系起来的民俗学者,却是第一个将母题视为民间故事的结构单元并界定、分类的民俗学者。相比此前故事学者用故事类型来处理数量丰富、形态多样的民间故事,用母题来分析民间故事能让民间故事的外部特征和蕴藏的文化信息更加清晰,同时有了进一步界定故事类型的学理基础。此外,汤普森的这一定义还将母题的易识别性、传承性特征揭示出来,成为影响最广的界定。此后,故事研究者对母题的界定多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细化和阐发。
汤普森的母题界定让人质疑最多的是关于母题的类别划分。汤普森将母题分为三类,包括角色、背景和事件,其中事件母题可以用来识别故事类型。汤普森将母题划分角色、背景和事件三种,或许与他1932年编撰的多卷本《民间文学母题索引——民间故事、歌谣、神话、寓言、中世纪传奇、轶事、故事诗、笑话和地方传说中的叙事要素之分类》有关。《民间文学母题索引》中的母题包括了汤普森所划分的母题的三种类别,如天神、地母、龟背上的地球、鸟形的灵魂、海底的另一世界、考验新娘:用破亚麻纱做衣服、毁掉皮解除魔咒,等等。尽管汤普森的母题界定及类别划分争议颇多,但它却是运用范围最广的民间文学术语之一。因为他所划定的母题类别,在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艺学、戏曲学等学科领域都能找到,已成了许多学科关注的话题。笔者在中国知网以母题为关键词、篇名检索,相关论著多达2883、1870篇(检索时间为2018年8月20日)。可见,母题这一术语能满足不同学科的研究需要,成为诸多学科的常用术语。
从逻辑层面看,事件母题本身就包含了角色母题和背景母题,如男子窃取到人间沐浴的仙女的羽衣母题就包含了角色母题——仙女和背景母题——神奇的羽衣。这就导致汤普森的母题界定在逻辑层面不周全,就连汤普森自己“也承认不管是母题的定义还是母题的分类根本就没有任何哲学原则”。因此,学界对汤普森的母题概念多有批评,其中美国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是批评最为激烈的学者之一。
(二)邓迪斯:从故事形态学和语言学视角解析母题
邓迪斯认为民间故事的研究单位应该是处于同一逻辑层面,像重量、热量、长度等单位一样可以用来测量。而汤普森将母题分为角色、背景和事件就不能成为民间故事的研究单位,“它们不是同一类量的计量单位。毕竟,不存在既可以是英寸也可以是盎司的类别。此外,母题下属的类别之间甚至并未相互排除……如果没有严格定义的单位,真正的比较就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民俗的比较研究需要已被仔细界定的单位,而如果母题和阿尔奈——汤普森的故事类型没有满足这样的需要,那么新的研究单位一定要发明出来”。
邓迪斯不满汤普森的母题界定,提出发明新的研究单位来替代母题,但新的单位从哪里来呢?他引入美国语言学家肯尼斯·派克的术语motifeme(母题位)、独创了术语allomotif(母题变体),将两者勾连起来分析民间故事的结构,“这两个概念是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理论与派克的语言学理论融合的结果”。
邓迪斯对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普罗普采用共时视角研究民间故事显得别具一格,在区分民间故事内部结构的稳定性和外部变异上非常成功。邓迪斯认为,母题具有流动性特点,用它来界定民间故事类型是不可靠的,而普罗普划定的31项功能是稳定的,应该从故事形态学视角界定民间故事。他还借鉴了肯尼斯·派克的语言学理论来区分民间故事的内在结构单位——母题和功能,认为“旧的最小单位母题motif和新的最小单位功能(function)之间的区分可以按照肯尼斯·派克对‘非位的’(etic)和‘着位的’(emic)这两个词的有价值区分来准确理解”。在他看来,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术语——功能“在派克的分析系统中应叫做MOTIFEME。由于功能这个术语尚未在民俗学家当中通用,这里建议用MOTIFEME来替代它”。邓迪斯用母题位来替代功能是故事学上的一大创举,这让我们明晰了功能(母题位)和母题之间的内在联系,民间故事的内在结构和外部表征的关联愈发明晰,民间故事的形态结构研究和文化意蕴研究就有了统合的可能。
邓迪斯把普罗普的功能术语套用到派克的语言学体系中,既然母题位(motifeme)替代了民间故事学的原有术语——功能,母题这个术语如何处理呢?他“借用语言学里的词缀allo-(别、变体),创造出allomotif一词来指代可以放置在同一motifeme位置上的所有motif”。母题则作为一个类似语音的“etic”单位来使用。
邓迪斯借用普罗普的形态学理论和派克的语言学理论来处理民间故事的内在结构和外部特征关系,显示了母题与母题位(功能)之间的紧密联系,并运用到北美印第安人的民间故事结构类型学研究中,在民间文艺界取得一定反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将母题位(motifeme)和母题变体(allomotif)两个存在层级关系的术语引入民间故事研究中,改变了此前只有母题、功能作为故事学结构单元的状况,为我们深入探究民间故事的内部结构起到重要作用。有学者评论说邓迪斯“以‘母题素’(motifeme)概念为核心的结构分析方法,融各家学说于一炉(他实际上还汲取了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对立’模式)使形态分析理论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邓迪斯用母题位(motifeme)替代普罗普的功能,将母题位和母题变体(allomotif)运用到北美印地安人的民间故事研究中,发现印第安人的民间故事中存在下列母题位模式:核心双母题位序列,两个四母题位序列,一个六母题位组合。核心母题位序列:缺乏/消除缺乏,插入的母题位有任务/完成任务;禁忌/违禁;欺骗/受骗。相比普罗普发现俄罗斯神奇故事的31项功能,邓迪斯的母题位数量大大减少,只有缺乏、消除缺乏、任务、完成任务、禁忌、违禁、欺骗、受骗、后果、试图逃避后果共十个。与普罗普的功能相比,这些母题位抽象性更强,与此对应故事文本中的内容就更加繁杂。如缺乏就有爱情、亲情、友情、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等多种,要消除上述缺乏状况所对应的母题变体成百上千。如帮助消除男子爱情缺乏的有龙女、仙女、田螺姑娘、花仙、狐精、女鬼等多种异类,结合的方式有报恩、姻缘天定、仙女下凡等多种情形,相应的母题变体(包括配偶身份、结合方式、结合地点及时间、辅助者)自然难以尽数。而普罗普的31项功能中,每一项功能在故事中所对应的内容相对还是有限的。
邓迪斯将派克的语言学理论套用到民间故事的结构分析中,尽管揭示了民间故事的内在结构和表面特征之间的关系,但民间故事的结构方式与词汇并不相同,motifeme和allomotif这两个术语之间涵盖的抽象和具象之间对应的事象繁杂多样,只靠motifeme和allomotif两个术语做分析单位来分析民间故事的内部结构关系还是不够的。民间故事的内在结构可能是多层结构,至少我们还应找到一个能勾连母题位(motifeme)和母题变体(allomotif)的术语才有助于研究者深入了解民间故事的内部结构特征。
邓迪斯批评汤普森在母题种类划分上界限不明,但他所创立的allomotif(母题变体)也未解决此问题。因为他创造的术语allomotif与motif在民间故事的内在结构层面上是同级的,只是所处位置不同和名称不同而已,或者说allomotif是母题的一个类别而已。事实上,邓迪斯批评汤普森关于母题的三种分类不在一个逻辑层面,但他并未对allomotif加以界定和分类,实质还是借用了汤普森的母题作为民间故事的结构单位,使用过程中不也会导致逻辑混淆吗?
邓迪斯看到将功能视为民间故事的内部结构单元可以说明民间故事的稳定性特征,但以母题的不稳定性来质疑其不适合作为民间故事的结构单位是难以让人信服的。邓迪斯在用母题位分析印地安人的民间故事形态结构时同样发现欺骗、受骗、设禁、违禁等母题位的位置也是不稳定的。实际上母题除了变异性之外还有稳定性特点,这也是我们能够确立诸如灰姑娘型、蛇郎型故事的原因。而且民间故事中的母题可以分为中心母题和变异母题,在同一类型故事中,中心母题是基本稳定的,变异母题则变化较大。
事实上,派克的“‘位/非位’(emic/etic)分别来自‘音位的’(phonemic)和‘语音的’(phonetic)的后缀。具体是指同样物理和生理属性的语音在不同语言中的‘位/非位’功能和地位可能是不同的,只能根据具体语言的语音系统来确定”。这对术语后来应用到人类学研究中,成为我们熟悉的主位和客位视角。派克的“位/非位”方法重在描述同一语音、语言或文化的不同视角。而邓迪斯将其套用到处理民间故事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关系上,忽视了民间故事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其实与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的关系更为相似,未能将母题(motif)、母题位(motifeme)和母题变体(allomotif)有机勾连起来,故运用到民间故事研究实践中并未产生典范效应。
既然母题(motif)、母题位(motifeme)和母题变体(allomotif)都和民间故事的结构单元有关,彼此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在回答此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回顾国内学者的看法。
(三)母题的内容与形式之争:“非此即彼”与“亦此亦彼”
国内学者在母题的本质究竟是形式还是内容问题上,大多数学者延续汤普森的观点,认为是内容,吕微、户晓辉等学者则认为是形式。总体而言,多为“非此即彼”的讨论,少有“亦此亦彼”的关注。
大部分学者在民间故事研究实践中还是沿袭汤普森的母题观:把母题视为民间故事的内容。陈建宪是国内较早使用母题分析法的学者。他认为:
作为民间叙事文学作品内容的最小元素,母题既可以是一个物体(如魔笛),也可以是一种观念(如禁忌),既可以是一种行为(如偷窥),也可以是一个角色(如巨人、魔鬼)。它或是一种奇异的动、植物(如会飞的马、会说话的树),或是一种人物类型(如傻瓜、骗子),或是一种结构特点(如三叠式),或是一个情节单位(如难题求婚)。这些元素有着某种非同寻常的力量,使它们能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中不断延续。它们的数量是有限的,但是它们通过各种不同的组合,却可以变化出无数的民间文学作品。
陈建宪对母题的定义基本沿袭了汤普森的观点,但也认为母题有形式特点,如三叠式;还可以是情节单元,如难题求婚;他还总结了母题的四组特征:易识别性与易分解性、独立性与组合性、传承性与变异性、世界性与民族性。这些总结对我们界定母题具有参考意义。金荣华也是从内容角度来界定母题,只是他认为motif译为情节单元更合理。
吕微和户晓辉认为母题是形式概念。他们对母题属于形式概念的分析引发我们对母题性质的新思考,启迪颇多。吕微早期认为“对于故事类型的分析、研究来说,叙事功能的提取和确认若脱离了故事的具体内容,或者脱离故事所仰仗的具体文化背景,都无助于我们把握故事的内容甚至形式”,把普罗普的功能术语和邓迪斯提出的母题素(位)术语结合起来提出“功能性母题”,后来又认为“母题是一个纯粹形式化的概念,其中不涉及任何对故事内容的主观划分,尽管母题的内容就是故事的内容。由于母题是纯粹的形式概念,因而导致了根据‘重复律’所发现的母题成千上万,数不胜数”。户晓辉进一步指出,“汤普森的母题实际上是没有内容的纯粹形式的东西,是不同于单个叙事中出现的内容成分的观念性存在即纯粹形式”。吕微和户晓辉的立论基点是美国民俗学家丹·本·阿莫斯提出的重复律,“母题不是分解个别故事的整体所得,而是通过对比各种故事,从中发现重复部分所得。只要民间故事中有重复部分,那么这个重复的部分就是一个母题”。重复律是以内容的雷同为基础的,假若没有内容的雷同又何来纯粹形式呢?当我们把重复律当作提炼母题的重要方法时总结出其抽象性特点后,又该如何看待母题的变异性特征呢?例如,天鹅处女型故事中共有的母题是人间男子窃取沐浴仙女的羽衣。在故事文本中,羽衣可能换成天衣,或漂亮的红衣;仙女可能是在湖中洗澡、也可能是在河中或池塘里洗澡。这些变异性特征在纳入《民间文学母题索引》或《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时并不影响我们是否归属同一母题的判断。而这种变异性正体现出母题抽象性之外的具象性特点。
刘魁立是国内少有从“亦此亦彼”视角关注母题的形式和内容问题的学者。他注意到了母题的抽象性和具象性兼备特点,认为“‘母题’这个术语,似乎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不变层面——指关于场景、冲突、事件、行为、评述等项的格式化的概括。母题的另一层面则是上述格式化模式的不变模式在个别具体而独立的文本中的现实展示。这两个层面关系,类似语言学当中‘音素’和‘语音’的关系”。刘魁立的看法与邓迪斯的看法表面相似,但立足点不同。邓迪斯着眼于考察民间故事的深层结构(母题位)与表层结构(母题)的关联,认为民间故事中稳定不变的是母题位(功能),与母题位对应的是母题位变体(实为母题),它们是两个互相关联的事物。刘魁立则认为母题一方面是对诸多民间故事中反复出现的场景、事件、行为的概括总结,类似普罗普所说的功能,具有抽象性特点。另一方面又是具象性的,是稳定性的内在结构在故事文本中的呈现。抽象性和具象性在母题中是合二为一的,是一体两面关系。母题还具备叙事功能,“具有能够组织和构成情节的特性。母题还有进一步展开叙述的能力,具备相互连接的机制”。变异性也是母题的重要特征,他说“母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属性,在于它的语义变化性和变异性。这种属性使母题在民间文学作品的不停顿的反复创作过程中,在传统情节不变模式的范围内,具有极大的活跃性和多产性特点”。
(四)母题、母题位与母题变体关系再探
邓迪斯、刘魁立等人关于母题位、母题的论述给我们很多启示。邓迪斯认为“民间故事可以被界定为母题素的序列。母题素的位置上可以被填充上各种母题,而且为任何给定的母题素位置特选的母题都可以被标志为变异母题”。在邓迪斯看来,母题和变异母题(allomotif)属同一层次的术语,是母题素(母题位)的外在表征。前文已述,母题位对应的母题变体是“包罗万象”的,因而母题位和母题变体的层级关系并未能紧密勾连民间故事的内在结构和表层文本的联系。我们还应寻找到一个连接母题位和母题变体的术语,帮助我们探析民间故事内在结构和表层文本的内在联系。而母题的抽象性和具象性兼备特点,正符合我们的要求。这样来看,民间故事的基础结构单元之间就不应该只有两层,应该是三层的等级关系:母题位——母题——母题变体。母题位等同于普罗普的功能,是民间故事共有的内在结构单位,如缺乏、消除缺乏、下达禁令、违反禁令、出发、救助他人、获得奖赏、陷入困境、难题考验、通过考验、争斗、获胜、追捕、逃避追捕、欺骗、受骗、变形、揭露、抵达、惩罚、返回、婚礼,等等。这些母题位并非在每个民间故事中都出现,但缺乏、消除缺乏这类的核心母题位通常会有。难题考验、通过考验、争斗、获胜等母题位经常在民间故事中出现,位置比较固定。其他母题位的位置比较自由。普罗普在对每项功能进行说明时,列举的不少实例就是母题,如第8项功能缺乏:1、缺少未婚妻;2、需要宝物;3、缺少魔力之物,如火鸟、长着金羽毛的鸭子等。其中主角缺乏未婚妻、宝物和魔力之物就是母题,概括性和具象性兼备。其中列举的实例如火鸟、长着金羽毛的鸭子就是缺少魔力之物的母题变体,是母题在故事文本中的实际呈现。普罗普的研究再次表明:母题是勾连母题位(功能)和母题变体的中介,是民间故事的基础结构单元。
以上是我们的理论假设。如果成立,我们应能从民间故事的研究实践中找到佐证。笔者发现,康丽对巧女故事丛的形态结构分析大体符合我们的设想。她发现巧女故事中普遍存在困境、考验、求助、代言、破题、困境解除、巧名外传、获悉、恶人得惩、认可范型。每个故事范型(母题位)有相对应的母题,如困境范型对应的母题是家人面临某种困境、巧女自己面临困境两种。家人面临某种困境母题下属的母题变体有:陷入牢狱、无法断案、讹诈、试探、不能履行承诺等。康丽对巧女所做的形态结构分析已经展示了故事范型(母题位)、母题和母题变体之间的层级关系。母题变体这个术语是她最先采用。她虽没有对母题变体做明确界定,但已表明母题变体是母题在故事文本中的实际呈现。笔者在运用普罗普的形态学理论研究中国天鹅处女型故事的形态结构时也注意到功能与母题之间存在对应关系。
母题位——母题——母题变体的层级术语体系改变了此前功能(母题位)和母题关联不够紧密的状况,这有助于深化民间故事的形态结构研究。当我们处理同一故事类型下的多种异文时,仅借助母题来分析形态结构难以明确异文及同一类型变体间的内在联系,而对母题变体的分析将有助于研究者深入了解故事文本间的内在关联及差异,从而拓展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空间。
二、母题再定义:故事类型学和故事形态学视角
综上所述,民间故事的内部形态结构单元可以分为母题位、母题、母题变体三个不同等级但互相关联的层次。但汤普森的母题定义缺陷依然没有修补,母题的界定问题依旧没有解决。接下来,笔者尝试对上述问题予以解答,以求教于方家。
汤普森将母题分为角色、背景和事件三种所造成的逻辑混淆是需要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笔者以为在民间故事学中,事件才是母题,角色和背景是构成母题的元素。比如田螺精变成美女帮助人间男子做饭的事件母题中田螺精是角色,精怪的变形信仰是背景。从逻辑上讲,角色和背景是事件母题的组成部分或元素而已,不能视为母题,好比语言学中单词和词组不是同级的语言单位不能并置成为研究对象。汤普森的这种处理方式在编撰《民间文学母题索引》时可以,因为《民间文学母题索引》好比民间文学研究的“字典”,是脱离民间叙事过程的排列。但在《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却不行,故事类型索引是故事情节的概括,只能纳入事件母题。实际上,当我们习惯性命名灰姑娘型故事、田螺姑娘型故事、百鸟衣型故事时,我们的判断标准不是角色而是角色的行为,是灰姑娘凭借水晶鞋和王子成婚、田螺姑娘帮助男子摆脱困境的行为成为我们识别故事类型的标准。换言之,灰姑娘可以被替换成叶限、小燕子、杉菜等人物,但下层女子和上层男子结婚的核心内容不能变,否则就不是灰姑娘型故事。再者,母题位(功能)是民间故事的深层结构单位,普罗普将功能界定为:“从其对于行动过程意义角度定义的角色行为。”这样来看,角色不能成为民间故事的结构单位,角色的行为才可以,所以汤普森的三种类别母题中与角色行为对应的只有事件母题才符合要求。
当我们确立了在民间故事中成为结构单元的只能是角色行为构成的事件母题后,接下来就是如何界定的问题。民间故事的母题具有形式和内容兼备的属性。就内容而言,母题成为我们识别故事类型的主要工具;就形式而言,母题位(功能)是民间故事的深层结构单位,应该成为界定母题的重要视角。日本故事学家稻田浩二从普罗普的形态学视角出发将母题定义为:“构成一个故事的主要登场人物所采取的主要行为,也包括与其直接对应的行为。”稻田浩二的母题界定借助了普罗普的形态学理论,便于操作,值得借鉴。但稻田浩二的界定并未将母题的传承性、易识别性等特征揭示出来。鉴于我们上文已讨论母题的形式和内容兼备特点,笔者在吸收前贤研究成果基础上,将故事类型学和故事形态学视角相结合对母题做以下界定:“母题是故事中与主角命运相关的事件或行为,具有抽象性和具象性、稳定性与变异性、易识别性与独立性特征,是构成民间故事的基本单位。”界定妥当与否,供方家指正。
笔者将母题界定为与主角命运相关的事件或行为是因为民间故事多为单线叙事,故事中的缺乏、消除缺乏、考验、难题、争斗、婚礼等母题位均是围绕主人公的命运展开叙事。母题是民间故事的基本单位,勾连母题位和母题变体,属中层结构术语。而母题变体是母题在民间故事文本中的实际呈现,相比母题而言,具象性、变异性特征比较突出。
抽象性和具象性特征是就母题的形式和内容特征而言。稳定性与变异性体现的是母题在传承过程中的变化情况,构成民间故事的模式化和形态万千特质。母题的易识别性是划分故事类型的重要标志,而母题位则不具备这一特点,正如普罗普最初想从形态学方法来给民间故事准确分类,“然而当他重新编辑出版阿法纳西耶夫的俄罗斯民间故事集时,又反过来借用Aarne和俄罗斯学者Andreev的成果,编制并附录了AT体系的故事索引”。独立性也是母题的显著特点,同一个母题可以在不同的故事类型、民间传说、神话、歌谣、史诗、叙事诗中找到,还会在通俗文学、作家文学中出现。
当我们重新界定母题概念、确立了母题位——母题——母题变体是不同等级但互相关联的层级关系后,就可以讨论故事类型的界定及故事学的术语体系了。
三、搭建以母题为基础单元的故事学术语体系
故事类型是故事学界很早使用的术语,影响最广的还是汤普森的界定:
一种类型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传统故事,可以把它作为完整的叙事作品来讲述,其意义不依赖于其他任何故事。当然它也可能偶然地与另一个故事合在一起讲,但它能够单独出现这个事实,是它独立性的证明。组成它的可以仅仅是一个母题,也可以是多个母题。大多数动物故事、笑话和轶事是只含一个母题的类型。标准的幻想故事(如《灰姑娘》或《白雪公主》)则是包含了许多母题的类型。
汤普森还将故事类型视为“一系列顺序和组合相对固定的母题”,但又认为一个母题(事件母题)就能组成一个故事。事实上,一个事件母题显然是无法构成民间故事的,因为从民间故事的深层结构来看,至少要有缺乏和消除缺乏两个母题位才能组成一个故事,故汤普森的类型界定存在不够完善的问题。对于形态结构复杂的复合型故事而言,母题的数量不是一个两个,往往是几组母题,常常导致含有多组母题的故事类型无法明确归类。尽管母题是构成民间故事的基本单位,但单用母题术语来界定故事类型是不够的,还需要更高级别的勾连类型和母题的术语才行。普罗普也曾对AT分类体系提出批评,认为“具有相同功能项的故事就可以被认为是同一类型的。在此基础上随后就可以创制出类型索引来,这样的索引不是建立在不很确定、模模糊糊的情节标志之上,而是建立在准确的结构标志上”。所以故事类型的划定也要参考形态学的视角才能避免界限不明问题。刘魁立在编撰《东亚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时就遇到这个问题。他将集录的28个浙江省狗耕田故事文本分为9个类型变体,发现“狗耕田故事类型的所有文本情节繁简不一,但是无论它怎样发展都脱离不开兄弟分家、狗耕田(或从事其他劳动:车水、碓米、捕猎等)、弱者得好结果、强横者得恶果这一情节基干,也脱离不开狗耕田这一中心母题。所有文本都是围绕情节基干和中心母题来展开情节的。如果脱离这一情节基干和中心母题,那么这个文本就应该是划在其他类型下的作品”。刘魁立提出围绕情节基干和中心母题来划分故事类型的方法对我们界定故事类型具有启迪意义。他提出的“母题链”相当于汤普森提出的“一系列顺序和组合相对固定的母题”,是比母题更高级别的故事学术语。母题是民间故事的结构单元,但单个母题并不能构成故事,不同母题的排列或组合才构成民间故事。刘魁立提出的“母题链”丰富了我们对民间故事内部结构的认知水平。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了划分故事类型的标准——情节基干。
情节基干是同一故事类型必备的要素,是划分故事类型的标准,是建立在中心母题基础上的结构单位,“情节基干由若干母题链组成,但是,母题链却不一定只存在于情节基干之中,它也可能是某些‘枝干’中的组成部分。中心母题是特指情节基干中的某一条母题链的核心内容,而‘枝干’中的母题链则不在刘魁立的讨论范围。在情节基干中,每一条母题链必有一中心母题,因此,该情节基干有多少条母题链,就会有同样数量的中心母题”。这样来看,用情节基干比汤普森用“一系列顺序和组合相对固定的母题”来界定故事类型更加明确,方法更为有效。因为在多个故事类型组成的复合型故事中,存在多个母题链,狗耕田型故事中就有两兄弟型、偷听话型、卖香屁型故事的母题链。这样划分故事类型时容易混淆,情节基干的提出就能有效处理这一问题。如果“狗耕田——耕田获利——兄仿效失败——杀狗——狗坟生植物”这一母题链处于情节基干位置就是狗耕田型故事,处于“枝干”位置就划入别的故事类型,避免了AT分类法中的类型界定混淆问题。后来他以情节基干为界定故事类型的基点,指出“类型是一个或一群故事,由一个或者少数几个中心母题组成的情节基干构成它的中心。假定两则文本的情节基干和中心母题不一样,它们就属于不同类型”。他用更为准确的术语——情节基干来划定故事类型,体现了中国学者对故事学的理论贡献。
情节基干是建立在中心母题组成的母题链基础上的,为保存术语的统一性,笔者尝试用中心母题链来替代情节基干。刘魁立还将同一故事类型诸多故事文本中出现的分支定名为类型变体。此前,我们常将同一故事类型中的异文称为亚型(sub-type)。“亚型”这个概念从字面意义理解有仅次于的意思,还是处于同一层级,没有兼容关系,并未显示出层级性特点。他将同一故事类型在故事文本中的实际呈现称为类型变体更能体现出两者间的紧密联系。
相比母题位——母题——母题变体的母题术语体系,故事类型的术语体系层次更加丰富,因为母题叙述的是单一事件,并不构成完整的叙事过程。故事类型叙述的是完整故事,包含众多母题位和形形色色的母题。在复合型故事中,母题链越多,类型变体就越多,形态结构愈加繁杂多样,就构成类型丛。类型丛是康丽将西方民俗学者安娜·伯基塔·鲁思(AnnaBirgittaRooth)的“母题丛”(motif-complex)概念与日本故事学人的“故事群”概念相结合提出的,“来标定同一故事类型群中存在于单一类型内部与多个类型之间的不同层级结构单元的多元丛构”。类型丛术语既考虑到民间故事类型变体的聚合性特点,又揭示了民间故事类型间的结构单元复杂性特征,是故事学术语体系中的高层级术语。
这样以母题为基础单元,故事学就形成了“母题位——母题——母题变体——中心母题链——故事类型——类型变体——类型丛”的多层级术语体系,民间故事的内在结构和外在表征得到有效关联,或者说民间故事的形态结构研究和文化意蕴研究有了勾连和转换的学理基础,这也是近年来故事学领域类型学研究和形态学研究不断结合的趋势所致。
术语是学术研究科学性、专业化的体现。学术研究的创新与新术语的出现及研究范式的更替密切相关。回顾故事学的发展史,母题、类型和功能一直是故事学最为常用的三个术语,也是体现民间文艺学学科本位的重要术语。民间故事学的学者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母题位、母题变体、核心母题、中心母题、母题链、情节基干、类型变体、积极母题链、消极母题链等术语,体现了学界对民间故事文本认知程度不断深化的过程。笔者以母题为基础单元搭建民间故事学的术语体系,旨在统合母题、类型及功能等术语,并借助术语体系的完善将民间故事的深层结构与外在表征有机联系起来,从而拓展民间故事研究的新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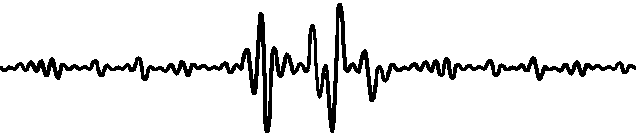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漆凌云,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万建中,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原文载于《民俗研究》2019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