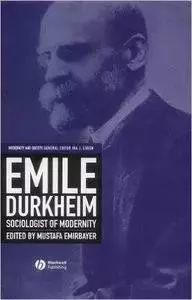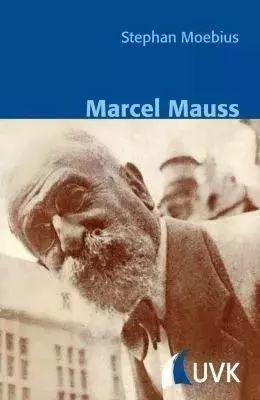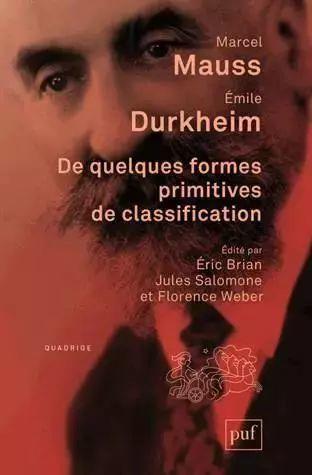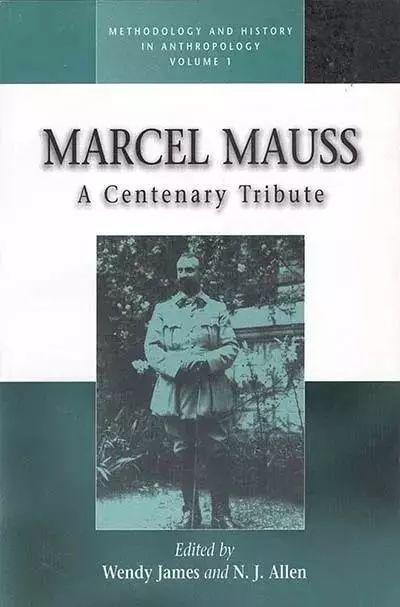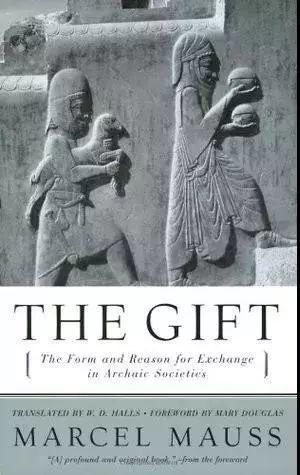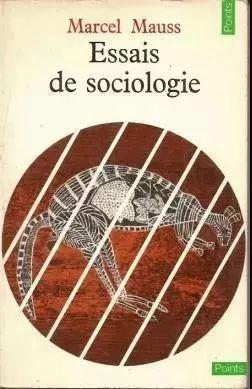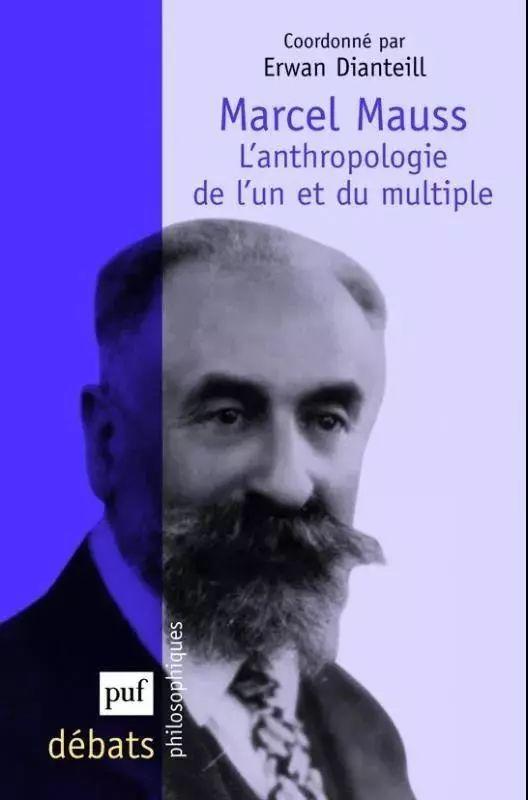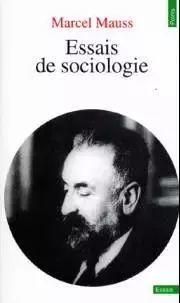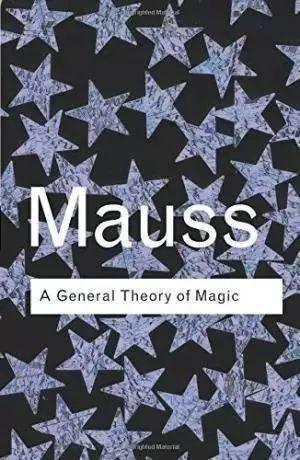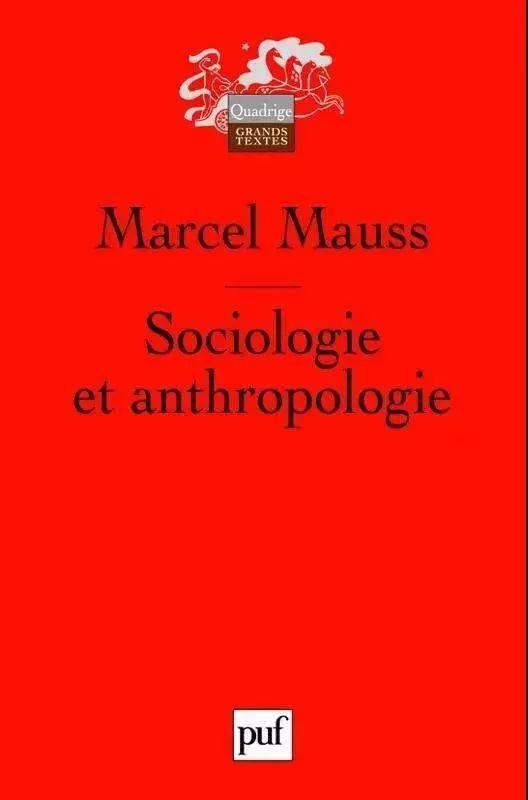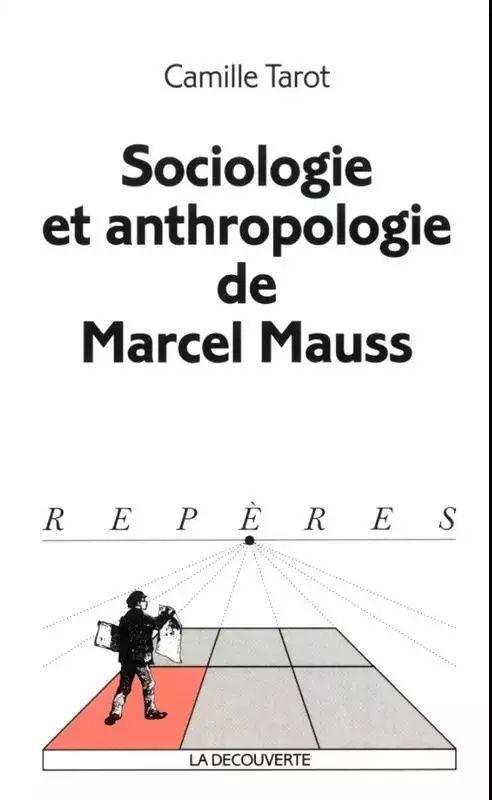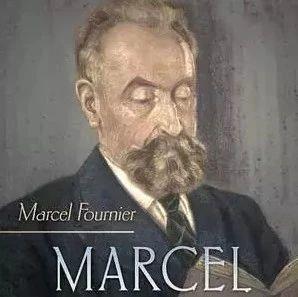

法兰西学派的工作
这些也使得我的学术生涯有两个特点。首先,我与他人协作得过多。这确实占去了我的绝大部分时间。我为涂尔干的《自杀论》出过力(我用计量方法将26,000个自杀案例分类,逐一填在卡片上,并放在65个盒子里)。我参与了他的每一项研究,正如他参与我的研究一样;他有时甚至将我的研究整页整页地加以重写。我与他合作发表过两篇文章,包括我们关于《原始分类》的文章,我负责提供所有的素材。我与于贝尔合作发表一篇有关“献祭”,以及一篇有关“巫术”的文章,还有《历史与宗教之综合》的前言。大略而言,我参与了他所有的严格说来并不是批判性或考古学的工作;而他总是检查我写的东西。尽管我只打算与布卡特(Beuchat)合作,但我不得不从头到尾重做我们有关“爱斯基摩人季节变动”的研究。我与学生和朋友合作进行研究的次数已经数不胜数了。我对目前的负担已经有点招架不住,因为我已经接手出版涂尔干、于贝尔、赫兹身后留下的大量未出版物的艰巨任务。正是因为我的付出,他们的作品才能以每年一卷或两卷的速度与大众见面。我在高等研究院和民族学研究所的教学和管理工作也许太过繁重,拖累了我自己的出版。但如果我的职业良知有如此繁重的要求,我会抱怨吗?我的学生遍及世界各地,其数量和质量都证明了这种教学是有价值的。我指定题目的研究,我确保其成功告成,修正草稿和证据,并启迪他们的方向,这些研究都证明我在这里的工作并非不值一提。要不是战争,它一定会盛极一时。 其次,我科学生涯中的大悲剧并不是四年半的战争中断了我的工作,亦非疾病而徒耗光阴,更非我因为涂尔干和于贝尔英年早逝而感到的极度绝望;在既往痛苦年月里,我失去了最好的学生和朋友,此乃莫大之悲剧。人们会说,这是法国科学界这一脉之损失;而于我而言,堪称一场灭顶之灾。或且,我一度能最好地付出自己者,已随他们而逝。战后我在教学方面重新获得成功,以及民族学研究所的创建与成功(当然大部分归功于我),再次证明我能够在这个方向上有所作为,但这能偿还我之所失吗? 在结束这个话题之前,我想澄清一下目前对我存有的一个带有偏见的误解。有人认为我的教学偏于社会学。并非如此。我的讲座无论多么富于成果,或竟多么无所成就,亦无论这些讲座给予我如许闲暇,或竟令我全然忙碌,它们与我的研究从没有完全合拍过。我担任“野蛮人的历史与宗教”的教席时,我忠于这一巴洛克式的题目,也忠于高等研究院的精神。因此我将自己的教学严格限定在历史的、批判性的、非比较的视野中,即令我所考察的事实唯有从比较的角度才能吸引我。我从没有以此教席从事于社会学的宣传。我在民族所负责教习描述性民族学时,我拟定大纲,并与瑞伟(Rivet)和列维-布留尔一道监督教学、出版还有其他的活动。在这里,我总是将教学限于纯粹的描述性民族学。或许这种责任心和公正可以被当作一种科学美德吧。 无论如何,这些因素表明为什么我在职业生涯之末,希望完全教授我所从事的研究:诸社会的比较历史学,尤其诸宗教的比较历史学。在我这个年纪,我以口头报告作为教学方式,内容为我初步的或已确定的研究,不管是未出版的还是出版但没教过的,这是非常正当的。我甚至想在我的教学计划中添加我的益友们留下的未出版作品;这样,它们的出版就会相对容易,他们的记忆能够得以更好保存,我较宽泛的教学能够收到更广泛的效果;这将不仅是我的,也是他们的教学。我不仅将教授我的研究,也传授从涂尔干、于贝尔到杜特(Doutte)、卡亨(Maurice Cahen)等这些朋友阐发的思想及其证据。  |
已出版作品
|
社会学年鉴
|
理论性作品
|
组织
|
宗教与思维
|
方法论
|
文章来源:中国人类学评论第15辑
Marcel Mauss/ 文
罗杨译、赵丙祥/ 校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