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德]约翰尼斯·费边
出版社: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人类学如何制作其对象
译者: 马健雄 / 林珠云
出版年: 2018-7
定价: 59.80元
装帧: 精装
丛书: 新史学译丛
ISBN: 9787303232161
本书初版于1983年
原作名:Time and the Other : How Anthropology Makes Its Object.
出版社: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在我的记忆中,当时我主要关注和担忧的是人类学会不会错过一个彻底的自我批评的机缘。这样的批评,主要针对伦理上人类学受到的殖民与殖民主义及其遗产的影响,所以应该有些规范和限制。如果人类学无法为殖民压迫进行全方位的辩护,那就要承认这个事实并为之忏悔;要合作,就要补偿。如果人类学能够继续作为一个知识生产的学科存在,它首要的也是主要的问题在于认识论,而非伦理。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谴责人类学,而是希望揭露它是怎样被一种根本性的矛盾所操控。
——约翰尼斯 ▪ 费边
《时间与他者》对人类学的方法论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人类学家的研究对象是“他者”,“他者”和人类学家自身所处的时间、地点、环境都是不一样的,如何更好地理解“他者”,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
——乔治 E. 马库斯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人类学系主任
《文化人类学》杂志创刊人
作者简介
约翰尼斯•费边,著名人类学家,曾在美国西北大学、卫斯理学院等多所大学执教,担任波恩大学、科隆大学、巴黎大学的访问学者。退休前任教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现居德国。他写了很多批评性的著作,《时间与他者》是他的代表作,这本书是人类学领域的经典著作,改变了人类学家“建立研究对象”的方法。
译者简介
马健雄,香港科技大学人文部副教授,长期在滇缅边疆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著有《再造的祖先:西南边疆的族群动员与拉祜族的历史建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
林珠云,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博士生。
内容简介
本书被英语学术界视为人类学经典读物,重点检讨人类学家与他们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特别提出“人类学是西方世界的一种宇宙观”的看法,并为文化批评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所从事的有关人类社会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方向。费边指出,人类学家常常将自己的立场假定为“在此时此地者”,与此同时将他们的研究对象假定为“在彼时彼地者”。因而,人类学将其研究对象作为与研究者所处的时代错开的“他者”。费边在这本书中挑战了西方人类学的“他者”假定。根据他的洞见,在西方人类学发展的历史中,由于人类学家们对“多样性时间”的娴熟运用,人类学的产生、发展和转变,都涉及到人类学背后的权力与不平等关系。许多著名学者因此给了该书极高的评价,乔治 E. 马库斯认为,该书“是对人类学书写的彻底的认识论批评。”
目录
第一章 时间与他者的出现/001
一、从神圣到世俗的时间:哲学家旅行者/002
二、从历史到进化:自然化的时间/014
三、人类学话语中某些对时间的用法/027
四、评估:人类学话语与对同生性的抵赖/032
第二章 我们的时间,他们的时间,没有时间:对同生性的抵赖/046
一、绕开同生性:文化相对性/048
二、阻止同生性:文化分类学/066
第三章 时间与他者的书写/088
一、矛盾:事实或是表面/089
二、现时化:方法还是结束/092
三、时间和时态:民族志的现在时/099
四、在我的时间里:民族志与自传体的过去/108
五、时间的政治性:披着分类学羊皮的时间狼/120
第四章 他者与眼光:时间与修辞的视角/130
一、方法和视角/131
二、空间和记忆:传统修辞主题的话语/135
三、安排的逻辑:可见的知识/141
四、分而治之:他者作为客体/146
五、“符号属于东方”:黑格尔美学下的符号人类学/153
六、他者作为象征:“符号人类学”的例子/163
第五章 总 结/176
一、追溯与总结/177
二、争论的问题/187
三、同生性:出发点/193
附 记 重访他者/205
一、简略的开始:人类学中的“他者”/206
二、在时间与他者中的“通往他者之路”/209
三、时间与他者“之后的他者”/215
四、结论:他者、众他者、他者化——漂浮的与膨胀的概念/223
参考文献(一)/225
参考文献(二)/233
译者后记/259
序言:批判人类学之综合(节选)

格尔茨在巴厘岛
《时间与他者》并不仅仅是费边个人知识发展的结果。它也是人类学批判的产物及其中的一个部分,它标志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学科的改变与重塑。反之,这样一种批判人类学植根于60年代末以来它与政治和社会现实之间的相互影响。“第三世界”的后殖民独立运动、在越南爆发的新帝国主义战争,以及美国国内的民权运动和学生运动,都不免影响到这个具有科学性的学科。表面上看,它不证自明的对象是相对于西方自我的那个他者。在60年代末美国人类学学会的会议上,有关人类学的政治责任与伦理的争议不断升温,尤其针对这一学科赖以产生的殖民政权结构以及继续支撑着它的新殖民关系的历史脉络(参见高夫,1968;勒克莱尔,1972;阿萨德,1973;韦弗,1973)。这些讨论后来成为发表在《当代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和《美国人类学学会通讯》(Newsletter of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上的系列文章。随后若干年,它们不仅见证了对“重新塑造”人类学的强烈呼吁(海姆斯,1972a),而且沿着这样的路径,一批激进的期刊创刊了,如《批判人类学》(Critical Anthropology,1970-1972)、《辩证人类学》(Dialectical Anthropology,1975ff.)和《人类学批评》(Critique of Anthropology,1980ff.)。
然而,置身于这样的情景中,尽管是就其实际各持己见,但它们也有共同的敌人:一种霸权人类学的研究假定和实践。这种研究自称从属于自由人文主义,立足于对非政治、无偏见的科学实证主义的信仰,其客观性是由保持距离的中立来保证的。在这种人类学中,构成性的分析工具是基本的相对主义概念,它宣称所有的文化表现就质而言是一样的。

托马斯·库恩
这一立场支配了美国人类学的文化取向、英国社会人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方法,虽有例外,但法国的各类结构主义同样如此。人们对这一立场的批评多是从科学性和政治性的视角出发的。近期值得关注的有关科学史与哲学的讨论,特别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关于科学范式的议题(库恩,1962)、鲍勃·斯科尔特(Bob Scholte)的批评对人类学的中性立场与价值中立持反对意见。作为一个根植于稳固的社会与文化权力结构之中的学科,人类学并不比其他任何学科更有能力声言能够在调查中多大程度地避免政治的影响。不过,就人类学来说,其所处政治条件及形势更加令人不安,即它的学科规范产生于西方帝国主义扩张的语境中——现实是,其结构性后果促成了后殖民与新殖民这两种条件下的人类学知识生产(斯科尔特,1970;1971;1972)。这样看来,对人类学传统的“对象”的持续性压制、学科的距离性的客观化,并没有让它成为非政治的科学性行动,反而让它的角色变得更加清晰可见,即作为侵略性殖民工程的一个部分,它以其自身的他者作为代价来守护西方的特权。因此,文化相对主义的口号还伴随着大量价值中立的专业队伍,这比披着伪善的外衣来主张其霸权的影响更大一些。我们能看到人们为什么失策:因为承认了西方权力的征服,或者将它作为话语主题,因而善良地屈从了(斯科尔特,1971;戴蒙德,1972;韦弗,1973)。
随着社会文化人类学的政治取向批评的发展,对人类学知识生产中占统治地位的认识论的反对意见不断涌现。费边的《语言、历史与人类学》(该文最初醒目的标题为“语言、历史与一种新的人类学”)就是这类反对意见中的一个代表性文本。就像斯科尔特,费边批评了人类学方法论中的实证主义核心,并指出学术实践中反思的缺失(费边,1971a)。就这两点批评而言,直观上他者的客观化并没什么问题(例如,作为人类学逻辑假设的经验性对象,或者具象化的文化类型),不过他指出这是一种非常有问题的科学帝国主义表现方式,因为它支持人类学家对他们在民族志田野工作中基于文化互动的真实性获取的数据进行无限的、抽离具体脉络的操控。这样的实证主义方法不仅回避对相关文化与社会语境进行反思,而且否定了他者在与民族志工作者一起行动及互动中的主体性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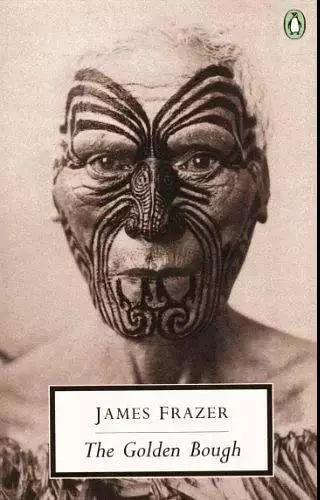
The Golden Bough
接着,这些针对民族志实证主义的批评成为建设新型批判人类学构想的基础。这样的新人类学,其中心是回应对政治相关性、道德责任和社会解放的取向的诉求。以互为主体性经验、团结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为基础,这是建立新形式的人类学内涵的基石,并让它来取代新殖民主义再生产对西方之他者的压制。这种压制是借助通过距离实现的客观化来实施的(海姆斯,1972b;贝里曼,1972;斯科尔特,1971、1972;韦弗,1973)。
这样一种批判人类学的认识论基础,建立在对民族志实践全方位的自我反思的前提之上。于是,斯科尔特提出,不仅应该对隐藏着政治行动的人类学学科历史重新进行批评性的评价,而且应该重新评价人类学知识生产中自觉的反实证主义和反思性问题(斯科尔特,1971、1972)。就像费边在《语言、历史与人类学》中指出的,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将民族志田野工作视为互为主体的实践性的立场,因此它属于天然的诠释学实践。这样的实践突破了西方主体的分析性霸权,利用置身于沟通理解中的具体的生产性对话情景,将其视为人类学知识的概念来取代前述西方主体性分析霸权。作为一种辩证的事业,它是互为主体性的整体中的一部分,不仅因此搁置了研究中的自我与被研究的他者之间的区隔,也在寻找永久性的自我超越。放下客观化的相对主义,人类学就能够追求一种理解和反思民族志的解放的理想,视民族志的洞察为前进的、政治的工具(斯科尔特,1972;费边,1971b)。

田野调查中的马林诺夫斯基
在70年代初期的理论宣言的激励下,一些学者开始努力为推进批判人类学的研究设立基本条件。例如,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根据他对摩洛哥田野调查的系统性反思所设计的方案,或者凯文·德怀尔(Kevin Dwyer)和文森特·克拉潘扎诺(Vincent Crapanzano)的努力也都基于他们在摩洛哥的材料来共同发展一种那个时期的对话性人类学(拉比诺,1977;德怀尔,1979、1982;克拉潘扎诺,1980;参见泰德洛克,1979)。费边的《时间与他者》写于1978年,也出现于同一时期。它延续了同样的发展趋势,甚至对这一新兴的传统作出了关键的贡献。这本书对异时论作为人类学话语的构成性要素所做的全方位批判,一方面是根据批判人类学原则展开的元分析,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对民族志实践的反思所做的“扬弃”的辩证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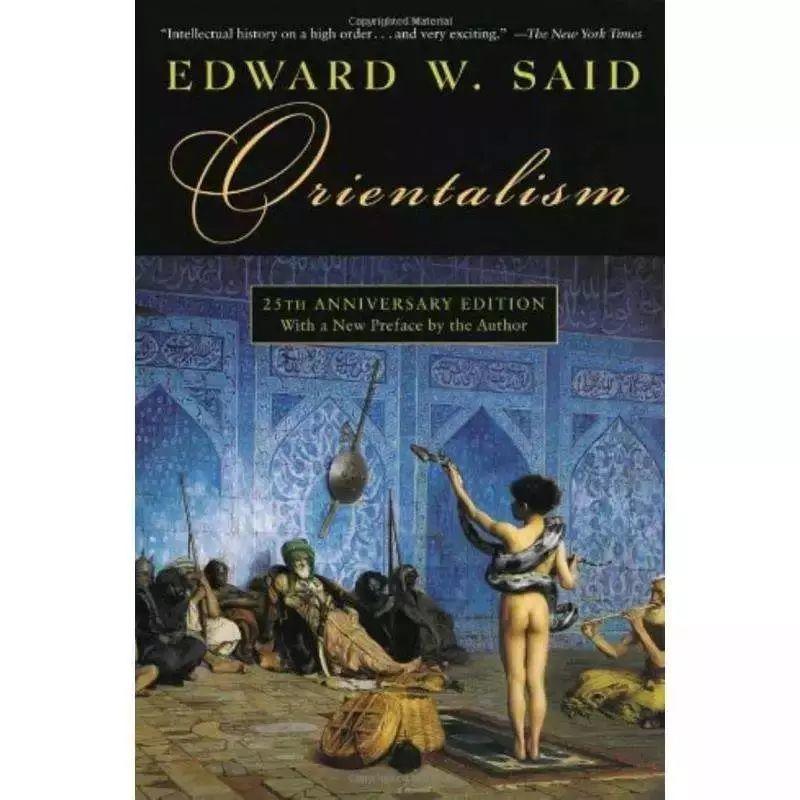
Orientalism
同时,费边将他对异时论的考察与修辞性图式的有力分析联系起来,将这一开创性的话语建构批评与人类学对象、批判人类学的解放理想相提并论,强调后结构主义对他者的表现方式的研究。对于费边而言,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介入起到了一种重要的鼓舞人心的作用。这是一种清晰的与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同时对“东方学”进行的平行的、针对话语构成的分析,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聚焦于西方文本中想象的、成套的、固化的、以东方为标志的他者(萨义德,1978)。费边自己也注意到这两本书“在意图与方法上的相似性”。和《东方学》(Orientalism)一样,《时间与他者》阐述了针对政治性进步和积极反思性的认识论的综合分析,并借助文本生产中的修辞性元素进行了批判性辨析。以民族志为焦点,它是建设迈向《写文化》(Writing Cluture)道路的关键性的一步。有理由说,《写文化》是一部美国人类学处于世纪的转折点上最有影响的著作(克利福德与马库斯,1986;参见马库斯与库什曼,1982;克利福德,1983)。
* 就人类学研究中激进被重新定义的角度看来,根基稳固的人类学有这样极端的反应并不奇怪。前述种种,《重新塑造人类学》(Reinventing Anthropology)的出版,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斯科尔特,1978)。1975年,费边自己成为人类学专业核心机构卷入争论的主要对象(贾维,1975;参见费边,1976)。
本文经公众号” 新史学之友“授权转载,欢迎关注!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