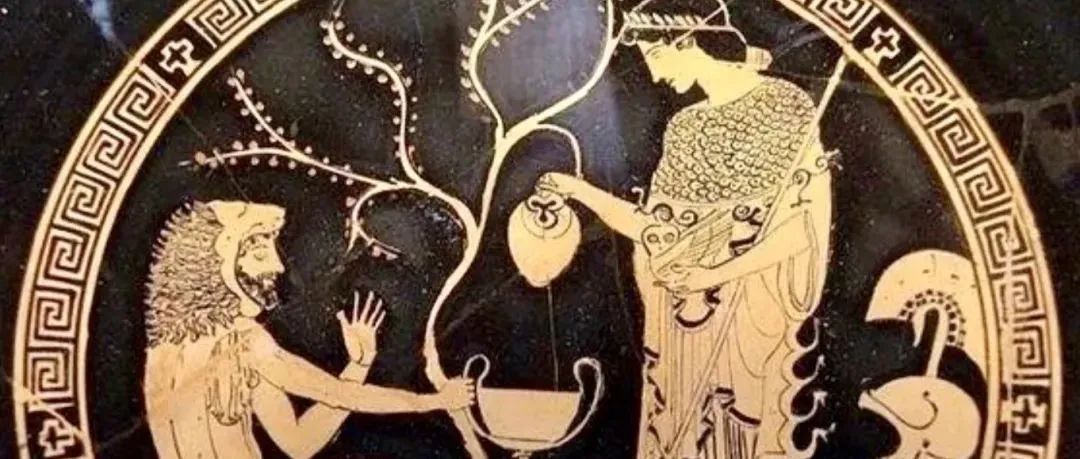
点击上方“民俗学论坛”可订阅哦!
//
口头诗学的文本观
朝戈金
原文刊载于《文学遗产》2022年第3期

内容摘要
在口头诗学视野中,音声文本的听觉属性使其在传播过程中被“整序接受”。“往昔的音声”转化为“书写的遗骸”,进而具有口头和书写“双通道双媒介”的特征,两者既各自发展又彼此纠缠,言文互缘,形成“文本聚簇”现象。文人制作的口头文学作为“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具有“言文桥接”的文学再生产意义。口头文学演述人的“大脑文本”则由“三层两径”构成其基本属性,在演述传统的规律性运作下源源不断地生成为多重形态的口头文本。口头文本的文类归属以谱系关系共存于文化生境中。在演述过程中形成的口头文本,还往往带有“伴生文本”,而演述人及其受众都深度参与了文本意义的共时性制作和历时性传承与传播。
关键词
文本性;整序接受;
言文互缘;文本聚簇;大脑文本

本文以“口头诗学”(oral poetics)为论域,在与书面文学的对照中讨论口头文学文本的几个基本问题。这里的“口头诗学”是指一系列从不同侧面研究口头文学的理论建构的总括,包括在20世纪围绕文学研究而发展起来的部分或主要理论流派——以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故事形态学等为缘起和推进,以北美的口头程式理论、讲述民族志、演述理论等为系统化发展的理论体系[1]。个别不在北美学术流派中但对口头诗学贡献卓著的学者,如芬兰民俗学家航柯(Lauri Honko)等,也被视为构建口头诗学理论体系的领军人物。在口头诗学的晚近发展中,中国学者基于本土的丰厚材料和理论积淀,立足扎实的田野调查研究成果,博采东西方口头文学理论之精粹,已然展现出参与建构口头诗学的理论追求,并得到国际学界的肯定[2]。本文不拟全面讨论口头诗学视域中的文学文本观,而是以书面文学的文本观为对照,从若干环节渐次展开比较,进而就有关口头文本的代表性论见作出评析,同时就若干概念工具的引申和发展进行阐释。
本文较多地参考了国外同行的成果。有些术语,如“歌”(song)和“歌手”(singer)在英文著述中分别指涉口头诗歌(oral poetry)和口头诗歌的演述人(performer)。为尊重作者的原文,行文中不强行与国内的惯常用法相统一。本文使用的“文本”概念,既指由书写符号构成的系统性艺术表达的语篇或片段,如一则记录下来的传说;也指一组言语交际符号或视觉表达符号构成的系统性表现形式,如讲述一段故事,吟诵一首歌谣,往往都会同时诉诸人的听觉和视觉。笔者在这里还会同时使用“口头文本”(oral text)和“音声文本”(voiced text)两个概念,虽然二者大部重合,但各有侧重。口头文本通常直接生成于口头交流的现场,以即时性的演述行为及其当下达成的功能和意义为表征;音声文本则是通过书写技术所留存下来的言语交流信息,其时空属性往往植根于过去的口头传统和演述实践。按我的理解,二者都包括但不限于摹拟音(ideophones)、超语言(paralinguistic)、身势语(kinesic)以及可能伴随文本意义生成的音乐、舞蹈、仪式行为、图像等要素。

一、音声文本和“整序接受”
文学的文本大略分为作家书写的文字文本和民间口传的音声文本。从人类使用信息技术的角度看,口头传统出现在前且使用至今[3],书写传统后起但在晚近占据支配地位。两相比较,口头文学在数量和种类上远远超过书面文学。弗里(John Miles Foley)说,人类有史以来只发展出大约一百种“地道的[书面]文学”传统(*),这与人类社会一共发展出大约七千种语言和三千种文字相比(*),简直不成比例。中国是世界上语言和文字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民族古文字有约四十种[4],语言则有一百四十种[5]。在中国境内诸民族中真正发展出“地道的书面文学传统”的也为数不多。
口头文学在历史上曾经风光无限。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最负盛名的畅销书如《圣经》和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及《奥德赛》最初都是口头传承的,这在今天的学界已经成为共识。回到东方文化传统来看,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特别是“十五国风”,最初也来自口头;而印度长达20万诗行的大史诗《摩诃婆罗多》虽然有抄本系统(分南传本和北传本)长期流存,但最初的创编和演述也是口头的。可见,文学伟大还是平庸,在于是否具有深厚思想内涵和惊人艺术力量,而无关乎产生自唇齿之间还是笔端纸上。
在口头文学文本的分类上,史诗和口头传统研究的两位旗手弗里和航柯的意见高度一致。[6] 他们以史诗为本,作出如下分类:(1)口头文本或口传文本;(2)源于口头的文本;(3)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这三类文本的代表性样本,分别是藏族史诗《格萨尔》,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以及芬兰伦洛特创编的史诗《卡勒瓦拉》。这里述及这一影响很大的分类法有几个原因:第一,该分类法虽然是关于史诗的,但史诗被认为是“超级文类”(super genre)——在其形成和流布的过程中,吞噬和吸纳了其他口头文类,如歌谣、故事、传说、谱牒等,所以不能简单与其他文类等量齐观,而应视之为统领性文类。第二,因史诗内容无所不包,往往被誉为社会文化生活的“百科全书”,所以史诗是主旨远阔的多面相文类。第三,在文体方面,史诗散韵兼行,长篇短制咸备,在格调上是神圣性和世俗性两通,幻想性和纪实性皆有,故当视为形式多重的文类。第四,在语言艺术上,许多史诗是各自诗歌发展的高峰,故当视为语言艺术的典范性文类。第五,在世界各地,关于史诗的调查、记录和研究相对较多,所以史诗研究是较为成熟的领域之一,也是进一步拓展文艺理论空间的最佳支撑点。
回到本文的基本问题上来,人类眼和耳两个感官以及目治与耳治两种能力,径直地对应着口头和书面两种文学形态,于是产生出不同的文本解读规则。不过问题不像看上去的那么简单。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在讨论视觉和听觉关系时曾转引萨丕尔(Edward Sapir)的论断:语音语言(音声)优先于所有其他类型的交际符号体系,相比之下,所有这些交际符号要么是替代性的,如书写;要么是过度补充性的,如伴随讲话的手势[7]。换言之,萨丕尔认为语言作为交际符号具有优先性。雅各布森则认为这种说法还需要进一步论证和澄清,理由是视觉和听觉的关系是在时间和空间中按照不同的法则在不同的维度上展开的:“视觉和听觉的知觉都显然是发生在空间和时间中的,但视觉符号的空间维度优先,听觉符号的时间维度优先。复杂的视觉符号包括一系列同时发生的成分,而复杂的听觉符号通常由一系列连续的成分组成。”(*)不过这是就这两种知觉方式的一般倾向而言的。当一个语言表达单元出现时,直接记忆或即时记忆(immediate memory)[8]会发生作用,从而让线性的口语流(verbal flow)转为以整体面貌呈现。“在这个阶段,整个序列,无论是一个词、一个句子还是一组句子,都表现为一个同时呈现的整体,通过‘同步合成’(simultaneous synthesis)来解码。”[9] 弗里在论及口头诗歌的接受时,曾用“整数的内在共鸣”(immanent resonance of these integers)来说明口头演述的“语力”(word-power)[10],这就与雅各布森的上述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
以雅各布森和弗里的论述为基础,笔者的进一步的阐释是:叙事中每一个程式化表达单元都可以理解为一个“整数的序列”(a sequence of integers),可简称“整序”,即在口头交流过程中出现的信息整序[11]现象,例如《伊利亚特》中“宴客”的典型场景,或蒙古史诗中“备马”的典型场景,有经验的受众会以“同时合成”的“整序”面貌加以接受。笔者将其称为“整序接受”现象。在演述人这一端,其曲库中的那些分属不同层级的大小表达单元,如语词程式、典型场景和故事范型等相对固定的“观念部件”(idea parts)[12],在演述中顺次流出,常被形容为“口若悬河”,其实此刻的语言流更似落下“大珠小珠”。在受众接受端,在时间维度上线性出现和消失的口语流,就被受众脑海中预存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模式识别为一个一个的“整序”来接受。用个比喻性说法,叙事过程犹如吐出一串珠子,而接受过程有如渐次接下一颗颗珠子。于是,每次说到雅典娜,都是“灰色眼睛的雅典娜女神”(《伊利亚特》);说到格斯尔,都是“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格斯尔》);说到掠夺敌国,都是“把他的奴隶全部赶来/不要给他留下一条母狗/不要给他留下一个孤儿”(《江格尔》)。即便在一个诗章中重复几十次也绝不拆散——在口头文学的表达中这都是不可分的“整序”。“整序”方便了现场创编,但常遭到来自书写文化立场的诟病,谓之“口内连罗”“本头活套”,这其实是两种不同的信息接受和解码方式的差别造成的理解错位。再回到听觉和视觉的差别上来,文字符号的重复会令眼睛“不忍卒读”,但用耳朵去听却往往并无问题。这或许与符号呈现方式有关——在相对的意义上说,共时呈现的符号重复更为刺眼,而历时呈现的符号重复则不仅不刺耳,反而时时带来提示和加强的效果。

二、“书写的遗骸”和“言文互缘”
“书写的遗骸”(written remains)这个醒目用法,来自研究《圣经》的学者赫龙(Holly E. Hearon)的文章《从“口头性”入手研究圣经文本》[13],是指往昔活态的口头传统被书写下来成为僵固的遗骸。在文字初创时代,口头传统和书写技术彼此常纠缠在一起,令熟悉书写规则的今人感到费解的是,那些古旧手稿的字词之间没有空格和标点,没有段落和章节,释读犹如猜谜般充满挑战。在赫龙看来,既然无法从页面安排布局上找到切分依据,就须另辟蹊径,譬如通过大声朗诵,让耳朵听到从一个音节到下一个音节的顺序,可能反倒是进入文本世界的有效途径,何况那还是音声交流占据支配地位的时代!再进一步,这些“书写的遗骸”大抵是“口述录记文本”(dictated text),因此通过口头演述寻找其意义传递和实现的路径应该是合理的[14] 。赫龙接着说,对于已经远离当时传统的我们而言,对这些遗骸意义的理解,还需要同时考虑可能的演述人和受众的情况,以及制作文本时的时间和地点等网状关系构成的多重维度。[15]
纵观中外文字发明和使用的历史,一个社会从单纯口头交流,到发展出一套尚不稳定的书写系统,混乱局面是难以避免的,秦朝施行“书同文”就是证明。起初,负责抄写工作的多是社会底层人员。从古希腊—罗马时代设置的缮写室(scriptorium)和抄写员(scribe),便可大致想见当时的手稿制作情形。抄写中必有“内部知识”和行规,从中国书法碑刻中的重文号、删除号、颠倒号等的使用也可推知这一点。一般认为,希腊的线性文字B(Linear B)的发明和使用早于荷马时代,但并没有被用来书写荷马史诗。在古典时期(公元前480年—公元前323年),口头演述荷马史诗是每年在雅典隆重举行“泛雅典娜赛会”(the Panathenaea)的重头戏,众多来自不同城邦的诵诗人(rhapsode)竞相登场献艺[16] 。这倒是能说明,即便有书写技术,口头演述仍在彼时彼地大行其道。晚些的例子还可以举蒙古族史诗《格斯尔》。故事最初在口头流传,到清代陆续出现了木刻本(1716年)和多种手抄本,但活跃在民间的口头演述仍然是最主要的传承方式。不过口头文本和书写文本之间有复杂的彼此影响关系。有学者认为北京木刻版《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1716年)传入卫拉特地区后,当地歌手和文人以之为基础,结合当地叙事传统,“对其进行了适当的增减或运用,并且运用卫拉特方言再创作,于是形成了与北京版《格斯尔传》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相似且又不同的卫拉特《格斯尔》”[17] 。布里亚特诸多口头格斯尔故事也与该木刻本之间有清晰的对应关系,这说明文字文本影响了口头文本[18]。总之,在文字书写使用的初期或不太普及的阶段,口头和书写的“言文互缘”[19]是常见现象。
口头诗学所聚焦的“源于口头的文本”,有时也被行内称作“往昔的音声”(voice from the past),专指那些历史上曾口头演述后来靠手稿等载体才得以传承的史诗(*)。如《尼贝龙根之歌》,历史上可能有过繁盛的演述活动,但今天只有三份手稿存世,分别庋藏于慕尼黑、圣加尔和多瑙艾兴根。至于被谈论最多的荷马史诗,其文字写定过程十分复杂。大致说来,在众多歌手演述的同时,便开始出现各类抄本。后来有人以其中某些本子为底本,汇编整理出来更为完整的文本。今天所见《伊利亚特》威尼斯A抄本(the Venetus A)和《奥德赛》劳仑提亚努斯抄本(the Laurentianus),皆为经过编订且堪称最为完整的文本。
荷马史诗的创编是口头的,但随着书写的介入,就形成了“口述录记文本”。所以,从其创编到写定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且是在口头与书写杂错间发展成形的,于是其传播过程也体现为口头与文字并行。所以,在前引弗里和航柯的分类中,言文并置,眼耳双通道接受,聆听的荷马史诗和阅读的荷马史诗分别对应不同的接受场景。据报告,在古希腊贵族子弟接受教育的课程中,就有学习荷马史诗的内容,这简直就是中土“不学诗,无以言”的有趣对照。总之,“源于口头的文本”在整个文学从生产到接受的环节,大概都是“双通道双媒介”的文本。这也是书写技术和口头传统彼此虬结时产生的特有现象。这种“双通道双媒介”现象不仅表现为一个社会同时使用两种媒介上,还表现在两方都有众多人士参与的现象上。如荷马史诗的演述人数量可观,所以才能聚集起来参加竞赛活动,而根据文献记载,古希腊的各城邦当时至少有上百种抄本流传[20]。这就进一步说明,书写文本在起初是附属于口头文本的,并没有所谓的“权威本”来一统江湖;同时还说明这些口头文本不仅彼此不同,也没有明确的高下之分,才有分别记录并形成不同书写文本的可能。假如允许我们进一步推测,很有可能某些书写文本会对口头演述产生一定的影响——造诣不佳的演述人可能怀揣稿本,用作“提词本”(prompt)以弥补其现场演述能力的欠缺。随着编订工作的开展,荷马史诗的标准化和定型化很快就完成了。这当然可以解读为书写文化法则对口头文化法则的一次胜利。就对口头和书写两种媒介的利用而言,总体上是转入了一个此消彼长的快速演变轨道。随着古希腊口头演述史诗传统的式微,以及阅读人口的增长,对视觉和听觉的利用也发生了偏转,阅读荷马而不是聆听荷马,就逐渐成为荷马诗歌接受的主流。
需要强调的是,在荷马时代,荷马史诗的书写文本与口头文本仍然应当视为一种一体化的“言+文”系统:二者必定是互缘的,这是第一层。荷马史诗与其他古希腊史诗曾经也当构成“互文”关系,纳吉(Gregory Nagy)也有同样推测[21],他认为在“英雄诗系”(the Epic Cycle)中,与荷马史诗构成互文的,至少有与特洛伊战争相关的《塞浦路亚》《埃提奥匹亚》《洗劫伊利昂》《归返》《特勒戈诺斯纪》等史诗,惜今仅存残篇,这是第二层。事实上,在世界上许多地区都能观察到在史诗群落中诸史诗形成互文的情况,以蒙古史诗传统而言,特定史诗生长在特定的精神文化土壤中,与其他同群落史诗共享程式片语、典型场景、故事范型等一系列单元和要素。小到语词程式,如一句“眼喷烈火,面放异彩”,居然数百年间出现在众多不同的史诗故事中[22];大到“母题系列”,数百个长篇和短篇史诗,是按照十四个母题系列中的若干系列来构造故事的[23]。在故事范型层级上,仁钦道尔吉总结说,蒙古英雄史诗的两大主题,是婚姻和征战[24] 。回到古希腊,荷马史诗在口头演述和文字抄本之间形成互文,史诗中的人物、事件、情节、场景等也出现在古希腊戏剧、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中,彼此构成互文。所以,对“书写的遗骸”进行阐释,就一定要将之置于由不同维度的绳索编织的意义之网中。来自中国的例子能进一步说明这种情况:藏族格萨尔史诗传统不仅以语词艺术形式广为流布,而且与唐卡、藏戏、石刻等形式共同流传,彼此形成互文。在语词艺术世界中被描述的形象,又在其他艺术形式中得到具象化的呈现,并且形成特定的传统,如藏戏中的服饰,唐卡中的构图等。特别是部分史诗演述人还会在演述故事时悬挂格萨尔唐卡,让语词营造的意象与视觉艺术有所融合。进入当代,随着社会需要的发展,又出现了漫画、影视艺术等。这种情况说明,活形态的口头传统会在不断发展中以惊人的存续力和创造力不断催生出新的艺术表现形式。
口头演述和传播的文本,常常呈现为聚簇的形态,我们尝试将其命名为口头传统中的“文本聚簇”现象。在民间的长期流传中,长篇故事或故事群总是诸“本”(不得已用此书写文化概念)并出。唐代李商隐“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诗句,道出了民间广为传颂“三国故事”的情景。一旦这种聚簇现象出现,就说明在这些口头演述的众多音声文本之间,构成了平行和错落的网状关系,而不是以某个“权威本”为中心构成辐辏关系。因为没有权威的规制,口传文本体系就具有开放性特点:随时吸纳新因素以固本出新,随时做出叙事策略的调试以迎合时下风尚,这就与书写文本一旦完成就闭锁起来的状态不同。那么,这些“书写的遗骸”就因为与口头文本的互缘关系,自动获得了口头文本的开放性特点,乃至在不断的成文过程中出现“文本聚簇”现象。我们今天见到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只不过是历史上众多文本中的偶然流存下来的两个荷马史诗文本,对它们的解读也应主要参照口头文本的规则来进行,即调用希腊神话、戏剧、绘画、历史等诸多参照物,同时考虑到作为其背景的“文化生境”。不过,要说口头/书写的“文本聚簇”,大概极少有哪个事例是能超过印度《摩诃婆罗多》的。这部史诗光是形成完整故事就用了大约八百年时间,后来又长期以口传和抄本两种形态传承并广为流布。晚近印度班达卡尔东方研究所主持的“精校本”是以“青项本”为基础,广泛参照了南北两个传本系统的大约七百种比较成型的文本编订而成的[25] 。而主要依靠口头传承的《摩诃婆罗多》故事,则在过去的大约两千年中从本土流传到周边诸国,以口述、书面、戏剧、皮影等多种形式传播。以这样的观点去看《诗经》的最终定型,其背后的道理大约也是一样的——虽然具有书写的形式,但最初可能也是诸本并出,从而有“文本聚簇”现象。其间的规则和特征,也时时与口头文化相关,所以引入口头诗学的解读方法亦属必要。王靖献《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26]一书就是这个方向上的有益尝试。
以口头诗学的理念来看,口头文本的解读方法有很多,例如程式化语词和片语,重复出现的典型场景,以及传统性的故事范型等。弗里对荷马史诗中“宴客”这一典型场景的多次出现所做的统计(包含主人/宾客、落座、举止、满意、调节等诸项),是典型场景按照特定格式和顺序反复出现的最具说服力的样板[27]。弗里还创造并使用了术语“传统指涉性”(traditional referentiality),意指口头诗歌中无法通过字面意思了解其含义的单元(*),如荷马史诗中出现“肥胖的手”意指“勇敢地”,出现“绿色恐惧”意指神要干预人间事务等(*)。以往有学者基于书写规则断言这是抄写中难免出现的“鲁鱼亥豕”,直到口头诗学理念的出现,结合彼时彼地的社会文化语境和文本聚簇中已经约定并共享的指涉性(有时要调用更大的社会文化语义网络),才能解读隐藏在文字符号背后的丰富意涵。作家在进行文学生产活动时,断不会制造这种他人不明就里的指涉,因其不利于文学的传播和接受。作家使用比喻,总是要在两个容易引发联想的事物之间建立联系。但口头文本是传统性的,一经约定俗成,就可以放心使用,无须担心给受众带来理解困难。顺便说一句,这种口语文化的智慧和法则,在今天的网络空间也能大量见到——特定语词的含义不能从字面上理解,意义是被传统或某些机缘另外“约定”了的。总之,只有在传统中历经千锤百炼和被广泛接受之后,传统指涉性才会变成高度凝练的、充满语词力量的表达单元。当然,互联网技术的瞬间交流和广泛参与特性,让今天形成“传统指涉性”的速度提高到令人咋舌的程度,与传统社会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形成约定的节奏相比,犹如马车遇到高速列车。
不过,幸亏有了书写技术,才彻底地克服了口头传统在存续力方面的脆弱性。那些遥远过去的口头音声,通过书写符号留存下来,虽是“遗骸”,却也让我们有机会体认往昔口头演述的大致样貌。需要强调的是,口头文本的定型化常常呈现为一个“过程”,而非一次写定就大功告成。纳吉曾指出:
荷马史诗作为文本的定型问题可以视作一个过程,而不必当作一个事件。只有当文本最终进入书写写定之际,文本定型(text-fixation)才会成为一个事件。但是在没有书面文本的情况下,也可能存在着文本性(textuality)——或更确切地说是文本化(textualization)……史诗的荷马传统按其自身的再创编模式,呈现出流变性越来越弱而稳定性越来越强的特征,随时间的推移而缓慢地向前发展,直至一个相对静止的阶段。(*)
关于荷马史诗文本化的过程,今天所能见到的资料极为有限。但纳吉通过转述一则传闻,告诉我们这个过程可能经历了三个步骤,分别对应着誊录本(transcript)、底本(script)和经本(scripture)。这则传闻说,最初是不诚实的泰斯多里德斯(Thestorides)说服荷马要从其唇齿之间记录诗歌(誊录本),打算让这个记录本成为底本(他本人仿冒荷马演述时的稿本),以达到让这个有权威来源且由他自己演述的故事成为受到认可的典范[28] 。从这则传闻中我们能解读出来的信息是:首先,只要有人掌握了书写技术,那么口头演述的文本是可以方便地制作成文字文本的;其次,这个写定本有可能被重新用于现场演述,并且巧妙地遮掩演述人不具备现场创编能力的事实;再次,只有通过在演述中得到受众认可,演述人才能获得声望。重点在这里:光是一个抄本不足以建立权威性,只有演述人和他具有的演述才艺,才是被当时的社会认可的关键。至此可做如下总结:在书面文化中,精校本至上;在口头传统中,演述人至上;若是“双通道双媒介”的情况下,杰出歌手的地位也当在稿本之上。所以,读者的口碑造就了书面文学经典,阅读聚焦文本;受众的口碑造就了口头文学大师,接受聚焦演述行为。这与口头文学具有演述性(performativity)相关,演述的内容固然重要,但演述人往往更重要。一个常见的现象是,传统环境中支付酬劳,依据的是演述人的名望,而不是他的故事。这就像时下的音乐会,演唱同一首歌,一流歌手和末流歌手的出场价码不啻天渊。由此联想,“孔子删诗”的旧说倒是符合口头文化的规则:《诗经》从誊录到作为演述的底本,再到作为经典被编定,需要一个过程,但尤其需要假权威之名,方能成全。

三、“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
与“言文桥接”
在航柯和弗里提出的“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29]中,最为出名的当属芬兰史诗《卡勒瓦拉》(Kalevala)。伦洛特(Elias Lönnrot,1802—1884)是芬兰语文学家和口头诗歌搜集者。他在乡间行医过程中大量接触到民间诗歌,引发了他搜集整理和刊布这些诗歌的想法。他先后出版有《康特勒琴》《卡勒瓦拉》《康特勒琴少女》《谚语》和《芬兰语—瑞典语词典》等。其中史诗《卡勒瓦拉》出版过不止一个版本,给他带来了巨大声誉,并很快就产生了国际性影响。世界上主要语言都有该诗译本,仅英语译本在过去一百多年间就有三十种之多。
芬兰并没有一部长篇史诗构成伦洛特编缀《卡勒瓦拉》的基本骨架。按照航柯的说法,芬兰﹣卡累利阿的史诗短歌(epic lays )主要发现于芬兰东部边界地区和若干相邻地区。这些短歌在本质上是史诗,但一般只有一百到四百诗行,经常出现在劳作间隙以娱乐民众,或出现在节日和庆典等场合。芬兰民间还有诸多咒语、婚礼歌、狩猎诗和各种抒情歌谣,以及其他各种诗歌样式,它们都是“四音步”扬抑格的格律(*)。以荷马史诗和《埃达》(Eddas)为样本,伦洛特追求一种相对松散的线性叙事结构,但在编纂“老卡勒瓦拉”(32诗章,12078诗行,1835年出版)时,他还是遵循了若干杰出歌手的“大脑文本”(mental text,将在后面讨论)。随着所掌握的民间诗歌从内容到形式的进一步丰富,他宣称他也拥有了歌手的权威,进而按照自己的“大脑文本”开始编缀诗歌。其结果是“新卡勒瓦拉”(50诗章,22795诗行,1849年出版)的面世并引起巨大轰动:芬兰拥有了民族史诗,增强了语言文学方面的自信,有了文化认同的标志,并从此在欧洲文学版图上拥有了一席之地。[30]
伦洛特的工作方法和背后的理念值得总结。在创编“老卡勒瓦拉”时,他创造了一种“多重音声的对话”(multiple-voiced dialogue)模式来呈现史诗故事。至于作为叙事者的伦洛特,虽然也出现在诗歌中,但却尽可能低调和隐身。经过学者仔细研究,伦洛特本人的独创部分,只占整个诗歌的3%,主要作为歌者发声(*)。总之,在编缀这部史诗的过程中,伦洛特以其三重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置身芬兰历史之中的故事讲述人;二是搜集、组织和出版史诗的中间人;三是芬兰历史文化的阐释者和代言人[31]。
伦洛特的开创性工作具有几方面的意义:首先,历史上“源于口头的文本”或“书写的遗骸”总体上是口头传统的派生产物,是在承载叙事的媒介上发生了转移。伦洛特则不同,他是有意识要创造民族史诗,以顺应时代的要求。所以有学者说,伦洛特既是过去的复活者,也是未来的幻想家,更是将芬兰民间诗歌所蕴含的精神与当时西欧社会文化思潮结合起来的诗歌编纂者[32] 。他的“以传统为取向”的文学创编活动,在史诗谱系中占据了专属位置,赢得了世界性认可。其次,伦洛特的史诗构合,完全是建立在他对芬兰传统诗歌(乃至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的全面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他比任何一位芬兰民间诗人对民间诗歌的了解都更全面,进而还将这些民间诗歌与民族意识觉醒和文化认同潮流相整合,指向自由和进步。这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严酷统治时期尤其可贵,而且大大提升了传统文化的境界和现实意义。伦洛特则成为传统的权威代言人,获得了无可否认的文化地位。再次,伦洛特所搜集的史诗短歌,原本是创编出来供聆听的,但他心中的预期受众,则都是用眼睛阅读的。文学接受活动从原来的供耳朵聆听,转到新文本的供眼睛阅读,就完成了从“耳治”到“目治”转变。洛伦特通过将民间叙事材料加工打磨整体贡献给精英和社会各界,让芬兰的知识界和广大民众从传统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力量,也就让传统艺术和思想获得了“第二次生命”。用航柯的话说:“最终口头诗歌在自然环境中开始凋敝,但其第二次生命通过这部民族史诗在国家的文学文化中得以延续。”(*)伦洛特的工作,就为口头文学在书写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如何自处和发展,做出了有价值的探索。最后,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占据了文学版图的两翼,在中间地带还有诸多“过渡性”现象。作为打通二者的杰出代表,伦洛特“以传统为取向”,大量使用民间材料,以民间诗性智慧法则为本,以创编“民族史诗”为鹄的,将短歌熔铸为鸿篇巨制,不仅成就了其个人一生的伟绩,也造就了芬兰民族文学的辉煌——在层峦叠嶂的世界史诗版图上出现了一座新的高峰。
除了像伦洛特这样热心关注民间诗歌的搜集整理人,也有假托古人或名人的冒名者,一个久负盛名的例子是关于莪相(Ossian)的诗作。苏格兰诗人和翻译家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1736—1796)曾刊布《莪相之诗》(The Poems of Ossian,1765),声称这是公元3世纪苏格兰说唱诗人莪相的作品,一时名动全欧洲。《莪相之诗》中流露出来的英雄主义精神和田园牧歌格调,对早期欧洲浪漫主义运动影响很大,歌德、司各特等人对其极为追捧。斯塔尔夫人认为欧洲文学有南北两个源头,南为荷马,北为莪相,足见其影响。这些诗歌后被证实是假托之作[33],麦克弗森的作伪方向是尽力模仿民间风格。与之形成有趣对照的是蒲松龄,在其《聊斋志异》中有诸多篇什改写自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由作者对民间材料进行了萃取和提炼,再以典雅文言写成供案头阅读的经典,赢得了长久的称赞。两种跨界利用材料,两种后果,不能不令人深思。
以今人版权意识观之,则假托、冒名等实不可取。不过,版权的观念和制度建设是私有制充分发展阶段的产物。在人类文明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知识、自然资源、技术和艺术创造都是共享的,没人声索版权和连带收益,也因为这种无障碍共享,大大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不仅各有其从生产到消费的循环体系,彼此也多有交集:口头的诗人向文人方向靠拢[34],文人则通过效仿民间的形式和风格而求变出新[35]。这种双向交流越是频繁充分,整个民族的文学生态环境就越健康。“以传统为取向”的民间文本通过文人制作,在口语的社会和书写的社会之间搭起了沟通的桥梁,我称之为“言文桥接”,以说明文学阅读的延伸及其多种可能性。那些久已消失或行将消失的口头演述,经由文人之手完成符号转换,附着在文字上,再度进入读者眼帘。这就像是昆虫的破茧羽化,获得了第二次生命。那些古老的歌诗,终于在书写技术通行的世界中翩然起舞。
四、口头文本:“大脑文本”
及其“三层两径”
口头文本承载着多重形态的口头性(orality)——口头创编、口头演述、听觉接受,乃至诉诸全感官的整体感知。获得口头文本,需要通过参与演述活动,运用特定技术手段(速记、录音、录像等)才能实现。学者进行分析研究时,一般还要将记录下来的文本进行“文本化”(textualizing),常用的方法是“誊写”(transcribing)。在人类社会发明和使用文字之前,所有的文学都是口头的文学。文字在一些地区先后被创造和使用之后,文学就两岔分流了。在许多无文字的社会里,口头文学传承至今;而在那些有文字的社会中,在书写文化逐渐发达之后,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长期并行发展。以下,我们集中讨论几个关联性问题。
其一,“言”与“文”交织。虽说是口头与书写二水分流,但在一个文学传统中,更常见的情况是彼此汇合、交叉和相互影响,前述“互缘”和“桥接”就是此意。在文字创用初期,口传和书写彼此交叠的情况很常见,形成“双通道双媒介”。而在长期使用文字之后的情况呢?航柯认为,在印度文化传统中,书本知识(booklore)和民间知识(folklore)之间的平衡大概比其他任何地方都保持得好。“书写知识诚然古老但时下仍用于口头,而且书籍在口头/书面环境中只是成为工具用于多样的表达模式中。”(*)印度文化固然可能是口头和书写长期“双通道双媒介”的一个样板,但中国也当以族群、语言和文化传统的多样性而不遑多让。
文字系统在使用中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依赖口头传统的情况十分常见。举一个彝族的例子:毕摩师承惯制中长期倡导“声教”,就是主祭毕摩颂唱各类经籍时,身旁若干少年生徒(彝语称为‘毕惹’)逐字逐句地跟读。老师领诵示范,生徒逐段记诵,积段成章,渐及全卷。在此之后,老师才开始教生徒识字、抄经、释读,同时掌握操演[36]。这种将口承、记忆、演述与书面知识结合起来的现象,乃是媒介技术在使用中经常出现的情况,就是根据需要混合或交错使用不同媒介技术。在毕摩这里,文字的作用是提示记忆,规范文本,并显示权威(文字受到民众膜拜)。毕摩在社区的声望,主要取决于他们对传统经籍的掌握及其现场演述的能力和水平。回到口头文本的话题上,一方面,学者经田野作业采录的文本,虽然来自纯粹的现场口头演述,但在文本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已然有了书写文化的参与;另一方面,毕摩记忆中的文本,并不是靠背诵完成演述的,而是在演述现场根据需要调用不同的文本,或在与对手唇枪舌剑的语词对决过程中即兴创编,比如在“克智”口头论辩和“勒俄”史诗演述中,都是既需要大量程式单元的储备,又能根据对手和现场情况随时即兴发挥[37] 。
其二,“某一首歌”与“这一首歌”。在口头诗学的文本观中,影响最大的论断之一,是关于“某一首歌”(a song,泛指,包括一首歌的所有变体)和“这一首歌”(the song,特指,仅指代某一首歌的一个特定变体)的精妙区分。洛德(Albert B. Lord)论述说,就大型叙事文类而言,去追寻所谓“原创的歌”是徒劳的。因为每一次演述的都是“这一首歌”,即特定的歌(the song),同时又是 “某一首歌”(a song)。故而,每一次演述都是一次“再创造”[38]。进一步阐释的话,在一位歌手掌握的曲库中,往往有诸多在当地长期流传和社区民众耳熟能详的篇目,例如在藏族格萨尔史诗歌手桑珠的演述曲库中,经录音、誊写后出版的,共有四十五个诗章,包括《天界篇》《赛马称王》《霍岭大战》《地狱大解脱》等,都是在藏族地区广为传唱的名篇[39] 。举例来说,在桑珠曲库中的《天界篇》是某一首歌(a song),其某年某月某日实际演述所形成的文本则是“这一首歌”(the song)。由于民间口头演述的故事没有所谓“原初本”或者“母本”,而每一次演述又与此前的若干次演述有所差异,与其他歌手的演述本也有所差异,所以这个在具体时空环境中形成的演述本,就是独一无二的。这里还涉及口头史诗的创作问题——“演述中的创编”(composition-in-performance)。洛德关于歌手的创作活动和演述活动在同一时空中完成的论断,又在弗里这里得到更透彻的总结:“传统性口头作品的单次演述既是独特的,是自在之物,也是观众通过前在的其他演述而了解的模式、人物和情景的实现。”(*)弗里将发生演述的实际场合命名为“演述场”(performance arena)。这个空间的隐喻,还有地理性的和仪式性的暗示(*)。简单说,演述人不是逐字逐句背诵故事的,而是掌握了一整套表达技巧,在演述现场根据储存在脑海中的构成单元——如程式、典型场景、故事范型等,流畅地现场创编着(composing)故事。这是口头文学研究界广泛接受的论断。
其三,“文本”和“诸文本”。“某一首歌”和“这一首歌”的问题,实际上还牵连“文本”(text)和“诸文本”(texts)的问题。如前所述,口头文本是“聚簇”的,不仅在“往昔的音声”文本中是这样,在当代完全形态的口头文本中更是如此。桑珠在其一生中演述过很多次《霍岭大战》,这些文本彼此并不相同。与桑珠大约同时代的演述人如扎巴、玉梅等,也都曾演述过该诗章,这些文本之间彼此的差别就更明显。光是叙事长度的差别,就会令调查者倍感困惑。航柯报告过令人惊异的事例,印度的史诗演述人有能力根据需要自如地压缩或扩展故事:歌手奈卡(Gopala Naika)曾用二十分钟演述完图卢史诗《库蒂与钦纳耶》(Kooti Cennaya),而三年前航柯亲自录制的同一部史诗则用了三天,总共十五个小时(*)。在这些彼此不同的“这一首歌”文本中试图分出高下,定出先后,找出优劣,这都是书面文学诗学的惯性思维,其结果是劳而无功的。所以,邓迪斯(Alan Dundes)曾尖锐指出,对于研究民间文学而言,并不存在所谓的“此文本”(the text)这种说法,只有诸文本(texts)。他进而警告说,不要抱持书面文学偏见看待童话,这会导致理论研究的偏狭[40]。不存在所谓单一的、理想的、排他的文本,也不存在批量化、精确化、复制的众多文本,只有聚簇的、彼此有别且相互映射的诸文本,这就是口头文学的文本现实。对于田野调查者而言,碰到并记录的演述文本,或许是内容比较详尽、细节比较充盈的长篇版,也或许是被高度浓缩后的精简版。以偶然得到的个别文本为基础从事研究,则易生偏颇。例如,故事线索繁或简、细节详或略、描摹丰或约,经常处于变动中,难以遽断而不走板。合理的方式是像帕里(Milman Parry)和洛德师徒那样,从事有一定时间长度的、系统的田野记录,把某地区、某传统的大量口头文本,按照同主题、同演述人、同主人公、同亚文化圈等维度,分项胪列,再做多重交叉类比,才能形成比较全面和准确的看法。
在书面文学批评中有“文本至上”(the text is king)的说法(*),口头文学研究也常聚焦文本,但通常从“这一首歌”出发。又由于不同文本彼此有差异,用某个特定文本投射乃至代替其他相同故事,则并不总是合适,需要参考与其构成“互文”的其他诸多文本。总之,研究往往是从个别文本出发的,但要在由诸多文本构成的网状系统中展开进一步分析。构成互文的网状文本系统,则由已经演述过的诸多文本[41]与未来会演述的“潜在的文本”[42]构成。口头文学文本研究的难度也在这里,文本量太庞大。只有贮备必要的文本量,并遴选确当的样例,采用合理技术路线展开对比分析,才能减少失误。
其四,“大脑文本”及其运作机制。“大脑文本”这个概念由航柯首创,用以帮助理解在实际演述过程中口头文本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问题。他说有必要预设一种“前叙事”(prenarrative),即前文本框架,一种存在于歌手脑海中的相关有意识和无意识材料的系统化结构。在航柯看来,这种预先存在的模块似乎应当包括:
(1)故事线,(2)文本因素,如情节模式、史诗场景的形象、多形式性等,以及(3)重新创编的一般法则,还有(4)语境框架,如对前在演述的记忆,只是这并非随意收罗传统知识,而是诸如在活跃状态的曲目库中那些明确的史诗,被歌手个体完成了内化的成套预先安排好的元素。我们可以将这种可变模块称作“大脑文本”,一个涌现出来的实体,可被切分为不同大小以适应不同演述场景而不失其文本特性。(*)
前面讨论伦洛特基于口头演述材料创编《卡勒瓦拉》史诗时,说到过他的大脑文本。综合各方面情况看,其大脑文本是明显大于最后出版的文本的。这种情况在口头创编中也一样:篇幅巨大的史诗从来没有在现实中一次完整演述过。据航柯观察,奈卡专门为其田野工作团队演述的《西里史诗》(The Siri Epic)在当地就从来没有“完整地”演述过,因为民间本无此需要。但在奈卡的脑海中则有这部史诗的整体框架,而且他的大脑文本在过去的30年中有变化,有发展,也有增益(*)。对于受众而言,情况也类似:受众脑海中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与大脑文本也有共鸣关系——听到的总是局部,但引发的是关于整体的联想,因为受众在经年的积累中已经对“西里史诗”的构架和基本内容有了全面了解。
可能是为了避免被批评该大脑文本概念对人脑艺术创造活动进行了过于机械的切分,航柯又发展了“大脑意象”(mental images)的概念,他说“让我们假设记忆凭借大脑意象和意义单元来工作,而不是凭借语词表达”。(*)按我的理解和阐释,航柯的大脑文本和大脑意象,是指口头歌手进行演述时的两个方面:大脑文本由比较“实”的各层级单元构成,而大脑意象则比较“虚”,是凭借经验和才情即刻组织不同单元以完成现场创编的“软件系统”。我赞同弗里的意见,大脑文本的“文本”这个术语的使用似可商榷,因为文本与固化、文字、书写技术等含义很难脱开关系,而航柯的原意是描述“无形”观念的[43]。
因其对于研究歌手脑海中所储存的信息资源有用,所以在没找到更好的替代术语之前,不妨暂且沿用“大脑文本”这个术语。但我认为,大脑文本至少具备“三层两径”的文本属性。具体说来,“三层”是说民间叙事可分为语言层、文学层和逻辑层[44],“两径”是说大脑文本有进出两个口径。歌手学艺——吸收故事本事和艺术技巧是“补进”,在演述中创编“这一个”故事是“导出”。一位歌手两次演述同一部史诗,根据口头诗学的大量实证研究,是既相同又不同的。具体说,可能其在“逻辑层”是基本相同的,但在“文学层”则彼此有别,在“语言层”则差别更大。这说明大脑文本的工作机制——有故事线约束故事框架,有程式、典型场景等较小变化的单元支撑细节,但每次演述都要“重新”组织语词和营造艺术效果。经常有进有出(遗忘曲目或某一曲目中的片段也应算是一种“出”)的大脑文本具有流变性,所以变动是常态,但核心的逻辑层持守故事的骨架,而外层则有游离倾向,与核心的关系相对松散,如特定语词程式就可以移用到其他文类中。仅举一例以示其余:在中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中诗句“那曾是位杰出君王”(Þæt wæs god cyning),这一程式也大量出现在非史诗作品中,如相同的构造(替换形容词如“贤明”“高尚”“残暴”“草率”等)用法,出现在《朱莉安娜》《梅特尔斯》《安德烈亚斯》《行吟者德奥尔》《远行》等中古英语叙事诗之中。[45]
口头文学之“大脑文本”是“导出”文本的前在状态,具有非确定性、流变性和开放性特点,这就与书面文本的确定性、稳定性和闭锁性,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从导出文本可以推知创编者头脑中有更大的存储,但却无从探究其规模和边界。无奈推想,若是把某位杰出演述人一生中所有的语词艺术表达都记录誊写下来,进行综合性大数据分析,或许能够对其“大脑文本”有大致的了解。就眼下的技术手段而言,口头文学研究者只能“有限接近”那个难以琢磨的全体。而另一个不可琢磨之处,是大脑文本经常被“对象化”或“客体化”[46]。在许多文化传统中,那些存储在脑袋里的无形文本,被刻意客体化,以抬升其权威性和超凡性,进而将其神秘化乃至神圣化。藏族格萨尔史诗演述人的“神授”和“掘藏”的说法[47],荷马史诗中对诗神缪斯的召请等,都是朝向将无形的大脑文本客体化的努力。

五、口头诗学:文化生境、
文类谱系及伴生文本
口头文学的文类划分方法主要依据两套范畴。“若要理清民间叙事的类型,重要的是区别‘分析的’和‘原生的’范畴。分析的范畴是由学者们描绘或附加的东西,原生的或民族学的范畴则涉及某一特定文化的‘原生’成员造成的差异。有时候这两个范畴会一致起来。有时则不。”[48] 在中国口头文学传统研究中,分析性范畴十分常见,如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史诗、歌谣、谚语等。但需要注意的是,还有一些是属于本土知识范畴的,通常叫做“原生的文类”或“地方性文类”,如哈萨克族阿肯弹唱、彝族克智论辩、蒙古族好来宝等。
诚然,对这些地方性文类进行研究,也需要将其置于分析性框架中。进一步讲,口头诸文类是以谱系关系共存于一个文化系统之中的,有若干轴线从不同维度标识着口头文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神圣性—世俗性,信实性—虚构性,抒情性—叙事性,庄严性—娱乐性,新生性—稳定性等。就具体文类而言,神话偏于神圣性、信实性,民间故事偏于虚构性、娱乐性,史诗等长篇巨制偏于制造更多新生性成分,而谚语等短小形式居于稳定性强的一端。这些文类不是彼此泾渭分明地各自占据一块领地,而是有许多交错和过渡的地带,形成丰富的谱系色彩,例如东蒙古地区的“镇压蟒古思的故事”[49],就同时带有蒙古英雄史诗和说书艺术的两重属性,这类居于过渡地带的文艺形式,总是给分类和确定属性带来困扰。
口头诗学强调口头性(orality),口头文本的音声属性(口头性)和演述属性(互动性)就决定了口头文学的文本必然带有过程性,而不仅仅是演述过程的一个记录结果。一部印刷品的副文本(paratext)通常是附属性的,作用有限。而一个在演述过程中形成的音声文本,天然带有我名之为“伴生文本”的内容——身势语、演述过程中的音乐旋律和语言格律、乐器辅助功能和介入效果、演述人与受众的互动等,都可以理解为伴生文本。伴生文本广泛参与了文本意义的制造和传递,故不能与音声文本分离,因为剥离了伴生文本就会导致语词文本接受的不完整。过去,口头文学整理和出版方式,因受到书面文学规训的钳制,加上技术手段的种种局限,往往只保留和转化语音符号,过滤掉一切伴生文本。弗里曾痛心疾首地说,我们习惯认可将演述转化为文本,这实际上掩盖了一个事实,就是我们遵循传统编辑程序,将原本活态的“物种”转化为博物馆展品,将语言艺术世界的“动植物”还原为化石[50]。
因为具有演述性,口头文学的文本生产就不是完全由演述人来自主决定,而必须配合社会文化设定(如在仪式、节庆、禳灾等民俗活动中的演述等),或与受众协商(在红白喜丧等场合进行),往往也各有“叙事界域”[51]。书面文学的作者在写作时基本上是自由的(“七步诗”或“奉旨填词”之类只是极端情况),作品是否被阅读是读者说了算。而在口头文学这里,演述人在现场演述时经常没有充分的自主性,有时乃至完全丧失了自主性——演述活动是应特定社会需要进行的(如禳灾或庆典等),从内容到形式,从语境到演述人,常常被事先约定好。也正是因为口头文学的生产过程伴随演述性,演述人的个人才艺就会成为受众评价的重点。于是,由哪位歌手来演述,就往往比演述哪些故事更为关键。在民众的生活世界中,故事是聚簇的,同题同类故事流传甚多,关注演述人超过故事“本事”是常见现象。所以,学者(通常是局外人)和民众(局内人)对叙事文本的定位就常是错位的:学者习惯于关注故事讲述的结果(文本及其完整度),受众关注故事讲述的过程和人(演述人及其才艺)。
口头文学的文本是在演述场中生成的。所以,文本离不开语境。语境是弹性概念,包含多个文化圈层,且对文本形成多方面的规制,如前所述。口头文本(含伴生文本)不是独立自在之物,而是出现在给定的、具体的、受众直接参与的时空场合,对其解释和说明也必须联系环境要素。因为口头文学与其语境的联系是更为直接的[52],假如不深入了解这个语境,就无法深入理解其文本。
书面文学文本的完成结果是“符号文本”(稿本),口头文学的完成结果是一个“演述事件”。书面文学作品用书名号标记,口头文学常常使用“格萨尔史诗传统”这种叫法——指涉整个史诗传统,这时用书名号反倒不妥。口头文学的命名规则与书写文化不同:例如有时江格尔史诗歌手演述完一个史诗诗章,在结尾时加一句“这是洪古尔娶亲之部”这样的说明。进入文本之中,书写规则通过标点符号、节或阕,章或部等单元做出区隔。口头文学不然,演述活动耗费体力,受众也需要休息,所以有间隔,还常用标记指示,如“且听下回分解”等。
总之,口头文学与民众生活的联系是广泛和深入的,必须联系生活世界的诸多方面才能做出合理阐释。弗雷泽(James Frazer)曾说过:“我们就可以说神话源于理性,传说来自记忆,而民间故事来自想象;与人类这些幼稚的产物相关而又比它们更成熟的是科学、历史和长篇小说。”(*)贝蒂的说法更直接干脆:神话是原始哲学,传说是原始历史,民间故事兴起于愉悦需要。(*)这些论断因有缺陷,现已被束之高阁,但就强调口头文学与社会生活的深刻而广泛的联系而言,亦不无道理,尤其是其中指向的理论图景,或隐或现,都为我们进一步探究人类表达文化之根提供了有益的自反性思考空间。
本文原载《文学遗产》2022年第3期,文中注释从略,注释位置以“(*)”或“[数字序号]”标注,注释内容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文学遗产》2022年第3期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cel.cssn.cn)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