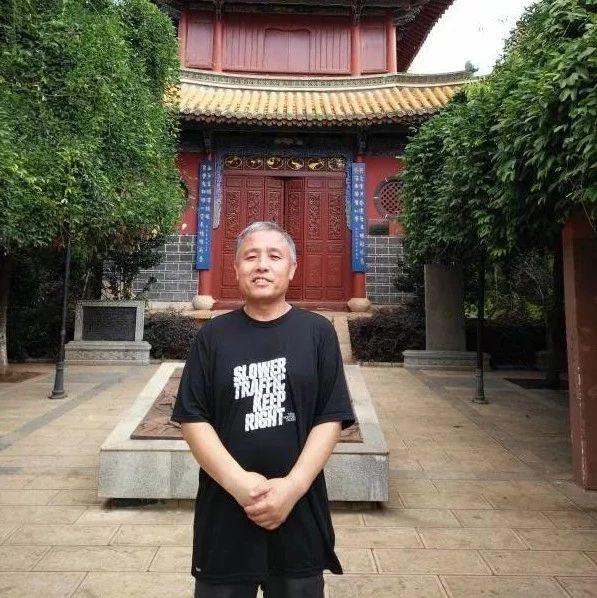

褚建芳副教授
学界有关中国傣族和东南亚上座部佛教社会宗教仪式和宗教花费的研究,大都把着眼点聚集到对一个单一的世界——今生的关注上,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对于有些社会来说,世界并不仅限于今生。在此视角下,这些研究认为,这种宗教花费是一种“奢侈”性的消费或浪费,反映了信众们对储积的忽视和理性的缺乏。这种今生视角在不同程度上与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理论有着一致性。在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理论中,“救赎”(salvation)是一个关键而基础性的概念,指的是一种与普通民众所拥有的大众宗教相对而言的通过文字而表达的有关抽象观念的理性化的哲学思想,由那些受过教育的知识精英们所拥有和使用,而普通民众所拥有的大众宗教对他来说则是一种令人不快的情绪性和非理性的东西。因此,韦伯的救赎观一方面是只关注一个生命世界——今生的,另一方面是只着眼于文化精英的。体现在其对佛教的论述方面,马克斯·韦伯把佛教视为“一种极为特殊的高贵知识分子的救世论”,认为它“不仅对立于古典婆罗门的救赎追求,也对立于耆那教的救赎之道”;“佛教的独特成就在于其致力追求‘生前解脱’这一目标,而且唯此一目标是求,并且义无反顾地排除一切与此无关的救赎手段”。可以看出,马克斯·韦伯的佛教观是其宗教社会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服从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论题的一个反证。然而,尽管它指出了佛教伦理出世品格的一面及其印度文化根源,却未能看到佛教中“前世-今生-来世”这样的轮回观念和相关的业力论信仰在现实生活中并非仅仅蕴含着“出世”——追求“生前解脱”这个面向,而是还有着“入世”——追求福报的面向。况且,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并非仅限于文化精英的知识体系,而是被广大普通信众们所信仰和奉行的意义框架与价值基础。因此,对于宗教在民间被信仰与实践的情况,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具体到普通佛教信众的日常生活与行为实践,佛教,尤其是有关轮回和业力论的信仰,有着比出世——涅槃更为切近的现实指导意义。
本文基于作者在云南芒市傣族地区的田野研究,对民众的佛教信仰与实践进行描述,重点关注这种实践佛教与民众日常生活,尤其是财富实践的关系。本文尝试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如何理解芒市傣族的宗教性财富实践;第二,芒市傣族民众的佛教信仰与教义性佛教的关系是什么样的。通过对前两个问题的解答,本文试图探讨这种视角对于社会学人类学的主流看法有何启发。为此,本文将首先描述芒市傣族民众的佛教信仰,尤其是有关业力和轮回的信仰,将其与佛寺或教义中的佛教理论进行比较,揭示其对诸如涅槃和功德的理解上的差异和共生关系。继而,本文将描述芒市傣族的“做摆”习俗,将其作为当地民众的佛教实践,力图揭示普通信众的佛教信仰与实践中的行动逻辑。接下来,本文将重点对芒市傣族民众对待财富的态度与行为——财富实践进行讨论,从而试图发现一种地方性的财富观和经济理性,并从其与佛教关系的角度对之进行探讨。最后,本文将指出,对于芒市傣族地区佛教信仰与实践,必须放到当地民众所普遍信奉的“前世-今生-来世”这样的轮回观和业力论的脉络下加以理解和阐释,从而对韦伯的单一生命世界立场提出批评和补充。
一、业力与涅槃:芒市傣族村民的佛教信仰及其实践
在芒市傣族村寨,除了极少数幼年时期曾进入佛寺做过和尚的男性老人以外,绝大多数村民只能听说傣语,而不能读写傣文。1950年代末以来,一些男性村民从新式学校教育中学会了新傣文,但这对他们认识以老傣文为主同时掺杂着巴利文和缅文的佛经并无多大帮助。所以,村寨中很少有人能够直接从佛经中学习佛教知识。大多数村民的佛教知识是在听和尚和卜庄们讲经或参观佛教建筑中的壁画、听当地流传的故事等活动中,以口头而非书面的形式获得的。
村民们对于佛教知识的把握程度和态度并不相同,这与他们的年龄、性别、人生经历和所处人生阶段有关。大致而言,村民的佛教知识和对佛教的虔信程度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高。尤其是做了爷爷奶奶以后,村民们学习佛教知识的热情和对佛教的虔信程度明显高于比其年轻的村民。他们不仅会定期到佛寺参加佛教仪式,还常常在诸如做摆、乔迁、婚礼、丧礼、求健康仪式等活动中听经诵经。女性的佛教知识虽然与男性相比并无明显差异,但其对佛教活动的热衷程度却比男性要高。无论男女,真正懂得佛教教义的村民并不多见。当然,有些小时候去佛寺学习过一段时间的识文断字的老人知道一些标准概念,比如无我、无常以及作为终极解脱的寂灭等,但绝大多数村民既不懂得也不关心这些。即便那些知道这些概念的老人甚至一些僧侣,往往也不会以之指导自己的日常佛教实践。大多数村民所理解的佛教,是一种地方化、实践化和生活化了的佛教,其中许多方面的内容和含义甚至与佛教的原意相反。比如,对于“布施”这样的功德善行而言,佛教本意是让人们戒除贪念,可是,到了村民们那里,却成了许多人追求来世福报甚至凡俗声望的手段。
对于绝大多数村民来说,他们的佛教信仰基本是以业力论和轮回观为核心的。业是佛教术语,在梵文中被称为Karma,在泰语和老挝语中被称为Kam,在芒市傣语和经文中被称为“尬姆”,表示由那些具有道德后果的行动所启动的力。
村民们对业力和轮回的理解主要停留在一些关键的佛教概念上,比如来世、业、善果、涅槃等。他们相信,人和其他众生都处在前世-今生-来世这样的前进序列中。众生的所作所为都有着道德性的后果——业:前世的行为决定着今生在相对幸福或远离苦痛的等级序列中所处的位置。同样,今生的行为也对来世的位置有着影响。尽管他们对于这种等级序列具体包括哪些层次的了解并不一致,但他们都一致认为,人与人以及人与其他众生的差异都是由其以前所作的业决定的。由于每个个体从前世继承下来的业不同,他们在今生的财富、健康、福运等也就不同。因此,有的生为男人,有的生为女人,有的生得美貌,有的生得丑陋,有的官能全面正常,有的存在缺陷或不足,有的生在权贵富足之家,有的生在贫穷困顿之户,有的甚至生为畜生。在他们看来,业是可以通过积累而结算的。行善或做合乎道德的行为——可以产生“功德”、福分或善果;反之,行恶或做不合乎道德的行为,则不仅不会产生功德,而且可能产生相反的后果。这样,一生行动的后果积累起来,如果善行大于恶行,业就是好的;反之,业就是不好的。前世的善行越多,恶行越少,今生的业就越好。反之,今生的业就越不好。相应地,今生通过做善行和戒除恶行,可以使业朝着好的方向变化,使自己在来世甚至今生获得等级序列中的更好位置。
当然,村民们并不以业来解释一切。通常而言,只有当他们的经验知识不能提供确切满意的答案或者遇到因果关系不明的情况时,他们才会诉诸业。但是,当他们使用业的时候,所谈及的往往是有关人生命运的重大事件,比如某个人或某类人为什么富有或贫穷等。比如,我在田野中曾与几位傣族朋友有过下面这段对话:
傣族朋友:我们比你们汉族有福气,因为我们信佛,我们的业好。
我:那为什么我们比你们清闲而且富有,而你们却这么辛苦而且贫穷呢?
傣族朋友:那是因为我们上辈子的业不如你们好。但我们这辈子信佛了,业就好了,所以,到了下辈子,我们就会富裕、清闲、快乐。而你们这辈子不信佛,所以业就不好了,下辈子就不如我们了。
在这样的情境中,对业的信仰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认知的基础、情感的依托和行动的方向。这不仅是傣族村民应对不确定性时所用的降低不安和缓解心理压力的认知策略,而且是激励他们忍受辛苦努力奋斗的动力。
与“业”相比,村民们对“阿嘬”的了解和谈论更多。这个词指的是因为功德善行而带来的好的“业”或“善果”。村民们常说,他们之所以喜欢拜佛献供,是因为想要“阿嘬”,拜佛献供可以得到“阿嘬”。
与之相关的是村民们的涅槃观念。涅槃本来是指佛家通过修炼而达到的一种彻底地断除生命中种种痛苦烦恼,超脱生死轮回的“寂灭”或“不生不灭”的境界,但在芒市傣族村民那里却被理解成了一个具体的地方或区域。他们称之为“勐里办”,直译为汉语,即“里办之地”的意思。他们相信,人死后会到“勐里办”去,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然后再根据对前世积累下来的业的结算来投胎转世,开启新的生命。基于这种理解,傣族村民为了积累好的业,在今世辛勤劳动,努力行善,以期在来世获得一个好的位置。
根据上座部佛教的教义,积累好的业的方式有3种,分别是布施、持守佛戒和禅坐。但是,在村民们的佛教实践中,禅坐和持守佛戒仅限于那些已经皈依佛门的“老人”和僧侣们执行,而且仅仅在佛教仪式或佛教戒日中执行。与之相比,布施尤其是献供则不仅是几乎所有佛教或与佛教有关的仪式活动必备的核心成分,而且是诸如婚礼、丧礼、祭祖、拜社、求神、祈福等人生礼仪和时令节庆所共有的内容。可见,献供是村民们最普遍实行的积累好的业的方式。这是因为,与禅坐和持守佛戒相比,献供具有很强的可实践性和可见性。
很多时候,这种为了积累好的业而努力行善的业不仅仅停留在宗教信仰和宗教实践的层面,而是渗透到村民们日常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了一种传统习俗和社会规范。比如,不管虔信与否,村民们都要按照习俗参加一定的佛教仪式和佛教活动。尤其是到了老年阶段,几乎每个村民都要按照习俗举行求戒受戒的仪式,定期到佛寺参与佛教学习和佛事活动。如有违背,则会受到处罚和鄙视。村民们家里举行佛教仪式时,往往会邀请邻居和亲属中已经持守佛戒的老人们到场听经诵经,而被邀请的老人们往往会带着一些米和小钱到场帮忙。邀请和应邀是一种互惠性的礼俗,所带的米的数量和小钱的额度也是村寨生活中约定俗成了的。即便是外出工作的公职人员退休后回到村寨,只要希望融入村寨生活,就要按照村寨的习俗参加佛教活动,否则就会疏离于村寨生活之外。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村民们对佛教活动的参与比对佛教教义的信仰更为重要。因而芒市傣族村寨的佛教又是一种被实践出来且更加注重实践的佛教,我们可以称之为“实践佛教”。其中,“做功德-求善果”是一种最基本的宗教实践。
二、“阿嘬”与“卤”:“做摆”的宗教实践
在村民们的谈论中,“阿嘬”这个词常常与物质财富有关。他们常说,有了“阿嘬”就有了钱。反过来,在谈到物质财富时,村民们也常常将其同“阿嘬”联系起来。他们常说,人们之所以有钱,是因为他们上辈子积累了很多“阿嘬”。上辈子积累的“阿嘬”越多,这辈子所能拥有的钱就越多。这辈子的“有钱”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生在有钱的人家;二是干什么活都能赚钱。
当然,在村民们的说法中,“阿嘬”并不仅仅限于物质财富,而是还包括身体健康、平安顺利、幸福和睦、称心如意等物质财富之外的东西,这些东西跟着物质财富一起到达有好的业的人,但物质财富是“阿嘬”最突出、最重要、最核心的成分。可见,在芒市傣族村民那里,做功德实际上相当于一种投资:有所投入,也就有所产出,至少是在信仰中被预期有所产出。这种为了来世而投资的逻辑最集中最明显地体现在村民对“做摆”尤其是“做大摆”的热衷上。从前,芒市傣族村寨的村民们对于“做摆”有着异乎寻常的狂热痴迷:为了做摆,他们可以牺牲所有,不顾一切。近20多年来,傣族村民们对做摆的痴迷程度有所减弱,但做摆仍被视为风光荣耀的事情。
在芒市傣族村寨,被称为“摆”的仪式很多,几乎一年四季都可见到。其中,规模最大、社会地位最突出的是帕嘎摆。帕嘎摆是指以向佛寺献供大型佛像为核心同时带有娱乐庆祝和商业活动的仪式庆典。其中,除了献供大型佛像和例行性的献供,比如鲜花、大米、定额现金和饭食等的献供以外,还有很多别的献供,比如佛幡、佛伞等。此外,摆主家还要请僧人到场念经讲经主持仪式,把所有献佛供品陈列起来进行展览;然后,摆主一家以及前来帮忙的亲戚们要抬着献佛供品绕着寨子的主要干道游街展览,接受村民们的羡慕和尊敬;主持仪式的僧人为摆主一家颁授功德名并为之诵经祈福;村民和外村的亲戚朋友结队到摆主家随份子祝贺;摆主家宴请前来捧场祝贺的所有宾客;如此等等。因此,做帕嘎摆不仅需要准备很长的时间、投入大量的人力,而且花费的物力财力极其巨大。在过去,做一次帕嘎摆常常需要花费一个家庭数年辛苦努力攒下来的积蓄,有的家庭甚至一辈子辛苦努力也攒不够做帕嘎摆的钱。近20多年来,帕嘎摆常常由几家甚至十几家亲戚联合起来举行,每一家的花费也下降不少,但从家户的收支情况来看,这一花费仍然相当可观。
除了帕嘎摆以外,别的摆虽然规模相对较小,但也都包括献供和宴请宾客,因而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除了摆以外,芒市傣族村民通常会在夏安居期间每周周末两天、在夏安居结束时以及在四月节(即汉人的春节)、泼水节和傣历新年那几天到佛寺里拜佛听经献供。平时的每个佛教戒日,老年村民们也会在家里拜佛献供。除了这些明显的佛教活动以外,芒市傣族村寨还有婚礼、丧礼、乔迁仪式、洗沐咂等佛教色彩不那么明显的仪式活动。可以说,芒市傣族村寨是一个充满仪式的社会。这些仪式虽然从每一单项来看,所需的花费明显较小,却极为常见,数量众多。因此,汇总起来看,这些宗教活动的支出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
从工具论的角度看,除了使花费者获得好的声望以外,这样的花费既不能给他们带来吃穿用度方面的好处,也不能给他们带来权力地位的提升,可以说没有任何“实际”用处。那么,傣族村民们为什么愿意甚至热衷于“支出”这样的花费?
对此,基于单一生命世界视角的回答是,这是一种宗教花费,属于“奢侈”性消费的范畴,为的是把财富消耗掉,反映了信众们对储积的忽视和理性的缺乏。然而,对于芒市傣族民众而言,这样的支出并不仅仅是一种消耗和花费,而是还有存储的意义: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这些支出性的仪式中,有一个共有的核心性的成分——向佛献供,这是一种向佛、佛寺或僧侣晋献供品,同时有僧侣或卜庄讲经说经且带领信众一齐诵经以让供品被佛接受和认可从而获得神圣性的仪式,芒市傣语称之为“卤”。因此,村民们之所以愿意甚至热衷于做如此巨大的宗教性支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认为这是具有神圣意义的功德善行,能够使他们获得善果和福报。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今生献供,是为了让来世有福。我们今生献供所花费的钱,来世仍然属于我们自己。不然的话,谁还愿意去献供?”
对此,他们常常用银行来类比:“我们这辈子献供,得到‘阿嘬’,等到下辈子再做人的时候,再取出来用。所以,这辈子献供的东西由佛给存着呢,到了下辈子还是我们自己的。这就像你们汉人把暂时用不着的钱存到银行里去,等到将来用得着的时候再取出来用一样”。
不仅如此,按照他们的信仰和解释,通过献供,他们今生的财产不仅能够得到存储,而且还能获得利息或加成,使他们在来世变得更富有。为此,他们常常会说:“姆咪迪卤,姆卤迪咪”?这是一句反问句,翻译为汉语,意即“没有就要‘卤’,不‘卤’怎会有?”。
而且,对于献供的费用,他们并非完全没有计划和预算。相反,在挣取、积攒以及使用这笔费用的时候,他们有着详细的计划和算计。比如,为了挣钱,家庭主妇们在做完田间劳动回家后,可以不辞辛苦地一边带孩子,一边洗衣做饭刷锅洗碗养猪养鸡养鸭,或者从事酿酒、做酸巴菜、酸菜膏、辣椒粉等农副产品的制造工作,以便将这些农副产品拿到集市上去卖,可以说,他们几乎抓紧了一切可以抓取的挣钱时间。在计划做帕嘎摆时,村民们不仅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辛苦劳动赚取和积攒足够的财力,而且会仔细思量和算计所需的花费,甚至在计划邀请帮忙者和客人的名单时,他们也要反复斟酌。受邀的客人也会认真考虑是否参加以及如何参加,甚至常常会翻出往年自己做摆时对方随份子的账单,以此来做决定。可见,这种为了来世所做的“投入”性的支出并非没有“理性”的成分。
三、芒市傣族村民的道德财富观及其物质实践
萨林斯认为,不同人群的物质实践乃是更大文化价值体系的结果,而理性则只是文化的一种表述,表现为围绕物质使用的意义体系。如前所述,对芒市傣族普通村民来说,“做功德”的最主要方式就是献供,而所献的供品则属于“物质财富”的范畴;村民们所理解和期待的“善果”,当然包括物质以外的成分,但其最本质、最重要、最核心的成分则是“物质财富”。因此,“做功德-求善果”的宗教实践的核心是人们在献供以及围绕献供组织起来的各种活动中对物质财富的态度和处理,属于萨林斯所谓物质实践的范畴,而萨林斯所说的更大的文化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在芒市傣族村寨则可被概括为“集体优先”的道德财富观和社会本位的意识形态。
在芒市傣族村民眼中,财富并不单独存在,而是与人们及其处理财富的态度和方式分不开。人们及其行为,包括与物质财富有关的行为都有道德性:他们既受道德的评判,又有道德的后果。行善或做合乎道德的行为是“功德”行为,可以产生福分善果,这样的人是有功德的人,能享受福分善果;行恶或做不合乎道德的行为,则不是功德善行,不但不能产生福分善果,反而可能产生相反的后果,这样的人不是有功德的人,无法享受福分善果。并非所有有关物质财富的行为,比如喝酒、赌博等都是功德行为。功德行为必须是对他人和社会有好处因而被村寨社会所赞许和称颂的行为,即有道德的行为,比如修桥、筑路、修挖公共水井等。
在村民们看来,财富有好和不好这样的分别。好的财富是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或靠自己勤俭节约积攒起来的财富。不好的财富则是那些并非继承或靠自己勤俭节约积攒起来的财富。村民们相信,只有好的财富才能供人们安心使用,尤其在献供的时候,只有那些好的财富才会受到佛的接受和保护,因而才是有效的。而那些抢来、偷来或捡来的钱则是不好的,如果用它们来献供,则不但不会被佛所接受和保护,而且可能会给献供的人带来霉运或造成伤害。甚至当小孩子为想买零食或玩具找老人要钱时,老人也不能舍不得给,否则用这钱献供就会不灵。
出于此,村民们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特别注重“不欠钱”。比如,从寨子里搭顺风车出行时,哪怕只是搭一辆恰巧出寨运货的手扶拖拉机,搭车的村民也会在到达目的地后付给车主一两元钱作为车费,而车主也不推辞。付费和收费的双方都视之为理所当然,丝毫没有不情愿或不好意思的表现。当然,如果搭车的是邻居或亲戚中已经持守佛戒的老人,车主可能会“谦让”一下,表示不收这笔车费。这时,搭车的老人就会面带微笑却很认真地口诵一套程式化的祝福话语,表示认可车主的功德善行,以“阿嘬”回报,就像僧侣或卜庄向献供村民诵经祝福那样。村民们相信,老人们的这种祝福话语具有一定的神圣效力,可以在将来的某个时间或来世得以实现。
在摆、婚礼、丧礼、乔迁仪式这样的聚餐中,前去捧场祝贺的客人们都会向举办仪式的主人家里送上一些钱物,作为贺礼。这种“礼金”包括“还礼”和“帮礼”两部分。“还礼”表示按照自己家此前举办仪式时对方送来的礼金数额所回的礼金;“帮礼”则是用来“帮吃”的费用。对于“帮礼”,村民们解释说,由于主人家举办仪式已经花费不少,客人不能去白吃,而是应该凑上些钱物,作为自己的饭费。在插秧结束以及收割完成之际祭拜社神的时候,同“社”的每一户人家也都会按照惯例带上一份“帮吃”的生米到聚餐的那户人家,作为吃饭的费用。对“随礼”和“帮礼”的明确划分,表明村民们对“不欠钱”习俗的尊重与实践。
此外,在插秧和收割水稻的时候,村寨中还存在着两种互助习俗:一种是由于各家插秧和收割的具体时间并不相同,不同家户的青年人便会互相到亲戚朋友家帮忙,等到自己家里插秧时,亲戚朋友也会前来帮忙,这叫换工;另一种互助形式是,当主人一家劳力不足,难以向前来帮忙的亲友们回报劳力或者前来帮忙的人们并非亲友的时候,主人一家就可以向后者支付现金,以后不必前去帮忙插秧或收割。这两种互助形式的存在,尤其是劳力与现金之间的交换,从另外一个角度诠释了村寨生活中对“不欠钱”习俗的看重与实践。
财富不仅在来路方面有好与不好的分别,而且在用的方面也有好与不好之分。用得好指的是用到正地方,比如用到诸如献供这样的能够带来“阿嘬”的活动上。这些活动都是被社会认可和赞许的,因而是有道德的。反之,如果把财富用到个人的吃穿、喝酒乃至赌博上,便会被认为用得不好甚至用得坏。这样的人和这样的做法通常不会受到大家赞许,甚至为人所不齿。村民们相信,用得好的财富能够有效地从前世传到今生也能有效地从今生传到来世,用得不好的财富则不能如此传递。
在评判财富是否用得好时,村民们还会看其使用者的态度:用的时候心里是慷慨、真诚和充满善意的,就是用得好,就有效力。否则,如果不是出自真心,或者不慷慨或缺乏善意,就不会有好的效果。我在芒市傣族村寨做调查时,常常听到老人们讲述他们在佛寺里听到的下面这个故事。
从前,有一对穷人夫妇,信佛非常虔诚,无论有什么东西,都愿意拿去献供。有一天,他们拿着仅有的糊口用的腌酸菜去佛寺时,路遇一位富翁。富翁拿着很多贵重的东西,也要去佛寺献供。见到穷人夫妇,富翁很是瞧不起,气势汹汹地说,“你们只拿这样的东西,也想去献供吗?走开!走开!”穷人夫妇慌忙躲让。由于路滑,二人跌倒在地。富翁洋洋自得地向佛寺走去。这时,忽然刮起一阵大风,把富翁的供品全部吹走,而把穷人夫妇直接吹到佛那里。佛愉快地接受了穷人夫妇献供的腌酸菜。夫妇二人回家后,发现家里有了很多金银财宝。他们把这些金银财宝拿去献佛。佛说,“你们有这份诚心就足够了,还是把这些金银财宝拿回去买些吃穿用品吧。”那位富翁后来又带上贵重物品去向佛献供。可是,无论拿来什么,佛都不接受。最后,富翁什么也没得到。
村民们在评价人和物的时候,常常用到“哩”这个词,表示“好”。比如,他们会说某人是“好人”或者说这个人“心好”。对于为什么说这个人是“好人”或“心好”,他们会说,因为他慷慨、大方,能够舍得,不小气。与之相对,他们会用“惕”这个词来评价和形容那些不被认为好的人及其心灵,会说他们“小气”,是“小气鬼”。
作为“心好”的典范,佛祖乔达摩的事迹常常会被拿来说明。他们常常说,乔达摩心好,因为他慷慨仁慈、乐善好施,总是喜欢帮助别人。他在成佛以前是一位王子,名叫“兆为散”,为了帮助别人,甚至把自己的金银财宝和妻子儿女都舍了出去。由于这种慷慨善行,他终于成了佛。
如果说佛祖乔达摩是村民理想境界中“心好”的典范,那么帕嘎和老人就是村民现实生活中“心好”的典范。帕嘎为了向佛寺献供或为社区修桥筑路、修挖水井等,不惜花费巨资,表现出慷慨仁慈乐善好施的品质。他们不仅在做摆时风光无限,备受称道和羡慕,在日常生活中也地位崇高,备受尊敬。而且,他们本身就生活在村民们身边,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为村民们所亲眼目睹,他们的成就具有一种真切感和可接近性,更容易被村民们学习和效仿。
老人在芒市傣族村寨中也备受敬仰与尊崇。一方面,成为老人的村民们大多都已做过摆,成为帕嘎;另一方面,能够靠自己的功德善行而得到真正帕嘎称号的村民大多都已成为老人。除了在仪式与日常生活中为年轻人所“惠顾”,比如当老人搭车外出时免收车费、在咋嘎仪式中为老人做饭做菜端茶送水、在老人面前经过时要躬身低头等,老人们还被称为“懂人话”的人。“懂人话”的意思并非懂不懂人的语言,而是懂不懂做人的规范,会不会做人。有关“懂人话”与否的标准虽未明确成文,但对广大村民而言却是不言自明的共识。这样的共识性的标准很多,也很具体,比如勤俭自立、慷慨大方、谦恭礼貌、言语温和、尊老爱幼、乐于助人、遵守集体纪律和积极参与集体活动等。其中,占支配地位的标准常常被表述为懂得佛经和能够持守佛教戒律,而最重要最核心的标准则与人们对财富的处理是否得当有关。村民们常说,老人们是“懂人话”而年轻人是“不懂人话”或“尚未懂得人话”的。他们会解释说,老人们已经持守佛戒,懂得佛教道理,能够约束自己,不会说不恰当的话或做不合规矩的事。其实,到了老人这个阶段,通过此前的辛勤和节俭,已经积攒下了一定的物质财富和人际资本,而且,他们的子女大多已经长大成家,他们可以不再像前面阶段那样受到个人和家庭责任的束缚,而更有条件把自己投身于佛教活动中,同时更有条件把财富投入到做功德上,展示自己的慷慨大方和舍得,也更可能克制私欲,遵守佛教戒律和社会规范。与“懂人话”相关,老人们常常被说成是“心好”的。他们与年轻人相比,既不贪心、不小气,也不乱发脾气,能更好地处理人、事和物的关系,更好地服从集体和参与到集体活动当中。因此,老人实际上被当成了傣族村寨生活的道德模范和社会代表。
这种道德财富观及其物质实践与理性计算并不冲突。相反,道德财富观鼓励人们通过理性计算而赚取财富。但是,道德财富观反映了芒市傣族村寨一种可被称之为“集体优先或社会本位”的整体氛围。在这种整体氛围下,理性计算需要在村寨公认的道德标准的框架内进行,要受到道德财富观的支配。比如,村民们开车外出时,可以遵照村寨约定俗成的做法搭载乡亲收取车费,而坑蒙拐骗偷或巧取豪夺等不正当敛财方式则被村民们所不齿,甚至在购物时流露出不慷慨的样子,也会受到村民们的批评。笔者记得当年曾有一次跟村民们去镇上买东西,问过价后觉得不合算就没买,结果同行的一位相熟村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问过价就应该买,否则显得小气和不守信用,这是很没面子的”。
四、来世的意义:生命世界类型与对“理性”的理解
如前所述,马克斯·韦伯对佛教的论述只着眼于一种精英式的宗教观。在这种宗教观中,只有一个生命世界——今生,“生前解脱”——涅槃是佛教徒追求的唯一目标,而轮回的生命世界则并不重要,仅相当于前进路上需要迈过的坎。然而,到了普通佛教信徒那里,追求的目标却并非“生前解脱”,而是福分或善果,而涅槃则被理解成从一个生命世界过渡到另一个生命世界的中转站,他们称之为“勐里办”。在这个中转站里,前一个生命世界的财富实践受到审核,并根据审核结果而被再分配,然后转到下一个生命世界。这种审核所依据的标准不仅仅是物质性的,更是道德性的,而且道德性优先于物质性且对后者形成一种支配。对于这种道德标准,村民们心知肚明。因此,为了成功通过审核,人们需要不断从事道德所允许的财富实践,比如在诸如摆这样的仪式上献供、帮助村寨社区搭桥修路、修挖水井以及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帮助别人等。从这个意义上说,芒市傣族村民在宗教仪式上的花费实际上与他们在生产生活其他方面的花费一样,都是在村寨道德财富观氛围下考量与选择的结果,是一种为了来世所做的投资。在这种考量与选择中,并非没有对成本与收益等的计算。因此,这种考量与选择实际上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行动者的理性计算和选择并无二致。如果非要说二者有什么不同,那么只能说它们所遵循的更大的文化价值体系不同: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行动者的理性计算与选择并未受到像芒市傣族村寨那样的道德财富观的支配,而是受到其自身社会之文化价值体系的支配,其所表述的也只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对芒市傣族村寨社会来说,对宗教仪式花费的考量与选择是在其“集体优先或社会本位”的整体氛围下进行的,而道德财富观则是这种整体氛围的一种表达。
在芒市傣族村寨社会,作为一种“更大的文化价值体系”,“集体优先或社会本位”的整体氛围既强调物质的道德属性,又看到这种道德属性与人及其行动的关系。因此,物质与精神、人与道德是结合在一起而不可分离的。在这样的世界观下,救赎的获得并不是靠外来的上帝或佛的力量,而是靠自己的道德努力和功德善行。这种“自我救赎”的信仰虽然强调来世,但并不否定今生,而是将今生与来世并置起来,将其作为一个连续而完整的链环的组成部分。在这样的链环中,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既是自己,又是对方。它们的身份都是相对而言而且是临时的。在这样的世界观里,人们的生活实践给我们这些只信仰单一生命世界的人们展现了另外一种可能。
在韦伯论者对理性的讨论中,物质与精神似乎是两种不同且独立存在的东西,因而是可以分离的。同样,物质与人及其道德品性也是可以分离的。因此,人的生命意义的获得与维持需要靠上帝的救赎而获得,而救赎的力量则需要通过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与获取来证明和确认。而本文对芒市傣族村寨社会“集体优先或社会本位”的文化价值体系的考察则让我们有可能看到,西方的理性计算其实也是蕴含在其特定道德财富观氛围之内的,只是不为经济学家所注意罢了。
韦伯的论题和论述主要是基于信仰新教的社会,有时也被理解为泛指整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而提出的。在这样的社会的信仰体系中,只有一个单一的生命世界——今生。在这个生命世界中,从表面上看,就像韦伯论者相信的那样,消耗与储积、消费与生产、产出与投入似乎是彼此独立甚至有时对立的过程。从这个角度出发来看,芒市傣族村民对包括摆在内的宗教仪式的狂热痴迷似乎确实是一种消耗,他们的生活似乎只是为了这种“消耗”而组织起来的。然而,若从芒市傣族村民们自身的主位视角,即轮回生命世界的角度来看,上述宗教性的“消耗”就成了一种为了来世所做的投资和投入。于是,消耗和储积就成了同一个行动过程。
继而,如果从上述轮回生命世界观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一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受其影响的非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财富的投入和产出并非如许多学者想当然地认为的那样截然两分且彼此对立,而常常是合一、互补和共生的。比如,以慈善活动和奢侈品的使用为例,它们从来就不是默默地进行的,其中最重要最必不可少的内容就是炫耀。这实际上是一种仪式性的表演和展示,就像芒市傣族村民做摆时的表演和展示一样。如果说芒市傣族村民做摆使其获得了一种“荣耀感”,那么有钱人做慈善和公关人员使用奢侈品同样使其获得了这种“荣耀感”。如果说做摆习俗有使傣族社会抹平财富两极分化的功能,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慈善活动和奢侈品使用同样有使社会抹平财富两极分化的功能。可见,在核心成分和所具有的功能上,芒市傣族社会的摆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慈善与奢侈品使用,实际上并无二致。它们都既是一种财富“消耗”,同时也是一种财富投入,是二者的统一体。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可被称之为“理解社会学”或“解释社会学”,其目的是通过理解个体行动与彼此间的互动来理解社会与文化。他的这一研究取向还深刻影响了人类学。比如,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宣称,人类学研究的目标应该是对人类社会诸“地方性知识”的“理解与解释”,并将这种范式的人类学称之为“解释人类学”。我认为,不管是否赞同格尔茨的看法,对于以“人的研究”为志业的人类学者而言,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理解与解释“人及其文化”至少是人类学的重要目标之一。那么,这种理解与解释应该如何达成?对此,人类学家曾经提出了“文化相对论”“文化批评”“(跨)文化比较”以及“主位与客位”“近经验与远经验”之类的主张。这些主张的具体内容各有不同,但其根本路径是相通的,即人类学要找出不同的文化,将其作为一个个进行观察和研究的靶子,再对之进行评价、批评或比较。这一点与马克斯·韦伯的路径是一致的。为了实现理解与解释社会文化的目标,马克斯·韦伯采用了历时性的文化分析(比如他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关系的历史过程的分析)和共时性的文化比较(比如他对中国儒教与道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等的比较)相结合的方法。然而,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在马克斯·韦伯的理解与解释尤其是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社会文化的理解与解释中,存在着一种可被称之为“西方中心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即以基督新教的伦理与其经济形态的关联和发展方向为标准来衡量世界上的其他一切宗教的理性化发展程度及其发展方向,从而把欧洲的地方性当作人类的普适性。在我看来,除了上述“欧洲中心主义”偏见以外,在马克斯·韦伯的论述中,还存在着一种“文化精英主义”的偏见,即把关注的焦点放到“文化精英”而对普通大众却予以忽视。反映到其对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理解与解释上,这两种偏见使得马克斯·韦伯论者们用基督新教的单一生命世界——今生的视角来看待南传上座部佛教社会的轮回世界观,将其对宗教事务的热忱投入视为一种消耗和浪费,而未看到其自身世界观中所蕴涵的另外一种解释,也未看到这种解释可能对欧洲中心主义世界观带来的启示。
图文转自微信公众号 南京大学紫金人类学 2019-12-26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