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通过梳理弗雷泽对图腾制研究的思考与理论变化过程,重现他以图腾制为出发点通向巫术与思维研究的学术进路,旨在阐明,接触律在阿兰达人图腾类型中的应用,使弗雷泽的图腾理论成为转喻研究,与列维-施特劳斯的隐喻研究共同构成了基于图腾制的思维研究的两大核心。弗雷泽是由转喻推导出了隐喻的部分,列维-施特劳斯则试图以隐喻为基础推导出转喻的部分,在他看来,人与图腾之间的关系是伪装的,非要藉由人类社会与自然秩序两种既有分类系统之间的隐喻关系为前提,是人类群体的相互性及婚姻交换的实在性,经历了命名程序中部分与整体的替换,也就是说,交换女人之群体间的区别性特征被替换为人群与自然物种之间的诸多类聚关系,才重现为图腾制表面看起来呈现出的人与图腾之邻近关系。而对于弗雷泽而言,列维-施特劳斯描述的人类群体与自然分类系统之间的整体性隐喻关系,是要基于图腾制的转喻才得以发生的。我们目前只能够把转喻和隐喻都看作是最基本的思维结构之必然组成部分。
【关键词】弗雷泽;图腾理论;图腾制;列维-施特劳斯;转喻;隐喻;巫术
作为19世纪突然跃入科学研究的早期人类社会重大制度,图腾制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罗伯森·斯密(W.Robertson Smith)、弗雷泽(J.G.Frazer)和涂尔干(Emile Durkheim)先后以各自方式从图腾社会所提供的人类集体存在的基本自然机制和道德内涵中,证明了社会并非起源于自然法系统,这也恰恰对应于图腾制研究所担当的三重角色,罗伯森•斯密在图腾圣餐中找到了宗教的重大根源,涂尔干以图腾崇拜揭示了社会的根本形态,弗雷泽在图腾制里发现了思维的根本结构。但与此同时,图腾制作为思考人的自然状态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经验材料之一以及不可或缺的概念,对其理论的辨析却远远不够,尤其是对中央澳大利亚部落作为最重要的图腾群体所引起的理论分歧及其学术价值均未得到深入讨论。
到目前为止,图腾制理论大致可以分为思维和社会两种主要取向。涂尔干采取社会学进路,围绕以图腾崇拜为核心的仪式与信仰,铺展出集体情感所表征的社会本体论,由此图腾制导致的分类系统就是集体范畴投射于自然的结果,思维也就成了社会作用于个体心灵的衍生品。列维-施特劳斯从思维的角度,认为婚级系统与自然分类的共同作用使得部落社会呈现出的对称格局,本质上来自二元心智结构的共通性,图腾是对人类社会的隐喻,由此图腾制作为社会制度的实在性便被取消了。但问题在于,列维-施特劳斯是援引了波利尼西亚的材料才对澳大利亚部落的图腾与婚级系统作出了换算,而涂尔干以图腾的宗教性为本质所进行的化约,实际上并不能对图腾崇拜在不同社会组织上的不一致作出有效解释。而与此同时,弗雷泽早在《图腾制》(Totemism,1887)一书中从思维与社会两个维度作出的开创性探索却少为人知。并且不难发现,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原始分类》基于图腾制展开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弗雷泽这一早期图腾理论的框架,但这本主要呈现为对材料的整理分类的小册子,只是弗雷泽对图腾制的最早思考。随后在斯宾塞、吉伦提供了澳大利亚土著部落的大量详实民族志材料后,弗雷泽又先后两次调整其图腾理论,发表“图腾制的起源”(The Origin of Totemism ,1899)“澳大利亚土著中间的宗教开端与图腾制开端”(The Beginnings of Religion and Totemism Among The Australian Aborigines,1905),最终在更多的民族志材料基础上,将前述理论一并收录,在《图腾制与外婚制》(Totemism and Exogamy,1910)中对自己的第三图腾理论做了详尽阐述。在这过程中,弗雷泽在其图腾制理论中非常清晰地一步步趋向了巫术领域,并最终把转喻处理成图腾制的首要问题,这恰恰与列维-施特劳斯对图腾制作为隐喻的推导构成了明显对张。
今天重新讨论弗雷泽的图腾制理论,一方面是因为,图腾制作为弗雷泽介入思维与巫术研究的根本起点,无疑提供了理解其人类学思想的重要资源。另一方面在于,弗雷泽图腾制理论的调整与斯宾塞、吉伦提供的中央澳大利亚部落的民族志材料密不可分,而这恰恰是被涂尔干在同一地区建构理论时大大过滤掉的,并且,自澳大利亚图腾制被处理为社会之为道德存在的理论基础之后,思维研究这一线索在列维-施特劳斯之前似乎就被中断了。但澳大利亚图腾制作为思维研究的根本出发点,为我们提供了为数不多的经验上的案例,而弗雷泽对人类文明在政治、宗教和社会方面演进的图景勾勒也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对澳大利亚图腾社会的理解,因此,本文冀图通过辨析弗雷泽图腾理论的思考脉络,澄清弗雷泽对图腾制研究的贡献,以更好把握人类学基于图腾制研究形成的理论脉络。需要说明,本文不是一篇图腾制的研究,而是对图腾制研究的思想史的重要文本再梳理。

一、19世纪的图腾制研究
从麦克伦南(J.F.McLennan)的《原始婚姻》(1865)开始,关于社会构成之基本法则的探究就成为亲属制度和婚姻制度研究的核心问题。图腾制、外婚制与关系的分类系统作为早期人类社会广泛存在的三种制度,被弗雷泽归为19世纪科学大发现最重要的成果,由此人们才开始意识到有关“野蛮人”社会研究的必要,摩尔根(L.H.Morgan)在美洲部落的亲属制度中独立完成了关系的分类系统的重大发现,麦克伦南则首次提出图腾制与外婚制对人类早期社会与宗教演进的重要性。其中,规范婚所表达出的无中心结构被看做人类更自然的状态,引发了对婚姻制度早期形态的大量关注。而图腾制一边则更多留给了对宗教起源与本质的探讨。
1869年,麦克伦南在《双周评论》发表名为“动物崇拜与植物崇拜”一文,指出图腾制在美洲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土著部落两大人群中的盛行。麦克伦南把澳大利亚和美洲分别设定为最低、较低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视美洲、斐济的太阳崇拜为从图腾制发展出的高级形态,认为部落成员与图腾的关系可能会发展成崇拜者与神的关系,进而导致安抚图腾的宗教仪式的确立,其他图腾信仰也可能循此路线。由此他推演出了人类进化链条,认为图腾制是物神崇拜的变体。这种把图腾制简化为物神崇拜的处理,与麦克伦南所总结的图腾制独有的三个特征,即部落对应一个特定神、图腾沿母系继承和图腾对婚姻合法性的规定,共同构成了后人图腾制理论的思考起点。因此,图腾制一开始就既包含了对宗教的起源与本质问题的探究,又与其对通婚、继承方面的规定交织在一起。

最早回应麦克伦南的是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他认为图腾制源自对昵称的误解,原始言语的缺陷使野蛮人无法清晰区分食物与其名称,于是那些以动植物或其他自然客体命名的祖先,在后人的脑子里就与这些以之命名的东西相混淆了。因此野蛮人是从崇拜自己的人类先驱,逐渐变成了崇拜这些动植物或自然客体,言语的模糊又让他们以为自身和这些物种一体。约翰•卢伯克(John Lubbock)与斯宾塞的观点大同小异。他认为图腾制是对自然客体的崇拜,是通过命名行为产生的,人们逐渐以同名物看做与自己相干的事物,对其有了尊重和敬畏的态度,先是个人以动植物或其他自然客体命名,然后是他们的家庭。这种言语误会的论调,与当时风靡于一派哲学家的神话学色彩相一致,言语混乱开启了想象早期人类智慧的无尽宝库。而弗雷泽却坚信,像图腾制这般遍布世界绝大多数地区的庞大社会制度不可能没有更深层次的基础,也因此最早使图腾制与魅惑炫丽的神话学划清界限。
爱德华·克罗德(Edward Clodd)首次尝试为图腾制给出明确的定义。他指出图腾制包含了宗教和社会两个方面,其宗教面相在于它促进了动物崇拜,人们相信在图腾动物的身体里存在某些精灵,视图腾为神的化身;其社会面相是指由图腾制所导致的禁忌,一个是禁止以图腾命名的部落内的所有成员吃图腾;另一个是禁止同一名字的人相互通婚,图腾作为氏族的标记,在语言产生之前作为象形文字来指导不同部落之间的性关系是否允许。这个定义首次明确了图腾与氏族之间的对应关系,即作为氏族标记。但对由此关系引发的宗教与社会两种功能的解释并不等同,如克罗德指出,不吃图腾的禁忌很容易从宗教方面得到解释。但把图腾的社会方面看做部落间通婚可否的象形语言,实际上已经独立于图腾制的定义了。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麦克伦南的学生罗伯森·斯密对其老师理论的继承及其在早期阿拉伯人亲属制度上的相当发挥。实际上,罗伯森·斯密是以推演的方式,假定阿拉伯人和其他许多地方一样经历过图腾阶段,第一次提出了图腾动物的“神圣”(sacred)概念。他认为,图腾部落是部落的所有成员确信他们出自同一血缘,这种信念带有宗教特征,图腾被看做神圣的并且经常被赋予神的特征。他证明阿拉伯人存在麦克伦南所说的图腾制,并且同样伴随了母系继承和外婚制,部落成员与神的亲属关系是早期阿拉伯人社会的根本特征,而这种亲属关系正是以共有的图腾氏族名称及在身体上刻画相应的图腾标记来标记的。在部落分散为许多个地方群体的情况下,以图腾动物命名的家系成员通过图腾记号来辨认是否对另一个人负有亲属义务,与对方之间是否存在外婚法则,图腾制充当了野蛮人容易理解的一种有形且直观的亲属系统表达。不久后,罗伯森·斯密在图腾共餐仪式中发展出了祭祀理论,使图腾制成为闪米特人的宗教基础。这一理论为涂尔干提供了重大启发,认为他实现了图腾制度与古代宗教的重大衔接,而仅将其视为动植物崇拜的麦克伦南并未领会到图腾制的真正实质。
总的来说,19世纪图腾制的讨论,并未超出原始社会研究的两大理论取向——自然崇拜和泛灵论——之外。对宗教起源及其本质的推测,是这一时期图腾制的核心问题。由于图腾制在大多数情况下与外婚法则的并存,当后一主题经由麦克伦南的《原始婚姻》(1865)、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等进一步研究获得大量关注时,对图腾制的讨论则相对来说是零星且散乱的。人们间或以言语混乱去想象早期人类的思维状态,匆匆归纳出一个宗教演化链,为数不多的民族学人类学家则努力辨认图腾的本质,试图从中找出灵魂、精灵等或许适用于人类普遍心灵的概念。无论如何,在图腾制领域,以语言见长的神话学家的象征主义正急速退场,而对早期社会之为道德共同体的想象则还无从谈起。不过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在涂尔干选定澳大利亚图腾制为基本社会类型,将泛灵论与自然崇拜归为图腾制的派生形式,以此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一书全面阐述了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之后,图腾制所暗含的早期人类思维研究的线索似乎就被包括《原始分类》 《乱伦禁忌及其起源》在内的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给定论了,直至列维-施特劳斯1962年以结构语言学重启。涂尔干表示不关心图腾制度的普遍存在,把神性观念追溯到社会,确立了现代社会的道德基础,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类学家以图腾制及其不断扩充的科学民族志材料对早期人类思维过程的一次次推演,却并非如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的批评“是伏尔泰主义的滋长”抑或列维-施特劳斯所讥讽是对西方中心论的辩护。

二、弗雷泽图腾制的研究及其比较方法
最初着手编写《图腾制》,是弗雷泽受好友罗伯森·斯密之邀为大英百科全书撰写“图腾制”一文,他发现这一领域自麦克伦南指出其对早期社会历史的重要性后竟无甚进展,便亲自对能掌握的现有材料做了细致的分类与收集工作,他也坦言彼时自己并未形成有关图腾制或外婚制的任何理论。在《图腾制与外婚制》中,弗雷泽透露了他最初的想法是认为图腾制的关键或许能够在体外灵魂的理论中找到。当时的灵感来自好友爱德华•克罗德和荷兰民族学家威肯(G.A.Wilken),两人从普希金神话以及凯尔特人、俄罗斯、古埃及、阿拉伯的神话中发现了大量“不死”主题与体外灵魂的关联。弗雷泽将之与图腾制联系起来,推测人与图腾的关系其实是与灵魂容器的关系,为了安全起见把灵魂存放到动物或植物中的原始人却无从知晓哪一个是他的“魂器”,由于害怕误伤自己性命,就放过了该物种的所有个体。随后他发现,新人在成年礼中都被杀死又获重生,是明确的灵魂转移仪式,交换生命的观念便由此产生,以人的形态死,以其图腾动物或植物的形态复活,在青春期实现这种转移,是为了抵御性关系可能带来的神秘危险。这些观点也构成了他1890年版《金枝》的相当一部分。但是这一观点在《中央澳大利亚的土著部落》发表后就迅速放弃了。弗雷泽同样解释了放弃的原因:首先,在中央澳大利亚部落,图腾氏族的祖先向“储灵珈”转移灵魂的证据模棱两可,并且这些神圣工具与图腾之间的联系也远远不够清晰。其次,尽管在西非、尼日利亚南部和喀麦隆的部落中确实找到了体外灵魂信仰与图腾制关联的正面证据,也足以解释人们对图腾的禁忌态度,但弗雷泽坚持认为,这些证据并不足以解释整个制度的来源。很明显,中央澳大利亚民族志材料的相对完整,让他对其他地区提供的零星材料保持警惕,更重要的是,对于图腾制这个遍布于不同语言、民族、在相距甚远的世界不同地区的存在及其习俗与信仰上令人震惊的相似性,弗雷泽是冀图将其作为人类整体的一个制度加以把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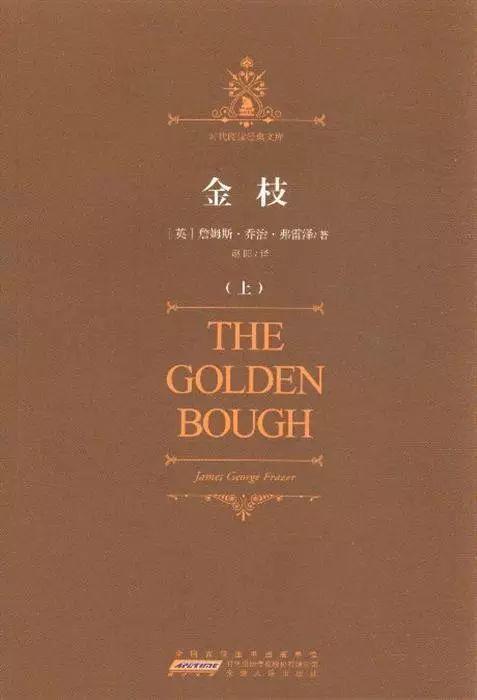
事实上正因为此,弗雷泽的比较方法长期为人所诟病,但如果明了他是以科学的方法对人类普遍思维作出探索,那么无论是其巫术研究,还是图腾研究,本身并不需受文化、社会、地理等因素的限制。这实际上是他的一贯立场,“(社会人类学)这门学科是人类思想和制度的胚胎学,或者更确切地说,首先是要去探明野蛮人的信仰和习惯……”。在弗雷泽看来,“野蛮人仅仅是在这些年才构成了科学研究的对象,我们还远远无法彻底了解他们。但是,对以理性主义解释的理论总是应保持怀疑的。在缺乏野蛮人对其历史正面证词的情况下,成功的惟一希望就是归纳的方法,而绝非演绎推理。导致它们产生的原因也必定要在野蛮生活的条件下去找,在野蛮人心灵的信仰、偏见和迷信中去找。如果我们渗透进野蛮人的心灵,理解其运行,我们就一定会公正地考虑较低民族中的真实信仰和习俗,对他们的调查必须尽量开阔,对他们的研究必须竭尽详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在一种情况下他可能会做的,才能知道在同样情况下他可能不会想到这样做。”弗雷泽对自己研究方法及立场的表明,结合他关于图腾制理论的变化——从1887年整理材料透出的草蛇灰线,到1899年以澳大利亚因提丘玛仪式为核心构建出巫术理论,再到1905年对澳大利亚土著部落的宗教与图腾制作出全面澄清——可以确定地说,对图腾制的思考是与弗雷泽转向巫术与王权研究相伴而生的。
三、图腾制的巫术面相:从自然崇拜到社会崇拜
《图腾制》使弗雷泽成为最早将图腾制作为人类重大社会制度予以单独处理的人。如果说麦克伦南和巴霍芬的母权论思想直接对话于梅因的罗马法研究,那么1887年的这一文本则很好地体现了图腾制一开始所包含的对宗教起源和本质的探究以及对婚姻制度的研究两个方面。弗雷泽沿思维与社会两条线索对图腾制作出细致整理,即便他请求读者重看《图腾制》时务必结合更正的部分,但在更为单纯的分类整理中体现于文本中的价值,同样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参考。
弗雷泽对图腾给出的定义是“图腾是原始人对其怀有迷信式崇敬的一类物质客体,相信在他与图腾的每个成员之间存在一种亲密的、总体来说很特别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相互有利的,图腾保护人,人以各种方式显示对图腾的崇敬,表现为不杀图腾动物,不采集或砍伐图腾植物;图腾从来不是某个分离出来的个体,而总是某一类客体,经常是动物或植物的一个物种,偶尔指无生命自然客体的一类,更罕见的是人造客体中的一类。前者强调人与图腾的关系是相互有益的,后者突出图腾作为类存在的特征。后一项界定了图腾的分类特征更显著地贯穿了弗雷泽对图腾制思考的始终,即,一群人与一群东西之间的对应关系。而前一项界定强调的相互有利关系,是弗雷泽在解释人对其图腾的态度时,与情感引发的崇拜区分的重要指标:最初解释人对图腾的尊崇态度时,弗雷泽认为是人们对图腾的巫术信仰以及出于被此种力量保护的心理,这里面并不必然包含情感因素,但仍不明确;随后在因提丘玛仪式中,弗雷泽确认了人与图腾物种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巫术思维,进一步排除了情感因素的可能;最后在阿兰达人怀孕图腾制的启发下,弗雷泽用接触律的思维法则解释图腾合一,由此我们可以放心地将弗雷泽图腾理论的本质界定在思维领域,以与涂尔干诉诸情感对图腾的神圣性的阐释作出明确区分。
根据先前的图腾定义,弗雷泽认为图腾至少可以分为氏族图腾、性别图腾和个体图腾三大类,其中氏族图腾是最重要的一类,其他种类都可以看做是氏族图腾的变异。氏族作为图腾的单位被明确出来,由于对彼此的共有义务和对图腾的共同信仰而结合在一起。于是图腾制便有宗教和社会两个面相,宗教面相是个人和图腾之间的相互尊敬与保护关系,社会面相则包含了氏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及其与其它氏族的关系。”弗雷泽对两重面相之间的关系的观察值得在此推敲,“图腾制的这两个面相在后来的历史中趋向于分道扬镳。有时,是它的社会系统比宗教系统存留得更久,反过来在另一些基于图腾制的社会系统业已消失的地区,则是其宗教系统保留了图腾制的痕迹。”第一种情况,即图腾现象已经消失之后,基于图腾制度而形成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发生实质的改变,这意味着图腾制在社会面相的运行并不依赖其宗教面相。第二种情况是说宗教面相的持续与社会面相的缺席是并行的,由此呈现出的社会,是图腾对社会组织不具备约束力。不难推出,社会面相的稳定性和独立性都要更强,不过弗雷泽似乎此时并未察觉到,“证据总体上都强烈指向的结论是,两个面相在源头上是不可分离的,也就是说,我们越往回追溯,就越发现氏族成员视自身与图腾为同一物种,对图腾的行为与对氏族同伴的行为,原始人对此并不区分。”弗雷泽显然对图腾合一的原则已经有所意识,只是并未明确意识到分类法则是在思维与社会两个层面运行的。
图腾的宗教面相这一部分,弗雷泽是围绕着对图腾所具有的巫术力量的信仰而展开的大体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与图腾合一的追求,他认为是为了最大程度获得图腾的全面保护,包括穿图腾动物其他部位的皮,把头发、身体都弄得跟图腾相像,通过疤痕、纹身和涂色在身体上再现图腾。另一个是与图腾之间的相互有利关系,对图腾的尊崇是以期待图腾回报人以同样有利举动为基础的,希望免遭图腾动物的伤害,或者特有某种治愈能力。图腾应积极地使它的人受益,如果图腾未能满足人的愿望时,人们还会对图腾施加压力以使其满足自己的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在弗雷泽列举人们追求图腾合一的模仿行为这里,出现了图腾的符号功能,这一功能附着于氏族单位之上,成为氏族成员的标记和证明:在住屋、重要财产、船只、盔甲、武器以及氏族成员的坟地都会有图腾标记;特林基特人的氏族代表们进行赛跑、跳舞时,要在身上纹自己的图腾;休伦人的各氏族都有自己的图腾样式,至少在酋长就职仪式上如此。两个面相在这里几乎是完全混合的,既作为氏族间彼此区分的凭藉,又包含了对获取图腾巫术力量的期待。弗雷泽没有对两种行为的动机作出区分——即对图腾在身体上的模仿是为了获取巫术力量,而图腾符号的再现则在于充当氏族标记,这意味着图腾的精神力量与社会群体身份之间的关联逻辑是模糊的,而这恰恰是涂尔干将图腾本原追溯到社会的关键。但实际上,弗雷泽这部分材料几乎全部来自美洲,在澳大利亚并不存在这一混淆,至少在阿兰达人中,图腾的巫术性与氏族群体的标记并无关联。
弗雷泽起初用对图腾的敬意来概括人对其图腾的态度,但这其实可以同时包含情感和思维两种因素,不吃图腾可以很自然地从对图腾的敬意中推出,既可以出于情感也可以出于同类不相食的逻辑,但冒犯禁忌所引发的巫术性惩罚,实际上只能诉诸思维层面,因为害怕冒犯图腾应当是先行有了对巫术惩罚的认知而产生,而不太可能是被图腾物本身激发出了畏惧情感,至少是无法从人与图腾之间的关系推导出来的。而且如果用禁忌来解释人与图腾的关系,在不同地区差异甚大。吃图腾会引发的巫术性惩罚在萨摩亚地区和澳大利亚都能找到,但是图腾引发的食物禁忌在澳大利亚却完全不齐整。首先,在中部澳大利亚,食物禁忌的名单远不止图腾,而是一套复杂的食物禁忌法则,在青春期最严格,随年龄增长而逐渐放宽,其次,在南部澳大利亚的迪埃里人中完全不存在对图腾的食物禁忌,他们杀起图腾动物来从不犹豫。弗雷泽的推测是对图腾的敬意衰弱甚至完全消失。但这已经表明在澳大利亚,想要把食物禁忌与对图腾的敬意关联起来是相当勉强的,因为既存在诸多非相关性情况(不是图腾也不能吃),又有着完全相反的明确例外(即便是图腾也照吃不误)。尽管弗雷泽是至1899年了解到因提丘玛仪式在中央澳大利亚部落的普遍存在后,才把人与其图腾的关系明确为巫术性的——也就意味着对图腾的态度并非情感所致——但1887年的文本线索中已经不难发现,若非借助演绎的方法,诉诸情感来解释图腾制面临相当多困难。
成年礼最初在弗雷泽看来也同时承载了图腾制的两个面相。因为成年礼的核心目的在于向年轻人传授一种特殊的性语言,这首先是图腾制的社会面相,但这种语言又以图腾的宗教面相为基础。一个是在氏族成员身上制造伤疤作为部落的纹章,或直接画他们的图腾,同时还伴有通过敲掉牙齿等残损身体的行为以追求与图腾的相似;另一个是通过图腾舞来使年轻人掌握特有的身体动作,这种图腾舞不是对动物的巫术性模仿,而是一种具备相当程度稳定性的择偶方式,他们能借此与语言不通的陌生人交流。这本质上和图腾作为氏族标记的符号功能类似。图腾充当了象形语言来指导氏族间的两性关系,这基本上延续了罗伯森·斯密和克罗德的观点,但霍威特提供了澳大利亚部落诸多特有的性交语言与其图腾并无直接关系,弗雷泽到1910年时也指出,在成年礼上为新人所表演的仪式与其图腾毫无关系,这些仪式可以是任何图腾。而成年礼的宗教面相则是向新人施加食物禁忌和向新人传递图腾的巫术力量,但前者是氏族层面,而后者则是部落。并且弗雷泽还在成年礼中发现了另一种不同于氏族的社会组织,“澳大利亚的成年礼并不是由跟其属于同一图腾的男人来指挥的,而是来自部落内他可以通婚的那部分的男性。有的维多利亚部落,任何跟年轻人有血缘的男人都不能在他的成年仪式上进行干预或辅助。”很明显,通婚单位和图腾氏族其实是被明确区别开的,并且前者在成年礼中更占优势地位。这同时也意味着成年礼上施加的食物禁忌,是关系到图腾氏族还是涉及通婚单位,换句话说,是基于图腾制的巫术面相还是社会面相,这种逻辑联系始终是模糊不清的,当然弗雷泽此时并未区分。
在成年礼之后,弗雷泽介绍了一类特殊的图腾崇拜非常引人注意。他在最开篇时其实就注意到这种图腾在分类上的特别,并将其专门命名为交叉图腾(crosstotem)和交叉分割图腾(cross-splittotem),前者的名字本身包含了好几个物种,超出了单一物种的范围,比如奥马哈人的小鸟、爬虫图腾,索克人和福克斯人的大树图腾;后者更为特殊,它们既不是一个完整的动物或植物,也不是动物或植物中某个特定种类中的一部分,而是所有(或者是许多种类的)这一动物或植物中的某个特定部分,比如所有动物的耳朵、鱼眼、骨头、血。在他看来,这些图腾群体看来更像个宗教会社而非图腾氏族,“这些跨越了图腾血缘的常规序列、但在许多北美部落的社会生活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的神圣舞蹈帮(band)或者会社(association),与图腾制密切相关。这些帮大部分拥有动物的名字,拥有特色的舞蹈,成员在跳舞时佩戴的标识常常由帮的名字的动物的部分所组成。与图腾氏族不同,这些帮的成员不是图腾血亲,而是由购得了某种入会特权的人构成,在每个社会中,他们一般都是同一年龄的所有人。有些帮被委以某种政治功能,比如在露营时、行进中和打猎时维持秩序等等。”弗雷泽推测,“这些会社很可能源于这样一种感觉:对图腾的保护,靠图腾自身是不够的,有了这种感觉,人们就寻求额外的保护。比如一些帮有用于出战前擦在身上的‘药’,相信这会让他们不受伤害。”
弗雷泽还专门在达科塔人中对“氏族”与“会社”做了区分,他认为费兰德•普利斯科特先生在于1847年的达科塔人中所描述的“氏族”,看起来更多是个宗教会社,而非图腾氏族。这些达科塔“氏族”是使用同一种植物根做“药”而组成,每个“氏族”有特殊的“药”,由于信仰,他们之间有着直接的世仇,每个“氏族”用自己的巫“药”去伤害其他“氏族”的人。每个“氏族”都有一些神圣动物(熊、狼、水牛等)或者动物的一部分(头、尾巴、肝脏、翅膀等),他们终生崇敬,不能吃也不能杀图腾动物,也不能踩到它或者走近它,触犯这些规则,会给违犯者带来麻烦。所有这些特征是图腾制的,但是这些“氏族”的认可机制(以伟大药舞的方式)说是会社更合适。而这时的图腾禁忌也更为严格,萨摩亚氏族的根部图腾被认为是神圣到了仿佛是有毒似的程度,绝不适用于日常的任何用途,这种由神圣性所引发的禁忌,在弗雷泽看来,由人与图腾关系引发的禁忌已经根本不同,因为之前对图腾的尊崇,是基于分类关系对图腾巫术力量的信仰,但这种会社的图腾与其成员之间并不存在这种分类关系,而是以图腾不可触犯的神圣性来维系自身,这和涂尔干有关图腾本原即社会的论述,仅一步之遥,这种图腾本质上指向的就是对这种兄弟会社本身的崇拜。但这种图腾崇拜在弗雷泽看来完全无涉道德,而是图腾的巫术力量下降到不足以对抗超自然危机时政治组织的诞生。
与这种兄弟会会社性质类似的图腾,是性别图腾。弗雷泽毫不犹豫地用了“神圣动物”一词来形容科奈人、塔塔西人、库林人中的性别图腾,虽然并未给出“神圣”的明确定义,但是他指出性别图腾比氏族图腾更神圣的原因在于,“男人并不反对其他人杀氏族图腾,但却会强烈地保护性别图腾不受到对立性别的任何伤害。”由性别图腾的“神圣性”维系的群体纽带所引发的敌意,在弗雷泽这里看起来是格外突出的。
个体图腾与氏族图腾的不同,在于与图腾的相互尊重有利关系开始且终止于个体,不通过继承传递下去。弗雷泽分别列举了个体图腾在澳大利亚和美洲的例子,虽然在两个地区,个体图腾的获得方式都主要是通过梦境,但在澳大利亚,个体图腾与超自然知识或力量的获得关系更密切,而在北美,个体图腾更多来自成年礼的禁闭期间,且常常是一种食肉动物,这些图腾与打猎或战斗密切相关,表现出了显著的力量特征,甚至出现了向个体图腾的献祭。不过弗雷泽到1910年最终只保留了氏族作为图腾的有效单位,性别图腾和个体图腾被更改为“性别守护神”和“个体守护神”,与前述的北美帮和会社一并归入“神圣会社或秘密社会”的主题下单独处理。这些最终被弗雷泽从图腾制中过滤掉的图腾形式,首要区别在于,它们并不像氏族图腾是遗传性质的,这些主要分布在北美和西非的会社崇拜,弗雷泽认为是处于图腾氏族所代表的共同体与守护神所代表的个体主义的中间形态。

四、图腾制的社会面相:巫术分类与社会分类
弗雷泽在图腾制的社会面相的论述中,包括了图腾氏族共有的血仇义务、同一图腾的人禁止通婚的法则以及继承原则三个方面。血仇义务以氏族为单位,图腾氏族的所有成员都视彼此为亲属,兄弟或者姐妹,一定要相互帮助和保护彼此,在澳大利亚西部、西北美洲的氏族中十分明显,弗雷泽认为这种图腾纽带很可能适用于图腾制度充分发挥作用的所有社会,即氏族作为共同体的行动原则,既非地域原则也不是人类亲属制度意义上的血缘原则,而是出自一种思维法则,基于图腾的巫术面相而导致的群体间的分类,这种图腾纽带的强度超越了现代意义的家庭或者亲属关系。杀害氏族同伴被等同于攻击图腾本身,是可耻的犯罪,这与图腾制的巫术面相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外婚制在弗雷泽最初的图腾制构想中,是被纳入与巫术面相并存的社会面相来处理的。触犯这一禁忌,招致的后果既有巫术性的——如纳瓦霍人认为氏族内通婚会导致违犯者的骨头枯竭而死——又有社会性的惩罚。但介入惩罚的也不止是氏族,还包括部落,“在维多利亚的一些部落里,只要察觉属于‘同一块肉’的人中间有任何求爱迹象,女人的兄弟或男性亲属都会狠狠地打她,男人则被带到酋长面前,被指控企图变成一块肉,并被部落严惩。”这种乱伦禁忌似乎比较常见,弗雷泽虽未交代其来源,但也没有跟道德关联起来,“在林肯部落的例外,是同一氏族永不通婚,但不认为氏族内的乱伦会有损道德。”
然而外婚制作用的社会单位远远超出氏族范围,弗雷泽在这里重新引入了一种新的分类逻辑,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胞族(phratry)在澳大利亚的利用。胞族概念来自摩尔根,弗雷泽认为在美洲和澳大利亚,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图腾氏族组成的同一部落内的外婚制群体可以称之为“胞族”。并且,弗雷泽用“胞族”替换了霍威特、费森对澳大利亚婚级单位的命名,由此,澳大利亚部落的典型社会组织就是二分胞族-四分次胞族-若干个图腾氏族,以卡米拉罗伊(Kamilaroi)部落为代表,这样一来,弗雷泽很清晰地看到,部落在外婚制上的一致性,胞族是外婚制的,胞族的次分单位(次胞族、氏族)也是外婚制的,但是在继承方面却出现了无法合理解释的特殊继承方式,即在这样的部落中,无论图腾的继承是沿母系还是父系,在胞族和氏族层面都是直接的,在次胞族一级是间接的。实际上弗雷泽这时没有意识到,继承本质上体现的是来自巫术面相导致的对自然物种的分类,而外婚制在部落整齐划出的社会分类,两种分类原则上的不一致,恰恰表明了图腾制两个面相的不可化约。实际上直到1910年,弗雷泽也没能将这两者统一起来,而是通过阿兰达人怀孕图腾体现出的感应原则,把外婚制与图腾制彻底择开为两个完全独立的系统。
但在推测澳大利亚部落的原始分类系统时,弗雷泽对氏族图腾与次图腾的区分,又展现出令人钦佩的敏锐。他指出,在典型的澳大利亚部落中存在的次胞族图腾和胞族图腾不同于氏族图腾,并假定氏族图腾是最初的联结,逐渐减弱后重现为次胞族和胞族图腾,以此,在澳大利亚部落对整个自然作出的一个初级分类系统中,弗雷泽看到了图腾在逻辑上的这种叠加过程,并指出这种叠加于图腾之上的图腾与种属的分类系统相似。以澳大利亚南部的甘比尔山(Mount Gambier)部落为例,部落分为Kumi和Kroki两个胞族,又各自再分为数量不等的图腾氏族,每个图腾氏族除了拥有自己的图腾以外,还被分配了其他一些自然客体,氏族成员被禁止杀害的除了氏族图腾,还有这些被分给他们的自然客体,霍伊特(A.W.Howitt)称之为次图腾,在瓦坎布拉(Wakelbura)部落、沃乔巴卢克(Wotjoballuk)部落都拥有这样的次图腾。弗雷泽指出,这些次图腾正是由于在图腾之下被分类因而共享了对图腾的尊崇。这意味着在弗雷泽这里,澳大利亚部落的原始分类系统单从思维角度就可以彻底得到解释,一种是图腾的巫术思维导致的对自然物种的分类,一种是前一分类基础上进行的逻辑推演,也因此呈现出图腾的样貌。
这里便不得不提,涂尔干、莫斯(Marcel Mauss)1903年的《原始分类》在同样材料的处理上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涂尔干认为,澳大利亚社会存在的两种分类体系,一种是在胞族、姻族之间的种属分类,直接对应社会群体的划分因而具有逻辑必然性;一种是在胞族或氏族(图腾)间的分类,同一胞族的氏族间历历分明,但在划归于氏族内的各种事物却含混不清。涂尔干认为第一种分类是首要的,它的逻辑必然性证明了分类来自社会给定的范畴,而后者则是由于使范畴得以确立的根据被遗忘,范畴本身则以个体为中介或准确或牵强地继续发挥分类作用,才有了初步的混淆。因此,涂尔干把分类系统的根源仍然指向社会。但涂尔干两种分类之间建立起来的推导关系,在弗雷泽这里则是内在于图腾制始终并存的两重面相。涂尔干其实是对这两重面相进行了化约,把澳大利亚图腾社会作为宗教原型,诉诸情感将图腾本原追溯到社会,以此,原始分类也是由对社会的宗教情感而导出的理性分类系统,以此来论证社会的必然性。但这种化约其实并不能完全实现,已经有人指出,涂尔干在以图腾巫术性导致的乱伦反感来解释外婚制时,却无法解释由图腾氏族构成的姻族何以在严格遵守外婚禁忌的同时却不存在图腾崇拜。同样,涂尔干批评弗雷泽没有看到澳大利亚原始分类的逻辑价值,恰恰表明在弗雷泽看来,这只是不足以涵盖图腾制的全部。
值得注意的是,在图腾的社会面相中,有两种非常显著的材料是弗雷泽无法纳入社会面相的一般性论述,而只能处理成特例作为补充。一个是澳大利亚吃人肉习俗的大量存在。“一些维多利亚部落把新生的婴儿杀死并吃掉,还分给年长一点的孩子吃,认为后者会因此额外获得婴儿的力量。”弗雷泽试着用“生命不能从家庭中离开”这一原则来解释这类习俗,认为这和成年礼上部落血不能外流类似。但这种解释很牵强,既和不能杀害氏族同伴的逻辑完全相悖,又与外婚禁忌“不能变成同一块肉”的逻辑相互冲突。可以看到,图腾的巫术面相与社会面相在此构成了最直接的冲突,而且不难发现,这种习俗似乎都是氏族和部落层面,完全没有提到胞族、次胞族中有吃人肉情况的发生,换句话说,在次胞族和胞族的层面,不存在人与图腾亲密关系的假定,至少这种图腾的巫术性是不够实在的。
弗雷泽提到的另一个特例,是在北美部落中发现了氏族间存在着明显的对称性二元分化,并且不全是功能性的。奥色治人的各氏族划分为战争氏族与和平氏族两组,外出猎捕水牛时,两组氏族在部落圈的相反方向扎营。和平氏族不许杀任何一种动物,他们必须以蔬果为生,但却可以吃从战争氏族那里交换来的肉。在这个例子中,图腾的氏族单位仅仅成为追求二元对称而填充的符号,图腾不再具备实在意义,这与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图腾制分析已经如出一辙。是到这个时候,图腾的巫术性意义才是可以被取消的,但也很难说是全部。当把吃人肉与北美部落中的二元氏族这两个特例对照起来时,实际上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氏族图腾的两种类别,即可以构成吃人肉正当性的巫术性图腾,和以二元对立为特征、不具备巫术意义的分类性图腾。
最后,弗雷泽根据霍伊特提供的次图腾趋向于独立的证据,结合摩尔根关于氏族倾向于发展成胞族的论断,勾勒出了一个完整的图腾生命周期:“次图腾是生长期,氏族图腾是至成熟期,次胞族和胞族图腾则是相继步入了衰败阶段。随着一个图腾抵达发展顶峰再日渐疲乏,同样的过程在一个又一个图腾上相继出现,直到自然的所有事物都参与其中,跟它所起源的广袤的自然汇成一体。”在1899年弗雷泽正式开始理论构想后,这一图腾生命周期说就被放弃了,弗雷泽转而愈加强调图腾制是巫术系统,图腾制便只能作为思维的一个阶段。但在此仍必须要指出,弗雷泽最早的图腾构想其实是涵盖了巫术与分类的一套完整的思维结构。我们几乎在这里看到了莫斯在《巫术的一般理论》中勾勒出的四维空间,即理性的三维空间分类与巫术思维共同构成的世界。莫斯认为巫术是作为一种信仰呈现于个体心灵当中,并不来自社会,玛纳则存在并流动于经验的理性的三维空间以外,既充当了个体思维与社会情感之间的一种单纯的巫术力量,又使巫术表现出了足够的理性。由此莫斯用玛纳建立起了巫术与理性两种思维的连接,但他指出玛纳有时但并不总是呈现为图腾,而弗雷泽恰恰是在图腾的构想中无意间对莫斯所描绘的人类思维世界做了奇迹般的预演。
在初期整理工作告一段落之前,弗雷泽以图腾制为人类社会划出了一条界限:当图腾物种中的某一个体被提升到一个凌驾于所有其他个体之上的位置时,图腾制便在实践中被放弃了,它的两个面相——宗教与社会——都开始向王权阶段迈进。弗雷泽在此收笔,把图腾制的界限停驻在无中心社会,尽管随后的图腾理论几经调整,但他对巫术关注的愈发凸显和理论取向则确保了澳大利亚图腾社会不曾突破这一边界。

五、中央澳大利亚部落的图腾制度
1899年斯宾塞、吉伦发表《中央澳大利亚的土著部落》,该书被弗雷泽评价为一份“重要性几乎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被高估的人类历史的文件”,“毫不夸张地说,在人类早期历史的研究者未来不免要翻阅的文献中,极少或没有比《中央澳大利亚的土著部落》更重要的了。野蛮人的消失也带走了一篇篇人类最古老的历史,随着能为将来后人保存下这些部落记录的机会在逐年降低,那些为数不多的我们有把握的可信记录,其价值只会增加而非降低。”他也第一次正面阐发了对早期社会研究与人类重大制度的关联,指出中央澳大利亚人存放储灵珈的山洞,如何在共同体以外的地方发展为一个“神殿”,这可能与非洲酋长或国王的坟墓遵循了相同的轨迹,进而成为一座城市乃至罗马帝国的起源。
而中央澳大利亚部落的新材料也使他重新调整目光,首先面对与旧有图腾制理论相悖的两个显著事实:首先,是规定一个人不能杀或吃自己的图腾动物或植物。这个规则大致被遵守地相当好,只在目前的澳大利亚中部有某些明显的例外,并且有证据表明阿兰达人的祖先一度自由行使吃图腾、杀害图腾的权利。第二,禁止与同一图腾的女人结婚的习俗,在以乌拉班纳部落为代表的一组部落中仍被很好地遵守,而另一组部落以阿兰达人为代表的部落,图腾却对通婚和继承毫无影响。因此,中央澳大利亚部落的传统与实践的分歧如何衔接便成为弗雷泽首要处理的问题。因提丘玛仪式的明确繁殖目标和图腾氏族的仪式性食用,使弗雷泽正面确认了与图腾合一是图腾制的首要原则,因为这样就同时解释了吃图腾与对图腾的仪式性食用,而禁止氏族成员吃图腾的原则则是附属性质的。因提丘玛仪式的季节性与欧洲仲夏节庆之间的相似,也使弗雷泽迅速得以确认为该仪式系统的巫术性质,在兴奋之余,把繁殖动植物的因提丘玛仪式推到了其他无生命图腾上——事实上他只找到了水图腾的降雨仪式,并且严格来说并不算繁殖仪式——并试图以此解释次图腾,认为中央澳大利亚部落的图腾制是一个有组织的巫术系统,目的是为了实现野蛮人所需要的对自然客体的全部供给。
与此同时,阿兰达人的材料使弗雷泽第一次看到外婚制的作用范围并没有与图腾氏族重合,也初步识别出图腾制两个面相的关系,即中央澳大利亚土著人中的外婚制是施加到目前图腾氏族的系统之上的。而中央澳大利亚部落中同一图腾的人结婚,从图腾合一原则来看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种与自然一致的系统恰恰是外婚制尚未引入,即图腾制未受到婚级系统的改造的表现。弗雷泽认为原因很简单,“在这之前进入到我们视野的图腾氏族普遍都实行外婚制,而这些图腾氏族在外婚制上的显著例外可以简单做个假设来解释,简单地说,外婚制的目标是首要是为了避免是兄弟与姐妹间的婚姻,其次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婚姻,但在这些部落中采用外婚法则并不能防止这些婚姻的发生,也无法对图腾继承加以规范。”
因提丘玛仪式在中央澳大利亚部落的显著存在,使弗雷泽确认巫术面相为图腾制的更早阶段。斯宾塞在书信中认可了这一猜想,并补充了图腾的巫术面相与地区生命条件之间的关联,即在中央地带,图腾的巫术方面几乎排除了社会方面,随着向海岸推进,呈现出巫术性递减、社会性(通过图腾的通婚规则所表明)递增的趋势。则但单从因提丘玛仪式把图腾制推导为一个庞大合作巫术系统的理论终归过于仓促,这一构想至晚到1905年就被放弃了,弗雷泽自己也坦言,“首次发现在中央澳大利亚人中间这些因提丘玛仪式的大规模存在时,我被这一重大发现深深震撼到了,当时想要在这些仪式中看到图腾制的终极起源……进一步思考后的结论是,控制图腾增减的巫术仪式可能是图腾制的自然结果,而不是其根源。”
最终,弗雷泽进一步缩小比较范围,将图腾制理论锁定在澳大利亚大陆上,于1905年发表“澳大利亚土著中的宗教开端与图腾制开端”,对图腾制、外婚制的性质与关系作出了全面澄清。弗雷泽重申,宗教在澳大利亚土著那里几乎是缺席的,经验研究显示出的人类早期图景是一群群自以为可以上天入地的巫师,每个人都幻想自己能对自然进程施加影响。
澳大利亚图腾社会的确蕴含了宗教初级阶段的多种萌芽,但在中心地带却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至上存在,受地理隔绝和自然条件的不稳定,中央澳大利亚部落的图腾社会尚未像其他地区一样开始朝向社会生活的更高形式进化。
把阿兰达人的怀孕图腾确认为最古老的图腾制类型,是弗雷泽解开图腾制的最后一步。其实1899年时弗雷泽已经获知了这种图腾类型,但他当时对图腾合一原则的推导,主要是基于因提丘玛仪式和储灵珈来解释人与图腾动物之间的双重转换。在对基于因提丘玛仪式构想出的巫术合作系统的理性与复杂程度产生质疑后,弗雷泽想要找到一种更简单的观念或是更原始的迷信,对阿兰达人图腾的重新审视让他如自己所想,在土著人自己对怀孕的解释中更进一步趋近早期人类的思维状态。在阿兰达人中,图腾既不来自父亲也不来自母亲,而是来自母亲首次感受到体内生命迹象那一刻所在地附近的精灵,这些精灵以类分布在全国各地地区,而土著人对这些地点非常熟悉,只要感受到子宫内的生命迹象,母亲就能根据她当时的印象判断出孩子属于哪种图腾。这种图腾几乎纯粹由偶然决定,人与图腾的关系可以经由生命在人体内的传递直接达成。“出于对生孩子真正原因的无知,他们想象,一个孩子只会在女人第一次感到子宫动静的时候闯入女人的身体,因此他们只能跟自己解释为什么是在那个特定时刻进入她的身体。这必然要来自外部,也因此只能是在女人得知自己有孩子那一瞬间所看到或感觉到的东西。”这一怀孕理论以再简单不过的方式使所有现存材料都通过图腾合一原则得到了解释:解释了人们不杀图腾,解释了为什么偶尔有义务吃一点图腾动物或植物,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会被认为分享了图腾的品质和特征,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会说自己是图腾的后代,解释了图腾制整体的庞大范围——从飞禽走兽,到自然的鬼斧神工,再到最蹩脚的手工制品——因为所有东西都可能会在那个关键时刻留下惊鸿一瞥,被女人断定是自己的孩子。弗雷泽相信,尽管这一怀孕理论并不直接解释人与图腾的关系,因为进入女人身体的是图腾精灵,而非图腾动物或植物,但这距绝对原始的图腾制仅一步之遥,因为它完美解释了图腾制的核心,即一群人与一群东西之间的认同。弗雷泽最终以阿兰达人的怀孕图腾作为其图腾理论的重要依据。他对纯粹图腾制的设想也被里弗斯1909年在班克斯群岛的发现所证实。
弗雷泽由此把怀孕图腾作为图腾制的第一阶段,澳大利亚既有的图腾系统便都得以解释:阿伦达(Arunta)和卡迪斯(Kaitish)人的图腾系统是结合了怀孕原则和地域原则,因为个体获得图腾的随机范围受地点及该地区物种所限,怀孕图腾在保留感孕原则的同时就会发展为某个物种的地方性图腾;翁巴亚(Umbaia)和格南吉(Gnanji)部落则代表了地方性图腾过渡向继承性图腾的一种,在那里几乎总是把父亲的图腾分给孩子,哪怕发出第一个生命信号的地点是别的图腾,比如一个蛇氏族男人的妻子,在一棵树下感到了子宫颤动,而那棵树是鹰精灵驻留的地方,但是孩子的图腾并不会是鹰,而是跟他父亲图腾一样是蛇,土著人自己的解释是只有丈夫的图腾精灵会跟着妻子,伺机进入,而其他图腾的精灵则会拒绝进入不是自己图腾的人。弗雷泽对这一过渡过程的辨析,实际上回应了莫斯的批评,后者认为,接触法则是指品性的简单转移,比如啮齿动物牙齿的坚硬性被传递给一个牙疼不止的人,因此接触律必须要和分类的原则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必须先有动物坚固的牙和你的牙都是牙的观念,才会产生动物牙的坚固特质传递给了你的牙,而不是动物变成了你。但弗雷泽这里解释继承原则的出现已经表明,分类或者品性的概念是到了继承阶段才开始发挥作用。阿兰达人的怀孕图腾也表明存在着一个纯粹的接触律阶段,孩子的图腾无法控制的,全凭接触律,经过某块地方,不知道就怀了哪个图腾的孩子。当父系图腾继承的制度发育出来之后,接触律才受到分类概念的限制——那块地方还是有很多图腾,但只有跟丈夫的氏族图腾相关的那个图腾动物才会进入女人的肚子。弗雷泽还指出,由于父系和母系两种继承都可以从怀孕图腾的系统独立产生,因此图腾的父系继承并不必然晚于母系继承,父权的概念很可能来自所有权的观念而非继承。
新的图腾理论却仍无法解释外婚制,也使弗雷泽进一步确证,外婚制是在业已由图腾氏族形成的共同体之上的一项改革,其作用的单位如霍伊特、斯宾塞、吉伦的猜想,是部落的二分组织。由图腾的巫术性导致的分类原则与婚级系统的二分原则自此在弗雷泽这里彻底分道扬镳。在修正自己先前理论的同时,弗雷泽也看到涂尔干对其旧有观点的采纳,后者把图腾制视为图腾崇拜的宗教,并在其中找到了外婚制的起源,弗雷泽再次重申,新证据表明至少就澳大利亚而言,外婚制的通婚单位或胞族是完全不同于图腾氏族的社会组织,在起源上要更晚,并且是叠加到图腾氏族之上的,只要把图腾氏族等同为外婚制单位,或者说,只要假定图腾氏族从一开始是外婚制的,那就永远不可能理解图腾制与外婚制的关系。早期人类对乱伦的反感,与其说是乱伦禁忌的开端,倒不如说是其结果。抛开理论取向和学科方法的差异,在对中央澳大利亚部落的证据予以全面考虑的情况下,弗雷泽最终以接触律切入的思维进路无疑是对阿兰达人图腾作出的最有效处理,但同时亦不得不承认,由此构建的图腾理论是以悬置了外婚制的起源为前提的。

六、结语
在长达二十余年的持续思考中,弗雷泽最终让图腾制与外婚制各归其位。他以阿兰达人的怀孕图腾所蕴含的对生命力的传递作为最根本的接触律,这种接触律既直接达成了人与图腾的亲密关系,又导致人们无法清晰区分真正的同类与图腾,图腾制由此呈现了人类思维的早期朦胧状态,也实现了人类与他者的最初结盟,“它是一种结盟和友情的约定,缔结为氏族与动物物种或某种东西之间的平等,结盟双方彼此尊重,但并不崇拜对方。这种结盟同时包含了人与图腾的肉体(corporeal)关系和社会关系两个方面,当人们越来越多在意后者时,也就逐渐放弃了吃图腾或亲人,这种对他者(即图腾)感受的更多顾虑——也就是越来越不把自己当做动物,而越来越多把动物看做人时——在弗雷泽看来便是高级本性的标志,而这一人性升起的过程是在由迷信和巫术所代表的思维内所完成的。
最后必须要指出的是,阿兰达人作为人类学理论策源的核心群体,弗雷泽在此应用接触律确立的图腾制的转喻关系,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处理。而列维-施特劳斯更多是以瓦拉蒙加人和弗思的波利尼西亚图腾制为基础,来讨论图腾制作为一种交换主体所形成的广义互惠,但这一理论对阿兰达人没有任何解释力,因为在阿兰达人中间,图腾根本不参与广义互惠,广义互惠是被婚级决定的,图腾则是随机的。而弗雷泽在阿兰达人中确立了图腾制的转喻关系,图腾制的这种随机性质——或者用列维-施特劳斯说的统计学性质——在继承关系出现后开始被严格规定,由此转入了图腾制与婚级制的紧密结合,而这一结合关系在后来发现的人类学案例研究中已经变得不可拆分。因此,本质上来说,弗雷泽是由转喻推导出了隐喻的部分。相较之下,列维-施特劳斯则试图以隐喻为基础推导出转喻的部分,在他看来,人与图腾之间的关系是伪装的,非要藉由人类社会与自然秩序两种既有分类系统之间的隐喻关系为前提,是人类群体的相互性及婚姻交换的实在性,经历了命名程序中部分与整体的替换,也就是说,交换女人之群体间的区别性特征被替换为人群与自然物种之间的诸多类聚关系,才重现为图腾制表面看起来呈现出的人与图腾之邻近关系。而对于弗雷泽而言,列维-施特劳斯描述的人类群体与自然分类系统之间的整体性隐喻关系,是要基于图腾制的转喻才得以发生的。但弗雷泽面临的困难在于,对于广泛存在的基于婚级制度的二分现象完全没有解释力,而列维-施特劳斯的困境则在于始终找不到突破思维二元对称性的机制,而无法解答政治组织的客观化过程。我们目前只能够把转喻和隐喻都看作是最基本的思维结构之必然组成部分。

图文来源:《民族学刊》2018年第6期,转载于微信公众号“民族学与人类学Anthropology”2019-12-11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