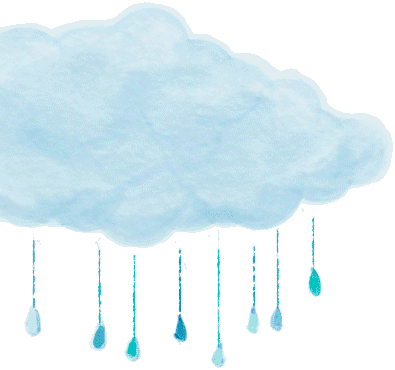一、皇太极赦令建延寿寺—宗教性的空间
公元1643年,清太宗皇太极赦令在距盛京中心庙东、南、西、北五里处各建塔寺。建在盛京庙西的“护国延寿寺”,取“祈祝圣寿、虔求国泰民安”的含义,作为其基座的白色藏式塔—白塔—就成为延寿寺的标志性建筑物,民众通常用白塔来指称延寿寺及其周围的区域。
延寿寺“祈祝圣寿、虔求国泰民安”的政治统治寓意,为以白塔为标志的物理空间蒙上了一层宗教色彩。延寿寺建成后,便有藏族喇嘛居住寺内,为百姓祈福延寿,附近百姓每逢初一都会来此上香祈拜。在这个意义上,延寿寺提供了一个不同于日常的神圣空间,喇嘛与香客之间的宗教互动实践就发生于这一寺庙的空间中。正如涂尔干所指出的那样,“空间并非是不确定和不清楚的介质,它可以根据源于社会的标准进行划分。”按照当时社会标准进行划分,延寿寺是一个具有宗教功能性质的场所。民众将“白塔”视为延寿寺的象征物,白塔便具有了宗教的空间品质,具有不同于日常的神圣性。这种空间品质将它与周围区域分割开来,在物理空间中同时也在民众的意识中形成了一个清晰的边界。
白塔坐落于城市西部,因其地理方位得名西塔。随着人口迁移、土地开垦,空间也得以不断拓展,但民众仍然沿用惯例,将“藏式塔”视为这个空间的象征物,换言之,民众仍然用西塔的名称概括这片区域。即便在白塔历经战乱残破不堪,以致文化大革命时期其物理建筑被拆除的时期里,西塔的名称仍然用来指称这一空间。对庙宇神灵的禁忌以及神圣空间不宜居住的民间信仰,让拆除后的白塔所在位置一直荒芜,在此之上并没有矗立其他任何形式的建筑替代物。在此意义上,白塔并没有随着物理空间的消失而消失,它依然存在于民众的集体记忆和精神空间中。这种精神空间的实践力量,是20世纪90年代末延寿寺得以重建的一个重要原因。2007年重建后的延寿寺被列入“沈阳市不可移动文物”,提醒人们注意西塔宗教空间品质的历史连续性。
二、难民开垦土地——村落化的空间
中法战争爆发以后,生存成为西塔民众面临的首要问题。西塔空间的宗教品质逐渐弱化,提供食物满足生存需要的生活区品质逐渐强化。据地方志记载,1883年汉族人刘玉朋逃荒至西塔,建造房屋,开垦土地,种植粮食。后来,又有两名族人投奔而来。刘姓族人共同构成为西塔空间早期村落化的行动主体,他们所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更新了西塔原初的宗教性。于是,发生在西塔空间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不只是喇嘛与香客之间的关系,同时还有家族之间的血缘、地缘与业缘关系。
为避战乱,陆续有人口来西塔定居,与刘姓族人一同添加到西塔的行动主体中。他们共同进行农业生产,交流生产经验,西塔土地的使用率日益提高。在土地耕种的基础上,手工业和商业开始出现。农业生产方式的普遍确立,使得业缘和地缘关系得到强化,行动主体之间的交往空间也进一步扩大,西塔逐渐从延寿寺邻近区域拓展成为拥有几十户汉族家庭的村落,形成了村落化的空间。
当生活由临时的战乱转为稳定的日常以后,西塔村村民的耕地扩展至村落边界以外。村落边界内外民众之间进行生产经验与生活经验的交流,让行动者的生活空间与生产空间进一步扩大。村落化的西塔让民众与空间以及民众之间形成一种持续的亲密关系,凭借这种亲密关系民众得以了解自我以及自然。当空间以村落化的意义存在时,西塔不仅生产了地方性知识,它还提供给民众一种归属感。
三、朝鲜人聚居—民族化的空间
20世纪初,有朝鲜族居民不断加入到村落空间中,这一主体行动重新形塑了西塔的民族结构。这些居民的生产方式主要是打草绳子、做小买卖、以及种地等。朝鲜族居民所拥有的独特生活方式与文化特色,与周围的汉族居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而在清晰边界的基础上对汉族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从而增进了村落空间内部两个民族的社会互动。这一互动表现在朝鲜族居民通过利用自己独有民族文化生产商品,与汉族居民进行经济上的交流。与此同时,朝鲜族居民也通过双方互动来吸收汉族文化。随着村落空间内部的民族主体之间互动内容的不断丰富、互动频率的增多,以及互动程度的加深,西塔越发显现出对空间外部的吸引力。
在空间格局的形成过程中,文化起到了重要的组织作用。“文化是城市空间变迁的重要建构力量,当空间被赋予某种文化意义时,便会有特别的象征意义,这会吸引相同文化与兴趣的社会群体的聚居,形成某一特定的空间格局。”20世纪30年代,有朝鲜族人在西塔开办企业,创办朝鲜族学校以及朝鲜族市场,从而吸引了众多朝鲜族外来人口的流入,使得空间的民族结构悄然发生改变,其朝鲜族民族文化特征因民族结构的变化而进一步增强。据地方志记载,这一时期朝鲜族人口已有500户,共2000多人。当西塔被赋予民族认同的意义时,朝鲜族文化就在西塔空间的变迁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
改革开放以来,民众利用西塔地区的空间优势创办商业,主要是出售大米、冷面、布匹等日常生活用品。对于作为重工业发展基地,缺乏日常生活必需品的沈阳而言,西塔民众经营的商品具有很大的不可替代性,这一主体的经济行为就为西塔在沈阳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在抓住这一机遇的同时,西塔还充分发挥空间的外部性,积极开展包括朝鲜族特色的餐馆、娱乐中心、服装商城等第三产业。经济效益以及民族文化影响的日益增长,让西塔空间的地理范围不断扩展。在这个意义上,空间变迁的历史不仅是西塔不断向外扩展的历史,同时也是空间格局被重新组织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初,西塔的土地与农业生产的天然联系逐渐为工业文明所中断,农业用地转变为居民住宅用地以及工业用地。在历经街区规划之后的空间安排中,居民住宅与工业区以及商业区相分离,为西塔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值得关注的是,空间的经济繁荣始终没有脱离民族认同这一核心,朝鲜族的民族认同最终成为西塔品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林立于空间之中的朝鲜族商业建筑则是这一品质的具体表现。

四、地方政府对民族文化的定位——符号化的空间
西塔空间的民族品质,最初是通过朝鲜族人“走亲戚”的民间沟通形成的。这种民间沟通形式带来了一种具有民族文化交流色彩的“包裹”生意,这一经济行动突破了西塔地域边界的限制,为西塔商业空间的生产奠定了基础。此后,西塔空间所呈现出来的越来越浓厚的民族品质,吸引了更多的韩国商人来此投资。于是,韩式风格的餐饮、娱乐、商店与原有的朝鲜族商业建筑同时并置于同一空间中。空间的经济增长及其显现出的民族品质为西塔所在的和平区政府所关注,“全国独一无二的朝鲜族特色聚集区和‘哈韩’特色区域”成为西塔的规划目标,正式写入和平区发展规划,至此西塔经历了一系列的空间改造。
进入21世纪初,西塔已经成为东北三省最具朝鲜族风情的商业街,空间演变成为超越其自身的朝鲜族文化的符号。围绕西塔朝鲜族文化这一符号的打造,2002年和平区政府在西塔举办了首届“韩国周”,用以推动中韩经贸的往来。至此,西塔连续12年举办“韩国周”,它通过民族艺术、民俗饮食等诸多展演形式,来表达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如今韩国周已然成为西塔空间符号化的重要实践载体。符号化的西塔不仅凝聚了具有同一民族文化传统的人,也吸引了对此文化传统感兴趣的人来此空间聚集,“通过将长期存在的非正式合作与交流制度化,他们将地区内共享信息的过程确定下来。这不仅仅是一个个公司通过加入生产网络重新界定自身的业务范围,而且地区本身作为一个整体也被组织起来,创造出新的市场与经济部门”。西塔这个地理上的空间作为一个整体重新组织起来,从而获得了一种新的符号意义,这一符号意义成为西塔空间发展规划的核心内容。

2010年“西塔民族特色街”进入西塔街道2011年工作安排日程。2011年和平区政府甚至将西塔与北市并列,统称为“北市西塔民俗文化产业发展空间”,将该产业发展空间的位置提升至年度五大特色发展空间之首,将其定位为“特色王牌”。在“十一五”规划中“,民族民俗产业聚居区”成为西塔空间改造的目标。2012年“朝鲜族文化特色第一街”空间升级改造项目启动,西塔已经成为展示和平区乃至沈阳发展的风向标,人们将其称为“中国小首尔”。“西塔民俗特色街”“西塔民俗文化产业发展空间”“民族民俗产业聚居区”以及“朝鲜族文化特色第一街”的空间定位,突出了该区域朝鲜族民族民俗文化特色,西塔空间的符号化意义日益凸显。目前,“智慧西塔街”的工程正在建设过程中,西塔门户网站、区域与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的建立,为西塔开启了一个网络化空间。
在一个城市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国家及其国家的在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换言之,在西塔空间内涵的符号化凝练中,地方政府是一个主导的推动力量。将朝鲜族民族民俗特征从区域的整体特征中分离出来,经过重新组织、合并,一跃成为西塔空间的最主要的特征。空间的所指意义,就是西塔空间的符号化,它为西塔乃至更大区域进一步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文化的内涵。随着历史的推进,西塔空间的意义仍在不断地生产过程中。
五、结语
借鉴空间社会学的视角,我们可以发现,西塔的变迁为行动者的行动所形塑,是行动者不断将意义赋予空间的过程。从宗教性的空间延寿寺,到村落化的空间西塔村,民族化空间朝鲜人聚居区,再到符号化空间“朝鲜族文化特色一条街”,西塔空间的意义一直在改变。尽管西塔在时间上具有一种连续性,但在空间上却是新意义的赋予和制造的过程。从这个角度上说,每一次新意义的赋予和制造都是一个新空间的生产。正是这些行动者———民族共同体、地方民众、国家以及国家的在场———共同塑造了今日的西塔。其中,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扮演了关键角色,而国家以及国家的在场(包括地方政府在内)对于民族符号的选择、运用与放大则起到了推动和主导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西塔是行动者的空间。


本文原载于《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图片来源于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