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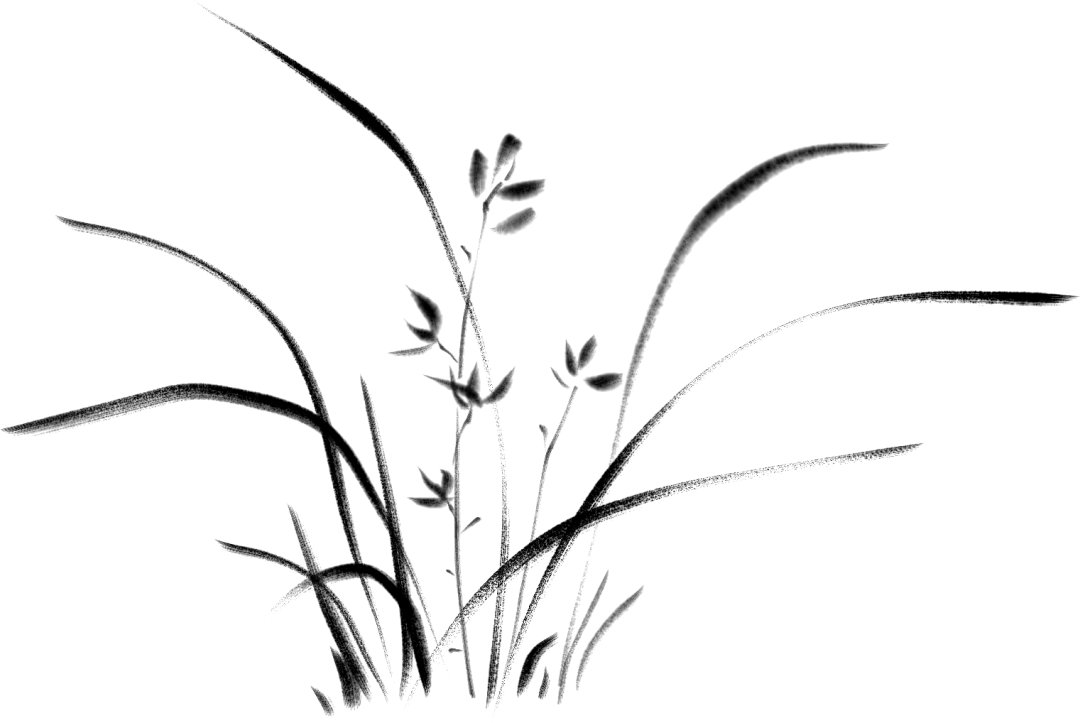
19世纪中期开始兴起的民俗学,发展到现在已有一百七十余年的历史,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即民俗学者和民俗,正如印度学者萨迪哈纳•奈沙尼(Sadhana Naithani)在民俗学伦理问题中所言,一直是中轴与核心。研究者对于民俗从最初像对待文物一样发掘、保存、展示逐步发展到注重对它的认知、体认:前者貌似“客观”,但实际上将民俗置于文明的另一端——“他者”,民俗成为文明进化层级中的前一阶序;后者增加了研究者的理解与阐释,关注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沟通,注重情感、互相理解,成为有温度的“展示”。民俗研究者与文化承载者——俗民之间也经历了“眼光向下”——“高高在上”的精英与“文盲”到彼此都是“普通人”的历程;“写文化”与“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开始注重研究者的立场、政治文化权力、对待文化(民俗)的方式等,却很少将研究者、文化承载者对文化(民俗)之不同阐释作为研究的整体去看待,民俗学领域此问题尤为凸显。
中国民俗学这一发展历程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国家话语、文化政策紧密相连。19、20世纪之交,通过“民间”思潮的兴起、北京大学征集歌谣运动、“到民间去”等,革命者、知识分子关注“民间”,努力发掘新的文化资源,其指向则是“新的文学”、新的社会体系的构建。从20世纪40年代起,在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的导向下,文艺工作者开始关注“民间艺人”,如盲艺人、链子嘴等,意识到他们对于民间文艺发展的重要价值,其旨归则是文学对革命的推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间文艺的文学性、思想性被进一步发掘、弘扬,民间艺人在文学批评视域亦受到极大关注,在民间文艺搜集、采录中,已有专门的艺人小传、谱系等出现,如《玛纳斯》《格萨尔》等史诗艺人及故事家、各民族歌手的采录等。但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民间文化的特殊承载者——传承人再度引起关注,尤其是在“中芬民间文学搜集保管学术研讨会”上,马名超、富育光、贾木措等学者都关注到了传承人,特别是马名超梳理了萨满传承人及其谱系,合作双方发起人贾芝、劳里•航柯(Lauri Olavi Honko)分别提到了资料的搜集、保管等,尤其是航柯当时已经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他对于民间文学的阐释超越了当时中国国内的历史文化语境,他将其视为人类不同民族、族群之“文化根基”,强调脱离了原本产生的文化背景,民俗就变成“解说人”的意思,而不是“创造者”之原义。“从民间文学衍生出的作品”容易保护,活态传承的民间文艺则可以通过保护“民间文艺说唱者个人”的尝试。解说人与创造者即指民俗学者、文化承载者(传承人则是文化承载者中的特殊群体)——俗民。那研究对象到底是“创造者”之意,还是“解说人”之意呢?当民间文学、民俗被现代科技社会所开发、利用后,民俗的“保管和保护”如何更有利于民俗学、有利于“它的创作人和合法使用者”?通过“博览会、文化节、电影、专题讨论会”等传播、展示后,“创造者”“解说人”对民俗的理解与阐释相辅相成,同时也形成了张力。但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的民间文学(民俗学)界尚未涉及或意识到这一问题。借鉴人类学、社会学等“主位”“客位”表述,以及“内视之谓明”,我们姑且将研究者对民俗的阐释称为“他观”,文化承载者对民俗的阐释称为“自视”。21世纪初中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传承人与非遗项目一样受到关注,也一样纳入了政府“命名”体系。研究者与传承人,两者对于民俗的阐释在民俗学问题谱系中逐步显现,“他观”与“自视”之差异、张力愈益凸显。

民俗学者将民俗视为研究对象,他们关注民俗的机理、同一区域或群体如何理解生活,期冀阐释他们生活的意义。在意义阐释与文化表述中,他们注重单线叙述、突出符号性文化事象,且往往将其对于文化的阐释“凝固化”。但文化承载者则是生活于丰富多样的日常之中,他们在生活中理解日常。两者的差异包含了立场、文化场域、情感等客观、主观因素,同时也彰显了民俗阐释的不同视域之张力,不同知识体系的碰撞。在非遗保护、传承人认定等新的语境中,传承人再释义、非遗传承人进校园等,使得研究者与传承人不再仅仅是研究与被研究的单向关系,他们对文化阐释的区隔亦愈发复杂。当下研究者的著述不再远离文化承载者,同时研究者也有主动将研究著述返回研究地者,如《来自田野的回音——〈背过身去的大娘娘〉读后感》,罗兴振阐述了对陈泳超基于自己文化“接姑姑迎娘娘”调查研究的成果《背过身去的大娘娘:地方民间传说生息的动力学研究》的看法,他的论述让我们看到民俗学研究长期忽视或被遮蔽的另一视域,他们的文化阐释可以说与研究者互构共存。他们在“对走”与“互看”中,增进了彼此认知,但如何将“所看”(他观)与“所知”(内视)置于文化交流的同一层面;将“看”的抽绎、逻辑与“知”的情感、丰富交融?在我担任“艺术遗产:一曲生命礼赞”讲座的与谈人后,这些问题更是萦绕于脑海,驱之不散。
2019年12月5日,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满古梅在四川美术学院进行了题为“艺术遗产:一曲生命礼赞”的讲座,在讲座中,她以鄂伦春民歌《高高的兴安岭》作为开端,自我独白式地讲述了只有8000多人口的鄂伦春族的节日、人群划分、生计方式的变革以及狍子皮、桦树皮工艺品的制作等。当访谈者与被访谈者的预设框架被去除后,她的文化表述外在呈现琐碎,但恰是她生活的日常。她从外来人最多的时节,吃柳蒿芽谈起。柳蒿芽与东北三少民族之达斡尔族紧密相连,即昆米勒节,但对于她们来说,共享着相同的自然物,并无严格的民族节日、食物边界,因此她的节日叙述不是从研究者表述的鄂伦春惯常的古伦木沓节开始。在她的讲述中,她将鄂伦春日常的时间概念引入,从正月初一讲起,到正月十五、十六的摸黑节,在节日期间讲述了鄂伦春人的饮食、聚会秩序等。接着她讲述了鄂伦春人以流域来划分群体的空间秩序,即鄂伦春人分为阿里河流域、多布库河流域、沱河流域、呼玛河流域等不同地域,与普遍性的行政区划不同。在她的讲述中,这种空间秩序具有强烈的地方感,她的“我是阿里河流域的,某某与我不同,他是多布库河流域的”自然流出。在她的表述中用得最多的就是“我们鄂伦春人是很讲究的”。她对于狍子皮帽子、鄂伦春服装、撮罗子、桦树皮工艺品的讲述不是工艺的制作程序、传承人的选择、传承谱系、传承人的学习等,而是从鄂伦春人早期的打猎生活讲起,讲述了鄂伦春人过去以猎狍子为主,并讲了猎狍子的规则,母狍子、狍子交配期、小狍子不猎,以及狍子肉在部落中如何分食,桦树皮作为鄂伦春人日常居住、生活工具的历史。说起撮罗子的时候,她讲述了鄂伦春传统的居住秩序,在撮罗子中老人等长辈的床放在哪里,谁可以待在这个床上,谁则不能到这个床上,年轻姑娘的撮罗子在哪里等。但是随着野生狍子减少、桦树皮也不能随意采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依靠养殖与符合国家要求的方式获取桦树皮等材料,而制成品则不再仅仅是他们日常生活用品,此种行为亦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精神,即本真性不应成为非遗保护的障碍。她对于鄂伦春生计方式变迁的表述以及兽皮工艺、桦树皮制作的讲述,尽管没有历史时间、事件的背景,但这恰是“自视”的一种历史时间秩序,从鄂伦春狩猎社会讲到他们定居生活,从穆昆达讲述到各个家族,内部的社会秩序既有延续也有断裂,但这些讲述都孕育于她的日常生活,在讲述中流露、呈现着她的“人生体验和当时的生存状况”,在娓娓道来中表述了自我“生活的意义”。她用“传承人”“自治区级”表明自己身份,这就将自己也纳入了他者表述的序列与秩序,在具体讲述中,她又提到自己的家族,自己的太爷、爷爷、父亲、叔父,她的祖上曾做过穆昆达,叔父也曾担任鄂伦春自治旗副旗长。

满古梅从民族文化典型符号“民歌”开始,身份表述则自然转换为与学术对接的话语体系,同时也从鄂伦春政治历史变迁中讲述了自己家族的民族身份、政治身份等。她在现代知识教育体系的公共空间讲述遥远的“故乡”“文化”,通过电子媒介发布分享自己在大学校园的“知识讲述”。这一切都自然地在她身上交融、共存。在她的讲述中,我们看到了鄂伦春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复杂性,同时也看到了生活在共同地域空间的鄂伦春、达斡尔、蒙古、满、汉等民族的文化交融,他们的生活日常复杂多样,同时又是中华民族文化网络上的一员,共享着当下的话语、文化空间,其自我表述呈现出多民族、多地域、多重身份之特性,也集他者视域的文化符号“民歌”“民族服装”与内视的文化表述于一体。
满古梅在国家话语体系中的身份是“内蒙古自治区兽皮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鄂伦春族民间手工艺师”,这是另一文化价值体系的外在赋予。相较于从前,现代科技、传统手工社会,学校教育体系、民间文化传统之间的交流、认知增进了很多。但两者之间的文化认知共同纳入学术研究,而且注重他们之间互通有无、整合交融,或许意义深远。就像对于兽皮工艺品,研究者挖掘鄂伦春族工艺品的“美”之所在,亦突出“手”工技艺审美独特,但对于狍子皮、桦树皮工艺品所在的文化网络,它在多民族文化交融、鄂伦春社会秩序中的普遍性、独特性及其在鄂伦春生计方式变迁、现代融媒体语境中所展示的流动性、多样性的“表述”在他观叙事中更注重呈现其“线性”“理性之逻辑”。除将两者审美分野整合于一域外,能将他观与内视的文化表述交融整合,方是对满古梅的兽皮工艺品全面的认知。其他文化事象研究大抵亦如此。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民间文化论坛》2021年第1期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