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框架下最重要的年度事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2届会议”于2017年12月4日到9日在韩国济州岛成功召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于2003年通过,2006年正式生效。因此,该公约又称“2003年公约”,以区别于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年公约”)。《公约》的宗旨在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尊重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所传承的遗产项目,在地方、国家和国际的层面提高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性的认识,推动国际合作和国际援助的开展。《公约》所规定的最高权力机关为缔约国大会(General Assembly),每两年举行一次常会(ordinary session)。同时,在教科文组织内设立政府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根据地区分配和轮换原则,由缔约国大会选举委员国,并以两年为周期更换半数委员国,且在任委员国不能连任两届。根据《公约》,政府间委员会拥有七项职能,其中第(七)项规定:“根据委员会制定的、大会批准的客观遴选标准,审议缔约国提出的申请并就以下事项作出决定:1. 列入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述及的名录和提名;2. 按照第二十二条的规定提供国际援助”。这也是法定意义上,各届政府间委员会主要讨论的议事内容。
2017年召开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2届会议,主要审议了法定周期内提交的49项由缔约国提交的列入申请。其中,包括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下简称《代表作名录》)的申请35项,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下简称《急需保护名录》)的申请6项,列入《优秀实践名册》的申请4项,《国际援助》的申请3项,还有1项从《急需保护名录》转入《代表作名录》的申请。经过6天紧张的讨论,上述项目中,最终共有6个项目列入《急需保护名录》,34个项目列入《代表作名录》,2个项目列入“优秀实践名册”。列入《代表作名录》的34个项目中,有1个项目显得非常特别,即由越南提交的自《急需保护目录》转入《代表作名录》的“富寿省唱春”项目(Xoan Singing of Phú Thọ Province, Viet Nam)。该项目的成功列入,是2003年《公约》发展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这意味着《公约》相关条款对于名录之间“转入”的相关规定,从文字成为了现实。此外,仅从表面上看,某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从《急需保护名录》转入《代表作名录》的成功实现,也在客观上说明了2003年《公约》在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所取得的成就,显示了《公约》框架下各项基本制度和保护举措的实际效果。再者,作为突破特殊情况下“两年一报”的硬性门槛,名录转入也为各个缔约国扩展其在文化领域的国际影响提供了新思路。也即,除了正常的两年一项的申请之外,各缔约国还可以寻求现有列入项目向其他名录转入,以此提高其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影响力并达到构建话语权的目的。有鉴于此,利用中国民俗学会担任“审查机构”成员(2015-2017)的独特身份,笔者将解析2003年《公约》及其《操作指南》关于名录转入的相关规定,回顾越南项目从提出申请到成功转入《代表作名录》的基本过程,总结教科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最新的发展趋势,以期为我国学界乃至政府相关机构提供若干线索和新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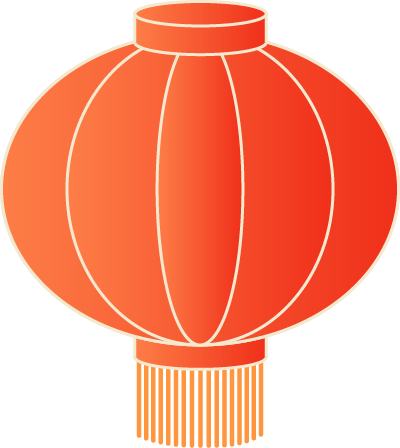
一、越南“富寿省唱春”项目简介
因研究主题及材料的限制,本文主要从越南向教科文提交的两个文本,即列入《急需保护名录》以及《代表作名录》的申报书出发,向读者介绍“富寿省唱春”项目的基本情况。从字面意思来看,“Hat”在越南语中意为“歌唱”,而“Xoan”为“Xuan”(春天,spring)的谐音。因此,结合越南申报文本中“Xoan Singing”的英文译法,“Hát Xoan”可以对应汉语中的“唱春”一词,。沿袭公约秘书处建议在项目名称中不使用具有排他性字眼的命名惯例,越南的项目列入《急需保护名录》和《代表作名录》时,均采用了“Xoan Singing of Phú Thọ province, Viet Nam”的说法,即“越南富寿省的唱春”的表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命名上不采用具有包含、统属关系的词语,这与2003年《公约》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其既符合非遗的基本特性,即大多数项目不为某个民族或国家独享,多为若干群体、社区共享的特点,也体现了联合国教科文在实践中所倡导的文化上的多元主义、政治上的多边主义,以及全人类共同对话、发展、进步的基本思路。
遵循《公约》规定的五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别的基本思路,该项目被越南界定为表演艺术,包含吟唱、舞蹈、击鼓、击板等文化表现形式。“富寿唱春”与越南古老的“雄王崇拜”(Worship of the Hùng Kings)密切相关,是一种根植于祖先崇拜的宗教行为。每年春季即农历的一月、二月,当地民众会在相关村落社区、庙宇、神祠中举行仪式,以此祭拜越南的国家英雄——雄王。一场完整的唱春演述仪式包括三个阶段:赞颂雄王及村落保护诸神功绩的礼歌(Hát thờ),14首赞美自然、人类和日常生活以祈祷平安好运的祝祷长歌(Quả cách),以男女爱情为主题的节日吟唱即会歌(hát Hội)。上述吟唱活动一般在农历春节的第一天于各地的雄王庙、圣地、社区公共空间等地点举行。此后,在农历春节的初2至初5日,传承唱春仪式的各个歌团沿袭祖制,将赴其他村落参加祭祀雄王的庆祝交流活动。在道德的层面,唱春仪式的意义在于向社区的年轻成员灌输“饮水思源”的传统观念;在仪式的层面,通过祭拜雄王的吟唱和舞蹈活动,当地民众祈求平安幸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家国兴旺;在社区的层面,唱春活动的仪式化实践,不仅是一种重要的社区成员之间的文化交流行为,更是维持社区团结、增进身份认同的重要社会文化活动。总之,唱春仪式在当地人的文化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功能,使得相关社区更加和谐、有序,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更加和睦,社区的凝聚力和文化的认同感也因此而得到强化。

根据2017年审议的该项目列入《代表作名录》申报书,越南富寿省的唱春传统主要分布于越南首都河内附近的富寿省和永福省(Vĩnh Phúc)。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该项目实践者的组织形式以歌团(Phường)为主,每个歌团则大约以30-100名成员为基本规模。据统计,来自富寿省越池市(Việt Trì)的四个歌团中,一共有249名经过系统培训的传承者。此外,该项目的传承者还包括热爱唱春艺术的一般性民众团体,其中富寿省有30多个民间俱乐部共1287名注册会员,永福省有3个民间俱乐部共1376名注册会员。富寿省的四个春歌团,可视作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群体。在歌团内部,男性一般被称为歌郎(kép),女性则对应为歌娘(đào)。歌团成员多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妇女和年轻人,同时也包括了工人、教师、学生、退休职工等职业和社会群体。歌团的会首被称为歌头(trùm)。歌头在传统上以男性居多,女歌头在晚近的发展中更为多见。富寿省4个春歌团的歌头中,有两位歌头为女性,分别是现年68岁的阮氏历(Nguyễn Thị Lịch)和55岁的裴氏娇娥(Bùi Thị Kiều Nga)。另外两位男歌头,黎春五(Lê Xuân Ngũ)现年87岁,阮文决(Nguyễn Văn Quyết)现年32岁,他们也是四位歌头中最年长和最年轻者。歌头的基本职责为组织歌团活动、搜存曲目、收授学徒、传承技艺等。作为唱春演述传统的实际承载者,富寿春歌团的4个歌头,加上越南认定的62名技艺精湛的歌郎(娘),在该项目的传承、教学和实践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66名年龄跨度从30-60岁之间、以女性为主的代表性传承人,广泛活跃于歌团、俱乐部、学校等活态传承活动的第一线。
根据2015年越南的国家名录,唱春项目的传统曲库共有31首传统曲目。这些曲目是当地社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并经由社区成员的口耳传递、祖祖辈辈传承而来,且其中的每一个曲目都具有独特的吟唱和舞蹈形式。该项目的实践者,需要掌握一定的传统艺术技巧,包括吟唱、舞蹈、击鼓、击板等,才能从事唱春艺术的相关演述活动。目前,该遗产项目的传承方式体现出多元化的倾向,既有老艺人以口耳为途径的言传身教,又有传统曲目和演述的书面誊写本和音视频资料的辅助下,口头与书面交互的创新性传承方式。在鲜活的社会场景和文化活动,即主要与雄王信仰有关的祭拜吟唱活动中,与该遗产项目有关的习俗、惯例、禁忌等传统知识,通过情景化的演述和实践,以书面和口头并行的方式在社区成员中实现了代际传承。在富寿省越池市,当地的学校、俱乐部会邀请技艺精湛、经验丰富的传承人来培训他们的音乐教师,之后这些老师再把他们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和俱乐部成员。上述措施为该项目的实践频率提供了稳定的社会基础,从而也就确保了该项目作为文化遗产的基本活力。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唱春项目所包含的歌词、舞蹈、动作等文化内容表达了人类向往爱情,追求美好生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价值典范。以春歌团为代表的传承人群体,在保护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升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功能和作用,也为当地社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该项目在2011年被列入《急需保护名录》,2017年成功转入《代表作名录》,客观上也说明了越南在相关文化遗产的保护上做出的显著成绩,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探寻出一条可资借鉴的示范性道路。最为重要的是,围绕该项目而展开的一系列文化实践,在国际社会中提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整体上的可见度。特别是,该项目一度濒危、处于急需保护的存续状态,通过相关保护举措的实施和举国上下的努力,其传承状况得到了本质性的改善,存续力有了较大提升。其中,该项目在年轻实践者的人数、传统活动的实践频率、保护措施的有效性等可量化指标上的显著提升,有力地证明了2003年《公约》在推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所发挥的纲领性促进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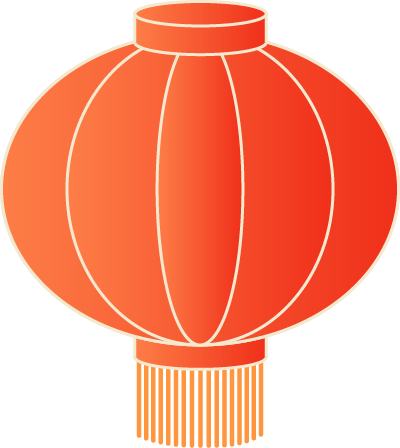
二、名录转入的文本依据
根据《公约》第一章“总则”“第一条:本公约的宗旨”的规定,“在地方、国家和国际一级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互欣赏的重要性的意识”。现有教科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lists)体系,即《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优秀实践名册》,都是在此宗旨指导下,以《公约》第四章“在国际一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第十六至十八条的具体规定为凭而建立的。因此,当我们提及教科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体系时,指的当为上述两个名录、一个名册的清单系统,属于在国际的层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和表述话语。其中,《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都是《公约》文本中有明文规定的。而《优秀实践名册》这一说法,虽然没有精确对应的文字指称,但也可以确定是“第十八条: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计划、项目和活动”的同义语。也因此,我们常常在众多国际场合中听到一种说法,甚至现任公约秘书蒂姆·柯蒂斯(Tim Curtis)本人也在一些正式、非正式的场合多次表示,即《优秀实践名册》并不在《公约》本身规定的范围内。我们需要明确,此类说法并不是指内容意义上的包含关系,仅指在名称上,《优秀实践名册》的具体字眼,并没有像其他两类名录那样“一字不差”地出现在《公约》文本中。此外,教科文还有“国际援助”的申请,属于第五章“国际合作与援助”规定的相关内容,体现了公约宗旨第(四)点“开展国际合作及提供国际援助”的具体要求。其在入选的要求和形式与上述三项差异较大,并不存在转入或除名的问题,而且其本身也不在我们一般所说的《公约》名录系统范围内。
还需要明确的是,2003年《公约》并未对名录转入的问题做出具体规定,只在第四章“在国际一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条款中提及基本的指导思想。其中,“第十六条: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规定:“为了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 提高对其重要意义的认识和从尊重文化多样性的角度促进对话, 委员会应该根据有关缔约国的提名编辑、更新和公布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及,“第十七条: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规定:“为了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委员会编辑、更新和公布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根据有关缔约国的要求将此类遗产列入该名录。”上述文字,涉及两个名录的更新问题,可视作相关遗产项目在名录之间转入、除名的文本依据。因此,从国际法的意义上讲,遗产项目从《代表作名录》中除名,转入《急需保护名录》,或反之从《急需保护名录》中除名,转入《代表作名录》,这两种操作均是有法律依据的。
参考2005年通过的《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第I.11部分“遗产从一个名录转入另一名录或从一个名录中除名”,第38段:“一个遗产项目不可同时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缔约国可申请将一个遗产项目从一个名录转入另一名录。此类申请必须证明该遗产项目符合申请转入名录的所有标准,同时,申请须按既定程序和申报期限提交”;第39段:“如委员会对保护计划执行情况进行评估之后,确认某一遗产项目不再符合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一项或多项列入标准,则应将该遗产项目从名录中除名”;第40段:“如委员会认为某一遗产项目不再符合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一项或多项列入标准,则应将该遗产项目从名录中除名。”从字面意义上理解,某遗产项目转入另一名录必定意味着从原有名录中除名。反之,从某一名录中除名,则不一定以转入另一名录为必要条件。这里的差别在于,言及名录的转入问题,在将其从现有名录中除名之外,还需要考虑其是否符合列入目标名录的所有标准,以此作为名录转入的依据。单纯的除名问题,则不必考虑此条规定。
我们再深入察看《操作指南》第39段的内容,如何理解这里所说的转入只要符合目标名录的所有标准,同时符合既定程序和申报期限就能实现的规定?以《公约》和《操作指南》的规定为基础,一旦缔约国申请将某个已列入项目转入另外一个目标名录,就必然在逻辑上衍生出两个相互关联且有先后顺序的过程:先除名、后转入(列入)。那么问题就来了,《操作指南》第39段只提及转入只要符合其申请列入的另一名录的所有标准,按照既定程序和时间规定就行。也就是说,从逻辑上说转入需要先除名,因为一个项目不能同时列入两个项目。但是,第39段压根就没有提及除名的说法,为什么?参考列入《代表作名录》和《急需保护名录》的所有列入标准,我们才能理解上述规定的内在合理性。
举个例子,如果明确规定了转入必须先除名,那么我们若要将某个项目从《代表作名录》转入《急需保护名录》,就需要先论证其不符合《代表作名录》的一项或多项标准。比较两个名录的列入标准,除了R. 2(对确保可见度、提高认识和促进对话的贡献)和U. 2(急需保护的必要性)这两条,其他标准的指向大致相似。因此,若要从《代表作名录》中除名,尝试否定以下标准中的任意一条:R.1(是否属于公约规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R.3(保护措施)、R.4(社区参与和同意)、R.5(已列入清单)的认定结果,其实也就等于直接推翻了将来评估U.1(是否属于公约规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U.3(保护措施)、U.4(社区参与和同意)、U.5(该项目已列入清单)的可能性。这就是说,如果要除名,其实并不能够从操作层面直接推翻R.1、R.3、R.4、R.5的评审结果。这样就只剩下R.2一条。但是,如果论证其不能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见度,不能提高人们的相关认识或促进文化之间的对话,那么该项目从最基本是属性上也并不适合列入《急需保护名录》。简言之,对于从《代表作名录》转入《急需保护名录》,在实际操作上就不能先除名。
我们再来看另一种可能性,如果某个项目申请从《急需保护名录》转入《代表作名录》,那么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不能否定U.1、U.3、U.4、U.5中的任何一条,因为这会推翻之后评估符合R.1、R.3、R.4、R.5这四条标准的可能性。唯一可能性在于否定U.2,即证明其没有“急需保护”的必要性。从上述分析来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综合上述两种可能性,如果明确规定了转入必须先除名,那么其只适用于从《急需保护名录》转入《代表作名录》的申请,并不适用于从《代表作名录》转入《急需保护名录》的申请。这就是《操作指南》第39段不提及除名,只提及符合目标名录所有标准的可操作性逻辑。也因此,《操作指南》中对于名录转入的规定,就只提及了必须符合目标名录所有标准的说法,并未列出在逻辑上除名先于转入(列入)的硬性规定。此外,先除名再列入的可能性,如上文分析只可能出现于从《急需保护名录》转入《代表作名录》的申请中。在下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越南的个案也是在《公约》并没有明文规定的前提下,利用字里行间的隐性话语实现了突破。
最后,虽说《代表作名录》和《急需保护名录》之间的转入是双向的,但这似乎也只是一种存在于理论上的可能性而已。因为,在实际的情形中,缔约国不大可能考虑将一个遗产项目从《代表作名录》移入《急需保护名录》。这无异于自曝其短,既反映出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力,以致相关项目陷入濒危的境地,同时也会严重影响该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因此,在梳理了上述理论上和实际中的各种可能性之后,我们现在可以把考察的目光锁定在从《急需保护名录》转入《代表作名录》这一可操作化的路径。参考教科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0次会议到第12次会议的实际情况,名录转入问题的基本走向还是比较符合上述文本意义上的具体分析。但问题在于,《公约》和《操作指南》只是在内容上对于名录转入和移除的问题进行了大体规定,并未附有具体的操作程序供缔约国展开实际操作。因此,这种法理上的程序缺环还是在实际中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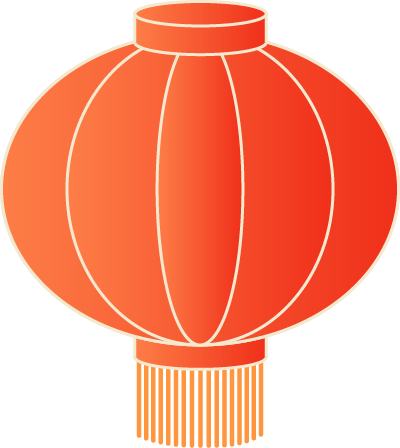
三、“富寿唱春”转入《代表作名录》的大致过程
追溯该项目从《急需保护名录》转入《代表作名录》的基本过程,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于2003年《公约》及其《操作指南》相关规定的基本认知。笔者借助中国民俗学会担任“审查机构”成员的契机,利用“辩论代表”的身份参与了自2015-2017之间的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评审工作。其中,与该项目的转入申请直接相关的重要事件,还可追溯至于2015年11月30日至12月4日在纳米比亚(Namibia)首都温得和克(Windhoek)召开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0届会议。根据《操作指南》第33、34段的规定,以及54-56段所列举的时间限定,除特殊情况外,缔约国一般每两年可递交一项列入名录的申请,且需要在第一年提交申请材料,第二年方能接受审查。从大的范围来看,越南的“富寿唱春”正是严格按照上述规定加以申请的:2015年向秘书处发出申请,2016年提交申报材料,2017年接受审查并转入《代表作名录》。
在第10次政府间委员会召开前,越南于2015年10月9日致函秘书处,表达了希望将“富寿唱春”项目从《急需保护名录》转入《代表作名录》的诉求,并希望该申请在2017年的评审周期中得到审议。因此,该议题在第10次政府间委员召开之前便已进入议事日程。笔者在场亲历了该项目的讨论,在此尝试向读者恢复该议案通过的大致过程。由于越南并非是届政府间委员会的委员国,按照规定没有发言资格,因此该议程从提交到决议草案的拟定均由当时在任的委员国比利时提出。比利时代表首先发言,邀请越南代表团针对该项目的基本情况进行陈述。越南代表在发言中表示,为了挽救处于濒危状态的富寿唱春项目,越南政府及其国内遗产的利益各相关方长期以来做了巨大的努力,使得该项目在国内的可见度得到很大提升,已成为举国皆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因此,从《操作指南》的相关条款及其规定来看,该遗产已与《急需保护名录》的宗旨有所冲突。同时,该代表还表示,在缺乏明确文本依据的前提下,与该项目有关的讨论,其重点不在于名录转入的合法性问题,而是与会各缔约国是否能够就相关议事规则取得一致的问题。他认为越南的个案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为《公约》的进一步实施提供了极有意义的实验场。因此,他提议越南于2016年向委员会提交一份项目报告,以及该遗产进入代表作名录的申报材料,供审查机构及政府间委员会在2017年的周期中加以审议。
越南代表的发言具有非常明确的目的指向,与之前公约秘书站在秘书处立场上的发言前后呼应。公约秘书处柯蒂斯此前曾表示,如果缔约国想实现遗产项目在名录间的相互转入,必须要向委员会提交报告,对该项目的存续状况进行汇报,并由委员会集体审议、评估。如果该遗产项目经过一段时间的有效保护之后,其传承情况确实得到了改善,脱离了之前的濒危状况,可以考虑从《急需保护名录》转入《代表作名录》。越南的项目事实上可能已不再濒危,但是在议事程序上,其需要在下一次政府间委员会召开之前的18个月,向秘书处提交有关遗产现状的报告,以及申请列入《代表作名录》的申报书,而且最好与秘书处4年一次的履约报告同时提交。上述做法的好处在于,可有效地减轻秘书处的工作负担,不用专门就名录的转入问题召开集体会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越南的动议得到秘书处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因此,秘书处的具体建议,即提交报告和申报书,分别指向了《操作指南》第40段和38段的规定。但是,除此之外,若要成功推动此项动议,实际上还需要明确程序说明。也即,当时的《操作指南》只在内容上对名录转入进行了界定,并没有附带明细的程序规定。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无法可依的违规操作,其合法性只存在于与会各国,能够就秘书处在经验基础上的阐释所达成的一致。也因此,秘书处的建议,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该申请在程序上具有合法性的基础。这一点可能是以后我们在研究《公约》基础文本以及秘书处的权力范围时,可以进一步深挖的话题。
比利时代表随后发言,他依据《公约》“第十六条: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第十七条: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二十九条:缔约国的报告”,以及《操作指南》第一章:“1.1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列入标准”,“1.2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列入标准”,“1.11将遗产从名录中删除”,以及第五章:“5.2缔约国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报告”等规定,论述了越南项目实现名录转入的申请符合现有文书的相关规定,表示支持越南代表的提议,并提出了名为“Draft Decision 10.com 19”的决议草案。韩国代表随后附议,支持比利时提出的决议草案,但对其中第8条内容进行了修改,将比利时提出的“若委员会未能通过其列入《代表作名录》的申请,则该遗产项目继续保留于《急需保护名录》中”,改为“不管委员会是否通过其列入《代表作名录》的申请,则该遗产项目都应从《急需保护名录》中除名”的说法。上述草案得到了拉脱维亚、土耳其、吉尔吉斯等国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因此,在最后通过的名为“Decision 10.com 19”的决议中指出:“越南富寿省的唱春”项目从《急需保护名录》转入《代表作名录》,为公约生效后首次接收到的缔约国申请(第2条),应对其加以专门考虑,并为2018年缔约国大会修订《操作指南》提供相关经验(第6条);进一步决定,如果越南在2016年3月31日之前同时提交该项目列入《代表作名录》的申报书以及该项目基本现状的报告,则委员会应在2017年评审周期中对上述报告进行审查(第7条);进一步决定,该项目列入《代表作名录》的评审工作,仅能在评估该项目报告的之后,即从《急需保护名录》除名之后,方可开启(第8条)。至此,越南提出的项目转入申请,已从从理论变成现实,并进入了正式议事程序。
此后,越南按照规定时间提交了相关材料,供秘书处进行材料复核和技术审查。随后,秘书处再将相关文件转呈至委员会及审查机构成员处,以便展开具体的评审工作。在2017年4月至6月,审查机构成员针对越南提交的项目定期报告和列入《代表作名录》的申报书进行了评审。鉴于该申请属于《公约》正式生效后的首次实践,不论在程序还是内容上,审查机构成员都处于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虽然决议案中提及,需要先从《急需保护名录》中除名,方可开启列入《代表作名录》的评审工作。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审查机构成员其实是同时处理上述两项工作的,即评估除名的可能性和列入新名录的可能性其实是同时进行的,并且偏重列入《代表作名录》的评审。从实际情形来看,在2018年韩国济州岛召开的第12次政府间委员会上,委员会通过了审查机构在客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后才形成的建议草案,正式将该项目从《急需保护名录》中除名并转入了《代表作名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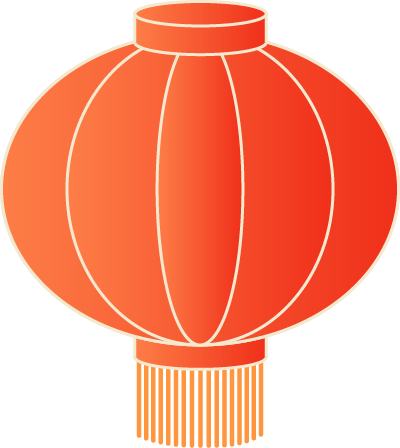
四、观察及总结
简要回顾上述过程,越南作为《公约》缔约国对于相关规定的深入理解让人印象深刻,这也是促成“富寿省唱春”项目成功实现名录转入的重要基础。从笔者参与过的《公约》框架下各种大大小小的会议来看,参会各方不论是缔约国代表,抑或非政府组织专家或学者,往往都会利用教科文提供的平台充分发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舞台中凸显自己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以至于类似的国际会议,在绝大多数场合中都会充满争议、对话和妥协,任何一个话题的讨论都可以巨细靡遗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单从这一点来看,越南实现名录转入的案例多少显得有点“另类”,因其从提出到讨论再到最后形成决议,平顺得有点异乎寻常。
需要明确的是,该过程表面上的平顺,当属一种比较意义上的经验概括,并不一定暗示着其操作过程中缺乏对话和讨论。故此,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一个重要启示,应当是越南在策略制定上的高明做法。我们说《公约》框架下的国际合作,应该是缔约国之间国际政治关系的一个缩影,这种说法相信大多数人都能同意。越南并非委员国,按说在政府间委员会的层面上没有太大的主动权,只能通过与其他国家协商,请在任的委员国为其出头。从各种迹象来看,比利时、韩国充当了代言人和协力者的角色。越南的主张在两国的有力支持下,得到了一些缔约国的积极响应。笔者认为更重要的一点,在于越南的主张并未引起其他国家的激烈反对,主要原因就在于其在一开始就已经将讨论的重点有意识地限定在议事程序的层面。因此,至少从政府间委员会这一环节来看,越南的动议并未引发其他国家针对其项目本身是否合乎符合列入《代表作名录》和移出《急需保护名录》之各项标准的公开质疑。另外,有意识地引导并限定讨论范围,还离不开秘书处的积极配合。当然,秘书处和比利时、韩国等也是各取所需:秘书处可以从名录转入中收获《公约》已取得重要进展的国际认可;比、韩两国则可以进一步凸显其对于非遗保护国际话语实际走向的导向作用。
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从越南的项目中收获对于《公约》及其体系的理解。至少在目前,虽然国际社会对于《公约》生效以来对于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的促进作用已达成共识,但也不会有意回避一个重要的前提:即2003年《公约》仍是一个“年轻”的公约体系。“年轻”意味着不成熟,或者至少仍不完善。这当然只是一种粗略的印象,但笔者在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中,常常听到一种说法,就是《公约》作为一种国际法依然偏“软”:既缺乏对于缔约国有效的约束力,又缺乏有力的监督机制评估遗产保护措施的实施及成效。在越南的个案中,我们能明显感受到《公约》自身的灵活性,而这也是其作为一项国际公约的独特之处。
再回到2015年纳米比亚政府间委员会上关于越南项目的决议即“Decision 10.com 19”一项。其中,第4条指出,“忆及《公约》第16、17和29条,以及《操作指南》第1章第1、2、7、8、11段和第5章的相关规定”;第5条指出,“考虑到需要修改《操作指南》,从而建立明确的程序,实现某一项目从一个名录中除名并转入另一个名录。”单就这两条而言,上述决议在内在的逻辑性上是有矛盾的。也就是说,项目在名录之间转入、除名,虽然在《公约》和《操作指南》中有所提及,却没有在程序上做出明确规定。因此,在法理上看,在2018年通过《操作指南》的修订之前,任何在程序上启动转入、除名已列入项目的做法,无论如何都是没有依据的。但是,该决议第6条指出,“越南项目值得被特殊对待,从中得到的经验,可为《操作指南》之修订草案提供反思”;随后第7、8条指出,如果越南按时提交材料,其项目可以在2017年的评审周期中得到审查,只是该项目在列入《代表作名录》之前,需要先行从《急需保护名录》中除名。言外之意,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是越南的动议值得尝试,从而可以为将来制定程序和时间表提供相关经验。这种程序上的灵活性,只能说明《公约》的相关规定没有绝对的约束力。前文提及的“摸着石头过河”似乎还不太确切,应该是“先找石头扔进河,再摸着石头过河”。
在笔者看来,越南的申请似乎有点“操之过急”,其大可在2018年缔约国大会召开并修订完《操作指南》之后,再启动相应的程序。因此,这种冒进的做法给2017年审查机构成员的评审工作造成了混乱。理由在于,审查机构成员评估其不适合列为《急需保护名录》的依据,主要为越南提交的项目定期报告,即该项目列入该名录后于第四年提交的关于项目现状的报告。而审查机构成员需要以该报告为凭,评估其与列入《急需保护名录》的五项标准之间的矛盾。这就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了,试想要用列入标准衡量其不适合列入的理由,逻辑上行得通,程序上却极不严谨(事实上的无法可依)。此外,列入《急需保护名录》有相应的申报书,而除名却没有相应的表格可资凭借。因此,虽然决议中提及要先除名,这只是做法上的先后顺序而已,因为除名的程序本身则没有文本规定可资参考,只能以秘书处的建议作为指导思想。事实上,上述做法只能算形式上的补漏,即符合某一项目不能同时存在于不同的名录之上的规定。同时,鉴于缔约国大会当时仍未修订《操作指南》,相关工作实际上属于一种“非法”的操作。这对于《公约》及其实践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需要在以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加以评估。
综上所述,回顾越南“富寿省唱春”的个案,有助于我们增进对于《公约》相关规定,以及与之有关的一系列文化实践的认识和理解。在笔者看来,至少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中,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从学理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发展进行反思,包括宏观的理论研究和微观的个案研究;另一种是从文化实践的角度,观察教科文的文化政策和话语实践对于各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作用和影响。这两种不同的思路,虽然看似有所侧重,实际上却并非毫无联系。甚至,在全球化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多元化特点以及研究本身的复杂性,已经对两种思路之间的对话乃至有机结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笔者看来,我国学者已在此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通过引入教科文的《公约》术语系统和实践范式,我国的民俗学者如朝戈金、巴莫曲布嫫、安德明、杨利慧、康丽等人近年来的学术实践,已经为这种学术潮流指明了方向。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朝戈金、巴莫曲布嫫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上的相关研究,安德明、杨利慧等人在社区参与问题上的专题讨论,康丽等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性别视角,朱刚等人对于文化空间的概念探讨,以及马千里等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编制的研究。这些学术实践实际上都与教科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新趋势密切相关,也可以说是紧扣《公约》精神实现学术研究创新的新做法。这一方面与上述学者深度参与教科文的相关活动和实践有关,部分显示出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领域逐渐成型的学术自觉。另一方面也与国内非遗保护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有关,既需要我们从个案比较的角度深入挖掘民俗事项的文化功能和意义,同时也需要我们把握国际遗产保护的政治、文化脉动,站在更高的层面来进行学理抽绎。唯此才能使我们的非物质无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真正成为推动民俗学及其他相关学科学术创新的动力。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第6期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