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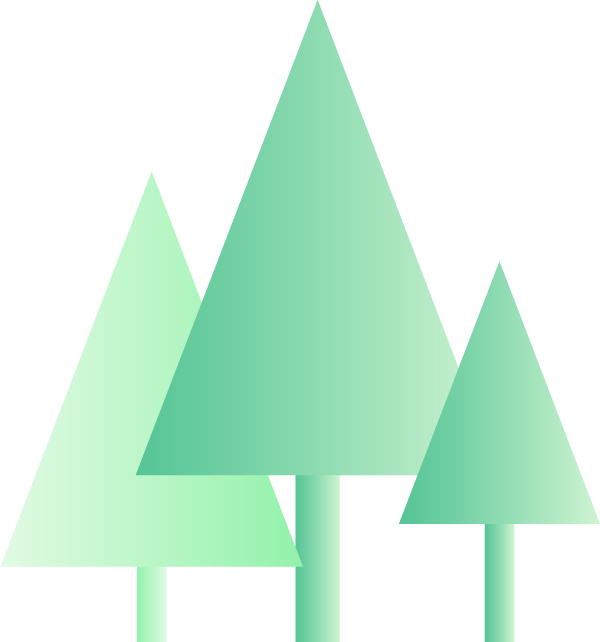
19世纪、20世纪之交,在西方“民”“民间”以及“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及国内社会政治变革的共同催发下,随着对现代启蒙及人之个性的重视,早期的启蒙主义者有意识地借助民间文艺“开风气,倡革命”,为通俗文艺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这种“从众向俗”的大众路向到了“五四”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新故事的通俗化实践在整体上表现为“民间性”与“革命性”的交融,在人民文艺创作与民间文学传统的融合中,新故事继承了延安时期讲述“革命故事”的叙事传统,构建了更为灵活、弹性的话语空间。
关键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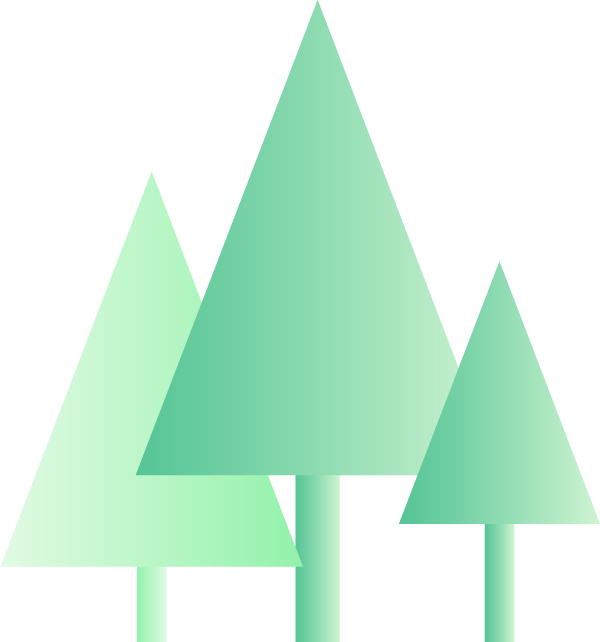
通俗文艺;人民文艺;新故事;《故事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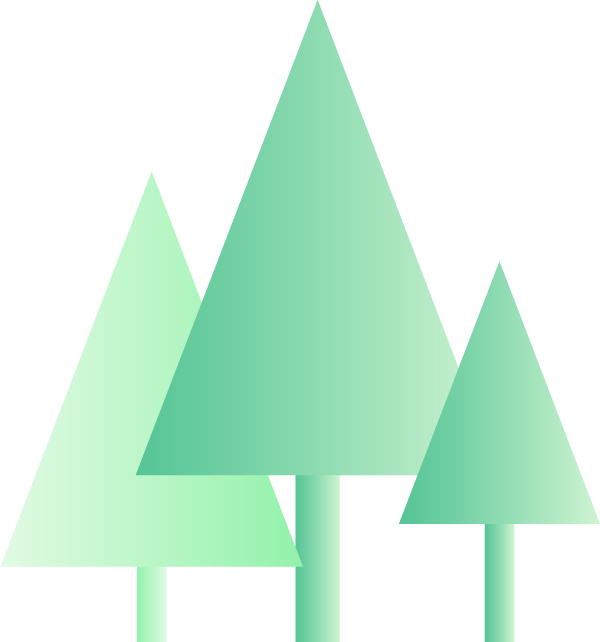
自晩明起,“文学品味的大众化”就以富有近代解放因素的民主思想作为鲜明旗帜,并且它逐渐成为一股具有近代市民资本主义特质和启蒙意义的新思潮。到了清朝后期,在西方“民”“民间”以及“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及国内社会政治变革的共同催发下,仁人志士关注“民”“民间”。其在政治思想上的表现就是平民意识;在文学上则表现为重视、推崇“白话文学”“平民文学”,提倡“言”“文”一致。1877年,黄遵宪所编纂的《日本国志•学术志二•卷三十三》中提及:“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言文一致”这一诉求即隐含其中。1903年,刘师培在《中国文字流弊论》中,提出了“宜用俗语”的主张,其“言语与文字合则识字者多,言语与文字离则识字者少”的论述基本沿袭了黄遵宪的观点。作为“文学革命滥觞时期”的代表,梁启超以“三界革命”为中心,提倡俗语文学,创造了一种“为文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款的新文体,作为“言”与“文”之间的过渡,“新文体”虽“言文参半”“半文半白”,但它“不避俗言俚语”,“古文白话化”的尝试创造了具有“现代传媒基础”的语言表达方式的雏形,代表了当时文学观念的新变,为通俗文艺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一、现代启蒙与通俗文艺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对现代启蒙及人之个性的重视,早期的启蒙主义者有意识地借助民间文艺“开风气,倡革命”。1899年12月正式出版的《中国日报》,在附刊《中国旬报》上即专门开辟一栏《鼓吹录》,刊载通俗的戏文、歌谣等,内容多为“或讽刺时政得失、或称颂爱国英雄”。革命派的学者和活动家们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亦对弹词、歌谣及地方剧等通俗文艺形式进行了广泛借鉴,如被视为“社会之药石”的小说《女蜗石》、章炳麟运用民间歌谣形式创作的《逐满歌》、秋瑾以“妇女解放”为主题创作的弹词《精卫石》等。1904年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刊载民歌民谣、地方戏曲和故事等大量民间文艺作品,其宗旨“专为开民智消隐患起见”,内容多以“伤国事、叹恶俗、兴民权”为主。
这种“从众向俗”的大众路向“五四”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以言为始”的文学发展理念,提出“八事”,将语言变革作为文学变革的突破口。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提出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将此前的“八事”总括作四条,提出“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等。胡适有关“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论述并不单纯指涉文学形式层面上的体裁格式或文学内容层面上的题材主题,而是隐含着将“民间”作为“一切新文学的来源”之理念。1918年刘半农、沈尹默发起了歌谣征集活动,对“有关一地方、一社会或一时代之人情风俗政教沿革者”的自觉认识亦激发了对民间文艺进行再发掘与再阐释的强烈需求。受俄国早期民粹派“到民间去”运动启发,李大钊在1919年发表的《青年与农村》中提到“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他指出,唯有如此,农村才可以“算是培养民主主义的沃土”,青年才“算是栽植民主主义的工人”。在李大钊的号召下,自我定位为“民众的导师,民众的领路人”的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纷纷走向农村。1919年1月,北京大学的学生组成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其宗旨为“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活动一直持续到1925年。“到民间去”也逐渐演变为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响亮口号。《努力周报》《批评》《新评论》等都刊载过题名为《到民间去》的文章,其中一篇1922年7月刊载的文章明确提出:
我们必须依靠我们的双手,运用讲演的风格和白话小说的形式去编辑通俗小册子……其次,我们必须依靠我们的口,使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去教育农民……

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文艺大众化与通俗文学的讨论中,“左联”成立了“大众化研究委员会”,号召作家们通过学习民歌、小调、鼓词、评书等群众喜爱的传统艺术形式来创作有革命内容的新作品。《文学月报》(上海)、《北斗》(上海1931)、《文艺新闻》等“左联”刊物围绕“大众化”“通俗文学“问题展开讨论或登载一些实验性的作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通俗文艺作品呈现出“新旧杂糅”的面貌:一方面延续了晚清至“五四”时“言文一致”的文学传统;另一方面,革命叙事在“左联”的“大众化”与“通俗文学”的实践中成为主流。如1938年林柷敔《文艺》(上海1938)上发表的故事《一条舌头》,题中特别标注“新故事体”,并在文末注明:
故事体也可用于通俗文学,茶后酒余讲讲很好。我就择了这么一段东西——略与事实不符,我认为无妨——来尝试。故事体,除文字通俗外,有三个条件:第一风景的描写不可多;第二对话也不可多,因为故事只在交代情节;第三多放插穿。有人如果感兴,也不妨试试。
据林柷敔妹妹在《记林税敌在“孤岛”期间的文学活动》一文中回忆,《文艺》是在地下党领导的“学委”和“文委“的支持下办起来的,其宗旨为服务抗战,推进文学大众化,内容上主要刊登文艺作品和讨论文艺问题的文章。在文中,她认为其兄创作的《一条舌头》为一篇别具一格、通俗易懂的通俗小说,适宜于向群众讲故事用。
此时通俗文艺进入了全面创作实践阶段,如《抗战文艺》1938年第11、12期合刊上登载了何荣的《义训报国》,《抗到底》1938年第9期刊载了老向的《李小姐计杀倭寇》,这两篇均被标注为“抗日通俗故事”,与其他文学体裁进行区分。与之类似的是,1939年胡考在周扬主编的《文艺战线》上发表的《陈二石头》,题中特别标注“讲演文学”,并对“讲演文学”做了解释:
《陈二石头》是为讲而写的一篇故事脚本。——或“讲的小说”。徐懋庸先生特地送了一个名词,称这类东西谓之“讲演文学”,我觉得很是适当。
他们所创作的这种介乎故事与小说之间的“新故事体”“讲演文学”及由“通俗小说”转变而来的“通俗故事”等,侧重于作品的“通俗性”与“革命性”。如1939—1940年期间,由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总会暨成都分会编辑兼发行的《通俗文艺》,它主要刊登各地抗战消息,宣传抗日救国的通俗小说、诗歌、民谣和抗日英雄人物介绍等。上面设有“前线故事”和“抗敌故事”栏目,刊载了老百姓杀敌、消灭汉奸的消息。“儿歌”栏目刊载的《麻子哥哥》《月亮光光》,小说连载磨刀人的《红枪会》以及“唱本”中《送子从军》等皆是为宣传抗日救国。
二、人民文艺与新故事运动
随着抗战的全民化及深入化,出现了“大规模的由都市向边缘地区的文化流动”,带来了文化中心的转移、读者群及社会环境的变化,抗战时期的文学进行着“有意识”的调整,以适应“文化中心的转移带来了都市与乡村之间文化关系的重构”。从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谈到的“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到1940年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讲演《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中提及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到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为什么人”这一立场、原则问题。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包含着民族、语言、传统与时代的“文化同一性”正在被创制。

“本格的、农村的”民间文学由于其在延安时期对于革命的重要意义,在新中国成立后被纳入“革命中国”的构建中,不同阶层的知识分子作为革命力量被吸纳到共产党的体制中,成为无产阶级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原先被视为“萌芽状态的文艺”“原始形态的文学”“群众的言语”等通俗文艺在政策的“外部性”与文艺的“内部性”的合力下,达到了“雅俗兼容”的艺术审美层次。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文代会”)确立了解放区文艺在全国文艺界的领导位置,延安时期“为人民大众”的文艺样式与实践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推广。1949年10月15日,在赵树理和老舍的积极推动下,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成立,赵树理发表《在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强调研究会成立初衷为“发动大家创作,利用或改造旧形式……创作大众需要的新作品”。1949年12月22日,通俗文艺组的贾芝等向周扬请示,拟设民间文艺研究会专事各种形式的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1950年3月29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以下简称“民研会”)成立。民研会成立后,主办了《民间文艺集刊》,所刊文章兼顾民间文学理论与民间文学作品。如第一册刊发:《毛主席改造二流子》(辛景月记)、《朱总司令来了》(戈枫记)、《关于红军的独》(吴群、岑风记)、《李闯王的传说》(夏秋冬记)等故事,这些皆以土地革命时期的民歌、传说的搜集整理为主。第二册则设置“新的传说”栏目,收录诸如《毛主席万岁》(康濯记)、《金日成将军的故事》(公陶记)、《我们的战友》(徐放周原记,沛之改写)、《许县长的故事》(邵子南原记,李方立改写)、《雪枫堤》(陈雨门记)等故事。第三册以西藏的和平解放为主题,收录少数民族民间故事,如《兔杀狮》(胡仲持译)、《白鸟王子》(远生编译)等。《民间文艺集刊》所刊载的民间文学作品关注与强调文本的思想性,注重对其历史文化价值的阐释,与“人民性”“民间性”“大众化”等文艺话语的形成密切相关。1956年开始的全国范围内民族识别与各民族历史调査,为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提供了契机,为新故事的创作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故事作为“社会主义时期群众文艺创作与民间文学传统的融合”,是一种具备独立文体样式和独特审美价值的新型文学样式。它继承了延安时期讲述“革命英雄人物事迹”与“地主、佣工与佃户的故事”的叙事传统。从1958年开始,随着以“三大”“六新”画为特点的群众文化活动在全国范围的兴起,新故事的创作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与“新秧歌”“新歌剧”“新民歌”等在某种意义上分享着相同的逻辑,“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风尚为原有的民间形式注入全新的革命意涵”由于其“比较适合群众的欣赏水平和欣赏习惯……又便于在讲故事的过程中结合当时当地的群众思想状况”,因此,随着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以及文化革命运动的逐步深入,“新故事运动”逐渐兴起。1963年,《人民日报》接连发表社论《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鼓动上海工厂、文娱场所的故事会受到欢迎》《两千多名业余故事员积极向社员进行阶级教育上海郊区大讲革命故事》《上海农村广泛开展讲革命故事的活动》,等等。据统计,仅上海一地,市郊农村已有一万多名故事员,不少公社队队有故事员。上海市区里弄也活跃着三千多名故事员,上海工人文化宫还成立了工人业余故事团,深入各工厂企业进行讲故事活动。在军队中,也产生了诸如《李科长再难炊事班》《过壕》《三比零》《擂旗》等优秀的新故事作品。在这样的创作机制下,“新故事融入了以政治主流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体系。”
20世纪60—70年代,“为帮助故事员解决故事脚本的困难,向广大工农兵群众推广优秀作品,扩大社会主义宣传阵地,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人民文学》增设“新花朵”“故事会”等栏目;《山东文学》《甘肃文艺》《山花》等地方刊物也增加了“故事会”“龙门阵”等栏目;《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陆续发表新故事作品《凌雪梅》《过客》《两个稻穗头》等,这些作品无论是在题材的选择上,还是在创作中对“故事性”的肯定与发挥上,都离不开对民间文艺传统的借鉴,不能将其简单地视为渗透着意识形态需求的文本。新故事作为一种“寄托了大众集体诉求的叙述”,在民间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碰撞中,“言”“文”合流,建构新的“民间”。
三、“革命故事”与《故事会》
延安时期,文艺领域时形成了“文艺为人民”的新的话语体系,这“决定性地影响到1949年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为了应对“通俗文艺”中存在的“暧昧质素”,“新故事”这一新型文学样式在对“革命理念(共产主义设想)”不断回应的过程中,成为文学接驳国家话语的重要场域。
1958年4月至12月号的《民间文学》上集中刊载了二十多篇关于义和团的传说故事,主要分为两类:一类直接反映了义和团的反侵略反压迫斗争,如《刘黑塔》《义和团战落堡》《洗大王大务》《托塔李天王》《红缨大刀》等;一类则是以洋人盗宝为题材的幻想故事,如《白母鸡》《小黄牛》《渔童》等。从1959年至1962年,《人民文学》《民间文学》《安徽文学》上搜集、整理、发表了约三百余篇捻军的故事,后结集为《安徽捻军传说故事》(第一集)、《安徽捻军传说故事》(第二集)、《捻军故事集》等。在对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文学总结中,撰写者强调“我们釆录新作品和发掘劳动人民的文艺遗产的工作,是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的,是为了使人们从这些作品里认识新、旧社会的巨大变化,为了鼓舞人们的革命斗志和培养新的一代”,尤其是对红色民歌、红军的传说、长白山抗日联军的传说、捻军的故事、太平天国的故事、义和团的故事以及说唱文学的搜集,这些既是“珍贵的革命文献”,又是“当地社会生活的历史变化”的记录,同时也具有重要的宣传教育作用。
196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其后制定了“前十条”“后十条”,一场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普遍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运动随之展开。“革命故事”因其在讲述与传播中能够凸显尖锐而急迫的政治氛围得到大力提倡。
“革命故事是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一朵新花。它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诞生的。”这一时期,“相比主流文学期刊的运作策略的微妙和隐晦,以民间文艺或通俗文艺面目出现的期刊更为直观地表现出对政治意识形态的依附。”以《故事会》为中心进行考察,可以看到新故事的通俗化实践中“革命性”构建的脉络。
1963年7月《故事会》第一辑《稿约》中提出:
凡是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传统的故事,不论是根据小说、报道、戏剧、曲艺、电影等文艺形式改编的还是创作的,只要可以口头讲述,适合群众的欣赏习惯,我们都很欢迎。
以现代题材为主,特别欢迎歌颂三面红旗的故事,反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的故事,反映革命斗争的故事,揭露和控诉阶级敌人罪恶的故事。
在1963年7月至1966年5月不定期出版的24辑《故事会》中,除反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革命斗争和反对封建迷信的故事等,还根据不同时期的政策和时事出版各种主题专辑。如第十二辑为“解放军和民兵故事专辑”,包括8则故事和两篇经验介绍。其中《插旗》和《三比零》是解放军对敌斗争故事,前者反映福建前线侦察兵深入敌岛粉碎敌人政治阴谋的英勇行为;后者描述空军战士歼灭美制蒋机的战斗气势。《李科长巧难炊事班》《快三枪》《宋文龙追车》和《过壕》生动反映了解放军炊事兵、飞行员、特等射手等在“练为战”的思想下勤学苦练、永不自满的革命精神。第二十一辑为“王杰故事专辑”分为“王杰的故事”和“在王杰精神的鼓舞下——学习王杰的故事”两部分;第二十四辑为“焦裕禄”故事专辑,其中“在革命故事活动战线上”这一栏目中的3篇文章,介绍了革命故事的创作特色、组织故事创作和用革命故事占领茶馆阵地的经验。

《故事会》“特殊的生产形态”使故事基本都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署名,比如“改编者”“口述者”及“整理者”。如《幸福桥》为上海市松江县“农村业余作者”徐林祥、周天华创作,上海市星火评弹团巽丽声整理,在故事后的附记中,整理者详细介绍了故事的搜集、整理、加工的过程、讲述时长及讲述重点。《故事会》第七辑为“上海市青浦县故事创作专辑”,在《编后记》中提到,在青浦县文化馆和出版社编辑的配合下,其创作方式为:
召开故事创作会议,发动各方面的创作力量摆题材、抓苗头,运用集体智慧,帮助作者取舍情节、安排结构、丰富细节,初步搭成一个“故事架子”,再由作者具体进行创作。
故事创作出雏形之后,在反复的口头讲述过程中,吸收群众意见反复进行修改,再记录整理成文字。如《母女会》“附记”中提到此故事根据家史改编,故事的主人公也参与了故事的改编工作,“并在故事改编过程中进一步追忆了旧时的苦难,提高了觉悟”。“附记”一般紧随故事之后,“为故事员提供全方位的引导和指示以有效地配合意识形态达到教育宣传目的”,对于故事创作情境的“重述”激活了故事的创作资源、情感体验、审美追求和价值取向。1967年8月至10月,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三辑《革命故事会》,它与《故事会》一脉相承,可视为其“革命性”的延续。1974年3月《革命故事会》复刊,到1978年12月共出版39期,并于1978年第6期刊载“自1979年第一期起,恢复《故事会》刊名”的启事。
结语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伴随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国文化(文学)在与世界体系的互动中,围绕通俗化实践,逐步构建起民间、启蒙、革命互动互融的话语空间。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民间文学被赋予了现代意涵,具有“民间性”的话语表述及审美趣味唤醒了共同的文化记忆。其中,1949——1966年的新故事,在承袭民间文艺创作传统的同时,适应新的历史语境,形成以“革命故事”讲述为中心的叙事脉络;这一时期新故事的通俗化实践超越“文本化的意义建构”,它在民间文学传统和主流话语的“耦合”中,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认同提供了生命经验和情感纽带,同时亦对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来源:《民间文化论坛》2020年第6期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