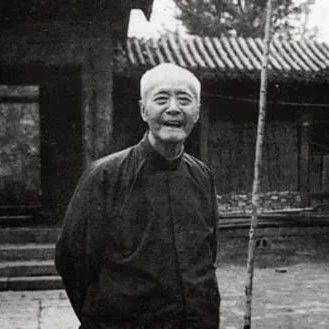
摘要
本文所指的理智与情感的双重认同,主要从两方面而言,一方面,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作为“语丝同人”的顾颉刚参与《京报副刊》救国特刊的编辑、写作,表达一个知识分子对国事的关怀。从顾颉刚刊载在《京报副刊》的相关文字中,能看出两点趋势:顾颉刚探索采用通俗文艺形式的作品将观念传达给民众;在与其他知识分子的救国救民态度对比中,体现顾颉刚务实理智的救国思路。另一方面,1931年顾颉刚的内陆考察旅行,让他在情感上体会到了民众无以复加的精神苦痛,此次的旅行触发了顾颉刚兴起第二次新文化运动的愿景。
关键词
顾颉刚;民众观;通俗;新文化
一
如果考察顾颉刚关注民众需要与思想之由来,还应从其年少之际讲起。顾颉刚从小由其祖母带大,善讲故事的祖母会给顾颉刚讲一些动听的故事,这在顾颉刚沉闷枯燥的经典学习之外无疑是一种温情的慰藉。顾谓这些故事“增加了我的向善心,打开了我的想象力,她高高的擎起了照亮我生命的第一盏明灯”。及至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顾颉刚梦想的居然是学农科,原因是那时痴迷文学的他觉得古典诗词把农村生活描写得太美好,比如陶渊明描述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情境让他感到有很“真挚的乐趣”。虽然顾从小对民间文艺有熏染,但他很少有机会接触民众,他之接触民众是由到北大频繁听戏引起的。那时在北大读书的顾颉刚不怎么爱去上课,倒是爱听戏,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无论哪一种腔调,哪一个班子,都要去听上几次”,这种“荒唐”的生活顾持续了两年有余。顾颉刚后来总结,听戏生涯让他得到了学问上的收获,又让他改变了观念,意识到了去接近民众。顾曾剖析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说早年听祖母讲故事,及至读书渐多,觉得那些故事是悠谬无稽之谈。他认为自己虽然恨过绅士,但自己身上沾染有绅士气也是不能抵赖的事实,他鄙薄说书场的卑俗与小说里的淫俚,因此不屑去也不屑读。他反思,“生长于诗礼门庭,自小就被强迫读古书,本没有和民众接触的可能。只缘到北京大学肄业,脱离了家庭的管束,一向羡慕北京戏好,就天天下午去听戏,这固然为了自己的兴趣,但借此却认识了社会的情状,而下层社会被压迫的情形也知道了不少。”在北京大学两年时间的听戏对顾颉刚民众观念的养成起了重大作用,也让他体会到了“人的气味”。
如果说北大的听戏经历让顾颉刚对下层民众有了亲切之感,那么1925年“五卅”惨案的爆发,顾颉刚直接参与唤醒民众的事业,则是更进一层的关注。五卅惨案的发生在当时引起了知识界极大的关注,顾颉刚自然也不例外。由于国难骤起,也引发了知识分子如何到民间去启蒙民众的争论。顾以“无悔”的笔名在《京报副刊》撰文进行鼓与呼,表达一个读书人对民瘼与国家的关怀,并且小试牛刀如何唤醒民众的方法。顾当时所写《上海的乱子是怎么闹起来的》作为传单印发,全文不长,从开头到结尾,文字都经过精心构思:
诸位知道。这次上海的乱子是怎么闹起来的。是因为日本人开的纱厂里头。开枪打死了中国工人。中国人看见了气不过。起来打抱不平。印了传单在街上分发。发到英租界的时候。给英国巡警看见了,把发传单的人抓进巡捕房去。中国人瞧见了越发生气起来。聚了好些人到巡捕房去。要他们把发传单的人放出来,谁知道巡捕房不由分说。就开起枪来。当时打死了十一个人。受重伤的有好几十。枪子儿都是从脊梁上打进去的。可见是中国人一边儿跑。外国人一边儿追着打的。自从那天以后。英国人跟日本人天天在上海随便杀人。打人。到人家家里去抢东西。调戏妇女。……可是外国人不是个个都是这样坏的。好的外国人,我们仍旧要待他们和和气气。我们的主意。并不是凡是外国人都恨。我们恨的是不把我们中国人当人看待的英国人跟日本人。这个意思。我们一定要明白记住才好。

句子不长,短句居多,每句话基本就是一个意思。采用传统评书说书之法,将事件前因后果描述清楚,一句接续一句,无废话,清楚明白,既有情绪,亦有理性。孙伏园在文末附识指出,为了让民众明白,第一,应该少用乃至不用特别或新鲜的名词。第二,不用标点,怕民众因没有看惯标点而不看全文。第三,为防止发生排外的流弊,需要在文末特别强调区别对待。为了更好地传播,顾颉刚还写了一首《伤心歌》:
咱们中国太可怜,打死百姓不值钱
可恨英国和日本,放枪杀人如疯癫
上海成了惨世界,大马路上无人烟
切盼咱们北京人,三件事情立志坚
一是不买仇国货,二要收回租界权
第三不做他们事,无论他给多少钱
大家出力来救国,同心不怕不回天
待到兵强国又富,方可同享太平年
欢迎翻印,看完送人
顾作为一个学术研究者,用孙伏园的话讲“向来是线装书,线装书,线装书里面钻着”的人,却模仿歌谣形式写出这样一支民歌。孙说作为语丝同人的顾颉刚若果不是深得民歌三昧,是无论如何写不出这种“惟妙惟肖”的作品,说明“语丝同人对于时事竟也破例热心,不落人后”。这首民歌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顾在1925年6月30日日记后的附录中说,“此传单发出后即生效,孩子们口中唱了,刷黑的墙上用粉笔写了,以是知通俗文学之易于入人。九一八事变后,予之办三户书社即因此故。然如非北大收集歌谣,予从而响应之,亦不能为此。”
二
如果说用通俗的形式吸引民众对焦点事件的关注就算成功,很显然顾颉刚不会这么认为,要想提振民众的观念与常识,按照顾的设计就应该更进一步在通俗的形式中讲更深的内容。通俗的文字本身不易做,尤其是在其中讲政治、外交、教育等等话题更是难之又难,这种难实在是民众的知识太过缺乏了。按照顾颉刚的说法,只具有初民时期知识的民众当然没法对诸如“帝国主义”“殖民”有所反应,这对他们脑筋而言实在过于隔膜。孙伏园举例说学生高喊“打倒帝国主义”,而妇人小子以及“游口好闲之辈”竞相效仿,变成“大,道,稽,古,祖,遗!”“打,扫,鸡,骨,猪,皮!”,除了恶作剧之外,民众对“帝国主义”这种名词是“未之前闻的”。面对这样的困难,采取何种样式让民众知道除了五卅惨案本身的来龙去脉外,更要知道外国殖民者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就不得不费苦心。顾颉刚采取了两种方法,一是吸收民间故事中习见的、民众能产生无意识反映的词汇来普及国家意识。为了让普通民众知道外国势力到底如何进入中国,顾写了一系列谈不平等条约的文章,他在其中一篇文章的末尾这样写道:
在这个时候,正似无赖恶霸抓到了一个百万家私的娇养惯了的大少爷一般,只要略施恐吓,便不怕不缴出钱财来。恶霸们拍一下桌子,骂一声贱骨头,大少爷就哀呼一声饶命,于是他们志得意盈的满载而归了。牛皮王二既从这个大少爷身上发了一注大财,于是泼皮李三,麻皮金五都垂涎起来,奋臂而至了。就是已经发财的牛皮王二,也因发财的容易,激起无尽的贪心,过了几天,又照样的演一番了。不到这个大少爷倾家荡产,他们决不肯完结。诸君,现在这个大少爷的动产是已经送得精光了,只剩下一所破旧的房屋还住着,而这班泼皮又在外边声势汹汹,带了凶器,见人乱刺,非进来拆卸木料,搬运砖瓦不可。为这个大少爷计者,是避去了他们的凶焰,让他们拆卸房屋,从此飘零荒野,冻馁而死的好呢?还是纠集了族人,同他们拼上一拼,胜则从此恢复了家业,败则得到轰轰烈烈的一死的好呢?费心,请替他想一想!
顾颉刚这一系列谈不平等条约的文章其行文思路基本是引用条约原文,但条约原文是文言文,对于普通民众可谓晦涩难懂,为了增强报纸可读性与民众注意力,顾颉刚在文末来了上面所引一段的叙述,有意用上“无赖恶霸”“大少爷”“牛皮王二”这类民众习知的词汇,还以民众熟悉的意象(“破旧的房屋”)作比拟。顾的探索虽然值得肯定,但在文末加上一段带着“伪民间”特点的描写显得太夹生。首先,最末一段忽然改换行文风格与前文不搭。文章前面是生涩枯燥的条文介绍,文后忽然插入一段风格完全迥异的叙述,显得相当不协调。问题是,一般读者不会忍受读完前面难懂枯燥的条约原文接续着读到最后一段。再加上《京报副刊》属于知识阶层的报纸,受众依然局限于知识界,这与普通大众还是有较大的距离。顾颉刚的这种试作看似通俗实则不然。一是并非采用了通俗之名就是通俗文艺,换句话说,通俗既是语言俗——俗是好懂之意——更要意思俗,不然民众依然不懂。对通俗文艺创作比较了解的老舍认为,我们以为把打倒帝国主义和赶驴的王二拉在一处成为“赶驴的王二打倒帝国主义”就以为是通俗文艺,其实大谬不然。为了迁就民众将意思进行改换,把外国入侵者比拟成牛皮王二,泼皮李三,反而显得不伦不类,“哎,哪知道这既不俗,又不艺呀!我们根本不晓得赶驴的王二怎么思想,和他怎样想像”!
顾后来也意识到必须借鉴通俗的形式来表达,多多揣摩民众的心理与思想,光靠文人的闭门造车恐怕还是太过隔阂。顾颉刚考虑采用比如鼓词、弹词、攤簧等民间形式来传播常识,他认为如果能将一班爱好歌唱的同志,联合起来组成团队,到民间去歌唱,这会是很好的策略。顾尤其侧重大鼓词的良好宣传效果,顾把大鼓词的宣传与学生的演说对比,认为学生演说,固然出于一腔热诚,但因为“口音的隔膜,用语的艰深,态度的失当,使得民众听了之后感不到切身的需要,只觉得还是‘他们’的事”,最后还是沦为一种漂亮话而已。如果同样的内容由民众信从的艺人用说书或唱的形式表现出来,基本妇孺能解,即使不懂,“经了善于揣摩民众心理的唱书人的解释,他们自然要感到救国是‘自己’的事了”。顾知道鼓词的宣传不能只让民众知道大意,还必须得让民众有很深的印象,若无深刻印记,大意仍然会渐渐澌灭,效果又为零,而这种深刻印象的取得恐怕不是靠单纯内容的获得,大概还要从民众习见的传播形式中不自觉的浸透。这其实说明,要想让民众得到常识,首先要让他们觉得宣传有趣味,对民众而言讲趣味比讲知识还更关键。只有有了他们熟悉的味道与气息,他们才能顺畅地接受信息,这样方能种下持久努力的种子。顾的目的是要把兴奋的感情变为持久的意志,要把一时的群众运动变为永久的救国运动,他希望有心人能借助鼓词多作一些如圆明园的焚烧、大沽口的失守、沙基惨案之类的国难题材,可惜好的鼓词太少。
顾颉刚的这种隐忧不止是他一个人的担心,当时在《京报副刊》“救国特刊”专号以及其他刊物上面,知识分子讨论如何觉醒民众以及给民众提供何种内容形成了一个话题圈。这些讨论中,郑振铎(署名西谛)的文章《止水的下层》值得重视。他认为唤醒民众实非易事。例如五卅惨案,于己身无切身利害关系,民众表面上表示一点关切,但也只是隔靴搔痒,无补于事,他们要的只是安稳日子,只要不打到自家门口,他们是不会睁眼反抗的,民气实在消沉得很近于一潭止水:
我们的民众是一泓止水,能被风雨所掀动的只是浮面的一层,底下的呢,永远是死的,寂静的,任怎样也鼓荡不动他们。他们一丝一毫的反抗思想和前进意志都没有。“现在”是最好的,是不必变动。就处在最逆境之下,他们也能如驯羊,如耕牛似的忍耐的生活着。至多只能发出几句追羡古代仁德的叹声。在今日是追想着袁世凯,前清皇帝,在清代是追想着唐宋,在唐宋追想着汉魏。……像这样乐天任命的民族,我们将如之何呢?他们又是最自私的,最现实的,眼光只能射到最近的一道圜线。你们如果不去打扰他们的田园,不去多征他们的租税,不去把他们现在的和平之梦打破,他们是什么事也不管的。……唉!止水的下层,止水的下层!我们将如之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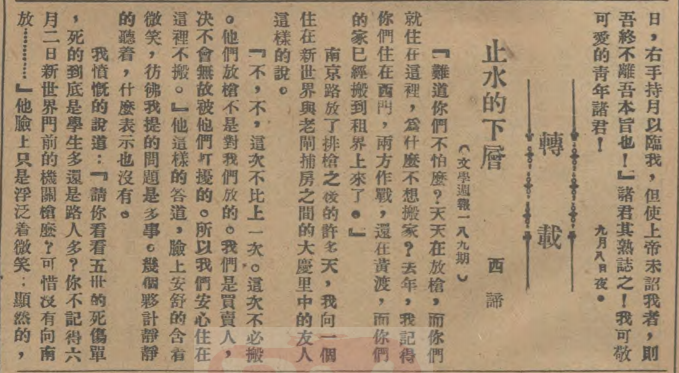
这样的民众笃信好死不如赖活着,郑振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心情溢于言表。知识分子的唤醒民众总是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当知识分子觉得国势日衰,民气不振,觉得快要亡国之际,他们认为最要懂得常识与理性的是普通大众,然而普通大众却只是安于现状,一边是热心的唤醒者,一边是昏睡致死的可怜民众,他们本身又不觉得自己可怜,加之这所谓的唤醒又只是局限于城市或是城市近郊的乡村。郑振铎文章的中心意思虽是看到民众如此之重的毛病,落脚点依然是我们该如何唤醒这止水的下层。顾颉刚在文后回应说,这实在是一个应该解决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民族终究是一个天生为顺民的民族”,“我常想,外国人这等欺侮我们,我们且慢一点生气,我们还是回过头去看看这班所谓的安分良民。实在教我们自己做了外国人,也是忍不住要来欺侮的!”这实在是恨之切的激愤之语。
总体来讲,在救国的态度上,顾坚持两个原则:第一,主张“近人情的救国”。顾颉刚这个意思是从钱玄同1925年7月19日致他的书信引申而来。钱信说因为救国上海各报均取消游艺栏,对于此种措施,钱表示不以为然,谓救国当然是严肃认真的事业,但也不能让人无时无刻都要救国,救国可以,其他工作也不当疏略,“我们的意见以为兵士在休战之顷,也未尝不可在战壕中讲笑话,也未尝不可与他的爱人接吻”,“故娘死了尽管哭得呕血,而清炖蹄膀仍可吃得”。顾由此生发说救国之外的事业与兴趣应该保存,救国之先要首先注意个体,首先要尊重肯定个体的人生乐趣,人生的乐趣当然也包含物质的快乐,但不是享乐,这是人生的基本要素与必要前提。若将生的乐趣剥夺,一味朝着民众喊救国,当然应者渺渺。顾分析我们的民族缘何生趣减少,缘何成为一麻木不仁的民族,“实因汉代以来的政治与教育过分把人生的享乐的欲望遏抑了。大家说去欲(宽一点说节欲),大家说知足,大家说恭敬,使得所有的人只觉得人生的本分是仅有奉侍长上与抚育儿孙两件事,此外一切非所当为;就是因情绪的冲动而忍不住去做,也只敢偷偷摸摸的做”,使得人的活动范围极小,“弄得偌大的一个国家竟布满奄奄待尽的空气”。因此要救国,必须使人感到生的乐趣,解放向来的礼节的束缚,顺从各人的情感去发展。
第二,顾坚持做基础实际工作,认为要将沸腾的情绪建立在永久的切实工作上,反对空洞的主义与名词。顾说现在的大学生和大学教授对于主义没有明了的概念,就滥用主义的名词做植党营私,扩张地盘的勾当,将救国的事业变成一己之私,“这种事情要是由人格久已破产的政客去做,我当然不觉得什么;现在号称清流的大学生与大学教授竟也是如此,这使我看了那得不心痛欲绝!”民众本来就不明就里,如此号召,“可怜的民众,只会随着这班人乱跑,做他们的牺牲!所以运动虽多,激刺虽强,民气虽盛,而国家却永远得不到实惠,只在这个时期之中制造出许多登场的小政客而已”。这样的空喊乱叫只是“天上的云霞”,虽然一时灿烂无比,不过来得快去得也快。顾分析中国人不喜欢做扎实深沉的工作,实因从本性讲,讲救国的同志高兴随了本能而冲动地做去,不愿意费了脑髓而作工作,前者可以得名得利,出尽风头,后者则无论形式抑或内容都隐蔽得多,做的人自然少。顾说这与数千年专制之国的影响有关。然而时潮的刺激,容不得叫嚣与浮泛,顾颉刚强烈呼吁:
我们不要和人妥协,也不要和人争权,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事业,这种事业是只有耗损我们的精力与金钱,却不会使得我们的地位升高到升官发财的地位的。我们也不要做群众所仰望的偶像;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工作公开给众人看,听他们的采择。我们要勤勤恳恳的做,拼尽了自己的一生的精力,成功也这样,失败也这样:成功了不居功,失败了不丧志。我们不要号召什么徒党;也不要预备组织什么政党;我们只要把自己的精力尽自己一部分的责任,不责望别人的帮助。我们只承认可以一步一步走的路是我们的路,不希望一飞冲天和一鸣惊人。我们自知这样做去,当世名流一定要笑为迂远,因为这是出不出风头的。可是到了我们成功的时候,他们的良心上也要感受到他们自己所作的罪恶的惩罚了。
顾颉刚始终认为实在长久的工作是必要而且有效的。他根本相信知识阶层通过努力是可以启蒙民众的。这一点与周作人大不一样。顾颉刚在文章中引用周作人一句话,“我以为读史的好处是在豫料又要这样了”,在周作人看来历史不过一循环,惨祸周期性发生,民众仍然无知无识。此话出自周的《代快邮》,刊于《语丝》1925年8月10日第39期,该文的意思是由五卅惨案引发的爱国运动声势浩大,但却找不出几个爱国的志士,当然“揭帖,讲演,劝捐,查货,敲破人家买去的洋灯罩”的人必然有,但却意义不大。周说我们应该痛加忏悔,知道自己的罪恶,要有“自批巴掌的勇气”,否则革新无从谈起。周作人认为要救国首先要把自己当人,“我们如不将这个拿自己当奴隶,猪羊,器具看,而不当做人看的习惯改掉,休想说什么自由自主,就是存活也不容易,即使别人不来迫压我,归根结蒂是老实不客气地自灭”。否则总会出现周作人说的一边是学生慷慨激昂地演说,一边却是糟蹋作践自己:两脚小得将要看不见的女人与从脸上看出他每天必要打针的男子从旁走过。从周作人对五卅事件发言看,他擅长从思想与细节入手对民众进行观察,固然体现他对事情洞若观火的冷静观察,不过他的一个总的意思是由于以上观察,他对爱国运动终持冷淡态度,也因此顾颉刚对周作人这种悲观论调表示不赞同。这大概是顾颉刚与周作人的不同。简洁而言,周作人看到了民众乃至整个民族的缺陷,他用一双冷眼已经提前预知了结果可能依然不会有太大太多的改变,便选择冷淡甚至冷漠的回应,懒于行动;顾颉刚未尝没有看到这些问题,他在文章中也提到救国运动每隔四五年来一回,三十年间也发生了五回,第五回便是这五卅惨案。但顾颉刚接下来的思路是采取何种方法提高民众孱弱的救国能力。顾颉刚是一个行动者,这可从顾在《京报副刊》撰写的“救国特刊卷首语”得以表现:
我们醒悟了!我们要永久这样做,直做到完全达到我们的志愿的时候。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弟兄们,我们在救国的工作上已经堆了几畚土了?
我们的身体里有的是血!我们的脑髓里有的是奋斗!我们的眼睛里有的是实际的救国的事业!
我们有的是什么?我们没有学问,没有金钱,没有一切的势力;但我们有清白的心和沸腾的血。我们要用了我们的心和血,努力吸收丰富的学问,赤手造成纯洁的势力,把旧有的污秽都洗刷得干净!
失败不可悲,失败而灰心乃是真的可悲。我们要在无尽的失败程途之中作继续不断的奋斗,这便是我们的成功。我们不怕失败,我们只怕灰心!
我们不要无条件的承受什么主义,我们的主义要建筑于我们的工作上,我们的主义是我们工作的结果!
我们要轰轰烈烈的生,也愿意轰轰烈烈的死。我们不愿意做本国军阀的良民,也不愿意做外国强盗的顺民,所以我们要自己站起来干!
我们要移山,只有把泥土一畚一畚的运掉。我们要填海,只有把砖石一块一块的投下。朋友们,我们空喊移山和填海是不中用的,我们还是大家去做运土投石的小工罢!
一束的薪虽烧完了,但火种却传下去了。我们祝颂这一星星的火种能够永久燃烧,发出伟大的光明,打破大地上的阴森黑暗!

这些卷首语充满着火热的炽情与坚定的意志,很难想到这是孜孜矻矻考辨古史的顾颉刚所写。格言警句式的表达背后彰显的是顾的决心与信心,他有高远的目标,扎实的思路,理想主义的情怀。
五卅惨案中,顾颉刚在《京报副刊》的发声是顾第一次参与唤醒民众的实践,做得十分认真。此时顾颉刚重视民众还是从理智上着想,他与民众的关联仍然有限,这种有限是止于理性的认识有余而情感触摸仍显不足。
三
真正触动顾颉刚,让其直面民众之惨、无法忘怀民生之多艰是1931年前往内地考察的旅行。1931年4月3日顾颉刚与容庚、郑德坤、林悦明、洪业、吴文藻等组成燕京大学考古旅行团进行考古调查,据顾潮《顾颉刚年谱》(增订本)介绍,此次考察行经河北之定县、石家庄、正定、邯郸、魏县、大名,河南之安阳、洛阳、陕州、开封、巩县,陕西之潼关、西安,山东之济宁、曲阜、泰安、济南、龙山、临淄、益都、青岛等,历时57日。
这次旅行也彻底打破顾曾受诗词歌赋影响认为田园村景是极乐天国的遐想,此次旅行最令人难以忘怀是国家民族的危机,这危机的表现就是民众生活的悲惨与无助。顾颉刚看到许多老百姓过着穴居生活,“我用了历史眼光来观察,知道炕是辽金传来的风俗,棉布衣服的原料是五代时传进中国的棉花,可称为最新的东西。其他如切菜刀,油锅之用铁,门联之用纸,都是西历纪元前后的东西,可以说是次新的。至于十一世纪以后的用具,就找不出来了。然而他们所受的压迫和病痛却是二十世纪的,官吏和军队要怎么就怎么,鸦片,白面,梅毒又这等流行,他们除了死路之外再有什么路走!”一言以蔽之,根本找不到一点现代文明的影子,“除了一把切菜刀是铁器时代的东西之外,其他差不多全是石器时代的”,然而他们却要承受二十世纪的苦难。民众的衣食住行,无一不劣,“自郑州以来,我们住过的客店,大大小小,没有一处是有玻璃窗的。地永远是泥的,墙壁永远是脏的。尤其是毛厕,一个小院内,你爱在什么地方下便就在什么地方下便。现在天气已暖,一阵阵的臭气直送到客房里。将来天气热了之后,叫人怎样下榻呵!”。顾颉刚描述他们住的客店,天气还不很热的时候,苍蝇已在饭桌上“满飞了”,“饭菜实在太脏”,一盘一盘放在簷下,不知过了多少天,无法下咽。一到下雨天,交通完全阻断,“我们住在高厅大屋里,听着雨声,很觉风雅,或者睡在被窝里,更觉安稳,哪里想得到路上行人的万千苦痛呢”,顾说他理解了陈涉吴广为什么有叛秦的勇气而没有冒雨行进的勇气,“哪里知道北方的道路不是苏州的道路,没有石子砌成的街道来漏水,更没有纵横的河道来宣泄呵!”
顾说这次旅行他算是“享受纪元前的生活”了。民众的生活已经是呼天抢地,让顾“心惊肉跳”,觉得中华民族的颠覆将“及身亲见”。这次学术旅行顾颉刚看到了古物的破坏,固然值得惋惜,但真正伤心是国计民生的愁云惨淡。顾回到北平后,北平歌舞升平的景致让其无法心安,农村凋敝的景象“永远占据了我的心”,“我总觉得在研究学问之外应当做些事了”。作为一个读书人,顾颉刚下了决心,他要效法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之志,要做救国救民的事业了。
顾颉刚决心好好做好救国救民工作的背后是想兴起第二次新文化运动。顾曾在不同场合谈过要再造一次新文化运动的愿景。诚如他在《旅行后的悲哀》一文中所说,就在他考察的这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别人都义愤填膺,他则独喜。因为他觉得借此机会能激起国族的奋斗心与上进心,正好可以来做启蒙与救亡工作,“如果天佑中国,能改掉五四运动以来轻薄浮华的积习,在适当的领袖之下做复兴中华民族国家的工作,不求个人的名利,不求成功的急速,有计划的一步步地走下去,中国还是有光明的前途的”。顾所指的“浮华浅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乡村民众基本是绝缘的,并且顾批评第一次新文化运动根基不稳,没有充实的知识与准备,导致的结果是“好似一声霹雳,虽然破人耳鼓,但不久云收雨散,就没有这件事了。堕落的还照样的堕落,害人的还照样的害人”。顾经常反思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工作只是局限于知识界,不及乡村。顾颉刚很沉痛地说,“我们用文字去教育,但大多数人不识字。我们在城市里去教育,但大多数人不在城市。我们开了学校去教育,但大多数人没有到学校的境遇。世变这样的急速,下手这样的困难,假使没有恒心,只希望他弹指立现,真要使人灰心丧意。”
他主张兴起第二次新文化运动是希冀在国难当头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与民众能有机融合,为民众解放开辟一条可行之路。在这条结合之路上,民众需要洗心革面,知识分子也需时时反省。顾颉刚用那饱含感情的语调说:
在这民穷财尽,赤地千里,人肉只卖几毛钱一斤的当儿,我们还能有饭吃,有书读,有研究的工作可做,我们的享用虽甚清俭,而在一般民众中比较起来,已是特殊的优厚;如果相信有上帝的,应当知道自己已是天之骄子。如果我们再不认清自己的地位,竭力负荷自己的责任,拼命去作有计划的进行,只是跟了快要没落的社会流转,我们便是这时代的罪人,我们饮的便是民众的血,吃的便是民众的肉,我们的行为正无异于罪大恶极的军阀政客。
每次读到顾颉刚剖析他所属知识阶层的文字,体会其间透露的歉意愧疚之情时,觉得“五四”那批文化人真能眼光朝下,对普通民众确能倾注关怀并身体力行的,顾颉刚可以算一个。顾认为知识分子应该肩负责任,与民众一起进退,知识分子的启蒙如果脱离民众,难免变成自说自话,搔不到痒处。道理虽然简单,做起来却不为人理解。顾在一九三零年代发动大规模的通俗文艺运动,采用大鼓词等旧形式进行新内容的宣传,创办“通俗读物编刊社”,编印通俗读物。据顾自己讲,从1933年到1937年间,他们总计出版通俗读物大约六百种,共印了五千万本,别人翻印的与图画还不算在内,数量可谓惊人。蒋梦麟就觉得,“顾颉刚是上等人,为什么要做这种下等的东西!”胡适讲,“你办这东西,足见你热心。但民众是惹不得的,他们太没有知识了,你现在放一把火,这火焰会成为不可收拾的,怕你当不起这个责任呢!”言外之意,胡适希望顾颉刚三思而后行。丁文江也认为,“你做千万件民众工作,不如做好一件上层工作。做好一件上层工作,就能收到很大的效果。民众无知识,无组织,是起不了什么好作用的!”蒋、胡、丁的看法很能代表这些精英知识分子的态度,感觉民众是一股无名的力量洪流,不能随便煽动,应保持克制,要严守“我们”(知识分子)与“他们”(普通民众)之别。

知识分子不愿意接触民众,自然有知识分子的傲慢与偏见在里面。顾颉刚曾深情又愧怍表述“我们”与“他们”的隔阂,将各自的心理细腻地描摹出来:“我们这般人就包办了雅的生活。天不下雨,农民担心的是田里的谷子快晒焦了,我们却因感觉不到雨打芭蕉,减少了作诗的兴趣。下雨下得大了,我们心里怨起老天爷来,出门时脚底下这双擦得发亮的皮鞋又要踏脏了,却不理会车夫和挑夫们早已湿透了衫裤,在雨潦中苦撑苦捱,一辆汽车飞驶过来时,还溅了他们满头满脸的污泥。”假使真的要“夜猫子叫醒雄鸡”,这叫醒应该是双向的。顾颉刚经过多次实地勘验、1938年还深入中国西北边陲多民族杂居之地近距离观察最底层民众生活,他发现知识分子实在不应该拉开距离以俯视的眼光看待群氓,民众的思想与生活对知识分子也有修正与启发的意义。
顾颉刚的这种民众情怀用傅斯年用来形容自己的话就是:“我本以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来之故,而思遁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去跑来,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其实说来,傅斯年、顾颉刚从某种意义讲是一类人,他们因为哀民生之多艰,不忍独坐书斋,便探出头来,弄启蒙,搞革新,谈政治,总想凭一己之力做点“公事”。顾颉刚如果一直深居象牙塔,研究他的古史,也无可非议。不过他们没有如此做去,在自觉不自觉间为时势所牵引,加之机缘、人事、理念的凑泊,演化成一种忍不住的关怀。这种关怀是古来读书人达则兼济天下的现代衍变,同时也是受五四新文化催发而作的未完成启蒙。
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呼喊恐怕是“人”的再发现,这“人”又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底层民众的深切关怀。新文化同仁们在文章、文学创作中关注各式各样的弱势者、畸零者、漂泊者,显得悲怆而又神圣。然而,从思想到文字再到现实变革,能始终如一对平民大众倾注关怀与心力的,顾颉刚可以毫不夸张名列其中。他对民众的亲近既有他小时候的熏陶,更有新文化时期观念的熏染。在社会实践中,他既看到了新文化启蒙大众的高远理想,更看到与大众远远隔膜的一面,因而下定决心想再造一次新文化运动,让知识分子与平民大众能融洽无间,再造新民。新文化之于顾颉刚,恰似鱼之于水,顾颉刚从中吸取养分,吐故纳新,既能入乎其内又能超乎其外,显得从容而冷静。行文至此,亦不得不指出,顾颉刚虽然倾心力于民众文艺事业,扎扎实实做了不少实事,的确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无法深入下层民众、在精神上隔膜下层民众的缺陷予以很大程度地改观,将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进行了紧密的融合,把书斋中的观念向现实层面掘进了不少,但从他的思想观念、办事风格与大量文字中,笔者不禁嗅到,顾颉刚身上有一种堂吉诃德的浪漫气质,往往喜欢于明知不可为的境地中做起偏向虎山行的事业,这是他的可贵之处。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文化遗产》2019年第4期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