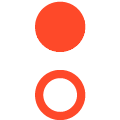摘 要:20世纪70年代韩国民俗学开始探索从“过去学”向“现在学”的转型。20年后,随着城市化进入尾声,城市与农村的地位在社会结构中发生根本性逆转,城市民俗学成为韩国民俗学界的焦点。林在海的城市民众主义与南根佑的FOLKLORISM研究的学术争论奠定了韩国城市民俗学的理论基石。韩国民俗学的转型实践对于中国城市民俗学的探索、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韩国民俗学;城市民俗学;城市民众主义;FOLKLORISM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民俗学迈入转型期,城市民俗学越来越受重视。虽然国内学者早于20世纪80年代就倡导对城市民俗的研究,但中国城市民俗学研究至今尚未完全开展起来。为此,探讨20世纪末就已基本完成城市化的韩国在民俗学转型与城市民俗学发展方面的历程,对于今后中国民俗学的转型探索与中国城市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韩国民俗学诞生于日本殖民时期的1932年。1966年推进的“祖国近代化”运动与1979年出现的“汉江奇迹”,致使韩国民俗学尚未来得及清算殖民地时期的“混种属性”,就需要仓促面对工业化与城镇化引发的研究领域骤然改变的新局面。20世纪70年代,金泰坤与李相日积极主张韩国民俗学应从“过去学”转向“现在学”,民俗学的研究重点应从农村民俗学转移到城市民俗学。这种主张在沉寂二十余年后,引发了林在海与南根佑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论。
林在海反对金泰坤的“现在学”观点,认同民俗学的本质主义,主张城市民俗学既是农村民俗学的衍生领域,又是新生领域;从民俗学的阶级性出发,提出从城市民众(即城市弱势群体)角度认识城市民俗学的主张。南根佑则支持“现在学”的观点,否定民俗学的本质主义,全面解构韩国民俗学;在批判林在海城市民众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用FOLKLORISM研究克服城市民俗学困境的主张。尽管韩国民俗学界至今仍未就城市民俗学的定位达成共识,但围绕城市民俗学而展开的学科史反思及学术争论成为影响当下韩国民俗学发展的理论基石。
一、“农村消亡论”中韩国民俗学的转型探索
1966年,韩国政府提出“祖国近代化”口号,大力发展工业,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化的影响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农村涌向城市,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农村则日益空心化。1970年,中央政府协同地方政府开展“新农村运动”,全面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农村消亡论”开始弥漫于韩国民俗学界。“今后山村消失,偏远村落消失,农村实现现代化时,我们的民俗学去哪里寻找研究对象呢?如果仍然只是固执于以前的研究对象,我们的民俗学恐怕要关门了。”危机意识促使民俗学界积极行动起来,谋求新形势下韩国民俗学的定位与发展。
1971年,圆光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在金泰坤的组织下成立,随后召开了以“传统与民俗学的现代性方向”(1971年10月)、“民俗学转型的课题”(1972年2月)、“民俗学的对象”(1972年6月)、“民俗学的方向”(1972年9月)为主题的四次学术研讨会。当时的参会者有韩国学者任东权、金宅圭、崔在锡、文相熙、金泰坤、李相日等,以及中国学者施翠峰、日本学者竹田旦等。会议以议题讨论的形式进行,会议过程记录在《韩国民俗学:原论性的对话》一书(1973年,益山:圆光大学出版社)中。

金泰坤在围绕韩国民俗学理论建构的四次对话中,积极主张韩国民俗学应实现从“过去学”向“现在学”的转型。金泰坤首先对以往的韩国民俗学进行了犀利的批判:韩国民俗学长期以来固执于偏远村落的原始残存文化研究,以期发现民族文化的渊源与民族精神的本质。这种研究方法与日治时期的“殖民地民俗学”并无差异,属于“过去学”范畴。然后他提出“今后的韩国民俗学将‘城市民间人’纳入研究范围,关注民间层现在的生活、文化现象,重视民俗学的现实性”的主张;最后倡议学者研究态度的转变:“民俗学者不应该站在‘客体的’立场,将民俗保有者当作动物园的动物一样,只关注其学术上的利用价值;而应该站在‘主体的’立场,站在民间人的立场。”金泰坤的主张虽然提及“城市民间人”,但没有上升到“城市民俗学”的层面,只是主张“社会民俗学”对新领域展开研究。
李相日是金泰坤“现在学”的支持者,也是被学界公认的在韩国提出“城市民俗学”概念的第一人。曾在瑞士学习德国文学(戏剧方向)的他受赫尔曼·鲍辛格《技术世界的民众文化》的启发,1974年3月发表题为“形成的民俗与残存的民俗——城市民俗学对农村民俗学”的论文。文中首先按照研究对象将民俗学作了二元化划分,将“僻地”的民俗学研究归类为“农村民俗学”,将“以技术产业现场所发生的民俗”为对象的研究归类为“城市民俗学”;接着对农村民俗学的浪漫主义进行批判;最后指出:“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发展,无数的现代民俗不断涌现,所以应当提倡用现代民俗学的体系与城市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关注日益更新的民众生活,从而探究民众意识与思维、行为。”李相日提出青少年的离家出走与叛逆行为、工厂的劳资纠纷、水库移民政策及其社会保障制度等都可以成为城市民俗学的研究课题,但没有论述具体的研究方法。
“城市民俗学”的概念出现后,并没有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因为当时抢救无形文化财是民俗学界乃至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新农村运动过程中大量民俗文化被以“破除迷信”的名义损毁,以至于1972年4月韩国内务部长官紧急下达了“全国民俗文化财保护令”。因此,1972年6月首次召开的“民俗学全国大会”将“民俗学的定位”与“文化财的保存和传授”结合在一起集中讨论。在这样的趋势下,“现在学”的倡导者金泰坤很快投身到巫俗研究之中,“城市民俗学”的提出者李相日则投入了戏剧研究之中。韩国城市民俗学一诞生便进入长达二十余年的沉寂期。
二、林在海的城市民众主义
20世纪末韩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建设进入尾声,城市人口趋于饱和,农村人口老龄化严重。另外,如火如荼的新农村运动已趋于平静,现代化技术与设施在带给农民生活便利的同时,也使农村社会完全暴露于大众文化与流行文化之中。民俗文化在农村的传承根基逐步瓦解,人口密集的城市则不断涌现出各种新民俗。不但如此,由于离农现象导致的人口迁移,即便研究农村民俗,有时也不得不去城市寻找相关知情人。总之,随着城市与农村在社会结构中地位的逆转以及城市文化对农村文化的辐射,“城市民俗学”成为韩国民俗学再也无法回避的课题。
2002年秋到2003年春,庆熙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先后召开了以“城市与民俗现场以及研究方法论”“城市与民俗生活”“城市开发与传统”为主题的三次学术研讨会。2003年8月与2004年2月,韩国民俗学会召开了以“20世纪与韩国民俗学”为议题的系列研讨会,通过反思20世纪韩国民俗学存在的问题,展望21世纪韩国民俗学的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2005年2月与2006年2月又先后召开了分别以“城市空间内民俗文化的形态”“城市民俗学的方法与方向”为主题的研讨会,集中讨论城市民俗学的学术定位。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韩国民俗学已经拥有了坚实的学科背景。韩国国立安东大学1979年开始设立民俗学本科专业,长期以来附属于历史学、国文学等学科的民俗学终于成为独立学科。1988年与1999年,该校又先后开始招收民俗学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1998年,韩国中央大学也开设比较民俗学本科专业。高校民俗学专业的蓬勃发展,为民俗学理论的构建与实践提供了平台。对韩国城市民俗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城市民众主义理论,正是安东大学民俗系教授林在海提出的。
林在海的城市民众主义理论由《民俗学的新领域与方法——城市民俗学的再认识》(1996年)、《对“现在学”观点审视20世纪民俗学的批判性认识》(2004年)、《城市中民俗文化的传承形态与城市民俗学的新纪元》(2007年)三部曲构成。1996年的论文对城市民俗的传承形态作了归类,并提出运用城市民俗学这种新方法实现民俗学研究从“民俗传承论”向“民俗生成论”转型的主张;2004年的论文批判金泰坤的“现在学”主张,探讨民俗学研究的问题意识;2007年的论文在前两篇论文的基础上,关注城市弱势群体,提出城市民俗学应实现从民俗主义向民众主义升华的主张。
林在海的城市民俗学理论建立在对20世纪70年代金泰坤与李相日言论批判的基础上,具体批判内容如下。

在批判的基础上,林在海指出:对城市民俗学的认识不应局限在空间位置上,而应将其视作一种时间性、历史性概念的新型研究方法。传统民俗学立足于“民俗传承论”,即关注民俗事象的传承问题,重视追溯文化的起源;产业化与城市化大规模推进后,城市民俗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民俗的现实性与功能性,城市民俗学作为新的研究方法应立足于“文化生成论”,从文化变动角度关注新民俗出现的原因。以“汽车开光仪式”为例,这种新民俗伴随着汽车的普及而出现,虽然保险公司有事后理赔服务,但驾驶者出于预防交通事故的心理,大多会在新车使用前准备祭品举行简单的祭祀仪式。这种祭祀仪式与过去渔船起航祭祀相似,从文化变动角度来看可以视作驱邪祈福仪式的传统民俗在新环境与新文物的冲击下发生的变异现象。
林在海将城市中存在的民俗按照传承形态归纳为五类。第一,城市土著民俗。这类由城市土著居民世代传承的民俗在城市化过程中,虽然传承力日渐弱化,但能很好地反映城市民俗的传承与变异问题。第二,新城市民俗。这类民俗是在城市规模扩张过程中农村被纳入城市版图后,在原来的农村民俗与城市文明碰撞中形成的民俗。第三,移民民俗。这类民俗是伴随农民进城而流入城市的民俗,大多以家庭或老年组织为单位传承。第四,移植民俗。这类民俗是由于城市经济与消费能力的吸引,具有表演才能的民间艺人向城市聚集而形成的民俗。第五,新生成民俗。这类民俗大多与商品化有关,如情人节、“双11节”等。林在海指出:对城市民俗复杂性与多样性的研究不仅能很好地阐释文化的传承与变异、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文化的生产与兼容问题,而且能从中捕捉城市居民的文化意识。
2007年,林在海对城市民俗学的认识发生了质的转变,在论证“民俗学是阶级性鲜明的学问,民俗文化是被统治阶级的文化”的基础之上,提出“城市民俗学的定位应是站在‘城市民众’角度,批判城市社会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商品化与市场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的主张。这里的“城市民众”是指居住在城市边缘、经济贫困、无固定职业或从事受歧视行业的弱势群体,如贫民窟的贫民、街头留宿人员、流动商贩、苦力、女服务员、性工作者等。
林在海将固执于寻找城市中新出现的民俗现象而忽视其传承主体——城市民众的民俗学研究定义为民俗主义研究,认为:这类研究大多与研究者看重个人业绩的利己主义有关,多采用Etic的研究立场;取而代之的民众主义研究则将探索民俗文化的健康传承与改善民众的现实生活作为主要目标,要求研究者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将民众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需采用Emic的研究立场。林在海认为,记录城市民众的故事与歌曲、信仰与梦想、生活法则与思维方式的调查报告以及从民众角度诠释生活真谛的学术研究将是城市民俗学发展的方向,将开启民俗学的新篇章。
林在海是韩国第三代民俗学者的代表人物,是“现场论”研究方法的创始人,曾担任2008—2018年“韩国口碑文学大系增补事业”现场调查团长,长期致力于农村口碑文学资料的收集,所以对农村民俗文化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传承变异有深刻认识。因此,他反对将城市民俗学作为地理性概念置于农村民俗学的对立面,主张民众主义城市民俗学与农村民俗学互为补充。林在海对城市民俗学与农村民俗学这种非对等关系的设定,对韩国民俗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城市民俗学仍被视为农村民俗学的历史延伸。
三、南根佑的FOLKLORISM研究
东国大学的南根佑教授毕业于日本筑波大学人类学专业,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致力于对韩国民俗学的解构研究,主张用FOLKLORISM理论解决城市民俗学的困境。南根佑与林在海的学术争论主要集中在《“民俗”的近代,脱近代的民俗学》(2003年)、《民俗的文化财化与观光化——以江陵端午祭的FOLKLORISM为中心》(2006年)、《从城市民俗学到FOLKLORISM研究的转型——针对林在海的“批判性认识”》(2008年)三篇论文之中。2003年的论文主要批判朝鲜民俗学会的殖民属性,呼应金泰坤的“现在学”言论;2006年的论文则导入“FOLKLORISM”概念,深入剖析了江陵端午祭的人为创作过程,尝试建构现代民俗学的研究范例;2008年的论文则对林在海的民众主义城市民俗学展开批判,主张不区分城市与农村而共同开展FOLKLORISM研究。
南根佑对韩国民俗学的解构主要从学史、学术定位、方法论三方面展开。首先从学科史层面来看,南根佑通过考证日文资料指出,1932年成立的朝鲜民俗学会标榜“民族主义”所开展的“抢救(salvage)民俗学”,与朝鲜总督府的殖民地政策存在“共犯关系”,即宋锡夏与孙晋泰所提倡的“乡土娱乐论”是响应日本为侵华战备而开展的农村振兴运动与厚生运动。其次从学术定位层面来看,南根佑认为“将民族文化设定为先验性存在,将探究其本质作为重要使命”的韩国民俗学定位不合理,“因为民俗文化的原始形态是无法探知的,包括民俗学在内的所有近代经验科学的方法论都无法进行证明”,“民族文化的本质与民族的精神元素其实并不是客观存在的实体,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政治语境中不断被重构”。最后从方法论层面来看,南根佑提出,韩国民俗学者代替“他者”为民俗主体发声的行为与东方学研究如出一辙,即如同东方学的研究者在否定东方人的话语权与自主权的基础上展开研究,这种方法无视民俗主体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在全面解构的基础上,南根佑援用金泰坤的“现在学”说法,倡导韩国民俗学应聚焦民俗主体,根据自身的生活需要有意识重构民俗文化的行为,即关注FOLKLORISM的实践现场。
“FOLKLORISM”概念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民俗学界盛行,20世纪90年代传播到日本民俗学界,是指“民俗文化在经中间人(second hand)传承的过程中,在脱离原传承地后产生新功能与新目标的现象;或者无关任何传统而被人为有意识地发明与创造出的类似民俗”。南根佑将这一概念与“文化客体化”(objectification:将文化视为可人为操作与不断创新的对象)结合在一起,指出“民族文化或地区文化是文化客体化过程中,经过人为筛选后向‘他者’展示的文化要素,这些被选择的文化要素已脱离了原有语境,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因此,南根佑主张,对民俗的创造与发明、改变与应用、观光资源开发与商品化、政策的影响与使用等课题进行文化政治学研究才是现代民俗学的重点。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南根佑对江陵端午祭的人为创造过程,即民俗学者与当地居民为申报无形文化财与世界无形文化遗产而对端午民俗文化要素筛选与重构的过程,进行了剖析。
南根佑构建起FOLKLORISM的研究范例后,围绕“城市民俗”与“城市民众”的界定问题对林在海的民众主义城市民俗学展开了批判。首先,南根佑认为林在海论证城市民俗时自相矛盾:林在海主张文化形态是界定民俗的标准,但城市民俗已发生变化,很难套用传统民俗的认定标准;林在海所列举的情人节等城市民俗事例也不符合“传承群体的民众性、生产的共同性、传播途径的口头性、生产者与享有者的统一性、现实认识的批评性、历史的传统性”等传统标准。其次,南根佑反对林在海将城市弱势群体定义为“城市民众”,对贫民窟的贫民、街头留宿人员、流动商贩、苦力、女服务员、性工作者等群体内是否存在民俗提出质疑,认为即使这些群体内存在民俗,也面临无法实地调研的困境,“难道要去首尔的地下通道,或者红灯区,或者饭店才能发现‘贫民层民俗’‘露宿人员民俗’‘性工作者民俗’吗?”南根佑犀利地指出,“城市民俗”或“城市民众的民俗”如果拘泥于传统的民俗定义(共同体的无意识性惯习)与传承要求(口头传承的连续性),那么其研究对象与方法会被歪曲,认识论也将陷入误区。
在解构民众主义城市民俗学理论的基础上,南根佑对民俗的传承主体重新定位:民俗传承主体是与民俗研究者共同生活在21世纪的普通人;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有意识地重构与重释“民俗”;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生活利益,有时会操纵自己的文化实践;他们也会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灵活利用民俗学成果与主流社会舆论。因此,南根佑认为民俗学研究无需区分城市与农村,自己将关注韩国农(渔)村兴起的乡村旅游,分析这些借助旅游开发发展地区经济的村落共同体成员立足现实,利用民俗等文化要素创造“新旅游文化”的过程,倾听围绕旅游文化的本真性与商品性以及经济利益分配等问题产生的多种声音,观察各种声音背后的政治权力及其他各种力量的对抗与调停过程,在参与观察的基础上展开FOLKLORISM研究。
四、学术争鸣中韩国民俗学的探索实践
林在海与南根佑的学术争论成为韩国城市民俗学乃至当下韩国民俗学的发展基石。21世纪韩国民俗学者在构建城市民俗学宏观理论体系时,大多在论及这场学术争论,即支持/反对一方或总体评价双方后,再提出个人观点。朴焕英在林在海所提出的城市民俗五种分类的基础上,结合美国民俗学家Dorson的分类,细化出城市民俗学的九类研究对象:(1)城市中存在的农村的社会民俗,如洞祭;(2)城市中少数群体的特有文化,如校园隐语与涂鸦文化;(3)城市中隐蔽存在的俗信文化,如校园祈考文化;(4)城市中的岁时风俗,如“双11节”;(5)城市中存在的多种城市传说,如学校怪谈;(6)国际婚姻引发的城市文化多元化;(7)多媒体与大众媒体中的文化创意与民俗诠释,如电视剧、电影中民俗元素的传达方式与诠释方法,以及观众对此的观看感受等;(8)贫民窟或城市街巷等特殊区域的民俗;(9)朝鲜民俗。
崔元晤认为:“林在海与南根佑关于城市民俗学的定位与研究合理性的争论为时尚早,因为在城市民俗学个案研究还未普遍展开的情况下,讨论过分抽象的理论问题犹如空中楼阁,实际意义不大。”因此,他在分析11套城市民俗志内容构成的基础上,指出城市民俗学的调查应由浅至深分为三个层次有序展开,即“城市与农村共存的传统民俗要素”“城市中独有的城市民俗文化要素”“现代城市的消费文化与大众文化”。随着研究层次的过渡,韩国城市民俗学也会如同日本城市民俗学一样,逐步从“都鄙连续体论”过渡到“城市异质论”,从关注民俗传承的群体转向个体。
在大部分学者聚焦韩国城市民俗学宏观理论构建的同时,部分学者与文化机构另辟蹊径,从微观个案研究出发,探索城市民俗学发展的可能,如金明子对城市岁时风俗的研究、金示德对城市葬礼的研究、朴景勇对城市集市文化的研究等。特别是郑衡浩对首尔龙山区六位居民个人生涯史的研究受到学界的关注,他指出:“城市民俗学不同于农村民俗学,研究结果会因选取的调查对象不同而产生巨大差异。农村地区的传统文化分布均衡,即使选取的调查对象不同,研究结论的差异也不大;但城市个体的文化背景不同,如果不在认真分析个体的生活经历与记忆以及其居住空间与谋生手段变化的基础上将调查对象进行分类的话,研究结论将没有意义,因此城市民俗学研究应建立在个人生涯史研究之上。”
2008—2009年,国立民俗博物馆与首尔历史博物馆联合对列为旧城改造对象的首尔儿岘区与定陵区进行了民俗调查,并出版发行了11部城市民俗志。调查者常驻调查区域,利用个人访谈与个人文书(ego-document)相结合的方式,采用“经验性民族志”的记述手法编写民俗志。这套丛书首次将“生活物质文化”纳入城市民俗学研究范围,得到了民俗学界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挑战以往城市民俗学风格(城市庆典与城市传说等)的积极尝试。
五、余论
20世纪70年代在“农村消亡论”中开始探索转型的韩国民俗学,至今尚未就城市民俗学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以及城市民俗的传承主体等问题达成共识。但是韩国民俗学者在反思本国民俗学史的基础上展开的理论探讨与个案实践,无疑为韩国民俗学的长远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与更大的空间。
随着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步伐的迈进,中国民俗学的研究领域也逐步从农村扩展到城市。中国城市民俗学的学术定位、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也正处于探索阶段。林在海的“城市民众论”立足民俗学的阶级性,将人文关怀注入城市民俗学研究之中;南根佑的“文化解构论”,关注FOLKLORISM的实践现场,将文化政治研究引入民俗学领域。这些理论体系虽然未必适用于中国,但可以为中国民俗学特别是中国城市民俗学的理论构建,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西北民族研究》2020年第3期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