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西方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早已对文学与神话原型的关系有了深入论证,学术史也说明众多民间体裁都能为科幻提供叙事模式和神话原型。因此,本文试图挖掘除了上述关联之外,神话与科幻的共通性以及新的研究视角。以最有代表性的《山海经》和《三体》为例,笔者认为,神话与科幻都是在时代理性和被时人认同的真实性基础上,运用“陌生人—王”(Stranger-king)模式,表达人类权力秩序与道德性的叙事。这些相通性能启发我们贯通思考从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智能革命的发展历程中,人类如何建构和表述“自我—他者”“自然—文化”的关系和文明法则。这也是今日再谈神话与科幻之时可以深耕之处。
关键词
神话;科幻;《山海经》;《三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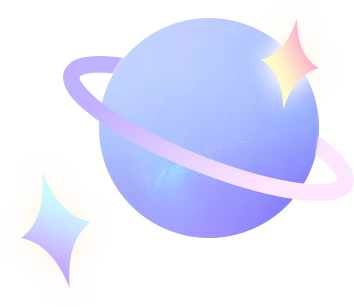
一、 神话和科幻有独享的共通性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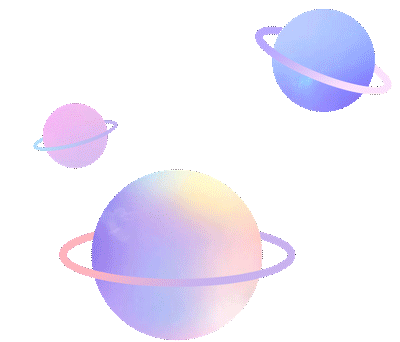
神话思维和神话原型、神话的深层结构和叙事模式能给科幻(文学或影视)提供宝贵素材和创作依据。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当数神话学大家坎贝尔(Joseph Campbell)对好莱坞科幻片的影响。博学广识的约瑟夫·坎贝尔因积极参加广播和电视访谈而在美国家喻户晓。他的系列著作,比如揭示了“神话原型”(mythological archetype)的《时空变迁中的神话》,以及阐述了“英雄行动的规律”的《神话的力量》,都是能打进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的学术著作。1993年,传奇大师沃格勒(Christopher Vogler)根据坎贝尔的理论出版《作家之旅》,总结出8种人物原型(Character Archetypes)和“英雄之旅”的12个阶段。此书被奉为好莱坞的“业界圣经”,科幻经典《星球大战》故事情节便来源于《千面英雄》的“英雄”模式,导演卢卡斯甚至说,“《星球大战》就是基于坎贝尔的理念创作的现代神话”。坎贝尔与沃格勒、卢卡斯的思想邂逅,缔造了神话与科幻之间最成功和典型的联盟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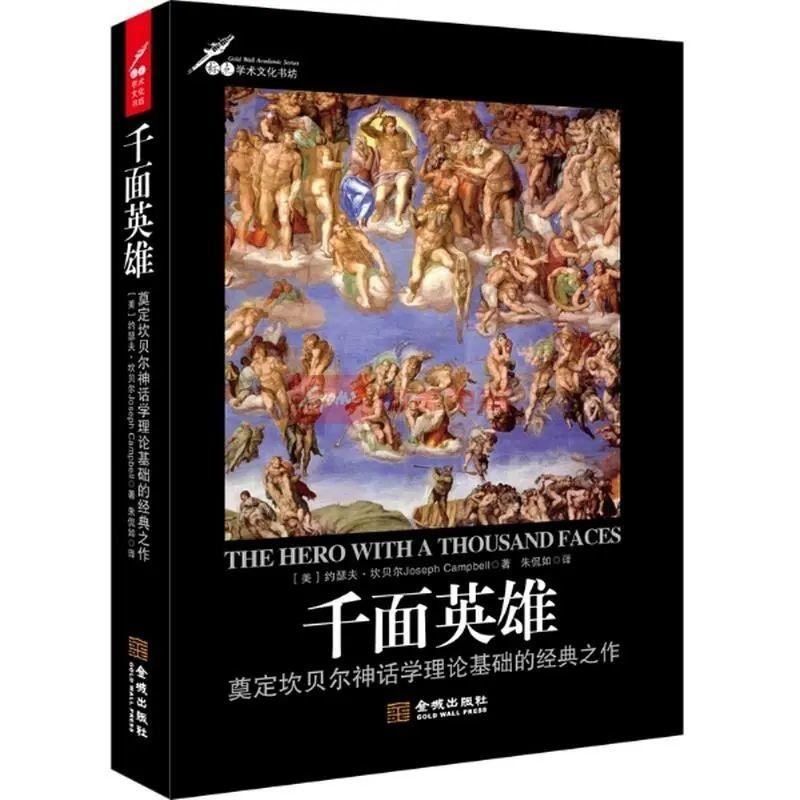
然而,在各种文类中,只有“神话”能够输出(或者优先提供)叙事理念、结构模式和文化原型吗?
我们先把目光前溯到19世纪中期。1864年,德国的冯·哈恩(Johann Georg Von Hahn)根据搜集的民间叙事诗归纳出16个共同的情节单元和基本公式。1881年,艾尔弗雷德·纳特(Alfred Nutt)根据凯尔特民族的14首英雄叙事诗对哈恩的公式做进一步修改。1908年,丹麦的奥尔里克(Axel Olrik)提出建立“系统的叙事科学”,并归纳出13条口头叙事法则。1909年,奥托·兰克(Otto Rank)从精神分析角度撰写《英雄出生的神话》为哈恩作出旁证。1928年,俄国的普罗普(Vladimir Propp)在《民间故事形态学》中归纳了不同英雄故事的结构和形态,影响甚广。在这些研究基础上,1948年,坎贝尔的早期力作《千面英雄》聚焦不同文化共有的英雄冒险故事,提炼出共同单元情节进行原型研究。
可见,不仅神话和神话学,百余年来,各国学者从民间传奇、传说、故事、史诗、叙事诗、仙话等文类中不断尝试总结共通的文化心理和叙事模式。或者说,围绕共同结构、想象心理、人物原型等问题形成了一个概念丛,它们与神话有关,但又不仅是神话。相应地,神话学、故事学、形态学、民俗学、主题学等都能给科幻或评论创作提供大有裨益的灵感与素材。同时,半个多世纪以来,文学与神话的关系是西方文学批评的重点问题。20世纪50年代,原型批评的代表人物弗莱(Northrop Frye)在《批评的剖析》中论证了一切文学的源泉是原型,揭示出文学对应于神话的内在结构,并与自然更替相呼应体现出的循环模式。20世纪70年代,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从陈词到原型》中从技术与媒介关系立场出发,认为原型包含在“陈词”(Cliche)中,能通过“经验的储存器”——语言在口语媒介、文字媒介、电子媒介中反复出现。
这些文学批评和文化理论研究已然深入挖掘了神话原型和文学叙事的关系。然而,我们不禁要追问:既然许多民间叙事体裁都能为科幻创作提供养分,那么,神话与科幻之间有特殊的共通性吗?既然神话与文学的关系已无需过多证明,今日再谈神话与科幻,能否找寻一些新的理解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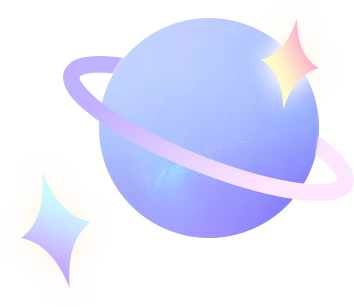
二、以《山海经》和《三体》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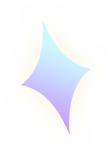
上述设问的答案是肯定的,限于篇幅要求,笔者仅抛出典型的案例掠影——中国神话学最重要的文本《山海经》和在中国科幻界最有名的《三体》。两者属性貌似迥异:作为实地考察和异域想象而记述的山川博物志,《山海经》是诉求共时性描述的王室典籍,没有一以贯之的跌宕叙事和人物模式。《三体》系列是精心编织的故事,是着眼于历时性发展的宇宙图景描述,且未曾听闻作者提及其创作受惠于《山海经》启发。这样的神话与科幻可能有关联吗?跳出常见思路,从两者的本质属性角度能窥得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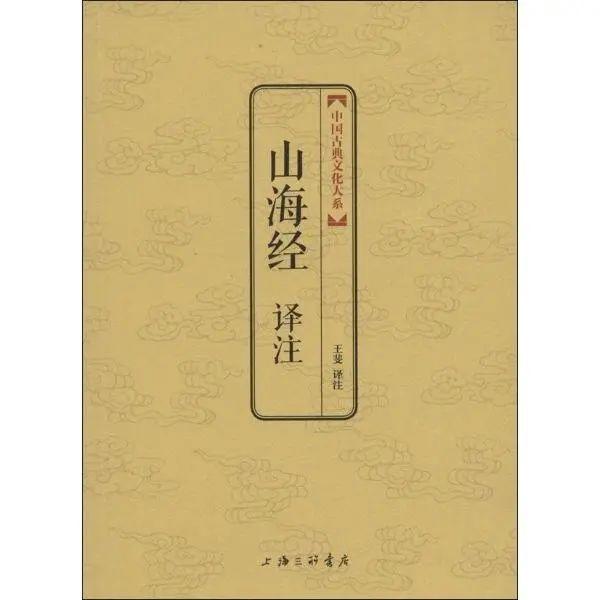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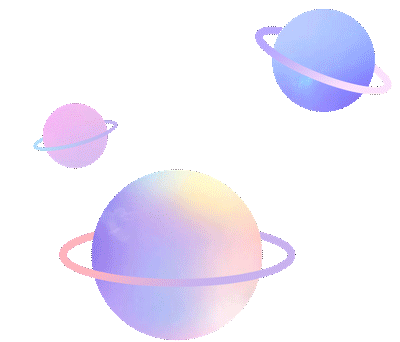
《山海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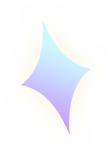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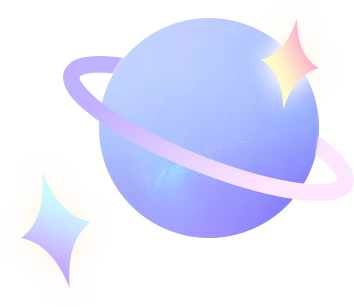
《三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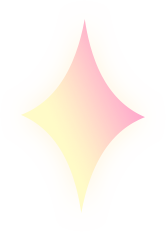

第一,相似的价值诉求:表达权力秩序和道德性。《国语·楚语上》记载了周王如何被各类巫史分工督导,不同的王室典籍如何发挥文化功能:“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故天子听政,使公卿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山海经》本质是宗周统治制度下的王官之书,掌握文字特权的巫史们通过地理和博物记载来表达王权对版图的掌控,维护宗周分封疆域秩序和华夷价值之辨;同时也督查周天子“事行不悖”。换言之,传统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巫史对世界的认识和表达方式。《山海经》所记的神、怪之物与所记的金玉、山川、河流、植物的属性相同,皆为象征王制。在巫史“物占”模式下,神异之物在特定时间的特定表现被视为天子或国家的凶吉征兆,天下之“物”都与王者之“德”有关。所以,对权力秩序的道德性象征与隐喻是《山海经》的特质之一,《春秋》《尚书》等宗周典籍所记的事、物、人、神,性质皆然。
对权力与秩序的道德性追问,同样引导和规范着刘慈欣对宇宙图景的想象,表达出他对人类生存境遇的理解。《三体》情节构思凸显了两个向度的道德性:1. 零道德的宇宙权力与秩序;2. 有道德的人类权力与秩序。有道德的人类如何在无道德的宇宙中生存?这是三部曲最扣人心弦之处。《三体》将人类社会放进极端的宇宙环境中考量,对权力与政治的明示或隐喻无处不在,比如从第一部的秦始皇开始,到红岸基地,到第三部中的PIA,再到掩体纪元中环星城和各个联邦组织,人类的权力与秩序没有丝毫温情脉脉,铁腕和极权是贯穿始终的氛围。零道德的宇宙更无比黑暗残酷,高级文明的歌者可以撕毁一切,人类的尊严荡然无存。极端的前者就是残酷的后者。极端性和零道德下,一切的文化、信念、坚持、挣扎都在为更绝望的权力秩序作出注释。在两千年前的王室记述与当下的文学描述之间,我们看到了历经岁月长河变迁却无法被洗涤的、相通的终极性叩问与呼应。
第二,相似的描述基石:时代理性和被认同的真实性。所谓理性不仅仅指现代科学和工具理性,从刀耕火种时代开始,古人在仰观天象、俯察万物和占卜祭祀中探索万事万物之规律,建构出诸多因果自洽的理性话语,比如月令系统、“周易”六十四卦、星占说、五行说、六道轮回说等等。作为表达权力秩序的王室档案,《山海经》既非完全客观的地理描述,也非纯粹主观幻想的创作。《山经》是巫史以四周的山为定位,参照天文、地理与历史传说对已知疆域和未知领域的描述;脱胎于祭司祭词(或创世图画)的《海经》有着与巫史相通的文化职能,在统治文化中起着上通下达、协调内外、知晓天地的作用。在汉武帝推崇《禹贡》之前,《山海经》一直被作为真实的记录,它的“四海八荒”模式具有权威性而被《楚辞·天问》《淮南子·地形训》《吕氏春秋·求人篇》引用。《山海经》用统治者的权力意志和那个时代的理性话语,为时人描述了一个被认为真实的世界。
作为成熟文学样式,科幻作品圈和评论界已形成判断“科技”使用优劣和高下之分的标准(即所谓的“硬科”分水岭),也形成普遍的文本情节流程。譬如《三体》在“设置悬念——推动悬念——渲染气氛——终极解谜”的流程中以瑰丽的科技发展想象来推动情节。不可忽视的是,《三体》之所以在“硬科”界内外都被叫好,乃因作者对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逻辑推演令不少人信服。全书在宇宙大爆炸和坍缩的天文学框架下,以光年作计算、以基本粒子为尺度去探讨权力秩序与道德问题,用逻辑自洽的科学理性思维,文学化地营造出一个令读者沉浸于其中的真实未来。
第三,相似的记“异”目的:“陌生人—王”(Stranger-king)权力模式。《山海经》记载了三千多个地名、四百多种植物、一百多种金属的矿物、四百多座山、三百多条水道,二百多个神话人物、三百多种怪兽。因此之故,围绕“异”去猜想或研究《山海经》内容所指是许多爱好者和研究者的热门首选。《三体》具体内容也是各种“异”:人类遭遇其他星球文明和不曾知晓的宇宙法则。其实,纵观所有优秀科幻作品,必然有异于地球文明和人类形象的他者世界,一个不曾被把握的神秘对象出现。
描述异于自我的叙事文类众多,但学者们发现围绕神话的记“异”却颇具意味。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名著《历史之岛》中通过考察南太平洋诸岛的土著文化,尤其本地人关于欧洲入侵者的各种神话传说,发现许多地方统治者的权力起源正是外来的陌生人。在当地人眼里,这些陌生人带着生与死的神秘性而具有超越力量,统治者通过一定的转化仪式,让内部社会的权力建构可以通过陌生人介入而得以稳定强化,这就是“陌生人—王”模式。萨林斯的立论前提是以血缘关系的原生族群为“内”,其实也适用于宗周王室的分封权力基础。虽然周王没有被入侵或与“陌生人”进行婚姻联盟或仪式转化,但是,王制需要用陌生的、异质的因素来自我神秘化,通过对未知异域的描述来表达权力版图,巩固自身统治。不妨讲,具有同质性的政治共同体永远需要对陌生人的想象与转化,需要借助与陌生异族和异域的沟通来实现自我权力的合法化。
当代文明和民主政治不再需要借助“陌生人—王”来形塑,但是,当科幻作家要对人类未来或外星文明进行权力想象、要对人类秩序与道德进行反思之时,自然而然地会使用“陌生人—王”这一思考模式。无论在农耕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还是智能时代;无论王室档案还是个人文学写作,大凡涉及表达权力与秩序的文本都在某种程度上与《山海经》相似,常能看到记“异”内容及“陌生人—王”模式的运转:周代分封制下的《山海经》《穆天子传》如此,秦汉郡县时代的《禹贡》《史记》如此,工业时代的《鲁滨逊漂流记》如此,信息时代的《三体》亦如此。到了未来更发达的智能时代,当人机联体成为现实时,是否还需要借助这套模式去表达人类对权力的理解呢?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描述了彼时图景:“曾长期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瘟疫、饥荒、战争已经被攻克,智人面临着新的待办议题:永生不老、幸福快乐和成为具有‘神性’的人类。”赫拉利是历史学家而不是科幻作家,无需用模式讲故事。但是,当作家要为未来的AI文化构拟权力、秩序、道德等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时,“陌生人—王”恐怕仍然是无法规避的叙事内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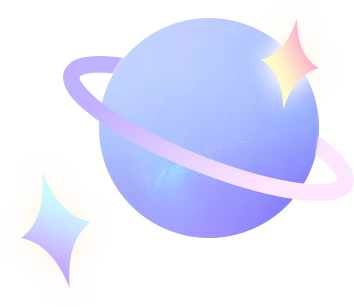
三、小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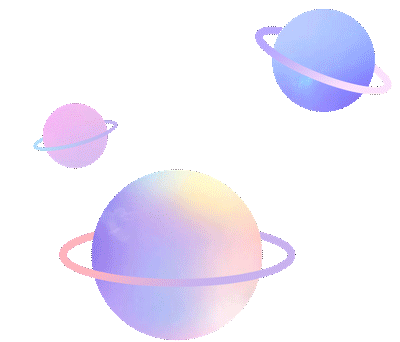
神话是过去的科幻,科幻是未来的神话。最近在国际科幻界大热的书籍《诸神与机器人》是一部突破性著作。作者安德林·梅厄认为当代世界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最先进的创新,其实早已在古代神话中有过预兆与先例;科学技术的发展往往由人类最狂野的遐想所驱动,这在古代和当今是一致的。不难看出,着眼于想象的神话研究持续地激发我们去思考人工智能时代的神话故事。但是,在行文中,笔者一直避免过多使用“想象”,而尽量使用“描述”。因为笔者想强调,悬置可供分析的叙事模式或原型问题,不从已有的神话与文学的对应关系入手,即使分析貌似最不同的《三体》和《山海经》,我们仍能看到,真正的神话和优秀的科幻除了都具备想象要素,还一定最能体现人类的权力秩序与道德性,运用当时的理性和权力模式,有着能被时人认可的真实性。比如,中国有《搜神记》《述异记》《太平广记·妖怪类》《太平御览·妖异类》《聊斋志异》等专门记载神怪的想象性叙事典籍。然而,只有《山海经》是王官之书,也只有在《山海经》的时代,统治者和民众相信它的描述是真实的。在真实性面前,《山海经》与《三体》并非简单的想象文本。甚至可以说,在各种文本形式中,只有神话和科幻对一切社会形态来说均可接受,是一种“没有反对的力量”(黑格尔语)的叙事。人类永恒的叙事主题终究是有关自身(人性与道德性)和群体(权力与秩序)的故事。天地如何产生,人类从何而来,文明何时毁灭,人间秩序和道德性是什么?神话和科幻都能用自己的方式描述出一个被相信和接受的图景,字里行间承载着描述者对文明、政治、信仰和道德的理解。在这层意义上,神话与科幻是最紧密的联袂体,只有神话与科幻能为人类的过去和未来建构法则,它们互通和碰撞的空间与启示将无可替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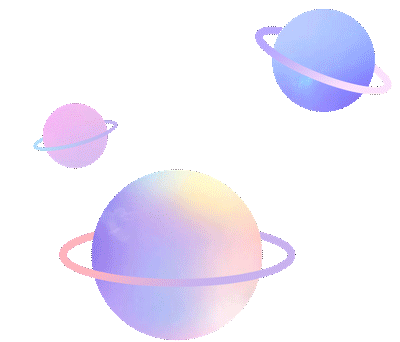
文章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06期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