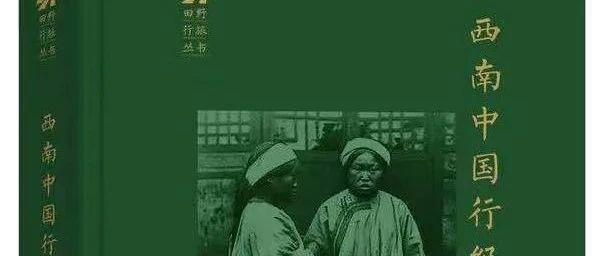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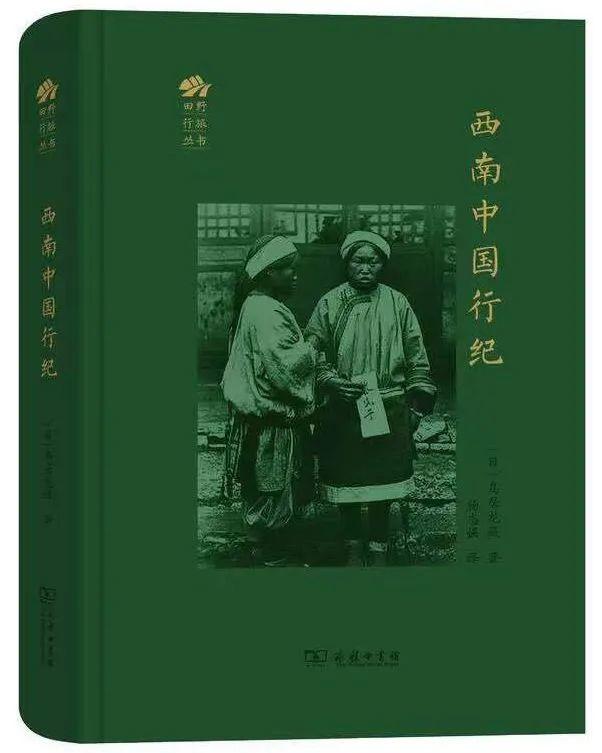
书 名:《西南中国行纪》
作 者:[日]鸟居龙藏
译 者:杨志强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年:2020
ISBN:978-7-100-18885-2
丛 书:田野行旅丛书
鸟居龙藏(1870—1953),日本著名的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东亚人类学早期开拓者之一。他一生的研究生涯中,涉足广远,著述丰富,曾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人类学研究室教授,后脱离大学成为独立研究者,晚年曾在北京燕京大学执教,系中国人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
1902—1903年期间,受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委派,32岁的鸟居龙藏只身来到中国西南,从湖南进入贵州、云南,继而北上四川,展开了一次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人类学旅行调查活动。《西南中国行纪》忠实地记录了鸟居龙藏此次调查的全过程,为我们了解百余年前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族群分布状态、族群关系乃至社会风貌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鸟居龙藏(1870—1953)是日本及东亚考古学、人类学的著名开拓者之一。其田野调查的足迹除日本本土外,还遍及内外蒙古、辽东半岛、东北、朝鲜半岛、东西伯利亚、中国台湾及西南等地,著述颇为丰富。这其中,1902—1903年鸟居氏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人类学调查,被视为外国人在中国进行的早期人类学调查的重要活动之一。
鸟居龙藏出生于日本德岛县的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从青少年时期开始,鸟居就萌发出对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浓厚兴趣。1886年,年方16岁的鸟居加入了成立不久的“东京人类学会”,并开始独立调查其故乡德岛县周边的石器时代遗存;17岁时他在《东京人类学会杂志》上发表了《阿波的古坟》等三篇论文,引起了当时在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的坪井正五郎的注意。1893年,坪井正五郎从欧洲留学归来,任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人类学研究室主任,随即邀请年轻的鸟居龙藏前来作他的助手。1894—1895年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日方称“日清战争”),清政府战败,被迫将台湾等地割让给了日本。为配合殖民统治的需要,东京帝国大学决定派遣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人类学的教授到台湾调查,坪井教授不愿深入险地,便将此项艰巨的工作交给了年轻的鸟居龙藏。接受任务后,鸟居先后四次赴台湾调查了山区各地和兰屿、绿岛等岛屿上的原住民,期间在《东京人类学会杂志》《番情研究会志》等刊物上连续发表了多篇调查报告和论文,开始崭露头角引起关注。1900年,鸟居龙藏结束对台湾的第四次调查后,便把目光转向中国西南地区的“苗族”。
当时“苗族”尚是一个泛称,类似于以往文献中记载“南蛮”,包括了中国南方几乎所有的非汉族群。鸟居龙藏之所以萌发出要去中国调查“苗族”的念头,是因为他在台湾调查土著民族期间,开始对大陆的“苗族”与台湾土著之间是否具有体质或文化上的关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感到需要通过实地调查来加以验证。为此他在完成了第四次台湾调查后,便向东京帝国大学提出申请,要求到中国西南地区调查“苗族”,获得批准。
1902年7月鸟居龙藏从日本横滨出发,开始了调查之旅,至1903年1月抵达四川成都为止,大约持续了半年多时间。除去旅途的耗费,鸟居在贵州、云南、四川三省逗留的时间大约有3个多月。在旅行期间,鸟居坚持每天撰写日记,回顾每天走过的路程,经过的驿站、城镇或村落,记录所经之处的所见所闻所感,如地质特征、风景、族群与民俗、建筑式样、往来行商、文物古迹、碑刻、民族/族群关系等等。在调查路线的选择上,当时从内地进入贵州、云南的线路实际上只有两条:一条是沿长江逆流上至四川泸州进入云贵,另一条则从湖南注入洞庭湖的沅江进入贵州;鸟居龙藏于8月中旬抵达武汉后,选择了从湖南进入贵州的线路。历史上,这条由湖南进入贵州的通道在文献中常称为“入滇东路”或“滇黔大道”,是连接云南与湖广内地的一条最重要的交通线路。鸟居龙藏进入贵州后大约逗留了一个多月时间,接着到云南后调查了滇池以南路南、弥勒等地的彝族;随后从昆明出发,北上过大渡河,沿“灵关道”古道一路冒着寒冬风雪,经会理、西昌、雅安等前行最终抵达四川成都。鸟居龙藏的所选择的上述路线,自古以来就是连接内地与西南边疆的交通动脉,沿线族群众多,互动频繁,历史积淀丰富,为他此次旅行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调查素材。在西南地区的旅行调查中,鸟居从贵州省镇远到贵定一路上调查的对象主要是苗语黔东方言的“黑苗”支系,进入贵定后调查了现属苗族西部方言“白苗”支系;在贵阳以南的青岩和八番(应为定番,现惠水)调查了“青苗”“白苗”“打铁苗”和“仲家”等;在安顺一带除苗族外,他还与自称明代移民后裔“风头鸡”(今屯堡人)“里民子”(今穿青人)邂逅。此后鸟居龙藏行至贵州郎岱厅城首次 “罗倮”相遇后,开始进入彝语支各族为主的分布地域。在云南旅行过程中,鸟居一路上所遇对象大多是彝语支各族的“罗倮”,如“散密罗倮”“白罗倮”“黑罗倮”“阿者猡猓”等。此后鸟居从云南至四川的旅途中,除“罗倮”外,还邂逅了“傈僳”“西番”“水田”“古猔”等,在宁远(今西昌)、越巂(今越西)附近还看到西藏的僧人。

▲鸟居龙藏拍摄的安顺苗族青年吹芦笙
在鸟居龙藏一生漫长的研究生涯中,此次他对中国西南地区的调查,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涉足中国西南,但这次调查却对中日两国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本书作为鸟居龙藏的调查日志,无疑是了解百余年前中国西南民族社会状况的珍贵史料,另一方面对探究鸟居学术思想也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首先,从人类学的学术史上看,鸟居龙藏的此次调查,可以说是近代以来外国人在中国西南地区展开的以“民族”为对象的最初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活动。调查前,鸟居就精心设定了相关调查内容;调查途中,每到一地,他都尽可能地利用短暂的停留时间,采集当地的少数民族男女的体质数据,调查风俗、语言、服饰等;而本书逐日详细地记录了他每天旅行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次,鸟居龙藏的中国西南调查,其初衷虽是以“苗族”为重点,但他对“苗族”的调查大约只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其余旅途大多是在彝语支各族分布的区域展开。回到日本后,鸟居除了向校方提交《苗族调查报告》结题外,还陆续发表了多篇有关“㑩倮”的研究论文。他还曾计划撰写一本有关“㑩倮”的专著,然最终未能实现。然本书中则保留了大量有关“㑩倮”等彝语支族族群的记述,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这一遗憾。第三,鸟居龙藏是最早将摄影手段应用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东亚人类学家。1896年,鸟居在台湾调查中首次使用摄影器材拍摄各地的“生番”。其后在中国西南调查中,他共拍摄了400多张照片。这些照片,除《苗族调查报告》(1907)一书中收录了以贵州苗族为主的90张外,其余在云南、四川各地拍摄的“㑩倮”等族的照片却一直未有机会公开发表。1988—1989年间,东京大学组织专家整理修复了两千余张照片,其中确认鸟居龙藏拍摄的有1357张,与中国西南有关的尚存203张,近半数未曾公开发表过,其中就包括了在贵州、云南、四川各地拍摄的“㑩倮”“散密㑩倮”“里民子”等的照片。本书原版原仅附录有十余张照片,此次籍翻译出版的机会,译者根据书中记载的相关场景,尽可能将这些图像资料都收录其中。第四,鸟居龙藏的此次调查从动机上看,最初系因怀疑台湾“生番”与中国大陆“苗族”有关而促成的,但结果却反而促使鸟居开始思考中国西南诸族与日本民族起源的关系问题。其后,鸟居龙藏在《史前的日本》(1918年初版,1925年修订版)中提出了日本文化起源复合论说,其中专门列出一章讨论了中国西南罗倮和苗族。鸟居有关中国西南民族与日本的关系之议论,其后虽经学者的不断修正,然对战后日本的比较文化研究,尤其是1970年代以后兴起的探讨日本民族复合起源的 “照叶树林文化圈”学说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本书中,鸟居对西南诸族与日本民族的关联性屡有记述,可以捕捉到其上述思想形成的端倪和过程。第五,此次中国西南地区的调查促成了鸟居龙藏学术思想的重要转变而影响至今:一是他在调查前后,通过接触汉文献有关西南少数民族的记述,深感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结合的重要性而不断予以强调,此后也成为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之一。二是这次中国西南之行还促成了鸟居龙藏由体质特征向文化风俗研究的转变。由于中国西南各非汉族群文化早已超出“种族”界限而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复杂样态,这使得鸟居龙藏感到以往以体质特征作为界定“民族”标准带来的局限,从此便转向以文化习俗为重点进行研究,这无疑具有前瞻性而超越了同时代的许多学者。鸟居上述注重“文化”研究的思想在本书中也得到充分的体现,其内容大多涉及“风俗”记载而甚少有体质测量方面的数据,书中还具体记录了鸟居在旅行中搜集文献的一些情况。
鸟居龙藏的中国西南之行的影响除上述的学术层面外,因其时间恰好与世纪之交中国兴起的“种族”言说和“排满兴汉”的民族主义运动发生交叉,因此他结束调查回国后密集发表的相关报告及论文也引起了在日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鸟居龙藏的西南调查成果,作为一种“客观”的知识体系,通过这时期在日中国知识分子“种族”言说的展开,也共时性地参与到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种族”言说流行和民族主义运动兴起过程中,“苗族”曾是中国知识界乃至舆论探讨的话题之一。其背景与当时流行一时的“汉族西来说”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的“汉族西来说”,指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的各种有关汉民族起源历史的学说;这些学说大多认为汉族并非中国的原住民,而是自西方迁徙而来,故统称为“汉族西来说”。在汉族迁入以前,一般认为原先占据中原的土著民族是“苗族”,由此形成了与“汉族西来说”对置的“苗族土著说”。如果以1902年章太炎等人在日本横滨成立了“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念会”为分界点,可以看到无论是此前“种族”言说的传播,还是之后“汉族西来说”的流传和“排满兴汉”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苗族”都被视为一支充满悲情色彩的古老民族。这时期,章炳麟、梁启超、邹容、刘天华、孙中山等近代著名人物的相关论说中,几乎都屡屡涉及到“苗族”。
然而在现实中,留日中国知识分子却对“苗族”的分布、语言、文化等都缺乏最基本的了解,这也使得他们亟欲了解中国南方非汉族群的生存现状,而此时鸟居龙藏的西南中国之行可谓恰逢其时,他回国后发表的一系列调查成果很快引起了当时在日中国学人的高度关注。这些学者除吸取有关西南非汉族群的分布、支系、语言、风俗等知识外,鸟居提出的西南非汉族群的分类观点也为他们所接受。这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鸟居龙藏
首先,鸟居龙藏根据他的调查,回国后一直强调的应将“苗”与“罗倮”(夷)视为两大不同的“民族”集团,他的这一分类得到了梁启超、蒋智由等学者的高度认同。进入民国以后,在学术研究乃至政治话语层面上,中国南方非汉族群的泛称不再只谈“苗族”而改称“苗夷民族”或“夷苗民族”。
以往汉文献记载中往往将“罗倮”视为“苗”分支,置于“苗种”框架内分类和表述,但鸟居龙藏在调查中发现,“罗倮”不仅在体质特征上与“苗族”差别颇大,在语言、建筑形式及风俗等方面也都明显不同,由此他认为应将“苗族”与“罗倮”(“夷”)明确地区别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结束回国后,鸟居龙藏除出版《苗族调查报告》一书外,还发表了《清国云南猡猓调查》(1903)、《猡猓的文字》(1903)、《关于苗族与猡猓》(1903年)、《人类学上的调查报告(清国西南部)》(1905)、《猡猓种族的体质》(1907)等多篇论文,专门介绍了分布在云南、四川一带的西南各地的“罗倮”或“夷族”,即现今属彝族各支系的情况。在这些论述中,鸟居龙藏主张应将过去归类于“苗种”中的“罗倮”区分出来,视为与“苗族”不同的两个“民族”。在本书中,可以看到鸟居上述观点形成的清晰变化脉络。如他在贵州省郎岱镇初次与“罗倮”相遇,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初次见到罗倮,就发现不仅在外貌、肤色上都与苗族差别很大,而且语言也迥然不同。想来他们各自的祖先是不同的。这些罗倮与苗族在语言、体质及其他方面表现出来的明显差异,在人类学上可能是最具研究价值之问题”。此后随着在云南南部各地的深入,这一想法变得更为清晰和确定。在调查路南、弥勒、通海等地的“罗倮”后,鸟居龙藏最终得出结论:“总之,迄今为止在各地所见的散密罗倮、或黑罗倮、白罗倮、阿者罗倮等,虽冠以不同名称分布各地,然一旦从语言、体质上对他们进行调查则完全相通,毫无区别。因此,统括以上四者,将其总称为广义的罗倮理所当然,对此谁都不会有异议。然而至于苗族、仲家等种类,把它们和罗倮比较时,可看到在体质及语言上都有很大差异。可以说他们与罗倮并非同一支系,在此可得到确凿的证明”。
其次,鸟居龙藏认为应将“苗族”区分为“广义的苗族”(泛称)和“狭义的苗族”(族称)这两个范畴对后世影响巨大,事实上奠定了今天作为中国56个民族之一的苗族的外延范围。
在鸟居龙藏对“苗族”进行实地调查前,当时人们所理解的“苗族”而言,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其外延范围大致相当于以往的“南蛮”,基本上将整个中国南方的非汉族群都涵盖在内。就鸟居龙藏自身而言,他基本上也是把“苗族”视为一个“种族”群体而非现今文化意义上的民族集团。1907年,鸟居龙藏基于此次调查出版了《苗族调查报告》一书,首次提出应将“苗族”区别为“广义的苗族”和“狭义的苗族”这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基本上沿袭传统上将中国南方几乎所有非汉族群,如壮、侗、瑶、罗倮(彝族)等泛称为“苗”的习惯称谓,后者则将“黑苗”“红苗”“青苗”“花苗”“白苗”“打铁苗”以及“仲家苗”(现布依族)界定为真正的“纯苗”,并指出上述不同支系的“纯苗”地理分布范围。鸟居龙藏提出的“广义的苗族”与“狭义的苗族”这一二分法对后世影响深远,但他的根据从何而来却不甚明了,在《苗族调查报告》中鸟居除指出:“凡与彼等接近者,莫不知之”一笔带过外, 基本上看不到进一步的解释。这也给后来的中国学者带来了困扰,如1936年《苗族调查报告》被译成中译本出版后,民族学家江应梁在发表专文给予高度评价之际,唯独对“广义的苗族”和“狭义的苗族”这一分类认为毫无根据且不可理解。在本书中,也可以看到鸟居这一分类的一些痕迹。如他对云南弥勒县彝族调查中最初提出的是“广义的罗倮”,但其后发表的研究中却未进一步区分。总的说来,鸟居龙藏对“苗族”提出的二分法以及由“体质”向“文化”的方法论转向,可能正缘于他在此次调查过程中的感受及认识所致。因为中国西南地区的多样性文化及复杂的族群边界往往突破了以身体自然特征为第一义来界定“民族”边界之传统框架。由鸟居龙藏首先提起的“狭义的苗族”之范畴,虽然根据不明,但从结果上看,基本上奠定了现今苗族的外延“边界”。
本书成书于20世纪初叶,距今已有百余年的间隔。然作者注重对西南诸族“风俗”的观察与书写,超越了当时“种族”“民族”混同的时代桎梏,价值愈久而益显,至今仍然是日本中国西南研究的必读文献之一。本书原名『人類学より見たる西南支那』,1926年初版发行,文字为日语文言体。1980年,日本学者因该书高度的资料价值,遂将文言体改写为现代文体,删节部分与西南旅行无关的内容后,由朝日新闻出版社更名为『中国少数民族地帯をゆく』重版发行。本书在翻译过程中以1980年版为主译本,并参照1926年版勘误和校正。书中涉及的沿线的汉字地名译者予以保留并尽可能考订,使用平假名注音者译者改为拼音注音,一些有明显错误的地方,译者改正后并附以说明。因书中所记地名达数百个,难以一一考订,只能留待今后弥补这一缺憾。此外,从时间上看,鸟居龙藏的此次中国西南之行正逢满清政权摇摇欲坠的动荡时期。鸟居作为日本的官派学者,其旅途中对官府颐指气使,对民众恐惧蔑视,对少数民族充满歧视的态度也屡屡跃然纸上,对此读者自可辨之。原著表述的“中国”原为“支那”,“罗倮”为“猡猓”,编辑过程中经协商根据语义统一置换为“中国”“汉人”等词,书中族称汉字反犬旁一律改成人旁,如此类推,特予说明。
经湖南溯沅江向腹地进发:汉口—黔阳
旅行之目的和出发旅程
舜与苗族
欲剃度穿法衣
抵武陵县
武陵桃源的传说和游览
参拜伏波将军庙
辰州风俗
由辰州至西风潭
中国与杨柳
关帝庙观赏戏剧
行船日渐艰难
黄献珍氏之宴会
由洪江司至连州
抵达黔州
迈向贵州苗地:黔阳—施秉县城
由陆路向贵州进发
罗薄甸至沅州城
歇宿便水
湖南最边之地
贵州省初见苗族
贵州风俗
苗族与汉人
青溪县
目睹苗族抵达镇远
凭吊汉苗冲突之遗迹
山路通行状况
苗族老妇
施秉城
意外展开的汉苗交流:施秉县城—安平
进入苗地
苗族村落
新黄平城
重安周边黑苗风俗
地理形势与苗族生活状况
花苗风俗
贵阳府与仲家苗
黑苗、青苗与打铁苗
八番苗族调查
被抛弃的明代遗民:安平—资孔
明代遗民凤头鸡
安顺府的位置与青苗及其传说
安顺花苗及其纹样与乐器
花苗风俗
探索古代文字途中之仲家苗种
红岩山古文字与罗倮之关系
诸苗与里民子
朗岱诸支系
初遇罗倮
仲家苗与市场
从毛口站至花贡
罗倮、回教寺院和法国人:资孔—云南府
进入云南
患甲状腺肿大病症的人们
霑益州城
云南省及其他地区之“石敢当”
马龙城和知州
知州阅兵与忠象碑
关索岭
回回教寺院
云南地方茶园
媲美江州濑田之景色
云南府附近地形及散密罗倮等
抵达云南府城
云南府城见闻
云南府古代遗物
法国人之势力
追寻罗倮南下云南腹地:云南府—弥勒县城
迈向云南省南部的第一步
春秋相聚之景致
七孔关坡至路南
邂逅罗倮
罗倮调查
迈向路南
进入路南罗倮地界
珠江上游的罗倮
花口附近仲家苗
弥勒县附近罗倮
花苗、黑罗倮和阿者罗倮:弥勒县城—云南府
迈向通海途中之花苗
石狮与花苗房屋
十八砦之罗倮
黑罗倮村落
阿者罗倮村落
婆兮市街
宁州与阿者罗倮
终于走向通海和途中之罗倮
通海至路居村
“setanmu”之黑罗倮
云南铁路计划
花是何时开
陶器碎片与穴居士兵
类似岛田髻之发髻
滇池
选择“危险之路”迈向四川:云南府—金沙江司
调查罗倮和迈向四川
由云南迈向四川省的风流之罪
“nasipu”之单词
临近四川省
踏霜翻越重岭
冷饭店之罗倮
路遇傈僳
武定县所见少数民族
相遇苗族
武定县和附近之少数民族
旅行中最高地附近之少数民族
马鞍山和灵仁之罗倮
罗倮与花苗之风俗和白罗倮词汇
半汉半罗倮之居民
本日所经之地貌和民众
随地势起伏而变化之风俗
金沙江司
类似铜铎图纹的罗倮土俗:金沙江司—会理州城
渡越金沙江途中之光景
姜站
白罗倮土俗与日本出土铜铎图纹之关系
途中光景
“alai”村罗倮和类似日本出土铜铎上图案之风俗
途中状况
从绿水河至川心店
邂逅傈僳族并至凤山营
途中光景
从凤山营至会理州城
会理州城
罗州山上的黑罗倮
调查罗倮
送别会与忘年会
万里异域迎新春:会理州城—宁远府
汉化之白罗倮
由白夷村落至白菜湾
异域赏樱
“fupiu-ku” 之阴阳石
沿途调查少数民族
途中光景
山村集市之罗倮
沿安宁河至宁远
三人白夷
调查西番
调查古宗和黑夷、白夷之词汇
途中相遇者皆系夷人:宁远府—越巂城
从宁远府至礼州城所见后汉古砖
邂逅西番
途中光景与罗倮
遇见水田
庐鼓站
旅途相遇者唯有夷人
黑白两罗倮之土俗
银色世界中旅行所见之光景
本日所见罗倮之土俗
地形概貌
越巂城附近之罗倮
越巂城
雪中所见汉夷冲突之故地:越巂城—大相岭
访问罗倮村落
西番村落
到达保安
途中所调查之项目
各族之跳梁和防夷之设施
西番村落
深奥溪谷与聚落
途中之罗倮、西番和汉人
罗倮与汉人混杂于雪中旅行
住居高山之汉人
途中之人类学观察
汉夷冲突之古战场
大渡河和富林场
唐家塘
沿路之石敢当
清溪县城
汉夷分界线之大相岭
大关山和二台子
黄泥堡
汉藏之交汇地点
荣经城和鹤田寺
鹤田寺及其周边
回归蜀地、汉人世界:大相邻—成都府城
汉夷分界线之大相岭
雅州府城和民族分界线之大相岭
雅河流域和渐近蜀地
名山县和百丈站
酷似武藏野之各地农村及其他
冲积层平原、义冢与中国人之公益心
浓雾中迈向蜀都
途中光景
成都府城见闻
连绵江岸之“蛮子洞”:成都府城—重庆
告别成都赴重庆
船中赏梅
锦江沿岸之“蛮子洞”
河口之“蛮子洞”
如画之江山与横穴之分布
“蛮子洞”是穴居抑或坟墓?
巨佛雕刻
由岷江向长江
小狗罗㑩之死
泸州及其附近
正月之气氛
驾舟行进
巴之故地重庆
重庆之“蛮子洞”
成都出发以来“蛮子洞”与日本横穴之比较
重庆所见之少数民族
出领事馆至舟中一宿
附录:
人类学上我的西南中国之行意欲何为?
本书解说
译后记
图文来源: 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2020-11-17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