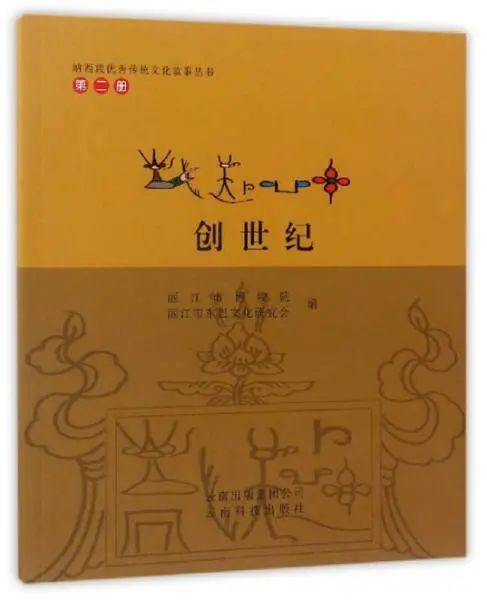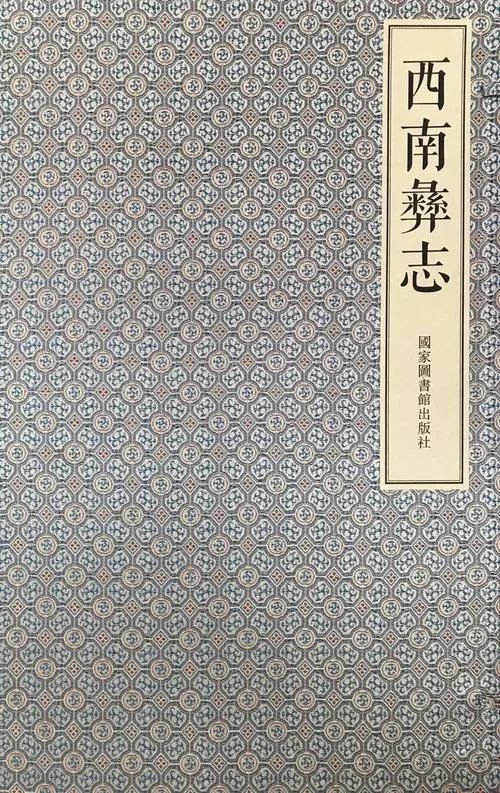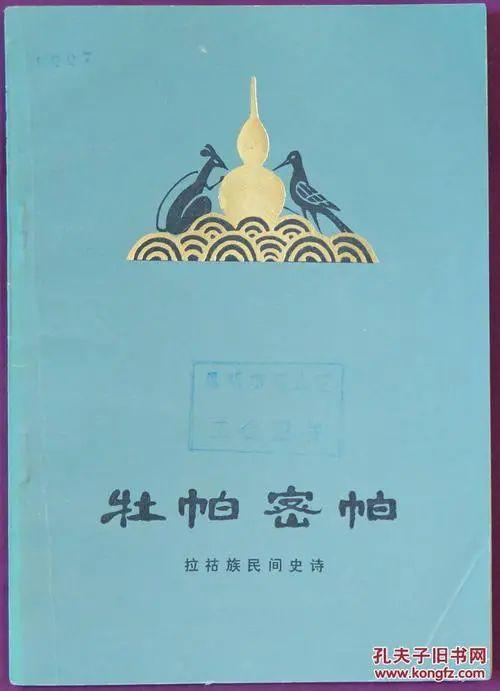摘要
西南彝语支民族拥有极为丰富的神话史诗文本,其中蕴涵着久远的原始观念意识和神话母题。本文梳理了彝语支民族原始共同神话的形态与文本,阐述了探寻其“神话母题”的文化意义及学术价值。为运用多学科方法研究西南少数民族神话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关键词
彝语支民族;共同神话;神话母题传承
作者
黄泽,云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云南大学神话研究所所长,博士生研究生导师。
西南彝语支民族即彝、纳西、哈尼、傈僳、拉祜、基诺、白等民族,渊源于有着共同文化、语言亲缘关系的古代氐羌族群或先羌民族集团。早在距今约四千年前就已奠定了族群的共同文化基因,其主要载体之一即原始共同神话,它们依托于原始宇宙观、原始神灵信仰、祭司阶层、祭祀道场、经籍而延续至今。从古代曾居于藏彝走廊北端的甘肃、青海,到现今南至金沙江流域、红河流域、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现今已大分散远距离迁徙分化的彝语支各民族,仍表现出强烈的原始文化记忆及其共同性特征。从文本来看,彝语支民族原始共同神话主要以原始宗教祭祀经典即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史诗为载体,表现出原始观念或神话母题的一致性,具有超越时空的特性。因此,在大量族别的、个案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从比较神话学的角度分析彝语支民族原始共同神话的学术价值,能够推动西南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的深化。

一、彝语支民族原始共同神话的文本及母题
彝语支民族是西南地区素有史诗传统的文化集团,口传及文字形态的史诗富集,文本丰富、异文较多。纳西族的《创世纪》《崇搬图》(又名《人类迁徙记》),是其祭天道场上由主祭东巴吟诵的东巴教经典。彝族《勒俄特依》被视为凉山彝族圣经,为毕摩拥有的彝文毕摩经书,《西南彝志》为流传于贵州毕节、大方、威宁等地的毕摩经书,《查姆》为流传于云南双柏等县的毕摩经,《梅葛》流传于姚安县马游乡及大姚县、永仁县一带,其“老年梅葛”部分后来被整理为史诗《梅葛》,依托于梅葛调演唱,富有音乐性和表演性。拉祜族《牡帕密帕》为非祭司的歌手传唱的口传史诗。哈尼族的《烟本霍本》《十二奴局》《奥色密色》《哈尼族古歌》等也是由哈巴(歌手)吟唱的口传史诗。呈现出文本形态、吟唱方式、吟唱者、吟唱场合的差异。
除以上通常被称为神话史诗的文本外,表现彝语支民族原始共同神话的文本还涉及哈尼族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及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鲁》等。至今一些流传在民间的散文体神话,则可能是以上史诗集群文本内容的流散、传播及衍异。
彝语支民族原始共同神话是从这些宗教经典、史诗、神话中比较归纳得出的。从文本形态及演述场合的演化来看,大致呈现三种状况:
其一,以纳西族祭天经典《创世纪》(《崇搬图》)为典型,东巴祭司居于社会结构顶层,主持全氏族、全民族祭天大典,以祭天群(各氏族组织)为社会基本结构。各祭天群由世袭祭司东巴执掌祭天、祭署、祭风等三大道场,拥有解释经典、宣谕原始观念、规范约束世俗人群行为的现实职能,神权大于王权。祭天经典与祭天仪式构成神话—仪典学派所述的相互阐释、对应或支撑。由于纳西族在彝语支民族中居住地相对集中于滇、川、藏交界的金沙江流域,至现代才被分割成东部、西部两个方言群体并分化发展。纳西族又处于藏、白、彝等民族交错地带,居住地狭窄而集中,未发生南向的大规模迁徙,因而封存了彝语支民族原始共同神话的活化石,文本形态和演述场合变异最小。
其二,以彝族尚依托于毕摩经书的《勒俄特依》《西南彝志》《查姆》《阿细的先基》为典型,虽仍由祭司毕摩在祭祖、丧葬等重要场合吟诵,但已失去全民参与的神圣性,而转化为由掌握文字的毕摩世代传承的历史典籍、天文地理类经书,其内容渗入英雄祖先业绩、部落分支、技艺传承、征战等后世内容。
其三,以《梅葛》《牡帕密帕》《烟本霍本》《奥色密色》《十二奴局》等为典型,已失去全民祭祀的神圣场合,缺失了至高无上的祭司主祭仪式,其社会阶层中已缺失了祭司,而代之以歌手,甚至出现以年龄分层的大众歌手,世俗性增强而神圣性荡然无存。内容上则添加了文化发明、生产技艺、历法气象物候、婚恋习俗等知识传承。《支格阿鲁》以英雄祖先降服妖魔、征战四方、开疆拓土为荣光,《哈尼阿培聪坡坡》着眼于民族起源地到现居地之间时空跨度极大的迁徙历史,这些文本表现原始共同神话的职能减弱,后世添加、变异内容增大。
以上分析,主要是以彝语支民族原始共同神话的神圣性逐渐弱化为线索,以三种类型的对比,拟设了最初氏族部落阶段演述原始共同神话的初始或典型形态,表现为史诗(口传或文字)、祭司、祭祀场合三位一体紧密结合的关系。后期之两种类型则表现为或祭司缺失或祭司兼歌手,或演述场合不再是祭祖、祭天等神圣祭仪。着眼于神圣性向世俗性的转变,或神权社会向王权社会的发展。史诗本身文本形态为口传抑或文字典籍并非要点,二者孰先孰后也不予讨论。也就是说,很难确定口传史诗与经籍史诗谁更早产生。当然,若同一史诗兼具口传、文字两种形态,则讨论二者源流及演化关系,就是可能且有意义的。
彝语支民族原始共同神话的母题大多依托于以上史诗中所蕴涵的原始观念、原始神灵信仰来体现,也可从“大的母题”“观念主题”或“神话原型”来理解。大致如下:
原始宇宙观
主要讲述天地形成,万物始生。如《创世纪》(《崇搬图》)讲述宇宙开初一片混沌鸿蒙,由气、声、云、雾、露等翻腾演化,天地创生,清者为天,浊者为地。其他彝语支民族史诗中也多有此类描述。又有天神创世之说,如纳西族天神子劳阿普、彝族天神格滋与恩体古兹、哈尼族天神阿培威嘴、拉祜族天神厄莎均代表了神权时代天神创造宇宙万物、奠定天人关系及相关伦理道德的形象。即如《梅葛》中造天造地的兄弟姐妹,也是天神所派或隶属天神家族。再有死体化生型创世观念,讲述虎、牛、鱼等创世奠定宇宙天地格局,具体情节史诗中均有表述。天梯神话及蚂蚁分天地等神话也表述了一些独特观念。

天神的正负形象
天神家族及其形象在早期的神权社会中借由东巴、毕摩等世袭(师徒、父子传承)祭司持续的定期祭祀而固化。他们代表着人间只能仰视、服从的神界、天界。天神创造宇宙万物,为人间带来福祉,理应受到赞颂祭拜。这时天神多为正面形象,而人类若触犯天条或懒惰、贪婪则遭天神惩罚,火把节起源神话中就有此类表述,彝语支民族打磨秋、打转秋之起源神话也有此类观念。但神权时代被以部落首领、氏族祖先为代表的王权时代取代后,天神转为负面形象。如格滋天神对人类的刁难,以及天神子劳阿普对人类始祖从忍利恩求娶天女衬红褒白过程中的刁难,以难题求婚、服役婚始,以祭拜天神才学会开口说话终,喻示人类社会发展到氏族部落阶段后,随着社会生产力提高,社会组织集约化增强,对氏族祖先、人类始祖的祭拜逐渐取代了天神家族。从天神为难、为害人类,到人类敢于向天神家族挑战的叙事表明了这一观念转变。
原始植物崇拜观念
在彝语支民族共同神话中蕴涵着一系列原始共同文化要素,这是基因,也是密码。具有文化观念和文化心理的初始性。纳西族《创世纪》(《崇搬图》)中清晰地表述以黄栗青㭎木象征天神,柏树象征许神即天舅。藏、纳西等族至今以松、柏树枝燃烧于白石神龛,祭祀天地诸神,俗称“煨桑”。纳西族摩梭人和普米族在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举行的“转山节”上以松、柏枝条燃烧祭祀狮子山女神(格姆女神)及女始祖“柴红吉吉美”,并连续投洒松香和五谷杂粮于祭坛,类似于周礼中的“燎祭”或“燔燎”。火把节以松树末、松香投洒燃烧祭祀天神、照田驱虫害。凉山彝族在老人去世后,要取房梁上的两根杉木做抬尸架,以杉树寓意灵魂归所。哈尼族素有锥栗树崇拜。彝语支诸民族都有“密枝林”“寨神林”等围绕树木崇拜的土地神、社神祭祀仪式。如路南彝族“密枝节”、红河元阳哈尼族“昂玛突”(祭寨神林)、绿春哈尼族的“阿罗欧滨“祭祀等。
西南地方民族文化研究开拓者之一徐嘉瑞先生较早便关注彝语支民族的树枝崇拜。基于大理古代文化源自甘青高原之古羌文化的认识,他例举了大理绕山林会上领队男子二人共扶高达六七尺的杨柳一大枝,以为朝圣队伍先导。“似与巫教杉、松、柽 、柿,同为代表最高之神”【1】,又例举了以树枝插于屋左上角代表已逝亲长灵位、以杉树枝插于方形石堆(即白石神龛)等川西羌民古俗,还以丁文江先生《爨文丛刻》中的《婚姻传》称松、杉为圣木、《天路指明》以 柽枝为圣石、《权神经》立九松、九杉、九柿于祭坛等贵州水西毕摩经典。又以方国喻先生《么些民族考》所云:“么些过年,以松枝植屋上祀祖”及《云南通志》所云:“丽江祀祖,于门外植栗树。”等材料力证“折松、杉、柽、柿以为神之象征,称之为圣木,插于石上,称之为圣石”为彝语支民族之原始共同信仰。【2】
此外,竹与葫芦是经常出现在彝语支民族神话及史诗中的生人或避水工具,也形成富有象征意义的母题、文本及相关习俗。

山神崇拜观念
神山圣湖崇拜是青藏高原特有的原生信仰,彝语支民族史诗中常出现此类神山。《勒俄特依》中说:“四根撑天柱,撑在地四方,东方的一面,木武哈达山来撑,西方的一面,木克哈克山来撑,南方的一面,大木低泽山来撑。”高山接着天,能撑住天,是神的居所或化身。又如纳西族史诗中提到居那若罗神山,东巴经《鲁般鲁绕》中说:“很古的时候,所有的人类都从居那若罗神山迁徙下来。”【3】人类未迁徙前,居那若罗神山四方,分别住着汉人、民家(白族)、古宗(藏族)、郭洛、盘种人、么些人、西番和武种人。【4】有学者推测与昆仑山崇拜有关,或是对贡嘎大雪山的祭拜。哈尼族史诗中的诺玛阿美等地都是神灵所居之高山高原。纳西族现居住地仍有梅里雪山、玉龙雪山、哈巴雪山崇拜,以及泸沽湖畔的格姆女神所居狮子山及周围男女山神祭拜。摩梭人以山神为始祖神,形成以柴红吉吉美为首的女神家族,与山神神话叠合。彝族自南诏后兴起的土主崇拜是以山神祭拜为载体的土地神、社神信仰,当有早期山神信仰的基因。南诏统治者基于辖境内众多彝语支民族属民的山神崇拜,而有封禅之举。胡蔚本《南诏野史》云:“异牟寻以点苍山为中岳,乌蛮(东川)乌蒙山为东岳,银生府蒙乐山为南岳,又封南安州神石为南岳,越赕(腾越)高黎贡山(名昆仑隅)为西岳,嶲州(丽江)雪山(一名玉龙山)为北岳,封金沙江、澜沧江、黑惠江、怒江为四渎,各建神庙”。【5】
以眼睛为象征的文化时代更替(换人种)
在《查姆》《尼苏夺节》《梅葛》《阿细的先基》《勒俄特依》等史诗中表达了生物进化论、文明更替论及原罪论。由于人种的更替、进化或人类的过失,早期人类经历过“以眼睛的象征”为标志的若干文化时代。横眼人时代已进入今天人类始祖开创的文明时代,如彝族始祖阿普笃慕最初娶四天女,后天地津梁断,遂实行兄妹婚。伊藤清司、张福三、傅光宇等先生均关注过这一文化现象。【6】但多局限于从野蛮人(独眼人、直眼人)到文明人(横眼人,以笃慕为代表)的分期。陶云逵先生在1935年进行了两个月的澜沧江及怒江上游碧罗雪山傈僳族调查,采录到一则人类起源神话,讲述换过三代人种。【7】彝族这一特殊观念也有民族史及考古学的材料支撑。如三星堆遗址(距今4500—3000年左右)2.6米高的青铜大立人和青铜纵目人面像,双目炯炯有神,均呈直立柱状眼珠突出,这是祭司法力的显现。三星堆遗址两个商代祭祀坑共出土54件青铜纵目人像及面具。或说蚕丛氏这位蜀国开国君王及其部族与纵目人有关。【8】也有学者认为直眼纵目象征鹰眼,能洞察天人之际,为祭司的象征。与相对空泛的史诗文本中的独眼人、直眼人、横眼人的表述相互参证,考古文化中的实证材料对直眼人的解读应较文化时代更替之说更可靠,具有更确切的释读可能性,值得关注。
“火把节”神话传说群及其观念
从“火把节”起源神话到“火烧松明楼”传说,再到现今彝语支民族最普遍的祭祀节日“火把节”,“火把节”神话传说群在彝语支民族原始共同神话中曾最受关注。徐嘉瑞先生所撰《大理古代文化史》初版于1949年印行,1963年中华书局以《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书名印行,书后还附有游国恩先生之《星回节考》。围绕火把节与火崇拜、天神崇拜、星回节关系的论文层出不穷。各地彝语支民族、各支系都流传着大同小异的“火把节”起源神话文本,当代学者所进行的传统节庆调查也注意到这一点。【9】
而自南诏国、大理国后出现的“火烧松明楼”传说,在“火把节”祭天祈年、火把照岁除虫害的“神话原型”和原有的天神崇拜、与天神抗争、火崇拜、星回节等历法星相观念之外,增益了部落社会生活、政治斗争的内容,甚至在某些地区或某些彝语支民族中出现“火烧松明楼”传说叠压遮蔽了上述原始观念的情形。【10】考虑到“火烧松明楼”传说已产生逾千年,涵盖面较广,故也可列入原始共同神话之序列。
九隆神话
徐嘉瑞先生《大理古代文化史》从大理古代文化与古羌文化的关系着眼,认为哀牢夷、昆明夷皆羌族。哀牢夷本居西昌(雟),其后进入永昌。由此九隆神话进入永昌。即哀牢夷与昆明夷同族,先后携九隆神话从西昌入永昌。蒙舍诏出自昆明夷,九隆神话为南中诸夷的原始共同神话。【11】尤中先生也认为哀牢夷是滇西昆明族的一部分。【12】这些论述反映了两种可能性:一是九隆神话是昆明夷(含彝语支民族)的原始共同神话,立论前提为哀牢夷与昆明夷为同一族系;二是九隆神话是昆明夷向哀牢夷借取的次生神话,与蒙舍诏崛起建立南诏国的统治谋略有关,前提是哀牢夷与昆明夷为不同族系,即哀牢夷本为濮越族系,【13】最早居住于西昌至永昌的广大地域,与渊源自西北的古羌集团后裔昆明夷交错杂处。
九隆神话为哀牢夷(哀牢国)、昆明夷(南诏国、大理国)、澜沧(南掌)王国(今老挝)的开国神话兼氏族起源神话,已产生逾两千余年,广泛流传于我国西南地区及东南亚国家,已成为跨族系、跨地域的共同神话,其产生、流传的过程十分复杂,将其认定为彝语支民族原始共同神话当属合理,将其视为彝语支民族次生神话来考虑也较为恰当,其在彝语支民族中的普遍性、产生年代及流传地域,尚需更多材料支撑。此论题尚无定论,探讨空间较大。
人类始祖、英雄祖先之崛起
支格阿鲁与阿普笃慕、从忍利恩等同属王权时代崛起的部落始祖或首领,因完成氏族部落兼并而被尊为民族始祖。如果说,在《勒俄特依》神话史诗中他们还只是作为配角登场,那么在英雄史诗《支格阿鲁》中已是主角。从最初的天婚、迎娶天女到人间自行婚配、兄妹婚等诸种情节反映了彝语支民族原始共同神话在这一文化时代的新特征。
近十年来西南各省区涌现了大批《支格阿鲁》史诗研究成果。有学者认为支格阿鲁主要依托毕摩和毕摩经书传承,表现了英雄奇特诞生、英雄征服恶魔、英雄神奇婚姻、英雄救母等母题。【14】而究其本原,《勒俄特依》中关于支格阿鲁身世的神圣叙事为其源头。在《勒俄特依》中,天神恩体古兹率先登场,派四个仙子造田造地造山川沟坎坡垭、草地等,塑造天地形状。而之前所述的天地演变史亦如同纳西族《崇搬图》所述由气、声、云、雾、露演化创生成万物,后万物又演变成雪族子孙十二种,有血的动物六种:蛙、蛇、鹰、熊、猴、人。无血的植物六种。支格阿鲁承袭了雪族子孙的精血,他是龙之子、鹰之子。史诗《勒俄特依》主要叙述其作为鹰之子的神奇诞生。其母蒲莫列衣在织布时头上编织发辫九层,腰间穿毡衣九叠,尾部着裙褶九层。突遇天降一对龙鹰,滴下三滴血穿透衣裙而孕。后某日早晨起白雾,午后生阿鲁。生育时请毕摩占卜、念生育经。但支格阿鲁生下后频现异象:不吃母乳、不同母睡、不穿衣。遂被母亲抛弃于岩脚,竟能餐风饮露生存下来。一岁放猪,会用竹片做弯弓,草杆做箭。两岁放羊,三岁知剑法,四五岁会用弓。天上当时有六个太阳、七个月亮,支格阿鲁射下五日六月,剩一日一月光照大地。《勒俄特依》中还提及另一位类似纳西族从忍利恩的神性始祖居木武吾(又说即仲牟由)。蜀地发大洪水后,天上居木家三个儿子唯有三子居木武吾命不该绝,居木武吾遂上天求天女相婚配,经考验婚、难题求婚等环节,娶天女归人间,生下三个哑巴。经指点祭天才学会说话,说出汉、藏、彝三种语言。【15】考察西南彝区流传的史诗可知支格阿鲁是流传最广,与近现代彝族社会结构、社会生活最紧密关联的神性英雄祖先,其神奇诞生、降服妖魔、开疆拓土、部落征战等光辉业绩荣耀于世。【16】
除上述八个方面外,彝语支民族人类起源神话中的卵生神话、感生神话、猴祖神话、兄妹婚神话、兄弟同源共祖神话等观念及其文本,以及洪水神话等都具有深厚文化内涵,可以继续讨论。

二、从民族史和人类学分析彝语支民族原始共同神话
彝语支民族原始共同神话所表现出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应从其族群分化迁徙与民族社会结构两个方面予以分析。
首先,彝语支各民族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后才由国家正式从族别(族体)的层面予以识别确认。其早在汉代出现昆明族、西南夷等族称,至迟在唐代已被以乌蛮、白蛮、乌蛮别种称之。该民族集团的主源从公元前两千年前至公元前后,已逐渐由甘青高原南下至川西高原的雅砻江、大渡河流域至金沙江流域。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述的游牧族群应包括彝语支民族。此后的两千年中又逐渐南向西向迁徙,并产生分化,至今已迁徙至红河流域、澜沧江流域和怒江流域。迁徙得越远越频繁,表明社会动荡越剧烈,适应新的居住地生存环境的压力越大,保留传统民族文化包括原始共同神话以及原始信仰、原始习俗因子的难度越大。同时与其他族系文化接触面增大,增强了族群融合的可能性。
纳西族保留彝语支民族原始共同神话及其母题最完整,与其居住于彝语支民族分布的最北端有关,属南向迁徙中位置最靠后的部分,与藏、羌两族分布地接近。唐代以前纳西族经历了从今西藏昌都、四川甘孜的巴塘、理塘到贡嘎雪山以南的木里、盐源逐渐南迁至金沙江河谷的历程,此后即留驻当地。虽曾南下到达宾川建立越析诏,南诏崛起后,即败退回金沙江河谷,至今上千年都在当地生存。直到明代才由明王朝扶持,确立地方统治权,保留了以氏族、村社为纽带的社会结构。在王权统治较弱的背景下,以原始神灵信仰为基础并受西藏苯教影响而形成的东巴教,维系了分散于滇、川、藏交界山地河谷间众多村落的社会组织系统。东巴教、东巴经一直保持完整的传习生态,维系着社会组织结构中的神权统治,纳西族又是今彝语支民族中与藏(羌)文化保持紧密联系的部分,这或许是其保存古羌文化较完整的原因之一,【17】值得深入探索。
民族史学界也有学者认为纳西族属西南“夷”系民族,与其他彝语支民族均为先秦时期已分布于滇、川、藏交界地带的土著部落,与氐羌族群并无直接的渊源关系。【18】但若考虑到纳西族曾有“牦牛羌”“牦牛夷”等族称,历史上又确曾与藏、羌民族发生过长期的语言、宗教、文化接触与融合,则可将纳西族视为彝语支民族与藏、羌文化的连接纽带,需关注这一联系对彝语支民族原始共同文化包括原始共同神话的影响,或反证之。彝语支民族与藏、羌民族为兄弟关系,都渊源于距今四五千年前的古羌文化集团,虽然彝语支民族最早从中分离南迁,并形成“西南夷”,但这并不能遮蔽古羌文化对其潜在而深刻的影响。
又以彝族为例,经过彝文典籍广为记述的“六祖分支”这一民族大分支事件后,现今较完整保存彝文典籍、尊崇毕摩的区域当属彝族分布最北端的四川凉山彝族和贵州威宁、大方、毕节等地彝族。云南、广西彝族各支系南向迁徙中与土著部落不断融合,在部分地区,原始共同神话不复存在或根本不曾拥有。一方面是长期迁徙作战使文化行囊丧失殆尽,另一方面是后来加入该族的群体从来不曾有过此类信仰和神话。【19】
就“六祖分支”传说而言,就有部分云南彝族缺失。作为南诏发源地的大理州,彝族支系有七种之多。史料记载源于“六祖分支”的有属于蒙舍诏王族后裔的“迷撒”支系,自称迷撒泼、哀牢夷、摩察(疑为蒙舍转音),他称蒙化族。“迷撒”先民可追溯到彝族先祖笃慕的长房长子武部始祖慕雅切。即“武家的蒙舍”(《西南彝志·谱牒志》)。另有“改苏”支系,自称“倮倮泼”,可追溯至笃慕的长房二子慕雅切、慕雅考的武、乍两部。与“葛泼”支系为近亲。还有“诺苏”支系,出于“六祖分支”时的次房糯、恒(古侯、曲涅)两部,系近百年前从凉山迁来,与大小凉山的古侯、曲涅后裔在服饰、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习俗方面相同,都保留“六祖分支”传说,并以背诵口传族谱来传承本支系、家支世系。
而“腊罗”支系,自称“腊罗泼”,他称“土族”“土家”,人数最多,是最早进入大理地区的彝语支先民,“聂苏”支系来自武定“罗婺”部。“格尼”支系自称“额尼”,他称“土人”,也是源于古代氐羌族群的部分,这三个支系均无“六祖分支”传说。【20】美国人类学家斯蒂文·郝瑞调查认为攀枝花市内分布着五个彝族支系:诺苏、里泼、水田人、红彝、白彝。诺苏来自大凉山,明确拥有源自古侯、曲涅部落的“六祖”血统,不与其他支系通婚。里泼为彝汉融合型,水田人为基本汉化型。白彝、红彝来自贵州威宁。这四个支系均无“六祖分支”传说及认同。【21】
因此“六祖分支”传说仅反映了部分区域之部分彝语支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并非原始共同神话,尚且出现了如此大的传承差异性,可推知前述原始共同神话传承流变的复杂性,与民族迁徙分支确实存在很大关联。

再看拉祜族,其从彝语支民族中分化后从西昌等地南迁至滇西南澜沧江流域的过程,史料记载至迟于南诏时期,较早便与其他彝语支民族分离,走上独立发展道路。傈僳族则在十五、十六世纪以后才从彝语支民族集团中分化形成,从金沙江流域大量西迁进入怒江流域,至今其人群还在不断越过高黎贡山迁至江心坡地区。迁徙动因来自历史上的民族压迫和朝廷、地方官府的镇压,以及现代人口与土地的压力。
哈尼族的迁徙较彝族更频繁,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讲述了从甘青高原诺玛阿美到达红河南岸的超过两千年的迁徙史。详细记录了所经过的地名、接触过的民族和发生的重大事件,堪称哈尼族的口传史书。大量材料表明其接受南方越系文化因子甚多,形成梯田文化这一兼具高原畜牧文化和南方河谷稻作文化双重基因的形态。其原始共同神话保持得就不如纳西族、彝族完整。
如果要推测出彝语支民族原始共同神话的形成期,从民族迁徙与分化的史实来看,上限为远古时期,下限为隋唐时期,即南诏国建立之前;而要推测其形成地域则较难,但并非无迹可循,结合纳西族留居当地及哈尼、傈僳、拉祜等族南迁分离,应为雅砻江、大渡河至安宁河流域,即今四川甘孜州到西昌地区的广阔地域。从族称说,此期还共享着西南夷、昆明夷、乌蛮等名号。此后,乌蛮、白蛮、乌蛮别种、和蛮、鍋锉蛮、牦牛夷等渐见于史著。彝语支民族原始共同神话也就封存于各民族的精神行囊,各自离别走向远方。
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则是审视彝语支民族原始共同神话的人类学视角。纵观彝语支民族各族,大都呈现出历史上神权社会向王权社会的转变。对此,印欧神话研究的权威学者乔治·迪梅齐尔的“三功能论”仍有启发意义。
美国学者S·列特尔顿认为乔治·迪梅齐尔秉承了人类学、社会学中迪尔凯姆关于“集体表象”的学说,并以此研究原始印欧民族的社会结构如何在观念层面留下痕迹。或者表现为一系列神灵隶属于特定的社会阶层,“当迪繆塞尔借助于杜克海姆的基本原理(神话中描述的人物、地点、时间、情节必然都是主要的社会文化生活的真实反映)来分析印欧语材料时,他试图表明最早的印度、欧洲及其他地方的印欧社会都具有一套共同的‘集体表象’特点。……它们都是等级森严的三分法式的社会组织,每一个等级在神话和史诗里都有相应的一群神和英雄的形象予以集体的表现。这三个等级依地位的先后秩序分为僧侣、武士、平民阶层,他们各自都与他们在神话中的相应形象一起,为整个社会或超自然的制度的存在分别起着具体的作用。”【22】“第一个或者说是最重要的职能(僧侣阶层及其在神话中的代表形象)是与维持神秘宗教和法律统治或制度有关的;第二个职能(武士阶层及其在神话中的代表形象)是关于体魄的力量;第三个职能——对印欧人来说也是最不重要的职能(平民阶层及其在神话中的代表形象)是负责生计的供给、物质的充裕、动植物的丰产以及其他有关的活动。”【23】
运用这种印欧比较神话学的研究思路,可看到纳西族及其《创世纪》(《崇搬图》)、祭天仪式、东巴经与东巴的完整传承,维系了神权统治即实现了第一个职能,而随着部落迁徙、征战、开疆拓土崛起的是王权统治,它以一批如支格阿鲁、阿普笃慕、从忍利恩等部落首领为崇拜对象,实现了第二个职能。
以凉山彝族社会为例,是以兹莫统治作为中央与地方的纽带,以黑彝家支为主轴的由兹莫、诺伙、曲伙、呷西等四个阶层构成的社会结构。兹莫是官,为朝廷或地方政权派驻或封赏的土司、土官、土目,其本身不一定属于黑彝,甚至不一定是彝族,也有汉、白、傣等族。而黑彝作为诺伙阶层,有可能是奴隶主,也有可能贫穷并且不蓄奴不占有财富,属于不事农作的职业武士集团。曲伙则是白彝家支。而毕摩则既可能出自黑彝家支也可以出自白彝家支,多数毕摩来自曲伙家支。这表明以开疆拓土、血亲复仇、部落(家支)械斗征战、掠夺并占有奴隶为特色的凉山奴隶社会,诺伙(黑彝)仍保存了武士集团的某些特征,并上升为最高阶层,以王权压制了神权。以战争及掠夺人口、土地、牲畜为主要生计,拥有对曲伙(白彝)家支及奴隶的庇护权和义务,这个阶层的观念表达或在神话中的代表性形象就是以支格阿鲁为代表的始祖英雄。其神圣性和影响力借助黑彝家支在凉山彝族社会中的声望持续制约着当代彝族社会。
而彝族早期社会阶层乃至支系分化则与阶层或职业有关。【24】陶云逵先生在1938年调查碧罗雪山傈僳族时采录的神话也提到最初兄妹婚生三子,长子为官,二子为巫师,三子为工匠。【25】由哈尼族著名歌手朱小和演唱,史军超、杨叔孔、卢朝贵记录翻译整理的《窝果策尼果》(古歌十二调)的下篇“窝本霍本”(人间的古今)第十三章“直琵爵”(头人、贝玛、工匠)叙述了远古时代这三个阶层或职业的起源及职能,每种职业又按能力分成上中下三等,共同促进了社会发展。【26】流传于红河地区的哈尼族史诗《三种能人》说,世间之物如平地、湖、树、花,都有官人、贝玛、工匠的各自一份。并说远在官人、贝玛、工匠三权鼎立时期,贝玛乃是世态安宁的根本。“三种能人在世间,官人跟前少贝玛,贝玛后边不闹鬼,工匠周围有利刃。”【27】
元代以后中央王朝在西南民族地区实行的土司制度,以“羁縻”政策分封各级土司、土官、土目或头人,在不同民族或同一民族中形成分级管理,以夷治夷,相互制约。致使在氏族村落组织阶段以神权制于人的巫师地位大不如前,而受到中央王朝扶持的“官人”则加大了统治本民族的实力,或对内实施部落兼并整合,或对外族发动战争劫掠财富人口、扩张领地。南诏大理国时期的部分彝语支民族已进入这一阶段。王权逐渐与神权分离,不再需要借助神权,王权最终凌驾于神权。仅在某些祭祀场合按民族传统表示对祭司(神权)的尊重。例如至今红河哈尼族地区的“苦扎扎”“十月年”都要由贝玛(摩批)、咪谷(村社头人)主持祭祀仪式,州长、县长、乡村干部都表现得与普通民众无异,同样对本民族原始神灵俯首贴耳、对祭司恭敬有加。

以上借助印欧神话研究“三功能论”,可以较好地解释存在于彝语支民族天神神话中天神正负形象的演变及人类始祖、部落英雄的崛起过程,即神权统治向王权统治的转换。至于以平民工匠阶层为依托的形象,即第三个职能,在一般神话史诗中表现为文化发明神话及知识技艺发明传承的相关情节,这在彝语支民族中也有表现,如哈尼族的古歌《窝本霍本》,但显然不是主要部分。
而处于长距离迁徙并较早脱离彝语支民族集中居住地的拉祜族、基诺族、傈僳族则在迁徙和社会发展中较为弱势,其神话、史诗中就缺失了支格阿鲁式的英雄情节。
2012年出版的四卷本《中国彝族通史》(王天玺、张鑫昌主编),把彝族起源与三星堆、金沙遗址联系起来。将古蜀国历史、人物、事件与彝族起源、迁徙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如古蜀国失国君主望帝杜宇与笃慕的关系等,有些思路是有意义的。三星堆遗址及其出土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等表明早期蜀国是神权统治,由祭司掌权,后来其内部发生权力更替,三星堆被废弃,祭器被砸毁焚烧。统治中心转移到金沙并由另一批人执掌神权。
此外,金沙遗址出土器物还呈现对太阳神鸟—鹰的崇拜。这一神话形象也出现在《勒俄特依》中对支格阿鲁神奇诞生的叙事中,这绝非偶然。在青藏高原南缘的藏区及彝语支民族中,至今存在雕及碉楼信仰。【28】从人类学到考古学甚至到分子人类学都表明古印欧民族及其分支如塞种人文化早在古羌文化时期就以各种方式融合进先羌集团,并沿藏彝走廊南下。【29】这支从中亚高加索地区发源的古印欧文化随着民族迁徙、融合或文化传播在距今4000年至3000年的三星堆文化遗址中,以及距今约2500年至2000年前的滇文化遗址青铜器物(牛虎铜案、鎏金青铜武士俑)中有所呈现是可以理解的。
此外,彝学界也有人认为彝族古代曾拥有如蜀国这样高度发达的国家政权组织,并不能断言现今散居于滇、川、黔、桂四省区的彝族社会只存在过部落形态的社会组织(如南诏大理国时期的滇东乌蛮三十七部)。而可能是先有古国,在经历失国或蜀地大洪水后才通过“六祖分支”而主动分支迁徙。逐步呈现以部(其建制、辖地相当于县)、部落、支系、村落分布的大分散小聚居状态。因此,关于彝族各地各支系内部社会结构的分层、演化及职能相当复杂,不能一概而论。
至于前述神权与王权的更替转换问题,某些古代部落社会有“巫、王”一体或“巫、王、史”一体的阶层,集神权王权于一身。弗雷泽的《金枝》所述国王、酋长兼祭司的职能为其研究肈始,这也可作为一种较宏观的理论背景予以参照。

三、彝语支民族原始共同神话母题之研究意义
以往研究者在论及世界各地各民族具有某些类似或相同的神话母题时,常用“共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相似的思维方式”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等予以非学术的解释。大的案例如源自苏美尔人的洪水神话对希伯来文化的影响而载入《圣经》旧约全书,随基督教传播而遍布全球。小的案例如中国各民族的兄妹婚神话等,从原始母题的产生到遍布各民族的广泛文本、异文,似乎很难寻找到每一母题的传承、传播途径及路线。因为这些文本的地域、时间跨度甚至族系跨度都太大,难以具体翔实地描述神话母题的扩散过程。
神话母题一经产生,大略有传承、传播两条路径。跨地域、族系的神话母题传播,多在不同文化体系的接触、碰撞、融合或转型中产生,如前述九隆神话。而神话母题的传承则多发生在同一文化体系或相同族系的不同后代分支的文本上。彝语支民族原始共同神话虽已经数千年传承变异,并伴随着其民族集团内部的分化、迁徙、发展而将神话母题植根于具有本民族、支系特点的神圣叙事中,但共同性特征仍大于差异性,传承性大于传播性。这些本民族集团内直接代际传承的神话母题及其文本为解读神话母题的演变过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证材料。
例如天神神话及祭天仪式,已为众多学者论证为彝语支民族乃至氐羌族群特有的神话母题。【30】其文化本原可追溯至古羌文化,涉及与氐羌族群有密切关联的华夏文化起源阶段的周文化,周礼中大量关于祭天的规定与氐羌族群的祭天同出一源,现今保存最完整的是纳西族。【31】由之可反证华夏先民与氐羌先民共同拥有的祭天神话及礼俗。
但在彝语支民族普遍拥有天神神话这一原始共同神话的同时,各民族的神话文本、神格、神迹则同中有异。天婚神话是介乎天神神话与人类起源神话之间的一个复合形态,或者三者间存在叠压交叉。天婚神话的完整文本情节以纳西族最典型,其他民族如彝族偶有提及,或在历史长河中湮灭了。这样,在比较彝语支民族天神神话文本形态的基础上,我们可能描绘出一个原始母题如何被保留、又如何变异乃至丧失的过程。还可探讨其原始神话母题究竟是天神、天婚、人类起源、兄妹婚四者的复合型还是单一型,以及四者之间的演化叠合关系。
从族群分化的视角看,彝语支民族从几千年前的民族集团不断分化、繁衍,仍保持语言、文化、宗教、神话的相似性,尽管地理阻隔越来越大,内部分化愈益强烈,如彝族就分化为六大方言和数十个支系。这一民族集团内部分化的过程都可由民族史研究佐证,同时也通过彝语支民族原始共同神话得以反映,二者是对应互证的关系模式。由此,可以反思以往的民族史研究仅注重族别研究的弊端,其忽略了上位的古代民族集团和下位的民族分化中的支系。而神话研究者若只关注某一族别神话,则难免受这种“族别史”视角的局限,仅就某族神话或个案单独探究,终究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只见参天大树不见繁茂根本,追流而失源,舍本而逐末的做法。
彝语支民族原始共同神话的探讨,还从另一角度解读了民族史研究和族群认同研究中一些疑难问题。以白族为例,其语言系属、民族系属及起源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云南学术界的难点,争议颇大。但倘若我们从“火把节”神话传说群的复杂文本来分析,则可看到白族与彝语支各民族至迟到南诏时仍共有“星回节”(火把节)时祭天、祭祖之俗。蒙舍诏借以吞并六诏的政治谋略颇多,既有白子国王张乐进求禅让之说,又有假托九隆王之后的正名运动,更有拥戴彝语支民族共同祖先并祭祖的“火把节”。“火烧松明楼”事件及其传说,反映了两点:一是当时各诏诏主均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赴松明楼祭祖、盟誓;二是“火烧松明楼”事件后该传说主要由白族讲述流传,并在原“邓赕诏”故地邓川、洱源等地兴起“慈善夫人”“柏洁夫人”之信仰及祭拜,有的村落还兴建了本主庙祭之。这反映了白族底层民众对南诏统治者得国不正的悲愤情绪,对忠贞守节的柏洁夫人的祭拜只不过是自家彝语支民族兄弟间权力斗争的掩饰。因此,考察当今彝语支民族“火把节”神话传说群之诸多文本,既可看到神话母题的传承,也可看到其变异。“火烧松明楼”传说就是叠压在“火把节”起源神话之上的新文本,已添加了民族内部分化争斗的变异因素,这亦导致白族的族群认同必然具有彝语支民族中的差异特性。
类似“火把节”神话传说群的分析,可以在上述彝语支民族原始共同神话母题及其文本中逐一进行,文本的支撑力度相当可观,因本文重点在于提出研究思路,就不展开。
对于彝语支民族原始共同神话的变异,还可以从神话—仪典学派来分析。从理论预设来说,每个民族在早期都可能发育出神话文本与祭祀仪式两两对应的典型形态,互为佐证,互相诠释,相互支撑。而随着社会历史发展或民族分化,有的丢失了神话文本,有的祭仪湮灭,甚至有的民族或支系二者都已缺失。缺失者因战乱、迁徙导致文化断裂,或自身是后来加入该民族集团者,要么逐渐传习获得部分原始共同神话,要么一直游离于这一文化体系之外,或尚未完全融合于彝语支民族集团。

四、结论
综上所述,彝语支民族原始共同神话展示了一个个鲜活的神话母题及文本从产生到持续传承、变异的过程。伴随民族迁徙、分化、繁衍,神话母题与文本呈现不同形态。这为研究时空跨度极大的神话母题传承流变过程提供了难得的样本。就研究方法论而言,运用民族史、人类学的丰富史料及民族调查材料,可以从文本之外的社会历史背景对彝语支民族原始共同神话进行深入解析,这亦凸显了多学科方法在民族神话研究中的作用。
(附记:本文是近年来为云南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专业及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授课的讲稿,一些博士生也参加了旁听。)
参考文献
[1][2],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第241至24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版。
[3][4],东巴经鲁般鲁饶.杨士兴、和云彩、和发源译.丽江县东巴文化研究室油印。
转引自李国文.纳西族象形文字东巴经中的五行学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编.宗教论稿.第238至23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5],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第260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6],(日本)伊藤清司.中国古代文化与日本.第284至294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张福三、傅光宇.原始人心目中的世界—西南民族原始文学研究.第26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7],陶云逵.碧罗雪山之栗粟族.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少数民族卷.第329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8],屈小强.三星伴明月——古蜀文明探源.第31至第37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9],邢莉.中国少数民族重大节日调查研究.“彝族火把节调研报告——以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沙力坪村2006年火把节为个案”.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
[10],黄泽.西南民族节日文化.第167至170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1],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第2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2],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第3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3],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第3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4],肖远平.彝族“支嘎阿鲁”史诗研究.第199至218页.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15],勒俄特依“公史”选译.载王昌富.凉山彝族礼俗.第180页至188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
[16],杨继中、芮增瑞、左玉堂.楚雄彝族文学简史.第105至118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17],杨福泉.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赵心愚.纳西族与藏族关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8],蒙默.试论汉代西南民族中的“夷”与“羌”.历史研究1985年第1期。石硕.藏彝走廊:文明起源与民族源流.第72至8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19],王桂馥、陈英,彝族六祖源流及其年代问题。陈英。关于“六祖”“罗甸国”等问题的调查。云南省编辑组编.四川贵州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62至180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0],王丽珠.大理州彝族的源流和支系.云南省编辑组编.大理州彝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至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1],(美)斯蒂文·郝瑞.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第1至15页.巴莫阿依、曲木铁西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2][23],(美)S·列特尔顿.迪繆塞尔教授与新比较神话学.叶舒宪编选.结构主义神话学.第296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4],卢义.彝族的族称、支系及其文化特征.左玉堂、陶学良编.毕摩文化论.第195至19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5],陶云逵.碧罗雪山之栗粟族.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少数民族卷.第29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26],西双版纳州民委编.哈尼族古歌.第253至291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27],红河州民族语文古籍研究所编.木地米地.第145页.李期博搜集整理。
[28],石硕.“邛笼”解读——一个隐含青藏高原碉楼起源真相的符号.民族研究2010年第6期。
[29],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下册)第17章.白种(同化于他族).第293至327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影印版。张增祺.中国西南民族考古.第36至4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石硕.汉代西南夷中“雟”之人群内涵——兼论蜀人南迁及与西南夷的融合.民族研究2009年第6期。
[30],黄泽.云南氐羌系民族的天神神话与祭天.中国民间文化.上海.1991年第4集。
[31],陈烈.中国祭天文化.第67至75页.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第187页云:“又羌族宗教思想,即夏民族思想,可以视为中国最古之宗教,如燔柴祭天,——以社树代表国家,皆当于羌族宗教中考其渊源。”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本文首发于“神话王国”微信公众号,引用请参照线上文献格式。)

图文来源:微信公众号“神话王国” 2020-12-21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