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礼俗”关系的研究,刘志琴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她视“礼俗”为一种文化现象,将“礼”“俗”作为一组对立的概念进行分析,“礼”代表的是国家的、制度的、精英的、文字的,而“俗”代表的是地方的、生活化的、民间的、口传身授的。她特别关注“俗”如何上升为“礼”、“礼”如何化为“俗”, 即“礼俗互动”,并视之为中国思想史的本土特色。然而,李安宅认为,中国的“礼”好像包括“民风”(folkway)、“民仪”(mores)、“制度”(institution)、“仪式”和“政令”等等,在社会学的范畴中,“礼”大而等于“文化”,小而不过是区区的“礼节”。他还特别强调,普通观念里都认为礼是某某圣王创造出来的,这种观念并不正确;因为成为群众现象的礼,特别是能够传到后世的礼,绝对不是某个人、某机关所可制定而有效的。而刘志琴本人也是将“礼俗互动”最终落实到“百姓日用之学”进行分析,考察日常生活中“礼”“俗”是如何相互依存、整合而致礼俗一体,最终铸就传统中国的“礼俗社会”特征的。
“礼”“俗”相互依存、整合,其实是不同社会力量的交流互动。李、刘两位先生的观点,启发我们对“礼俗”的观察应该从现象层面跳脱出来,下沉到行动者的层面。当我们从行动者层面观察的时候,便会发现“礼”“俗”的分立其实并不是那么绝然的,相互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固化的。何者为“礼”,何者为“俗”,会随着互动双方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在“我”为“俗”,可能对“他者”而言却是“礼”。所谓的“入乡随俗”,对于“他者”而言的应“随”之“俗”,在“我”看来则是“他者”初来乍到时必须遵循的“礼”,否则将会“失礼”。在这种互为他者的互动关系中,我之“俗”即为他之“礼”。因此,“礼俗”现象背后蕴含的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行动者之间的结构性权力关系,“礼俗”其实是不同的组织、群体或者个人之间互动交流的行为表象之一种。由于不同的行动者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最终形成了“礼俗”的上/下、内/外、文/野、礼治/法理等等不同的结构性权力关系面向。其中“上/下”“礼治/法理”关系,已有许多学者分析研究,此处只浅谈学界相对忽略的“内/外”“文/野”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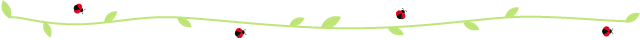
一、“内/外”关系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指出,以人伦为中心形成的“差序格局”,是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在这种社会结构中,是以“己”为中心不断向外推延形成的从己到家、从家到国、从国到天下的伸缩性同心圆社会结构。在具体的社会行动中,不同的组织、群体或者个人,在其内部各有相互区别的“地方性知识”,强调“内外有别”。而“礼”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在社会的组织、群体、个人之中确定彼此的差异,“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

以古代作为“礼之本”的婚礼为例。据杨树达的《汉代婚丧礼俗考》,婚仪有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系列仪式。在这个特殊场合的“过渡礼仪”中,范热内普称婚姻实质上是社会行为,正如《礼记·祭统》所言:“既内自尽,又外求助,昏礼是也。”男女缔结婚约,不仅仅是个人的人生大事,更因“合二姓之好”“事宗庙”和“继后世”而成为两个家族之间的大事。男方通过婚礼迎娶作为外人的女方,其中的一系列仪式既是礼,也是俗。对于男方及其家族,婚礼是他们缔结婚姻时必须遵循的礼仪,也是他们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习俗。而对于婚礼的男女双方而言,本质上则更具有“礼”的功能和意义。通过系列严格的婚仪规训,“成妇礼”让这位刚迎娶进家门的外人“明妇顺”:“顺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以成丝麻布帛之事,以审守委积盖藏”,使之明确自己在家庭中的身份、地位、职责和应尽的义务。按照范内热普的说法,婚仪中的纳彩、问名、纳吉、纳征等可以说是婚礼这一仪式中的“边缘礼仪”,而最终的亲迎、飨客共餐、圆房等则是“聚合礼仪”,将新人结合到新的群体,两个家族建立婚姻交换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显示新娘从一个亲属关系群体过渡到另一个新的亲属关系群体。所以在中国的许多地方,人们用“过门”指称女子的出嫁仪式。“门”分隔了两个不同的亲属关系群体,婚礼中的仪式象征性地喻指女子处于身份模糊的边缘期,仪式一旦完成,身份即成“媳妇”。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婚礼就是以己之“俗”作为接纳家庭新成员之“礼”。重要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礼之本”的婚礼,更因在民间化的过程中,各地新生了各种地方性的婚仪,从俗渐成礼。这些地方性的婚俗,甚至为人们所诟病的各地“闹洞房”习俗,与普同性的婚仪一起,共同构成了婚礼中男女双方及其家族都必须遵守或默认的“礼仪”。“礼俗”的内外关系,实际上隐喻了不同群体之间社会关系亲疏远近的稳定与变化。
二、文/野关系
“礼”“俗”还可以用来标记甚至命名族群、地域之间的文明与野蛮的区别,大到中原与周边、华夏与蛮夷的差异,小到家族、村落之间的差异。“礼”“俗”的标签,实际上隐喻了中心与边缘的权力不平等关系。《礼记·王制》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广谷大川,地形气候不同,民生其间而异俗。此“异俗”决定了不同族群“不可推移”的禀性,其中有中国夷蛮狄戎诸民。虽然承认夷蛮狄戎诸民与中国之民一样,“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 但他们的“不火食”“不粒食”“被发文身”“雕题交趾”“被发衣皮”“衣羽毛穴居”等不同生活习俗,则是将他们命名为“夷蛮狄戎”等不同族群的符号标记。尽管言语不通,饮食服饰习俗迥异,但先王在“不易其俗”“不易其宜”的前提下,推行礼仪教育,统一政令刑法。希望通过“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以六礼、七教、八政统一道德,风俗因受德教而逐渐发生变化,最终规范统一百姓的日常生活和行为,达到以礼化俗的目的。
如果说《礼记》所叙乃儒家理想的礼俗文明秩序,那么在现实的人群互动之中,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境况呢?王明珂曾经以清至民初川西北的北川为例,讨论过北川这个“华夏边缘”形成的微观过程及其特质。他发现,清代任职石泉的地方官在他们的诗文中鄙夷土著的风俗习尚,斥之为“陋俗”,同时模仿、夸耀、崇尚汉族文化。他们以儒家的道德观为唯一的、理想的文明秩序,认为除此之外的其他习俗都是野蛮行为。经此过程,清末以来,北川民众在居住形式、婚丧礼俗、年节活动、庙会信仰等方面,与川西北的汉人无异。在这一微观过程中,造成了一种“一截骂一截”的边缘情境。在20世纪上半叶的北川山区,自称“汉人”的村寨人群辱骂上游村寨的人为“蛮子”,但他们自己也被下游村寨人群骂作“蛮子”。虽被骂作“蛮子”,但人们都宣称自己的祖上为汉人,践行汉人年节习俗,并批评邻人的年节习俗不地道。由此可见,在地方性的微观情境中,模仿高阶层文化的习俗,被不同的人群用来攀附高阶层族群及其文化,并作为向其他人群夸耀的资本,以达到鄙夷、诋毁其他人群的目的。在此微观情境中,某一人群的“俗”,被其他人群作为“礼”来模仿和攀附。不同的人群通过其族源传说、生活习俗以及文字传播的知识,建构起地方性的、小传统的“礼/俗”关系,其结构与国家的、大传统的“礼/俗”关系是同构的,即人群之间的生活习俗,构成了他们之间社会地位的等级差异。

萧凤霞、刘志伟的研究也发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风俗习惯也被当地普遍用作人群区分的标签。他们在江门市潮连乡调查的时候,当地的大族居民反复强调,潮连岛南端某个宗族社群原来就是疍民。当他们问到后者的时候,他们强烈否认这样的标签,并指仍在河上居住的渔民才是疍民。长期以来,当地正是通过生活习惯来对不同的人群进行标签化的划分,以确定那些在水上过着流动生活的人们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如道光《肇庆府志》有这样的记载:“其种不可考,舟楫为宅,事网钓,见水色则知有龙,又曰‘龙户’。性粗蠢,无冠履,不谙文字。入水不没,客船有遗物于水者,辄命探取。性耐寒,虽隆冬霜霰亦跣足单衣,体不瘒瘃。婚娶率以酒相馈遗,群妇子饮于洲坞岸侧。两姓联舟,多至数十。男妇互歌,男未聘则置盆于梢,女未受聘则置盆花于梢以致媒妁。婚时以蛮歌相迎。其女大曰‘鱼姊’,小曰‘蚬妹’,以鱼大而蚬小也。妇女皆嗜生鱼,畏见官豪右。有讼之者则飘窜不出……贫乏者一叶之蓬,不蔽其身,百结之衣,难掩其体。”疍民以舟楫网钓为生计,跣足单衣,衣不蔽体,谈婚论嫁以酒相馈赠,婚礼以歌唱相迎,畏惧官员,躲避官司。无论其生计还是习俗,都与岸上的人群相异,而这些正是将水上生计人群命名为疍民的符号性标签。
无独有偶,埃利亚斯发现,西方社会的法国、德国的“文明”概念,喻指“有教养的”“有礼貌的”“开化的”等意义,也与社会上层宫廷贵族的特性联系在一起。在法国,那些被称作“文明人”的人群,可以说是体现了宫廷社会理想的“正直的人”之扩大了的变体。“文明化”,与“有教养的”“有礼貌的”“开化的”等概念,几乎被人们视为同义词。宫廷社会中的人们通过这些概念来表明他们高度的社会教养及其行为规范,以示与其他普通的、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在教养方面的差别。在德国,那些讲法语的、按照法国模式“文明化”的宫廷贵族,依靠他们已经和正在形成的上流社会的举止行为来证实自我以及建立起自我意识。康德认为他们讲究“繁文缛节”“追求名誉”的行为,使得“文明变成了累赘”。 由此可见,埃利亚斯将西方的文明概念基本等同于“有教养的”一词: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文明的最高形式,即便是在“文化上”“一无所成”的人和家庭也可以是“有教养的”。与“文明”相同,“有教养”首先是指人的行为和举止,人的社会状况,他们的起居、交际、语言、衣着等等。由此可见,在西方,通过人们的社会地位,日常饮食起居、服饰装扮、交际行为等等,将人群进行“有教养”和“无教养”的区分,以此确定某一人群是否“文明”。与西方的“文明”概念相比较,中国的“礼”也是从“百姓日用之学”的日常生活行为入手,进行规范训导,比如秦汉以来南迁的北方汉人带来了中原的礼乐文化,对岭南地区产生的教化作用,逐渐改变岭南当地的蛮风夷俗,使得岭南地区自秦汉以来即浸染中州清淑之气,最终“今粤人大抵皆中国种”。
王明珂、萧凤霞和刘志伟、埃利亚斯的研究给予民俗学视角的“礼俗”研究之启发在于,民俗学应该发挥自己的长处,在地方性情境的人群复杂互动中,理解“礼俗”这个“很大、很复杂、不断变动的问题”(赵世瑜)。“地方性情境”意味着研究对象可以超越传统的乡村视角看“礼俗”关系,任何具备人群互动关系的情境,都可以构成一个可供把握观察的“地方性情境”。这个时候的礼俗关系就不仅仅是大传统/小传统、精英/民间的互动,而很可能是地方性情境中生成的一套复杂的、交织着大小传统、精英民间、国家地方、不同群体等各种话语,而且处于流动变化状态之中的“礼俗”关系系统。在“地方性情境”中生成的这套“礼俗”系统,与其说是群体各自不同的生活行为,不如说是一种进行社会群体的等级区分的工具。从这一意义而言,礼俗的“文/雅”关系,可以说是以“礼俗”来区分不同群体社会地位的等级高下。
总之,如果民俗学着眼于生活文化的视角,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层面,而非仅仅从历史的层面理解“礼俗”,“礼俗”就不仅仅是国家/社会、精英/民间、上层/下层、大传统/小传统的关系,可能还有其他更多可待发掘的结构性权力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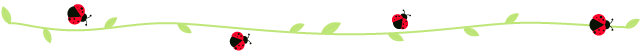
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20年第6期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