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文学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值得关注,即对地方性知识、边缘文化、弱势族群关注的作品越来越多,这些作品在对巫术、神话、宗教等的充分展示中表现了对“他者”的关注和认同。更重要的是,在创作过程中,作家往往运用人类学的思想和手段,从书斋走向田野,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人类学家的角色,而且最终的作品也呈现为具有民族志性质的文化文本。目前,批评家将这类作品称作“人类学写作”或“民族志写作”。
“民族志写作”的产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老一辈人类学家林耀华的名著《金翼》就是一部小说体式的民族志作品,而且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群体一直以来都不吝惜自己的“作家笔墨”,如潘光旦的《铁螺山房诗草》、费孝通的《孔林片思》、庄孔韶的《自我与临摹——客居诗选》等。近些年来,庄孔韶、萧兵、潘年英等人类学家还对文学性质的写作进行了理论总结,提出“不浪费的人类学”等观念,对专业作家的写作不无启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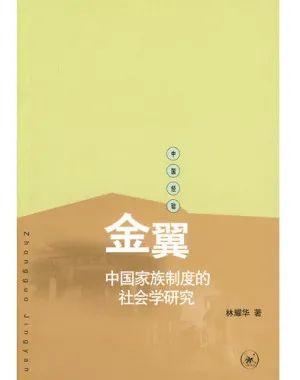
人类学领域中的文学写作早已被证明是合理的存在,无论是格尔兹的“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还是盛极一时的民族志诗学,都关涉其中。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的“表述危机”和“写文化”的大讨论中,人类学的“文学转向”甚至被称为一场范式革命。在文学领域,民族志写作实践是走在观念的前面的,虽然致力于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也曾提出过文学的“人类学转向”,但对文学民族志这一类作品的研究还缺乏系统性和学理性。20世纪90年代,“词典体”的小说、魔幻现实主义、“文史杂糅”的风格等都不乏用来呈现文学民族志。进入本世纪,文学民族志在“非虚构”思潮的影响下,还诞生了阿来的《瞻对》、潘年英的“人类学笔记”、Y.C.铁穆尔的《星光下的乌拉金》等大批非虚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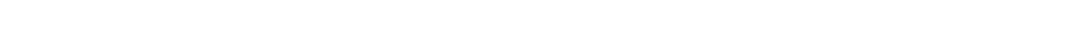
因此,是时候将目光投向文学民族志了,对其功能和价值的分析也有必要放在民族文学的整体视野中考察。文学民族志最显在的价值就是对所谓“地方性知识”的记录,换句话说就是文学的认知价值。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地方性知识”是一个关系论话语,它没有一个确定的边界,即便体现民族性最集中的神话、仪式、民族风情、文化象征等也是在更大的参照系下才愈加体现其意义。而且,优秀的文学民族志都不是对“地方性知识”做简单的记录,经过文学的审美转化后远超越作为事实的价值。彭兆荣在《再寻“金枝”——文学人类学精神考古》一文中认为两个“F”:事实/虚构是可以在文学人类学中相互转化的,这种可交换性体现在自然与文化、历史与故事、进程与话语三个方面。文学民族志亦然,在事实与虚构、根基论与工具论之间,文学民族志就衍生出若干的功能。
在诸多的功能中,文学民族志的文化记忆和阐释的功能是最突出的。文化记忆与文化阐释是具有不同矢量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指向过去的主体行为,一个是基于当下的赋值行为,两者并不孤立,文学的文化阐释预设了文化记忆功能的合理性,文化记忆也立足于当下的时间基点。另外,文学民族志功能的显现离不开文学之外的主体,如学者、媒体、旅游等,甚至可以说,文学民族志并不是自足的,而是一种主体间性的产物。
文学民族志大量出现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领域,文化记忆是文学民族志禀赋的基本功能。我们知道,书面的民族文学形成较晚,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少数民族文学”才得以命名并跻身于中国文学的整个版图中。即便如此,当时依然有大量的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书面文学或以汉语作为写作语言。在这个意义上,书面的民族文学对少数民族来说就涉及到记忆媒介的改变和民族文化的存续、传承。一定程度上说,90年代以来广泛出现的文学民族志就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到特定阶段的集体征候。文化记忆与个体记忆不同,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就已经设定了记忆离不开社会框架,记忆的形成离不开社会化和交往。20世纪70年代,扬·阿斯曼、阿莱达·阿斯曼夫妇正式提出“文化记忆”,并在个体记忆与文化记忆之间引入了交往记忆,认为交往所能维系的集体记忆最多只有80到100年,这时候就需要文化记忆对其制度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文学中掀起了一股“重写历史”的热潮,很多还深入了民族的精神秘史,如张承志的《心灵史》、乌热尔图的《鄂温克史稿》、Y.C.铁穆尔的《苍天的耳语》、阿来的《瞻对》等,这些被评论家纳入到历史民族志的范畴。“重写历史”当然是在现代性、全球化的冲击和压力下保存记忆延续性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在主流叙事和民族国家话语之外开辟的新史学或“后设历史”写作,它们即便不与民族国家话语相龃龉,也不想完全被整合。所以少数民族文学中的历史民族志往往是被主流文化记忆遗漏或遗忘的历史,具有典型的边缘性质,“记忆意味着将其他事物推至幕前,对事物进行区分,也意味着为彰显某些事物而遗忘其他事物”。另一方面,主流的文化记忆有选择、区分和遗忘,民族文学的“重写历史”也未尝不存在,这也是《心灵史》引起极大争议的原因。批评家普遍意识到民族文学的“重写历史”有着主体诉求和身份政治的意义,在二元对立的立场下,“重写历史”并不是真正的历史。“重写历史”的文化记忆很少有私人化的写作,作家似乎有了一种意识,若是要构造民族的文化记忆便无法容纳私人的话语。这样一种谋求差异性的集体身份不排除情绪化的对抗态度,但也往往显示了不同的美学趣味和世界认知,乌热尔图笔下的鄂温克族驯鹿文化、张承志《心灵史》中的穷人教派“哲合忍耶”、铁穆尔散文中的“尧熬尔”游牧文化记忆都各有声色。如刘大先所说,“少数民族文学的再造文化记忆,显示了身份追求和特定认知合法化的尝试。其意义不唯在所叙述的内容本身,也不仅仅是其叙事形式的转变,更在于它们建立了与曾经的外来人的不同的感觉、知觉、情意基础上的概念认知工具”。
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相比较,文学民族志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现象,就是其中包括了大量具有知识品格的文化文本,它们既是作为独特的文化文本而存在也是因为文化文本而得到阐释和接受,因此,文化阐释是民族文学不可忽视的功能。90年代,乌热尔图搁下了写小说的笔转向文化随笔和文史类读物的写作,同时期还有张承志、扎西达娃等大批作家一改文风,在这一方面倾注大量精力。现在,文化文本已经成为民族文学中一种典型的文学民族志类型。阿莱达·阿斯曼曾对“文化文本”给予了细致的界定,她认为,文化文本在“身份认同”“接受关系”“创新表达和经典化”以及“超越时间性”四个方面与文学文本有明显的区别,一言以蔽之,文化文本是在传统的视野中被经典化的,它有对真相的要求,其读者也是某个群体中的一员。
民族文学的文化阐释涉及两个梯度:一是文化文本对民族文化的阐释; 二是对文化文本的接受和解读。前者是将社会历史视为大文本,参照文本—语境的语义框架,文学被视为一种表征,后者是挖掘作品的少数民族知识、地方性知识以及知识谱系等问题。无论在哪个梯度上,民族文学的文化阐释都不支持仅仅将知识作为“留照”式的符号,或者进行抽离地解读。在文学的文化阐释中,格尔兹所说的“深描”经常作为一种有效的方法,“深描”的精髓在于它特别注重揭示行动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格尔兹认为,“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既揭示他们的通常性,又不淡化他们的特殊性。这使他们变得可以理解:将他们置于他们自身的日常状态之中,使他们不再晦涩难解”,这一点与他所说的“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是相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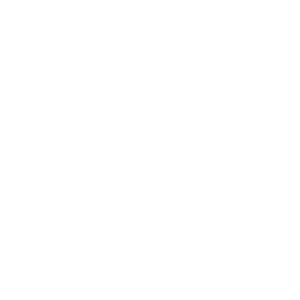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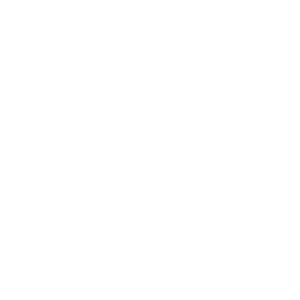
20世纪60年代,反思人类学针对民族志写作的主位与客位问题展开激烈论战,这场有关阐释主体合法性的讨论也给我国民族文学带来一定的震荡。90年代初,乌热尔图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声音的替代》《不可剥夺的自我阐释权》等文章,随后姚新勇也在《读书》上发表了《未必纯粹自我的自我阐释权》,对少数民族作家的主体性展开了“解构”式的批评。遗憾的是,这段交锋并没有走上几个回合,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当代少数民族作家自我解读的某些文字中看到它的影子,例如侗族作家潘年英在《故乡信札》“自序”中说“我更倾向于‘本土’人类学者的研究,原因很简单,就是‘异地研究’的学者很难做到像‘本土’学者那样对文化背景有一种‘吃透’的深刻”。90年代以后的民族文学进入到新的阶段,姚新勇称之为“后殖民弱势文学”,这一阶段民族文学主体意识不仅有国家宏大话语之外民族本位意识的高扬,还在于同时期后殖民思想的刺激,文学民族志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也离不开这个原因。以小说、诗歌等体裁呈现的文学民族志构成了本土经验的重要表达,无怪乎西方人类学家会说“来自于第三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大量当代小说和文学作品,也正在成为民族志与文学批评综合分析的对象”。
总之,文化记忆和文化阐释是民族文学的基础功能,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量出现的文学民族志中有集中的体现。文学民族志是民族文学在特定时期受到跨学科、跨文化影响而展开的写作实践,但对这种写作实践的探索我们已经经历了相当长的积累。民族文学的文化记忆功能虽有一定的缺陷,却体现了独特的情、知、义的文化表达,文化阐释是作为文化文本的解读,它是探索正确理解民族文化的方式。文化记忆和阐释牵涉甚广,关联的地方性知识、民族国家和权力话语等也值得在具体的文学现象中深入剖析。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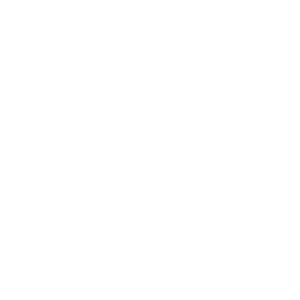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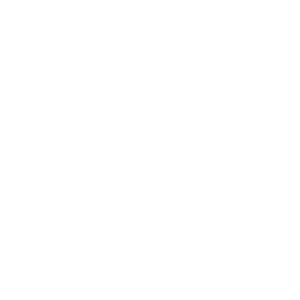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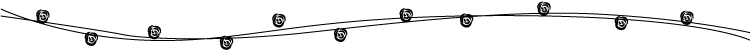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研究》2020年第5期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