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作者授权首发于“神话王国”微信公众号,
欢迎大家订阅!
文明起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中国文明起源尤为引人瞩目。揭示中国文明的起源,对于认识中华文化的特质、坚定文化自信以及思考中华民族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也很重视学术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中央政治局专门组织了学习会。在这方面,有很多引起高度关注和争议的重大学术问题,如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国文明探源工程等。
神话学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应该说,神话学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的联系较为间接,其作用仅次于考古学和历史学,神话学对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有自己独特的角度。多学科研究某一问题,必须对相关学科的方法、视角及材料运用作联系和比较、区别。
一
考古学对探寻文明起源的直接作用
探寻文明起源,就需要对“文明”一词进行界定。“文明”有一个通行的标准,这个标准是西方学术界提出的。文化可以是一个广泛的概念,而文明必须是制度性的,必须有一些基本标准,例如产生文字、青铜器和城市,形成王权、国家形态等。具有一定物质文化特点的文化可以很多,如仰韶文化、红山文化,而若以文明的基本标准来衡量,文明的数量就少得多。

在中国文明起源、夏商周三代研究方面,考古学研究成果突出。张光直先生认为,西方文明是一种破裂性的文明,反而是文明的特例,中国文明的型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型态,是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流。西方制定的文明标准和法则并不适用于中国,中国自身的足够资料可能拟定新的社会科学法则,如文明如何在中国开始。【1】夏商周三代的“古代中国”,夏代虽文献有征,却并未发现有说服力的地下实物,现在讨论很热的二里头遗址,能否作为夏代文明的确凿遗址,也是一个值得关注和争议的问题。许宏认为,夏也许只能算作一个过渡性存在的阶段,或称“广域王权”的准国家形态。【2】目前考古学界有确凿证据的中国古代文明始于商代,商代是中国古代青铜器技术发展的顶峰,周代的青铜文化是在商代的基础上继承和延续的。

在文明起源问题上,考古学提出的观点是最直接、最有说服力的,考古学能够以实际的证据,颠覆历朝历代对历史的记录。以考古发掘的实证来说,最有说服力的观点是苏秉琦先生提出的“满天星斗说”,苏秉琦先生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区系类型学说,认为我国数以千计的新石器遗址可以分为六大区系,一是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也是传统意义上的黄河文化中心(含陕西关中、晋南、豫西);二是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山东、苏北、豫东地区的东方文化;三是四川盆地、湖北及洞庭湖地区的巴蜀文化和楚文化,属西南部文化;四是长江下游环太湖文化,最有代表性的是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属东南部;五是南方文化,从江西的鄱阳湖到广东珠三角;六是从陇东到河套再到辽西的长城以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是红山文化和大河湾文化。【3】
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争议过程中,也涉及“文明”标准的界定。比如,以其他的文化因素取代文字、王权国家等文明标准。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涉及民族观念、国家观念、政治观念。
在论及良渚文化是否可以作为中国文明起源地的问题上,叶舒宪等一批学者大量运用考古学成果,指出良渚文化区虽然出现大型的城池和水利系统,符合联合国关于世界遗产的文明城市定义,但良渚文化所达到的文明程度,不能仅用城邦城池来标定,并进一步提出了以玉教文化为标定,玉文化统一中国的类似“广域王权”的观点。该学派认为,玉器作为一种礼器,远远早于文字的产生,也早于青铜礼器。在中国古代,玉文化包含了人们对神权与王权的双重建构。这样一来,中国文明起源就大大提前了。玉礼器文化源远流长,以玉器来说明中国文明起源的独特性也有一定根据。辽宁红山文化“C”型玉雕龙(玉猪龙)就是最好的证据,红山文化中玉器就是一种典型器物。广汉三星堆也发掘出玉器,陕西石峁文化遗址,也发现了镶嵌在墙上的玉石。叶舒宪等人的观点很有影响,但关于玉文化,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当时已经建构出一个玉神话的体系。这一点,从神话学角度来看,想要用玉文化来证明文明起源是不够的。真正完整的、系统的玉器礼制,出现在周代,周代玉器有各种明确的含义与象征,如璧、琮、圭、璋、玉钺等。更早期的良渚文化有玉器而无玉神话,没有神话材料的支撑,观念性与叙事性的神权王权就没有建构起来。即便有良渚玉琮的兽面纹饰,也仅提供了神话图像叙事的可能性。

此外,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三星堆文化发掘中,也发现了刻在玉石上的刻画符号。有学者考证,三星堆文字系统早于甲骨文,是一种自成体系的较成熟的文字系统,但仍属于卜辞类。龙山文化中发现过“丁公陶文”(有说可能是赝品),仰韶半坡文化中也发现几十个陶器上的刻画符号,亦称“半坡陶文”。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先生认为陶符文字为占卜、观天象所用,并非真正的文字,只能算作是一种符号。饶宗颐先生认为考察中国的文字起源,要把图画文字放在前文字时代。前文字时代的神符巫图有巫术功能,后逐渐向文字转化,并产生世俗化功能,由神的世界转化为世俗世界,因此,文字具有神灵体系里的文字和世俗世界里的文字两种体系。【4】《淮南子·本经训》记载“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从仓颉造字开始,文字的发明使得“绝地天通”,天人分离,神人分离。人类历史从神权时代走到王权时代。由此,文字的历史可以归纳为“前文字时代”(神符巫图)——仓颉造字——文字世俗化。前文字时代的神符巫图继续作为神灵体系里的“文字”存活于当代部分偏远地区和民族中。【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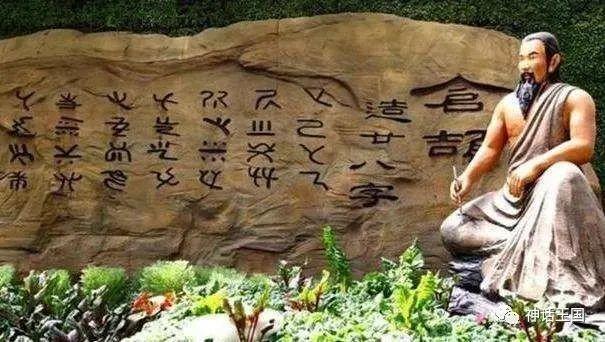
讲到考古学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贡献,我们说考古学是最为直接的、用器物说话的学科,但是考古学也有自己的问题:一是历史上对于古物完整形态的破坏,例如中国历来存在的对死者生前使用过的器物和物品的烧毁或破坏,以及历代盗掘对文化层的扰乱和器物组合关系的破坏,这对我们准确了解文明起源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障碍;二是仅通过出土的器物无法了解古物出土前所附带的文化信息,考古发掘报告往往只作客观的记录描述,这就需要靠神话学和宗教学知识给予解释。
神话学、宗教学,可以对考古学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例如,三星堆文化祭祀坑中的器物通常被毁坏了,青铜器很少是完好的。从神话学、宗教学的角度就很容易解释——古人有“事死如事生”的观念。毁器,是让别人不能再使用这些死者生前使用的器物,这种风俗习惯至今仍在广大地区流传。
二
历史学与中国文明起源的关系
所谓历史,就是在权力书写的作用之下,人为地建构出来的一套有关过去发生事件的话语。中国上古时代应该有过巫、王、史一体时代,仓颉造字后,神权和王权开始分离,中国文化进入“史官文化”,王族士大夫开始书写自己的历史。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中通过对内米湖畔古代居民定期杀死国王兼祭司祈祷万物死而复生的古俗,记述了人类社会早期广泛存在过的“巫王”一体制度的民族志材料。王权要使自己的统治取得合法性地位,需要吸收神话的要素,通过改造和利用神话元素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因而出现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简狄吞卵)和“姜嫄履迹”等感生始祖神话,将部族图腾始祖神话演绎固化为国家神话、王朝神话,用以证明英雄始祖的神圣性和王权受命于天的正统性。这是史官文化对神话的改造,是王权对神权的利用。也是中国古代神话政治化、历史化运用的典型样本。

儒家文化兴起以后,“子不语怪、力、乱、神”,对中华民族始祖黄帝的神话传说进行了理性化的解释。孔子与弟子们的对话就涉及黄帝神话的世俗化解释。但由于西汉时期儒家尚未取得压倒性的权威,儒家文化还没有发展到顶峰,所以汉代是神话得以整理的一个重要时期。当时有大量的方士,产生大量的仙话。统一后的帝国疆域内的地域神话、民族神话被广采博收,如盘古神话;全新的神灵信仰体系也被建构起来,如汉画像石画像砖神灵图像、武梁祠汉画像及其神灵系统、马王堆汉墓飞衣帛画神灵世界等。
司马迁的《史记》被认为是中国上古至先秦历史最权威、最全面的集大成者。但上古时代历史、传说与神话混杂,如何处理上古历史?司马迁对于中华文明始祖——黄帝的书写耐人寻味。司马迁是太史令家族,其《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黄帝的记录,踏勘了从陕西、山西到河南河北、山东大部分地区,访问耆老,采录民间传说。最终选择了传说入史,舍弃了神话的部分。“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循齐,成而聪明。轩辕之时,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炎帝)莫能伐。”《史记》中重点记录了传说中的黄帝与蚩尤之战,而舍弃了神话中关于黄帝形象的记录,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在于上古神话中黄帝“一目、四面、轩辕、长寿”的形象不符合文明始祖雅驯的形象。下面我们就神话中黄帝的形象进行说明。
(1)“黄帝一目”。儒家解释为黄帝睿智,一目了然、一眼看透复杂的形势,纵观天下。从神话学来看,“黄帝一目”有可能与希罗多德《历史》中记载的中亚“独目人”部落(戴上了独目面具的武士)有关。
(2)“黄帝四面”。儒家雅驯的解释是黄帝的四个手下炎帝、太皞、少昊、颛顼去为他治理四方。从神话学角度看,黄帝四面,指的是四面神的形象。相应的支撑材料除了泰国有四面佛信仰,印度史诗《摩柯婆罗多》中,大梵天就是四面神。黄帝的形象也许与印度教三主神(大梵天、毗湿奴、湿婆)之一的大梵天有关,黄帝的形象很有可能与印度的古印欧文化有共同起源。
(3)“黄帝,名曰轩辕”。有学者认为,轩辕氏是一支以熊为图腾的民族。也有学者指出,“轩辕”指使用高车的民族,中国直到商代才出现有关使用战车的考古实物和记载。而公元前2000年左右,大量蒙古岩画中已有关于战车类型的详细描述。【6】说明黄帝族很可能是一支活跃在欧亚草原的外来游牧民族。《史记·匈奴列传》提及“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大禹是黄帝的嫡系苗裔,而匈奴是夏后氏之苗裔——也就是说,匈奴是黄帝族之后。同时,黄帝又称有熊氏,以熊为图腾,也是草原游牧民族的习俗。一些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也同样提供了旁证,古代氐羌族群和印度东北部各邦、缅甸克钦邦以及越南有些民族尊炎帝为民族始祖,我们可以推测炎帝族很有可能才是本土的民族,在黄帝族到来之后,炎黄大战于阪泉,黄帝胜出之后才被黄帝族兼并融合。

从历史上看,王权和史官文化的发展,本身就意味着对巫文化的压制和神权的旁落。20世纪初,在“中华文明西来说”的影响下,很多学者开始对中国古史进行反思,认为中国古史有可能是为了政治民族大一统的需要改写的。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又称“疑古学派”)对传统的“三皇五帝”等概念构成的中国古史系统进行了反思,质疑中国上古历史传说的可靠性,认为司马迁将“文化地图”改写成了“历史年表”,把共时性的“满天星斗”的中国古代文明改写成了历时性的“一条线的历史”,甚至把兄弟改成了父子。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对“古史辨派”的观点进行了反思,力求“证史”,证明了西部、东部三大部落集团黄帝、炎帝和蚩尤相互融合的过程。
因此,历史学对于古史的构拟,是对古史的一种巨大的改变,历史学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问题出发,往往倾向于文明有一个特定的中心(例如“中原中心说”),把中华文明从一张共时态的文化地图,改写为一个历时性线索的历史年表。历代正统意识、国家观念、政治权威建构,也要求历史学进行文明中心的建构。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大一统”观念:中国主要是一个以儒家为主导的文化,一个以中原为华夏中心的文明。从农耕文化的角度来说,黄河中下游也确实是当时一个宜于耕作的区域,具有成为文明中心的诸多便利条件。
这些观点和结论由来已久,但也越来越受到中国考古文化遗址的实际状况的挑战与质疑。
三
神话学研究对于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贡献
上面谈到,考古学对文明起源有直接的作用,考古证据直接地肯定了文明的存在,或是直接否定了历史的建构,是考察文明起源最有力的工具。历史学则是一种基于建构文明形态和国家民族观念的历史叙事,有强烈的政治目的。那么,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神话学的作用何在呢?
首先,神话学贡献于中国文明起源不是那种实物的、量化的、精确的证据,而是质性的研究。神话学研究的是文化源头处的文化现象,如原始思维、无文字时代的口头文学等。但神话学不能单独进行文明起源的探索,必须有跨学科的视野。可以通过比较世界上几个重要文明发源地的神话母题,来厘清各文明之间的关系,能拓宽文明起源的全球视野。

这里,我们就需要谈一谈神话母题研究的可行性。神话母题研究具有超越地域性、民族性的特征。从比较神话学来看,世界范围内的相似神话常常可以追溯到一个共同的母题,人类神话有共用的、通用的母题,意味着可能有一个共同的起源,这是一种原始共同观念和信仰母题。以滇青铜文化为例,江川李家山古墓群中发现的珍品“牛虎铜案”,可能来自于斯基泰(Scythians)文化中的“兽斗”母题,体现一种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观念和习俗;晋宁石寨山发现的古滇国贮贝器和贝类,这些贝类很可能来自印度洋,与哈尼族服饰和神话中的贝类母题相呼应,实际上应该与生殖崇拜有关,象征人口繁衍、人丁兴旺。从古滇青铜文化图像与纹饰提供的资料来说,古滇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7】从神话学的角度,许多中国古代神话中著名的神祇,有可能与外来的文化有关。如《大戴礼记·帝系》写:“吴回氏产陆终。陆终氏娶于鬼方氏,鬼方氏之妹,谓之女馈氏,产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启其左胁,六人出焉。”该记载中 “胁下生人”的故事与亚当取肋骨生夏娃的故事有相似之处,当属印欧神话母题。陆终氏为黄帝第六代孙,相传为黄姓始祖。又如有学者认为盘古神话、伏羲女娲神话也是外来的。神话的起源地点、民族我们很难断定,但母题传播及原型、心理意识等原初性因素,却可以帮助厘清一些文化因素的起源与传播路径及其与民族迁徙融合的关系问题。
为了帮助大家更深入地理解以上论点,下面我从两个较具体的论题展开讨论。
四
作为礼器的玉——考古学与艺术史的视角
近来随着良渚文化遗址(距今5300-4300年)于2019年7月6日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大型城市遗址及外围水利工程引人注目,制作工艺精巧的成套玉礼器及其可能承载及表现的神灵观念、祭祀礼仪也成为热点。部分学者试图提出“玉文化在5000年前率先统一中国”“良渚玉礼器及礼仪影响周边”“良渚玉文化表现于玉神话的可能性”等论题。从国际公认的文明标志看,其文字与青铜器缺失,但玉礼器确实是这一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交替阶段最具特色的有广域神权兼广域王权可能性的标志性器物。参考二里头考古领队许宏谨慎提出“广域王权”可能是夏或早商遗址的二里头的独特的国家形态【8】,对良渚文化也可作类似推测,即良渚以璧、琮为主的礼器系统影响广域,具有广域王权或神权之可能性。作为石之美者的玉,从几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到七八千年前进入新石器时代,都有发现并制作玉器的物质文化渐进演化可能。亚美文化圈上迄数万年前形成,亚洲与美洲均有用玉传统,说明玉器起源久远,当有广阔地域及较早时限。

中国诸文明起源地的用玉传统并不统一。1990年,巫鸿即指出:“在古代中国青铜器出现之前,雕琢玉器被大量制作,所有的物质属性均被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这个现象揭示了一种炮制特权及权力的视觉符号的愿望,这个愿望只出现于人类历史的特定阶段。礼器艺术的一整套特征随之逐渐形成:礼器艺术品总是需要以当时最先进的技术来制作;这些作品通常是以珍贵与稀少材料制成,并且需要耗费具有技术的工匠的大量劳力;它们往往集各种不同类型的符号(包括原料、形状、装饰和铭文等)于一身,以便表达其内涵。”“在中国历史和艺术上有一个玉器时代,所有后来的礼器时代都遵循它并从中汲取它们的艺术标准及价值。”【9】巫鸿又以民族史上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的文献研究为指引,以张光直对以仰韶和龙山为代表的两个史前文化传统的考古学材料对比入手,指出玉礼器当为东夷集团所有,可称为“泛东方玉器文化”。巫鸿据此讨论了红山文化玉器、大汶口文化及龙山文化玉器、河姆渡与良渚文化玉器乃一脉相承。“到了公元前三千年左右龙山文化开始的时期,一整套形态特点已在东夷文化中被牢固地建立起来以定义一种象征性艺术。”“中国古代的礼器艺术基于四个同样重要的视觉元素,即媒介(材料)、形状、装饰和铭文。远在三代建立之前,这四种因素就都已出现于东夷艺术中,这些因素间的互动继续左右了三代时期礼器艺术的发展”。【10】
即以材料而言,红山文化之玉来自本地辽宁岫岩玉及远至贝加尔湖与西伯利亚地区,龙山文化之玉亦来自当地,良渚文化之玉则有本地玉与和田玉,或许良渚文化达到顶峰也与玉出昆冈、采用和田玉有关,从而可能将玉礼器制作工艺与礼仪西传。对比之下,陕北神木县石峁遗址虽年代为稍晚的公元前2300年至1800年,仅有较单一的“藏玉于墙”礼俗,另具意义;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至前1000年,但以卓越精美的青铜礼器闻名,见于神圣的祭祀坑,而少量玉器仅见于玉器作坊遗址,并有模仿复制青铜礼器的现象,疑为外来或后起。四川民间及海外还流传着真假莫辨的三星堆玉器或玉器文字。
又以器物形状或器型来说,东夷文化内部亦存在差异,红山文化为玉猪龙(或为玉玦前身),石家河文化亦有玉猪龙,大汶口文化为石斧、玉斧并存,良渚文化则以器型巨大且具装饰性的玉璧及兽面纹玉琮见称。东夷玉器纹饰具有鸟与太阳或单一或组合的统一性。即使礼仪性玉器出现一定范围的传播扩散甚至继承,但其器型、组合尤其纹饰的涵义仍然由原创者拥有权威性及解释权,部分涵义可能随技艺与工匠传播至其他地域或部落。而《穆天子传》提及周穆王持壁、圭宾于西王母,又游历西域诸国,访求数十乘和田美玉满载而归,则是后话了。

由上可知,在中国文明起源前夜发生的新石器时代玉礼器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这亦符合苏秉琦先生倡导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区系类型学说【11】,与中国各考古文化遗址的实际情况相吻合。玉礼器的形状、纹饰则为神话文本的图像叙事提供了一定可能性,但需小心求证阐释。
五
亚美及环太平洋文化圈视野下的神话研究
20世纪上半叶,以李济先生为首的一批中国考古人类学家,受美国历史文化学派和人类学四分科(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浸润与训练,具有跨越时空的学术视野,在面对考古学、民族学、艺术史材料时,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跨文化比较方法,反对就一地一族材料或文化现象作武断分析,而常常倾向于联系比较。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形成学术传统,迁台后又由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续其学统。如芮逸夫先生1938年发表的《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12】,运用了丰富的环太平洋区域神话材料;凌纯声先生1970年代出版的《亚洲及环太平洋地区的文化》【13】,张光直先生的《连续与断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14】、《中国古代文明的环太平洋的底层》【15】;乔健先生的《印第安人的颂歌》【16】(含其博士论文对美国那瓦霍部落文化与喜马拉雅山地藏族在宇宙观、沙画祭祀、巫医治疗等方面的比较),都具有学术方法与视野的一脉相承。民国时期的卫聚贤、徐松石等前辈亦广泛论述了亚洲与美洲上古时期的移民与文化联系【17】。

从神话的母题与文本来看,环太平洋文化圈拥有比较神话研究的广阔领域。如浮土(潜水捞泥)创世神话、地震鰲鱼神话、凿齿拔牙神话、猎头祭谷神话等,涉及东北亚地区南太平洋地区、东亚地区含中国东南沿海至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到菲律宾及印度尼西亚等南岛及东南亚地区。
亚洲与美洲的史前文化联系研究在我国素有传统,研究空间巨大。徐松石先生列举了流行于墨西哥、危地马拉和秘鲁之阿兹特克人、玛雅人和印加人中的51项文化习 俗,作为亚美神话比较研究的文化底层。【18】其中有四大方向的神秘化;巫师作法或表演时的白鹿皮、玄玉和鸟羽头饰三宝;宇宙三层观念;祭天观象灵台(三层高台上设神庙);含玉葬和捡骨藏(二次葬);睡扁头(头部整形);渔猎、使犬与半地穴住屋等。其以较详细的文本描述了潜水捞泥型(又称浮土创世型,含地震鰲鱼型、龟负大地型)神话的广泛分布;印地安洪水神话与中国黄河流域洪水神话比较;日本《古事记》与印第安神话比较;印第安雷鸟、黑鲸神话与《列子》《庄子·逍遥游》之鲲鹏神话比较;翌射日神话与印第安十日神话比较;印第安苇舟(避水工具)与亚洲葫芦神话比较;印第安人面蛇身羽人神像、羽蛇崇拜及天日大神与中国龙、伏羲的比较;印第安狼祖或犬祖神话与盘瓠及瑶族之比较。这些研究虽不尽令人信服,其亚美古文化比较及神话母题与“神话原型”的溯源性呈现还是开启了广阔的比较神话学研究视角。

列维-斯特劳斯在《嫉妒的制陶女》与《神话学》等系列美洲印第安神话研究中作出了示范,也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神话文本。美国历史文化学派之父博厄斯的《人类学与现代生活》揭示了开展特定地域全面历史文化研究的必要性及四分科人类学作为研究工具的优势,其又以《原始艺术》一书中对印第安人图腾艺术的民族志材料整理予以实证研究。张光直、乔健等中西贯通的学者对美洲印第安人三层宇宙观、宇宙树与中央之柱、鸟作为神人中介、四方观念及其颜色象征、四方神等予以阐述,认为其构成“亚美巫教”之史前文化共同传统【19】。这些基础性研究都揭示着这一文化圈内的神话比较有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神话学者应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例如,《山海经》有载“凿齿国”,山东大汶口文化有凿齿现象,江南多地至南太平洋区域广有该俗,贵州近代有“打牙仡佬”,仅从考古学遗物不得其解,或释为与男女成年礼仪有关。直到在贵州仡佬族神话材料中找到神圣解释:上古女子“阴中生齿”,阻碍两性交合繁衍人类,遂打牙(犬齿)疏通。这是典型的神话思维结果,具有类比思维、以物类物、以物喻义的象征与隐喻等特征,云大中文系民俗学前辈傅光宇教授于此有论。假如说司马迁《史记》代表中国经史大传统之“拟古”,国际通行的文明起源标准四要素是更早的“拟古”,则来自考古学的“玉礼器统一中国”又拟了更早的“古”,最终是神话学解释结合民族学材料拟了最早的古(其材料来源的绝对年代最晚近,性质却最久远,达成了“溯古”与“文化复原”的功能)。
亚美文化圈这一考古学、史前史、宗教学、艺术史等学科遵循的学术概念与神话学通行的母题类型方法具有一致性。神话学虽然不擅长于历史学之断代,考古学之实物证据与文化层分析,却在还原史前人类原始观念等“神话原型”,呈现这些观念的跨越巨大时间段落、地理环境的传承与传播方面有其独特价值。尤其比较神话学所秉持的“母题”方法所具的全球视野与全人类精神家园情结意义重大。神话学对中国文明起源的影响是间接的,它指向人类精神信仰及原始意识的源头,时间更早,地域更广,所揭示的共同性更多。有别于以“文明”标准衡量的后期的个体的世界各文明体系。
正是神话学的这种特性,使它能较模糊地建构起伴随民族融合、迁徙交流而形成的民族精神,通过对原始神灵的祭拜和神话人物的叙事,建构起民族文化符号及象征系统,高扬民族精神的旗帜,以教喻后人、延续民族文化血脉。鲁迅先生毕生致力于国民劣根性批判,也通过“故事新编”对古神话中的昂扬精神予以高歌,即为佐证。
神话学以其与历史学、考古学在学科传统、研究方法、视角、材料等方面的联系与区别,亦可有效参与中国文明起源讨论,或许不必过于在意介入中国文化大传统如历史学科的必要性及其得失,田野考古学及民族学亦为外来学科,正确认识本学科的优长与不足即可,如此则无所谓迷失与否了。
注释
【1】【14】张光直:《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载《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2】【8】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
【3】【11】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4-99页。
【4】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5】宋兆麟:《会说话的巫图》《寻根之路——一种神秘巫图的发现》,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
【6】(苏)诺甫戈罗多娃:《蒙古山中的古代车辆岩画》,(苏)奥克拉德尼科夫等著,陈弘法编译:《亚欧草原岩画艺术论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冯汉骥:《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文物的族属问题试探》,《考古》1961年9期;(日)白鸟芳郎:《石寨山文化的担承者——中国西南地区所见斯基泰文化的影响》,《石棚》1976年10期;汪宁生:《晋宁石寨山青铜器图像所见古代民族考》,《考古学报》1979年4期;张增祺:《再论云南青铜时代“斯基泰文化”的影响及其传播者》,载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青铜文化论集》,1991年版。
【9】【10】(美)巫鸿:《“大始”——中国古代玉器与礼器艺术之起源》,载《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12】芮逸夫:《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载《人类学集刊》第一卷第一期,1938年。
【13】凌纯声:《亚洲及环太平洋地区的文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版。
【15】【19】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第353至35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年版。
【16】乔健:《印第安人的颂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7】【18】徐松石:《华人发现美洲概论》(一二三)、《禹迹华踪美洲怀古》,载《徐松石民族学文集》(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附注
此文是2020年10月15日上午为云南大学文学院2020级博士生讲授“中国语言文学基础理论”之《神话学与中国文明起源的联系》讲稿。王自梅记录、整理。此文与2019年10月为2019级博士生讲授的《20世纪中国神话学的走向》相互联系。部分观点要感谢谭佳老师在云南大学神话研究所于2020年7月19日晚主办的腾讯讲座《中国神话学的迷失:以钱穆和顾颉刚的古史辩论为考察》的启发;亦感谢叶舒宪教授团队在《百色学院学报》发表的神话学系列论文的贡献。
作者简介
黄泽,云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神话研究所所长。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