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研究概念,性别最早被用于解释人类社会的性别结构现状。在这种解释过程中,性别被框定为兼具自然与文化基础的二元结构:既包括指向解剖学意义上两性区别的生理性别(Sex),又包括强调社会、历史与政治对两性认同具有建构作用的社会性别(Gender)。
在性和性别研究领域,从20世纪中期开始,便有了关于生理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的论争。随着女性主义研究与实践的推进,社会建构论逐渐占据了论争的上风。从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中,强调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差异化的生产本质开始,性别的社会建构性逐渐得到学界的认同。到1975年,美国人类学家、激进女性主义流派的代表人之一盖尔•卢宾(Gayle Rubin)在《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一文中,用社会建构论强有力地诠释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关联。她提出“性/社会性别体系”(sex/gender system)的概念,用以解答造成人类社会历史文化建构中女性缺席和匿名这一社会现实普遍存在的原因,即“使女性从属于男性,变成一个受压迫的女人的关系,是与经济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的、有自身运作机制的一种人类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将生物的性转化为人类活动的产品的一整套组织安排,这些转变的性需求在这套组织安排中得到满足。”随着女性主义对性别的生物决定论的批判,性别逐渐被诠释为建立在个体生理差异基础上的,由语言、交流、符号和教育等文化因素构成的判断个体性别身份的社会标准与规范制度。

20世纪70年代,当女性主义以“女性研究”的形式进军学术界时,其初衷还只是借助女性主义运动的力量,厘清隐匿在社会正统知识与女性经验分离现实背后的知识生产问题,同时为解释女性能否成为知识的建构者、女性所处的不平等的生存境况和寻求走向未来解放的可行途径,提供理论上的依据与知识上的储备。这种基于女性立场的思考与政治初衷,令学术界习惯于将性别直接等同于女性。纵观女性研究的历程,我们能够清晰地发现,女性主义的知识转变最初始于填补鸿沟阶段,即纠正性别偏见以及创造来自女性经验的新主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主义发现许多鸿沟都是由同一原因造成的,即现有的范式系统地忽略或抹杀了女性经验或性别制度的重要性。因此,这种从性别制度到女性视角的置换,促使学界将研究转向对女性群体的生活与实践的重新发现,将以往被屏蔽的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形态下,以“第二性”的方式生活着的女性及其生活实践突显出来,着重强调了从女性自身的立场去理解女性主体的感受与经历,以及她们对社会公共生活做出的贡献。在人类文化进程中,女性普遍处于被统治、被忽略、被边缘化的“他者”位置,使她们能够获得一种不同于男性的批判的眼光和立场。这种源自女性生活经验的研究转向,在为缺席的主体和经验创造展示空间的过程中,为生产更加完整和更少歪曲的知识提供了潜力,同时也实践了为女性群体进行赋权的初衷。

与女性研究在其他学科中的表现相似,女性视角进入到民俗学的研究中,也是通过对性别社会建构变量的强调和提升,使得被边缘化甚至无形化的众多女性问题或所谓非正统的议题“浮出水面”,并将它们纳入研究范围,从而改变民俗学以男性及相关议题为唯一正统和标准的局面。举例来说,赵旭东曾在讨论田野研究方法时,提及中国很多地区都存在的一种观察身体的经验,即能够通过适婚女性的体形,尤其是臀部的形状,进行传宗接代能力的判断。这种从民众的身体认知,发现民众对宗族或群体传承问题的思考能力,是民族志洞察力的展现。但在这种洞察力中,如果加入女性视角,那么女性就不会只是作为被凝视与言说的客体,以符号的方式抽象地存在着,而是可以通过深究下述问题:生活在同一社区中的女人们怎样看待这种身体标准?她们是以内化的方式遵循着这种性别规范,还是以其它的实践策略和这种身体知识进行博弈……让女性化了的性别视角成为指引我们走出迷宫的阿里阿得涅之线,将以往一直以缄默状态存在着的女性的生活知识完整地呈现出来。郭于华对骥村妇女口述集体化记忆的分析,康丽对巧女故事中性别规约的讨论,刁统菊对女性民俗学者田野经历的反思,王均霞对纪村社会关系网络中女性建构与维持功能的思考等诸多民俗学的研究实例,都可以看作是在女性/性别视角促动下,对女性生活世界与知识范式的有效探赜。
需要注意的是,“女性/性别视角”的加入,强化了探索日常世界的女性主义立场的同时,也有可能因为对两性二元性别架构的固守,引发知识霸权的诟弊。就像朱迪斯•斯泰西(Judith Stacey)与巴里•索恩(Barrie Thorne)在讨论女性研究对社会学科的影响时提出的,女性主义研究所宣称追求平等的目标,在实施过程中,容易显露出一种强烈的“精英”意识,把作为研究者的女性“我们”与作为被研究者的“她们”分离开来,形成一种知识内部的等级体系。而“女性”概念的普适化与均质化,也有可能抹杀在性别主义压迫中不同女性群体经验的差异和多样化,使女性主义研究带有一种殖民主义倾向。实际上,将性别与女性进行同化后的性别转向,可能引发的问题远不止这些。最为严重的,其实是在这种对单一性别凸显中的同化置换,表露出对多元性别实践的简化认知与对性别二元认知框架的僵化实践。就如劳拉贾恩•史密斯(Laurajane Smith)在讨论遗产与性别认同的关联时指出的,“对有关文化遗产的论述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性别问题,即便被提到,也往往变成了女性问题,犹如男性没有性别一样。”
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呈现的一个事实是,在世界范围内,性别认知与实践是以多元化的方式存在着。譬如,在越南,跳神筹文曲(Châu văn shamans’song)演唱仪式上,男女祭司承担的性别角色是完全倒置的;在巴西,男性性工作者群体中有着明显的“跨性别”(transgendered)现象;在北美洲的一些土著部落中,竟然有着多达七种不同性别认知的存在。诸如此类的文化事实,不胜枚举的。但是,简化性别认知的倾向与对性别二元框架的僵化遵从,却会在极大程度上疏离于对性别多样性的尊重,极有可能导致上述这些弱势的文化传承与表达,被高举的女性旗帜所屏蔽、覆盖,直至完全消逝。

严格来说,上述多元性别实践的情况,实际上是性别与文化、资本、政治等多重权力关系复杂纠葛的延伸。唯女性的文化立场,是很难解答下述这些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的:如何将多样性的认知真切地纳入性别问题的理解?怎样说明在生活世界中女性与其他性别的文化被忽略或未被辨识的情况?如何能在反思原有性别规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前提下,唤起文化享有者对这些弱势群体的关注?如何解释相关诠释与文化政策将性别刻板印象合法化的过程……
诚然,如前文所述,现有的范式系统地忽略了女性经验或性别制度的重要性,确实造成了社会认可的知识生产与女性群体的疏离,是关乎性别认知的“大麻烦”。但是,性别遭遇到的最大的麻烦却是在这一疏离基础上,现有范式对多样化性别经验或性别制度的重要性的系统性抹杀。想要更定现有的范式体系以规避性别麻烦,至少要做两个方面的工作,即现有概念框架的转变与这种转变能为其他学者所接受。在这个层面上,后现代话语体系的渗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里不能不提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对性别概念的全新诠释。相较于前辈,巴特勒并未驻足于性别的社会建构特性,而是走得更远。她将性别视作创造主体的表演规范,完全消解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二元对立。在她看来,“性别不应该被解释为一个稳定的身份,或者能导致各式各样行为的代理场所。而应被看作是在时间中缓慢构成的身份,是通过一系列风格化的、重复的行为于外在空间里生成的f一种约束性的规范。”性别的持续存在,“取决于它在社会实践中实施的程度,取决于它通过肉体生活的日常社会仪式得以重新概念化及重新确定的程度。”在巴特勒对性别建构操演性的分析中,性别不单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认知索引,而成为可以去深思那些被视作自然法则、不言而喻的事象和制度合法性的重要视角。借由这一视角可以去思考:性别问题是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变得“可见”或“不可见”的?日常生活中的两性关系如何复杂地与个人、群体、代表着社会规制的政治、文化资本等复杂权力体系搅和在一起的,还有其他诸多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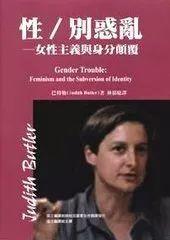
因此,与女性研究相比,立足于多元架构的性别研究不会将视野仅限于女性群体的知识生产,而是会更侧重主体性别的建构过程与差异形态。目前学界所见的性别研究,至少包括下述三种类型:
其一,女性群体仍然可以成为性别研究的重要对象,但在分析的过程中,会强调性别主体文化实践的差异与多样。比如,玛格丽特•约科姆(Margaret Yocom)对有关个人生命史的口头叙事策略及其讲述空间进行的讨论,就是在对比男女两性讲述人差异化实践的框架下完成的。约科姆发现,女性讲述者惯于用自己的讲述将其与听众联系起来,而男性讲述者更倾向于显露自己经验的某种优越性。但这些差别并不影响讲述实践中公私领域边界对两性的开放。口头讲述的私密空间,实际上是在一个手头工作与谈话能共同进行的空间中,与所有参与者都能感觉彼此关联的社交模式。在强调亲密互动的私密空间中,性别并不是讲述活动设限的标准,能否适应亲密氛围才是设限的关键。
其二,性别只是剖析文化事象的视角,并不牵扯对哪一个性别群体的特殊关注。就像林恩•斯克印克(Lynn Skkink)与玻利欧•乔克(Braulio Choque)合作对玻利维亚南部阿尔蒂普拉诺高原安第斯山脉的景观故事讲述与变迁的讨论,没有对任何一个性别群体生活进行特写,只是通过对当地民众进行景 观故事讲述时转换山神角色性别的文化动因进行分析,清晰地揭示出生活在该区域的康都移民的历史被重新书写的过程。
其三,更关注主体性别建构动态机制的研究。譬如,唐•库利克(Don Kulick)在1998年对被称为Travestis的巴西男性性工作者群体的研究。在他所研究的社区中,存在三种性别身份,女性(female)、同男(homen)与非男(no-man)。通过这些男性性工作者的叙事,库利克发现,社区中女性的性别身份相对稳定,而同男与非男的性别身份则会随语境及其行为表现而变化。同男身份向非男身份的转变,是单向性的。判定同男与非男的标准,是个体是否有触摸同性生殖器官的兴趣与行为。那些有触摸兴趣与行为的个体,其性别身份会被认同为非男,且这种性别身份一旦确定,便不可逆转。库利克对上述三种性别身份生成过程的细致描述,揭示了巴西这一特定群体性别建构的动态机制:个体性别身份的确定不在于生理事实,而是在于个体在性别化行动中的角色表演。严格来说,这样的个案研究是对性别二元架构的冲击,也再次说明了女性视角不再是性别视角考量某一项文化事象的唯一度量标尺。
总体来说,无论是作为议题,还是视角,性别在民俗学研究中依然处于较为边缘的状态。但退一步说,正是这种边缘状态使得这种学术立场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也因此具有无法预知的前景。“让缄默的人发声,让缄默的知识最终具有一张具有人性的脸和一颗富于情感的心。”这不仅是性别研究的立场,也是民俗学研究的初心。
参考文献及注释参见原文
文章来源:《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第4期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