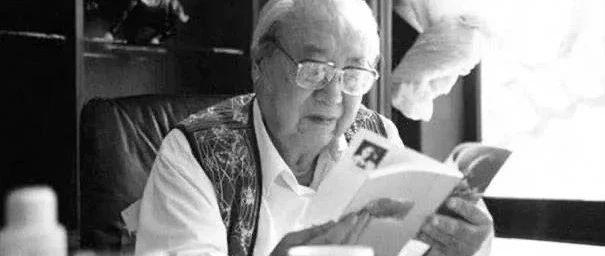

人类学家 费孝通先生
人的研究需要从“生态研究”转向“心态研究”,这不仅是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的内在要求,也是超越社会学的既有传统的可能途径。心态研究是费孝通在晚年的学术反思过程中立足于生态研究的既有基础而提出的,他在多个场合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二者之间的区别及其联系。如果仔细梳理费孝通对于心态研究的表述可以发现,心态研究不仅是他晚年学术反思的重要方面,同时也与既有的志在富民、文化自觉及文化转型等讨论紧密勾连在一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心态研究是费孝通未能完全施展开来的一个研究课题。为此,本文首先从时间的脉络梳理费孝通关于“心态研究”的表述,以厘清生态研究与心态研究之间的区别。其次,结合当时的社会现状,认为文化转型的发生实际上构成了心态研究的重要背景,是心态研究开展的现实性。最后,将费孝通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与心态研究并接在一起以讨论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并且认为文化自觉实际上就是在心态研究的脉络之下提出并且使得心态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成为可能。
一、心态研究的提出:时间的脉络
费孝通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这十多年的时间里多次提及心态研究,这种研究取向的提出无论是出自于他的学术自我反思还是忧虑于学科发展的未来方向,都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虽然有学者已经敏锐地注意到这点,但可能受限于费孝通并没有对此问题进行系统阐述的缘故,以至于未能从时间的脉络对它进行系统的梳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为了更直观地了解费孝通提出的心态研究,我们以表格的形式呈现这一概念提出的时间脉络,具体参见表1。

这里有必要征引他第一次提出心态研究这个概念的具体表述。
我从三十年代开始研究的是如何充分利用农村的劳动力来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物质资源的利用和分配还属于人同地的关系,我称之为生态的层次。劳动力对于财富的占有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我个人的研究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跨出这个层次。现在走到小康的路子是已经清楚了,我已认识到必须及时多想想小康之后我们的路子应当怎样走下去。小康之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人与人的关系的变化,进到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这个层次应当是高于生态关系。在这里我想提出一个新的名词,称之为人的心态关系。心态研究必然会跟着生态研究提到我们的日程上来了。
从费孝通的表述来看,我们能够很清晰地看到生态研究与心态研究之间的转向,结合上述表格提及的这10次具体阐述,可以了解到这种转向实际上包括了诸多方面。
从学术旨趣及研究目标而言,生态研究强调的是志在富民,而心态研究则讲究遂生乐业。费孝通曾经明确表示:我这一生有个主题,就是“志在富民”。且如此说道:“当我在朋友们庆祝我八十岁生日那天宴会上,他们要我总结我一生所作所为,我不加(假)思索的以‘志在富民’四字相答。”在费孝通刚满20岁的那年暑假,他便决定从学医转向社会学,就是因为他知道即使成为一个医生,也只能治好少数几个人的病,而导致千千万万人悲惨痛苦生活的却是不合理的社会。而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如此直言:“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这样的认识与判断促使他孜孜不倦地为中国农民生活的改变而奔走。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国农村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费孝通进而思考“小康”之后下一步研究的问题,即他反复提及的心态研究。换言之,如果“富民”的目标得以实现,那么“民富”之后的社会现实又该如何面对?费孝通认为:“生态关系是指人和人的共存关系,心态关系是指人和人的共荣问题,人和人既要共存也要共荣。我是想说,人在温饱之后应当可以谈得到人生的荣辱了,可以说,做到人生的价值,也就是要做到如孔子所提倡的‘遂生乐业’。”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因此,他强调需要从解决贫困的问题转移到建立一个共存共荣的心态秩序。
从研究层次及研究内容而言,生态研究注重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心态研究则强调人与人的关系研究。若对费孝通晚年的思考做一总结,那么一定是围绕着“人”这个概念展开的。他曾经说道:“我考虑小康之后的问题是除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之外,似乎应当提到人与人之间怎样能相处得更好的问题了。所以我们的研究似乎应该从人与环境及资源的生态关系进到人和人的心态关系了。”在晚年的学术反思过程中,他不停地提及自己的研究是“只见社会不见人”以及“只见社区不见人”,反思既往的研究太局限于结构性及社会性的层面,而忽视了作为能动者的个体的存在。所以他才如此表示:“我回顾一生的学研思想,迂回曲折,而进入了现在的认识,这种认识使我最近强调社区研究必须提高一步,不仅需看到社会结构,而还要看到人,也就是我指出的心态的研究。”这在他后来的反思过程中也被再次提及。因此,他特别强调要注意到人的变化。
从研究方法而言,生态研究侧重于由费孝通等人引领并实践的社区研究方法,而心态研究则需要超越社会学既有的传统界限,从心理、心态等层面入手。他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和方法上都需要及时跟上当时蓬勃发展的社会形势,并反思自己的研究太过偏重社会结构的分析与描述。关于既有的研究方法,费孝通曾如此说道:
就我个人学术牵头的研究工作,经过这十多年的研究实践,可以提出两个研究方向。一是以微型调查为基础,逐步进入宏观格局的探索,即从村—镇—县—区域—全国,从小到大,进入全局研究。另一个方向是从解决温饱问题到实现小康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注意到有关的社会制度和心理以及思想状态的变动,即从生态领域社会领域进入心态领域的研究。
而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这篇文章中,费孝通谈论的“精神世界”“意会”“心”“我”等概念实际上指出了心态研究的可能方向。在该文中他提醒我们应该注意人和人交往过程中的“不言而喻”“意在言外”的这种境界,这在社会学既有的研究中一直没有说清楚,应当成为社会学的一个基本的关注点。同时他也告诫:“忽视了精神世界这个重要的因素,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人、人的生活、人的思想、人的感受,也就无法理解社会的存在和运行。”他反复倡导要超越既有的研究路数及传统,以便顺利完成心态研究的转向。
二、文化转型的发生:现实性
对于费孝通来说,既往的“生态研究”主要包含的“两篇文章”就是“农村研究”与“民族研究”。无论是多达27次的重返江村,还是“六上瑶山”回到他人类学思想的起点,他以一种“行行重行行”的方式所开展的生态研究的所有目的便是他后来所总结的“志在富民”。而当他意识到这个目标已经不再是遥不可及而是翘首以盼之时,他进而在“文化转型”的背景下提出要考虑我们今天通常意义上的“富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并将思考的范围从民族—国家的范围扩大到不同文化的碰撞带来的共存共荣的问题。换言之,费孝通的学术旨趣已经从志在富民转向遂生乐业。而要想达成此目标,心态秩序的建立以及心态关系的研究便是关键。当心态研究逐渐被提上研究的日程之后,那么既有的研究层次自然也就从已有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转移到人与人的关系研究。如何跳脱既有的研究思路,关注到实实在在的个体,关注到真真切切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考虑他们的感情、内心、希望乃至梦想,这是费孝通在反观自己的学术研究之后给出的继续研究之路。这也是费孝通晚年学术研究转向的大致方向。
心态研究是一种研究转向的明确阐述,这种研究转向的出现与文化转型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我们都是生存在文化转型过程中的人物”,这是费孝通早在1997年之时便给出的准确判断。而文化转型的发生,更主要还是来自于人类自身没有很好地处理费孝通所谓的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所以他才会如此说道:
我认为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的共同问题,因为现代工业文明已经走上自身毁灭的绝路上,我们对地球上的资源,不惜竭泽而渔地消耗下去,不仅森林已遭难于恢复的破坏,提供能源的煤炭和石油不是已在告急了么?后工业时期势必发生一个文化大转型,人类能否继续生存下去已经是个现实问题了。
然而,让费孝通担心的不仅仅是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共存问题,同时还有人与人之间共存共荣秩序的缺失问题。他相信,人类的共存共荣的心态秩序会来自于文化的隔阂而引起的矛盾的威胁。因此费孝通说道:“建立的新秩序不仅需要一个能保证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公正的生态格局,而且还需要一个所有人类均能遂生乐业,发扬人生价值的心态秩序。”在费孝通看来,我们需要在“道义的秩序”上形成这样一种局面:“人同人相处,能彼此安心、安全、遂生、乐业,大家对自己的一生感到满意,对于别人也能乐于相处。”无疑,这样的一种判断及其期望与当时民族和宗教问题突出的国际大环境也有着很大的关系。他显然是意识到一种文化转型即将到来,而转型的发生进而逼迫人们不得不面临这样的一个困境,即“旧的文化已不能给我们心安理得的生活方式,新的文化还正在形成的过程中”。因此,如何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为人类找到一个和平共处的共同秩序自然也就成为现实所需。费孝通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尝试着用“心态研究”这个概念去解释既有的现实困境以及指明未来的可能之路。
对于晚年的费孝通而言,尤其是在开启自己的“第二次学术生命”之后,他始终秉持一种“行行重行行”的从实求知的态度,前往祖国大江南北进行考察与调研,这样的一种紧迫感自然与他失去了20年左右的学术时光有着紧密关联。而他也恰恰是在这样一个“行行重行行”的过程中实现他心中那份认识中国以及推动中国进步的愿望。除此之外,这也与他一直以来的为学态度有关。他毫不掩饰存在于自己身上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烙印,将自己的身份认同界定为“我还是绅士,没变!”,被称之为“最后的绅士”,并且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学以致用”作为自己为学的根本态度。他强调要在从实求知的过程中求得知识的理解与传播,恰如沈关宝所说:“记得在费老师门下时,他曾告诫我,要了解他的学术思想,最好的办法是跟着他一起‘走路’(作实地调查),直接去读社会这本无字之书。”费孝通在晚年很多场合都提及了孔子,甚至呼唤新时代需要新的孔子的出现,即便他多次强调自己并没有接受一整套的中国传统教育,而是在晚年才从钱穆、陈寅恪等人那里完成了部分的“补课”,可是这些丝毫不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他的影响。他在回应利奇的诘难之时,也曾从孔子这里寻求到了答案。这样一种务实的为学理念及实践以一种连续性的姿态贯穿于费孝通的整个学术生涯。
事实上,心态研究到底应该如何展开,费孝通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反思与摸索的阶段。费孝通曾多次表示,“我自当努力参与这项学术工作……愿我这涓滴乡土水,汇归大海。”因为他明白,“尽管研究‘心态’问题是下一代人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这一代已经意识到研究人与人如何相处、国与国如何相处的问题有多么重要,那么,我们在继续进行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时,就多了新的方向了。做起事情来就会更加自觉,更加有益了!”承自费孝通早在20多年以前就已经明确指出的心态研究进一步拓展的可能路径,无论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学、人类学还是社会心理学都或多或少已经涉入心态研究。

赵旭东教授和罗士泂博士丨作者提供
三、文化自觉的提出:可能性
心态研究是基于志在富民的学术追求及实践,根据实际的社会变迁而生发出来的不可回避的重要学术问题。因此,当我们谈及费孝通的贡献,尤其是提及他一生只为志在富民的学术旨趣之时,恰恰不能仅仅停留在翻看他志在富民的学术成果及学术实践的历史之上。更应该清晰地看到,他在20多年前已经警醒地反思并告诫我们应该接续志在富民的生态研究而转向新的心态研究。在此,“也许我们是可以把费孝通后来有关文化自觉的诸多讨论一直回溯到他最早有关心态问题的讨论上去”。不过这种研究的转向可能并非就是“思想转向”,因为在距离1997年“文化自觉”概念的正式提出之前,费孝通这段时间实际上一直在思考的就是如何将既有的“生态研究”转向“心态研究”。把握费孝通关于心态研究的表述,我们将会对于他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这个概念有重新的认识。如果将心态研究与文化自觉这两个关键词联系起来,能发现后者恰恰是费孝通在思考心态研究之时提及的一个重要概念,而这实际上也构成了我们谈论费孝通晚年学术思想的一条重要线索。处于文化转型之中的我们,如何顺利实现从生态研究到心态研究的转变,不仅是费孝通晚年的学术期望,同时也是更好地理解人类的心态,建立一种和平共处及相互共荣的心态秩序的关键所在。
正如上文所言,费孝通晚年学术思考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落脚点便是尝试从中国传统文化既有的脉络中寻求新的突破,从而帮助人类——而非单纯的一个国度、民族——能够在这个地球之上和谐共处。他一直在呼唤“新时代的孔子”的出现,并且认为:“新的孔子必须是不仅懂得本民族的人,同时又懂得其他民族、宗教的人。他要从高一层的心态关系去理解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目前导致大混乱的民族和宗教冲突充分反映了一个心态失调的局面。我们需要一种新的自觉。”这种自觉的说法虽然距离他1997年正式提及的“文化自觉”还有几年的时光,不过显然已经是在谈及“文化自觉”的根本议题。及至1997年,费孝通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主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如此说道:
到最后一刻,我想总结一下,问一句:我们大家在搞什么?心头冒出四个字:“文化自觉。”这四个字也许正表达了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是世界各地多种文化接触中引起人类心态的迫切要求,要求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这样生活会为我们带来什么结果?也就是说人类发展到现在已开始要知道我们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这些冒出来的问题不就是要求文化自觉么?我们这届研讨班上大家的发言和对话不是都环绕这几个问题在动脑筋么?我提出“文化自觉”来作为我们这个研讨班的目的是否恰当和适合,还得请大家思考,体会和讨论。
结合上文提及的心态研究的具体表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提出文化自觉这个概念之时,强调的社会事实也同样是多种文化的接触所带来的“人类心态”的变化。如果我们再次返回去看看他在1992年至1997年期间关于心态研究的表述就可以确信,这种逼问显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自他提出心态研究的议题以来就苦苦思考并一直探索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先前关于心态方面的讨论与思考,文化自觉这个概念可能也不会无缘无故地“心头冒出”。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要从原有的生态研究转向心态研究开始,经过几年的持续思考与反思,文化自觉的概念以及具体阐述也终于在此次研讨会中得以初具雏形。而当我们仔细阅读文化自觉的具体表述便能够意识到这不正是费孝通在心态研究中指出的一个重要方面吗?他一直思考的问题不就是如何在多元文化相互碰撞的背景下构建一个能够相互共存共荣的心态秩序吗?毫无疑问,文化自觉与构建一个共存共荣的生态秩序显然存在着紧密的勾连。
在《费孝通全集》的“文集前记”中,费孝通曾吐露,正是因为自己是一个以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为一生兴趣的人,所以他愿意将自己留下的文字提供给别人做研究中国这段历史的素材。他始终保持着一个清晰的认识,那就是“我看人看我”必然与“人看我”将会呈现不一样的状态。换言之,这种自我反观与他者凝视无疑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谈论费孝通的晚年思想之时,我们实际上便是依循他已料想到的路径,即依托他留下的文字素材进行再思考。通过梳理他关于生态研究到心态研究的研究转向,我们不仅能够明白他究竟是如何通过反思而获得一种自我学术的“文化自觉”,同时也为我们如今的社会学、人类学既有的研究提供了可把握、可探索的研究方向,“何以仍要纪念费孝通先生?”的意义在正在此。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意识到“文化自觉”的概念之所以如此重要,正是因为在多元文化的世界中,不同的文化始终都处于“看”与“被看”的状态之中,也就是费孝通提及的“我看人看我”与“人看我”之间的这种差别。人类的心态也无非如此,当人处于“看”与“被看”的状态之时,其呈现的姿态必然也是不一样的。费孝通之所以如此强调“心态研究”的重要性,就是因为他很清楚地把握住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只是,在此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这种“看”与“被看”实则建立在一种“从实求知”的文化实践观之中,而绝非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冷眼旁观”。此外,在践行文化自觉的过程中,我们同时也需要做到“文化容忍”。文化容忍,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概念,我们经常提及文化自觉却忽视了文化容忍。文化容忍,并非一味地妥协与退让,而是在文化自觉的意识之下包容文化的多样性。“人类学者是否有责任在建立文化容忍方面做一些贡献呢?”,这是费孝通的拷问,同时也将是每个人类学者的责任与担当。人类学向来以承认文化的多样性而著称,如何在更广的社会群体之中建立“文化容忍”“文化自觉”等文化态度,对于人们理解人类心态可以说是至关重要。
四、结语
从生态研究转向心态研究,这是费孝通早已表露出来的研究旨趣及研究方向。如果说要追溯该学术转向的来源,无疑要从费孝通的个人学术反思的角度切入。本文基于费孝通思想的延续性的角度尝试聚焦晚年的费孝通关注心态研究的旨趣所在,细致整理了心态研究提出的时间脉络,并分析了该研究提出的现实背景,同时指明了该研究实践的可能性。基于学术反思的再反思重新梳理费孝通提出的心态研究,实际上对于我们理解他晚年的学术思想至关重要,志在富民、文化自觉等重要概念显然都能被纳入到心态研究的脉络之下,并成为我们讨论这些概念及表述的起点。从中我们发现,这种研究旨趣的生发不仅具有大的时代背景,也与学者个人自身的学术关怀有着莫大的联系,这也正是费孝通在一种学术延续性的视角下进行的自我超越。在这个过程中,费孝通不仅提供了纲领性的学术指导,同时还以自我实践的方式为我们做了很多破题的工作。即便心态研究并没有在费孝通身上得以完全施展开来,但是在此我们之所以仍然愿意将心态研究摆在费孝通晚年学术思想中如此高的位置,正是基于上文的梳理而认为从生态转向心态不仅仅是费孝通的学术转向,同时也是学界后续研究的重要指引。毋庸讳言,今天的“心态研究”需要落实费孝通早已为我们提供的研究思路,那就是秉持一种“从实求知”的态度,在“行行重行行”的基础上进而不断反思既有的研究并超越既有研究的界限。即便我们说费孝通言及的心态与今天的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社会心态”存在一定的差别,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再次返回去思考费孝通当初提出心态研究的历史背景以及具体思路,他关于心态研究的表述对于今天的心态研究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