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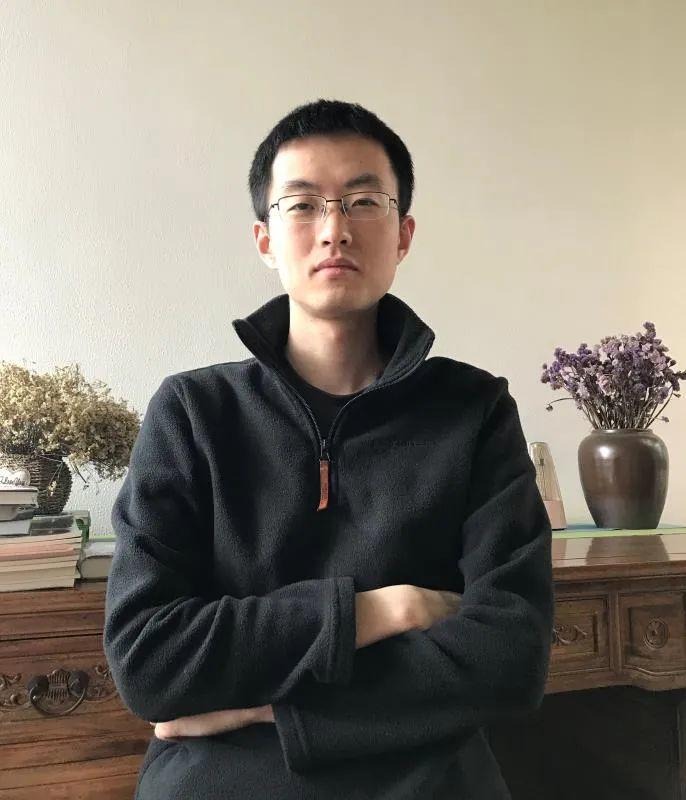
金恺文,哲学博士,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内容摘要
关键词:民国;成都;城隍信仰;祈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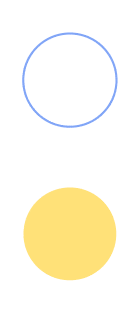
文章将城隍信仰和祈雨活动合论,并不是为了强调二者存在着一种必然联系或相同内涵,也不是为了将其系统划分和归属为民间行为或特定宗教。尽管有时候它们的确存在关系和界限,比如民国灌县的一些祈雨仪式就在城隍庙内由道士主持。而重点是因为它们同作为民间信仰的一部分,在时代变革中的遭遇和处境表现出一种相似性,甚至是一致性,尤其表现在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神祠存废标准》之后。
不同于伏羲、黄帝、释迦牟尼、老子等部分先哲、宗教类神祇,因受政府认可而得到长期保留;也不同于送子娘娘、财神、瘟神等信仰,被归为淫祀、巫觋受到严禁,虽然在民间屡禁不止,但政府几乎从未公开支持。城隍和祈雨相关神祇,被界定在古神类中“山川土地”“风云雷雨”之神的范畴,这些神祇多载于明清以来祀典,合法存在,而按照民国“科学”“现代潮流”考察,许多信仰已无“崇祀”和“存在”的价值。政府对于这类民间信仰的态度较为模糊,称“亟应详加更正”,尽管认为部分崇祀应“一律废止”或“宜禁”,有时也不置可否,没有对待淫祀的强硬态度。因此城隍信仰和祈雨活动,拥有更灵活的生存空间。共同表现为先受到外来冲击而遭抑制,但仍在民间广泛存在和流行,加上某些不可抗拒的形势所迫和民众请愿,在政府做出一定让步后在局部有所复苏。
本文通过对部分民国、现代地方志和民国报刊杂志的解读,梳理民国成都地区城隍信仰和祈雨活动在民间的一些表现形式,更重要的是其所受改良和冲击,民众对传统仪式、活动、观念的坚守和依赖,在禁止和复苏之间的徘徊,以及政府和知识精英批判和让步的多重态度和行为,试图反映传统与变革矛盾的一些具体情况。期借助成都这个相对保守和闭塞地区的样本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对民国历史变革中,民间信仰乃至传统一般处境的认识。

一般认为,城隍是从早期八蜡之祭中的坊和水庸发展演变而来,城指城墙,隍指护城河。据研究最初的城隍神出现在三国东吴赤乌年间(238-251年),至迟在杜光庭编订的道教科仪中,城隍神已进入召请之列。唐宋以来,城隍信仰逐渐突破吴越之地走向全国,官方也加以重视和崇奉。宋代城隍信仰的内涵得到丰富,从早期与城池安全和防御有关,发展到城内紧要事务都归其管理,生产、生活、水旱、虫灾、度亡都多少与城隍有关同时城隍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人格化,地方多将已故功臣或英烈奉为城隍,因此各地城隍神往往都不相同,封号也较丰富。明清时期,在人们的观念中,城隍神会在暗中监察人们的行为,也是监管阴曹地府的社会神,保护善良之人,惩罚奸恶之徒,故民众普遍对其有敬畏之心。官员上任之初,多首先致祭城隍庙,祈求护佑,管理好地方事务。
民国时期,成都官员上任祭祀城隍的习俗已被禁止,同时国民政府也希望取缔城隍信仰:“近世城隍东岳等庙中,多有阎罗殿,俗传为司地狱之神,塑刀山剑树,牛头马面等鬼怪。以威吓愚民,考阎罗之名,虽见诸佛经,然并无事迹可考,亦并一律废止。”但在民众心中,其行为监察、惩恶扬善、管理阴间等功能依然存在,城隍会也有持续进行。
当地竹枝词载:“牛鬼蛇神当昼现,城隍出驾此经过。纸钱银锭孤虽祭,新旧冤魂死太多。”说的是民间城隍出驾仪式,这一天“城乡小儿妆扮鬼卒,百余随神游街,观者云集。”当时成都各县基本上都在举办城隍会,城隍出驾是最主要的一种形式,往往是各县、镇、场规模最大的活动,各地时间各不相同,参与人数众多,场面极为热闹。城隍会既是民众娱乐的节日,也是商贩云集、物资交易的市场,同时也向民众传递着“阴曹地府”“因果报应”的观念。
温江县鱼凫镇每年农历三月十二日举行城隍会。人们用十六人抬的彩色大轿将城隍爷和城隍娘娘抬起在四处游行,队伍以鼓乐、旌旗、伞仗导前。灯队随后,挂灯人赤裸上身,两手平举握木杆,用铁丝把油灯悬挂在前额、胸部和大小臂上。灯队后是装扮的各种鬼神,和沿途抢食的小鬼,城隍的轿子位于队伍最后。
崇庆县城区的城隍会,崇奉的是明末张献忠起义军破成都时,守城战死的知州王励精。相传其葬于城隍庙北,后人们在城隍庙侧建王公祠崇奉,尊其为城隍神。该会为崇境内庙会之最,每年农历八月十二至十五举行。十二日城隍神陪城隍娘娘回娘家,出驾北门外永盛寺。期间由装扮的阴差鬼神和参与民众组成的队伍长达两里,沿途居民焚香稽首,观众众多。十五日回殿的规模也同样壮观。在历次城隍会中,以1924年甲子年最盛,人们演戏酬神60天,萧公庙有60节长龙出游,庙市也极为兴旺。
广汉县县城农历五月二十八日举办城隍会,抬神像出巡,称之为“城隍菩萨出驾”。人们会装扮各种鬼神,如吴常、鸡脚神、判官、魁星,以及众多腰间挂着猪肠扮演开肠破肚的恶鬼。彭县农历三月十八日为城隍会,会期时县城举行山歌比赛,优胜者获得彩红。海窝子城隍庙有城隍出驾活动,当地民众称“排鸾出驾”,称装扮鬼神者为喜神。在彭县丹景山东岳庙和城关城隍庙,有阴曹地府的雕塑。塑有判官、小鬼、牛头马面、下油锅、磨子推、望乡台等阴森恐怖画面,宣扬着因果报应的观念。什邡县农历五月二十八日为城隍会,会期长达半个月至二十天,届时许多川西和省城的行帮也来赶会。城隍出驾之日,人们扮成阎罗、鬼卒,一些自称“阴差”的巫道亦混杂在庞大的人群之中。灯队会在上身皮肉上挂油灯,当地人称之为“九莲灯”。当地和外来剧团多来演戏助兴。新津县农历五月二十日的城隍会是民国时期全县规模最大的庙会,会期从30天到50天不等,演戏酬神,耗费甚巨。期间前来祈求、拜神的信众络绎不绝,有的通宵“念佛”。会期结束时,举行城隍出驾仪式,鬼卒、护卫、神像在城郊游行一周。商贾云集,交易百货,茶水小吃摊贩营业至深夜。
尽管如此,根据一些描述,清末开始成都部分地区的城隍信仰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成都通览》称农历十月初一成都、华阳二县的城隍出驾仪式“在前极为热闹,不亚于三月二十八日之东岳会。近来城隍之仪仗执事亦均冷淡。”1926年出版的《崇庆县志》也称:“古乡厉祀无主鬼神,使有所依不为民书,中秋为县城城隍会,嘉道间最盛近逊音时。”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在国民政府《神祠存废标准》公布以前,成都地区城隍会已不如从前兴盛。1947年铅印本《新繁县志》称从前的城隍会“街衢则高张彩幔,缀以华灯,累累然望之无际。士女嬉游,乐而忘返,诚太平景物也”,但“民国久废”。
民国以来,城隍信仰至少受到来自三方面的打击:
其一是各类新兴县政机关对城隍庙的占用。如温江县1917-1919年在北洋政府颁布的自治法规指导下,在城隍庙后殿东厢设立地方公款收支所、司法经费收支所、警团经费收支处;金堂县征收局1917年迁至东街城隍庙后殿;新都县将地方收支所设城隍庙后殿右侧;崇庆县1922年在城隍庙成立工会。
其二是军阀、新式学堂对庙产的提取。如郫县旧俗本以农历三月二十六日为城隍生日,二十五日晚,信众即通宵上香跪拜,二十六日中午开始城隍出驾,1930年,城隍会产被驻军提卖,活动被迫停止。崇庆县怀远镇城隍庙,自1906年就被改作当地初级小学;温江县私立储才小学1905年成立于西街城隍庙,1912-1914年间仍沿用,并受政府颁“有功教育”匾额。
其三是《神祠存废标准》颁布,该标准当属民国以来,国家从“科学”和“现代潮流”角度,规范民间信仰最为系统的条例之一。条例认为“在科学昌明时代,城隍实无存在之必要”。生前有功于国家人民者,应按先哲崇祀,不得附会为城隍;城隍庙中“阎罗殿”“阎王”“刀山剑树”“鬼怪”等形象,皆不可考,为威吓愚民,应一律废止。在政府明令禁止下,各县理论上应当不会主动举行规模如此之大的城隍出驾仪式,公然对抗法规。1932年4月《新新新闻》的一则报导即表明城隍出驾确实因此遭到限制:“此间习惯,每年清明中元及十月初一,城隍神例有出驾赏孤之举,俱皆聚会于外北城隍庙,目下此举虽已禁止,一般善男信女,仍有以香炬楮锭来会焚化,以结鬼神缘者。”
但城隍出驾仪式并未就此消失。1932年8月一篇名为《迷信与科学——与其迎神出驾不若讲求卫生设备医药》的评论表明此时成都市民众仍然在以城隍出驾的形式驱除瘟疫,并得到一些军政、学界人士的支持:
成都市此疫传来,为时不久,死亡动以千计。一般人惴惴焉不于科学上分析此病之来源,亟谋预防及救治之办法,反以为瘟神下降,今日迎东岳出驾,明日抬城隍清街,甚或迎府县三城隍同时出驾,闻不久又将请地藏王菩萨游街驱瘟,每届此举,信男信女,成千累万,拈香迎送,充塞街巷,最可怪者,闻尚有军政之要人,学术界之朋友,捐款保护,资助提倡,呜呼,此诚成都市之成都欤?
1934年8月19日的新闻报导称政府允许民众举办城隍出驾仪式:
旧历七月十五日为城隍出驾之期,本市各神会日前曾具呈市团局恳予转呈警备部,准予照旧举行,以表诚敬,警备部已准如所请,指令市团局,文云:“呈悉据转报旧历七月十五日城隍神驾出巡祭孤,如请找准,惟随驾人员,纯用香盘,以表诚敬,不许装鬼做神,用除习俗,仰即转饬遵照为要,此令。”
此次出驾仪式得以举行,一方面是成都市各神会向市团局努力申请的结果,同时也反映出城隍在民间仍然有着较为深厚的信仰基础。尽管如此,政府对其仪式进行了改良和规范,传统装扮鬼神的形式遭到废除,随驾人员统一端香盘。政府在向城隍信仰作出妥协的同时,也表明了其改良民俗的坚定态度。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城隍会中出驾仪式的成分慢慢暗淡,逐渐朝着“庙会”“庙市”的方向发展,而这本就是城隍会的一部分。民众仍积极参与其中,其基于出驾仪式的信仰和娱乐需求缺失,似乎在庙会上得到了填补。
如成都市外北城隍庙,1932年会期时“各商贩如木器铁器,以及布疋丝绵各货,先期到□,即露宿于庙前之田边□干,以冀届时就地,以作市场,无不利市三倍,昨又值清明济孤日,远道之赶会者,络绎不绝,而进香之人,以妇女为最多云”。1936年下元会期间,该庙也会举办为期三天的大型庙会,“庙门外一带田坝搭棚,商货虚集,农器,陈列摆满售卖,生意发达,中道两旁,悉为花草市,男女游人,拥挤不通,庙中香火大旺,烧香妇女,如潮水狂蜂一般的争先跪拜城隍云。”被称之为“都市里的迷信风光”。直到1949年,邻近成都的眉山青神县仍大办城隍会,期间庙会,庙市,演戏热闹非凡,耗费达千万元。因此被斥之为:“助长迷信之无益消耗,实为不合时代之要求,且当此国家多难,民不聊生之际,此种粉饰太平之举,徒贻笑大方而已。”
城隍信仰有着牢固的信仰基础而无法根除,长期活跃于民间。为了对抗和改良这种顽固传统和思想,除了政策限制,关于城隍信仰和庙会各方面的负面评价和宣传,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在批判“迷信”和“无益消耗”基础上,媒体逐渐认识到仅从打击“迷信”和限制“娱乐”的角度,来削弱城隍信仰的影响力是不行的,于是他们开始有意无意地将庙会描绘成一个非常混乱、危险的场所,试图从“人身安全”和“道德”角度打击民众信仰和活动的积极性。
1931年11月,一位年轻女性在外北城隍庙会上遭流氓调戏,不堪其辱,终自缢而死。于是新闻以“城隍会害死人”为题报导了这一事件:
昨阴历十月初一日,外北金华街之城隍庙,颇为热闹,陈氏因邀其邻妇某,同赴城隍庙看会,游兴方浓之际,突有流氓数人,尾随讽笑,陈氏当出口大骂,该流氓等竟上前乱摸,事正危急,幸遇其老表某,现充某部军人力为保护,始得脱险归家,不图事被其夫觉察,以为败坏门风,复加毒打,经邻人劝解始息,杨因闷气不过,遂出街自遣,陈被夫打后,以妇人意识有限,一时理想不开,遂萌死念,乘其夫外出时,即将门户紧闭,在卧房悬梁自缢而死。
1933年东大街府城隍庙被指“有多数滥兵流氓,在两廊摆赌摇宝,掷骰抽头,引诱一般无知青年,入局者甚伙”,1936年又发生火灾,该庙“香火甚旺,以致大殿顶板房柱被烟炽干燥,因是时有居士焚烧黄纸,冲顶高化该庙龛司未觉落于匾缝内,惹燃阳尘”。此外,当时民众时常祈求城隍为其治病,病愈后常献烟土以示回报,社评在指出毒品为害甚广之时,也以“阴间阳间不两样”“城隍也抽烟”等语言讽刺城隍信仰和民众的行为。
于是城隍会与流氓、兵痞、火灾、赌博、鸦片等形象不知不觉就联系在了一起。或许很多现象与城隍信仰并无直接关系,是人群太过集中,卫生、防火意识不足造成的。至于女性在会场遭辱自缢之事,很大程度上与其丈夫不仅未予慰藉,并因“败坏门风”为由施暴所致,与其说是城隍会“害死人”,不如归咎于其夫保守的礼教思想和处事不当。然而在宣传角度上,反将妇人参与城隍会与其“风流成性”扯上了关系,称其自缢原因是“妇人意识有限”,而对于其丈夫的行为未作任何批评,并顺带让城隍会“承担”了其死亡的一部分责任。
显然,这样的媒体文章过于主观,并不能代表所有知识精英的看法。相反的,有人基于对政府机关和司法的不满,对城隍信仰表示同情和理解。他们认为司法是民国建立以来发展最为缓慢的一个领域,不仅程序繁琐,也缺乏具备职业操守的律师为普通民众发声:
抗战建国的现在,关于行政教育财政,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善,都表现着长足的进步,惟有司法,死板板的,老是什么程序,什么不告不理,无非为有产者作保障,替一般滥律师们□包袱,那没钱没势的被压迫者,当然无力来请金钱主义的律师,东不成,西不就,只好判来败诉。
由于司法的不完善,普通民众在遇到纠纷时,花费大量钱财和精力却得不到满意的结果,所以他们有时不会选择法律程序,而依然延续过去“进城隍庙去赌咒”的形式。尽管作者呼吁“不要使人人都以城隍庙为唯一解决是非的场所”,但实际情况让其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法律是专门保护有钱人的”,以及“打官司进衙门,没如到城隍庙去赌咒”这些流传于民间的说法和解决纠纷的传统方式。

中国作为农业社会,历来重视祈雨。历史上不仅民间祈雨活动频繁,国家也时常参与其中。民国以来,随着科学观念兴起,祈雨被认为是“以现代之潮流考之,均无存在之价值矣”。《神祠存废标准》规定应取缔海神、龙王、雨师等与雨水有关的神灵崇奉。但祈雨活动和龙王、龙神等崇拜并未在民间消失,人们仍视之为管理雨水的神灵,各地都建有龙王庙、龙神祠加以崇奉,常“因水旱之灾,祈于龙神”。如民国《郫县志》记载:“乙卯(1915年)、丙辰(1916年)春夏旱,廷弼命人至龙池请水,设坛祈雨,雨辄应,人尤异焉。”广汉县若逢干旱,乡镇会组织祈雨。民众将龙王塑像抬上轿,上街游行,街民则焚香祈求。祈雨期间,一般会命令禁屠,不准宰杀猪、牛、羊,以期感动神灵降雨。
不过禁屠有时只是虚文,“假定明天开始断屠了,屠夫们今天总要赶着多杀几条猪,人们到了买不出猪肉的时候,总是多杀几个鸡鸭来代替。而且在四月初间,成都断屠的时候,到处饭馆里,一样吃新鲜猪肉,实际是肉市上的肉,搬到人家里卖去了”。不仅如此,禁屠有时还会引起民间冲突。比如1936年6月,金堂县赵镇“因久晴不雨,农田大多数无灌溉,乃由民众筹款设坛建醮祈雨”,并禁止屠宰。而屠商为了盈利,在禁屠期间仍杀猪私售。民众发现之后,认为其“有违建醮禁屠之旨”,于是将查获的猪肉扔进粪池或河中。这就引发了商民之的冲突,“商团持枪出头调解未遂,竟开枪威骇,当场击毙民众一人,受伤三人”,肇事商团亦遭民众联名反对,并请县府查办。
民间祈雨形式十分多样。其一称之为“耍水龙”,用竹子和麻布做成的“水龙”,龙头、龙身、龙尾共七节,七人各执一节,在街头舞动,人们舀水泼龙。什邡县俗:“凡久旱不雨,地方士绅或神会会首常雇人扎柳条龙,沿城乡游行,群众备水浇泼,求天公降雨”。双流县祈雨在龙王庙举行,同时也采取耍水龙、捉旱魃等形式。其二是“演戏酬神”,如广汉民众为“诚心祈雨,早际甘霖,以安人心”,设坛供奉关岳五圣和龙王雨师,并演戏酬之以祈降雨。其三称之为“打龙潭”,各地都有不少以龙潭、龙王凼之类命名的水潭。天旱时,民众齐聚水潭边,焚香鸣炮,将石块砸进水潭,意在惊醒龙神降雨。其四称“抬雨功”,雨功俗传为专管降雨的神灵,龙颜青面。若久不雨,民众则聚在供奉雨功的庙里,先进行焚献,再将神像抬上椅轿游街,后跟乐队或僧道念经。游街之后,将神像放在太阳下暴晒,直到下雨才请回原位,并焚香化纸表示歉意。其五和一种民间俗谚有关,在灌县、广汉县、双流县等地都有“笑狗天不晴”这一说法,天不晴则可能下雨。于是人们取此义,将狗穿戴上人的衣帽,放在特制的椅轿上,两人抬着游乡、游街,并有乐队跟随,人们则尽情取笑。等等不能尽数列举。
种种表明祈雨不一定像城隍会那样有相对固定的会期、形式和规模,有时也不需要特定的宫观庙宇场所,可以逃过部分因庙产侵占带来的损失,具有相当的自发性和多样性。只要民间有对雨水的需求,人们就会举行各种各样,大小规模的祈雨仪式。加上雨旱对农业丰歉起着决定作用,关系民众生计,因此在民间可能比城隍会还难以禁绝。人们为了预测来年收成,还自创了一些占卜方法。如在除夕夜迎灶之后,“置十二酒杯于灶上,中各贮水,每一杯下一豆,俟元旦察其干湿,以占是年十二月雨旱,遇闰则用十三酒杯。又置豆谷各种于灶上,合成一团,然后用大碗覆之,俟元旦揭开视之,有移至碗边者,则此种是年必主丰收,亦往往有验。”表现出人们对雨水和丰收的渴望。
有时祈雨会请道士做法事,申文上表,祈请有关神祇降雨或降晴。如灌县久旱不雨,则由道士在城内祈神请水:
城内祈神先关闭北门,由道士多人在城隍庙内设坛诵经。七日后燃烛供天。次日有首事、掌坛师率领信众,由轿亭抬上净瓶表文、祭品并彩旗、鼓乐,到灵岩东岳庙或龙溪白龙池请水。请水前由掌坛师指导执事诸人行三跪九叩礼。礼毕掌坛师唱赞焚文,继而将瓶注满池水,仪仗如前,抬回城隍庙供于神前。若雨至,则复礼如前仪,送水回池,始启北门。乡间请水,行礼如仪,但一般多在就近河、井中取水。
关于祈雨法事,有一种说法是“做这请水工作的人,地位愈高,大概求雨的效果愈大”。因此,民众不光对“掌坛师”要求颇高,还会邀请当地政府领导参加。部分县长,乃至区级行政专员,都曾“手捧香盘”混迹于道士之中,“虔诚跪拜”,参与到“请水”仪式中。
但这种规模较大的祈雨法会,宗教界人士并不能主动举办,基本上必须先得到政府的支持和认可。而政府的让步,并不意味着“禁止祈雨”的命令将在之后失去约束力,仅仅是为了应对当时一些特殊情况。
如1937年四川旱灾极为严重,约有130余县受灾,其中26县重灾,64县稍次重灾。面对难以抗拒的灾难和民众的请求,政府不得不选择妥协以“顺应民意”。1937年4月28日,四川省政府电令各县市准其祈雨,认为“此种举措,虽云事涉迷信,但各地灾荒严重,人民望泽情殷,不能不加以曲谅,亦借以顺应民意”,除抓紧筹款赈灾外,要求“各市县政府官民一律斋戒,并禁屠宰,绅民祈有雨者,加以保护,全省合作,庶可感召天和”。佛教界当时即在四川省佛教会号召下,由各寺社举办多场“祈求甘霖早降”的法会。道教的玉参慈善会、青羊宫、二仙庵等祈雨法会也是在此期间组织起来的。
1937年4、5月间,成都市的绅耆善士在玉参慈善会联合组办祈雨法筵,法会由王伏阳主坛,尹仲锡亲自撰写祈雨疏文。4月27日预备工作和仪式已基本完成,慈善会内被重新布置,“请水仪式”也格外慎重,分别从三处取得,二仙庵和孝德慈善会均参与其中:
入门为雨坛,有三丈六尺高,上设神位旗旙,再进大殿为□坛,又进为皇坛,极为庄严。其主坛者,为二仙庵退隐老方丈王伏阳律师,本日午前七时开坛,坛□迎水,据□主坛云,系分三处,一于灌县宝瓶口所取,一于外北万□桥所取,一于新西门孝德慈善会所取。三瓶皆□□坛,外北迎水为二仙庵申方丈竹青主科,灌县迎水,系法筵交际主任文成章君,会同灌县宣化慈善会郑维之君迎归,新西门迎水,系陈光廷杨柱臣两君,同往迎归,所召坛事,皆王老方丈住持,至于会务一切,则由玉参慈善会洪主席幼三办理。
27日中午,绅耆方旭、尹仲锡、刘豫波等,及市各慈善会主席和委员到坛拈香。29日夜,王伏阳正式在雨坛作法,“静中见东北角雨气浓厚,知有感应,或川东北于是时获甘霖矣,正默祷毕,细雨密蒙,已浮佳音,乃谢圣下坛”。《新新新闻》记者认为王伏阳素来“为人和善,修持有年,或无诳语”,于是向川东北各县友好处探寻是否下雨,后被告知“川东北各县日昨多获甘霖”。因此于5月1日以“昨日午夜均喜雨,祈雨果然应验”为题报导了此次祈雨事件,并对王伏阳予以积极评价。祈雨获验后,众绅耆、善士“以旱区辽阔,恐雨泽尚未普遍”,在5月2日再次进行祈祷。时任四十五军军长邓锡侯,对于祈雨法筵也“极表赞同”,因在病中特派秘书石芝于5月2日前往雨坛代为行礼,并附其名于祈雨文书上。
同一时段,青羊宫和二仙庵也进行了设坛祈雨。4月28日,两宫观集合道士百余人,着道袍,捧香盘,张彩帐,持色旗,“并画八卦图,继后着便服,捧香盘者又数十人,以锣鼓喇叭作先导,凝精会神,奉诵经忏”“青羊宫的老君殿,更设坛祈祷,坛堂中央供有老君、玉皇、龙王诸神,两旁置以彩帐色旗,五色缤纷,坛前对立四人诵经,左右地上又跪八人合诵,坛堂下方用八张木方桌摆成八卦形,每桌置花瓶,中插柳条。又三人各持清水一杯举于额上相对密祷,交义行进,用柳叶将水洒于地上,行动极为整齐,如是许久,又变成一列纵队,绕八卦转圆,仍用柳叶将水洒于地上,水洒尽,各人手持三角形色旗一面,仍复原来步法,仍举于额上相对密祷,交义行进”。宫观外信众和游人“绵延半里,车马充塞,颇为热闹”。

事实上,除了政府偶尔会“徇民之请”允许祈雨活动外,通过一些媒体文章,可以发现许多知识精英虽然在批判这类活动,但他们对于祈雨的态度和认知也“模棱两可”。一方面他们认为各类祈雨活动都是“荒诞不经”和“迷信”的,政府准许各县市祈雨实属“掩耳盗铃”。但同时他们又报导着各种祈雨“应验”的事实,比如1934年8月称“湘省祈雨后果然获大雨”;1936年广汉县和新都县分别组织演戏酬神和水龙游街,报导称凡此类活动“须属迷信”,但面对随之而来的降雨,作者开始感到困惑,称其“收效迅速,俨如有求必应之功,当于立坛起连夜果降倾盆大雨”“收效颇大,连日果降大雨”;包括1937年王伏阳祈雨“果然应验”的报导。似乎他们也开始对祈雨到底是“巧合”还是“必然”产生了怀疑。而当这些试图改良民间信仰的知识精英都无法把握祈雨的“本质”时,普通民众在灾害中对于祈雨的需求和渴望似乎也情有可原。对于政府而言,虽然时常以“迷信”视之,但在特殊情况下却不得不以“民俗”待之。
结语
民国时期的城隍信仰和祈雨活动,活跃在成都地区各县、镇,包括成都市区中。城隍出驾仪式往往还是各地规模最大的庙会形式。仪式上的鬼神装扮,和城隍庙内对“地狱”“鬼怪”形象的塑造,向民众传递着“因果报应”的观点。1928年《神祠存废标准》颁布之后,政府仍会在民众的请求下偶尔准许出驾仪式进行。30、40年代,城隍出驾仪式逐渐销声匿迹,并向着“上香祈神”“庙市”的方向发展。祈雨活动也是在相同背景下遭到取缔,但相较城隍信仰而言,其形式和内涵更为丰富,在大多数时候没有城隍出驾那样相对固定的会期和声势浩大的规模,更有自主性和随机性。只要民间有对雨水的需求,他们就会自发组织各种各样的祈雨活动。因此它可以零散而灵动地存在于民间,也更不易禁止。
二者在政府和知识精英多重态度中的境遇也十分相似。他们都被视为“迷信”“落后”“非科学”,阻碍社会进步,遭受批判、取缔和禁止,甚至是无端非议。而由于城隍和祈雨相关神祇,被界定为“山川土地”“风云雷雨”之神,虽未得到像部分先哲、宗教类神祇崇奉那样的认可,但禁令也不及淫祀那样严苛,保留了相对较广的生存空间,民众依然有相关信仰需求。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有时不得不做出一定让步。允许举行城隍会,主要是认识到民间广泛而牢固的信仰基础,移风易俗需要循序渐进。对祈雨的妥协则更现实,因为雨旱直接关系社会稳定和发展。但这并不是纯粹的退让,允许城隍出驾而把鬼神装扮换作手持香盘,支持祈雨的同时仍称其为迷信活动,表明政府仍然要坚持改良民间信仰。
部分知识精英,也开始反思他们曾经对传统不遗余力的质疑和批判。在抨击“进城隍庙赌咒”以解决是非的这种方式时,他们也认识到“司法”的不完善往往让普通民众无法选择法律程序。在批判祈雨为“迷信”时,不仅少有提出“科学”建议,还屡屡惊讶于那近乎“有求必应”的事实,陷入矛盾之中。也就是说他们了解到,受固有观念、社会环境和技术条件限制,面对许多难以抗拒的天灾人祸和社会不公,民众选择传统而非“科学”方式去解决问题,在特定历史环境中,既有其局限性,也有一定合理性。站在今天的角度更可以看到,不仅是普通民众,当时的政策制定和知识精英,尽管无可厚非,也多少陷入了同样的历史和认知局限。
变革与妥协的交织,城隍信仰和祈雨活动在改良、禁止和复苏间的循环往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时期,国家和知识精英在重塑基层社会方面的努力和成效,也体现了民间信仰广泛的民众基础和顽强生命力。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新旧交替之际,“迷信”“信仰”和“科学”之间尚未调和的理论局限与现实矛盾,又给人们对传统与现代的思考带来了新的迷惘和无奈。或许诸多民间信仰、民俗、宗教等传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社会、文化环境中,缓慢、亦步亦趋地从古老走向今天。
(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