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探寻《玛纳斯》史诗的早期演述者是史诗研究者关注的话题,且其热度持续不减,相关讨论亦可谓见仁见智。文章根据柯尔克孜族民间传说和《玛纳斯》的文本内容,阐释了 该史诗“第一位演唱者”——主人公英雄玛纳斯的四十勇士之一厄尔奇乌鲁的演述活动;并在与荷马史诗比较的基础上,对《玛纳斯》的早期演述进行较为系统的论述。
关键词
《玛纳斯》;史诗歌手;
玛纳斯奇;厄尔奇乌鲁
对于《玛纳斯》史诗的产生年代,国内外学者一般认为:最初产生于 9—10 世纪,并且在之后若干个世纪中经过不同时期的史诗歌手们的反复演述,不断雕琢加工,发展和完善,直到16世纪才形成比较完整的文本。但是,谁是《玛纳斯》史诗第一位演唱者?谁是史诗最初的创编者?这是长期困扰国内外学界的问题。尤其是在国内,对此尚无比较系统的梳理、探讨。在无文字时代或文字尚不普及的口头文化盛行的年代,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记录和传承主要以口头形式进行。所有那些具有历史价值并发挥一定社会功能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包括部落长老、创造各类非凡业绩的著名人物(主要是战争英雄和文化英雄)的事迹往往通过口头形式传播并留存在后辈的记忆中。而这正是英雄史诗生成的根基。当然,本文并非要讨论史诗的多种形态、产生机制、产生原因以及其传播方式,而是要从史诗文本和民间传说的脉络中探寻《玛纳斯》史诗在被记录成纸质文本之前的创编者、演述者。
一
玛纳斯奇既是史诗演述创编者,又是《玛纳斯》史诗的传承者。但是,关于《玛纳斯》史诗最初的创编者,除了《玛纳斯》史诗各类口头文本或民间传说中留存的点滴信息外,我们几乎找不到其他任何明确的记录。史诗的很多经典唱本都提到了厄尔奇乌鲁(Erchiuul)这个名字,称其为史诗的“第一位编唱者”或者是“创作者”。也就是说,人们通过史诗文本中留存的点滴记载与民间传说对这位厄尔奇乌鲁略知一二,但对历史上为史诗传承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早期的伟大史诗歌手的名字却毫无知晓。在柯尔克孜族民间有一句俗语称:“要成为托合托古勒(Toktogul)那样的歌手,托勒拜(Tolubay)那样的圣哲。”很多人根据这句俗语推断,柯尔克孜族历史上可能确实曾出现过一位名叫托合托古勒的声名远播的伟大史诗歌手。根据民间传说,正是这位天才史诗歌手把厄尔奇乌鲁以来在民间以不同形式传播的《玛纳斯》的零碎史诗片段串联汇编成了一部韵文体、结构完整的史诗作品。对于这位传说中的大歌手,除了上面那句民间广为流传的俗语或传说之外,我们依然说不清其身世。近年来,有学者从点滴的历史传说资料中挖掘论证,认为这位名叫托合托古勒的歌手生活在14—15世纪。在吉尔吉斯斯坦19—20世纪的大玛纳斯奇萨恩拜·奥诺兹巴克(Saginbay Orozbak,1867—1930)的《玛纳斯》异文里还提到了一位类似于厄尔奇乌鲁的另一位名叫加依桑·厄尔奇(Jaysang Irchi)的武士歌手,说他仅描绘毡房装饰的片段就咏唱了半天之久。与上述第一位歌手一样,关于这位传奇歌手也没有任何新的材料可作辅证,甚至在其他任何玛纳斯奇的口传文本中也未提及过他。所以,很多学者提出后者不具有普遍性,关于其最先创编《玛纳斯》的说法可以说只是一种猜想,根本没有任何强有力佐证。在《玛纳斯》史诗的口头传播史上,虽然上述两位史诗最初演述者的身世资料只是零星地出现在史诗文本之中,但或多或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

史诗最初创作和歌唱者的名字出现在史诗内容中的现象极为普遍。一些世界著名史诗中都记载有该史诗最初演述者的名字。比如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歌手德摩道科斯,《摩诃婆罗多》的创编者为婆罗门先知黑岛生(Krsna Dvaipayana),苏格兰的莪相,以及高加索地区诸民族和中亚地区流传的英雄史诗《阔尔奥格里/呙尔奥格里》主人公阔尔奥格里(盲人之子)或呙尔奥格里(坟墓之子),乌古斯史诗《先祖 阔尔库特书》中的阔尔库特等等。
根据目前的资料,关于玛纳斯奇比较明确的信息最早出现于19 世纪末。即便18—19世纪的一些玛纳斯奇的名字也只是在 20 世纪的《玛纳斯》文本以及在一些民间即兴诗人的作品中有所提及。但令人奇怪的是,在广大民众的记忆中,甚至在18—19世纪出现的交莫克楚口中,除了上述最初歌者厄尔奇乌鲁的名字之外,其他人的名字却一个都没有保存下来。为什么《玛纳斯》史诗的绝大多数古代演唱者的名字都没有保存下来呢(这里不包括关于史诗最初创编者的信息)?按理说,凡是继承了前辈传统的史诗歌手最起码应该记住其中某些代表性人物的名字。但是很显然,20 世纪之前每一个功成名就的玛纳斯奇都对前辈歌者的名字隐讳不谈。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解释。一是史诗在民众心中的崇高地位。柯尔克孜族认为《玛纳斯》史诗的文本是神圣的,无论谁都不能轻易对其进行随意改变。玛纳斯奇只是一位演唱家,只是古老故事的转述者,只是用自己的诗句复述传统故事的内容。歌手在演唱过程中对于传统的任何一个有意无意的插叙,任何一个改动都被认为是对传统的破坏。歌手在演述中随意的个人发挥都是不被允许的。在听众看来,史诗歌手即使是顺便插入几句导言式的抒情插叙或一些分支情节,也被认为是破坏了史诗的传统结构和规范内容。按照这种观点和逻辑,可以说《玛纳斯》史诗的内容是自始至终保持如一的。因此,在很多史诗歌手的唱词里只出现厄尔奇乌鲁这位最初歌者的名字,而其他前辈玛纳斯奇甚至自己的师傅的名字都多被遗忘了。他们试图以此来维护自己唱本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当然,这种神圣性不仅是对史诗文本的崇拜,可能更多的是源于人们对英雄主人公玛纳斯为代表的系列英雄人物的崇拜,与柯尔克孜族古老的祖先崇拜、英雄崇拜有关。二是在柯尔克孜的交莫克楚群体中,自古就在一定程度保持着对“神灵梦授”的笃信。这种观念的重要性可能并不亚于前者。很多知名玛纳斯奇,尽管都拜师求艺,却并不去强调自己的学艺过程,反而将自己的史诗演唱用“梦授”来解释,说自己在梦中遇见英雄玛纳斯或厄尔奇乌鲁等圣灵,是由他们把史诗“梦授”给自己。将其看作是某种天意的启示,把它解释为一种超自然力的干预,仿佛正是这种超自然力召引他们去执行演唱史诗的使命,使他们这些被选中的人领悟到《玛纳斯》的“学问”。这就导致了玛纳斯奇群体中的一种普遍认同,那就是无论哪一位玛纳斯奇,想从前辈歌手那里学会整部史诗根本不可能。虽然很多来自不同流派的玛纳斯奇的演唱内容基本一致,但每一个歌手都自觉地断定自己的演唱内容完全是独创的,是受了“神意”的指使而演唱的,所演唱的文本属于自己个人的“艺术创作”。这成了玛纳斯奇群体的一种默契,任何一个玛纳斯奇都刻意维护它。诚然,《玛纳斯》的传承有不止一种途径,除了师徒相传之外,家族内传承也是《玛纳斯》传承中的重要方式,这种传承方式是父辈传给儿子或者家族内的另一名后辈成员。但即便如此,“玛纳斯奇”还是会坚持“神灵梦授”的观点,坚持自己对“圣灵”的崇拜。这种超自然信仰的事实本身是不可忽视的,具有深厚的民间观念基础,而这也顺理成章地排除了提及前辈歌手姓名的可能性。毫无疑问,这种笃信虽然遮蔽了口头史诗传承链中的师徒关系以及处于传承链前端的前辈史诗歌手,也遮蔽了史诗长期传承过程中先辈玛纳斯奇们在史诗传承中所发挥的作用,但这却也丝毫没有影响史诗最初编唱者的名字被人们永久牢记。

黑格尔指出:“史诗作为一部实在的作品,毕竟只能由某一个人生产出来。尽管史诗所叙述的是全民族的大事,作诗者毕竟不是民族集体而是某个个人。尽管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的精神是史诗的有实体性的起作用的根源,要使这种精神实现于艺术作品,毕竟要由一个诗人凭他的天才把它集中地掌握住,使这种精神的内容意蕴渗透到他的意识里,作为他自己的观感和作品而表现出来。”在《玛纳斯》传统中,厄尔奇乌鲁便是这样的人。在柯尔克孜族传说及绝大多数史诗文本中,《玛纳斯》史诗的第一位演唱者是跟随英雄玛纳斯东征西战建立赫赫战功的四十勇士之一厄尔奇乌鲁。也可以说,他是我们已知的最早的 《玛纳斯》史诗歌手。他在史诗中充当了勇士和歌手的双重角色。在战争时期,他是一名骁勇的将士。在和平时期,他则是一个无人可比的歌手,在各种大型集会上专门用歌声赞颂玛纳斯的英雄事迹。也就是 说,他既是英雄时代的亲历者,也是史诗的首唱者。
从语义学方面考察,Erchiuul(厄尔奇乌鲁)从词面上就非常明确地蕴含着“歌”与“歌手”的双重含 义。这个词由名词“er(厄尔)”+附加成分后缀“-chi(奇)”+名词性修饰词“-uul(乌鲁)”构成。在柯尔克孜语中,“er”从广义上表示古往今来所有韵文体作品,狭义上指民歌和短篇的诗歌。“-chi”则是指具有某一方面专长的艺人或匠人。比如“玛纳斯奇”指专门以演唱《玛纳斯》史诗为职业的民间艺人,“铁密尔奇”指铁匠,“考姆兹奇”指考姆兹琴手等。“厄尔奇”便是指才华出众具有即兴创编诗歌能力的民间歌手。“-uul(乌鲁)”作为名词,其原意为“儿子,小伙子”,而在史诗中的引申意可以理解为“勇士”。比如在玛纳斯的四十勇士名单中除了“厄尔奇乌鲁”之外还有另外一名叫“波孜乌鲁”,意为“棕色脸堂的勇士”。在这里, “乌鲁”作为名词性修饰词附加到了“厄尔奇”一词后面,构成了具有多重含义的特有专属名词,既“具史诗演唱才华的勇士”。以上信息完整地揭示了厄尔奇乌鲁作为史诗歌手的身份。显而易见,“厄尔奇乌鲁” 并非这一史诗人物的本名,应该是他的绰号,但这个绰号影响力极大,以至于完全遮蔽和替代了这位英雄的本名,成为《玛纳斯》史诗独一无二的演述者、创造者的文化标识和生命符号。意味深长的是,厄尔奇乌鲁的父亲额拉曼(Eraman)也并非等闲之辈,而是一位能通过石子和牲畜的肩胛骨给人看相、算命、驱邪治病的占卜师和巫师。这也从另一个角度确证了厄尔奇乌鲁不仅是一位浸染了柯尔克孜族古老萨满文化因素的人物形象,而且从家族血缘和民族文化两个层面呈现出他何以被誉为玛纳斯奇鼻祖,深受后辈玛纳斯奇敬仰的深层文化因素。这就不难想象,为什么是他,而不是别人独享《玛纳斯》史诗第一位歌者的荣耀。

在这一点上,厄尔奇乌鲁与荷马有一定相似之处。“歌手是介于神和听众之间‘通神的’凡人。通过他们,听众了解发生在以往的重大事件。这批人司掌陶冶民族精神的教化,坚定人们仰慕和服从神明的信念。如果说《伊利亚特》里征战疆场的勇士们集中体现了古代社会所崇尚的武功,《奥德赛》里能说会道的诗人们则似乎恰如其分地突出了与之形成对比和相辅相成的‘文饰’。……荷马除了把征战(即会打仗) 视为神祇赐送给某些(有幸接受此项馈赠的)凡人的能力外,还特别提到了歌舞和智慧。作为歌手的‘代表’。他似乎要人们相信,像宙斯钟爱(或养育)的王者们一样,像嗜战如命的英雄们一样,高歌辞篇的诗人也是人中的豪杰。事实上,他在赞美诗人忠诚(eriēros)的同时,也称之为‘英雄’”。正像希腊史诗的创造者荷马一样,厄尔奇乌鲁也是《玛纳斯》史诗的原创天才,他的诗篇被后继演述者们持续不断地复制着。
拥有战绩武功的歌手受到人们尊敬古已有之,在希腊史诗中德摩道科斯被带到阿尔基努斯面前时,人们给他拿来“银钉嵌饰的桌椅”,将竖琴挂在他的头顶上面,殷勤款待他。此外,《奥德赛》中还有一 位同样受人尊敬的著名歌手菲弥俄斯。除此之外,克尔特人的预言家和诗人,史诗传统的保持者兼魔法师雯尔在爱尔兰小郡主的宫廷;婆罗门在印度显贵家庭中因为了解其家族谱系,作为史诗传统的体现者而在节庆和宗教仪式上演唱关于祖先的事迹,受到崇拜。在古老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贝奥武夫》中侍卫武士歌手是君王、首领亲信之人,赐坐在一边,在宴会上,在竖琴的伴奏下说唱古老的往事。凡此种种,都表明古代史诗歌手所扮演的荣誉角色。厄尔奇乌鲁在史诗《玛纳斯》中不仅作为勇士浴血奋战,也作为歌手第一个创编和传唱了这部史诗。因此,他几乎被后世所有的玛纳斯奇视为《玛纳斯》史诗演唱这一职业的佑助神。玛纳斯奇们把自己的学习和演唱史诗的活动自觉或不自觉地同他联系起来,以极大的 热情说他在一个不平凡的时刻进入自己的梦乡,介绍玛纳斯及身边的英雄人物,甚至会强制性命令演唱 《玛纳斯》,并威胁说如果不唱自己就会残废或遭受肉体的病痛。而当玛纳斯奇开口演唱时他便把史诗的内容源源不断地灌输到前者脑子中,鼓励和帮助他完成演唱《玛纳斯》的使命。这是玛纳斯奇中存在的一种共识。任何一位功成名就的《玛纳斯》歌手也许可以规避自己师傅,但却不会不提及厄尔奇乌鲁。

《玛纳斯》史诗何时产生,从何时起在民众中演唱,目前是《玛纳斯》研究领域悬而未决的问题。与此相关,史诗最初的演唱者到底是谁?这一问题至今依然是被学者们热烈讨论的议题。但是,各个时代的玛纳斯奇根据自己传唱的《玛纳斯》的内容,认为史诗的主人公英雄玛纳斯的四十勇士之一厄尔奇乌鲁就是史诗的第一位演述者。
二
苏联时期有很多学者对厄尔奇乌鲁的身世及史诗中的角色进行过研究。其中,哈萨克斯坦 M. 阿乌埃佐夫和吉尔吉斯斯坦柯·热赫玛杜林、穆·玛木若夫等的研究成果比较突出。他们一致认为玛纳斯的四十勇士之一厄尔奇乌鲁作为武士兼歌手就是《玛纳斯》史诗的第一位创编者和演述者。无论如何,厄尔奇乌鲁是史诗中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这一点与其在史诗中所承担的角色也十分吻合。此外,史诗中还描述他不仅仅是大型婚礼、盛典、祭奠等仪式的主持人和司仪,而且跟巫师、占卜师等一样,是专职的阿肯(即兴歌手)。在《玛纳斯》的众多英雄人物中,具有歌手兼勇士双重身份的也只有厄尔奇乌鲁一人。他作为史诗故事的亲历者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
厄尔奇乌鲁与玛纳斯一起创建英雄伟业,并以亲历者的身份用歌声赞颂玛纳斯的业绩,创造了《玛纳斯》史诗最初唱本。比如当英雄玛纳斯启程前往征讨肖如科途中额热曼之子厄尔奇乌鲁,在英雄身旁放声歌唱;他与玛纳斯并辔前行,一边将豪迈的战歌高唱。在居素普·玛玛依、萨恩拜·奥诺兹巴克等经典唱本中,玛纳斯为了迎娶铁米尔汗之女卡妮凯来到对方宫殿外时,也有厄尔奇乌鲁高唱歌曲的情节。也就是说,无论启程前召集兵马或者与亲近之人相遇,厄尔奇乌鲁都会用即兴的歌声向玛纳斯汇报兵马筹备队伍运行情况。这给我们提供了以下三个信息:第一,英雄前去迎亲或者出征,勇士们在途中所发生的所有情况,所见所闻,四十勇士状态等厄尔奇乌鲁都会编成歌词用歌声向玛纳斯详细汇报。第二,用歌声向对方的官民传达英雄本次前来的目的和原因。第三,不管在何种情况下都要向人们介绍和赞颂玛纳斯 的英雄伟绩。相比于其他玛纳斯奇的唱本,居素普·玛玛依唱本中对于厄尔奇乌鲁有最明确最生动的描述,其人物性格也极为鲜明。比如对卡勒玛克怀有世仇的巨富额拉曼从自己统管的喀拉卡勒帕克 (Karakalpak)、吐克曼(Turkmen)、居尔居特(Jurjut)、朱达(Juda)、巴壤(Barang)、乡卡依(Shangkay)、喀勒恰(Kalcha)、克依巴(Kiba)、塔吉克(Tajik)、斯亚(Siya)等部族中挑选二十名能征善战的年青勇士,并把自己的儿子厄尔奇乌鲁也加编其中,让弟弟克尔哥勒率领前往投奔玛纳斯,并与其他各方前来投奔的勇士组成四十勇士,跟随玛纳斯征战,同入侵者进行顽强斗争。

厄尔奇乌鲁以战士和歌手的双重身份出现,而他的歌手身份是他不同于其他勇士的突出特征。他不仅战功显赫还总是以动听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打动人心、说服众人。史诗中还明确记录了厄尔奇乌鲁受命编唱英雄玛纳斯家族的事迹,承担了要将玛纳斯的业绩用歌声传给后代的神圣使命。比如在史诗中,玛纳斯率领大军远征,不慎遭敌人暗害,后颈部被空吾尔拜的毒斧砍中而被迫在阿勒曼别特的反复劝说下离开战场回塔拉斯养伤。空吾尔拜则幸灾乐祸,派人给各地的亲信送信,聚集大军,广罗将士,欲将玛纳斯的大军一网打尽。玛纳斯手下的哈萨克汗王阔克确率五万人马进行堵截,与空吾尔拜展开大战,但终因寡不敌众,被空吾尔拜、穆拉迪里、涅斯卡拉的大军包围,最终自己也落入敌手。空吾尔拜驱赶着阔克确行进,阿勒曼别特和楚瓦克两位英雄从正面突然出现堵截敌人。空吾尔拜一时心虚,在惊慌中挥刀砍下阔克确的头颅提在手上逃跑。两位英雄抱着阔克确的无头尸体痛哭流涕,悲伤无比。当阔克确无头 尸骨被抬到军中时,阿勒曼别特预感到大难即将临头,他准备破釜沉舟、与敌人决一死战。在危难时刻他与各位勇士诀别。他做为大军总首领向各位勇士又一次强调各自的职责并一一与他们拥抱。他对玛纳斯四十勇士之一的厄尔奇乌鲁特意叮嘱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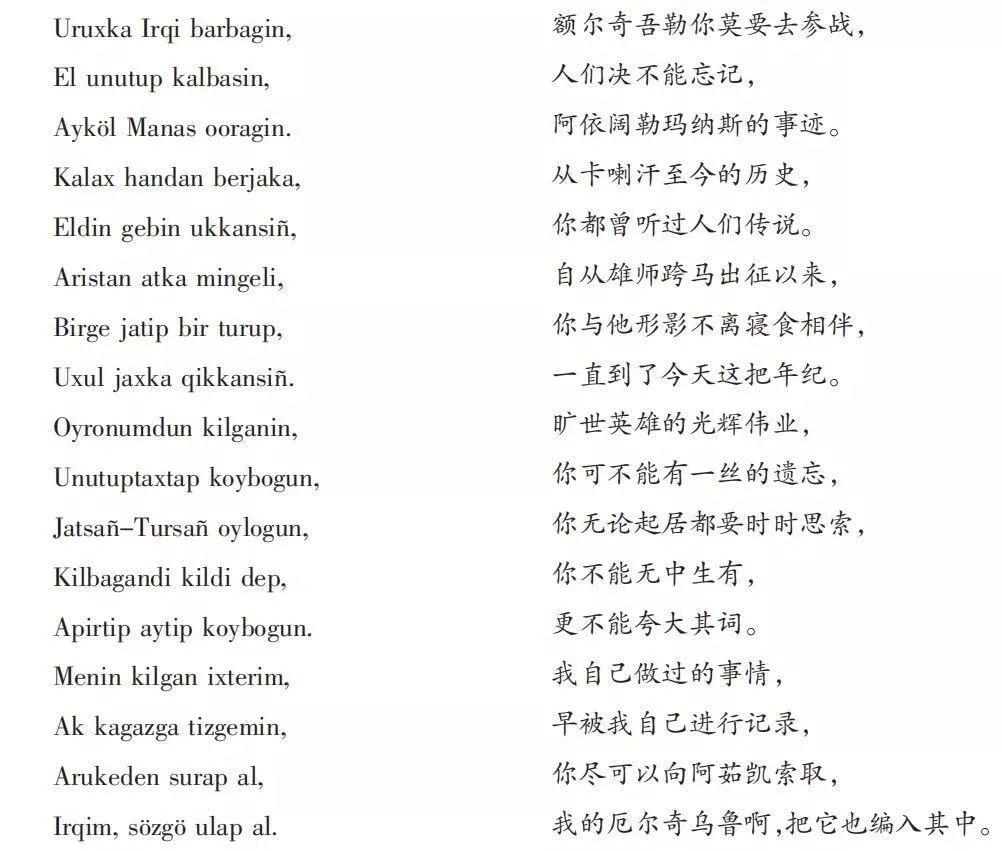
除了居素普·玛玛依唱本,吉尔吉斯斯坦20世纪最著名玛纳斯奇萨恩拜·奥若孜巴克、萨雅克拜·卡拉拉等许多玛纳斯奇的唱本中无不如此。史诗中,他因超人的口才和机敏而受到玛纳斯的器重,被接纳为四十勇士之一员。关于他的事迹,在萨恩拜·奥诺孜巴克的唱本中,有这样的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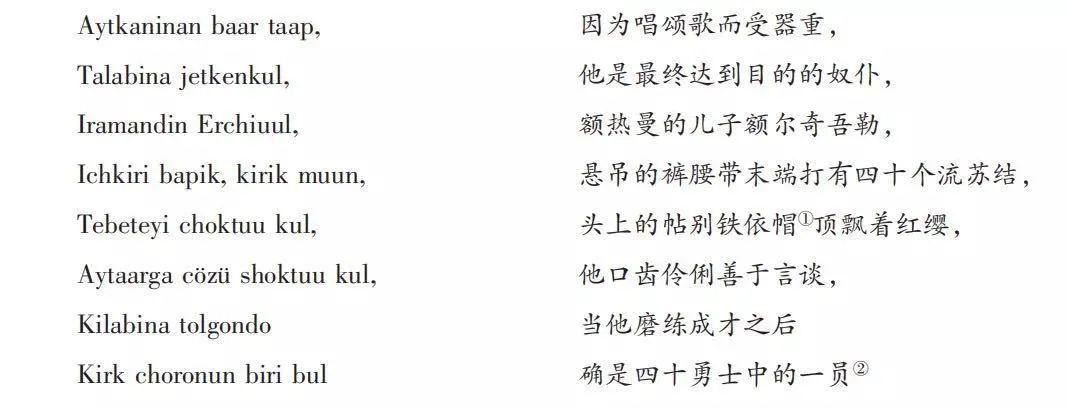
在萨恩拜·奥诺孜巴克的唱本中还有以下记述,说额热曼之子厄尔奇乌鲁原名叫喀拉太,由于他心灵手巧、勤快能干,口齿伶俐、能歌善辩,头脑机敏、聪明过人,成为玛纳斯的勇士之后,因其出众的才华而使他原名喀拉太逐渐被厄尔奇乌鲁(歌手勇士)的绰号所替代。萨雅克拜·卡拉拉耶夫和居素普·玛玛依唱本中,厄尔奇乌鲁都是主动前来投奔玛纳斯。史诗中经常出现这样一句谚语:“杀敌的是众勇士,名声却留给玛纳斯”。很显然,玛纳斯周围的四十勇士奋勇抗敌,但荣誉却都归结到玛纳斯头上。而跟随玛纳斯参加无数惊天动地的战斗,目睹勇士们所向披靡勇敢杀敌的现实场景,与英雄同悲欢的厄尔奇乌鲁的功绩就是把英雄玛纳斯的事迹编成歌词传唱给后人。
三
根据柯尔克孜族古老的民间习俗可以断定,厄尔奇乌鲁是在英雄玛纳斯去世时通过编唱送葬挽歌创编《玛纳斯》史诗。也就是说,他作为亲历者和见证者将英雄的事迹以霍硕科(koshok,哭丧歌或挽歌)形式当众唱出来。从此,这首挽歌开始在民间以口头形式广泛传唱,并在不同时期史诗歌手的传承加工下逐渐发展成了今天的《玛纳斯》史诗。自古以来,柯尔克孜族家族部落中凡是有德高望重的老者去世,人们都要用悲哀的歌声歌颂亡者业绩,以此表达对死者的怀念。死亡无论对哪一个民族都是一件具有仪式感的重要事件,尤其是一位超级英雄的亡故,给人们带来的心灵冲击是无与伦比的。英雄玛纳斯作为古代柯尔克孜人的精神支柱,其亡故给人们心灵带来的伤痛无论如何都值得人们永远纪念。因此在其葬礼上,由一位跟随其征战,亲历和见证过他英雄伟业的天才歌手用哀婉的歌声向人们回忆其业绩,缅怀其音容笑貌,赞颂其英雄伟业自然是最合适的纪念方式,也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深厚的民俗文化根基。这就类似于格雷戈里·纳吉对于印度拉贾斯坦邦史诗传统中关于召唤英雄神灵的描述。这种死亡事件作为故事生成点而发挥作用,导致神格化,导致崇拜,导致祭仪,最终导致叙事,这种叙事伴随着仪式而得以演述,以召请死者魂灵的降临。英雄亡故后的丧葬仪式上哭唱哀歌是人类古已有之的普遍传统。在 《奥德赛》第 24 卷中,阿基琉斯亡故,九位缪斯神女附在他身上唱哀歌,轮流交替,彼此呼应,海中神女放声哀号。在《伊利亚特》第 24 卷中,在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的儿子赫克托耳的尸体前,歌手们唱着诀别的哀歌。二十位勇士围绕着贝奥武甫的陵墓策马而行,一边哭诉,一边唱颂歌。哥特族人首领阿季拉亡故,人们选拔出最优秀的骑士绕着安放其尸体的山岗唱起赞歌。这类哀歌在演唱过程中的哀怨、哀号、泣别等抒情因素很自然地同关于死者事迹的追述、回忆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也与可以单独称之为挽歌的成分交替出现。它们彼此渗透彼此交融,而需要追述一位英雄一生的事迹时,即兴创作,即兴吟唱起决定作用。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有学者从柯尔克孜族历史的世俗生活角度出发,对《玛纳斯》史诗的阔绍克(哭丧歌、哀歌或挽歌)产生说提出质疑。其理由是给人们带来无限悲伤或让人回忆起悲惨往事的哀歌虽具有震撼人心的神圣性和仪式感,但基于其特殊的文类特征,受特殊预警的影响,它只能在葬礼上或者在其他悲哀的场合演唱,而不能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演唱。在当前的民俗文化语境中观察,情况的确如此,它在很大程度上受演唱时间及演唱语境的限制。但是,在古代是否也是如此就另当别论了。
《玛纳斯》之所以被人们千年传唱,历久弥新发展到今天这样宏大的规模和高度艺术化的程度有多方面原因,并非一位神一般存在的厄尔奇乌鲁和神圣的送葬哀歌那么简单。我们撇开史诗所蕴含的历史层面,仅从其内容所呈现出的多种文类融合特征以及传承方式观察,《玛纳斯》确实是在柯尔克孜族民间文学根基上逐渐发展完善而成的。史诗中除了丧葬歌之外,值得我们关注的还有“加尔恰柯茹(jarchakiruu,仪式前奏歌)”,“乌楚拉术(uchurashuu,见面歌)”,“阔舒托舒(koshtoshuu,诀别歌)”,“玛克托(maktoo,颂 赞歌)”,“阿尔曼(arman,哀怨歌)”等多种形式的柯尔克孜民间歌谣以及其他很多规模较小的口头史诗作品和各种其他文类。它们无一例外地在史诗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每一种文类从不同 侧面反映柯尔克孜族生活,形式古老,在民间广为流传,它们随时可以编入史诗中演唱,且不受时空和语境严格限制。比如在重大仪式开始之前召集人为了向众人转达汗王的指令,宣布庆典仪式竞赛的规则,介绍主要客人嘉宾,用韵文演唱的“加尔恰柯茹(仪式前奏歌)”蕴含着回顾部落历史,赞颂部族英雄业绩, 描述部落礼俗等信息。《玛纳斯》史诗中,玛纳斯的婚礼上,在汗王阔阔托依的周年祭典上,就有“加尔恰柯茹”这类歌谣的非常典型的案例。而在《玛纳斯》中与“阿尔曼(哀怨歌)”这一文类有关的专题片段就有“卡妮凯的哀怨(Kanikey din armani)”“阿勒曼别特的哀怨(Almanbettin armani)”等经典片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卡妮凯的歌和阿勒曼别特的歌除他们两人演唱外,其他所有的类似的歌都是通过厄尔奇乌鲁之口唱出来的。

可以肯定,厄尔奇乌鲁在柯尔克孜族传统习俗语境中,以英雄业绩见证者亲历者的身份创编并首次演述了《玛纳斯》史诗。关于史诗故事的亲历者讲述故事其实也有古老的历史渊源和理论根基。陈中梅通过梳理西方荷马研究史提出,荷马史诗的故事来源有两个:第一,荷马本人的神赋论,也就是被朱光潜所 称为的“灵感说”。荷马在他史诗的开头便向缪斯女神呼求灵感。这种行为便暗示一种诗的创作理论——即诗篇的形式乃是神赐灵感的结果。在《伊利亚特》中,荷马吁请缪斯给他唱诗的灵感:“歌唱吧,女神!……”以此既到位地表达了对神的敬仰,也非常得体地表露出请求神灵助佑,祈望与神力沟通的心情。这种“神授观”与玛纳斯奇学唱史诗如出一辙。在《奥德赛》第 8 卷中,“满足了吃喝的欲望”,缪斯催动歌手唱响“英雄们的业绩”或“勇士们的作为”……诗人接受神的馈赠,受神的点拨,他们讲诵神的意志,歌唱神和凡人(人间豪杰们)的业绩。这种吁请神灵的方式也与居素普·玛玛依在《玛纳斯》史诗的开头部分所唱的“哎……哎……依,我要演唱英雄玛纳斯,愿他的灵魂保佑我,让我唱得动听而真挚”基本相同。19 世纪,俄罗斯语言学家拉德洛夫在田野调查中询问一位玛纳斯奇如何能记忆和演唱如此宏伟的史诗时,他回答说:“我能够演唱所有的歌,因为神灵赐予我这样的能力。万能的神灵把这些词句放入我的嘴里,所以我无须去寻觅它们。我没有背诵任何一首歌。我只需开口演唱,那些诗句就会自动从我的嘴里流泻而出。”第二,特洛伊战争的现场目击者的口述。荷马没有把自己无条件地囿限于神赋论的狭隘天地里,而是勇敢地迈出诗歌神赋的虚渺,另辟蹊径,走向目击者讲述的真实。在荷马看来,神和神力几 乎无处不在地参与到史诗英雄的行为中,觉察到了神无处不在的咄咄逼人的目光。比如在《奥德赛》中雅典娜几乎全程伴随着奥德修斯返乡后的复仇。宙斯率领众神端坐在奥林匹斯山上黄金铺地的宫殿中,一边喝着可口的琼浆,一边聚精会神地俯视着特洛伊人的城邦。神在观察特洛伊战争的进程,他们是那场旷日持久、给交战双方造成重大伤亡之战的目击者。荷马生活在一种重视亲眼目睹和眼见为实的文化氛围中,他会很自然地把古代诗人对“知”的理解融入自己的诗篇制作中去。奥林匹斯神明,尤其是缪斯姐妹和阿波罗,是人间事物的见证者。缪斯无所不在,无所不见,无论在奥林匹斯神山,还是在人间的什么地方,她们都能目睹普天下的风云变幻,她们明察秋毫的眼睛总是“在场”,录采所有的事情,随时能为诗人提供故事情节,帮助他们如愿以偿地讲诵人们爱听的往事,把神的活动揉入民族的历史,借助缪斯赐予的神力,构组传世诗篇。当然,在荷马的心目中,奥德修斯是特洛伊战争的当事人。荷马的明智在于把 奥德修斯放入“诗评”的语境,借助他既是战争亲历者,又是重现目击者知识的故事高手,明晰而又恰如其分地表述了他的诗歌来源。如果荷马史诗中歌手们是借助神灵完成自己的使命的话,那么柯尔克孜族史诗歌手玛纳斯奇则不仅求助神灵佑助,而且还有一位史诗故事亲历者或是直接参与者厄尔奇乌鲁 所创作并留下的英雄故事成为他们史诗演述的滥觞。从这一点而言,玛纳斯奇们是幸运的。厄尔奇乌鲁 亲自参与并见证了英雄玛纳斯所有的英雄业绩,而且凭借自己的才能将英雄的故事创编成诗歌演唱出来,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玛纳斯》演唱群体崇拜敬仰的神一般的人物。

玛纳斯奇是《玛纳斯》史诗的创作者、演述者、传承者和守护者,在《玛纳斯》的传承中具有重要作用。无论《玛纳斯》史诗在柯尔克孜族民众中具有多么崇高的地位,无论其在柯尔克孜族传统文化体系中占 据多么重要的位置,也无论其从产生和发展过程具有多么凸显的集体性,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那样,它归根结底还是民间个别富有才华的天才的杰作。作为柯尔克孜族历史集体记忆的《玛纳斯》史诗虽然从文本层面以及创作层面都有集体性特征,但每一位天才的大玛纳斯奇在史诗传承中所起的作用不可替代,每一个富有才华的玛纳斯奇都在其中贡献了自己的才华与智慧。以说唱史诗为职业生涯的这些天才歌手们,不断传承、充实和丰富史诗的内容,将它变为民族的口头遗产和瑰宝,并使这部史诗在不断地循环往复的演述中得到拓展、提高和完善。玛纳斯奇群体在《玛纳斯》史诗传承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毋容置疑,作为史诗最初演述者的厄尔奇乌鲁,犹如古希腊史诗的演述者荷马一样,受到神的点拨和关爱,以自己的歌声回报神的恩典,用自己的歌喉为英雄玛纳斯树立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更为后人留下了永恒的精神寄托。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研究》2020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