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语
陶立璠先生一生从事民族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理论教学。在访谈中,他回顾了中国民协 1978 年恢复工作以来的学术史。20 世纪 80 年代,在中国民协的倡导和组织下,中国民间文学队伍不仅重新集合起来,而且日益发展壮大,开创了中国民间文学搜集、抢救、保护和研究的“黄金时代”:建立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中国民俗学会、中国神话学会等研究组织;创办《民间文学论坛》学术理论刊物、主办刊授大学、编写教材、培训培养人才;开展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日联合调查等学术活动。
关键词
民研会;《民间文学论坛》;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日联合调查
一、难忘1978年
我是中央民族大学的退休教师。我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以下简称中国民协)的关系,属于中 国民协体制外编制,但从业务关系上,我又是中国民协体制内的学者。某种意义上,我的学术活动与 民协的关系更加密切。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是中国民协重要活动的直接参与者。
回顾我和中国民协的接触,是在“文革”以后。原来我在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讲授《文学理论》《古代文论》等课程,业余研究少数民族文学。1978年以后,我的教学、研究方向,完全转到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引起我学术生涯的这种变化,很重要的原因是 1978 年的“兰州会议”。兰州会议是由西北民族学院(现西北民族大学)发起、组织召开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教材编写暨学术讨论会”。 这次会议是“文革”以后规模最大,也是最有影响的一次会议。按照钟敬文先生的说法,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会议。因为这时候开始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民族文学终于迎来了初春的景色。我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做了很长时间的民族文学研究,中央民族学院和西北民族学院是兄弟院校,于是我接到邀请,参加了这次教材编写会议。
说来也巧,就在我赴兰州的途中,在首都机场,遇到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简称中国民研会, 1987年改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参会的杨亮才先生。他作为中国民研会恢复重建领导小组成员,应邀参加这次会议。他有篇文章《同是民间守望人——祝贺立璠兄七十岁生日》,专门回忆了兰州会议 的情景。之后的岁月里,亮才兄常常推荐我参加中国民协的学术活动,并介绍我加入中国民协。于是 我和中国民协相识、相知,相伴至今。
这次兰州会议,钟敬文先生参加了。那时钟老76岁,身体还很健朗。大家也都精神振奋 , 想干一些事情。压抑了多年的学术低迷状态一扫而空。我那时还很年轻,40岁左右。参会的也是一些和民族文学有渊源的像我这个年龄的中青年,如柯扬、段宝林、魏泉鸣、郝苏民等。1978年的兰州会议,对动员和组织民间文学研究力量,开展民间文学研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一时期是中国民研会恢复、重建时期。贾芝、杨亮才、陶阳、张文等民研会的老同志组织进行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为恢复和重建民间文学学科,大家走到了一起。
二、民间文艺的80年代
继兰州会议之后,1979年夏,在成都又一次召开了“少数民族文学教材编写会议”。这次会议的另一成果是发起成立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学会的名誉理事长:周扬;理事长:贾芝;副理事长:马寅、马学良、王沂暖、额尔敦·陶克陶和王松;秘书长:杨亮才;副秘书长:陶立璠、段宝林、魏泉鸣、忠禄(锡伯族)、黄勇刹(壮族)、李瓒绪(白族)。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民间文艺的复兴时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先后在北京、广西武鸣、吉林延边、新疆乌鲁木齐召开多次学术会议,推动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这些活动都是在中国民研会的参与指导下进行的,因为中国民研会是群众性组织,团结了全国的民间文艺研究者。当时所有的民间文学研究者,无论是从事教学的,还是从事研究的,都团结在中国民研会周围。中国民研会组织了许多学术会议,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诗人、歌手座谈会,为“文革”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民间歌手平反。因为“文革”以后,这些少数民族的歌手都心有余悸,在北京开会,给他们平反,意义深远。
这一时期,全国各高等文科院校普遍开始讲授民间文学课程。这是一件大事情。因为只有民研会这个组织还不行,还必须在高校里培养民间文学人才,在高校本科恢复民间文学的教学。在北京,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央民族学院率先开设民间文学课程,其他地方的一些高等院校,如辽宁大学、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学院,也都恢复了民间文学的课程。同时,教材的编写也跟上来了。最早出版的有钟敬文先生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乌丙安的《民间文学概论》、张紫晨的《民间文学基本知识》、段宝林的《中国民间文学概论》、陶立璠的《民族民间文学基础理论》,以及云南朱宜初和李子贤主编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论》。这些都是当时比较早的一批概论性的著作,为民间文学的全面恢复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的成立,也和中国民研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首先,成立中国民俗学会的倡议,是由时任中国民研会副主席的钟敬文先生,联合顾颉刚等7位教授提出的,并在中国民研会第二次全国会议上,再次发出呼吁。在这一呼吁下,许多地方成立了相应的民俗学研究小组。其次,中国民研会专门成立了民俗学部,钟敬文担任主任。当时就中国民研会成立民俗学部来讲,说明民俗学研究已引起国家机构的重视。后来,中国民俗学会的成立得到胡乔木、周扬一些领导的重视。1983年的春天,中国民俗学会正式成立。
此外,和民间文学相关的国家重点项目,纷纷上马。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参与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是由德高望重的文化学者姜椿芳先生牵头的。姜椿芳先生在“文革”期间受牵连蹲了监狱。在监狱里,老先生就想,等有一天出狱以后,就筹划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这个大工程,中国民研会也是积极的参与者。当时我们参与的主要是《中国文学卷》。《中国文学卷》里有两个分支,一个分支是民间文学,由钟老担任主编;还有一个分支是少数民族文学,由马学良先生担任主编,我和刘魁立担任副主编,从框架的拟定,组稿、撰稿,到最后的修订,主要是由我来完成。借着这个项目,我跑遍了全国民族地区,和作者见面、约稿,进行沟通。《中国文学卷》少数民族文学分支有二百多条,收录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和民间文学作品,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从来没有过的。第一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工程历时15年(1978—1993),1994年74卷本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这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中国从来没有编过百科全书,因为这套书、专门成立了中国百科全书出版社。

80年代还有一个国家级项目是“中国民间文学集成”,习惯称作“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这个工程主要是中国民研会主持的。项目进行得很艰难。从课题的申报到最后结项中间经过很多曲折。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后来并入周巍峙部长主持编纂的“中国民间文艺十套集成志书”。这一工程从动议到1989年,用了七八年的时间进行民间文学普查。而这次普查,从民间文学研究角度来讲是空前的,动员了全国的力量,涉及200万人次。各地的民间文学爱好者和专家都参与了这次调查。在完成普查的基础上,大部分县市编辑出版了各个县(市)卷本。
1989年以后,三套集成进入案头工作,编纂出版国卷本。三套集成由民间故事、歌谣和谚语构成。民间故事卷钟敬文先生任主编,刘魁立、许钰、张紫晨任副主编。歌谣卷贾芝先生任主编,张文、陶建基任副主编。谚语卷马学良先生任主编,陶阳、陶立璠、李耀宗任副主编。这一项目从起步到完成,前前后后用了大概25年时间,四分之一世纪。大家都是业余从事编辑工作,靠的是一种奉献精神。比如我们这些人在学校都是从事教学工作的,但为了完成集成工作,随叫随到。在编辑过程中,严格要求,保证学术质量。和民间故事卷、歌谣卷比起来,谚语卷是比较难做的项目。一方面,谚语一句两句就是一条;另外,普查工作也不好进行。即便是这样,我们也千方百计,想尽办法补充材料,三审三校,反复好多次。《中国民间文艺十套集成志书》被称为“文化长城”,三套集成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三套集成,就是一个缺陷了。周巍峙部长更是为十套文艺集成殚精竭虑。没有钱给找钱,没有人找人,最后才圆满完成了这个大工程。
80年代完成的两项工程:《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民间文艺十套集成志书》意义重大。意义在哪里?以三套集成而言,就是为传统文化、特别是为民间文学的保护抢救赢得了非常宝贵的时间,起码争取了20年的宝贵时间。如果今天再次去做普查的话,无论你动员多少人,是不可能收集来那么多珍贵的资料,而且当时都是民间文学专家们参加的。按照民间文学特殊的规律,我们在信息的采集量上是做得比较好的。特别是经过层层筛选把关的国卷本,具有很高的价值。这一工程如果放在别的国家,可能没办法进行,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集中人力办大事的优越性吧。国外的学者也很羡慕这一点。1991年我在日本筑波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筑波大学的副校长小泽俊夫(他是大家熟悉的指挥家小泽征尔的哥哥)约见我,因为他也是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我给他讲了三套集成的普查、编辑工作,他听了非常感动。觉得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对于国外学者来讲,它的影响也很大。前两天我还见到日本奈良大学的真锅昌弘教授,他是研究日本歌谣的。他问我,三套集成是不是出全了?我说,出全了,已经出版了。我还告诉他,我们还建起了民间文学数据库,数据库把县卷本也收进去了。现在他们看到的是国卷本,数据库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应用,那就是下一步的事情了。
1983年8月,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后,开办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讲习班,在中央民族大学举办。当时正值暑假,场地借用学生宿舍和办公楼的地下室。中国民研会杨亮才先生参与了这个培训班筹备,他代表中国民研会,也代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这次讲习班全国来了150多人,分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两个班,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培训。给讲习班讲课的都是我国著名民俗学家、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宗教学家和民间文艺学家,如钟敬文、费孝通、马学良、杨堃、杨成志、容肇祖、常任侠、白寿彝、罗致平、罗永麟、宋兆麟、张紫晨、刘魁立、陶立璠、张振犁、柯杨等。我曾经有一篇文章《难忘一九八三》回忆了讲习班举办的情况。当时特别缺乏民俗学、民间文学人才,办讲习班是最好的应急办法。这种讲习班一共办过两期,一期是在中央民族大学,二期是在门头沟。平常大家戏称“黄埔一期”和“黄埔二期”。讲习班成员结业以后,都成为各地研究的骨干,现在好些人都成了大学或研究机构的教授。
整个80年代是中国民间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虽然这个领域按照钟老和老一辈先生的说法是“惨淡经营”,没有什么经费,但是人们的精神状态都比较好,不计名利,不计报酬。中国民间文学界的专家学者,在中国民研会的协调组织下做了很多工作,召开了很多学术会议,成立了很多学会,像神话学会、歌谣学会等。通过有组织的学术活动,凝聚力量。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很多事情都是白手起家做起来的。比如中国民研会在这一时期,以《民间文学论坛》为阵地,举办了中国民间文学刊授大学。刊授大学设置的课目很多,除民间文学外,还包括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原始艺术等等。当时我们的教学任务很重,记得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撰写《民族学》教材a。在中国民间文学刊授大学教授民族学的时候,我正在中央民族大学讲授民俗学。接到任务后,我阅读了大量的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原始艺术等方面的书籍。因为从事民间文学的人,没有广博的知识是很难进行研究的。中国民研会大概是1985年开始举办中国民间文学刊授大学,培养了不少人才。这个时期,中国民研会做了非常有益的工作,从保护和传承民间文学角度讲,赢得了时间。所以,后来提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大家都觉得保护工作不是现在才有,不是从申遗保护才开始的,我们早就呼吁这个事儿了,是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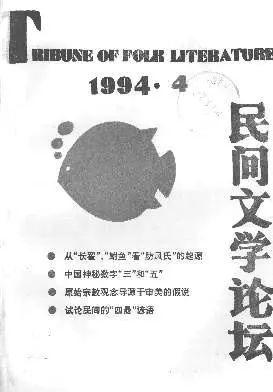
1986年,中国民研会响应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号召,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过一次民间文学保护座谈会,希望通过呼吁,国家以立法的形式来保护传统文化。钟敬文先生作了长篇讲话,还形成一个建议书。可见,我们在80年代,就已经呼吁保护传统文化,而且付诸行动,三套集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为后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当初大批的专家参与了三套集成的普查,了解掌握了中国民间文化的传承和保存状况。后来这些人都参与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工作,大家对什么样的东西应该成为国家项目很熟悉,能做到胸中有数。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民研会在民间文化保护方面还是先知先觉,不但有想法,而且有行动。21世纪初,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也是如此,中国民协表现出强烈的责任和应有的担当。
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民间文艺工作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人才的培养必须从基础理论的学习开始。《民间文学概论》就是告诉大家一种基础的理论方法。现在好多研究深入不下去,就是因为概念不清楚,确定不了研究方向在学科里的定位。我自己是从这几个方面努力的:一是基础理论;二是积累大量的民俗和民间文学资料,就是所谓的“资料学”;三是风俗史和民间文学史的研究。《民间文学概论》《民俗学概论》是我用功最勤的方面。在本科阶段,概论是必修课程。到了研究生阶段,那就是资料学、风俗史和专题研究。在80年代,我就发动学生搜集民俗资料,编印了《少数民族民俗资料》5册,将近300万字。在这个基础上,90年代开始,大概用了10年的时间,编辑出版《中国民俗大系》。《中国民俗大系》分省立卷,31卷,将近1400万字,2004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写过一篇文章《<中国民俗大系>出版5周年祭》,回忆这一工作的艰难曲折。当时没有一分钱的课题经费,还是把这件事情办成了。最近出版了我写的《中国风俗发展简史》,算是我教学经历的一个总结。基础理论、资料学、历史文献的研究,这三个方面合起来才是中国民俗学的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和结构。现在的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最缺整体的布局,只抓一点,不及其余。我们应该从中国民俗和民间文学现状出发,做好研究规划。钟敬文先生提出了建设中国民俗学派的问题。中国民俗学,能不能建立学派?我们应该有这个自信,我是有信心的,可惜年龄大了,力不从心。今天年轻的学者,应该很好地研究钟先生的学术思想。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演时,对年轻的学子们说:“这个任务是你们的,钟先生培养了三十多位博士,你们拿不下来这个课题吗?”就从三个方面出发,有专门研究中国历史文献的,有研究基础理论的,有做专题研究的,建设中国民俗学派,这是可以做到的。
三、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
“集成”概念最初是中国民协提出的。开始叫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后来约定俗成叫“三套集成”。“集成”的意思就是集大成。因为当时中国民研会的工作已步入正轨。经过80年代,实际上不只是80年代,“文革”前中国民协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工作积累,民间文学方面的搜集整理工作一直在进行,无论是少数民族的还是汉族的,积累了不少的资料;到了“文革”以后,搜集整理工作的视野更开阔了。有了前几十年的积累,大家觉得应该做一个比较大的工程,能够把已经收集到的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等,做成集成类的大项目。起初,这个项目的设计上也有它的问题,比如歌谣集成还有很多类型的作品没能收录,如民间叙事长诗、英雄史诗等。中国的民间叙事长诗是很丰富、很发达的。原来以为汉族没有叙事长诗,现在湖北咸宁、神农架地区发现几十部民间叙事长诗。还有英雄史诗《格萨尔》《玛纳斯》《江格尔》等,一提起来都是几十部。像《格萨尔》,原来说是五十多部。前几天我到青海,青海民协主席索南多杰说有一百多部,而且内容都能贯穿起来。《玛纳斯》8部已经搜集完。《江格尔》有二十多部。这样看来,还有好多工作要做。现在启动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正是三套集成的延续、发展。现在国家经济发展了,也重视了,这个工程可以做得更好。中国民协在抓紧数据库的建设,这为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将来数据库建好以后,会给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提供很多方便。但是这个工程要抓紧,一是中国民协要抓紧,一是要配备一定的人力去做好这件事情。

当年编纂谚语集成的时候,编委会成员走南闯北,每到一处,都是先看卡片,上万张卡片,一盒一盒分类编排。看完卡片提意见,修改后形成打印书稿,复审再提出意见,再作修改,最后终审交付出版,非常严格。三套集成从普查到编辑出版,培养了一支优秀的民间文学队伍。比如谚语集成,从概念到分类,遇到许多问题。怎么办?办讲习班,统一认识,明确体例。把三套集成的人员集中到北京,用十多天的时间,讨论体例和分类。如谚语卷编辑,除明确概念界定外,集中讨论编选过程中如何避免重复、去留问题。假谚怎么识别,谚语跟俗语、歇后语的区别。从不同的角度讲解:副主编陶阳讲原则性的东西,即三性问题;本人讲在选编过程中怎么避免谚语条目的重复;李耀宗从语言学角度,讲怎么区别谚语和俗语、歇后语等。三套集成的意义是什么?是带出来了一支队伍。
《中国谚语集成》出了30卷,印象比较深的是首卷《宁夏卷》。宁夏是回族自治区,地方小,收集到的谚语也不多,但是这一卷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明确了最后进入国卷本的谚语应该怎么编,应该有什么样的水准要求,怎么严格地按照编辑体例实施编纂。记得当年编《宁夏卷》的时候,河北省把编的打印稿拿到会议上来,我们翻阅后发现完全不合格。从第一卷我们吸取教训,必须要有严格的编辑体例要求。按照这个标准,后来其他各卷的编辑就比较顺利。
另外,谚语卷编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少数民族谚语。西藏、新疆、内蒙古的谚语,非常有民族特色和地区特色。内蒙古的牧业谚语,是生产经验、生活经验的总结。西藏藏族谚语,新疆维吾尔族谚语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关键是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你不能按照汉族的谚语格式套路翻译。为此中国民研会组织召开过专门的关于翻译问题的会议。新疆、西藏费了很大劲儿完成谚语条目的翻译,但是编辑力量不足,于是编辑部协调力量,帮助西藏、新疆、内蒙古完成了谚语卷的编辑出版任务。
此外,谚语中有些谚语以歌谣的形式表现,特别是少数民族谚语,这种谣谚现象更多。还有一些谚语,早就被爱好者编辑出版,像山西的《马首农谚》,收集作为《山西卷》的附录,以丰富该卷的内容。又如藏族的英雄史诗《格萨尔》,这样大部头的著作,好多谚语在里面,我们也建议摘录,形成《格萨尔谚语》附录在《西藏卷》。
在谚语集成审稿中,我们还注意到歌谣和谣谚的不同。歌谣一般是反映生活、思想、感情的,谣谚则侧重讲道理,带有哲学、道德意味在里面。三套集成有歌谣集成,一般在歌谣卷里收录的,谚语卷就不收。如果歌谣卷认为是谣谚的,转到谚语卷,经认真鉴别、讨论,收入谚语卷。
谚语集成是按照内容分类编排的,具体到每一类,在谚语条目的编排上,在实践中形成一定的编排技巧,如“凤头法”“聚串法”“去重法”等。
三套集成始终是在中国民协的规划、协调和指导下进行的,虽然经历的时日很长,但自始至终,都在保证编纂的质量。实践证明,三套集成是中国民协举全国之力完成的一大文化工程,为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四、中日联合民俗考察
1989年,由日本历史民俗博物馆研究部主任坪井洋文率队的日本民俗学访华团到北京。在北京师范大学访问,与钟老见面时,提出了中日民俗学者联合进行民俗考察的建议,得到钟老的同意。但是不久,坪井洋文去世,这一任务落到福田亚细男教授身上。福田先生向日本文部省申报,得到批准。于是组织中日两国民俗学者联合进行民俗文化考察。这次考察的地域主要是中国的江苏、浙江地区。联合考察团日方8位学者,中方也是8位学者。日方团长福田亚细男,中方团长张紫晨,我任副团长。

福田亚细男
这次考察历时3年,分为3个时段。第一年摸底考察,第二年正式考察,第三年撰写考察报告并做补充调查。我把这个归纳为“一步三回头”。民俗考察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过程,不能像我们国内有些学者的考察,都是“一去不回头”。第一年在江苏苏州白茆乡考察,主要是摸底,看中国民俗文化的现状究竟是什么样的。第二年去了日本的茨城县、千叶县、冲绳县,做日本南方民俗文化考察。第三年到浙江金华、兰溪,最后到丽水。在丽水主要是对畲族村落进行考察。考察结束以后,大家分工合作,有考察村落民俗的,有考察农耕民俗的,有考察卫生医疗的,还有考察信仰习俗的。这次考察所写的论文,收录在福田亚细男编的成果报告书《中国江南的民俗文化》。
1991年完成江南民俗考察之后,紧接着日本筑波大学佐野贤治教授申请到日本文部省的考察经费,进行中日联合的第二次考察。这次考察同样为期三年,主要内容是汉族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主要是纳西族、彝族)。对云南纳西族地区进行了两次考察。第二次考察后期,从纳西族地区转移到四川凉山州美姑县进行考察。第三次又回到云南纳西族地区考察。
后来,中日联合调查继续进行,而且主要由中国民协组织,浙江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王恬自始至终参与了考察活动。从时间上讲,中日联合调查在福田亚细男先生的指导下,先后进行大概20年。20年是一代人的光阴啊。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一代人的光阴》,回忆中日联合考察活动。
中日联合民俗考察的意义在哪儿呢?要知道,当年中国民俗学正在恢复和重建时期,不仅缺乏人才,更缺乏科学的田野作业训练;而日本学者在这方面有着很好的经验可以吸取。当时参与考察的中国学者,大部分都很年轻,白庚胜、巴莫曲布嫫、周星、刘铁梁、何彬、尹成奎那时年龄都算小的,江苏的周正良,浙江的朱秋枫,北京的张紫晨和我算是中年人。浙江民间文艺家协会的王恬,一直是这个项目积极的协调者,她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期都参加了考察。我曾对王恬说,你的贡献太大了。
这次考察,对于怎样进行民俗学田野作业,让中国学者受益匪浅。不间断地用20年的时间,多次进行田野考察,考察又进行得这样顺利,这在中日民俗学合作与交流方面,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作为民俗学者来讲,深入自己的课题,去研究或者教学,是本职。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一批有组织能力的、有活动能力的学者,协调各方,形成凝聚力。这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民俗学实践证明了的。自己做学问是一个方面,也可以做得非常好,但是你要把周围的学者团结带动起来,特别是一些地方的学者,需要去帮助他们、发现他们,给他们提供一些方便的条件。有一些课题是需要地方学者协助的,像我们编纂《中国民俗大系》,尽管没有课题经费,各省的民俗学家还是乐意参与撰写。不计名利,为了把各个省卷编好,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民俗文化的全貌,大家都尽心尽力去做。不管10年也好,8年也好,要把《中国民俗大系》最后完成。遗憾的是这套丛书国内发行的很少。今天这套书即将由学苑出版社再版,书稿都修改好了,但现在出版审查出现新的情况,包括内容的审查等等。我催促出版社能抓紧一些,希望读者能早日见到这套丛书。
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中国民协这些年来做了许多工作,中日联合民俗考察是做得最出色的,坚持了20年。此外中国民协还开展了许多国际的交流、展演活动,取得不小的成绩。希望今后注意资料的积累,进一步加强民间文化理论研究。中国民协有一个很好的理论阵地——《民间文化论坛》,可以刊发更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中国民协这么大一个群众团体,有深厚的民间文化资源,要很好地利用它、研究它。我曾去银川参加《民族艺林》刊物发展座谈会,这个刊物能坚持下来,经历了许多磨难。当刊物遇到困难时,曾采用过招租方式,招租不行,改变方式,编辑出版小人书。目的是为了保留好不容易得到的刊号。现在《民族艺林》办得很有起色。《民间文化论坛》的前身是《民间文学论坛》,初创时期《民间文学论坛》影响很大。80年代我在日本访问时,每到一个图书馆,都能看到书架上有咱们的杂志《民间文学论坛》,感到很亲切。
中日联合考察坚持二十多年,自始至终都是中国民协负责组织协调,到浙江是浙江民协联系,到上海是上海民协联系,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还召开过几次总结会议,在浙江、北京都开过这样的会议。中日联合考察,中国民协起了纽带的作用。而参与者大都是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一些学者,如果在适当的时机,把这些参与者召集在一起,开个座谈会,用口述的形式记录这一段历史,一定有许多逸闻趣事在里面。
拉拉杂杂谈了如上的经历和感受,而且许多是退休以后的学术经历,这要十分感谢中国民协给了我退休后发挥余热的机会。和中国民协同仁相遇、相知,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本文由陶立璠口述,王素珍、周利利整理
文章来源:《民间文化论坛》2020年第3期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