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
吕跃军,山东邹平人,大理大学东喜玛拉雅研究院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肖文,江西南昌人,大理大学东喜玛拉雅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生态学。


【摘要】绕三灵是云南洱海地区沿袭上千年的白族传统民俗,其中有许多关于灾害的民间传说和应对灾害的祭祀仪式。运用灾害民俗学的观点和方法,围绕传说、仪式与灾害的关系,对绕三灵记忆装置中的干旱、洪水、疾病、生育等灾害记忆进行解读,从中发现洱海地区灾害的文化特征及人们应对灾害的文化选择。绕三灵的灾害记忆是通过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两种记忆装置进行传承,这种传承体现了白族人民积极应对灾害,与灾害抗争的意志和智慧,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关键词】民俗学;灾害;白族;绕三灵;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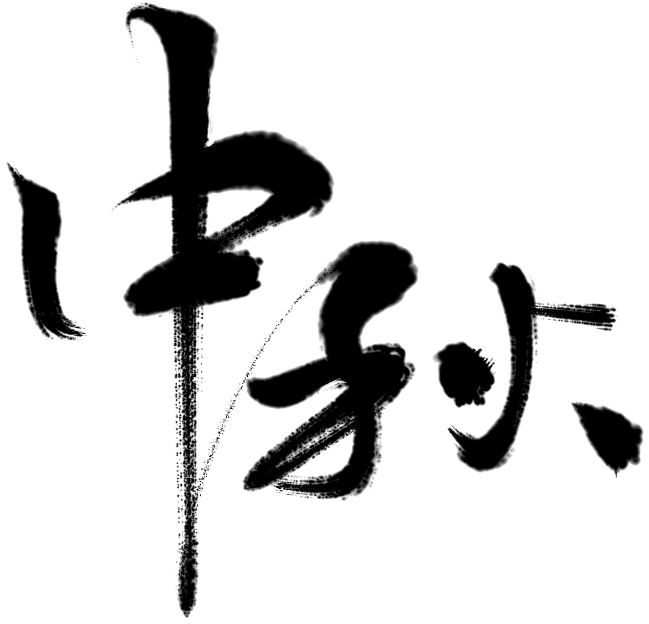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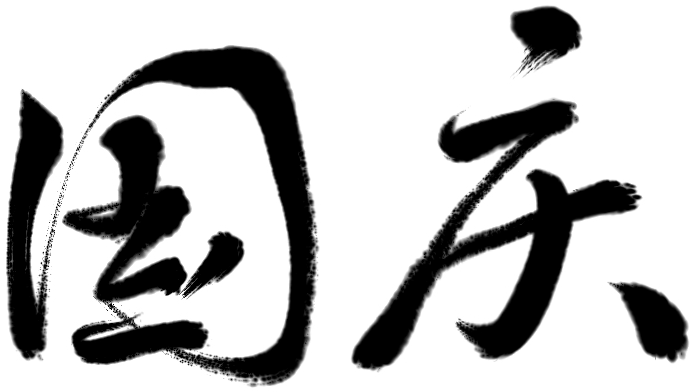
灾害民俗学是灾害学与民俗学交叉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由日本学者樱井龙彦提出。他认为,民俗学也应该像其他学科一样来承担起应有的社会使命,引导人们以民俗学的视点来正确应对灾害,把既是自然现象又是人为现象的灾害放在人、自然和神三者交涉的关系中来考察,并且从记忆装置中来抽取出灾害民俗的知识与智慧。绕三灵是云南洱海地区沿袭上千年的白族传统民俗,其中有许多关于灾害的民间传说和应对灾害的祭祀仪式,保留着明显的灾害记忆,对白族人民灾害意识的养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绕三灵的定义
绕三灵,自语称为“观上览”或“拐上纳”。由于其最初的含义早已流失,因而又有绕山林、绕桑林、绕三年、逛桑林、祈雨会等多种汉语名称。只要是有自语的名称,那就说明这种民俗由来已久。对白族来讲,绕三灵是他们一年中最重要的民俗活动之一。
关于绕三灵的起源,由于缺乏文献史料和考古发现,我们只能从民间传说中作一个大致的推断。相传,在很早以前,大理是一片汪洋大海,白族先民居住在苍山上,从事采集和狩猎,过着极其简单的原始生活。每逢猎获到很多的野兽,他们就会感到无比的兴奋和快乐,以为这是苍山神帮助了自己,于是便欢聚在山林之间,燃起火堆,烧烤野兽,边唱边跳,绕着山林尽情歌舞,以此来祭拜苍山神,祈求今后还能得到苍山神的保佑。这大概就是早期的绕三灵。由此可知,绕三灵应该起源于洱海地区的原始社会,与白族先民的山神崇拜有关。

绕三灵到底指的是什么?据《滇中琐记·绕山林会》载:“(绕山林)会凡四日,甲日在郡城古城陛庙,乙日经三塔寺至圣源寺,丙日河埃城,丁日马久邑。盖南遵苍山麓绕至圣源寺,又北循洱海滨绕至马久邑,故谓之绕山林也。”这是有关绕三灵最早的文献记载。从狭义来讲,绕三灵就是“绕”三个地方。所谓三灵,是指洱海地区三个神灵象征,它们是白族宗教信仰中的几个重要神祗,供奉它们的庙宇分别称为佛都、神都和仙都。佛都,最初指圣源寺,位于苍山五台峰下的庆洞村,始建于唐代,后经多次修复、重建。如今,崇圣寺被称为佛都,经调查,绕三灵的祭祀活动并不包括崇圣寺。神都,指庆洞村本主庙,与圣源寺相邻,为清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重建。庙里供奉的是中央本主段宗榜,被称为五百神王,统帅洱海地区71个村的本主。仙都,指洱河祠,位于洱海西岸的河矣城村。祠里供奉的是斩蟒英雄段赤诚,被称为洱河灵帝,是洱海的保护神。实际上,绕三灵不仅仅“绕”这三个庙宇,还包括大理古城南门外的城陛庙,以及位于大理古城东北马久邑村的护国祠。
白族民间还流传着接金姑、送驸马的习俗。笔者认为,接金姑、送驸马应该是绕三灵民俗活动的组成部分,广义的绕三灵,应当包括接金姑和送驸马。
传说,三公主金姑是自子国王张乐进求的小女儿,性格倔强,因被父亲呵斥,负气离家出走,私自嫁给了蒙舍川(今巍山县)主细奴逻。张乐进求很生气,却又无可奈何。由于思恋女儿心切,便答应了这门亲事,叫人去接金姑回门。得知这个喜讯,人们纷纷穿上节日盛装,于二月初八,吹吹打打,到蒙舍川去接金姑。金姑见到故乡亲人高兴得热泪盈眶,细奴逻也组织了送亲队伍,一起送三公主回乡省亲。他们来到苍山莲花峰下的保和寺后,细奴逻自知长得又黑又丑,怕父王见了不高兴,便让三公主独自回家多玩几天,自己在保和寺等她。转眼到了三月初三,细奴逻感到幽困难当,遂想提前回蒙舍川。于是,男女老少纷纷来到保和寺,唱歌跳舞,欢送驸马回家。这就形成了接金姑、送驸马的习俗。
绕三灵的会期是每年农历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人们穿红着绿,吹吹打打,边唱边跳,沿苍山脚、洱海边,欢送三公主回巍山。四月二十二日,绕三灵的队伍来到城陛庙祭拜。四月二十三日,到达圣源寺和神都祭拜,当天晚上就在庆洞村举行歌舞狂欢活动。四月二十四日,到达洱河祠祭拜。四月二十五日,到达护国祠祭拜,人们依依不舍,将金姑送上回家的路。至此,通过接金姑、送驸马、绕三灵等三个仪式,一年一度的绕三灵民俗活动才得到圆满结束。
接金姑、送驸马和绕三灵的民俗活动,都是围绕着三公主金姑和驸马细奴逻来展开的。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苍山与洱海之间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环境中,形成了一个别具一格的文化空间。

二|干旱:神灵、祈雨与崇龙思想
南诏应该是绕三灵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洱海地区已是一个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业社会。白族先民对农田的管理已达到精耕细作的水平,与汉人社会相差无几。《南诏德化碑》载:“厄塞流潦,高原为稻黍之田。疏决阪池,下隰树园林之业。”《蛮书》(卷七)载:“蛮治山田,殊为精好。”因此,南诏有关绕三灵的传说突出了农耕的主题,并带有佛教的色彩。传说观音下凡,制服海中恶魔罗刹,海水向东退去,苍山脚下现出一片平地。从此,白族人民就从苍山上搬到坝子里居住。观音归天时,把辅助她制服罗刹的西天护法神——五百神王留下,封他为建国皇帝。建国皇帝教村民植树造林,盘田织布,生活逐渐好起来。他就住在庆洞庄,和村民一起种了很多桑树、柳树。每逢农历四月间采摘桑叶的时候,人们便和建国皇帝一起欢聚在庆洞庄,一面采摘桑叶,一面唱歌跳舞。唱累了,跳乏了,大家就把柳树一枝折来顶在头上遮阳。此后,就形成了一年一度的盛会,人们称之为绕桑林。这里的“盘田织布”是洱海地区农业生产的写照,人们通过娱神的方式来庆祝农业生产的丰收;“绕桑林”的欢聚活动为每年农历四月,正值大理坝子水稻播种、栽秧的时节;“庆洞庄”即今庆洞村,是绕三灵最重要的活动场所。这一传说反映了绕三灵农耕文化的特征。
作为以农业为主要生计模式的白族,对于气象的认知,在白族的传统知识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秦汉以来,洱海流域的气候演变呈现出暖干、冷湿交替的组合特点,与不同时期人类活动的强弱变化具有较好的一致性。洱海地区历来是云南省人口较为集中的区域之一。由于人口持续增长,人类活动加强,植被遭到破坏,导致气候向偏暖干燥发展。距今130年以来的气象观测表明,19世纪80年代,20世纪30至5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气候明显偏旱。
早期的绕三灵与祈雨并无关联。随着生计方式由采集狩猎向农业耕种转变,降雨对洱海地区的人们来讲就显得至关重要。因此,在绕三灵的变迁过程中,加入了祈雨的内容,是白族人民适应气候演变和生计改变的文化选择。
白族先民对灾害的认识,是把自然灾害作为社会或文化现象来思考,主要从人为的因素去找原因。他们认为,干旱发生的原因是神灵对人们的一种惩罚。从有关传说可以看出这一点。相传,有一年快到五月五端午节了,天上没下一滴雨,连洱海也快要干洞了。眼看庄稼种不下去,人们不知怎么办好。一个年寿顶高的老人说,可能是许多年没有朝拜山林之神,神灵发怒了。于是,大家唱的唱,跳的跳,一直闹了三天。第四天果真乌百盖顶,下起了大雨。从此,人们就把朝拜山林之神的这三天(农历四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定为绕山林节日。凡事必有因果,只要是人为的因素,灾害的发生就一定是可以解释的。在白族先民那里,灾害被解释为神灵的警告。
绕三灵的另一个传说,可以说明白族先民以怎样的方式来达到预防干旱的目的。传说,有一年,天旱无雨,眼看庄稼快要种不下去了,村民们焦急不安。到绕三灵时,人们来朝拜建国皇帝,祈求早降大雨。晚上,建国皇帝显灵,赐给他们一个宝葫芦。人们拿着宝葫芦找到了段赤城,段赤城在宝葫芦中装满洱海水,叫他们带回去。到了栽秧时节,果然天降大雨,各村各寨的秧苗都栽下去了,这一年获得了大丰收。后来,人们便把绕三灵称为祈雨会。由此可知,在遇到干旱时,基于对龙的信仰,白族先民以祭祀祈雨的方式,来达到预防干旱的目的。白族的龙文化源远流长,早在远古时期,白族村民已有崇龙习俗。白族村民通过祭拜建国皇帝,从而得到斩莽英雄段赤城的帮助,最终达到预防干旱的目的,反映了白族“人龙为友”的崇龙思想。
与干旱之年临时性的求雨活动不同,白族人民将祈雨嵌入绕三灵的民俗活动之中,使之成为固定的祭祀仪式。这是白族人民对气候变化规律深刻认识的结果。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人们认识到农业生产与气候变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尤其是水稻种植更依赖于充足的降雨。绕三灵的活动时间为每年初夏,正值大理坝子“两季同期”时节,即小麦、蚕豆即将收割,紧接着便是水稻插秧。根据气象统计,每年六月是洱海地区降水最多的月份之一,正好适合水稻栽插及农田灌溉。事关农时,绕三灵选择这样一个生产节令的前夕,来开展大规模的祈雨祭祀活动,正是适应了洱海流域气候的变化规律,表达了洱海周边村民们的共同期盼。

三|洪水:恶魔、水神与抗争智慧
历史上,洱海地区为洪水多发地带,这与洱海地区的自然环境有密切关系。不同的时代对洱海的称呼亦有不同,汉代称叶榆泽、昆明池,魏晋称叶榆河,隋代称西二河,唐宋称西洱河,元代以后称洱海。苍山洱海,山水相依。洱海北有弥直河注入,东南收波罗江水,西纳苍山十八溪水。研究发现,在近万余年中,洱海的水位有过大幅度的上升和下降,与洱海的出水口有密切的关系。
洱海最初为内陆湖。新第三纪,洱海断裂以东的山体上升,河流溯源侵蚀强烈,致使位于洱海东北的落漏河,经大王庙袭夺洱海水,向东流人金沙江,使洱海成为外流湖。《水经注》(卷三十七)载:“叶榆河,出其县北界,屈从县东北流”“与淹水合”。这里“叶榆河”即洱海。“其县”即叶榆县,治所在今喜洲。“淹水”即金沙江。新第三纪以后,洱海断裂东侧山体上升缓慢,河流溯源侵蚀停止,大王庙袭夺地段淤塞,洱海又恢复为内陆湖。进人全新世,由于苍山断块上升迅速,在洱海西南和东南分别形成了两个出水口,洱海再次成为外流湖。在洱海西南,西洱河溯源侵蚀强烈,经天生桥袭夺洱海水,向西流入澜沧江。在洱海东南,洱海水沿断裂带裂隙南流,经弥渡盆地流入礼社江,成为红河水系的一部分。《水经注》(卷三十七)又载:叶榆水,“东南出益州界”“入牂牁郡西随县北”“而东南注于交趾”“东入海”。这里“益州”即益州郡,郡治在今昆明市晋宁区。“牂牁郡”治在今贵州省贵阳市一带。“西随县”即今云南省金平县。“交趾”即交趾郡,位于今越南北部。公元1111年至今,洱海东南水道完全阻塞,西洱河成为洱海的唯一出水口。
白族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洪水的灾害记忆。徐家瑞记录了一个有关大理的洪水传说:龙母是一个贫穷的女子,她住在绿桃村。在古代的某一天,龙母去山中砍柴,看见一颗绿桃,就摘了下来吞下喉去,后来就有孕了,生下一个男孩。孩子长大后,常随母亲到山中砍柴,渴了就去龙潭喝水。他发现龙王有病,就用山中的一株草药治好了龙王的病。龙王送他许多珠宝,他都不要,他愿在龙宫多住几天。某一天,他偷偷地把一件黄龙袍穿在身上,忽然大雷震电,他已经变成一条龙了,龙王见了大怒。这时腾越坎死凹黑龙盘踞下关,大理洪水为患,龙王命他去驱逐黑龙,立功赎罪。他和黑龙在江峰寺大战,黑龙被打断一只角,伤了一只眼,向天生桥冲开一个洞穴,逃回腾越的坎死凹去了。大理的洪水从此平了,他变成一条小蛇,回到临水亭,即是现在的洱海神祠。他永住在这里,他的母亲就成了龙母。
对于灾害的救助,白族先民多决定于宗教、巫术和咒物。斩莽英雄段赤城的传说反映了白族先民与洪水进行斗争的智慧。南诏时,洱海里出现一条巨蟒,侵扰村民,吞食人畜,兴风作浪,淹没庄稼,百姓深受其苦,哀声遍野。白族青年段赤城,身披铠甲,手持利剑,与巨蟒搏斗,被巨蟒吞入腹中。他在巨蟒腹中奋力翻滚,将利剑刺穿巨蟒腹腔,最终与巨蟒同归于尽,从此除去水患大害。罗振常藏本《南诏野史》(上卷)载:“唐时洱河有妖蛇,名薄劫,兴大水,淹城。蒙国王出示,有能灭之者,赏半官库,子孙世免差摇。部民有段赤城者,愿灭蛇,缚刀人水,蛇吞之,人与蛇皆死。水患息,王令人剖蛇腹,取赤城骨葬之,建塔其上,假蛇骨灰塔,名曰灵塔。”塔在今苍山马耳峰下羊皮村,名蛇骨塔。斩蟒英雄段赤诚,被洱海地区的白族居民奉为洱河灵帝,供奉于洱河祠,成为绕三灵祭祀活动的重要内容。
以科学的视角来看,白族民间也有关于洪水治理的传说。相传,点苍之巅有高河,亦名冯河。蒙劝利晨王,一日巡点苍,遇一叟牧二马。劝利与叟言谈。叟精水利,曰:点苍本天河青苍龙君所化。混沌之初,元始治世,苍龙行雨有误,洪泽漫漫,而贬苍龙于世,衍化点苍以赎过。苍峰十九皆龙脊骨所化,溪流十八皆龙之肋骨间隙。高河本苍龙之脊心凹槽,积冰渍雪水而成。若开引,水可利良田千顷,足千家之食。劝利王知天人点化,洗马于高河泽。后派军将董晨君,带将士5000人修高河。半年成,建水神祠,内供一牧马叟,为点苍水神。二马为冯,劝利王命高河为冯河。段氏得大理,每年治理冯河,并于茫涌溪旁建水神祠,封董晨君为治水龙君,每年四月祀以三牲。“点苍”,即今苍山。

四|疫病:巫术、宗教与神药两解
绕三灵还有另外一个来源,即禳疾病。以巫术治病为世界各民族在文化低级时代的普遍现象。受楚文化影响,白族先民崇拜天鬼。他们认为,鬼神作祟是疾病的原因,有痘鬼、咳嗽鬼、痔病鬼、产房鬼等20余种之多。大理地区的巫师是世代相传的。男的叫神汉或叫巫公,女的叫巫婆或叫女巫。巫师的家里都有香堂或叫家堂。香堂设有神案,案前摆放一个香盆,每天都在香盆里焚烧纸钱和甲马。有香堂的巫师,地位比较高一些,称为香堂主。据说香堂主都有一对专门供他驱使的阴司童子,每天所烧的纸钱和甲马都是供这对童子使用的。甲马亦称纸马或脚力,为白族巫术仪式中的神圣法宝,是巫师借以交通鬼神的媒介。
白族民间巫术仪式大体上分为四种:一是阴间寻找亲人魂。自语称为问细木,意为问祖先的魂。这是巫教后期仪式的生动场面。二是酬神谢神神满堂。白族民间认为,人生病是因为冒犯了鬼神而引起的。冒犯了哪里的神灵,就要到哪里去请神。三是迎神庙会舞翩趾。这是白族巫师最主要的风俗节日活动。迎送本主、绕三灵、放生会等,都离不开巫师的参与,巫师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四是降魔驱鬼上刀梯。这是白族巫教最高的巫术仪式。一般要在瘟疫流行,或遭受重大灾害,或家里屡遭大故,或对本主有特大祈求的情况下举行。
由于生活贫困和缺医少药,至今,巫术治病在白族民间特别是贫困山区依然存在。笔者曾对云龙县诺邓镇五宝山云峰寺白族“朵兮薄”祭祀活动进行过调查,其实即是巫术治病的一种仪式。“朵兮薄”是云龙白族对巫师的称谓,被视为人与神的交通者。“朵”是伟大的意思,“兮”为神秘之意,“薄”即对长者的尊称。实际上,巫师为了得到人们的信任,也学到一些草药秘方,也懂得一些医学知识。在祭祀仪式上,借神灵之口说出一些秘方,给病人几付草药,叫病人煎汤服用。在白族民间看来,这叫做神药两解。
《滇中琐记·绕山林会》说:“(绕山林会)每岁季春下洗,男妇堂集殆千万人,十百各为群,群各有巫觋领之。男子则头簪纸花,足著芒鞋,纨其袴,绸其褕,袒褐其衣襟,高低其裤缘。其为老妇则颈挂牟尼珠,背负香积囊,垂带而蹇裳,戴笠而持杖,装饰与男子异,而独红纸花则皆插之。男者犹执巾秉扇,足踏口歌或拍霸王鞭。”据费茨杰拉德考察,绕三灵的舞蹈表演与“舍之”的“跳鬼”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舍之”是仙人的意思,即巫师。“跳鬼”意思是将鬼跳出去,即把恶魔从病人身体里驱逐出去,是“舍之”做的法事。“舍之”平时过着与其邻居一样的农民生活,他们有土地,耕田种地,只在特殊的场合被请去做法事。当生病时,如果病人认为有鬼魂或者病魔缠身的,就把巫师请来驱鬼。“舍之”行动诡秘,被一层神秘的面纱笼罩着。绕三灵的跳舞者是否就是“舍之”,已无法得到证实,而“跳鬼”的法事与绕三灵的舞蹈却极为相似。

大黑天神为佛教密宗的护法神,是专治疾病的医神,在白族民间受到广泛崇拜。大黑天神一般为三头八臂或三头六臂或三头四臂,三眼,骑白牛或黑牛,以骸骸为璎珞,手脚毒蛇缠绕,有的头戴牛头冠,全身青黑色,形象十分狰狞可畏。传说大黑天神原是玉皇大帝身边的侍者。三月初三玉帝临朝时,好几位大仙不来上朝,原来都已私逃人间。玉帝坐在龙椅上,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心想今天我倒要看看,人间有何美景和乐趣。于是来到南天门外观看人间。玉帝看见人间一幅生气勃勃的春景,胜过天宫,心生忌妒,派侍者把瘟药撒到人间,让人间人亡畜死,树枯水干。侍者不仅长得俊秀,而且心地善良,看到人间男耕女织,勤劳淳朴,不忍心把这么美好的人间给毁了,于是决心牺牲自己,拯救下方生灵,便把瘟药全部喝下。人间免除了一场大难,可是侍者面目发黑,浑身发肿,从天上掉到了地下。白族人民十分感激侍者舍身相救,为其建盖本主庙,根据其相貌尊称为大黑天神,作为白族本主世代供奉。三月初三是送驸马的日子,大黑天神的传说可能与绕三灵有关。
在古代洱海地区,神祗和灵魂均被认为是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瘟疫,或是能够帮助消除瘟疫病魔。因此,人们为了应付瘟疫所采取的措施目的主要有三个:一是恳求某些神祗的饶恕或帮助,这些神祗可能降瘟疫以惩罚有罪的人,或具有驱逐瘟疫的力量;二是给那些被确认为带来瘟疫的神祗巨大的压力;三是安抚与超度亡灵。这类宗教仪式与科学方法往往交织在一起。在祭祀的同时,或在房屋门前悬挂艾叶,或在垃圾堆上放一些艾叶、麦秆及松树枝一起焚烧,其实是杀菌、驱蚊和去病的有效措施。

五|生育:桑树、求子与生殖崇拜
人口问题是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将给人类带来灾难。绕三灵起源于原始社会,与白族先民的生殖崇拜有密切的关系。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口死亡率高,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大量地繁殖人口,因而产生了生殖崇拜的观念。位于剑川县城西南的石宝山石窟,有一罕见石刻,自语称为“阿姎白”,在主龛中部须弥座上雕刻着一具女性生殖器。据费孝通考证,“阿姎白”雕刻可能是早期白族居民生殖器崇拜的遗物,说明白族先民曾有过一个早期文化,与人石崇拜有关。李东红认为,这里的女根造像,实际上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即送子观音,当地民众来此祈子的风俗,与佛教信仰有关。
菡芳1964年记录了一个喜洲老人讲述的传说:很早以前,我们这里发大水,是一片汪洋大海,只剩下两兄妹没有被淹死,他俩抱住一棵撑出水面的桑树活了下来。大水退了,孤苦伶仃的兄妹俩结成夫妻,一代又一代地繁殖成了如今这千千万万的人类。人们为了报答桑树的搭救之恩,就拜它为神树。所以,在洱海地区,人们是从来不兴砍桑树当柴烧的。这个传说与白族的生殖崇拜有很大的关系。桑树在古代男女性爱中扮演了特殊角色,桑林往往是男女恋爱乃至交媾的场合。《特经·鄘风·桑中》这样写道:“爱采唐矣?沫之乡矣。百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这里的“桑中”即桑林之中。古代女子多务蚕桑,诗中女子可能借采桑之机,在桑林深处幽会情人。
很明显,绕三灵充满了生育的内容。参与祭拜的或者是新婚的妇女,或者是她的婆婆,而后者居多,莲池会更是扮演主角。绕三灵的歌舞普遍使用一棵柳树,柳枝上悬挂葫芦、红布等饰物,其队伍前行均以柳树为先导。徐嘉瑞引缪鸾和调查报告说:“榆有胜会,日绕三灵。阖郡士民,相率赴喜洲小朝(即神都),进香众可数万。循苍山之麓而进,遵洱海之滨而归,历时三四日,载歌载舞,兢艳斗奇,极一时之甚。凡七十一村,村各奉其本主,各为一队,自成行列。领队为二男子,共扶杨柳一大枝,高可六七尺,婆娑前进,载舞载歌,一人主唱,一人打诨,自有曲本,如十二属叹五更等。及至小朝,将树一枝供于神前。”最初,绕三灵的队伍前引路的是桑树,后因桑树难找,而改为柳树,为白族先民生殖崇拜的一个例证。

早在20世纪40年代,许烺光就已经注意到绕三灵与求子之间的关系。许烺光写道:“阴历二月十七,在喜洲镇西南方九十多英里的蒙化(今巍山县),人们在巍宝山寺举行一个盛大的庙会。到那时,许多喜洲镇人都要去那里拜佛求子。……三月三,在离喜洲镇七英里的湾桥,人们为纪念太子在宝(保)和寺举行一年一度的庙会。所谓太子,是一个很小的木头像。来赶庙会的男男女女都要朝太子像扔钱币。据说用钱币击中像的人,神将赐其得子。……在喜洲镇西面约一英里半的地方,有一个圣源寺。寺内有一座两英尺高的小脚老妇人泥像,人们叫她阿太。虔诚的妇女带着一双双新鞋来敬拜阿太。求子心切的女人大多前来寺内朝拜。她们从阿太脚上拿去一只鞋,带回家中,将鞋带燃成灰烬,吞人腹中。而后,她们必须再做一只新鞋还给阿太。”巍宝山、保和寺、圣源寺、神都等都与绕三灵的祭祀活动有关。根据笔者调查,“阿太”供在隔壁的神都,并不在圣源寺。如今,有的求子仪式已不复存在,但求子本身仍然是人们参与绕三灵祭拜的重要目的之一。
有人认为绕三灵有不检点及放纵的行为,事实上这并不那么明显。民国时期,绕三灵曾因此遭到政府的禁止,而当地人却充耳不闻。《[民国]大理县志稿》(卷六)载:“(四月)二十三四五等日为绕三灵会,在喜洲圣元寺,居乡人多迷信之,今禁废,神像毁。”1949年以后,绕三灵受到了更多的限制,“文化大革命”时曾一度中断。其中原因仍是绕三灵“有伤风化”。据张锡禄调查,绕三灵确有风流事。年轻人会趁“唱调子”的时候结成“架尼”,即情人的意思。“架尼”只在绕三灵相会,不会破坏彼此的正常生活。如果女子不孕,可以在绕三灵期间“借种”,人们说这是神赐,自王保佑,要在名字中间加一个“爱”字,代表爱民皇帝。绕三灵中可能存在的“风流”,应该是白族先民生殖崇拜的孑遗。

六|结语
种种迹象表明,未来的灾害将越来越多,造成的经济损失将越来越大,影响的范围和领域也将越来越复杂,灾害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因此,灾害研究必将受到更多的关注。虽然民俗学对灾害的研究起步较晚,但当世界面临危机的时候,民俗学可以将自己积蓄的知识应用到灾害的研究中,发挥民俗学的独特作用。灾害民俗学不同于直接以防灾减灾为目标的灾害学,它研究的对象不是灾害本身,而是灾害的文化特征以及人类应对灾害的文化选择。人类学对灾难的关注,为灾区和灾民增加了一份社会与人文关怀。灾难人类学对社会、文化和族群的“生死考问”,使人类学处于人文探索的前沿。民俗学可以借鉴灾害人类学的方法,通过民俗志研究,挖掘人类灾害的共同记忆。
民俗在灾害的起因、预防以及救助等方面都有表现。民俗观念认为,灾害源于天神的警告或旨意,人们借助怪异现象的认识,可以预防灾害,运用咒语、咒术和祭祀、礼仪可以避免灾害,宗教信仰以及纪念物等有助于在精神上将人们从灾难中解救出来。在现代社会的灾害研究中,民俗学可以从经验世界找出心理救助模式,从而发挥民俗学的独特作用。民俗是长期积累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民俗信仰在民众的精神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民俗在民众应对灾害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动员作用。
从灾害民俗学的视角看,绕三灵关于灾害的民间传说、应对灾害的祭祀仪式以及歌舞表演,记录了白族人民共同的灾害记忆,包含着白族先民传达给后人的灾害经验。作为超自然的民间传说是不可能被证实的,但作为从经验世界发现的心理救助模式,它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祭祀仪式、歌舞表演等民俗活动,在灾害救助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绕三灵经过历代的文化积累,形成了有关灾害的知识系统,这个知识系统与白族人民的生产生活相结合,已经成为白族民间应对灾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灾害记忆的传承,也是民间传承的重要内容。记忆的传承,有以可视的物质的形式传承的情况,也有以潜在的非物质的形式传承的情况。灾害记忆也是通过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两种形式来传承的。绕三灵所形成的文化空间,包括庙宇、神像、器物、传说、歌舞、祭祀、仪式等记忆装置。其中庙宇、神像、器物等是物质的记忆装置,而传说、歌舞、祭祀、仪式等是非物质的记忆装置。绕三灵的灾害记忆,正是通过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两种记忆装置进行传承的。绕三灵对灾害记忆的传承,体现了白族人民积极应对灾害,与灾害抗争的意志和智慧,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图片来源于网络
原文刊载于《贵州民族研究》2020年第8期。
文章转载:微公号“民族学与人类学Anthropology”2020-09-25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