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面对非遗运动的巨大声浪,岩本通弥教授的《东亚民俗学的再立论》从欧亚比较的角度,将各自有着演进历程的中日韩三国的民俗学视为一个整体,明确提出东亚民俗学再出发的基点是在继承历史的基础之上回到日常。有鉴于此,进一步审视其提出的“Folklore-民俗(学)”中英互译这一学科发端的根本问题,就有了必要。与此同时,也需要注意到在现代中国民俗学的演进中,除了Folklore一脉的影响之外,中国民俗学还有受到美国民俗学家、社会学家孙末楠Folkways影响而在燕大社会学系进一步发展出的“社会学的民俗学”,也即社会科学化的民俗学的这一支脉,因为采用局内观察法,在社区-功能论引导下的民俗学研究,本身就是直面当下,面向日常的。
关键词:民俗学;folklore;folkways;民俗;风俗;燕京学派;社会学
作者简介:岳永逸,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民俗学、民间文艺学。

面对东亚政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亲睐的强劲与持久,迎来重大机遇的民俗学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此语境下,“日常”再次成为一个严肃的理论话题。截至2019年,岩本通弥教授主持,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参与的《日常与文化》(日常と文化/Everyday life and Culture)已经出版了七期。作为领军人物的岩本通弥教授在2019年发表了新作《东亚民俗学的再立论——向“作为日常学的民俗学”进发》,这是一篇在忧思中力图为民俗学建立学科的当代合法性、自信心,从而使之能安身立命的力作。对中日韩三国民俗学历史演进的勾勒、点染只是策略,其目的是在对东亚民俗学历史演进的回顾中,回答当下民俗学何以可能与寻求可能朝什么方向发展的问题,即民俗学向“作为日常学的民俗学”转型的必然与应然。此前,对民俗学,岩本通弥教授有“以‘民俗’为对象即为民俗学吗”这样的诘问,也有记忆是民俗(学)“最本质性的存在”这样的断语。这些都对中国同仁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基于东亚立场和欧亚比较的此文,应该同样会激起不小的波澜。
本文对岩本通弥教授《东亚民俗学的再立论》一文的回应,将不会涉及其文中对德国和东亚对非遗公约理解差异和申报策略、理念之异的精微辨析。因为,他关注当下而开篇入题的这一细致探讨,还是意在理解东亚民俗学可能有的不足和应该有的再出发的再生点,即指向的还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民俗学,在当代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而且,本文仅就与现代中国民俗学历史相关的两点问题进行粗浅的回应:其一,洋务运动以来,作为学术用语的“民俗(学)”一词在汉语圈的演进;其二,中国民俗学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社会科学化,也即中国民俗学在Folklore这一主流之外演进的另一条路径,抑或说支流。简言之,前者主要指向英国学者汤姆斯(W.J.Thoms,1803-1885)创建的Folklore,后者则指向美国学者孙末楠(W.G.Sumner,1840-1910)创设的Folkways。
一、谁将Folklore译为“民俗(学)”
1928年出版了《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的江绍原(1898-1983),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一位重要的民俗学家。在其编译的《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中,江绍原写过这样一段话:“又此学普通称‘民俗学’,从日本译名也。然日本人所谓‘民俗’,虽有时是民间——俗间的意思,移植到中国来,却颇有被误解为民间风俗之危险”。在引用了这段话之后,岩本通弥教授谨慎地提出了其疑虑:“虽然以江绍原为代表的很多学者认为“民俗学”是源自日语的译语,但笔者不得不说,还有一种很大的可能性,便是这个词一开始便源自于中国。有关英华词典方面的检证,如果已经有先行研究,还请多多赐教,如果还没有,研究生们可以就此话题进行一番探讨。”
显然,这个看似细枝末节的小问题,实则是刘禾、陈力卫等不同学科学者都在关注、诠释的“跨语际交流”和概念史的大问题,而且牵涉到中英日多方。因为翻译——文化译写——“不只是言语形式间的相互转换或曰符号转换,而是理解,是一种阐释;尤其是文化、社会、政治概念之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思想之传导”。
其实,关于源自Folklore的现代学科意义上“民俗(学)”一词是否一定就来自日本,当年的江绍原本就有着今天岩本通弥教授的疑虑。在《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中,江绍原还写过这句话:“‘folklore’通译‘民俗’(袭日本译名?)”括号中,“袭日本译名”之后的“?”,就表明了中西皆通的江绍原,对这一语词来源的不确定性。
1846年,汤姆斯创立的Folk-lore一词成为世界民俗学史上划时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后,该词逐渐盛行开来,并日渐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认可。在日本从兰学向英学转向的过程中,1866-1869年间由罗存德(W.Lobscheid,1822-1893)编纂的《英华字典》扮演了重要角色,是“近代新词源源流入日本的一个重要通道”。1872年吉田贤辅的《英和字典》和1873年柴田昌吉、子安峻的《附音插图英和字汇》等都深受罗存德《英华字典》的影响。然而,在罗存德《英华字典》中,尚未收入英语世界的“新词”Folklore。
就目前笔者检索到的材料而言,作为一个学术用语,Folk-lore在中国正式登台亮相可能是1872年。是年在香港,戴尼斯(N.B.Dennys,1840-1900)在其主编的《中国评论》第一卷第二期,刊发了征集“Chinese Folk-lore”的启事,且强调征集的是来自“事实”(facts)而非出版物中的Folk-lore。其希望征集到的具体内容包括日月年、幸运数字、符咒(charms)、巫术、新年、鬼之类的俗信(superstitions)和童话(fairy tales)等。遗憾的是,或者主要面对的是在中国,尤其是在通商口岸生活的外国人,这则英文启事没有同步翻译为中文。此后,泰勒(G.Taylor)、高延(J.J.M.de Groot)和白挨底(G.M.H.Playfair)等,尤其是戴尼斯本人在《中国评论》上发表了相当数量的关于中国民俗的文章。四年后,戴尼斯出版了他关于中国民俗及与雅利安、闪米特比较的专著。
此后,虽然同样无法断定是否有Folk-lore的影响,但少量汉语书面文献中的“民俗”一词的语义,与汉语中原本有的常和“淳朴”“彪悍”或“刁顽”连用的“民俗”之习惯性旧义相比较,则有了细微的变化。
1876年,《寰宇琐记》第九期刊载有《瓯宾辩论八则》。其中,一则是“论泰西民俗有稍胜中国者”,以两个分别代表中、西的子莘子和瓯宾对谈的方式,辩中西之优劣。基于十室之邑,且有忠信的共性,瓯宾认为万里之地、列国数十的泰西,必有“流风善政”胜于中国者。对此,子莘子并不否定,并细数了西之优:“中国之民智,其弊也狡;泰西之民愚,其美也直。中国文章浮华无用,泰西机器精巧是使。中国谈天多支离附会,泰西算学实信而有征。此则有似稍胜。”然而,子莘子讥讽道:这些“稍胜”者,“皆事之小者”,实乃不足道的奇技淫巧。这一基本认知与洋务派的“夷技”这一总体定位是一样的。
然而,无论基于哪种立场,随附《申报》发行的《寰宇琐记》的作者们,显然有着世界与比较的眼光。1876年2月到1877年1月,《寰宇琐记》发行的这一年,正是洋务运动势头正旺的时期。有意思的是,瓯宾的“流风善政”、子莘子的民智愚、文章、机器、谈天、算学都统合在了“民俗”这一语词之下。或者,可以将这里的民俗,对等为广义的文化(culture)或者文明(civilization),以及文化生态或文明形态。这在汉语写作中应该是前所未有的。
1881年,大名鼎鼎的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主编的《格致汇编》第四卷第十期刊载了《西班牙国民俗略谈》一文,并配图两幅。作者开篇写道:“昨晤回华之友,言在西班牙国驻搭数年,观其风土人情,有甚可奇者。”在简要介绍斗牛、鬼脸(化妆)舞之后,详细介绍了西班牙加拉拿大省穆斯林的一些风俗。如:这里的人们喜净水,味觉尤其灵敏,并能辨别水的肥、瘦、浓、稀,迁居亦有“换水”的别称;古城陀里宝的壮美;当地人锻刀淬火工艺的精湛,等等。这里,标题中的“民俗”对应的是正文的“风土人情”。然而问题是:如果正文中的风土人情对应的就是汉语中古已有之的“风俗”,为何标题不直接用“风俗”?换言之,对作为“中国通”的主编傅兰雅而言,这里的“民俗”并非中国古语之“风俗”,也非“民俗淳朴/刁顽”之“民俗”,应该同样有着微妙的新意。
1886年,以大不列颠民俗学会(Folk-Lore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在香港的负责人(Local Secretary)身份,骆任廷(J.H.S.Lockhart,1858-1937)在《中国评论》第十四卷第六期和第十五卷第一期上连续两次刊发了他在同年6月7日撰写的征集中国民俗的启示。有意味的是,在第二次刊载时,附加了简要的中文,而要征集的民俗事象则全都翻译成中文,还举例说明。同样,这一次的中英文互译还是没有出现“Folklore”和“民俗”之间的对译。中文译文中反而出现了“民风学”一词。正如后文将要提及的那样,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少中国学者选择了“民风”来对译“Folkways”。骆任廷所列的四类征集事象,第一类是包括歌谣、故事等在内的“世故”(Traditional Narrative);第四类是包括成语、古语、谜语、混名和童谣等在内的“俗语”(Folk Sayings);第二类“Traditional Customs”对译为了“风俗”,包括“各方风俗”(Local Customs)、“岁时纪”(Festival Customs)、“礼仪”(Ceremonial Customs)和“戏术”(Games);第三类“Superstitions,Beliefs and Practices”对译为了“习俗”,包括“鬼祟”(Goblindom)、“巫觋”(Witchcraft)、“星占”(Astrology)和“笃信吉凶”(Superstitions connected with MaterialThings)。
进入二十世纪后,个别在汉语语境中出现的“民俗”与Folklore更趋近,应该疑问不大。1903年,《北洋官报》第九十九册第八页“各国新闻”中,有一则是“巴宴王近事联志”,说的是“德国考察东俄古物民俗会”,邀请巴宴国禄亲王为首董一事。1904年,课吏馆选印的《秦中官报》第九期“外报汇钞”中《俄国民俗通考》一文,涉及到衣食住行、婚礼、嗜酒等方方面面。有意味的是,1910年,《甘肃官报》第九期有一则“礼学馆调查民俗”的报道,云:“闻礼部人云礼学馆各员核议,以现在核订大清通礼,事务繁杂,惟必须体查各省地方民情,方能施行无碍。若□由各省□报,势难周密,议仿照调查法律、习惯之例,由本官□请时派专员赴各省详细调查,以昭核实,而备施行。”在此,民俗(地方风情)与法律、习惯并列,属通礼的一部分。
台湾英华字典数据库,收录了1815-1919年间极具代表性的英华字典。查询该数据库可知,Folk-lore一词并未出现在该数据库中收录的1900年之前的英华字典中,而都是出现在此后的英华字典中。其释义情况如下表:

还要注意的是,在颜惠庆英华大字典第378页,Citicism的英文和中文释义分别是:“The manners of citizen”“国民之行为、民风、民俗”。而“民俗学”一词则出现在该字典第1365页对Lore的释义,其第六个义项是:“folk-lore,野史、民俗学”。这也是整个英华字典数据库中“民俗学”唯一出现的一次。颜惠庆(1877-1950)的这本字典对1883年井上哲次郎(1855-1944)编纂的《增订英华字典》多有吸收。但是,收录有《增订英华字典》的台湾英华字典数据库显示,《增订英华字典》中并未出现将“Citicism-民俗”和“folk-lore-民俗学”对译的词条与解释。或者,从目前检索到的信息而言,是否有可能将folk-lore翻译为“民俗学”,视为是颜惠庆这位从弗吉尼亚大学留学归来的“译学进士”在中国,甚或东亚的首创?
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在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用英文写的自传中,颜惠庆提到了早年在主编《英华大字典》时,他还有大多毕业于其任教六年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十余位助手。编纂英华大字典时,他们主要参考的是纳托尔的《英语大词典》(Complete Dictionary)、韦氏大词典和其他大型工具书。换言之,颜惠庆英华大字典中出现的“The manners of citizen-国民之行为、民风、民俗”和“folk-lore-野史、民俗学”的互译,也有可能是其某位助手的功劳。同时,有鉴于台湾英华字典数据库并未将1815-1919年间所有的英华字典搜罗殆尽,上述推测就更不能说明Folklore在日本的翻译情况,以及在翻译过程中,中日之间可能存在的相互影响。正如岩本通弥教授在文章中指出的那样:1903年,上田万年、上田敏编的《最新英和辞典》就将之翻译为了“俗说学”“古俗学”;1893年,鸟居龙藏将之翻译为“土俗学”。遗憾的是,目前我们仍然无法探知日本学人的这些译法,是否影响到颜惠庆的翻译。
治中日民俗学、文学的人,都非常关注周作人(1885-1967)与“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1875-1962)之间的关联。尽管未提及“民俗(学)”一词,但今村与志雄的细考,说明了周作人以及鲁迅对柳田国男著作、学说和学术事业的熟悉。正因为如此,“民俗(学)”从日语引进这一说法,虽然让对周作人以师事之的江绍原多少有些迟疑,但大抵还是沿用了此说。遗憾的是,二人皆已作古,无法求证。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晚年在回忆他1903-1906年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时,提及使用的“华英字典”在重印时改名为“英华字典”之事。周作人从这本字典接触过Folk-lore这个词也不一定。但是,周作人并未提及他使用过的字典的版本。一切也就无法考究,岩本通弥教授存疑的问题,依然只能存疑。
二、Folkways:中国民俗学运动的另一支流
在现代中国的民俗学运动中,长期与“民俗”纠缠一处的还有“风俗”一词。巧妙地从“风俗”与“民俗”这两个关键词-概念的角度,王晓葵简要地梳理出了他的“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他将旧瓶新酒的“风俗”和受西学影响新生的“民俗”(Folklore),都纳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生成史的谱系中来审视,从而强化了这两个语词不乏浪漫色彩的民族主义意涵以及新生过程中的国民意识。当然,这也在一定意义上淡化了岛村恭则强调的民俗学惯有的“反启蒙性”和“在野性”。对于“风俗”,王晓葵在澄清汉语原本有的古义的基础之上,选取了1911年出版的张亮采(1870-1906)《中国风俗史》、1922年出版的胡朴安(1878-1947)《中华全国风俗志》和1929年发表的陈锡襄(1898-1975)《风俗学试探》三个文本进行辨析,清楚地指明了中国在艰难地进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历程中,受到西学影响的学人对风俗的当代释义,或者说赋权。换言之,因时应世,旧词新释的“风俗”有了求强、求新的现代性和民族性意涵,并成为形塑民族国家认同和国民意识的一环。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06年,邓实(1877-1951)就使用了“风俗学”一词。只不过,邓实将风俗学等同于严复(1854-1921)1903年译介进来的“群学”(sociology),即社会学。在那个暗流涌动、动荡交替之际,邓实在评述明季顾炎武(1613-1682)的学说时,将学术分为了君学、国学和群学三类。君学,功在一人;国学,功在一国;群学,功在天下。对群学,邓实专门做注解释道:“群学,一曰社会学,即风俗学也。”这与当下对社会学殿堂化、量化——越来越窄化、琐碎化的理解、将民俗学视为资料学的陋见,明显有着天壤之别。不仅如此,邓实强调的是,功在天下的社会学与风俗学的一体性。其实,邓实这一因对顾炎武推崇而生的主观判断,还暗合了二十多年后的中国社会学初创时期的基本情形。
颇有意思的是,为了阐明二十世纪前三十年“风俗”意涵的嬗变,王晓葵两次提到美国社会学家和民俗学家孙末楠的Folkways一书,尤其是其中的“德型”(Mores)一词。在当代中国民俗学界,对孙末楠民俗学说用力最勤的是高丙中。只不过,高丙中将孙末楠音译为了萨姆纳。在其对当代中国民俗学认知产生重大影响的专著《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高丙中用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重释、译介孙末楠的民俗学说。然而,在当代中国民俗学界对现代中国民俗学运动的梳理中,学者们几乎忽略了孙末楠民俗学说对中国民俗学以及社会学演进的重大影响。事实上,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孙末楠就是中国社会学界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其终极旨趣指向社会学的关于民俗的巨著Folkways,不但为中国社会学界所熟悉,还深远地影响了燕京大学的民俗学研究和现代中国民俗学运动的格局与图景。
简言之,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孙末楠的民俗学说在美国有着巨大影响。1905年,美国社会学会成立。1907年,孙末楠当选为美国社会学会的会长。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孙本文(1892-1979)、吴景超(1901-1968)等一大批中国社会学的先行者留美归来后,孙末楠的民俗学说也就紧随其后来到了中国。在中国,最早介绍孙末楠的应该是孙本文。
1927年,在《社会学上之文化论》一书中,孙本文写有“孙楠William Sumner之民俗论”一节。在该节文字中,孙本文将作为书名的Folklways译为了“民俗学”,将在同一“超机官”上三个层次的民俗分别译为了民俗、俗型(Mores)和制度(Institutions),并介绍了孙末楠民俗学说的核心观点,诸如:“民俗在个人为习惯,在社会为风俗”;“社会的生活societal life全在造成民俗与应用民俗”;“社会的科学The Science of Society即是一种研究民俗的学问”,等等。当然,孙本文对孙末楠民俗学说的介绍,与他对“文化(论)”情有独钟关联紧密。他认为,孙末楠的民俗学“实开近时文化学派分析文化之先河,无可疑也”。
与孙本文一样,在一定意义上,作为燕京学派的游离者,李安宅也是较早译介孙末楠学说的学者之一。1927年,在哈特(Hornell Hart)梳理的对社会思想有着重大影响的学者名单中,孙末楠位居前列。1928年,李安宅翻译了哈特的文章,将孙末楠音译为撒木讷,将Folkways翻译为“民风”,并简介了民仪、制度和民族等概念。英文原文和中文译文分别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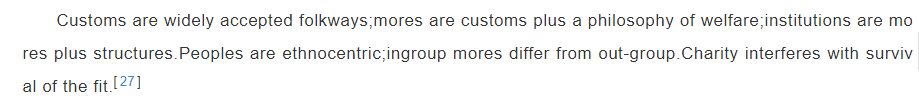
风俗是广被接受的民风;民仪(Mores)是加上公益理论的风俗;制度是加上了结构的民仪。民族是族化自中的(Ethnocentric);内群的民仪与外群的不一样;慈善阻碍适者生存的演化。
自此,源自孙末楠的民风、民仪与制度,不仅是李安宅1929年在燕大社会学系完成的毕业论文《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的关键词,也成为其整个学术写作中的核心词汇。
1932年,人文区位学(Human Ecology)的旗手、美国芝加哥都市社会学的领军人物,派克(Robert.E.Park,1864-1944)前来燕京大学讲学。其对孙末楠民俗学说言必称是的宣讲,再次激发了燕大社会学系师生以及中国社会学界研读Folkways一书的激情。派克刚离开中国不久,就出版了燕大师生学习心得的《派克社会学论文集》。其中,相当多的篇幅都涉及到孙末楠的民俗学说。1934年,黄迪还专门撰写了以孙末楠社会学说为题的硕士毕业论文,其讨论的核心还是Folkways一书。这些都使得孙末楠和他的Folkways成为后世称之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并不断追加、诠释的燕京学派的共有常识。
如同岩本通弥教授文中提及的当年对Folklore的多种中文译名,在二十世纪前半叶,除已经提及的孙本文和李安宅有别的翻译之外,前辈学人对Folkways始终有着多种译名,诸如:民俗学、民俗论、民风、民风论、俗道论。仅从这些译名,就可以确证当年孙末楠民俗学说在中国学界广泛且持久的影响。
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详述孙末楠民俗学说的基本内容、中国学者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对其的植入和创新性使用,仅想说明,对于明确且长期将风俗视为十大研究之首的燕大社会学系而言,孙末楠Folkways势必造成的影响,和这一影响对于中国民俗学与社会学演进的意义:
其一,孙末楠的Folkways有别于汤姆斯一脉偏重口头传统的Folklore。
其二,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孙末楠民俗学说在燕京大学这个平台与中国学者选择并创新的社区-功能论合流之后,再在对法国涂尔干(émile Durkheim,1858-1917)一派社会学和汪继乃波(Arnold Van Gennep,1873-1957)民俗学熟稔的杨堃(1901-1998)的具体引领下,中国民俗学已经在认知论、方法论和实践论层面,都大抵实现了向社会科学化的转型,至少说形成了现代中国民俗学运动中的“社会学的民俗学派”。
其三,孙末楠的民俗学说同样使得早期的中国社会学运动,尤其是以燕京大学社会学为阵地的北派——社区-功能学派(燕京学派),有着浓厚的民俗学基底。
毫无疑问,上述这些观点抑或说命题,是需要长文、专书来说明论证的。更不用说,在这一复杂的演化过程中,与江绍原同等重要的民俗学家,也是“社会学的民俗学”的干将黄华节,以及后来的邓子琴等人一度还提出过“礼俗学”。在此,仅想指明,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有着更加丰富的位相(phase),不但有着诸如传教士司礼义(Paul Serruys,1912-1999)这样研究中国民俗的“土著之学”,还有着明显有别于Folklore(当然受到Folklore影响)的Folkways这一支脉。
对Folklore和Folkways之间的异同,前辈学人是清楚的。作为社区-功能学派的领袖,吴文藻(1901-1985)在1933年写的这段话,值得今天的民俗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细细品味:
季氏以为社会反应之限于个人行为者,通称为习惯;其涉及集合或众多行为者,以前常称为风俗,今则统称为民风,以孙末楠的名著《民风论》(Folkways)而得名。他承认欲尽情描写一人群多行为及其生活方式,当莫善于“民风”一词。民风乃社会习俗,积久成风,原义渐失,而成为毫无意义的行为。西国文字中本有“民俗”(Folklore)一词,惟孙氏的民风论,比民俗学更进一层。他发觉民风中有较重要的习俗,一旦经过社会审定,予以认可,为团体态度所强制执行,则此种习俗,不复为民风,却已变为德仪(Mores)。德仪所异于民风者,在其专指社会上是是非非的成规而言:习俗以为是则是之,习俗以为非则非之,莫由强辩,这就是德仪。如此说来,德仪实是民德与民仪的混合物。
正是因为对社会学和民俗学兼通,吴文藻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还特意指导不少本科生写了关于婚丧、产育礼俗和民俗学运动史等民俗学方面的毕业论文。
结语
从Folklore的翻译、“民俗”一词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汉语语境中语义的微妙变化,从Folkways对中国民俗学以及社会学的影响这两个层面,本文尝试回应了岩本通弥教授《东亚民俗学的再立论》一文中涉及到的现代中国民俗学运动历史的问题。虽然有将前一个问题作为主体的趋向,但因跨语际释读能力以及材料的限制,对究竟是谁最先将“Folklore-民俗(学)”对译这一带有根本性的学科“小”问题,除罗列了些许事实之外,还是只能存疑,而求教于方家。关于孙末楠Folkways对中国民俗学演进的影响,只是提出了“社会学化的民俗学”或者说社会科学化的民俗学已经在燕大形成这一命题,并未展开详细的论证。
之所以提出这一命题,原因有二。一方面,是想回应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中国民俗学界不时在讨论的民俗学人类学倾向和究竟要不要以及如何社会科学化的问题,尤其是希望有更多的同仁关注燕大的民俗学研究,厘清中国民俗学演进更加复杂的位相与家底,从而继往开来。这一厘清,或者也能给今天中国民俗学究竟如何创造性的移植国外理论一些启迪,以尽可能减少机械的套用,将民俗学做成“术语”叠出却不接地气的“玄学”,而是将民俗学回归到岩本通弥教授所言的“日常学”。另一方面,则是希望有治社会学史的同仁,关注、正视燕大社会学的民俗学底色,从另一个角度丰富燕京学派的研究,也丰富中国社会(人类)学史,进而能给当下越来越偏重量化统计、理论模型建构和迷信“方法主义”的社会学研究一些启示。
此外,则还有孙末楠Folkways可能对日本早期民俗学产生影响的直觉。当然,这需要精研日本民俗学史的同仁回应与批评了。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本文刊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年第7期。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