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根据不同故事类型之间接合部分的结构特性,我们可以将蛇郎故事与螺女、老虎外婆、灰姑娘等故事类型的组合形态分为嵌入式、连缀式、复合式三种。嵌入式是蛇郎叙事过程中组合进螺女及巧女型,嵌入部分的两端都有机地编织进蛇郎主干中,类型之间的相似性提供组合基础,叙事逻辑、框架互相协调和限定。连缀式是两个类型前后连接组合,包括两类:“老虎外婆+蛇郎”是相对完整的连缀式,两类型中间衔接处具有双重形态意义的功能性事件,是角色转场、叙事过渡的关键;“灰姑娘+蛇郎”是不完整的连缀式,由蛇郎妻回娘家的文化符码在衔接处提供了文化参考构架,使叙事承上启下时浑然天成。复合式是嵌入式和连缀式的叠加,兼具两种组合方式的特点。
关键词
蛇郎;螺女;老虎外婆;民间故事类型;组合形态

1930年,钟敬文在《蛇郎故事试探》中,将蛇郎故事形态分为:原形的、变态的、混合的。原形的是比较单纯的、近于原始的模型;变态的蛇郎故事,男主人公不是动物而是人,包括单纯的(不组织入其他故事情节的)和混合的(混合了螺女型故事等);混合的包括混合了任何其他类型的蛇郎故事,如与老虎外婆型混合、与螺女型混合、与老虎外婆及螺女型混合、与灰姑娘及螺女型混合等。这是我国最早的蛇郎故事组合形态分类研究,准确地概括了最常见的几个类型组合的复杂情况。1937年,艾伯华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中归纳“31.蛇郎”时指出,比较老虎外婆结尾和蛇郎开头,3则异文都有“在小贩那里白菜变成了女孩”的情节,此外,除“灰姑娘”出现在蛇郎开头之外,蛇郎还同老虎外婆及螺女组合在一起。这一发现,与钟先生一致。1978年,丁乃通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发现,333C“老虎外婆”的异文中,2则与433D“蛇郎”组合。在“蛇郎”情节归纳中,“驱除魔惑”一节虽包括了螺女要素,但丁乃通将它作为固定的情节单元(Ⅵa),大概是因为27个异文都有此情节,所以没有视之为蛇郎与螺女组合。他还对510A“灰姑娘”与蛇郎组合的10个文本予以标明。这些发现,与钟先生基本一致,同时也扩大了文本和类型的对比范围。1997年,刘魁立在《中国蛇郎故事类型研究》中简要论及蛇郎与其他类型的组编及其对人物的突出作用。他认为,灰姑娘型的组编,“继母”母题仅作为蛇郎故事开头的扩展,强调主人公和谋害者的品性,是“为两者的本质和两者在情节发展中的行动,作扩大的展示和详尽的注解”;蛇郎妻和谋害者的争斗部分,组编了螺女型,是为了突出“对正面人物的亲善”。此外,2012年康丽对巧女类型丛的形态结构组编特点做了细致研究,把巧女类型丛的组编方式分为连缀式(发生在完整类型之间)、拼合式(母题或母题链嵌套在其他类型中)、混编式(上述两种组编形式的融合)三种,并阐释了它们的结构特点。这种探讨类型丛内部构成机理的视角对解析类型与类型、类型与母题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启发。
从上述研究中,我们仍然无法洞悉促使类型与类型之间组合起来的结构特性。尽管康丽做了巧女类型丛的深入探析,但是中国故事类型众多,不同类别的故事之间(如幻想故事与生活故事),叙事结构差异很大,因此,我们依旧需要继续追问:蛇郎组合螺女、老虎外婆组合蛇郎以及灰姑娘组合蛇郎在结构上各自有哪些特点?为什么这些类型彼此组合时能如此自然而不突兀?本文拟从蛇郎型故事的各种组合形态展开讨论。
本文以现当代采录的蛇郎故事70则为分析素材,其中,老虎外婆组合蛇郎8则,灰姑娘组合蛇郎5则,蛇郎组合螺女(同时又混入老虎外婆或巧女等)33则。本文采用了民间故事类型学方法,涉及的主要类型有五个。下面是钟敬文、艾伯华对它们的情节归纳:
(一)蛇郎型
1.一父亲,有几个女儿。
2.一天,他出门去,为蛇精所困,许以一女嫁之。
3.父遍问诸女,惟幼女肯答应嫁蛇。
4.幼女嫁蛇得幸福,姐姐杀之,而代以己身。
5.妹妹魂化为鸟,以詈咒其姐,复被杀。
6.她变形为树或竹,姐姐又恨而伐之。
7.姐姐遭妹妹之变形物的报复,受伤或致死。
(二)螺女型
1.一人在水滨得一螺(或其他小动物)。
2.其人不在家,螺幻形为少女,代操种种工作。他归而异之。
3.某天,其人窥见螺女正在室中工作,乘其不备,搂抱之,因成夫妇。
4.若干时后,螺女得其前被藏匿的螺壳,遂离去。
(三)老虎母亲(或外婆)型
1.一妇人,有两儿女(或一女一儿)。
2.一天,母亲外出,有老虎(狼或野人,或其他猛兽)幻形为他们的母亲(或外婆、叔婆)来到家里。
3.夜里老虎吃小妹,声为其姐姐所闻,惧而逸去。
4.老虎寻觅(或追赶)其姐,但卒失败(有的已尽于此,有的则下接卖货郎得七个女儿的情节)。
(四)灰姑娘
1.一个长得漂亮的继女受到继母的虐待。
2.她照料着由生身母亲变成的一头牛。
3.继女不得不满足各种各样的条件(理清一团乱麻),牛来帮她的忙。
4.继母发现牛在帮忙,便把牛宰了吃了。
5.继女把牛骨头收集保存起来。
6.继母和长得很丑的妹妹去参加一个庆祝活动。
7.继女从牛骨头里或者通过牛骨头得到了节日盛装。
8.她也去参加庆祝活动,结识了一位秀才,跟他结了婚。
(五)聪明的女人II:完美的回答
1.聪明的女人或者她的丈夫面临困难的问题。
2.女人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大多数情况下通过反问)。
3.人们佩服她(或者娶她)。

根据类型组合的结构关系,并借鉴钟敬文、康丽对类型组合的分类,笔者将蛇郎故事的组合形态分为三种:嵌入式、连缀式、复合式。没有任何其他类型混入的蛇郎,仍借用钟敬文的命名,称为单纯式。若按照各类型(指析离后的单纯式)在叙事中出现的顺序,将其编码为A、B、C、D……,用()表示嵌入,+表示连缀,【】表示整个故事文本,那么,三种蛇郎组合形态可进一步符号化为:
嵌入式:【A(B)】
连缀式:【A+B】
复合式:【A(B)+C】或【A+B(C)】或【A(B)+C(D)】
(一)嵌入式:【A(B)】
嵌入式,即在类型A叙事过程中,插入类型B的叙事板块,主人公没有退场,继续在B中采取行动,B结束后接叙A的其他情节,直至故事结局。这种组合中,主人公及其追求对象始终不变,B总是隶属于A的叙事时空和叙事链条。如果嵌入了两个以上类型,则变成【A(B)(C)】、【A(B)(C)(D)】……当然不可能无止境地嵌入,故事总要完结。在蛇郎异文中,蛇郎与螺女组合大多为嵌入式。
1.【A(B)】:蛇郎(螺女)嵌入式
就情节的连贯性和逻辑性而言,类型B的文本两端都很关键,应有机地编织进A中,成为整个故事的枝干。B的叙事篇幅小于A,是A的构成部件。蛇郎异文中,常在真假蛇郎妻最后一次交锋之后嵌入螺女型。根据叙事空间变换与否,即蛇郎妻是否被带离蛇郎家,该嵌入式可分两种情况:
(1)叙事空间改变。由突然造访的老妇(多为邻居)发现蛇郎妻并带回家,有13则。例如下面辽宁的《蛇郎》(异文一)中的片段(螺女嵌入前后用于衔接和过渡的句子,划波浪线标出;螺女的叙事部分,划直线标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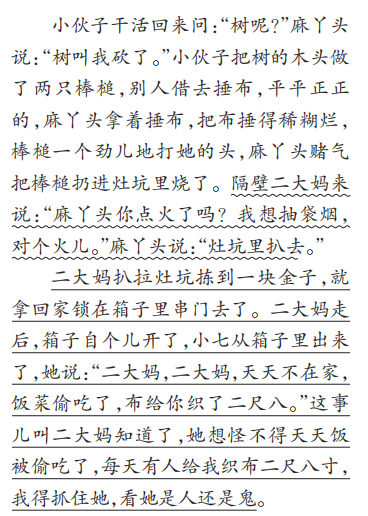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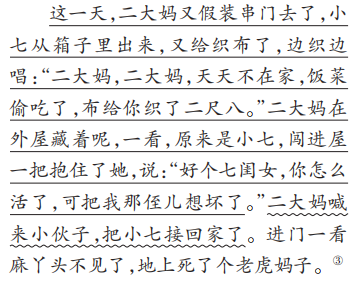
这则异文讲到棒槌被烧后,出现了新角色,也变换了叙事空间。同时螺女型嵌入的界线很明显,其首尾都有衔接作用的话语。嵌入之前,是真假妻子的最后一次交锋:小七变棒槌复仇,麻丫头把棒槌烧掉。接着,交锋结束,转而引入一个新人物,也是小七的助手——隔壁二大妈,她来找麻丫头对火儿点烟,麻丫头很不礼貌地让她自己到灶坑找火,这为二大妈拾取小七的变形物提供了契机。由此顺利进入了螺女的叙事单元:二大妈发现一块金子,带回家锁起来,以后出门回来总有人偷吃饭菜、给她织布,遂藏匿偷看,发现小七复活。单纯式螺女中,主要情节有拾取归养、现形做工、窥视成婚;此处嵌入的螺女中,蛇郎妻变形物不都是田螺等水生物,但依然保有被珍藏、现形做工、窥视团圆等类似情节。其差异在于:前者发现螺女偷偷做工的是单身男子,后娶螺女为妻;后者发现螺女的是隔壁老妇,后帮助螺女走向团圆。接下来,老妇让蛇郎把妻子接回家团聚,叙事也从螺女嵌入部分成功跳出。
(2)叙事空间未变。蛇郎妻由蛇郎发现,有11则;由假蛇郎妻发现,仅2则。例如山东的《七姐和于郎》,发现者是蛇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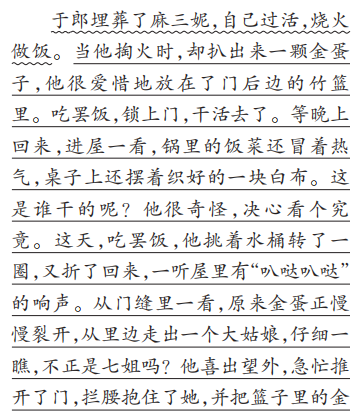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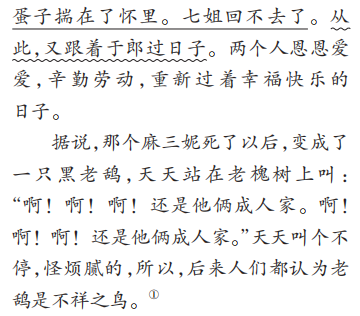

再如河南的《三妮儿和花郎》,发现者是坏姐姐(即假蛇郎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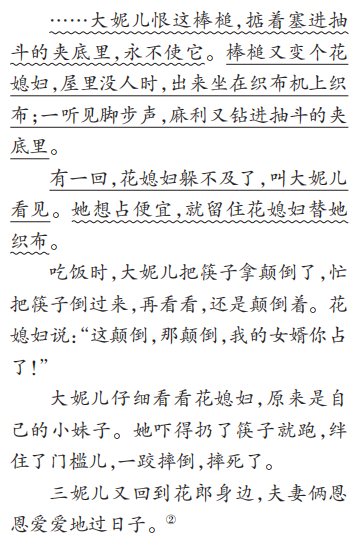
对比来看,山东异文的叙事空间未变,角色也未增减。在真假妻子最后一次交锋中,假妻子已死,男主人公变成孤身一人,这更与单纯式螺女故事相匹配了。因此,螺女嵌入的开头只有一句过渡(见波浪线部分),就轻松地进入螺女的叙事:由蛇郎收纳妻子变形物并发现妻子复生、做工,一直到抱住妻子、藏起金蛋、让她无法回去为止。结局是完美的夫妻破镜重圆,最后还交待了坏姐姐变成黑老鸹的应有下场。
河南异文中,叙事空间和角色也没变,但因发现者是蛇郎妻的对头——坏姐姐,所以斗争没有结束,紧张气氛仍在。嵌入时过渡话语也比较明显,特别是大妮儿发现了花媳妇,为了占便宜留着她织布,把故事重新引向两人的善恶对立中,接着是又一次交锋:筷子神奇的颠倒,三妮儿巧嘴的讽刺,令对手吓跑并摔死,终于成功复仇。
可见,发现者不同,由此展开的叙事方向也不一样。当发现者是新增角色——隔壁老妇时,女主人公被带回家,叙事空间也发生变化,从蛇郎家移到老妇家,由她发现蛇郎妻复活、做工、哼唱,再使之重返,与蛇郎团圆。女主人公离家又返回,犹如做了一次有关复活的旅行。老妇的出现,似乎显得突然,但她是为了抽袋烟、对个火儿,这是东北人吸烟时点火的一种习惯。罗兰•巴尔特将这类叙事因素称为“文化符码”,是“发自人类传统经验的集体而无个性特征”的知识性表述。这一文化符码使老妇的出现合理化,也符合听讲者日常生活经验,继而由她帮助了蛇郎妻,情节嵌入一点也不显得生硬。
当发现者是原有角色,有两种情况:一是坏姐姐发现她,必然导向彼此再次交锋,蛇郎妻继续声讨坏姐姐,直到恶有恶报;二是蛇郎发现她,则非常契合单纯式螺女型仙侣奇缘的主题,螺女型成分就有更多的保存,特别是坏姐姐的离开或死亡,为蛇郎夫妻重逢扫清了障碍。角色呈现的情感有所不同,原螺女型男子发现田螺变形为人感到的是惊奇,蛇郎发现妻子死而复生,体验的是悲喜交集。
总体来讲,由隔壁老妇或蛇郎发现螺女的异文最多,这或许基于与螺女型故事的契合度:螺女总是在珍藏她的善良者家中变形为人,为之劳作,似乎是回报善待她的人们。再对比那些没有嵌入螺女的异文(其结尾是坏姐姐被杀死,或蛇郎妻直接变形为人),螺女的插入,使蛇郎故事中女主人公顽强的生命力有了更神秘而深广的扩展。
上述异文中,嵌入部分的叙事链两端衔接得非常自然,毫无违和感,原因何在?这主要是基于两个类型的相似性以及组合时的限定性。概述如下:
(1)蛇郎和螺女都是婚恋主题,男女主人公彼此珍爱。与坏姐姐斗争的蛇郎妻,具有多次变形的神奇本领,这与螺女相类似。主题和角色特质的相似,为类型组合提供了良好基础。
(2)嵌入部分的开头和结尾,都是两个类型中共有的、固定的情节单元,同时,在彼此组合时,遵循各自结构的限定性而选择、组编起来。
首先,嵌入的开头都是女主人公变形物的发现、收藏。螺女整合进蛇郎时,蛇郎妻需要找到复活之法,这种情境隐含着两种行动取向:要么活命(自救或求助于他人),要么等死。而“等死”这一项,不具备继续展开民间叙事的必要性,因为叙事不会选择“等死”而让故事简单地结束。这正如巴尔特讨论叙事的行动序列时所说:“结果叙事在面对着每一种二中择一行动前永远选择其有利项(赋予它某种后果),即何者确保其作为叙事的存在。叙事绝不选择会终止故事或使其夭折的项目(似乎表达着自身的完成)。某种意义上确实存在有一种叙事保存本能,叙事在被表达的一个行动中所蕴涵的两种可能结果之间,永远选择会使故事‘重新活跃起来’的一项。”那么,蛇郎(螺女)嵌入式中符合叙事保存本能的、赋予故事重新活跃能力的行动项,就剩下“活命”(自救或他救)一项。未嵌入螺女的故事里,自救和他救方式都有:自救方式如蛇郎妻在葫芦、雪莲花、果子中复活或从小鸟直接变成人等,“他救”如蛇郎做法使她复活、蛇郎浇灌相思树并用鲜血使她复活等。然而,嵌入螺女的蛇郎故事,选择的是他救之法,常常是隔壁老妇或蛇郎珍藏了她的变形物,而后发现她复活劳作,有时还增加了复活的难度,如需要人的鲜血滴在身上,或要从淹死她的河里挑水回来,或需要用筷子、勺子做骨架等等。总之,这两条活命之路都合情合理,又让叙事重新活跃起来。不过,螺女故事内在结构具有限定性,它只能让人物在规范的框架内行动,即蛇郎妻要被人收藏,再于幻形时被人发现。因此,螺女嵌入蛇郎而面对“二中选一”的情境时,必然采取他救之法,这也是螺女型叙事的行动序列逻辑的制约。
其次,嵌入的结尾是女主人公变形为人,与心仪的男子结婚或团圆,而蛇郎和螺女中又都以此结束,叙事从螺女部分跳出时逻辑上顺理成章。原螺女型还有螺女离开的母题,在嵌入蛇郎时,只有团圆的结局,这亦是蛇郎故事对女主人公行动的限定性选择。
上述这些限定性选择,通过制约角色行动进而形塑了角色形象的表达。在无螺女嵌入的蛇郎中,女主人公多采取自救方式,其勇敢、机智的品格和行动的主动性、独立性得到充分的肯定;在螺女嵌入的异文中,因增加了助手,女主人公战斗的独立性有所削弱,却平添了浪漫、柔美的特质。

2.【A(B)(C)】:蛇郎(螺女)(巧女)嵌入式
有时,蛇郎故事同时嵌入了螺女、巧女等两个类型,角色的行动、叙事的衔接又有了新变化。例如福建的《蛇郎君》在后半部分嵌入了螺女型和“聪明的女人II:完美的回答”型。下面节选其片段(类型之间衔接和过渡处划波浪线标出,螺女型的嵌入部分划直线,“完美的回答”型的嵌入部分划虚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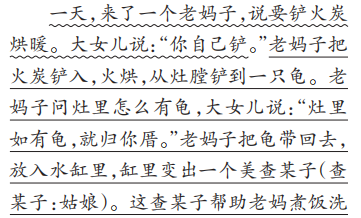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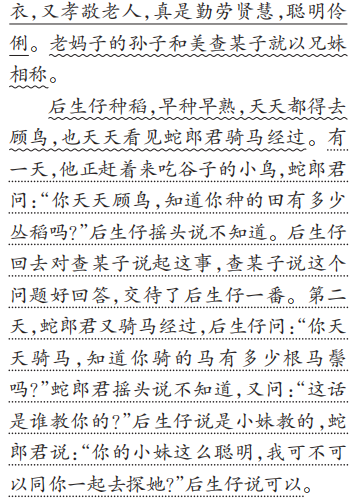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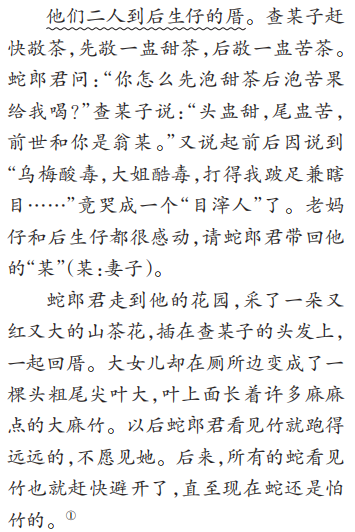
在此片段中,螺女型嵌入时仍是引入了一个新角色——老妇来借火炭,发现蛇郎妻的变形物,并带回家,她复活了。但是缺乏偷偷做工、窥视搂抱的情节,它呈现为弱化形式。嵌入的结尾,老妇把蛇郎妻视为孙女,和孙子成了兄妹。这又出现了新角色——老妇之孙,是另一个为蛇郎夫妻重逢牵线搭桥的助手。接下来,故事嵌入巧女问答情节,问答双方在原类型中是巧女丈夫(或巧女本人)和陌生人之间多次难题问答,在这里是老妇孙子和蛇郎,仅一次问答,这显然也是一种弱化。两个男人在田野里相遇、发问,叙事时空至此发生了几次改变,由蛇郎家移到老妇家又到了户外,角色从争斗的两姐妹换成了互助的祖孙(老妇与蛇郎妻),再换成发难的两男人。这里一问一答的难题,不仅仅是为了考验男人的智慧,或显示男人间的竞争,更是寻找妻子的行动,为了成功地让蛇郎夫妻相聚。
概括而言,这则异文中,螺女型和完美的回答型的嵌入,篇幅都不长,也都没有充分展开,其作用是为主角增加两个助手:一是老妇,她把蛇郎妻带离与对手交锋的时空,为其复活提供新场所,二是老妇孙子,他把蛇郎引到妻子身边,使夫妻团聚。故此,原类型中螺女仙妻带来的奇妙爱情、巧女因丈夫平凡而受到陌生男子揶揄的微妙心绪,当嵌入到蛇郎中都遭到摒弃,转而围绕蛇郎夫妻从生离死别到执手相认的故事线来重组情节、增删人物,仅保留了它们的大致形制。可以说,此蛇郎故事是三个类型的叙事逻辑和结构框架互相协调和规制的结果。
(二)连缀式:【A+B】
连缀式,按照康丽的界定,是两个以上完整的故事类型连接而成。笔者把连缀式限定为单纯式彼此组合,以区别于嵌入式、复合式;还有所谓完整的故事类型,是一种理想而已,实际上只有相对的情节完整。蛇郎连缀式有两类:老虎外婆和蛇郎的连缀式、灰姑娘和蛇郎的连缀式。“老虎外婆+蛇郎”中,两个类型都是相对完整的,表现为A叙事结束后,通过中间的过渡、转换,新的主角和对头登场,展开B的叙事,A的主角和对头退场(或至少暂时退场或变形为B中全新角色),叙事时空也随之彻底改变。“灰姑娘+蛇郎”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类型(灰姑娘)与一个不完整的故事类型(缺少求婚等部分的蛇郎)的组合,类型A和B中的主角和对头是相同的,叙事情境分别对应于婚前继母迫害和婚后坏姊妹(或继母)迫害,叙事空间随着婚礼而由继女家扩展到蛇郎家,人物则在这两个家庭间穿梭。此外,在连缀式中,类型A和B除了衔接部分之外,都可以充分展开各自的内部情节单元,不像嵌入式那样A、B基于内在框架而彼此牵制。
1.完整的连缀式:老虎外婆+蛇郎
老虎外婆与蛇郎的连缀式,是两个相对完整的类型组合,首尾衔接的部分则非常关键,好的过渡、转换方式有助于A顺利转场到B中。辽宁的《老虎妈子》、安徽的《老虎外婆》、河南的《老扒子》都是“老虎外婆+蛇郎”连缀式文本。下面以辽宁《老虎妈子》为例,讨论两个类型连缀的基本特征。仅节选两个类型中间结合部分,划波浪线处是完成衔接、过渡作用的段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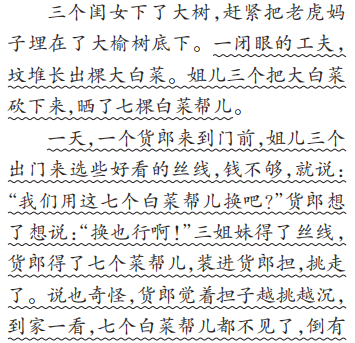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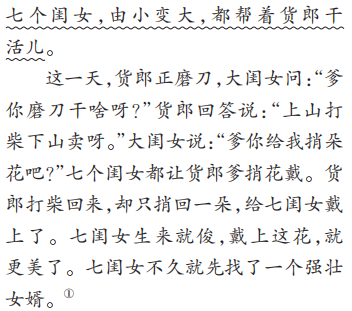

从节选部分来看,类型A讲到老虎妈子被三姐妹摔死后,变成一棵大白菜,被三姐妹砍下来,晒了七个白菜帮儿,又卖给货郎,到了货郎家变成七个闺女,就做了货郎的女儿。至此,A中的主角和对头(三姐妹与老虎妈子)换成了B中的货郎家两姐妹,叙事空间也从三姐妹家转移到货郎家,女性的人生阶段从少女时期变成了青年时期。可见,货郎买走会变形的白菜帮儿(有些故事是白菜),具有空间过渡、角色转换、类型承转的功能,缺了它,老虎外婆和蛇郎故事无法组合起来。
货郎(偶尔是其他人物)是类型A中结尾部分出现的人物,负责见证妖怪的变形样态。尽管妖怪变形具有多样性,但是货郎的行动取向始终包含两项:除掉或不杀妖怪变形物。在单纯式老虎外婆的部分异文中,货郎选择除掉妖怪,成为最后除妖的英雄,故事在他的胜利中结束。如黑龙江的《老虎妈子》中,老虎妈子被三姐妹摔死后变成七棵大白菜,卖给了货郎,一路上还说话,货郎不敢生吃,让媳妇炖豆腐吃,在锅里还说话,货郎夫妇把它喂猪了;辽宁的《老虎妈子》(异文)的结尾,黑狐精变成两棵大白菜,当货郎来时,大白菜变成除妖的姐妹俩模样去买花不给钱,后被货郎和姐妹俩发现,砍烧之。在“老虎外婆+蛇郎”连缀式中,货郎选择不杀掉妖怪变形物——女孩们,做了养护她们的父亲,接着女孩们的婚姻成了故事的核心,故事继续扩展开去。如上文的辽宁《老虎妈子》,货郎买回的白菜帮儿,变成了能帮忙干活的七个大闺女,货郎就做了她们的爹,成了亲亲热热的一家人,然后面临女儿们的婚嫁问题。货郎采取哪种行动,似乎最终取决于妖怪变形物的性质。当变成蛊惑人的精怪时,货郎除之,叙事则完成;当变成乖巧的女孩时,货郎守护之,叙事则重新活跃起来,蛇郎故事就有了接续的机会。
问题是,A与B的衔接处为何不觉得突然?连接两个类型的功能性事件是关键。普罗普指出,一个功能项可以具有双重形态意义,如丈夫离家时禁止妻子出门,而加害者引诱妻子出门,妻子出门的行为则既是接受了加害者的劝诱又是打破了禁忌,即一个行为具有了两种功能。基于普罗普的这一理论,处于A、B两类型衔接处的功能性事件,也具有类似的意义。妖怪的变形,在单纯式老虎外婆的结尾处,是加害者第二次出场,需要主角与加害者继续交锋。然而,在“老虎外婆+蛇郎”连缀式中,妖怪的变形没有导致激烈的交锋,而是卖给货郎带走。这既是交锋的弱化形式,也是时空转换、角色走马换将的时机:货郎回家,得到了白菜变成的女孩们,这形成了蛇郎故事的初始情境。因此,买卖妖怪变形物具有了“双重形态意义”,一方面,A中的主角与对头交锋结束(即A的主人公卖掉它,完成战斗的终结),另一方面为B设置了初始情境,买了它的货郎有了女儿们,成了一家子,为蛇郎的叙事做好准备。
此外,老虎外婆和蛇郎在主题上也有延续性,老虎外婆讲的是年少的女孩们守护家园、抵御外力入侵,蛇郎讲的是婚恋中的成年女性如何守卫自己的爱情和家庭。统合起来,如果把邪恶的老虎精和坏姐姐看成是女性成长历程中需要战胜的负面因素,那么两个类型都致力于揭示女性成长的困境以及突破困境的努力。主题上的前后承继,让两个类型的组合更像是踏上一条上行的阶梯一样,有了层层递进之感。
2.不完整的连缀式:灰姑娘+蛇郎
在“灰姑娘+蛇郎”的连缀式中,灰姑娘是相对完整的类型,以继母迫害开始、以婚礼结束,接着是蛇郎故事的后半部分,即幸福的婚姻引起继母和坏姐妹的嫉恨、杀害等行为。两个类型连接部分是它们共有的母题——婚礼,承接得非常自然,只是幸福婚姻显得如此短暂,直到彻底战胜坏人的诡计,主角才能重获幸福。
例如,云南的《喜鹊》讲的是继母让继女给有破洞的缸挑满水、分拣出混杂起来的谷物,这些难题都在花喜鹊的帮助下完成。后来,打猎路过的王子看中美丽的继女,娶了她。当他们回家探望时,继母把她推下井淹死,把亲生女儿送回王宫做王妃,王子质疑假妻子的相貌,被继母的种种狡辩糊弄过去。当假王妃和王子再次回娘家时,花喜鹊告诉王子真相,继女的尸体被找到,继母受到惩罚,花喜鹊啄醒了继女,假王妃被赶走,王子夫妇过上美满的生活。这则异文中蛇郎部分,缺少婚前求嫁和女主人公变形复仇的情节,由此女主人公一直处于被动状态:婚前被迫害、婚后被害致死。两个类型连接处如下,划线部分则进入蛇郎叙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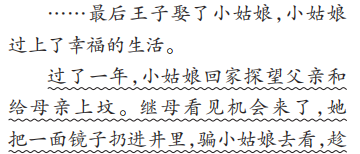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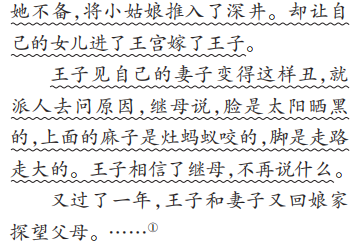
连缀在一起的A和B,看不出丝毫拼接的痕迹。这首先归功于两个类型共有的婚礼母题,其次因为文化符号——婚礼后夫妇二人回娘家,这是再自然不过的我国传统风俗习惯。作为“文化符码”,它“带给我们一个十分熟悉的现实……为特定的文本提供一个文化参考构架”,听众会在“回娘家”这个参考构架下继续听讲和预测接下来发生的事件。A和B就是利用了这一文化符码衔接起来的,向上承接了继女的婚礼,向下展开了婚后继母和坏姊妹的破坏行动。
(三)复合式:【A(B)+C】或【A+B(C)】或【A(B)+C(D)】
复合式是上述两种基本形式的叠加形态,每个异文则同时具有嵌入式和连缀式的结构特点,这使故事更显曲折(或是活跃),情节单元更为丰富。复合式有两种情况:
1.单纯式与嵌入式的复合
若A嵌入了B,再连缀了C,记为【A(B)+C】。如江苏的《老臊狐与花花小蛇郎》、河北的《三姐妹》,是嵌入了老虎精型的老虎外婆,又与蛇郎故事连缀在一起。若A与嵌入C的B连缀起来,记为【A+B(C)】。如河南的《颠倒筷,筷颠倒》《老狼婆》中,老虎外婆与蛇郎连缀,蛇郎中嵌入了螺女;广东的《疤妹和靓妹》是灰姑娘和蛇郎连缀而成,蛇郎中嵌入了螺女。
2.嵌入式与嵌入式的复合
A嵌入了B,C嵌入了D,最后A和C又连缀组合成一个大故事,记为【A(B)+C(D)】。它比前两种情况更复杂一些。例如河北的《三姐妹》(异文),是嵌入了老虎精型的老虎外婆与嵌入了螺女的蛇郎相复合。
相比于【A+B】单纯式两两连缀,【A(B)+C】或【A+B(C)】的复合式蛇郎故事更为常见。但是,【A(B)+C(D)】的情况却很少见。这一点需要扩大文本采集范围再做定论。
限于篇幅,也由于复合式的结构特点是嵌入式、连缀式的叠加而已,所以不再解析赘述了。
本文探讨了蛇郎故事三种基本组合形态:嵌入式、连缀式、复合式。嵌入式是蛇郎故事中插入了篇幅小于自己的类型,如蛇郎(螺女)嵌入式,突出了蛇郎妻复活与丈夫团圆的过程,嵌入部分的两端都有机地编织进蛇郎叙事链中,同时两个类型之间叙事逻辑和框架互相约制、调和。连缀式是两个类型前后连接,如“老虎外婆+蛇郎”是相对完整的连缀式,首尾相接之处的功能性事件,具有双重形态意义,使叙事承转顺利过渡;“灰姑娘+蛇郎”是不完整的连缀式,衔接处的文化符码提供了文化参考构架,发挥了承上启下作用,使两个类型的衔接水到渠成。上述两种方式叠加成了复合式,它兼具嵌入式和连缀式的特点,令叙事更具丰富性。
对比单纯式、嵌入式、连缀式及复合式的叙事纵深度,单纯式和嵌入式蛇郎故事集中在青年女性婚恋前后,连缀式和复合式蛇郎故事中角色生活时空跨度更大,从少女时代为人女儿到青年时代为人妻母。其中,“灰姑娘+蛇郎”连缀式或复合式中,女主人公前后一致,角色跨度和成长表现得更为直接而鲜明。在“老虎外婆+蛇郎”连缀式或复合式中,女主人公前后不同,其成长历程具有象征性,勇斗老虎外婆的少女们恍若蛇郎妻之少年影像,蛇郎妻变形复仇的斗志亦如老虎外婆中女孩们智勇的延续。连缀式和复合式蛇郎故事所包含的情节单元更多,因此展现女主人公和对头的行动序列和性格面相也最多。简言之,在与其他类型组合的蛇郎故事中,类型之间的角色模式、叙事意义的关联性,也有待深入研究。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民族艺术》2020年第3期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