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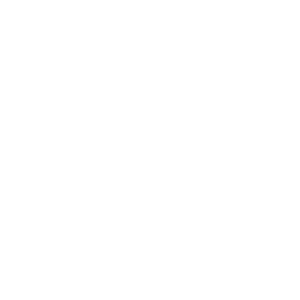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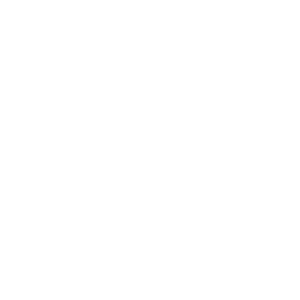
摘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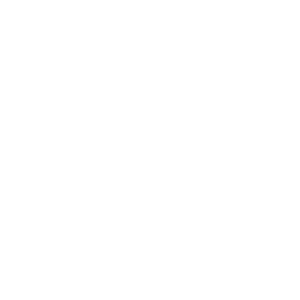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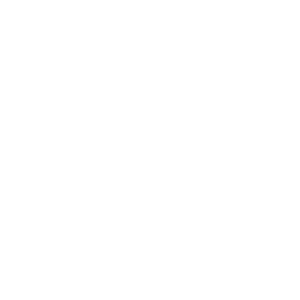
文化记忆是一个被建构的意义系统,关于祖先和英雄的文化记忆对于族群来说具有重要的价值,在传承过程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锡伯族海尔堪的民间传说、家族记忆以及集体记忆,共同塑造和建构着海尔堪大神的文化记忆。在其建构的过程中,传承人个人化的叙事策略凸显出对传统的强烈认同感以及进行传统阐释和“再现”的努力,并力求使文本适应当下的阅读语境,以实现其承续,由此,传承人以及他的讲述也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文化记忆的建构也通过外在的纪念物、博物馆、书写等媒介形式发挥凝聚与认同的功能,从而实现文化记忆的连续性。神圣性的“精神文本”是文化记忆中的深层文本,关乎信仰、仪式和“高级秩序的真理”,是文化记忆得以传续的内在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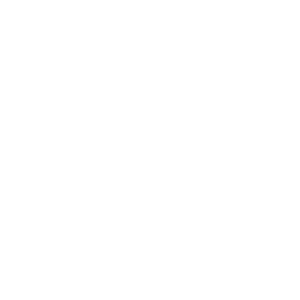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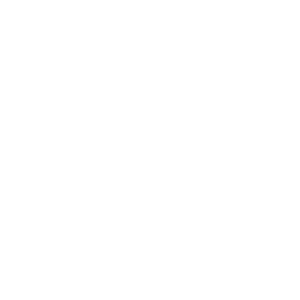
关键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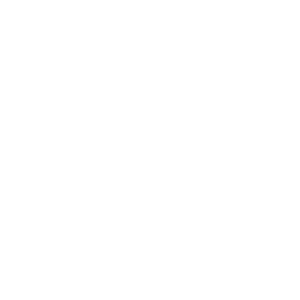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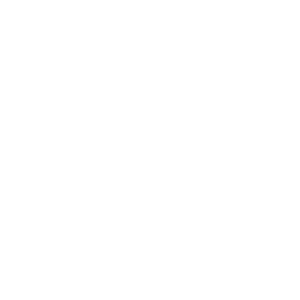
锡伯族;海尔堪;文化记忆;信仰;建构
文化如何传承,记忆如何建构,这一古老的命题近些年来随着文化记忆研究的兴起而具有了新的观照角度。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夫妇在20世纪末提出来的文化记忆理论,对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人文学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以及阿莱达·阿斯曼的《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等著作探讨了文化记忆的类型、形式、变迁,以及书写文化、文化认同、政治想象等理论问题。文化记忆凝聚着一个族群关于传统、过去的情感与意义的认知,激发着族群的归属意识和身份认同,相关的人借此确立自我形象和政治身份。文化记忆与集体记忆、社会记忆有着深刻的联系。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共同回忆创造了一种凝聚感,形成“集体意识”,对于族群和个体认同感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中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强调人是在其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记忆,集体记忆受到社会框架的制约,认为“社会思想本质上必然是一种记忆,它的全部内容仅由集体回忆或记忆构成。但是,在其中,只有那些在每个时期的社会中都存在,并仍然在其现在的框架当中运作的回忆才能得以重构。”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也强调了“记忆”的社会性特质,认为在个体记忆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记忆,即社会记忆,并强调社会记忆通过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的方式进行延续和传递。纳日碧力戈在调查各烟屯蓝靛瑶时发现社会记忆在信仰仪式中延续,思维观念和肢体仪式共存互生,成为社会记忆的一部分,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操演,和经济理性对话,使传统在表层蜕变的同时保持底层的沿续。这些观点为民间口承叙事研究提供了启发。
关于祖先和英雄的文化记忆对于族群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虽然发生在遥远的过去,但是却在族群成员的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那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文本被视为核心文献,经常被抄写和背诵,最后成为经典之作,拥有了规范和定型的价值。”通过文化记忆的视角来看神圣祖先的口碑文本与信仰,可以发现神圣记忆在传承过程中的建构路径以及个体的能动性如何影响了族群意识的认同和凝聚。
锡伯族的海尔堪信仰在锡伯族族群中即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记忆,历经了漫长的历史时期,虽然一度中断,却又“复苏”,尤其难得的是锡伯族的何钧佑老人讲述的带有鲜明史诗性的锡伯族长篇故事《海尔堪大神传奇》,延续并传承了古老的海尔堪玛法文化记忆。那么,这一文化记忆传承至今,它的记忆系统是如何形成的?在传承与建构的过程中被赋予了怎样的意义?这些问题的展开,也许能够使我们更进一步走进锡伯族文化的深处,也能够触摸文化记忆的脉络是如何在历史中铺陈与播衍的。

一、海尔堪玛法传说
与锡伯族的集体记忆
海尔堪,锡伯语为保护牲畜的意思;玛法,锡伯语为祖宗的意思。海尔堪玛法,即保护牲畜兴旺的男祖宗之意,又叫“马神”。海尔堪玛法是锡伯族萨满神灵系统中的神灵之一,至少在清代,就已经是锡伯族重要的民间信仰形式,与喜利妈妈(锡伯族女性祖先神)并列为祖先神灵。“他原来代表的是男性祖先,后来经过父系社会漫长的历史发展,逐步演变为保护家畜兴旺的神。1949年以前,每户均立有其龛位。”根据老人口述以及一些资料的零星记录,可以了解到,海尔堪玛法一般供在房屋外西南墙的房檐下,在檐下的墙内掏出一个长方形的洞,约一尺半深,一尺高,半尺宽,里面放个木匣子,匣子里装有或木雕、或泥塑、或纸画的神像,即海尔堪玛法;在洞的下方钉两根木桩,上面放一块木板,板上放置香炉等祭器。关于为何将海尔堪玛法供奉在屋外,民间认为在古代社会,男子经常外出狩猎或者放牧,龛位空间位置和供奉物体现了这一古老的经济模式和男女性别分工,“供奉物反映了古代锡伯族经济生活中,以男人放养牲畜为主,牲畜的兴旺直接影响人们的生计,故用男人象征‘海尔堪玛法’。所谓男祖宗,是保佑牲畜兴旺之神。辽宁地区锡伯族家庭至今尚有供奉,供在屋外面,寓意男主外。今瓦房店市和岫岩一带锡伯族称海尔堪为外老祖宗。”海尔堪玛法的“神像”具有地区差异性,即使同一地区,形象也不同,有的是带有胡须、身穿狍皮的中年男子形象;有的是以物替代神像,用马鬃、马尾或写有“供奉马神之位”的黄布替代。供奉海尔堪的家庭,每逢初一、十五,以及逢年过节,都要烧香叩头,祈求牲畜兴旺。
关于海尔堪玛法的传说,在锡伯族民间广为流传,有几种不同的版本:一是说他是有名的“族长”,在带领锡伯族与敌人打仗时战死,其坐骑成为他的替身,神勇无比,击退了敌人,马老死后被供奉为族神,以族长海尔堪名字命名。二是说他是拯救牲畜的著名的放牧手,死后被族人奉为保佑牲畜繁衍生息的神灵。三是说他是一名穷苦的放牧手,避免了族人牲畜的一次大灾难,后来成为牲畜保护神。在《锡伯族民间故事集》中还收录了一则在东北锡伯族中具有代表性的《海尔堪玛法的传说》:汉朝时期,锡伯族先祖的居地经常遭受匈奴的侵袭。部落里有一位英雄叫海尔堪,带领大家制作武器,练兵习武。在一次战斗之前,海尔堪把部落里的老人和儿童疏散到山里,带着一群青年迎战,终因寡不敌众,死伤惨重,最后只剩下海尔堪一人,危急时刻,他的白龙马奋起四蹄,扑向敌人,并驮着海尔堪涉水渡河,把敌人全部引入滔滔冰水之中。传说海尔堪和白龙马后来回到了大兴安岭,为千家万户看护着马、牛、羊,锡伯人把他奉为神灵。此外,这本故事集中还收录了一则《达尔洪爷爷的传说》,传说有一位孤独的老人一年四季手不离放牧杆,人们叫他达尔洪,达尔洪为乡亲们放牧并繁育牲畜,受到人们的爱戴,被供奉为神灵,后来人们又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海尔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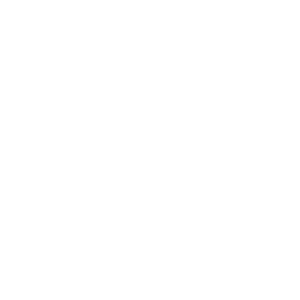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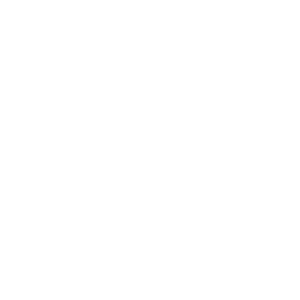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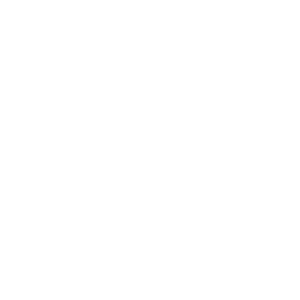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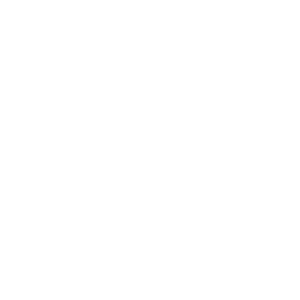
关于“海尔堪玛法”的传说,也有人认为与“鲜卑瑞兽”有关,“鲜卑瑞兽”是锡伯族崇拜的一种图腾,相传锡伯族人在穿越大兴安岭时,因山高谷深,行进困难。这时出现一形似马、声似牛、行走如飞而善解人意的神兽,被称为“瑞兽”,后来逐渐演变成马神“海尔堪玛法”。锡伯族爱马,认为它通灵性、通人情,懂得报恩。洁白如雪、英俊吉祥的白马形象成了民族精神的象征。《魏书·帝纪》记载:“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东胡人以此兽状铸刻带钩之上,即所谓‘鲜卑郭洛带’,译言瑞兽带,或神兽带。”现在在锡伯族民间还流传着有关神兽的传说,说神兽在鲜卑人南迁时曾经引领族众走出大兴安岭,因此受到鲜卑人的崇拜。也有学者认为鲜卑瑞兽糅合了马和猎狗的形态,体现了从渔猎到畜牧以及农耕文化的过渡痕迹。还有学者认为神兽其实是产自大兴安岭的一种家狗,锡伯族人狩猎时经常带着它。关于鲜卑瑞兽的种种揣测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的是,“鲜卑瑞兽”是鲜卑人动物崇拜的核心,体现了鲜卑人与动物之间紧密的依存关系。海尔堪玛法与鲜卑瑞兽都体现了对马的崇拜,是锡伯族动物崇拜的表现。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海尔堪玛法已经从动物神变成了人神,超越了最初的动物崇拜,虽然锡伯先民信仰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但依然保留了动物崇拜的信仰根基。
作为过去的一种生活印记,海尔堪的神龛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很难看到了。现有的田野调查显示,在锡伯族民众生活的地区过去供奉海尔堪的习俗非常普遍,如今基本消失不见,只留下关于海尔堪的传说。关于供奉海尔堪玛法的实物,有学者发现过两处,一处是岫岩县红旗营关姓家,一处是东沟县龙王庙镇沈姓家。目前尚不排除在其他地方也可能零星存在,并且锡伯族新建住宅中也已经开始出现了新的海尔堪神龛(后文将提及)。


二、《海尔堪大神传奇》
与传承人的家族记忆
在锡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何钧佑老人的长篇故事《海尔堪大神传奇》中海尔堪玛法是以人神同体的保护神形象出现的。《海尔堪大神传奇》由两部分组成,分别介绍了海尔堪的祖先答鲁红及海尔堪的生平和征战事迹,记录了锡伯族在氏族部落时期的生活、战争以及部落的兴衰,蕴含着锡伯族先民时代古老的生活习俗、生活状况和风土人情,为我们展现了一幅鲜活多姿的锡伯族早期社会历史图景。在《海尔堪大神传奇》中海尔堪是一位擅长驯马的英雄,他为鲜卑人养马、驯马、制造马具,做出了很大贡献,因此为后世传颂,最终成了锡伯族的马神和家庭保护神。那么,《海尔堪大神传奇》是怎样被记忆的呢?它以什么样的方式保存和传承着海尔堪这一男性祖先的文化记忆呢?它有怎样特殊的叙事方式呢?
何钧佑(1924-2012)出身于锡伯族官宦世家,祖父曾是清代盛京城的骁骑校。进入民国时期,何钧佑家族仅靠祖父留下的田地度日。何钧佑父亲三十多岁时,受到了当地官员的陷害,险些含冤入狱,一气之下,发誓要供儿子读书,将来有能力打倒贪官污吏。1940年,何钧佑十六岁时,父亲卖掉了家里的田地,送何钧佑去日本读书。在日本,何钧佑学习了四年哲学,受一位日本老师的影响,开始思考社会变革问题,并接触到社会主义理论。1944年,何钧佑从日本返回中国,为寻求社会理想,历尽千辛万苦经外蒙古偷渡去了苏联。在苏联,何钧佑做过八年的塔斯社新闻编辑,之后被当成中国间谍,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三年。1955年,何钧佑告别在苏联的妻儿,回到了中国,在哈尔滨商业系统工作,1959年,在“反右运动”中,何钧佑被错判入狱八年,出狱后在乌奴尔林业局工作。1978年,何钧佑退休后回到沈阳,定居在于洪区马三家子乡东甸子村,并开始根据记忆整理和记录祖辈传下来的锡伯族故事。
何钧佑的故事属于家族传承,从其曾祖父伊京阿起,就开始讲述这些故事,并传给子女。何钧佑的祖父、大爷(祖父长兄)家族中均保留了讲述故事的传统。何钧佑的直接传承人是其祖父,其故事主要来自祖父的传承,大爷也为何钧佑讲述过故事。其三姑也是重要的传承人,当祖父为何钧佑讲述故事时,何钧佑年岁尚小,很多故事内容不太理解,后来到了三姑讲述的时候,随着年龄的增大,对祖父讲述过的故事才豁然开朗。二大爷(祖父的二哥)何俊泰也曾为何钧佑讲过故事,何钧佑对其讲述风格有很高的评价。


何钧佑和他的手稿(隋丽2010年8月4日摄于何钧佑家)
综上,何钧佑故事属于典型的家族传承,故事讲述的活动在何氏家族、韩氏家族中均比较普遍。据何钧佑回忆:“我爷爷说最早他们老韩家祖先就在伯都讷(今吉林省扶余县),当过部落长。”清代,锡伯人未迁入盛京之前曾驻防在齐齐哈尔、伯都讷。康熙年间,齐齐哈尔、伯都讷两地锡伯人陆续迁入盛京。何氏家族和韩氏家族祖先即由伯都讷迁入。据何钧佑介绍,青堆子老韩家有过一个满文的折子,是黄布的,记录着他所讲述的锡伯族部落时代故事的梗概,他祖父见过。
何钧佑所讲述的故事大多是鲜卑部落时代的故事,如果假设这些故事最早在韩氏家族中流传,之后传至何氏家族,由于韩何两个家族祖上是姑爷亲,紧邻而居,关系密切,这个可能性是完全具备的。因此何钧佑故事的发现,并不突兀,有着现实的文化土壤和完整的传承谱系。
自幼被祖父抱在膝盖上,讲述古老的锡伯族的长篇故事,这给何钧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在求学以及成年以后,何钧佑非常留心锡伯族的民俗和历史文化,同时与锡伯族内的一些文化精英多有交流,也在不断丰富他的记忆。
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说:“谁也不会以一种质朴原始的眼光来看世界,他看世界时,总会受到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的剪裁编排。即使在哲学探索中,人们也未能超越这些陈规旧习,就是他的真假是非概念也会受到其特有的传统习俗的影响。”对于祖先英雄以及民族历史的记忆已经内化在了何钧佑的讲述活动以及叙事中,或者说讲述人尽可能还原了祖辈的讲述内容以及习俗观念。何钧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爷爷他们那会儿就是这么讲的,他们就是这么认为的。”
何钧佑讲述的《海尔堪大神传奇》与在东北锡伯族中广为流传的海尔堪传说除了情节有所增加,故事长度有延长之外,核心的主题差别并不太大。《海尔堪大神传奇》中讲到:
海尔堪为鲜卑人养马、驯马、制造马具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还让部落长奖赏那些保护自己家族和保护邻居的英雄。他经常帮助年老体弱的和鳏寡孤独的人,他认为鲜卑的家庭很重要。
海尔堪经常说:“鲜卑要是没了家庭,就会被其他民族吞并。”
……
海尔堪不仅能保护百姓家庭的安宁,还能指挥马。他回到家里,所有的马都来了,他叫头马往哪去,头马就带着马群往哪去。海尔堪自己的马从来不用带笼头和马嚼子。
海尔堪过世后,鲜卑的后代就说海尔堪是家庭的保护神,也有说他是六畜的神仙,还有说他是马神,但是大多数鲜卑人都还认为他是家庭的保护神。
海尔堪作为牲畜保护神保护牲畜、繁育马匹、制造工具、保护百姓安宁的英雄形象,在《海尔堪大神传奇》与东北锡伯族地区的传说相比较并没有太大差别。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海尔堪大神传奇》既是个体的记忆,又是集体的记忆。在民间的口头传统中海尔堪玛法的传说虽然已经经历了从口头到书面文本的传播形式的改变,但其核心元素并没有发生改变,体现了海尔堪信仰以及集体记忆的稳定性。
此外,正如江帆教授所指出的,何钧佑锡伯族长篇故事是锡伯族历史的“活化石”,蕴含着丰富的反映锡伯族族群历史与文化变迁的细节。《海尔堪大神传奇》是锡伯族早期社会生活的生动反映,也是在锡伯族中广泛流传的史诗故事,“故事中的许多人名、地名和故事情节,与新疆查布查尔地区锡伯族流传的此类故事中的人名、地名和故事情节大体相同,只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新疆锡伯族民间流传的这些故事,其完整与清晰程度已经远不如何钧佑家族保存下来的这些故事文本了。”因而,何钧佑讲述的《海尔堪大神传奇》具有珍贵的文化史意义,是不可多得的关于锡伯族早期社会的记忆文本。


三、民族文化建构与传承人的个体策略
作为文化记忆的形式之一,传统的再现既是记忆的内容,又是表现形式。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何钧佑对于锡伯族传统文化的再现、记忆与讲述,始终充满庄重感、敬畏感。他的文本讲述与其说是把锡伯族视为“回忆的民族”,不如说是把锡伯族视为“历史的民族”。出于强烈的民族身份认同意识,他用讲述祖先故事的方式建构了民族的历史记忆,“再现”了祖先的传统。“一旦文化连续性的重担完全落在具有奠基意义的文本之上,相关的人群必须想方设法让这个文本保持鲜活的状态,尽一切可能克服文本与现实之间不断加大的距离。”《海尔堪大神传奇》就属于这样一种具有奠基意义的文本,何钧佑通过个人化的叙事策略,通过对传统的阐释和“再现”,让文本适应当下的阅读语境。
他一丝不苟地讲述锡伯族传统生活习俗,并每每提及锡伯族过去的传统时,都用“那时候”“我们鲜卑人”“我们民族”等开头,并且异常详细地再现和重复着古代的生活习俗和场景,而这种对传统的重视,有时超越了故事情节本身。
《海尔堪大神传奇》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传统再现的故事文本。在《海尔堪大神传奇》中,何钧佑的故事向我们描绘了一位勇敢、智慧、无私奉献的保护神的形象。同时在讲述中,着重介绍了锡伯族鲜卑时代的历史场景与生活方式,形成了一个带有百科全书性的文本,对了解鲜卑时代锡伯先民的生活以及海尔堪大神产生的过程具有重要的价值。《海尔堪大神传奇》不仅讲述海尔堪的驯马功绩,而且详细地展现了锡伯族鲜卑时代生产生活的图景。这些生产生活图景向我们展示了海尔堪大神的生活背景及其被神化的过程。
开篇第一部分“海尔堪的祖先”开头就用了大量的语句来介绍鲜卑人的历史、生计方式、打猎的技术、弓箭发明的传说。
最早乌洛厚国的鲜卑人叫须卜人,也有汉人叫他们山戎。最早的时候他们不是靠打渔、打猎为生的,因为那时候的野猪、野牛、野羊什么的到处都是,特别是到了夏天的时候,洞口和大栅栏的外面有的是。所以鲜卑人不论男女老少都能抓猎物,也会抓鱼,因为到了秋天的时候,鱼多得往岸上直跳。后来人越来越多,野牛、野羊、野马什么的慢慢地就少了,这时候才开始打猎了。
最早的时候鲜卑族还没有弓箭。那时候打渔、打猎用的就是棒子、绳套,再不就是给老虎、黑瞎子挖陷阱,一般用套子的时候多。传说是有一次鲜卑祖先捕虎的时候,无意间打了三个虎套,虎套刮到别的树枝上了,就变成了一个弓的形状。他们找了一个大树的软枝,几个人把套子拉到地面,用一根一庹多长的粗木棍把套子挂上,然后搬一块大石头压上,木棒的上面再放一只死鸡什么的,只要老虎和熊用爪子一抓鸡,棒子一头的套就套在老虎的爪子或者脖子上,它越挣扎,树枝的劲越大,也就勒得越紧,到最后就能把老虎或是熊给勒死了。
关于养马、驯马的各种技术,在《海尔堪大神传奇》中记载得尤为详细:
最初答鲁红的祖先就找容易驯服的马练习骑。有的马你摩挲它,它不尥蹶子,这样的马养长了试验着就能骑。那时候还没有鞍子,也没有马缰绳,骑的时候不容易,经常掉下来摔伤。后来就用绳子拴在马的脖子上,人抓住了骑,就不容易掉下来了。再到后来,答鲁红的祖先发现要马往左往右,只要用手拍它的脖子,马就知道了。他就找了绳子把马拴上,这就有了嚼子和马缰绳。答鲁红的祖先找了一百匹马,让一百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学着骑马。开始的时候总往下掉,三个月过去了,就很少掉下来了。
……
古代时的马鞍子比现在的简单,都是搁桦树皮做的,最早的马鞍子就是搁桦树皮卷上个卷,把这两个卷绑在中间离开那个脊梁骨,搁肚子一勒就是马鞍子了。
《海尔堪大神传奇》展现了古代社会原始而古朴的生活方式,其中也包含了锡伯先民对自然、动物、器物、工具和技术的认知,而这一切恰恰是那个时代精神最完整的体现。正如黑格尔在评价《荷马史诗》时谈到其中一个著名的穿插时所指出的那样: “荷马却仍然在阿喀琉斯的盾牌上对整个大地和人类生活,例如婚礼、法庭审判、耕种、牛羊群、城市中的内战之类,用高明的艺术手腕作出令人惊赞的绘描。”史诗是以展示客观世界为目的的,在何钧佑的叙事中,这一特征也非常明显。在一次访谈中,他谈到了对于民族精神的理解。他说,“民族精神不是体现在英雄身上,而是体现在生活的点滴之中。”在何钧佑身上,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敬畏与坚守。他对传统的理解不同于普通的族群成员,他是更坚定的传统的维护者、守卫者,是锡伯族的文化精英。
在《海尔堪大神传奇》中,何钧佑讲述海尔堪有过两次显灵,这构成了对海尔堪神化的一种重要方式。
鲜卑人传说海尔堪有两次显灵。头一次是匈奴的冒顿三万骑兵攻打乌桓的时候,眼看着就要打胜了,乌桓抗击他们。他们死了一万多骑兵,冒顿看他们死了这么多的人就生气了,就让剩下的一万多人去抢乌恒的百姓。
打仗弄得乌恒的百姓跑到南边一部分,北边一部分,还剩下一部分,也是冒顿要去抢的地方。
这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冒顿率领这些骑兵疾驰向东边的几个还没来得及撤走的部落。这些部落里就只剩下些老人、孩子和妇女。眼看着要遭抢了,一大群的妇女就大声地喊:“海尔堪大神,救救我们吧!海尔堪大神,救救我们吧!”
……
海尔堪的谋士大雁神尼雅帮助海尔堪成就大业,也被奉为神灵:
鲜卑人为了纪念尼雅为鲜卑的太平做出的贡献,从此以后,猎人打猎时从来不伤害大雁。从那以后,鲜卑人年年保护大雁在精奇里和东那水繁殖,鲜卑人更没有一人在大雁南北迁徙时射杀它们。
海尔堪不仅是英雄大神,也成为鲜卑人的保护神,锡伯族人的家庭保护神。在原始社会的晚期,随着阶级分化的出现,人的社会身份逐渐等级化,首领崇拜和英雄崇拜的观念凸显。孟慧英在《中国原始信仰研究》中,也同样得出这样的结论:“父系血缘关系的确定和神化是父系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的重要基础,对这个基础的强化和神化是出自现实生活的必然要求。男性祖先崇拜是父系氏族社会的典型宗教形式,它集中表现在对亡故的氏族首领、英雄和氏族萨满的祭祀上面。”在《海尔堪大神传奇》中,海尔堪大神完成了从英雄到氏族保护神、家庭保护神的神化历程。
族群的记忆方式是多样的,其记忆文本总是受到来自“现在的”以及外界的各种因素的影响,“文化记忆是复杂的、多样的,就像迷宫一样,包含大量的纽带记忆,以及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差异性的群体身份,正是在这些张力和矛盾中,文化记忆获得了活力。”《海尔堪大神传奇》作为一个文化记忆文本,是记忆的“存储器”,包含着族群对身份的认同和归属意识,也包含着对“传统”的坚守与追求,同时也体现了传承人的记忆选择与建构。每一位民间精英型的传承人都是一部民族文化和民间知识的宝典,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他们不仅主动地自觉地关注本民族文化,同时对本民族文化充满深厚情感。这种基于强烈民族意识的文化自觉性是民族文化得以传承的内在驱动力。对于每一位个体的传承人而言,这似乎又是一种文化的本能,传承的使命与责任推动着古老文化和民族传统一代又一代地延续、承接。而传承的行为本身,都是他们对历史的充满深情的回望与凝视。民间叙事文本承载着传承人以及一个民族的情感记忆、历史记忆和生活记忆。
通过对《海尔堪大神传奇》的研究,可以发现锡伯族民族精神体现在对祖先的记忆之中,体现在古老的信仰机制之中,也体现在具体而庞杂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何钧佑所讲述的《海尔堪大神传奇》体现了锡伯族口头传统的遗留,同时,从讲述行为和文本内容可以看到民族文化精英的立场和视角,他讲述的故事不仅仅是锡伯族历史记忆的一部分,他以及他的讲述也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同样具有文化史的价值,这可能也是何钧佑及其故事研究的另外一个可探索的角度。同时,在《海尔堪大神传奇》的文本和讲述中,也为我们提供了族群文化记忆的一个典型个案。


四、文化记忆的社会认同与承续
当文化记忆以显性的方式存在时,它会通过纪念物、博物馆、书写等媒介形式发挥凝聚力与认同的功能,从而实现文化记忆的连续性。何钧佑讲述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这样一个记忆的储存器和发动机。“‘被回忆的过去’并不等同于我们称之为‘历史’的、关于过去的冷冰冰的知识。被回忆的过去永远掺杂着对身份认同的设计,对当下的阐释,以及对有效性的诉求。因此关于回忆的问题也就深入到了政治动因和国家身份认同建立的核心。”文化记忆在建构的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能量和认同性。
文化认同的一个表现为,何钧佑讲述的故事被作为锡伯族民族文化遗产受到珍视和重视。作为一位锡伯族民族精英,何钧佑在退休之后,一直自觉地在整理家族中流传下来的锡伯族长篇故事,由于信息闭塞,他当时并不知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回事。一直到2007年6月,在沈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中,何钧佑被发现,并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何钧佑所讲述的锡伯族长篇故事从民间口传文本,变成了“非遗文本”,从2008年开始,地方文化馆和辽宁大学师生对何钧佑故事进行采录整理,并陆续出版了多部《何钧佑锡伯族长篇故事》。“何钧佑锡伯族长篇故事”先后入选市、省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10年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2012年12月何钧佑病故,几乎与此同时,文化部的官方网站上正在进行何钧佑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公示。何钧佑虽然离世了,但他传承的锡伯族文化记忆却刻写在不同的媒介和空间之中,在沈阳市锡伯家庙和沈阳锡伯族博物馆中,何钧佑的大幅照片和六卷著作,整齐地摆放在陈列展柜之中。在锡伯族西迁纪念活动上,何钧佑以及他的故事也成为锡伯族文化的一个标识。
文化认同的另一个表现是何钧佑所“创作”的喜利妈妈和海尔堪大神画像被锡伯族人接受和认同,并成为锡伯族人家供奉的祖先神像。
在文字出现之前,人类处于“以图言说”的时代,他们以图像符号表达对世界的认知和自己的宗教信仰,对于祖先的记忆和崇拜也往往通过图像符号来表示,藉由图像建立了对祖先的记忆系统。这个祖先的记忆系统除了图像符号外,在史诗、神话、传说、故事等口头文学作品中,也是一种神圣的存在。正如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所指出的那样,文化记忆借助的媒介很多,比如文字、图画、塑像、纪念物、节日等等。在文化记忆中,锡伯族海尔堪形象从“无形的”精神形象变成“有形的”物质形象。
2017年,笔者在沈阳市沈北新区喜利妈妈信仰习俗代表性传承人吴吉山家里,看到在新建住房的西墙外,有一个小洞(约一尺半深,一尺高,半尺宽),用砖砌成,里面有一块木牌位,上写“海尔堪玛法之位”,他家里供奉着喜利妈妈和海尔堪大神的画像,画像即是何钧佑老人生前所作画像,2018年,吴吉山家西墙洞里的木牌位被泥塑的海尔堪玛法坐像代替。如图:


何钧佑所画的海尔堪玛法画像和喜利妈妈画像
(丁林野2019年2月摄于吴吉山家)

神龛里的海尔堪玛法坐像
(丁林野2019年2月摄于吴吉山家)
经过时间的过滤,海尔堪玛法的祖先记忆已经从抽象的图像符号、实物符号,具象为祖先画像和塑像,成为被供奉的“圣像”。
何钧佑所画的喜利妈妈与海尔堪玛法从画风来讲,明显受到俄罗斯东正教的绘画风格影响,巴洛克风格褶皱的帘子以及人物构图等与西方宗教风格绘画有相似之处。这种画风与何钧佑本人的人生经历有关,但不论怎样,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需要这样的画像符号,似乎也并不在意画得是否像。画像符号的海尔堪玛法体现了锡伯族祖先信仰的历史变迁与现代的记忆方式,以及对祖先及传统的“想象与发明”。
海尔堪玛法的信仰仪式也是对海尔堪祖先记忆的强化,但是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在很多锡伯族聚居的地方,海尔堪玛法的信仰仪式基本中断,在房屋的建筑中,海尔堪的神龛之位基本已不复存在。近些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兴起,以及锡伯族民族文化的复兴,出现了海尔堪玛法的祖先的神像以及祭祀活动。以沈阳市沈北新区吴吉山老人为例,他家现在的海尔堪玛法神像和神龛,也是在政府资助下新建房屋中才得以恢复。在吴吉山家每年春节前祭祀喜利妈妈的仪式中,海尔堪玛法作为男性祖先同样也得到祭祀。
祭祀仪式在文化记忆的传承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这些仪式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纯粹的程序,即形式不是简单地为行为减负,而是在记号功能意义上,在某种程度上将一种意义内容长久地稳定化,而这一意义内容不是为服务于行为的首要目的而产生的。”“仪式通过定义超越日常生活和日常行为目的的视野,指向一个更高级、更普遍、更高一级的领域,这个领域以象征的形式出现。”海尔堪玛法的祭祀仪式从中断的传统,变成“恢复”的传统,体现了在现代语境之下民族文化记忆的建构过程及努力。
纵观何钧佑的《海尔堪大神传奇》的讲述,可以发现文化记忆中的“文本”除了图像、口头和书面等显在的“文本”之外,在记忆的深层还有一个“精神文本”,“在阿斯曼看来好比是无形的宗教,在一些别的民族学家的语言中,它就像是有一颗‘集体的灵魂’,在背后掌控着社会成员的思想言行。”这个内在的、隐性的文本是核心性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它体现了文化的内涵、价值观念以及集体的灵魂。扬·阿斯曼把具有奠基意义的故事称为神话,“神话是这样一种历史,人们讲述它,是为了让自己在面对自己和世界时可以找到方向;神话又是关于更高级秩序的真理,它不光是绝对正确的,还可以提出规范性要求并拥有定型性力量。”这种神圣性的记忆文本或者奠基性的故事是文化记忆中的深层文本,关乎信仰、仪式和“高级秩序的真理”,是文化记忆得以传续的内在动力机制。在《海尔堪大神传奇》中这种文本就是海尔堪的信仰传统。《海尔堪大神传奇》中经过记忆选择和整理的文本细节对于解读锡伯族的海尔堪信仰传统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也使我们得以窥见文化记忆建构的过程以及动力系统的面貌。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文化遗产》2020年第4期
图片来源:原文&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