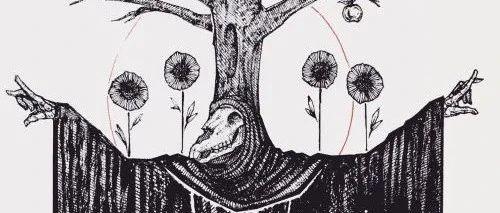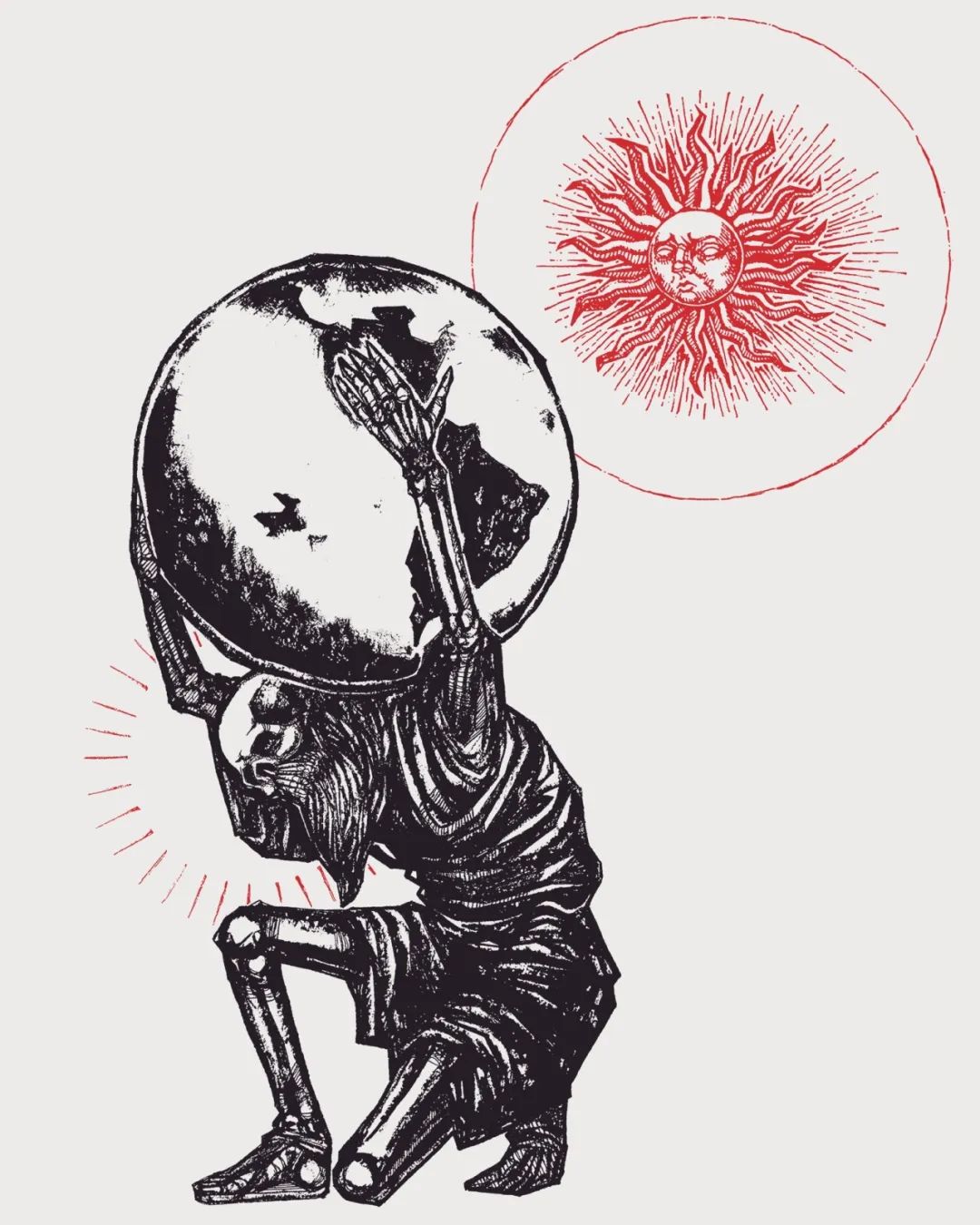摘要: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社会中兴起了一股新萨满教信仰和实践的热潮。这种新型的萨满教与传统的西伯利亚或北美的萨满教不同,是西方社会文化的产物。它的出现体现了一部分西方人对现代性的反思以及他们的生命体验与西方主流社会范式的紧张关系。本文主要对新萨满教的研究状况做一回顾和简要评价。
▼

“20 世纪 70年代以美国为中心在西方社会中兴起了一股新萨满教信仰和实践的热潮。这种新型的萨满教与传统的西伯利亚或北美的萨满教不同,是西方社会文化的产儿。”1950年代,美国进入了所谓的“丰裕社会”,“丰裕社会”在迅速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快速变革了人们的价值观念: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这两项支持着美国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在此时分崩离析,时装、摄影、广告、电视和旅行等将人们的欲望急速地膨胀起来,注重游玩、娱乐、炫耀式消费成为中产阶级生活中的重要内容。社会价值观迅速倒向享乐主义、消费主义。但是,传统规范性价值的丧失意味着“神圣的帷幕”庇护的撤离,在没有建立新的价值意义观之前人们的心灵必然会处于一种 “漂泊无家”、生存性空虚的危机状态 。

另一方面,战后美国国内冷战思维下的核武器、麦卡锡主义与对越作战使民众笼罩在一种白色恐怖和死亡阴影之中。水门事件又使民众对国家政治失去信心。原来作为统一美国民众精神的“国民宗教”意识在此时受到严重打击。加上美国国内少数族群的民权运动( 如美国墨西哥人的“奇卡诺运动”、印第安人的“泛印第安运动”、黑人民权运动) 在此时风起云涌。在此种社会情景下,引发了1960年代中产阶级白人青年为主的反正统文化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萨满教与致幻品被看做西方文化的解毒剂,人们试图在传统仪式萨满所经历的“意识改变”状态中寻找“真实”、“纯净”。这为新萨满教的“侵入”准备了条件。
进入1970年代,随着美国政府的调控,美国反正统文化运动逐渐消退,致幻品也被列为禁品,但是人们的精神性需求还存在。而此时,新时代运动( New Age Movement) 兴起。新时代运动吸收了东方与西方许多古老的精神与宗教传统,并将它们同现代科学的观念(特别是心理学)融合在一起。而此时,人类学家迈克·哈纳、卡斯塔尼达等人分别建立核心萨满教修行工作室、萨满教“无极”工作室,这标志着西方新萨满的成立。具体来讲,西方新萨满教就是在击鼓声、电子音乐、精神性药物或其他手段的辅助下,使实践者迅速地改变人的普通意识状态从而快速进入到所谓的“萨满意识状态”即与现实世界分离的幻觉状态,使普通人能够体验只有传统萨满教中作为文化仪式专家萨满才经历的“入迷”体验。因为新萨满教很好地契合了新时代运动精神,其过程带有某种魔幻神秘色彩,而身处科层制和理性体制下的常人将其视为脱去窠臼、放纵非理性情感、发现内在真实自我的一种途径,加之一部分人视其实践为一种身心治疗法,吸引了很多人的加入。

目前,新萨满教在北美、欧洲、亚洲、南美洲等都有其机构和大量的实践者。此外,新萨满教的还在不断造势,通过定期发行刊物、出版修炼书籍、建立宣传网站、利用电视媒体等多种手段扩大其影响。总之,它已经成为宗教学、人类学等研究领域不得不关注的一个主题。
西方学者对西方当代社会中的新萨满教的研究是近 20 年来的事情。从已出版的著作、论文来看,数量不多,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出现在当代西方社会中这种萨满教如何来命名,西方学者至今没有统一的叫法。迈克·哈纳( Michael Harner) 将自己发明的通过击鼓的方式进入所谓的萨满意识状态的这种实践称为核心萨满教( core shamanism) 。哈纳自己的原话是“我曾在亚马孙河流域上游的两个印第安部落学习萨满教,同时为了发现全世界范围内萨满教跨文化的原则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所有这些修习萨满术的基本法则我都将它称为核心萨满教”。其他的西方学者也有将这种形式的萨满实践方式称为哈纳式萨满教( Harnerism) 或者实践性的萨满人类学,将哈纳称为萨满人类学家( 除了哈纳之外,这一称谓还指著有《巫师唐望的教诲》等书的作者卡斯塔尼达) 。1995年人类学家维特斯基( Piers Vitebsky) 在他的《萨满》一书首次了neo-shamanism 一词指称包括核心萨满教在内的西方式萨满教,并且指出这种形式的萨满教是欧美60年代反主流文化、环保、新时代运动和西方人的心灵自我完善需要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他还指出“新的萨满教徒也许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有关萨满教的理想形象,然后又判定传统社会没有按这种形象行事”。从此,新萨满教一词被大多数学者使用,如《城市景观中的萨满展演: 当代瑞典的新萨满教》《萨满教与新萨满教: 入迷、考古与当代异教》《入迷和北欧异教运动中的新萨满教》等。“现代西方社会的萨满教( Modern Western Shamanism) ”或者“现代萨满教”是另一种较常见的叫法,可见《重新着魅的实质: 现代西方萨满教与19世纪的想象》《名字的涵义: 新萨满教、核心萨满教、城市萨满教、现代萨满教或别的名称》 等。除此之外,有的学者还用都市萨满教( urban shamanism) 、白人萨满教( white shamanism) 等词来指称西方非传统的萨满现象。


许多学者在西方社会中的这种萨满教的名实这一问题上存在争议。有些学者认为它就是一种新形式的萨满教并对它的出现持肯定态度。如《重新发现萨满文化遗产》一书中指出:无论如何, 核心萨满教是对萨满教的浓缩,它并不是也并不打算成为传统的图瓦的或西北海岸或任何其他社会的萨满教。这样的结果是将来被实践的萨满教可能会是核心萨满教方法与土著传统中的碎片的合成品。我们可能由此会看到萨满教传统的进化,其显然更像是被向全球散布的综合体……现代萨满教精神生活特别是核心萨满教,有些时候是对那些需要它并且正在试图重新获得正在消失的萨满教传统的人们的回复。结果可能是一个重新组装的萨满教,但也可能是早年的传统萨满教。重新组装和发明的传统也能从西方和本土的普遍主义发明者那里进入土著社会,在那里他们可能被用于政治和精神的双重的目的。简·思文凯( Jan Svanberg) 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指出今天所谓的新萨满教实际上是近40年来人类学研究方法、方式发生变化的产物: 一方面,新萨满教是对传统萨满教的重新评价; 另一方面,它促进了学术研究成果的推广。《萨满教: 西伯利亚的灵性与西方的想象》的作者称“西伯利亚本土的萨满教为哈纳奠基的新萨满教在欧洲、美国建立的发展提供了源泉,但是新萨满教绝不是传统萨满教的堕落而是它的变形” 。沃利斯在《萨满教与新萨满教: 入迷、考古与当代异教》一书中通过文献和考古遗址的考察,试图将西方现代萨满教和英国本土的史前萨满教衔接起来。他深刻地指出如果能辨析萨满教和新萨满教形式的异同,那样就不用心存偏见地臆断哪个萨满教是真的、哪个是新的这样的问题。同时,他还提醒众多研究者“将所有的新萨满教看做是一模一样、毫无差别的,那不仅仅是误导更是无知。”


当然也有学者对西方新出现的这种萨满教持否定批判态度,认为它就是一种退化的、资本化的、混杂的宗教、快餐宗教或者认为它是假的萨满教: 以萨满教之名,其实质是“兜售土著的灵性” 的商业性活动,从事这些活动的人被称为塑料巫医( Plastic medicine men) 。这些人既包括作家卡斯塔尼达、马克( Jay Marks) 、希尔( Ruth Beebe Hill) 等人,也包括以萨满工作室名义赚取钱财的人和售卖土著仪式获得暴利的人。沃德·邱吉尔( Ward Churchill) 直接指出西方新型萨满教是近20年来美国兴起的一种新产业,“可以称它为美国印第安人的灵性产业……西方大众接受了盗版的印第安灵性主义,正宗的却遭到了拒绝。”基欧(Alice Beck Kehoe) 称:“出售萨满的旅行是件可赚上百万英镑的大生意。向迈克·哈纳这样的销售商还声称自己是为了帮助修习者实现与神灵的沟通、治疗疾病、探悉宇宙知识,但是很多其他卖方却完全是以赚钱为目的。”利萨(Lisa Aldred) 通过分析指出新萨满教的顾客多是婴儿潮时代出生、富裕的、反正统文化的白人,目的是逃避正统文化并表达不满、促进自我心灵完善。


这种新的萨满教为什么会在西方拥有很大的市场,这是很多学者思考的问题。戈琳娜·林德威斯特( Galina Lindquist) 通过对瑞典的田野调查指出原因有以下几个: 一是萨满教宇宙观念即万物之间相互联系的、彼此平等; 二是新萨满教是民主的灵性形式、个人可以直接体验接触灵界; 三是它为想拥有神秘力量的个人提供了自我实现的方式; 四是它可以对西方人现在关注的生存、和平和环境等问题提供灵性的答案; 同时它也是瑞典传统灵性主义复苏、瑞典人文化寻根的结果。汉妮克· 明克坚( Hanneke Minkjan) 通过对荷兰新萨满教信仰者的调查指出: 在荷兰社会中,人们面临着心理和生命存在等许多问题; 新萨满教作为一种灵性形式,人们试图借助它来解答存在性的恐惧( existential fears) 和心灵本身等一些问题。伯克特( Tim Burkett) 对在哈纳工作室学习核心萨满教的人员进行访谈,试图回答核心萨满教如何作用于他们。调查结果与汉妮克·明克坚对荷兰人的调查相似: 修习者认为借用萨满旅行比只凭想象更容易解决问题,萨满式灵性体验过程中的逻辑是否合理并不重要,他们看中的是这一点: 它对他们的生活赋予了意义。

一些学者则认为这种新萨满教吸引西方人的原因在于它本身就是西方人自己的想象和建构的结果,是隐喻性的、“被发明”的信仰和实践,代表作可见《原始之美: 萨满教和西方的想象》《萨满教: 西伯利亚的灵性与西方的想象》。
罗纳德·赫顿在《萨满教: 西伯利亚的灵性与西方的想象》一书开篇写到:“七十年代以来,‘萨满教’一词已经变成西方人类学家、宗教研究者和反正统文化团体关注的热点。”在这本书中赫顿试图回答西方学者为什么和怎样建构萨满教的。书中分为三章,分别为: 为什么我们认为我们了解萨满教、我们到底知道关于萨满教的多少知识、萨满教世界中的西伯利亚。在最后部分,作者指出,萨满教的焦点已经从广袤、神秘的西伯利亚本土转移到美国本土,但是西伯利亚的萨满教仍然为西方新萨满教提供着灵感源泉。赫顿最终的答案是西方人对萨满教的认识是建立在自我想象和不断建构的基础上,所谓的新萨满教不过是美国人对萨满教想象和建构的继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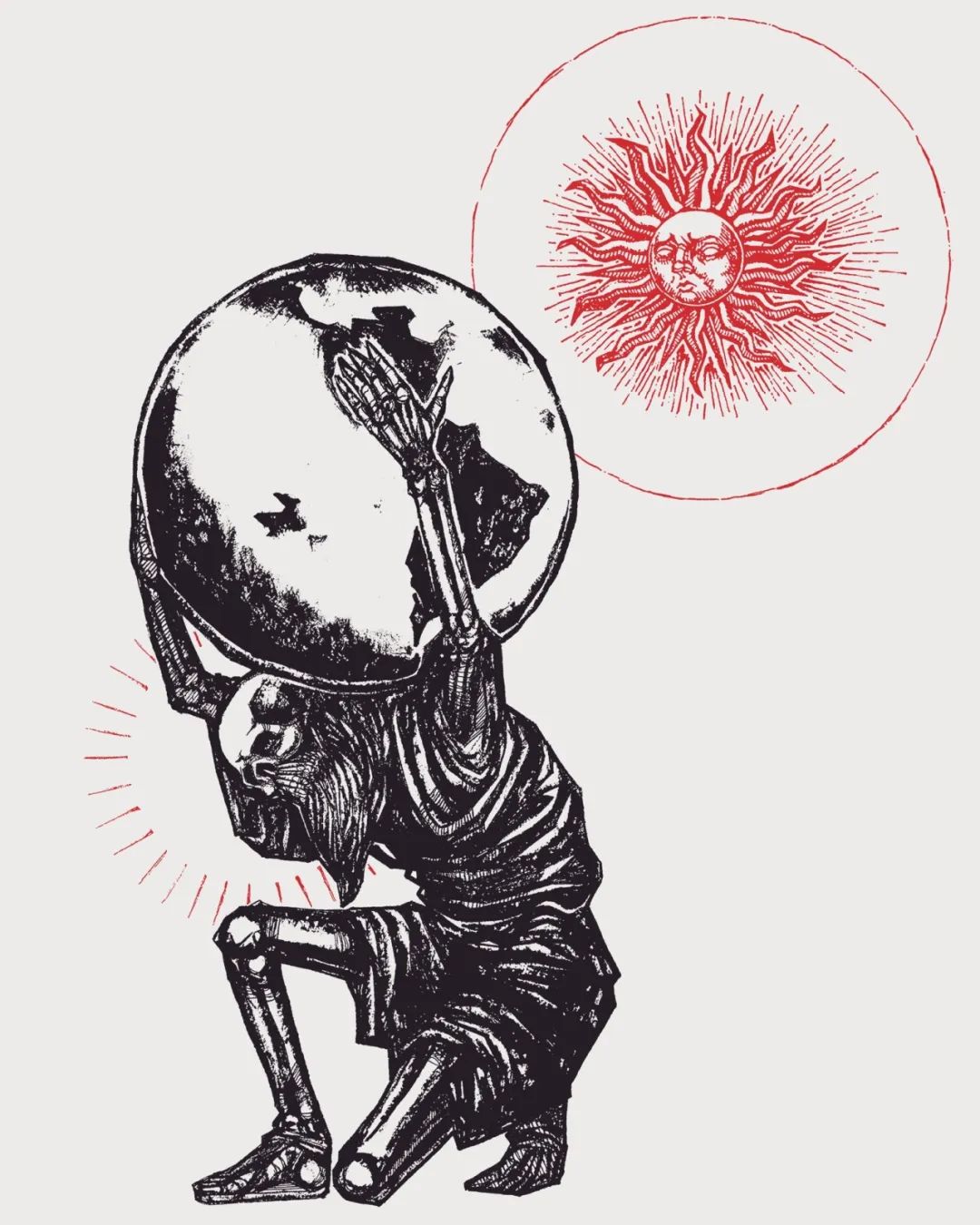
赫顿曾经高度的赞美一本书说:“这本书是目前为止最好的研究现代萨满教的学术著作。作者之所以能够写出这么优秀的书,是因为他能够很好地理解现代萨满教之前的历史。”这本书就是《原始之美: 萨满教和西方的想象》。这本书的作者安德烈通过对18世纪以来西方萨满教认识史的考察,试图回答萨满教是如何进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又是如何获得1960年代来西方的自然主义者和异教徒团体(nature and pagan communities) 的青睐以及他们怎样利用它来满足自己对精神性的探索和反现代性的情愫。作者以时间为顺序,关注了一些重要人物和他们的时代背景 ( 这些人包括启蒙主义作家、浪漫主义作家、俄国“流亡”民族志记录者到人类学家博厄斯、心理学家弗洛依德,再到伊利亚德、卡斯塔尼达等作家、学者以及西方众多追寻灵性体验的大众) ,分析了西方社会对萨满教认识的转变(从魔鬼异教、骗子把戏、非宗教的巫术到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制度化的原始人的疯人院再到古老的入迷技术和充满智慧的身心治疗术) 。他指出,西方人对萨满(教)的理解是与西方社会自身的社会文化和思想潮流有着密切的关系,即西方人对萨满教的认识史就是西方人对萨满教想象的历史和根据想象建构的过程。具体到新萨满教,作者认为它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传统文化复兴、生态运动、反正统文化运动、女性运动等多种思潮和心理学、人类学等多学科共同建构的结果。同时,作者还指出新萨满教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它反映了那些关心社会问题、全球化问题、生态问题等多种问题的人们的声音; 这些人试图将此类问题归因于人类精神世界的不健全,希望借助萨满教的修习达到个人的自我完善而不是通过改变社会和他人来解决它们。


宗教与心理健康、宗教在治疗中的作用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宗教学、社会学、医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十分关注的一个主题。从目前积累的大多数研究结果看,多半研究者认为信仰宗教有利于治疗和信仰者的身心健康。就像墨菲( N.Z.Murphy) 指出的那样: 宗教体验之所以优于一般体验,是因为超自然力量的参与和宗教文化的熏陶,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理并给参与者带来愉悦的享受。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 宗教能够促使信仰者产生一种类似于吗啡效果的物质,在这种物质的效应下人们会感到愉悦、身心放松、疼痛感也会减轻,从而开启信仰者的自我治疗机制。
就新萨满教与治疗的研究而言,有几篇文章值得关注: 《对成瘾的补充治疗: 利用鼓声走出毒品》《灵魂的治疗: 新萨满教的索魂体验》《将灵魂带回自我: 新萨满教中的索魂术》。在第一篇文章中,作者通过观察、访谈药物滥用者组成的哈纳式萨满击鼓小组和咨询师,得出如下结论: 击鼓进入萨满状态可以使戒毒者放松心情、产生愉悦的感受、释放情感创伤和自我进行重新整合。同时,击鼓也可以减缓他们以自我为中心、自我隔离和疏远他人的处世态度。最后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 当常规的戒毒模式不起作用时和毒瘾反复发作时,击鼓小组可以作为一种治疗药物成瘾的特殊的辅助手段。在《灵魂的治疗: 新萨满教的索魂体验》一文中作者研究了新萨满教修习者以治疗为目的的索魂体验。调查结果表明新萨满教的索魂治疗术对病人病情的改变是有效和可测的。《将灵魂带回自我: 新萨满教中的索魂术》一文的作者林德威斯特关注的是西方新萨满教的索魂仪式,通过对它的田野调查和具体分析提出如下的观点: 索魂术为治疗者设置正式的语境,在这一语境中他们被赋予新的意识和自我表述方式( new narratives of the self) ; 通过将个体自我、凡俗、神圣物连接起来的方式,索魂仪式促使病人心理发生变化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


国内学者对西方当代社会中的新萨满教的关注是近10年的事情。孟慧英是最早关注西方新萨满教的国内学者。她在《尘封的偶像——萨满教观念研究》等著作中,围绕新萨满教的核心人物之一迈克·哈纳及其研究、实践对西方的新萨满教做了介绍,并且指出新萨满教研究的重要性: “萨满神媒职责与治病技术在新萨满教中的复活,使人不能不将研究的视野推向新领域……新萨满教促使人类学者重新面对萨满的实践和他们的作用。”在《试论西方萨满教研究的变 迁》一文中,她指出萨满教在西方学术界经历了魔鬼化、骗子化、精神病理学化、理想化等认识变迁,其中新萨满教处于西方萨满教理想化阶段。在这一阶段,西方人并非想要复原和实践纯粹的传统萨满教,而是要在其中提取最普遍、最吸引人的东西。“他们把萨满教转化为一种完全的个人实践,去分享这种古代智慧。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一种萨满教传统的进化。”除此之外,孟慧英等编辑的《萨满文化研究信息与情报选辑》等书中也收集有与西方新萨满教相关信息。郭淑云是最近几年来开始关注西方的新萨满教的学者。她围绕“出神”“脱魂”等萨满现象,借鉴西方新萨满教研究的成果来研究中国北方传统的萨满教; 同时在她编、译的《域外萨满学文集》《意识变异形态与萨满教》等著作中也有与新萨满教相关信息。另外,金泽、何其敏翻译的《宗教人类学导论》一书中简短地介绍了西方的新萨满教,称其为“工业化西方的萨满教”,并指出卡斯塔尼达式和哈纳式西方新萨满教在西方赢得众多信众的原因在于: 将包括“新时代”思想、精神分析学的实践、寻根和探寻古代智慧、追寻异国浪漫情调在内的大众文化口味成功地结合在一起。除上述学者之外,叶舒宪还从文学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对西方的新萨满教进行了解读。虽然这些论著中涉及的新萨满教内容不多,但是他们却是国内研究西方当代社会中的新萨满教的先行者。


由于新萨满教发生在西方社会,大多数西方本土学者都目睹了它的发生、发展,自然就具有了 “在场”的优势,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远远多于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但是,他们中一部分人身兼研究者、倡导者、实践者的多重身份,所以研究中难免有主观和吹捧之嫌; 而另一部分人则鄙视其为杂教、异教,不能中立地评价它。作为一个新出现的事物,新萨满教既体现1960年代后新兴宗教的特征,又是西方人反思资本主义文化、转向“他者”学习的典型,同时还是当代新时代运动中的一个典型个案。自产生后,它的形式还在不断变化,如与生态保护主义思想结合下的生态萨满教( Ecoshamanism) 、与电子流行音乐结合下的高科技萨满教( technoshamanism) 。这些都非常值得人类学、宗教学、文化史等领域的学者去认真地进行研究。
原文刊载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图文来源:微公号“ 迦南神秘学”2020-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