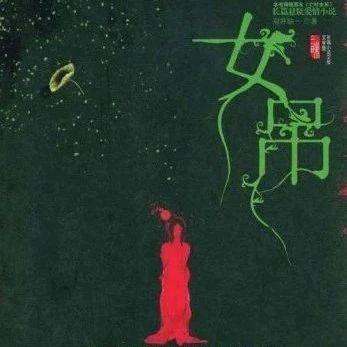
内容提要
《女吊》并非“朝花夕拾”风格之回归,而是特异形态的“故事新编”。女吊“复仇”精神实系鲁迅之“发明”,但其所谓“复仇”不具现实行动可能,仅存留于精神层面,这也是《女吊》叙事困境之所在。鲁迅将与复仇精神不相谐的女吊形象纳入复仇书写序列,很可能与他在陶元庆画作《大红袍》中得到的女吊印象有关,陶氏稍后为《苦闷的象征》设计的封面画几可目为《大红袍》之升华,鲁迅之复仇观亦深蕴此苦闷象征的个人化隐曲。鲁迅假托“民间”以祛魅知识权力司掌者的克里斯马光环,仅以“民间”为方法而非立场,他实际吁求的是超越一般精英知识分子,能启人“心声”与“内曜”的“一二士”。
关键词
鲁迅;女吊;复仇;民间
作为鲁迅生命末期的创作,《女吊》以其特殊的写作时间和“朝花夕拾”风格的回归在鲁迅作品序列中引人注目。自作品问世以来,“民间”和“复仇”始终是解读《女吊》题旨的两个关键词,作者对绍兴目连戏中女吊复仇精神的称颂,使人们再次辨认出那些“构成鲁迅生命底蕴的童年故乡记忆和民间记忆”,而鲁迅精神结构的渊源之一,正是“那个在乡村的节日舞台上、在民间的传说和故事里的明艳的‘鬼’世界”。

无论从地域文化着眼还是借助“狂欢化”理论来解读《女吊》,其论说均基于同一认识,即鲁迅笔下之女吊乃以绍兴目连戏中之女吊为蓝本,基于此,《女吊》的回忆性散文属性应该毋庸置疑。然而,如果对此前民间戏曲中的女吊形象进行一番“检验”,《女吊》的性质则变得面目可疑:在鲁迅创作《女吊》以前,女吊并未以复仇者形象示人。也就是说,“复仇”主题实系鲁迅之“发明”,而非植根于绍兴民间戏曲舞台。那么,《女吊》究竟是人们所说的“朝花夕拾”,还是另一种风貌的“故事新编”?真实存在于民间戏曲中的女吊应为何种面貌?鲁迅“发明”的复仇精神,其具体指涉是什么?作者笔下的女吊形象是否另有灵感来源?其对民间资源的调用与改造又是在何种意义上进行的?
关于女吊故事本末,《鲁迅全集》注释如下:
杨家女:应为良家女。据目连戏的故事说:她幼年时父母双亡,婶母将她领给杨家做童养媳,后又被婆婆卖入妓院,终于自缢身死。在目连戏中,她的唱词是:“奴奴本是良家女,将奴卖入勾栏里;生前受不过王婆气, 将奴逼死勾栏里。阿呀,苦呀,天哪!将奴逼死勾栏里。”
这则注释最早见于1958年《全集》,并在1981年和2005年版《全集》中延续使用,以解释“奴奴本是杨家女”这句唱词。然而考察各地目连戏抄本,女吊生前或是做媳妇,受公婆打骂,负气悬梁;或是双亲亡故,卖入行院,最终自缢身死;并不见两次被卖,先做童养媳后入妓院的说法。虽然民间目连戏版本众多,留下文字的只是凤毛麟角,不过从注释所引四句唱词来看,这则注释的编写却并非依据某个秘而不传的孤本,而只是绍兴目连戏的一种常见版本。在现存各种目连戏抄本中,清代绍兴敬义堂杨杏芳抄本(今亦称《绍兴旧抄救母记》)中的唱词与此最为近似:“奴奴本是良家女,被人卖在勾栏里。生前受不过亡八气,将身缢死高梁里。嗳吓苦吓天那!将身缢死高梁里。”此外,绍兴地区其他版本,诸如新昌县胡卜村清抄本《目连救母记》、新昌县前良村清咸丰庚申年抄本《目连戏》、绍兴民国九年斋堂本《救母记》等均与此大同小异,只有个别字句存在差异。1956 年,前良目连班受邀赴上海参加“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演出”,赵景深将艺人携带的敬义堂杨杏芳抄本购入囊中,因此《旧抄救母记》成为1958年《全集》出版以前,众多绍兴民间目连戏抄本中唯一一个由知识分子收藏的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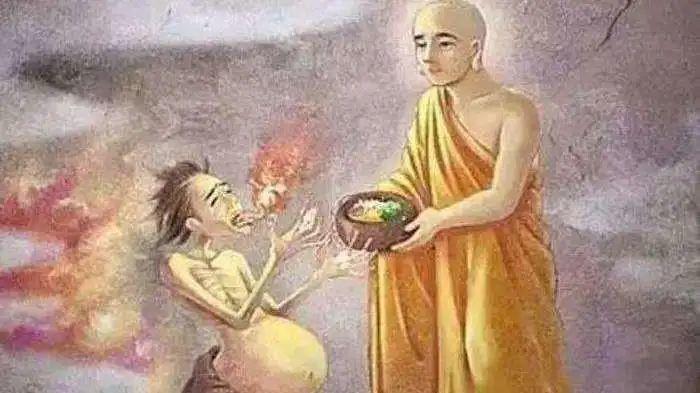
《旧抄救母记》是否与《女吊》注释有直接关系尚无从查证,但注释者显然参照了某个妓女故事版本。由于其与鲁迅提供的童养媳一说无法匹配,于是采取了将两种说法拼合的处理方法。实际上,童养媳版本在民间演剧中的确存在,1942年柯灵在文章里回忆他年少看戏时听到的几句唱词:“奴奴本是良家女,从小做一个养媳妇,公婆终日打骂奴,悬梁自尽命呜呼。”不过其中“良家女”显然与童养媳无关,只能源于妓女故事系统。一种可能是柯灵在1942年的记忆已被鲁迅《女吊》“改写”过,另一种可能是童养媳版故事晚于妓女版故事系统,而其唱词直接在后者的基础上重新加工。
不过就形象设定而言,童养媳故事显然派生于更早的媳妇故事系统。稍早于鲁迅写作《女吊》,朱今曾于1934年发表《我乡的目连戏》一文,介绍江苏溧阳一带目连戏的形态,尤其详细记录了《赶吊》一折的演出形式。这一部分故事主要讲述东方亮妻子独自在家,因行善被骗去金钗,丈夫在外偶见金钗,遂疑妻子不贞,归家诟谇,妻子无奈衔冤悬梁。一众鬼魂闻讯来讨替身,其中尤以吊鬼形象恐怖,正在她准备“讨替”之际,王灵官出场驱赶吊鬼东方亮之妻因此得救。这一故事模式广泛存在于各地目连戏中,具体细节则因地而异,并无定章。但一个比较稳定的细节是吊死鬼的死因:因与公婆不睦而悬梁。直到死后数十年她仍未能寻得替身,因此后悔当初气量狭小,不能忍一时“闲气”。在这一故事结构中,真正的主人公是投缳的妇人,而吊死鬼在剧中只须用一两句话概述身世并自悔前番。在这里吊死鬼几乎不承担艺术功能,而只负责两项意义功能:就仪式而言,天神在故事结束时赶散冤鬼,以喻示地方安宁,是演出目连戏的主要目的。就世俗伦理而言,一方面,吊死鬼讨替失败,是为验证“善有善报”,好人自有神明护佑的观念,以达到劝善目的;另一方面,女吊以做鬼的凄凉景况现身说法,从而警诫轻生者。

绍兴目连戏在“出吊”之前也采用东方亮故事的基本情节,但在吊死鬼形象和演剧模式上自辟蹊径,以男吊、女吊“争替”取代众鬼“争替”。《男吊》一折无曲文,全靠男演员在一根悬空绳索上进行杂技表演,为绍兴目连戏所独创;女吊则从一众冤鬼中提炼出来,成为完整独立的形象,出现长达数百字的唱词;同时摆脱“无名”状态,有了“玉芙蓉”的名字。其生前身份也不再是与公婆不睦的媳妇,而是命运凄惨的妓女。这一系统的女吊表演有四个清晰的层次,出场时女吊玉芙蓉自述生平,讲述幼年时父母亡故,被卖入勾栏,生意惨淡时屡遭鸨妈虐打,最终病卧床榻,于行将就木之际被抛至荒郊。之后,女吊来到妇人房中,试图引诱妇人上吊。继而,妇人被救下,讨替失败的女吊面向观众,恫吓世人须与人为善,不可轻生,否则自己便是下场。到了最后,女吊依例须被“打下台”, 完成“赶吊”仪式。这意味着,绍兴女吊虽然发展为一个较丰满的艺术形象,但其承载的劝善和禳灾功能仍是这一形象的“立身之本”。
1990年丸尾常喜随田仲一成率领的考察团赴浙江进行关于目连戏的调研,事后形成《浙东目连戏札记》。作为鲁迅研究者,丸尾对《女吊》一出格外关注,他开始意识到:“不能说鲁迅所介绍的老年人的说明明确了《女吊》《男吊》本来的意义。它们本来的意义大约与前面所述的朱今《我乡的目连戏》所介绍的状况相似。”此时的丸尾清晰地界分了鲁迅之女吊与目连戏之女吊。然而,在之后写作《“人”与“鬼”的纠葛》时,这个界限却重新模糊起来。他对鲁迅小说的分析建立在目连戏的“原型结构”上,并指出:“要了解中国民众的世界观、生死观,《目连戏》是很宝贵的资料。在对这散落、湮没下去的《目连戏》的发掘、介绍工作中,鲁迅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一复归常识的结论最终封闭了其详细考释目连戏与“祖先祭祀”“幽灵超度剧”关系后可能打开的阐释空间。

丸尾常喜的前后矛盾在于他是以两种不同的身份进入两个领域的研究,在以民俗采风者的姿态进入目连戏时,其思路与田仲一成一致,关注的是一般乡民关于“鬼”的观念,以及“目连戏”用以稳固包括家族、宗族在内的传统社会关系的祭祀功能;而作为鲁迅研究者时,他则指出鲁迅的“孤魂野鬼”书写表现了“对宗族主义逻辑的悲愤” 。就后者而言,丸尾的思路不是以民俗学的视角重释鲁迅,而是以鲁迅思想来重释民俗。其后果是鲁迅对民俗的创造性书写遭到遮蔽,与此同时,鲁迅化用的民俗又反过来被视作影响过鲁迅的某种精神传统。如此,鲁迅、民间、传统三者间的关系仿佛清晰可辨,实则愈发混沌。
实际上,即使在《女吊》文本中,读者也无法从女吊身上找到作者声称的那种复仇精神,这是鲁迅无法跨越的叙事障碍。夏济安很早就发现了《女吊》中的叙事缝隙和复仇说的杜撰性质:“这种复仇性其实是鲁迅的一己之见,据他回忆,真正的表演中,女吊用哀怨的音调和可怕的动作,细述她以自杀告终的悲惨一生,随后,当她听见另一个准备自杀的女人的悲泣,不禁感到‘万分惊喜’。” 也就是说,鲁迅的“回忆”与“见解”之间存在着不小的出入。回顾文本,《女吊》中言及复仇的几次均系作者自行阐释,与女吊本身无关。而“复仇”主旨乃由文章开篇强行定调:“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这意味着,《女吊》的复仇内涵与其说是由女吊这一民俗形象建构起来的,不如说是借由古典话语创造出来的。
鲁迅引用这句话而非其他诗句辞章或更为相宜的民间谚语为“复仇”立论,恐怕并非随机选择。对于身处 1936 年的鲁迅而言,这句名言不仅是一个遥远的“典故”,同时也与彼时诸多文本和事件存在着某种互文关系。
1936年前后,鲁迅突然开始反复征引“会稽”一语,查《鲁迅全集》可见三次,除《女吊》外,其余两次均与一个叫黄萍荪的人有关。2月10日,他在答复黄萍荪约稿的信中写道:
三蒙惠书,谨悉种种。但仆为六七年前以自由大同盟关系,由浙江党部率先呈请通缉之人,“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肯在此辈治下,腾其口说哉。奉报先生殷殷之谊,当俟异日耳。
大约同年,鲁迅又作《关于许绍棣叶溯中黄萍荪》(未刊)一文,言及他所了解到的黄萍荪与官吏勾结,暗中撰文诋毁自己,并以此发迹之事:
当我加入自由大同盟时,浙江台州人许绍棣,温州人叶溯中,首先献媚,呈请南京政府下令通缉。二人果渐腾达,许官至浙江教育厅长,叶为官办之正中书局大员。有黄萍荪者,又伏许叶嗾使,办一小报,约每月必诋我两次,则得薪金三十。黄竟以此起家,为教育厅小官,遂编《越风》,函约“名人”撰稿,谈忠烈遗闻,名流轶事,自忘其本来面目矣。“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然一遇叭儿,亦复途穷道尽!
文中“然一遇叭儿,亦复途穷道尽”一语,正可作《女吊》中“我也很喜欢听到,或引用这两句话。但其实,是并不的确的”这个拗口句子的一个简明注释。两次引用“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都与黄萍荪有关,写作《女吊》时一起手便抛出这句话,不会不想到他与黄氏间的这段“宿怨”。
1948年,黄萍荪将鲁迅复信的手稿公开,并撰文表示他见信后便找浙江党部熟人询问通缉自由运动大同盟诸人一事,党部人员回复并无此案;并称自己后来还就此事与鲁迅当面解释清楚,已冰释误会。黄萍荪的说法未必足信,早在1935年,他就写过《雪夜访鲁迅翁记》,杜撰了他与鲁迅的会面,这一点他在后来也私下承认过。此番是否故伎重施不得而知,但鲁迅说的“办一小报,约每月必诋我两次”应该也是道听途说,否则不会知道“薪金三十”这样的幕后细节;此外,目前也没有资料显示黄萍荪曾经办过诋毁鲁迅的“小报”。至于鲁迅此文写就后留在手里不发,不知是否由于还未完全确证文中提到诸人诸事的真实性。
不过这里要谈的问题不在于黄萍荪是否当面与鲁迅澄清过此事,也不在于黄萍荪是否蒙冤,而是与“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这句为《女吊》全篇奠定基础的引语真正形成互文关系的,并非乡间的女吊形象,而是与《越风》编辑、“教育厅小官”黄萍荪有关的一信一文。
其实早在1925年,《语丝》上曾登载过一封桑洛卿给周作人的信,周作人进行回复,两封信以《乡谈》为题刊登。在复信中,周作人也使用了“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一语。需要提醒的是,这句话在王思任的《让马瑶草阁部》中原作:“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区也。”他在文中怒斥马士英拥立福王后竟“兵权独握”,尤为人不齿的是“叛兵至则束手无策,强敌来而先期以走”,最后更以越乡民众的复仇精神恫吓马士英,逼其自裁以谢天下。从周作人和后来鲁迅所引的异文来看,他们最初见到的并非《让马瑶草》原文,而是清末李慈铭在《越中先贤祠目序例》中对王季重其人其文的称赞:“檄马士英一书正气凛然,其云‘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二语尤足廉顽立懦,景仰千秋。”1928年周作人在《〈燕知草〉跋》中再次征引这句话:“明朝的名士的文艺诚然是多有隐遁的色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有些人终于做了忠臣,如王谑庵到复马士英的时候便有‘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的话,大多数的真正文人的反礼教的态度也很显然。”仍然强调了 “隐遁”之下实为“反抗”。及至1934年周作人作《〈文饭小品〉》,再度提及王思任致马士英书时,却已是另一种看法:“此文价值重在对事对人,若以文论本亦寻常,非谑庵之至者,且文庄而仍‘亦不废谑’。”已在强调反抗色彩之下仍不能掩的“谑”,这无疑是在与“载道派”对垒。1936年9月16日,即鲁迅开手作《女吊》的三天前,周作人致林语堂的一封信刊载在《宇宙风》上,称“近日拟写一小文,介绍王季重之《谑庵文饭小品》,成后当可以寄奉,此书少见,今年以屠隆之《栖春馆集》一部易得之者也”,颇有珍重之意。信末又以明末比附当时,以为“虏患流寇,八股太监,原都齐备,载道派的新人物则正是东林,我们小百姓不能走投其中某一路者活该倒楣”。很长一段时间,周氏文末都像这样,每每须与载道派交锋一番,使其“谑”的趣味显得格外沉重。其实,言志也好,载道也罢,当鲁迅在生命末期不断使用这句周作人曾反复征引的“改造”后的乡贤名言,不仅是兄弟二人曾经共享同一传统知识资源的见证,更是时空相隔下,两人从同声相应走向各言其志的一场颇具象征意味的潜对话。

更重要的是,当鲁迅反复征引王思任的“报仇雪耻”之言时,“晚明小品热”正逢其盛,而王思任正是被大力推崇的一位。1932年北平人文书店出版沈启无编选的《近代散文抄》,选入王季重小品文16篇,数量上仅次于袁中郎、李长蘅、张宗子,内容几乎均为游记。1935年,施蛰存更是直接借用王思任《文饭小品》之名,在上海创办新刊。同年他又主编了“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虽云“中国文学”,而公安、竟陵两派分量极重,《王季重十种》亦入选其中,由阿英校点。这年年底,鲁迅作《杂谈小品文》,提及“今年又有翻印所谓‘珍本’的事”时有这样的评价:“现在只用了一元或数角,就可以看见现代名人的祖师,以及先前的性灵,怎样叠床架屋,现在的性灵,怎样看人学样……”直把古人今人一网打尽。不过鲁迅所非议者并非“小品文”或“性灵”本身,而是“独尊”之态:“虽说抒写性灵,其实后来仍落了窠臼,不过是‘赋得性灵’,照例写出那么一套来。”而“经过清朝检选的‘性灵’,到得现在,却刚刚相宜,有明末的洒脱,无清初的所谓‘悖谬’”。这本质上是在谈“性灵”作为“一是之学说”的虚伪性。在此前所作的《“招贴即扯”》中,他更是举出袁中郎如何服膺具有“方巾气”的顾宪成作为实例,说明小品文的师祖也并非只有一张面孔,只贯彻一种主张。而到《女吊》时,鲁迅基本采取了相同“策略”,他对王思任“会稽”一语的征引,击中了晚明小品推崇者对王思任人其文“谑”与“性灵”的单一面向的言说,翻检出其极具“方巾气”的一面。
不难看出,无论是与黄萍荪在现实生活中的恩怨,与周作人自觉或不自觉的潜对话,还是与晚明小品文推崇者的观念交锋,“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都去民间女吊形象远矣,而指向了鲁迅与知识界的多方纠葛,潜藏着真正的“民间”大众无从了然的用心。这是面向知识分子的发难,而非向着“乡土中国”的发声。
《女吊》中鲁迅对“复仇”的赞颂是热烈的,这种态度同样见于《铸剑》《复仇》等作品中,但不应忘记,很多时候他却对“复仇”采取一种否定性书写。未庄乡民用“灯”和“亮”的“禁语”取笑阿 Q 时,他“没有法,只得另外想出报复的话来:‘你还不配……’”被革命军拒绝后,阿 Q“对于自己的盘辫子,仿佛也觉得无意味,要侮蔑;为报仇起见,很想立刻放下辫子来,但也没有竟放”。这里,复仇心理被鲁迅纳入国民性批判叙事。消除了《阿 Q 正传》的戏谑笔调,《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则正面表达了这一观点,他说中国人“大抵无端的互相仇视……我因此对于中国人爱和平这句话,很有些怀疑,很觉得恐怖”。1925年写就的散文《颓败线的颤动》和小说《孤独者》中重复闪现着同一个场景,孩子手持芦叶,向人喊“杀”。这种人性中自带的仇恨“种子”,使鲁迅和他笔下的人物都感到莫大的惊惧,魏连殳终于“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以此作为复仇——一种绥惠略夫式的复仇。1926年鲁迅谈及绥惠略夫时表示:“绥惠略夫临末的思想却太可怕。他先是为社会做事,社会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杀害他,他于是一变而为向社会复仇了,一切是仇仇,一切都破坏。中国这样破坏一切的人还不见有,大约也不会有的,我也并不希望其有。”无论是阿 Q 式的复仇,还是绥惠略夫式的复仇,都为鲁迅所反对。因此辨鲁迅在不同语境中的“复仇”话语是必要的,也就是说,真正的问题不在于鲁迅是否主张复仇,而是他主张的是何种复仇。

鲁迅的复仇书写可以追溯回早期的《摩罗诗力说》,在这篇论文中,他称拜伦“复仇一事,独贯注其全精神”;“怀抱不平,突突上发,则倨傲纵逸,不恤人言,破坏复仇,无所顾忌,而义侠之性,亦即伏此烈火之中”。并着意提醒:“若为自由故,不必战于宗邦,则当为战于他国。”即复仇并非民族主义式的,而是为自由之战,或者说,不是利己的,而是利他的。那么,鲁迅对拜伦以及此后密茨凯维支等人“复仇”精神的称颂,是相对何种观念而言的?他在文中也做出了解释:
人人之心,无不泐二大字曰实利……夫心不受撄,非槁死则缩肭耳,而况实利之念,复姑黏热于中,且其为利,又至陋劣不足道,则驯至卑懦俭啬,退让畏葸,无古民之朴野,有末世之浇漓。
以此反顾中国,他指出中国文化的缺点正在于“以孤立自是,不遇校雠,终至堕落而之实利”。也就是说,鲁迅试图宣扬的“复仇”本质上是一种纯粹的、去功利性的复仇,要求摒除对复仇以后的“实利”的谋求。
实际上,这种纯洁的复仇观其来有自,章太炎曾作《复仇是非论》强调“人苟纯以复仇为心,其洁白终远胜于谋利”, 鲁迅对理想复仇的阐释与此相通。不过,章太炎把“复仇”视作“排满”的一部分,因此他一开始就提出:“今以一种族代他种族而有国家,两种族间其岂有法律处其际者,既无法律,则非复仇不已。”显示 出强烈的民族主义诉求。而“复仇”之后,他提出了下一步建设性对策:“若以汉人治汉,满人治满,地稍迫削,则政治易以精严,于是解仇修好,交相拥护,非独汉家之福,抑亦满人之利。”即借助复仇手段,最终要达到的是各民族“解仇修好”之旨归。而章太炎一直强调的“民族主义”仅作为一项策略提出,不具终极性,他说:“举其切近可行者,犹不得不退就民族主义。”既然 “民族主义”只是一种政治方案,那么其哲学底色又是什么?章太炎在文末做出这样的自白:“人我法我,犹谓当一切除之。”对“ 人我法我”的破除在此后的《建立宗教论》中又得以深化,即建立“以自识为宗”的新宗教,章太炎进一步阐释:“识者云何?真如即是惟识实性,所谓圆成实也。”“圆成实性”是印度唯识学和中国法相宗所说的“三性”之一,与“遍计所执自性”“依他起自性”相对。“遍计所执自性”是观念的产物,离开意识便不具意义,比如“色空”“自他”“内外”等概念;“依他起自性”则指一切依因待缘之现象,而“逮其证得圆成,则依他亦自除遣”。章氏的“真如”哲学主张“无量固在自心,不在外界”,但“自”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我”,而是“特不执一己为我,而以众生为我”。因此,章太炎是把复仇视作最初级阶段的“行动”,而最终要去除“人我法我”以抵达“真如”境界。
章氏意在以“复仇”之术求“真如”之道,这种术道相离、体用二分的做法本身就充满危险。在鲁迅这里,“复仇”则被赋予本体性,而不仅是一项政治实践。章太炎对“复仇”之后的构想是“解仇修好”,鲁迅却说“平和为物,不见于人间”。在政治上鲁迅则指出:“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有人撄人,或有人得撄者,为帝大禁,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诗人却正是触犯这一禁忌的“撄人心者”,“其声激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而污浊之平和,以之将破”。鲁迅无意将“复仇”滞留于“民族主义”立场,而使其超越实在的行动,进入抽象的精神力量和审美资源层面,即“撄人心”。因此与章太炎把复仇寄托于革命不同,鲁迅更倾向于将复仇寄托于文艺,他一方面作《摩罗诗力说》称颂拜伦谱系文学家的“摩罗精神”,一方面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展示这种复仇精神,《复仇》中一男一女“持刀对立旷野”却“也不拥抱,也不杀戮”,以最大的无聊向看客复仇;《复仇(二)》中被凌辱的“神之子”因悲悯人们的前途,而仇恨人们的现在;直到《铸剑》,黑色人将“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复仇表现到近乎极致。
这种复仇观的困境在于它只能停留在精神层面,而无法通向“动作”之“旨归”,否则极易滑向阿 Q 式复仇或绥惠略夫式复仇,即鲁迅自己反对的内容。这也造成了《女吊》的叙事障碍——“讨替代”作为传统女吊形象的核心行动无法直接过渡为“复仇”,作者更是特意区隔了复仇与讨替代的意义:“中国的鬼还有一种坏脾气,就是‘讨替代’,这才完全是利己主义”,“习俗相沿,虽女吊不免,她有时也单是‘讨替代’,忘记了复仇。”这样叙事的后果是作者只能指认女吊为复仇者,却无法提供女吊复仇的实例。
以“单是‘讨替代’”而“忘记了复仇”的女吊作为复仇精神的代表,其说服力显然不足。那么这一存在天然“劣势”的形象为何仍能被鲁迅纳入其复仇书写序列?
事实上鲁迅关于女吊的印象应该并未落在童年时故乡的戏台上,而很可能来自于多年后陶元庆的画作《大红袍》。1925年鲁迅在陶元庆的个人展览上见过这幅画后,即与许钦文商议:“《大红袍》,璇卿这幅难得的画,应该好好地保存。钦文,我打算把你写的小说集结起来,变成一本书,定名《故乡》,就把《大红袍》用作《故乡》的封面。这样,也就把《大红袍》做成印刷品,保存起来了。”本应起辅助作用的封面画,这时却有些“喧宾夺主”的意思,足见鲁迅珍重之意。
作为陶元庆的好友,许钦文见证了《大红袍》的整个创作过程:
(陶元庆)当时住在北京的绍兴会馆里,日间到天桥的小戏馆去玩了一回,是故意引起些儿童时代的回忆来的。晚上困到半夜后,他忽然起来,一直到第二天的傍晚,一口气画就了这一幅。其中乌纱帽和大红袍的印象以外,还含着“吊死鬼”的美感——绍兴在演大戏的时候,台上总要出现斜下着眉毛,伸长着红舌头的吊死鬼,这在我和元庆都觉得是很美的。
陶元庆还向许钦文阐述过创作中一些更具体的想法:
《大红袍》那半仰着脸的姿态,当初得自绍兴戏的《女吊》,那本是个“恐怖美”的表现,去其病态的因素,基本上保持原有的神情:悲苦、愤怒、坚强。蓝衫、红袍和高底靴是古装戏中常见的。握剑的姿势采自京戏的武生,加以变化,统一表现就是了。
两人的说法 基本还原了创作的三个步骤:首先,《大红袍》是从绍兴戏剧中的女吊取材,构成画面主体;其次,画家在女吊原型的基础上滤去了原有的病态之恐怖,而着力塑造“悲苦、愤怒、坚强”的神情;最后,在外形设计上吸纳了京剧元素,这主要体现在大红袍和厚底靴等行头以及武生的握剑姿势上,这一切都带有典型的男性印记,而这一阳刚化改造正是去除女吊原型病态因素的重要环节。经过陶元庆改造的女吊和后来鲁迅笔下的女吊给人的印象几乎一致,只是《大红袍》仅凸显女吊的“悲苦、愤怒、坚强”,还未发展为鲁迅反复强调的“复仇”。
但鲁迅很可能已经从《大红袍》那里“误读”出“复仇”精神。他对《大红袍》的倾心无关于其女吊的选材,而主要来自画面中“剑”的意象,他向许钦文称道:“璇卿的那幅《大红袍》,我已亲眼看见过了,有力量;对照强烈,仍然调和,鲜明。握剑的姿态很醒目。”据许钦文回忆 ,鲁迅后来专门写信给陶元庆,告诉他“有个德国的美术家叫Eche 的也说《大红袍》很好,剑的部分最好”。无论是鲁迅自己的评价,还是向画家转述别人的评价,都对“剑”的意象给予格外关注。可以说,“剑”是鲁迅通向《大红袍》的理解之门。而综观鲁迅的复仇书写,“剑”几乎可以视作其核心审美意象,《铸剑》毋庸置言,《摩罗诗力说》中言及拜伦处多次出现“孤舟利剑”意象,《复仇(二)》中赤裸的两人也“捏着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鲁迅将复仇的审美想象凝结在剑意象中,而陶元庆的画中之剑很可能触发了鲁迅的心中之剑,这为鲁迅日后把女吊形象与复仇精神关联起来提供了重要的艺术资源。
1924年,鲁迅译作《苦闷的象征》的封面亦出自陶元庆之手。陶元庆到北京后不久,许羡苏即在鲁迅处提及此人。鲁迅又向许钦文详细询问了陶元庆的情况,对其绘画风格有了基本了解后,便托请许钦文邀他为《苦闷的象征》绘制封面,这是两人多次合作中的第一次。封面的基本构想是头发蓬乱的少女舔舐手中的一柄镋叉,所有元素均由曲线线条抽象凝练而成,包孕在圆形轮廓中,融入日本图案风格,颇具象征意味,色彩主要由黑、蓝、红三色构成,对比度极高。

有意思的是,对比《大红袍》和《苦闷的象征》封面,两幅画的基本元素和用色如出一辙,散发的女子,寒气凛凛的兵器,黑、蓝、红的配色,几乎可以把《苦闷的象征》看作高度抽象化之后的《大红袍》。陶元庆较少自我重复,这两幅画的内在联系不言而喻。在鲁迅那里,虽然《大红袍》的创作早于《苦闷的象征》封面,但鲁迅先见到的却是后者,这不仅为鲁迅后来鉴赏《大红袍》提供了理解的“前结构”,也为鲁迅重新想象女吊形象,为之灌注个人化隐曲提供了途径。
虽然鲁迅的女吊印象极可能受到《大红袍》影响,但在作品中他仍旧将其复归于民间社戏舞台上。实际上,鲁迅虽然在《社戏》《无常》《女吊》等作品中一再表达对于社戏的倾心,但其童年时代真实的观剧体验却未必像文学作品中叙述的那样。在《偶成》里他透露了关于社戏的另一种记忆:“前清光绪初年,我乡有一班戏班,叫作‘群玉班’,然而名实不符,戏做得非常坏,竟弄得没有人要看了。”这提示我们,日后鲁迅对社戏的欣赏并非看重其本身,而是看重其观念意义上的阐释空间。
早在1908年所作的《破恶声论》中,鲁迅已经摆明捍卫社戏的态度:
若在南方,乃更有一意于禁止赛会之志士。农人耕稼,岁几无休时,递得余闲,则有报赛,举酒自劳,洁牲酬神,精神体质,两愉悦也。号志士者起,乃谓乡人事此,足以丧财费时,奔走号呼,力施遏止,而钩其财帛为公用。嗟夫,自未破迷信以来,生财之道,固未有捷于此者矣。夫使人元气瘰浊,性如沉鞠;或灵明已亏,沦溺嗜欲,斯已耳;倘其朴素之民,厥心纯白,则劳作终岁,必求一扬其精神。故农则年答大戬于天,自亦蒙庥而大嵩,稍息心体,备更服劳。今并此而止之,是使学轭下之牛马也,人不能堪,必别有所以发泄者矣。况乎自慰之事,他人不当犯干,诗人朗咏以写心,虽暴主不相犯也;舞人屈申以舒体,虽暴主不相犯也;农人之慰,而志士犯之,则志士之祸,烈于暴主远矣。
他在这里指出,禁止赛会的“志士”们本着经济的需求、功用性的观念,否认人的超越性精神需求,这是对人类精神的暴政,比独夫之暴政更甚。因此,鲁迅将“志士”斥为“伪士”,称其“借口科学”不过“拾人余唾”,实则对“科学何物,适用何事,进化之状奈何,文明之谊何解”不明就里。如此,被宣扬的“科学”已非科学本身,而是一个概念空壳。在《科学史教篇》里,他更清晰地表述了“科学”能与时俱进,而非一定之规。当“科学”成为“一是之学说”的知识话语,即取得统驭社会、“以众虐独”的权力。正是基于对话语权力的抵抗,或说出于“伪士当去”的诉求,“民间”资源在鲁迅那里获得了“意义”。
但“民间”本身在鲁迅看来并不可靠,这从鲁迅对京剧的态度即可见出。社戏和京剧均植根于民间社会,但鲁迅对二者的评价判若云泥。一方面,社戏和京剧虽然都是民间大众的艺术,但却属于两个不同的“民间”世界,从《社戏》中我们可以理解鲁迅是将京剧放置在现代市民社会中来打量的,而社戏则属于前现代的乡土社会,只有后者可以获得“民间”的称谓——五四以来,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民间”的发现正是沿此思路展开。在这一思路中,“民间”并不处于建构中的“当下”,而被视作已完成的实体,它本身不具自足性,而是作为抗衡官方社会和主流传统的“他者”被想象与征用。另一方面,鲁迅否定京剧的原因已经在批评梅兰芳时说过:“梅兰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宠儿,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鲁迅深谙“民间”的不稳定性及不可靠性,这意味着他对“民间”资源和“民间”概念的频频征用,实际只是将“民间”作为方法,而非立场。

那么,鲁迅的“立场”,或说最终要求是什么?这需要溯回他在《破恶声论》中提到的两个核心概念:“心声”和“内曜”。“内曜者,破瘰暗者也;心声者,离伪诈者也。”其真义在破除“他信”以重建“自信”。而其所谓“迷信可存”的原因也正在于此:“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睹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出古异,淑诡可观,虽信之失当,而嘲之则大惑也。”这意味着他看重的 是“迷信”表象下的“神思”,即太古先民不因袭“他信”的想象力。多年后,鲁迅翻译《苦闷的象征》,亦可视作对其早年论述的接续,在《苦闷的象征·引言》中,鲁迅把翻译他人著作时“压在纸背的心情”亮明在纸面上,他直言:“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但中国现在的精神又何其萎靡锢蔽呢?”
不过他又进一步解释,对“心声”和“内曜”的激发却“不大众之祈,而属望止一二士,立之为极,俾众瞻观”。即不能依靠民间大 众,而须依靠少数几个人来为大众示范。因此,通常意义上的重启民间资源以破壁固化的精英社会或官方社会于鲁迅而言仅是具备可操作性的第一步,其核心却恰是反面,即对“一二士”——那些有能力对世俗“精英”和士大夫传统进行清扫,并重新激发人的上古天然之心的人——的吁求,而此中蕴含的实为更具理想色彩的精英意识。
如此,我们得以理解,“民间立场”作为一种策略性话语使得女吊成为可资征用的形象;“精英意识”却使作者对女吊不得不进行一场根本性重塑,使其由一个承载劝善与宗教祭祀功能的传统民俗形象转为向“他信”的知识权力和话语权力“复仇”的文学资源。至于从《无常》到《女吊》,鲁迅对古老目连戏中那些鬼魅的念念不忘,正是为其“逞神思而施以人化”的古异淑诡所吸引。从鬼魅书写中渗透出的苦闷与寂寞,更是作者无以为外人道的“象征”之所系。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文学评论》2020年第2期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