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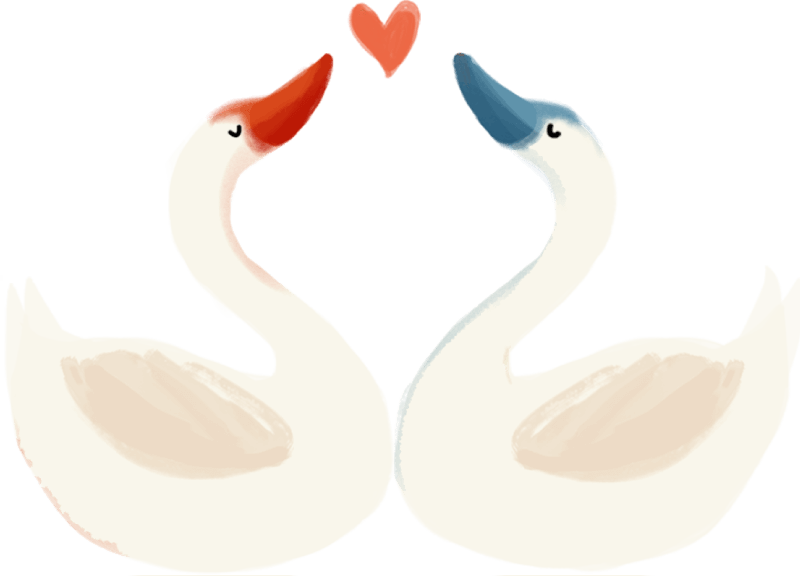
内容提要:少数民族儿童文学被想象和关注的焦点往往集中于民族特色与民族差异,由于刻板印象的建立与“被看”视域的束缚,常存在过度书写“民族性”而忽略“儿童性”的现象。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应摆脱“看”与“被看”的视域束缚,将“儿童性”作为提升自身艺术品质的首要标准,探求融入日常生活的自然质朴的“民族性”表达。文章以新时期以来比较有代表性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原创儿童文学作品为例,探讨当下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创作的叙事选择与艺术品质。
关键词: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叙事;儿童性;民族性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亦是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构成内容,肩负着塑造和培养下一代民族性格和审美情趣的神圣使命,同时展现了当代少数民族少年儿童的生活图景与精神风貌。然而长期以来,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似乎一直受困于外界的期待与想象,背负着展示“民族特色”的沉重标签,却始终与当代生活保持距离,很难令当下的少年儿童产生共鸣。本文以新时期以来比较有代表性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原创儿童文学作品为例,探讨当下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创作的叙事选择与艺术品质。
一、被过分强调的民族特色与民族差异
少数民族文学一直存在于他人的“想象”之中。人们习惯于用自己的固有印象和“猎奇式”眼光去“定义”少数民族文化图景。宗教、历史、文化、习俗……这些“陌生化”元素共同构成的“民族性”特征,通常是一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被期待的核心价值。在少数民族文学领域,普遍存在着对“民族性”过度书写或流于表面的现象。有学者认为:少数民族文学为迎合主流意识形态,格式化地书写着自己的“民族特色”,其实并没有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格式化”书写的原因有二:刻板印象的建立与“被看”视域的束缚。

我们今天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期待和想象,其实很大程度上源于汉族作家创作的少数民族题材作品。当代少数民族题材写作,在汉族作家中存在着“对少数民族生活的误解和歪曲”和“对于少数民族生活外在色彩表现出来的浓厚兴趣,积年累月形成了一种抒情散文式的猎奇”两种扭曲。首先,一些汉族作家总是从“差异性”视角切入对少数民族生活的观察和体认,则很容易放大民族差异而忽略不同民族的普遍性与共通性。其二,汉族作家创作少数民族题材,有意识形态上的诸多限制,多正面而绝少负面,渐渐形成歌颂少数民族美好品质的固定写作模式。其三,一些汉族作家始终无法真正深入少数民族生活,所关注与描述都集中于少数民族的外部特征,继而形成碎片化的拼接,久而久之形成外界对该民族较为稳固的刻板印象,成为该民族的“对外标准化形象”。而这种刻板印象的建立反过来又影响到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
一方面,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和民族认同心理的影响,少数民族作家认为自己有宣传本民族文化和代表本民族立场的责任和义务,因而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靠近主流意识形态业已塑形的“标准化形象”,很难冲破固有印象的藩篱。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知识分子的“私人化写作”和“批判立场”,使作家很难对民族根性和人性做出尖锐深刻的剖析和自省,转而选择更为保守的创作姿态,而诉诸于外部色彩的民族特色或地域风情显然是作家安全并讨巧的选择。另一方面,作家的潜意识里时时有对读者的关注,读者对作品的接受与期待反过来也会制约作家的选择,读者对“民族特色”的看重让少数民族作家从无奈地“被看”转向自觉地“展示”。因此,汉族作家对少数民族的“看”与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时呈现的“被看”姿态共同构成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困境中的双重制约因素。

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靠近和对读者期待的迎合,也是身处当下为时代所裹挟的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选择。以维吾尔族长篇儿童幻想小说《楼兰古国的奇幻之旅》为例,其目标读者定位明显是维吾尔族以外的其他民族读者(不仅仅是少年儿童),因而作者几乎将所有心力都放在展现维吾尔民族的文化历史和地域风情上,小说中出现的维吾尔族少年、楼兰公主、魔鬼城、坎儿井、千佛洞、回纥文、英雄史诗、萨满教仪式、维吾尔族穿戴、特色食品、娱乐项目、节日、乐器等民俗文化十分丰富。在仪式感极强的萨满教活动与传统节日中,维吾尔人表达出对天神、祖先、土地、动植物的敬仰和尊重,富于浓烈的地域文化风情。这样一种风情画卷式的“展览”方式让这部作品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看上去十分丰沛,在“让世界了解维吾尔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和显著的作用。但我们同时也能感受到作者作为民族“代言人”的愿望过于强烈,想将维吾尔族的历史文化民俗精华都浓缩在一部小说里,造成民族元素过于密集,令读者只能如游客般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很难领会到民族文化的深层内蕴。与此同时,小说人物也被高密度的“民族特色”喧宾夺主,五位小主人公沦为展现一路上所见所闻的功能性“道具”,可见“被看”视域的束缚之深。
人们对少数民族儿童文学还存在一个长期形成的心理误区,似乎只要是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写的就是过去的故事,年代久远的故事,反正与当下的大多数少年儿童不在一个时空坐标轴中。这是因为人们只重视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和“地域性”,而忽略了它的“时代性”与“社会性”。似乎“民族性/地域性” 与“时代性/社会性”是一对天生对立的语法概念,是不能共存的——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他者眼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许多少数民族作家都写到了儿童的苦难成长历程,如哈萨克族儿童小说《长满蒿草的原野》《阿依波力的信》,维吾尔族儿童小说《坎吉》《书包》等。这些小说中少儿主人公所经历的苦难并非民族的苦难,与宗教信仰或民族政策无关,而是时代的、社会的共同苦难,六七十年代全中国的儿童都在经历苦难,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贫瘠是相同的境遇,只是经受苦难的形式略有不同,有的孩子拾粪,有的孩子种地,有的孩子流浪,有的孩子放羊。然而在人们的惯性思维中,少数民族儿童的苦难是独属于那个民族的苦难,忽视了其与整个中国社会及时代的密切联系。
事实上,当下的社会生活是少数民族儿童文学表现的重要内容。例如,维吾尔族儿童小说《一瓶沙子》写维吾尔族少年远离家乡到“内高班”求学,就充分显示了时代性,“内高班”是配合民族政策所产生的特有教育现象,少年西尔艾力只身在上海产生的对家乡亲人伙伴的思念令人感同身受。维吾尔族童话“骗子吐苏克系列”,讽刺的则是当代社会的种种丑态,领导的好大喜功、下属的阿谀谄媚、担责任时互相推诿等现象,极具时代性和社会性特征。可见,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也与汉民族儿童文学一样,具有时代的普遍性与同一性,能够代表这个时代少年儿童的共同属性。因此,我们也应当与时俱进地来看待“民族性”,破除对“民族性”的误解与偏见。
二、“儿童性”是“本”,“民族性”是“根”
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民族性”并非少年儿童所重视和感兴趣的内容,它所指向或迎合的并非儿童读者,而是以“他者”眼光审视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成人读者。过度重视隐含读者(成人)的需求而忽略目标读者(儿童)的期待,这表面上看是读者定位的错位问题,实际上折射出的是少数民族作家的“儿童观”问题。儿童观是成人社会如何理解儿童与如何对待儿童的观念与行动。儿童文学作家有什么样的儿童观,儿童文学就有什么样的艺术精神与美学品性。作家如果以成人为本位,便会站在成人角度提供成人认为儿童所需要的内容;如果以儿童为本位,就会“看到儿童生命体内蕴含着不可替代的珍贵的生命价值”。这种“珍贵的生命价值”在儿童文学中具体表现为儿童思维、儿童心理、儿童想象、儿童情趣、儿童幽默、游戏精神等品格特质,统称为“儿童性”。“儿童性”是儿童文学的核心价值和根本属性。不同时代不同国籍不同种族的少年儿童天性都是一致的,情感都是相通的,只是成长轨迹和环境不同,他们欣赏和喜爱的儿童文学作品必然是有共性的,这也是经典得以形成和流传的原因。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不应一味追求“特性”——“民族性”,而应首先重视“共性”——“儿童性”。

蜚声国际的日本童谣诗人窗满雄,他的童诗朴实无华,就是用最质朴的言语写出儿童最真实的思维和想象:郁金香在水中的倒影是叫香金郁吗?乌贼长成箭头的模样,是用来指示大海的方向吧?这样简单而绝妙的创意,恰恰最为接近儿童的本真,这是世界各国各族儿童都能产生心灵默契的思维方式,也是成人世界无法企及的充满灵性的儿童特性。“儿童性”是作家通过对自己童年的了解和对当下儿童的观察、相处捕捉得来的,具体可以表现为“童言无忌”的语言、憨态可掬的行为、弄巧成拙的误会、任意跳跃的思维、儿童特有的心理活动、天马行空的想象等。“儿童性”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的质感所在,通常是很难编撰的。以一组维吾尔族儿童文学为例,散文《幼儿时的我是那样想的》再现了儿童的奇思妙想:“我的年龄什么时候能赶上奶奶?”这大概是每个盼望着快快长大的孩童都产生过的想法;“闪电把白云的肚子扎破不会伤心吗?”对自然万物的拟人与情感想象正是儿童“泛灵论”原始思维的体现。小说《黄色风筝》中,小男孩听说“谁有本事风筝就归谁”,慌忙跑回家翻箱倒柜找“本事”,是儿童特有的稚拙和误会。童诗《健忘的松鼠》中,滚圆的松鼠在秋天埋下许多青核桃,冬天跳来跳去怎么也找不到埋核桃的地方,像极了丢三落四、天真烂漫的小孩子。童诗《谁去买醋》写的就是儿童家庭生活中的真实一幕,妈妈指挥爸爸、爸爸指挥“我”、“我”指挥弟弟、弟弟指挥猫、猫命令它的尾巴:你去买醋!寥寥几句便充满了儿童情趣。童话“骗子吐苏克系列”没有任何说教内容,通篇都是冒险吹牛,充满热闹好玩的游戏精神。这些少数民族儿童文学作品中没有陌生的“民族性”,也没有奇异的“地域性”,写的就是天下儿童的普遍共性,但又是只有儿童才具备、成人早已遗忘的特性,并且只有童心丰盈、将儿童视为独立个体去尊重和了解的成人才能发现并满怀天真地书写,这样的作品充满了灵动的想象和细腻的感触,让儿童如遇知己,也让成人与自己的童年相遇。虽然我们无法从这些作品的“外部特征”辨认作家的民族身份,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充满丰沛“儿童性”的作品无论放在何时何地都是优秀的儿童文学杰作。
这里绝不是说儿童文学中的“民族性”不重要或可有可无,“儿童性”和“民族性”并不是矛盾对立的,“儿童性”是“本”,“民族性”是“根”。只有写出贴近儿童心理、符合儿童审美、充满儿童情趣、塑造儿童真形象的作品才有资格跻身世界优秀儿童文学之列;同样,也只有将长期在民族文化熏染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民族性”纳为自身的文学底色,才能成就独特的“民族风格”,因为“民族性中的文化因素,给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对民族性的认识注入审美力量;民族性中的历史因素,给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对民族性的认识带来内涵和厚度。”而兼具审美高度和内涵厚度的民族文学,才是真正成熟的民族文学。因此,少数民族作家不能丢弃自己最熟悉和擅长的“民族性”,但也绝不能采取罗列展览式的言说方式,将民族性“表面化”“形式化”。虽然那些极具特色的少数民族建筑、服饰、工艺品、仪式活动、特色食品等都是“显性”的 “民族性”表征,但真正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其实是“无形胜有形”的,它们绝不需要大声势、大阵仗,它们不动声色地散落在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中,演化为思维、观念、习惯等一些很难具象化又十分驳杂的生活内容,是不可刻意为之的。要想让“民族性”落地,将民族特性融入涓涓流淌的日常生活,当是最好的书写方式。

比如,馕是维吾尔族的传统食物,在维吾尔族文化体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维吾尔族一日三餐都离不开馕。“无畜可为家,无馕不成家。”“马在槽里喂,馕在炉中烤。”这些谚语形象地表明了馕在维吾尔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儿童诗《辛苦的母亲》便截取了母亲起早贪黑为全家打馕、眉毛和睫毛都被烧没了的情景进行肖像速写来歌颂母爱,这就是一种“民族性”角度的自然选取。馕坑是制作馕的地方,也是维吾尔人门庭前的标志。维吾尔族儿童总是坐在馕坑边一边吃着香喷喷的烤馕一边听妈妈讲故事。“骗子吐苏克”系列童话初版时就叫做《馕坑边的故事》,相当于汉族儿童的“枕边故事”。

又如,维吾尔人自古重视栽种果树,甚至把园艺生产与粮食作物的生产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维吾尔族谚语有云:“巴扎繁荣靠货物,庭院秀丽靠葡萄藤。”“男儿像高山,女子像果园。”维吾尔族儿童文学作品中,就有许多对园艺和瓜果的随笔描绘,如“骗子吐苏克”系列童话中,伪装成记者的吐苏克在猴子的家乡参观了红枣园、石榴园、核桃园等各种果园;儿童小说《一瓶沙子》里通过爷爷和爸爸的对话就能看出他们对果园的重视,爸爸抱怨一场沙尘暴后“杏子还没来得及开花就被风给吹落了”,爷爷让他把葡萄墩重新绑一下,并嘱咐“不要让霜把葡萄墩冻坏了”,这些细节都是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对话,却透露出一股纯正的维吾尔味道,它们成为维吾尔作家融入血液的一种方式,是其他民族作家模仿不来的。《一瓶沙子》中的维吾尔儿童边游戏边唱“偷甜瓜”的儿歌,就比汉族作家笔下写少数民族孩子唱“月亮光光,你别躲藏,到我手里,给你奶糖。”更贴近维吾尔族儿童的现实生活,因为“甜瓜”比“奶糖”更具有少数民族的特性和味道。“民族性”不用夸大,也不用刻意搜寻和展示,它就是这样融入生活的点点滴滴,俯仰可见,质朴平凡。
三、“儿童性”与“民族性”兼美的叙事范例
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应是“儿童性”与“民族性”兼美并自然流露的艺术文本,其实这样的作品早已有之。比如维吾尔族民间故事《阿凡提的故事》,维吾尔族崇尚幽默,儿童也喜欢幽默趣味;维吾尔族崇尚智慧,儿童也喜欢机巧斗智;阿凡提讲的是地地道道的维吾尔族生活故事,却能经久不衰地广受各族少年儿童喜爱,秘诀就在于“儿童性”与“民族性”的统一。当代的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创作,如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笔下的驯鹿鄂温克部落,便在引人入胜的故事和细致入微的感情之外,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民族风格。

维吾尔族儿童小说《被舔过的馕》以维吾尔人的宗教生活为背景,却不直接写宗教仪式,而是从儿童的角度截取了一个生活场面。村里的孩子热切盼望着封斋结束后,去挨家挨户表达祝福,大人们会把馕、糖果、干果塞满他们的口袋,就如同汉族孩子向长辈拜年会收到红包或礼物一样。当长老开始诵经时,“所有孩子像是听到了口令一样,‘阿赞!阿赞!阿赞!阿赞!……’就那样大喊着往自个儿家跑了”,孩子们的声音让全村都震动起来,封斋的大人们开饭了。这一幕描绘得极富感染力和场面感,读者仿佛能身临其境地听到孩子们整齐、嘹亮又激动的喊声响彻傍晚的村庄……开斋节诵经本是一种宗教活动,但孩子们把它视作游戏一般热情高涨。小说真实地讲述着本民族儿童的故事,表达着儿童的情感和心理,不露声色地将“民族性”融入到现实的日常生活之中,真正抓住了“民族性”表达的精髓,借用王蒙曾评价艾克拜尔·米吉提作品的话——“不在于写‘奇装异服’‘奇风异俗’或堆砌听来的与杜撰的‘谚语’,他写得更重神而不在形。”
哈萨克族长篇儿童小说《托姆帕克成长记》还原了原汁原味的哈萨克族游牧生活,又时刻凸显着儿童的真实心理与本真性格,是一部“儿童性”与“民族性”兼备的成熟之作。小说叙述牧区的哈萨克少年们面对生活中的种种贫穷困苦丝毫不以为意,还特别擅长苦中作乐。面对猖獗的老鼠,他们在墙上钉钉子,把书包鞋子和食物都挂在上面,校长在大会上让他们给学校提建议,他们竟然建议一间宿舍发一只猫!少年们帮学校食堂往菜窖运冬菜,总想占点小便宜,与管理员斗智斗勇,美餐一顿后甘愿写检讨书。由于没有浴室,男孩们去教室里洗澡,一桶热水只够三个人洗,大家都很会节约用水,一个提醒另一个说:“别把水洒在地上,省着点儿,一个人只能用十碗,你已经用了四碗了。”一个男孩洗完后光着屁股坐在满是灰尘的课桌上,一个清晰的屁股印成了第二天全班的笑谈。这群可爱的哈萨克少年懂事得让人心疼,却又淘气得令人忍俊不禁。正值十五六岁长身体的年龄,食堂缺乏营养的饭菜难以满足他们日渐成长的肠胃,拥挤的大通铺难以舒展他们快速生长的身体,但他们那爱玩爱笑爱闹爱恶作剧的“顽童”本色和善良纯真的童心与同龄少年是一模一样的,这也是小说写得最为出彩的地方,作者的主调虽然是苦难,但从不缺少希望和信念;小说的主人公是在艰苦环境中成长的少年,他们虽比同龄人多懂事而少任性,却绝不是“小大人”或“缩小的成人”,他们用积极的态度拥抱生活,用“童心之力”战胜苦难,游牧民族的血液中那随性、豁达、宽厚的性情令他们在艰苦的岁月和环境中锻炼出了坚韧不拔的意志,他们是符合年龄阶段个性特征并有着真实生命体验的“真”少年。
这部小说的“民族性”也写得自然而厚重,形成了典型的民族风格。小说中有这样一幕:旋风吹走了托姆帕克家的毡房,乡亲们一边帮忙一边和托姆帕克的母亲扎黑开玩笑:“老嫂子,旋风没把您带走,说明您是个有福之人哪!”扎黑则完全没有气恼也没有咒骂着“倒霉”,而是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重新搭起毡房。如果了解哈萨克族传统和居住的自然环境就会明白,对于这样的“小灾难”,哈萨克人早已习以为常。哈萨克牧民生活是典型的草原文化模式,具有“自然主义特性”和“经验主义特性”,即“靠天吃饭”,全部生产活动都依赖于自然界的恩泽,完全遵循“顺乎自然”的原则。这种被动性和封闭性决定了草原人民的生活方式,因为长期被艰苦的环境肆虐,他们应对灾难的心理承受能力极强,几乎随时做好了重头再来的心理准备。哈萨克族的民族传统让牧民再苦再难都不忘本。托姆帕克的奶奶生了十三个孩子,妈妈生了十一个孩子,家中生活十分拮据,都是大孩子带小孩子,大的衣服补补改改再给小的穿。妇女们“无论再好再新的裙子,只要见到干牛粪,就会毫不犹豫地兜在裙摆上拿回家。”

正是在这种敢于吃苦、宽容乐观精神的鼓舞下,托姆帕克一次次克服困难,一步步向着理想迈进,后来成为作家、学者——一个贫困牧民的儿子创造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奇迹。小说为哈萨克少年儿童倔强而坚强的成长骄傲和振奋,古老伟大的游牧民族自有他们不屈的气概和挺拔的信念,这是他们源远流长并世代传承的内在精魂和不竭动力。而这种内在的民族精神不是口号喊出来的,也不是刻意为之的,而是在如呼吸般自然的日常生活中让读者感受到的,正因去除了人工斧凿的痕迹,这种“民族性”的表达才能如此质朴通透,浑然天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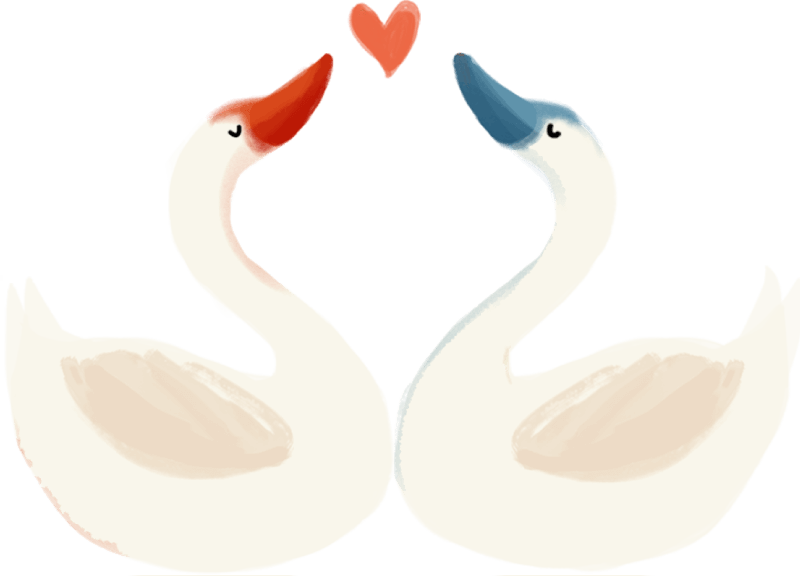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研究》2020年第2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