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琪峰曾经说,拍周星驰的电影,可以不需要自己这个导演。这是一句玩笑话,不过也说明了周星驰独特的表演艺术,是自成一体的,以至某种程度上不受导演和剧本的影响,反过来为影片预设了某种风格和基调。所以,就像影迷指认的那样,我们有理由命名一种“周星驰电影”,包括他主演和导演的作品,尤其是那些公认的代表作。
差不多二十年前,《大话西游》在内地刚火的时候,许多影迷学会了一句粤语“无厘头”,且被视为周星驰电影专属的美学标记。什么是无厘头,那些挤在宿舍对着大脑袋显示器前仰后合的大学生们,自然说不出个道道;不过京城里的先锋理论家及时提供了一个洞明世事的诊断,叫“后现代”。但什么又是后现代,就更加让人“不知所谓”了。二十年过去了,周星驰从星仔、星哥变成了星爷,在内地打破了一次又一次的票房记录,收割着一拨又一拨的粉丝,理论家早已不理会这个大众文化现象了。而当第一拨粉丝开始谢顶,在周氏喜剧中逐渐看出悲剧来时,终于明白,哪里有什么无厘头,哪里是什么后现代,周星驰电影的世界,根本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就是一群小人物,面对种种不甚如意的处境,左突右撞,捶胸顿足,装疯卖傻,又或破涕颜开的命运。无厘头中的逻辑性和我们的命运一样严丝合缝。这个逻辑,其实就叫作民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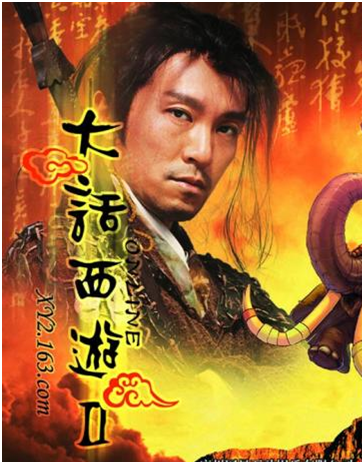
一
民间是什么样子?二十年前上海的文学评论家们发明的一些说法广为流行,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狂欢。据说民间就是一种狂欢状态,而这个词则意味着上下颠覆,群魔乱舞,藏污纳垢,当然也包括自由、活泼、本能、欲望等等。但是,这些说法恐怕寄托的是大都市文人们不安分的想像,与社会学意义上的那群人有关,但并不能等同。
周星驰的电影描绘的是后面这个民间,是形形色色的小人物,是小人物们的人生幻想。毫无疑问,这个幻想里有狂欢,有颠覆,但不是全部。不如说,这个被正经的理论家不屑的世界,流转的主题恰恰是正义、崇高、善良、英雄以及爱情。让我们仔细想想,周氏有哪部电影颠覆过人类的这些基本价值?没有。几部经典的公案戏如《九品芝麻官》、《审死官》以及《算死草》,赞美的不是正义吗?《回魂夜》里牺牲的Leon身上没有崇高吗?《新精武门》中因误以为打死师父而甘受惩罚的刘晶不崇高吗?此外,哪个80后没有接受过《大话西游》的爱情启蒙呢?哪个不是被朱茵在《逃学威龙2》中羞涩、躲闪的眼神打动过的呢?这里面哪里有价值的颠覆?
不如说,在先锋理论家眼中,这恐怕是一个正能量到乏味的世界吧。因为近几十年间的文艺界,流行一种美学潜规则,仿佛只有发掘出人性的黑暗,解构或混淆传统的价值,才足够先锋。某位经常上凤凰卫视的文学评论家甚至总结出一个金科玉律,说明确的是非观念是俗文学的标记。理论家的立场何以如此呢?因为颠覆恰恰代表某种资格,某种优势,不是谁人都行的。
颠覆从来是权势者的肆意,民间的价值观其实是趋向保守的。理论家们想像的民间,据说是发生在统治薄弱的地方,所以为自由或藏污纳垢留下了空间。这恐怕也是一厢情愿的想像。相反,藏污纳垢永远发生在统治最强大的地头,发生在大内野史,朱门青楼,以及VIP会所。颠覆价值的永远是意气风发随心所欲的权势者,是《世说新语》里的王谢子弟,是时尚领袖,因为这是他们与下层相区隔的标牌。所以,周星驰让《食神》中炽焰冲天的史蒂芬·周在西装革履的随从中独穿一件裤头出场时,丝毫不会令人惊讶。而民间,因为他们往往是被压迫与被损害者,是颠倒了的世界的受害者,是流行价值的负极,所以首先需要的不是解构和颠覆,而是小心翼翼的保守,保守住一点价值的防护衣,以免彻底沦为异类。

二
英雄是民间世界的另一个主题,但周星驰告诉我们,这个主题的意义远比我们想像的复杂。
《逃学威龙》是无厘头英雄形象的代表作。虽然片子的内涵不如其他一些作品丰富、厚重,但其精彩的构思最能体现英雄对于民间的意义与机制。这个飞虎队员假扮学生返回校园当卧底的故事所讲的,其实是一场高中生的青春期梦幻,它圆了青春期男生的所有梦想:帅气、聪明、英勇,还能征服美丽的女老师。但这个梦体现的是一种普遍的人格机制。
这个机制就如同皮影戏,英雄是线头上的剪影,现实是提线的演手。但是,从来不是演手在操纵皮影,而是皮影在引导演手。没有前头的剪影,提线的歌喉发不出高亢的心声。英雄的梦幻就是那个皮影,它为现实提供前行的想像。就如同在电影里,飞虎队第一杀手周星星是英雄,同桌黄小龟是相形见绌的小丑;而在电影外,黄小龟是众人的现实,周星星则是他们的梦幻。
《逃学威龙》所显示的这个英雄机制,在民间逻辑中具有普遍意义。英雄是民间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主题之一,民间传说中从来不乏英雄,因为他们最迫切地需要一个想像的剪影来指引他们卑微的当下。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正是士兵的真实心理机制。因为真正玩世界于股掌之上者,不再需要一个英雄形象来鼓动自己。将军们的梦幻,是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他们喜欢某种举重若轻,他们的目标是更轻,是隐士。英雄是属于民间的,是属于小人物的。所以只有最乡野的戏文,才喜欢三国水浒,喜欢云台二十八将瓦岗三十六友等等。
有些理论家说周星驰塑造的是“反英雄”,说明他们完全不了解这个英雄机制。在周星驰电影中,英雄从来是最强劲的主题。《逃学威龙》里的警员周星星是英雄,《武状元苏乞儿》里的苏察哈尔灿是英雄,《新精武门》里的刘晶是英雄,《国产凌凌漆》里猪肉佬特工是英雄,《少林足球》里的众师兄弟是英雄,《功夫》里的小混混阿星最后成了英雄。哪里有反英雄?
不过,理论家们创造的“反英雄”一词还是捕捉到了无厘头英雄的一些特殊之处。电影中的英雄某种意义上是现代都市的产物,是都市中产者们的梦幻剪影,是他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处境的对应物。因为只有中产者既有受压制激发英雄梦的动机,也只有他们才能回头比比落跑者不断地确认和培育这个梦。007电影就是这些都市中拘谨卑微的男性们的梦幻,一个可以持续滑入持续沉睡的梦幻。持续沉睡是说,现状总是坏到让他们生发英雄梦幻,又没有坏到让梦惊醒过来。梦幻的发生,需要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某种平衡。

三
但对小人物而言,最不易维持的恰是这种平衡。所以,英雄梦幻对于民间,就具有了正负两种可能的效果。除了正面的引导和催眠,它还能成为一道强光,一面照妖镜,愈发照见现实的不堪。这是民间的英雄梦的复杂之处。
而且,英雄的梦幻需要不断的滋养,不断的自我催眠。要维系英雄梦,民间文化有两件最常用的法宝。第一种,有学者称之为“机智”。机智不是一般所谓的智慧,而是周星驰电影中整蛊专家、扭计祖宗式的智慧。机智人物是民间文化中的一类光彩夺目的形象,阿凡提是最为人熟知的代表。这类“机智人物”是生活中的弱者,却是精神上的强者,他们最善于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戏弄或战胜现实中的强者。机智人物是民间自我肯定的一种方式,它不是“卑贱者最聪明”式的盲目自恋,而是对自身现实的情形判断——民间的卑贱地位不是由于“我很蠢”,而是“我没有办法”。所以机智的重心,是发现高贵者的愚蠢,利用他们的漏洞;机智发挥的途径,则往往漠视高贵者们的通行办法。前者在周星驰电影中的经典例子,莫过于《九品芝麻官》中包龙星诱使常威承认罪行;后者的例子则比比皆是,比如包龙星通过和人吵架习得了判案辩护的嘴上功夫,《算死草》中陈梦吉建议酒楼老板表演跳楼来揽客,《唐伯虎点秋香》中唐伯虎以夸张的自残博取华府的同情,或《国产凌凌漆》中用色情录像带代替疗伤的麻药,等等。喜剧人物形象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卑微,更在于他们的机智。卑微对应着观者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机智则寄托着观者的自我肯定和超越的希望。
民间英雄梦的第二件法宝,我想称之为“传奇”,即对某种奇迹的狂想。对奇迹的嗜好在民间文化中根深蒂固,绝非没有来由。当现实与理想之间有道路可通达时,或者至少能让人看到这条道路时,人不会陷入狂想。比如,某种意义上农民和中产者都不会陷入狂想,他们能看到自己的努力与成效,所以农民相信人勤地不懒,中产者相信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对于他们,狂想是种有害的东西。但对于那些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看不到任何通道的人,狂想就成了支撑梦幻的唯一条件。所以民间文化喜欢传奇,喜欢天降仙女,喜欢树落金子;周星驰电影中的小人物,也各有各的特异功能,《赌侠》和《赌圣》中的阿星有天眼通,能看穿底牌,《新精武门》中的刘晶右臂天生神力,《少林足球》中的众师兄弟各有绝学,就是这个道理。
但这两件法宝,不足以支撑英雄梦的平衡。一旦平衡打破,英雄梦幻对于小人物,就不再是种引导,而是一种逼视,愈加显出他们的卑微,这样,英雄梦也就变成了恶梦。于是,抵制英雄梦幻的诱惑,甚至铲除英雄梦幻的苗头,就是一种非常必要的防护措施。这才是周星驰电影中反英雄的真实含义。反英雄不是指拥抱英雄的反面,不是像理论家有时候用“审丑”所说的那样。不,它绝不是某种天生或自甘沉沦的癖性。反英雄的根基仍然是英雄崇拜,它是英雄崇拜的副作用,是对所有那些成不了英雄的人、所有超越现状的努力的否定、嘲讽甚至仇恨。
电影有两种方式呈现这种对英雄的抵制。一种方式由配角形象来承担。周星驰的电影中塑造了一系列形象生动的配角,比如如花、酱爆、吹箫萍、达文西、阿欢、龅牙珍,以及周星驰的黄金搭档吴孟达出演的无数角色。但他们的功能不是直接现“丑”。电影要呈现的,不是他们丑,而是要呈现他们想变美的笨拙与无效,暴露他们要超越的努力及其夸张的失败,它要观众一起嘲笑他们的失败,嘲笑他们的努力。《少林足球》中安排了一场戏,让众兄弟肆意地嘲笑阿梅的化妆效果,就是导演对这个意图的表白。在这种方式中,主角与配角往往承担不同的功能,主角是英雄,或最终会成为英雄,配角不只是凡人,而是成为英雄之路上的失败者。
这种主角和配角之间的关系,用王晶导演的行话,就是上把和下把的关系。但上把和下把也可能由主角自己一身二任,周星驰所有的英雄形象往往都是上下把并存的。《国产凌凌漆》作为对OO7系列电影的解构,就是最精彩的一个例子。凌凌漆既是英雄,也是一个时常出糗的猪肉佬;它不会用枪,但将切肉刀能运用到出神入化;它是大隐隐于市的特工,但也是一个付不起过夜费的无赖。人物形象上的矛盾导致整个故事像一段不断被插入了包袱的单口相声,叙述的条理不时被打断。但这正是无厘头英雄的复杂之处,即一边是对英雄梦的渴望和放纵,一边是对英雄梦的恐惧和拒绝,反英雄们实际上徘徊在沉入梦幻与抵制梦幻之间。

四
使得民间的英雄梦幻如此纠结的,是来自现实的障碍。这个障碍除了生存条件的种种匮乏,还有来自权势层的压迫,包括文化上和心理上的压迫。对于民间而言,如何在现实中克服这种压迫是个难题,如何在心理上克服这种压迫更是个绕不开的难题。周星驰自己导演的几部作品中,这个主题一再出现,萦绕不去。它既是周星驰的某种个人情结,也是民间文化的一种潜意识,一种无法回避的困扰——是去超越自己被压迫被侮辱的境地,还是超越这个压迫结构本身。
在周星驰自己导演的作品如《国产凌凌漆》、《喜剧之王》、《食神》、《少林足球》、《功夫》,包括近来的《美人鱼》、《新喜剧之王》,以及陈嘉上导演的《武状元苏乞儿》中,这个困扰的主题一路贯穿了下来。导演让主角经历命运的大起大落,仿佛就是对这个问题中各种立场各种可能的探索。而周星驰电影的伟大,正在于它选择了后一个立场。《食神》中,如日中天的史蒂芬·周飞扬跋扈,却遭到他人嫉恨身价败落,流落庙街的小食摊。在他带领街坊再次打拼事业的过程中,才又寻回了良知与初心。《功夫》中的小混混阿星,平日受尽他人欺凌,所以一心想加入斧头帮,可是一路阴差阳错,终于改邪归正,成为真正的英雄。《武状元苏乞儿》的经历更是当得起周星驰的经典台词,“人生的大起大落太快,实在是太刺激了”。纨绔子弟苏察哈尔灿为了一见钟情的女子一句戏言——她的夫君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武功盖世,状元之才”——去考武状元,却被贪官陷害,沦为乞丐,不料却成了丐帮帮主,最后选择行乞人间。这些都是对那个压迫结构的真正超越。
对压迫的超越,也意味着对自己出身阶层的认肯,和向这个共同体的回归。周氏的电影塑造了许多充满温情的民间共同体,比如《行运一条龙》中的行运茶餐厅,《龙的传人》中的大澳,《食神》中的庙街,《功夫》中的猪笼城寨等等。这里不只是小人物们日常揾食的环境,也代表着一个有人间温情的家园。周星驰的电影中的主角,经过逃离、失败,和更高层次的领悟,最终回到他们的这个出发点。就像《食神》中,斯蒂芬·周最终认识到,真正的食神不是权势,而是善良。这是民间艰难的自我确认。
当年读大学时,经常听文化人讲,香港是个文化沙漠,言下之意是香港没有高雅的文艺。估计周星驰的电影在他们眼中也只能算这沙漠中的一堆沙丘吧。我不了解高雅的文化什么样子。不过我发现,与周星驰同龄的内地电影人,拍的人物是和他们自己的身家一路高升的。拍农妇起家的,最后拍起了帝王将相;拍胡同串子的好梦一日游的,最后只玩私人订制;拍小偷起家的,最后一定要拍跨国资本家。周星驰,无论当主演还是导演,几十年间始终在上演小人物的卑微与传奇,慰藉着一代又一代的影迷和粉丝。那么,就让这样的沙漠,能沙化得更广阔些,更永恒些吧。

作者像
胥志强,文学博士,八零后青年学者,现任教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民间文学教研室,在《民族文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原文刊载于《文学教育》2020年第6期下旬号,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图文来源:微信公众号“文学教育”2020-06-05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