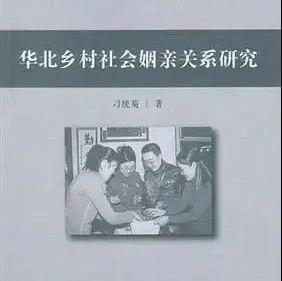



在汉人亲属关系的研究中,研究者更重视对宗族的研究,对姻亲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在研究路径上,对姻亲关系的研究整体上也仍采取宗族研究的范式路径,多是从男性视角来分析姻亲关系对于两个建立了联姻关系的父系家族(庭)的政治、经济、宗教意义,而忽视了女性在姻亲关系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及这种关系之于她的意义。基于对这一研究范式的反思,一些研究者从女性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女性的亲属关系,发现了女性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例如,李霞延续了玛格丽·沃尔夫(MargeryWolf)的研究路径,从女性的视角重新审视乡村女性及其亲属关系实践。从性别视角来看,以上两种研究范式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前者在制度的框架下暗含着男性的视角,强调女性的依附性;后者则从实践出发发现了女性视角,强调女性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在性别的天平中,二者分别走向了两个端点。刁统菊的《华北乡村社会姻亲关系研究》(以下简称《姻亲关系》)一方面承袭了宗族研究范式,另一方面与以上两种研究路径都有所不同。《姻亲关系》跳出了直接的性别视角,借由基于田野调查的民俗志的方法,从家庭的视角与日常生活实践的视角切入到对姻亲关系的调查与研究之中,在父权制的亲属关系结构中发现了女性,显示华北乡村女性在乡土社会的民俗规制中的与在实践中的姻亲关系中的位置,这对乡土社会的亲属关系研究而言,还是对女性民俗研究而言,都具有启示性。

▲ 《华北乡村社会姻亲关系研究》

一、在父系亲属结构中发现女性
基于田野作业的民俗志的方法是《姻亲关系》所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作者在两个层面上实践民俗志的概念:首先,同时兼顾民俗志描写的区域(华北乡村)与事象(姻亲关系),在铺开“面”的广度的基础上,注重对“点”的深度的把握;其次,从村民的视角出发进行描述,“力图通过本地人的行动和语言去透视隐藏在其身后的动机,尽可能接近当地人的生活实际”。
从村民的视角出发来进行民俗志写作并非易事。本书的民俗志书写至少从两个方面保证了作者的写作视角接近村民的视角。一方面,作者的主要田野点为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红山峪村,而作者的家乡为滕州市。山亭区与滕州市同属于枣庄市,两地毗邻接壤,文化趋同。另一方面,本书描写的一个主体是嫁女的生活经验,作者的已婚身份使她与她所描写的“嫁女的生活经验”相融合。这两个方面——与受访者有共同的乡土文化背景和相似的嫁女生活经验——使得作者的民俗志写作具有强烈的局内人特征,从而保证了作者的民俗志写作更接近于当地人的生活逻辑,也使得其民俗志描写具有了局外人难以企及的深度。
借助于这些来自于田野的、接近于当地人的生活逻辑的深度民俗志描述,我们得以看到《姻亲关系》对华北乡村姻亲关系习俗及习俗实践的充分描述。而正是在这些描述中,我们发现了传统的父系亲属结构中女性所处的位置。
例如,在第一章以“通婚圈”为中心的描述与分析中,作者主要描述的是适婚女性及其父母对通婚村落的物理距离与社会位置的考量与选择。在这场“女人的交流”活动中,较之娶儿媳的父母,嫁女的父母更关心通婚村落的物理距离与通婚村落的社会位置。第二章和第三章对姻亲关系的仪式性表达的分析暗线实际是女性婚姻缔结及其生命历程,从中可以透视华北乡村女性在亲属关系中的位置、身份角色的变化以及她与婆家/娘家关系的实质。从习俗的角度来看,婚礼、回门以及回门之后的送节仪式标志着外嫁的女儿与出生家庭的关系从“女儿”变成了“亲戚”;生育以及生育仪式最终确立了外嫁的女儿在婆家的身份以及娘家之于女儿的小家庭的责任。而丧礼举行时婆家人与娘家人的互动,体现了娘家人对外嫁女儿的关切之情的再次确认。第四章对婚姻偿付制度的描述与分析中,着重讨论了缔结姻亲过程中与嫁女息息相关的嫁妆的实践过程。作者指出,嫁妆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与女子在受妻集团的生活息息相关。在其婚姻生活中,嫁妆是属于女性的绝对财产,它还为女性创造了独立空间。第五章则集中分析了嫁女的身份归属问题,着重分析了嫁女与娘家的关系,试图“通过父系宗族制度、嫁女、姻亲关系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来理解嫁女与娘家的关系,强调的是将嫁女置于亲属制度体系和姻亲交往的动态过程之中来理解她所处的地位”。为实现这一目的,作者详细描写了嫁女的亲属关系的特点(以结婚为界限分为两个阶段)、嫁女与娘家的仪式往来与日常生活实践(回娘家)、嫁女的身份归属(娘家人还是婆家人?)等。第六章对姻亲关系对家族组织的作用与影响的分析中,其中分析了姻亲之于家族组织的离心力作用。尽管其着眼点在姻亲与家族关系,但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却很大程度上呈现了女性在娘家与婆家家族互动过程中的位置。
尽管作者描述与分析的着眼点被集中于家庭视角之下的给妻集团与受妻集团的姻亲关系实践,但综合以上内容,在其细腻的民俗志描述中,我们仍然能感受到其中暗含的“嫁女的生活经验”,并较为清晰地看到了作为姻亲关系形成之媒介的女性在其姻亲关系结构中的位置及其亲属关系实践。正是这一过程,使我们在父系的亲属关系结构中发现了女性。这改变了传统亲属关系研究中对女性的忽略状况,对于过去以男性为中心的亲属关系(包括姻亲关系)研究范式(男性视角与男性主体描述并重)是有力的范式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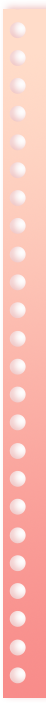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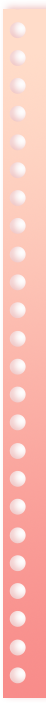
▲ 农村婚礼

二、在第三种视角下理解女性
及其日常生活实践
跳出亲属关系研究来看,在父系亲属关系结构中发现女性还有另外一层重要意义,那就是它揭示了在相对单一的男性视角或者女性视角之外理解女性的日常生活的可能性。
新时期研究者更强调从女性视角出发、从微观层面上揭示女性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例如,新妇女史研究者致力于在文献中发现女性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女性主义人类学学者试图在田野中凸显父权制框架下女性的主体性与能动性。
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作为行动者的女性,其主体性与能动性的发挥是受当下的日常生活实践情境及其过去的生活经验积淀制约。在父权思维模式仍结构性地影响着大多数人的思想和行动的今天,人们过去的生活经验积淀都或多或少地隐含着对父权制观念的内化,因而,研究者对作为行动者的女性当下日常生活实践的考察,也必须嵌入到对女性个人生命史的解读中去了解在其生命历程中内化了哪些父权制的观念才可能更接近于行动者的日常生活逻辑。如果不注意那些被内化了的传统父权制观念对作为个体的女性当下的行动的影响,孤立地在女性视角之下强调或者放大女性的主体性与能动性,无助于认识女性日常生活诸多面向的内在关联性,也丧失了在宏观的社会结构中审视女性的位置的机会。
综合以上,与从女性视角出发强调女性的主体性与能动性的研究路径不同,《姻亲关系》回避了或者说跳出了直接以女性视角作为立足点的亲属关系分析模式,而是从家庭视角和日常生活实践视角切入华北乡村社会以女性为媒介所建立的姻亲关系及其实践,以第三种视角在传统父权制的社会结构中理解女性及其日常生活实践。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认识乡村女性在父权制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位置实践的第三条路,客观上是对强调女性视角以及女性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研究范式的补充,抑或说是某种程度的矫正。使我们得以在父系亲属结构中发现了女性,从而弥补了在制度化亲属关系研究中对女性关注的不足;这也许并非《姻亲关系》的主要追求,但它于女性民俗研究而言,却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女性民俗研究的更多可能性。

本文刊载于《东方论坛》2017年第6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