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地方性知识是指各民族的民间传统知识,其使用范围要受到地域的限制。通常的科学研究虽然也会接触到地方性知识,但是很少将其作为主要的研究内容。文化人类学及其当代分支学科——生态人类学则不然,它不仅高度关注各民族的各种地方性知识,而且致力于发掘、整理和利用地方性知识去开展生态维护。这样的研究取向容易引起世人的误解与责难,也因此造成了地方性知识保护与利用的困难。为此,文章列举我国各民族中一些有代表性的地方性知识事例,说明它们在生态维护中的特殊价值,借以重申生态人类学关注地方性知识的深层考虑。
关键词:生态人类学;地方性知识;普同性知识;生态维护;生态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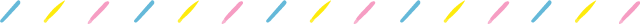
生态人类学高度关注地方性知识,是因为地方性知识在维护人类生态安全上,可以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提到生态维护,人们总是习惯于单纯动用技术、法律、经济或行政的手段,去完成既定的维护目标。然而类似的手段只能在特定的时段内,解决某些局部的生态维护问题,这远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原因在于人类的生态安全是一个全局性超长期的复杂问题,人类日常生产与生活中的一切活动都与人类的生态安全直接或间接相关联。维护人类的生态安全当然需要各种工程维护措施,但更需要的却不是单一的对策,而是协调一致的可持续社会行动。协调的社会行动又只能建构在并存的各种社会行为之上。为此,生态人类学的研究任务正在于,搜集整理不同人们群体的社会行为资料,辨析梳理不同人们群体的社会行为特点,分析归纳各种社会行为造成的不同生态事实,探索总结不同生态事实的各种生态后果,并以这些研究为基础,进而探索人类社会存在的生态意义与生态运行规律,从中找出人类社会在地球生命体系中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方式,以便更好地维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

人类的社会行为始终受到各种知识系统的规约和引导,除了普同性知识外,各民族各地区的地方性知识,一直在潜移默化中规约和引导着不同人们群体的社会行为。把握了一种地方性知识,也就获得了预测和引导特定人群社会行为的能力,凭借这种能力自然不难运作该社区的社会行动。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将社会行动引入有利于生态维护的轨道上去。生态人类学主张凭借地方性知识去推动生态维护,其理论依据是地方性知识必然是特定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民族文化固有的综合性和可自主运行性,地方性知识自然也会具有同样的秉性。于是地方性知识规约下的社会行动,同样会具有至关重要的自主运行和综合作用秉赋。这就使得有利于生态维护的社会行动一经正确启动,即使没有外力支持,也能自行运作,综合发挥多种作用,不断地收到生态维护效益。
鉴于生态系统的高度复杂性,生态维护的办法自然也需要多样化,并具有必要的灵活性,才能确保生态维护成为全方位的并相互协调的人类社会行动。为了使维护办法尽可能多样化,这就必须发掘和利用各种地方性知识,使我们拥有尽可能多的生态维护经验与技能,并如实地了解这些经验与技能的利弊得失。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建构起全方位的生态维护体制。有了这样的体制,即使遇到生态维护失误,或碰到不测的生态变故时,我们也才有可能灵活地选用不同的对策,加以有针对性的补救。为此,生态人类学正在努力探明各种地方性知识及其存在与延续的前提和范围,辨析不同的地方性知识作用于不同的生态系统时,会造成哪些不同后果,以便对不同的地方性知识作出准确的使用价值评估。只有奠定了这样的认识基础后,我们才能进一步弄清各种社会行为聚合为社会行动的机制,协调一致的生态维护体制也才可能建成。与此同时,各种地方性知识与普同性的技术、法律、经济或行政手段的结合也才能作好。因此,只有珍视各种地方性知识,最大限度地发掘与利用并存的各种地方性知识,人类社会才可能获得真正的生态安全。
不言而喻,生态人类学全面发掘和利用地方性知识,大力推动地方性知识与普同性知识有效结合的研究任务,是一项超长期的艰巨使命,这应当是生态人类学研究的长远目标。在短期内,生态人类学还做不到这一步,但是却可以就特定地区的某些地方性知识,进行系统发掘和利用,并在促成与普同性知识结合的前提下,使这些地方性知识获得在一定范围内推广的可能,使其发挥更大的生态维护效益。这是生态人类学近期内可以实现的研究目标。总之,不管在近期还是在远期,地方性知识在生态维护上肯定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其独特性归纳起来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地方性知识具有不可替代性。一切地方性知识都是特定民族文化的表露形态,相关民族文化在世代调适与积累中发育起来的生态智慧与生态技能,都完整地包容在各地区的地方性知识之中。地方性知识必然与所在地区的生态系统互为依存,互为补充,又相互渗透。相比之下,普同性知识则不可能具备如此强的针对性。若能凭借生态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系统发掘和利用相关地区的地方性知识,肯定可以找到对付生态环境恶化的最佳办法。如果忽视或者在无意中丢失任何一种地方性知识,都意味着损失一大笔不可替代的生态智慧与技能。
其次,发掘和利用一种地方性知识,去维护所处地区的生态环境,是所有维护办法中成本最低廉的手段。地方性知识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与当地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当事的个人在其日常活动中,几乎是在下意识的状况中贯彻了地方性知识的行为准则,地方性知识中的生态智慧与技能在付诸应用的过程中,不必借助任何外力推动,就能持续地发挥作用。由于不必仰仗外来的投资,而是靠文化的自主运行去实现目标,因此这是一种最节约的生态维护方式。
最后,地方性知识具有严格的使用范围,这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维护方法的误用。地方性知识之间总是处于相互制衡格局之中,这样的制衡格局又必然是并存多元文化交互依存、交互制约的派生结果。地方性知识的制衡格局可以确保人类社会对地球生命体系的冲击均衡化,从而大大降低人类社会对生态系统的干扰。在这样的制衡状况下,维护方法一旦被错用,就会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牵制,及时得到纠正。同时,利用地方性知识去维护生态安全,既不会损害文化的多元并存,也不会损害任何一个民族的利益。因此它是副作用最小的稳妥维护办法,也是不容易被用错的维护办法。

生态人类学得到学术界承认前,人们习惯于认为,生态维护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离开了现代高新科学技术的指导万难生效。按照这样的维护思路,各民族的地方性知识自然被贬低为无补于事的雕虫小技,甚至被看成愚昧落后的历史垃圾。可是我国半个世纪的环境救治经历,却对我们的救治办法不断地提出质疑。反省半个世纪的努力,我们不得不承认,不少环境救治工程采用的恰好是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有的还是高价从国外请专家指导施工完成的。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工程,也大多没有达到预期的治理目标。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不少工程技术人员也不得不承认,我国多年来防治沙漠化的努力,仅仅是“局部好转,全局恶化”。耗费巨资兴建的大中型水利工程,竟然由于水土流失而损失了一半的有效库容。
类似的失误不是科学技术的过错,而是生态维护的思路有失偏颇,没有看到地方性知识的不可替代价值。其实就在这些工程兴建的相关地区,早已并存着发掘利用并不困难的各民族地方性知识。遗憾的是,当事人一直没有意识到应该提供一个机会,让这些地方性知识发挥作用,以便提高生态维护的成效。
生息在我国西南水土流失敏感地带的侗族、水族、苗族、土家族,其传统的治水治土办法是,在陡坡地段预留一到三米宽的水平浅草带。靠这样的浅草带去降低山坡径流的速度,截留顺坡下泄的水土,实现了重力侵蚀严重山区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除了防止水土流失外,这种办法还有四重好处:一,可以形成小片牧场,放养家畜家禽。二,可以构成防火带,保护森林、农田和村庄免受火灾的威胁。三,由于这样的浅草带会自然生长,因此无需额外投资维护,一经形成就可以持续生效下去。四,这样的浅草带还丰富了生态构成的内容,形成了多样化的生态景观,可以支持更多种类的生物生长繁殖,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维护。其成效持续而稳妥,并不比任何高精尖工程逊色。
不幸的是,多年来的生态维护工作,一直没有认真地发掘和利用类似的地方性知识,致使维护工程投工大而收效差,个别特殊地段还可能导致灾难性悲剧。2003年7月,湖南省永顺县永茂镇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山体滑坡,不仅村庄被泥石流掩埋,焦柳铁路也因此中断了一个多月。事后人们都认定这是一次纯粹的自然灾害,其发生具有不可抗拒性,就是不愿深究其发生的人文社会原因。然而类似的特定地段在我国西南地区还很多,若不从中吸取教训,同样的假性自然灾变还会频繁地发生。
永顺县发生山体滑坡的地段,是新生代强烈地质活动形成的重力侵蚀敏感地带,风化后的砂岩和页岩与石灰岩碎片混合成松散的泥石层顺坡堆积。这样的松散泥石堆积一怕上方重压,二怕下方地下水水位升高。前者会加大重力侵蚀的强度,诱发大面积的山体滑坡批;后者则会在基岩与泥石层之间形成滑动带,使泥石层山体更容易成片滑落。当地土家族对付类似特殊地带的传统做法包括四个要点:一,将这样的松散泥石层用作刀耕火种的烧畲地,或用作牧场,以便降低地表植被的自重,防止重力侵蚀强度加大,同时避免植被的根系将泥石层的表面连成一体,导致成片的山体大滑坡。二,对山谷底部的河流决不壅塞,而是就地取材用鹅卵石构筑低矮的半坝,引导流水绕过泥石层下缘,既避免流水切割泥石层,又巧妙地利用了流水的回流作用,将洪水季节携带的泥沙淤积在泥石层的下缘,以此提高泥石层的稳度。三,在泥石层的上方绝对禁止建立村庄及其他比较重的固定建筑,以免加大泥石层的自重,诱发山体滑坡。四,对那些已经松散的泥石区段,则不加维护,任其有限地自然滑落,甚至用人力促成其滑落,既做到有控制地减轻山体自重,又避免了泥石的突然滑落而造成灾害性后果。应该看到,这四项办法是对付大面积山体滑坡的最佳模式,是地方性知识独特价值的集中体现。若能延续上述做法,悲剧本来可以减少或避免。然而,近五十年来发生的事情,却背离了这些地方性知识的生态维护原则。
泥石层的上方,牧场陆续改作了固定农田,休闲烧畲地也陆续改成了固定农田,为了方便就地耕种,村民们开始在这里建筑临时住所,随着农田的落实到户,放牧不得不全面禁止。与此同时,由于这里土层深厚,气候温和湿润,不能开作农田的地段,以及弃耕后的农田和牧场,在得天独厚的自然背景下,迅速发育成繁茂树林。但是这里地势太高,生活水源不足,干旱季节难于久住。不就地居住耕种,投工太大,成本太高,做固定农田使用并不合算。国内粮食供应一旦宽松,村民们就陆续放弃这些边缘的耕地。一经放弃,不久就自然成林。到了全国退耕还林时,耕地全部放弃,人工种植树苗。几年后,整个泥石层顶部发育成了茂密的森林。乔木强大的根系把泥石层顶部3~5米深的松散泥石连成一个整体,随着乔木的生长,顶部整体自重与日俱增,泥石层头重脚轻的局面就此形成。在重力和风力的合作用下,笨重的顶部还以整体的形式,不断地震动下方松散的泥石层,整个泥石层与基岩的结合开始全面松动,造成山体滑坡的隐患。
由于这里的透水层太厚,基岩又向河床倾斜,位于泥石层下缘的村庄周围没有理想的打井位置。为了解决旱季用水的困难,村民们又在河床上修了个水库。饮水问题虽然得到解决,但却埋下了成灾的伏线。一方面水库提高了地下水的水位,使泥石层下部更加松软,并在基岩与泥石层之间形成一个滑动层。在重力的作用下,泥石层的下部开始沿着倾斜的基岩缓慢地下移,整个泥石层的基础随之动摇。再一方面,水库修成后河水的流向发生了改变,不再绕过泥石层的下部边缘,而是直冲泥石层的根基,逐步切割了泥石层的基础。近年来兴建的公路、铁路又切割开泥石层,于是大面积的山体滑坡就在所难免了。总之,这是一次掩盖在自然灾害背后的人为灾变。人们在不经意中贬低了地方性知识的价值,忘记了土家族世代积累的生态智慧与技能,才遭到了大自然的无情报复。灾变中虽然殃及无辜,但却不能全部归咎于大自然无情。
利用地方性知识维护生态安全,在发挥效益的同时到底需要多大的投入,学术界一直没有人认真作过统计。其间的原因很复杂,一则,地方性知识总是与特定民族文化融为一体,作用于生态维护的具体投入由于无法剥离,也就难于加以统计。二则,这样进行的生态维护是一个无间断的持续过程,其间的投入与产出也具有连续性,致使统计取样的时段与范围用常规的办法难于界定,规范的数据也就无从获得。三则,这样的投入游离在有意识的政治、经济行动之外,因而从有意识行动的角度出发,很难注意到它的存在,也就无法加以统计了。四则,主持有意识的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的人为了突出自己的成绩,不情愿看到这种客观投入的存在,致使在常规的统计中看不到地方性知识的生态维护投入。所幸的是,如下两个实例由于情况的特殊,地方性知识的投入可以得到突出的展现。在这两个实例中,常规的生态维护与地方性知识的生态维护起步时两种投入并存,其后常规的维护方法久不生效,或是工程量太大,由于难以实施而主动退出,任凭地方性知识去独立运作,致使地方性知识的生态维护投入变得可以直接估算。结果地方性知识的办法取得了全面的成功,两者投入的鲜明反差才得以体现出来。
贵州省毕节地区金沙县平坝乡是一个苗族山寨,由于对土地资源长期的不合理使用,导致了土地的石漠化。全乡70%以上的土地都是裸露的基岩,或是覆盖着碎石,乡民们只能在石缝中种植玉米和洋芋勉强糊口。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自从20世纪50年代原生植被遭到破坏之后,这里也曾多次植树造林,造林办法也是按照同一的模式,但因土地的高度石漠化,种下的树苗只有极少数成活,而且这些侥幸成活的树苗总难以长大,经过二三十年,这些残存的树依然只有1米多高,被人戏称为“老头树”。20世纪80年代后期,毕节地区为了贯彻实施“天保”工程和“长防”工程,特意邀请林业专家对该乡的林地做了评估。专家认定的结论相同,该乡现有林地是一片残林,必须实施全面更新,才能恢复达标的森林。他们要求将林地全面挖翻清理,移开碎石修筑保坎并填土建成梯土后,再行定植树苗。按照这样的规划,种植一棵树的代价需要数百元。贵州省省、地、县三级均无法筹集这笔巨额资金,也没有人敢于承包林地更新工程。这一残林更新工程也就一拖再拖地被搁置下来。

该乡乡民杨明生时任该乡党委副书记,主动要求更新残林建设家乡。他的条件仅是要乡政府为自己作保,批准他借贷一笔资金,暂时解决造林人员的生活困难。有关部门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自然顺水推舟让他带职造林。但是事情并不顺利,造林工程一开始,杨明生就与林业专家因意见不合而发生了争执。因为杨明生的造林办法对于林业专家来说,简直是闻所未闻,由于大家都没有把握,因而害怕他造不成林,还不了贷款。于是大家出于好心,多次出面劝阻,甚至不同意让他继续干下去。但杨明生却胸有成竹,依然硬着头皮干到底。
而今,杨明生所承包的残林更新任务已经全面完成,他确实在岩缝中种出了参天大树。其造林办法的特异之处如下:一,既不清理林地,也不挖翻土壤,而是在已有残林中相继移栽野生的草本和藤本植物,作为以后苗木定植的基础。二,既不建苗圃,也不购买苗木,而是从周边已有树林中,选择林下的各种合适的幼树苗进行移栽。三,移栽时完全不清理定植点的原有植被,而是在灌草丛中直接开穴定植,树苗移栽后完全隐藏于灌草丛中。四,对原先无灌草的石漠化地段,则不惜工本移开碎石,或是人工填塞土壤,先撒播草种,或移栽灌木。待草类长大后,再定植合适的苗木。五,随着树木的生长,待树冠超过灌草丛后,才及时相继清理灌草丛,割去喜欢阳光的植物,留下耐阴的植物。而且仅仅割去植物的上半部,留下半米的残段,目的是让它们继续发挥截留水土的作用。六,割下的灌草和落叶不焚烧,与泥土混合后,填入低洼的石坑中,作为日后定植新的苗木基础。正是这套植树育林办法,遭到了专家的质疑,他们规劝杨明生不要白费力气,最后造林不成无法还清贷款。杨明生事后告诉我们:树与人一样,没有伙伴活不了也长不大。杂草灌丛就是树的伙伴,把它们清除之后,孤零零的树苗就肯定长不好。
杨明生取得成功之后,有关他的事迹报道频繁出现在各级报刊中,但撰文的记者却很少正面提到他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人们很少提到,他运用了自己了如指掌的地方性知识,更少有人指出苗族的传统生态技能在其中发挥了作用。而这些传统知识正集中体现于上述六项植树造林办法之中。苗族的生态技能是什么,杨明生可以总结如下:一,利用植物的残株落叶截留水土,富集可供林木生长的土壤,同时为日后定植的树苗提供庇护。二,从已有树林中移栽树苗,则解决了当地适用树种的汰选难题。三,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要领是,他的造林并不是一次性完成,而是分多次进行,凭借自然力不断优选出可以成材的植株来。四,整个造林过程并不局限于原先拟定的规划,而是顺应自然,与具体的自然背景相契合。因此,当地苗族的传统生态智慧就集中体现为对自然生态背景的认知和尊重,为树木找寻和营建适合其生长的最佳条件,而不是简单要求自然顺从人类的意愿。
这一成功实例中,苗族乡民到底付出了多大的人力物力投入,显然无法明确计算。我们只知道,杨明生当年仅贷款20多万元就完成了造林任务。但若按专家的残林更新规划,那么杨明生完成的这片林地更新所需的投资总计得耗费数百万元以上。两相比较,苗族居民按传统知识所完成的造林任务资金投入量还不到专家规划的十分之一。而且,杨明生所借贷款主要是用于日常生活开支,而很少用于原先造林规划中必须包含的苗木购置、林地整理和技术指导等费用。由于两者资金投入的统计办法完全不同,要准确计算杨明生的造林办法到底省下多少费用并不可能。但这一实例本身却可以明确告诉我们,用传统办法造林在这一特殊地段所需资金投入远远低于任何一种其他造林办法。
甘肃省黄河南岸的秦王川目前正在规划新建大型的提黄灌溉工程,计划将这一片地区改造成粮田区。需要提到的是,当地的各族居民在秦王川地区依靠砂田进行种植。营建一亩砂田需要500~800吨的砂石,因而砂石的搬运量较为可观,但砂田一旦营建之后可以持续耕作数十年。因此平均下来,人们每年在砂石搬运上的劳动力投入并不算大。而兴建提黄工程情况则大不一样,除了工程投资之外,每年提水所耗费的电费平均到每亩必然高于砂田的兴建费用。若再加上购买水资源的费用,其实际的投入费用更是大大高于砂田办法。此外,在这一地区实施漫水灌溉方法种植会引发盐碱化等许多生态恶果。两相比较,当地居民采用传统办法实施的砂田种植办法同样比兴修工程的办法来得划算。因此在我国西北地区保持和推广这一传统办法依然是有利可图的举措。
发掘利用地方性知识进行生态利用和维护,其最大长处还在于它不容易导致维护办法的误用。任何地方性知识都是针对特有自然地理环境和生态资源,建立和完善起来的专属性认知与应用体系,离开了这些特定的自然环境条件,地方性知识就会失去原有的效用。因而生搬硬套地方性知识注定会很快曝露其缺陷,并较早引起当事人的警觉,从而得到及时的矫正,错用地方性知识的事例也就很少发生了。我国云南哀牢山区哈尼族的高山梯田水稻种植办法,只适用于面向海洋的高海拔迎风坡地段,离开了这些地区,就根本无法建构类似的高山梯田。其他地区的各族居民当然也就不会照搬哈尼族的做法了。再如,我国彝族对猪也采用野放的方式喂养,并利用猪食性广的特点,去控制牧场中某些恶性杂草的蔓延,这种做法仅适用于温暖潮湿的缓坡谷底。而这些地段主要分布于滇黔桂三省比连地区,因此也不会为其他民族所误用。相比之下,普同性知识指导下的生态利用和维护,却经常发生被误用的情况。
一个值得反复重申的教训是,在已经石漠化的地段强行开辟梯田并不是正确的做法。从农田种植的常规上看,在山区开辟梯田是一种普遍认同的做法,也是有利于水土保持的对策。由于受到普同性知识的引导,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国外,山区种植大多仰仗梯田。但是应当清醒地看到,客观存在着诸多例外情况。比如,在温暖潮湿的喀斯特山区,如果地表已经高度石漠化,那末修筑梯田肯定会贻害无穷。其原因在于:一,在这样的地段基岩间缝隙极多,施工兴建梯田时一旦松动了基岩,土壤和水源会更容易地顺着这些缝隙下渗,进入地下溶洞和地下伏流,从而导致更为严重的水土流失。二,在石多土少的情况下,修梯田主要的工程内容是石方建筑,还需要大规模地长途找土运土进行铺填,修筑的梯田才能勉强种植。兴建一亩梯田的代价十分高昂,而效益又不明显,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根本没有推广的价值。三,这样营建的梯田由于需要从石缝中掏土铺田,将会导致周边地区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残存在石缝中的泥土被掏去后保水保土能力进一步丧失,周边的地段将真正成为不毛之地。而所建构的梯田却类似于一些大型花盆,它与周围环境的物质能量交流被人为切断,因而无法保证这些梯田的稳产。四,由于梯田周边地带的生物多样性严重受损,这些孤立的梯田将会成为各种病虫害滋生的温床,若不仰仗农药和化肥,农作物就无法正常生长。这又会进一步加剧农田及周围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
我国滇黔桂边区就是这样的地带。如果按照当地苗族、布依族的传统做法,则可以保证对生态环境的利用和维护到位。他们利用已经石漠化土地资源的要点是:首先,不轻易触动已有的残存植被,而是在残存植被中见缝插针地种植有一定经济价值的木本植物,如槐树、构树、马桑、桐油树、山苍子、椿树、漆树等等。此类野生或半野生的植物在取得经济收益时,只是收取植株的有用部分,如:叶、果、花、枝、汁等等,无须连年种植和清除残株,也就不必连年翻土,自然不会扰动脆弱的表土,从而控制了继续石漠化的势头。其次,保持这些木本植物和野生杂草灌丛的自然存在,不强行改变其物种构成。这样做既能加速植被的扩大与恢复,支持多种动植物的生长繁殖,又能拦截从高处自然下泄的水土,使已经石漠化的土地逐步增厚扩宽表土,稳步恢复土地的生产能力,持续稳妥地获得石漠化救治成效。最后,农田用地仅仅限于低洼的溶蚀盆地,靠人工塞住地漏斗的办法,构筑小片的农田,种植农作物,满足粮食供应。一般不盲目扩大农田,十分必要时才动用草坡种粮食,种一年后立即休耕,使之自然恢复。按照这两个民族的办法,不仅可以防止石漠化,而且能救治已经石漠化的土地资源。以此为例,我国目前很多生态失控地带,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误用普同性生态维护办法而导致的恶果。面对当前实际需要,地方性知识特有的不易误用性就更加显得难能可贵了。
地方性知识不易被误用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那就是地方性知识与相关民族文化结合十分牢固,由于不同文化之间存在互斥作用,各民族一般不会轻易地采用其他民族的办法去利用生态资源。我国甘肃和宁夏的比邻地带,野生苦杏林对于生态的维护具有重要价值。这一地区的汉族居民早就注意到,猪会自动采食落地的苦杏果。由于杏核十分坚固,因而在猪的消化道里不会被消化,而是随猪粪排出体外。来年,这些杏核中的杏仁会在猪粪中发育成苗,移栽这些杏苗就能扩大苦杏林面积。当地居民一直都采取这种办法操作,早年对维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然而20世纪60到90年代,当地汉族居民的做法却相反,为了获得短期经济利益,他们从猪粪中拣出苦杏仁核,然后剥出杏仁出售,供作药材和食品。这样一来,原先可以稳步扩大的苦杏林,在30年间却日趋萎缩,给当地肆虐的风沙敞开了大门。但是地方性知识的错用仅在当地汉族中流行。当地的回族居民因宗教信仰关系,将猪视为不洁之物,他们决不会接受这种办法,去利用生物资源。于是汉族地方性知识的跨文化误用,在回族中也就很难发生了。
同样的情况在我国南方的侗族与汉族间也可以看到。我国湖南、贵州两省的毗连地带杂居着汉族与侗族。这里的汉族居民和其他地区的汉族居民一样,当前已经普遍使用各种化学杀虫剂去对付水稻害虫,使用化学除草剂,去消灭水田中的杂草,并大量施用化学肥料。目前类似做法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浅水湿地生物群落的生物多样性也蒙受了重大的损害。然而在侗族居民的水田里却不会这样,原因在于侗族对于稻田害虫的价值定位不同,他们凭借地方性知识建构起来的治理办法也不同。侗族是将好几种水稻害虫作为食品食用,他们在收集害虫供作菜肴的同时,控制了虫害的蔓延]此外侗族的水田里还要放养鱼虾,田中的许多动植物也是他们的取食对象,因此侗族的稻田不会轻易使用化学药剂和化学肥料,他们的水田生态环境当然也不会像汉族地区那样受到损害。在类似的情况下,民族文化间的制衡机制发挥了作用,使得各民族的地方性知识获得了免疫力,有效地控制了生态受损范围的扩大。因此,发掘利用地方性知识,推动生态维护,在通常状况下是最为稳妥的做法,一般不会导致明显的副作用。

发掘利用地方性知识去维护生态环境,不会损及任何一种其他民族的文化,也不会打乱文化多元并存的格局。多元文化相互制衡的结果,最终会引导人类均衡地利用地球上的各种生态资源。既减轻了人类社会对于地球生命体系的压力,又能确保任何一种生物物种都既有人加以利用,也有人不加以利用而保护起来,从而形成利用和维护的相互兼容。在这样的多元文化背景下,无需对自然生态系统加以特意的维护,也能坐收生态维护的实效。
正是考虑到地方性知识的上述特性,以及地方性知识与特定民族文化的依存关系,生态人类学高度重视地方性知识的发掘利用,并将其作为根本性的研究任务去展开工作。同时坚信,如果能全面地发掘和利用各民族的地方性知识,人类就能扭转当前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确保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文章来源:《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