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ESE FOOD
摘要:历经百年,中国饮食风俗的变革几经移易,“分食”与“共食”在中国仍然是高下难分。总体上看,整个近现代的饮食方式变革之讨论与实践的实质,与其说是一场中国文化遭遇西方文明冲击后的饮食风俗改革,不如说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饮食文化所历经的一次现代化的本土尝试。饮食对于中国人而言,已经不只是满足人类温饱需要的生理行为,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社会文化活动。在当代公共生活中,饮食风俗也将在现代卫生与身体观念的影响下,通过民众的传习与接受,不断潜移默化,约定俗成,形成契合当代中国人的饮食实践模式。
关键词:分食;共食;移风易俗;现代化


“民以食为天”,普通民众对饮食一直都非常重视。对于传统儒家礼乐文化而言,“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由此可见,饮食习俗是中国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民众的生存。现代社会里,大家往往喜欢热闹、团圆的气氛,一般都是围桌共饮,觥筹交错,亲密接触,不亦乐乎。饮食,不仅仅只是为了满足人类温饱的生理需要,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社会文化活动。然而,这种历时悠久、约定俗成的历史传统是否就说明了中国饮食的共食制已经拥有了最大的正当性呢?
事实恐怕并非如此。尽管影响饮食风俗的因素非常多,但是由于近现代以来西方饮食风尚的传入、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卫生安全的宣传与重视,以及当代中国人的身体观发生变化,中国的知识分子主要围绕“卫生”与“文明”,展开变革“共食”这一中式饮食方式的讨论。因此,本文尝试梳理近代以来不同时期有关共食与分餐的变革与讨论,由此我们可以检视近代以来中国传统饮食风俗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系,并且尝试探究当代饮食风俗将何去何从。
一、从分餐走向共食
实际上,中国传统的日常饮食方式也是经历了从分餐逐渐转变为共食的漫长演变过程,自此以后一直延续到了明清,并未发生重大变化。为了便于展开后续讨论,首先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中国饮食风俗中共食制的发生及演变过程。
最早的史前氏族文化阶段,由于生产力低下,人类只能通过共同劳作来求得生存,劳动生产的成果并不丰富,生产资料实行严格的平均分配制度,采集的食物也是共同所有, 可谓是“天下为一家,而无私织私耕,共寒而寒,共饥其饥”。食物通过加工后,按照人数平分,然后各自进餐,这是最原始的分食制。这种饮食模式持续时间十分漫长,即便是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集体生活形式开始向家庭生活过渡,氏族内部出现阶级分化和贫富差距,“分食”模式也没有被改变。但是,史前人类开始大量生产陶制炊具和骨质餐具,这为商周时期“分食”的精细化提供了物质条件。
等到商周时期,中国人开始席地而坐,凭俎案而食,人各一份,分食制成为非常厚重的一种饮食传统。同时,食材的品种日渐丰富,烹饪的方式不断变革,逐渐开始出现“宴饮”的公共饮食方式,也就是说,饮食最原始的“献祭”意义经由风俗变迁逐渐隐蔽,开始变成了一种“礼物”的馈赠与共享,共食的形式则具有建构生者之间“我们属于同一个共同体”的文化功能。此后,这种饮食方式一直延续到唐中期,普通民众恐怕也是如此,《后汉书·逸民传》中所记录的孟光与梁鸿夫妻俩“举案齐眉”的典故,可谓是对平民日常生活饮食方式的一个侧面写照。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文化逐渐融合,也带来了饮食风俗的变化,最为典型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高足坐具。高桌大椅的出现,促使大家开始同桌而食。在敦煌四七三窟壁画中已经开始出现家庭式的合桌会食场景。

孟光与梁鸿夫妻俩“举案齐眉”
但是,这种情况并不代表大家已经开始“共食”了。实际上,食品的分配上仍然是一人一份,只是围桌而坐,有了“共食”的那种气氛而已。实际上,在一些晚唐五代的上流阶层饮宴场合中,基于长幼尊卑、主客有别的观念,还是会在筵席中实行分餐制,是否“经济”反而不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如南唐《韩熙载夜宴图》里面就保留了一副生动的古代饮宴的分食“现场”。有意思的是,在食桌上的碗碟旁边分别放着餐匙和箸,这与现代的饮食餐具摆设无异。相较于先秦两汉时期的文献资料多数只是描述“礼食”或者贵族宴饮的场合,魏晋南北朝至唐代的图像资料更加丰富,也为今人一窥古代民众生活提供了不少蛛丝马迹。

南唐《韩熙载夜宴图》
到了唐末宋初,食材的多元化、烹饪样式的多变极大地丰富了宋代餐桌的菜色,教坊酒楼、勾栏瓦舍等公共饮食空间的出现,促使饮食文化走向商业化,这是中国民众饮食文化的一次重要改革。另据尚秉和考证,中国人坐椅子围着桌边进餐的情形出现的时间应不早于北宋。自宋以来,美食开始从豪门贵族走向街头百姓,从琳琅满目的飨宴到贴近民众的茶楼酒肆,极大地丰富了当时百姓的饮食活动。而且,不管是何种饮食情境,但凡是有客人上门,“好客”的中国人常会以丰盛的菜肴来款待客人,席间主人还会“劝菜”,既是主人害怕客人因为过于谦逊而吃不到美食的缘故,也是主人表达视乎远客为自己人,并不见外的一种情感流露,通过“共食”这一中式饮食风俗习惯,主客之间的距离一下就被拉近了。
总体上而言,无论是日常的家庭饮膳还是社交性的公共宴饮,中国饮食空间变成私人性的家庭饮食与公共性的社会聚餐两种,饮食方式从分食制逐渐变成以共食制为主,并且由此产生了一些与之相匹配的饮食习俗。中国汉族家庭的日常饮食一般都是以“户”为单位开伙,以共食的方式进餐,除非兄弟之间分门别户,另立炉灶,否则就算是分家也未必会分爨。即便是分爨,也只是大家庭单位的一种重组,分家之后的小家庭仍然是“共食”的。自宋以来,中国汉人特别喜欢在婚丧嫁娶、生日节庆的特殊日子里大摆筵席,形成一种作为礼物流动的“办桌”文化。这种酒席一般菜色丰富、分量足,基于经济的考虑,都会采用“共食”的方式开席。更何况,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能与人共桌吃饭,“同吃一盆菜”,就是一种“与有荣焉”的人际关系建构,“敬陪末座”也不会计较,觥筹交错间呈现出一种人情社会的彼此认同。
二、当中餐遇到西餐
自明末清初以降,与西方传教士关系较好的一些中国文人开始接触到西方的饮食。康熙时期,安文思、南怀仁编撰《御览西方要记》,节录艾儒略的《西方答问》,介绍了西方的饮食习俗:“每人各有空盘一具以接,专用不共盘,避不洁也。”但是,西餐及其相关的饮食习惯并未在当时的中国产生多少影响。
1840年后,中国饮食文化再次遇到西餐这个“强敌”。随着国家的门户逐渐洞开,西方大量的咖啡馆和西餐厅传入中国,不少中国人开始出于好奇的心态,前往西餐馆就餐或者直接在家模仿西餐的饮食方式宴请宾客,甚至还有出版专门帮助培训人员在家中制作西餐的食谱。这种情况在建立民国的革命年代愈演愈烈,因为革命人士多有海外经历,经他们的身体力行,一时之间全国上下“器必洋式,食必西餐。无论矣,其少有优裕者亦必备洋服数袭,以示维新”,崇洋之风甚嚣尘上。这一时期的上海地区,西餐被民众称为“大菜”,而本土的中餐却反而称为“小吃”,吃得起西餐,并且能够熟练地、符合餐桌礼仪地在西餐馆进餐,被视为是一种个人财富和西方文化涵养的表现。为了方便民众学习烹调西餐,时希圣曾在民国21年(1932)7月出版了一本《中西精美食谱》,其中就有专门介绍西餐的烹调法,西餐食谱的出版无疑为西餐饮食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增加了可能性。但是,当“西餐”被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官僚普遍视为一种进步、文明、高贵的“身份”象征之时,另一种反对声浪很快出现,不少人士开始大声疾呼“维持国货”,进食方式的选择就不再只是日常生活的平常小事,而是关乎民族气节的一种身体力行的表态。但是,西餐的繁盛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选择,抵制“西餐”的呼吁收效甚微。

实际上,中西方餐饮之间除了食物和礼仪存在差异以外,最为明显的差异在于进餐方式是“分餐”还是“共食”。饮食方式存在这种差异则与两种饮食文化中的餐桌形制和饮食主体的社交观念有关。西方的宴饮空间多为窄长的方桌,食客不便于取用离自己较远一端的食物,因此需要事先将食物分配成更小的份额,然后再提供给食客。就此而言,西方的饮食组织模式是个体性的,食客自己对食物有相对自主的支配权。相较之下,中国使用圆桌或八仙桌,每个个体与餐桌中间的菜肴之间的距离是相等的,比较“公平”。加之取食过程是一个“分享”的过程,与祭祀仪式后的“分胙”很类似,通过食物的分割来连接整桌人的身体,因此,“共食”也可视为一种人际关系亲密的隐喻性行为,体现了中国人重视和气、热闹的饮食氛围,在饮食空间上对“整体”的重视。应该说,两种不同的饮食方式实际上都是贴近各自饮食主体的饮食风俗,本质上并无高下之别。
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关注西方的“卫生”知识,一些学人通过书籍、报刊向民众普及有关卫生的“新知识”,民众了解到“肺痨”与“细菌”、人的体液与疾病传染之间的关联性,大家开始出现排斥“人我津液交融”的情感倾向,这使得以“共食”为标志的中餐成为所谓开明之士的诟病对象,尤其是菜肴的“共食”问题。同时还有专业人士指出国人十一种不卫生的“恶习”,其中就认为“共食”是肺痨“传染之道”的“一大因”。实际上,中国传统中医学饮食观除了认为“医食同源”,讲究“食疗”和“养生”以外,也非常注重饮食卫生问题。如张仲景在《金匮要略· 禽兽鱼虫禁忌并治》中“秽饭、馁肉、臭鱼,食之皆伤人”的记载,以及孙思邈《急备千金要方·道林养性》“茅屋漏水堕诸脯肉上,食之成瘕结。凡曝肉作脯肉不肯干者,害人”的说法,都是明证。而且,孔颖达在解释《礼记·少仪》“凡洗必盥”的说法时,就说“凡饮酒必先洗爵,洗爵必宜先洗手也”,可见古人非常重视饮食器具的清洁。此外,袁枚在《随园食单》中也谈到厨房卫生的“洁净须知”,同样强调“多洗手,然后治菜”。但是,总体上而言,中国传统的饮食卫生观念与清末民初西方传入的卫生知识存在一个较大的差异,即中国饮食卫生注重的是食物的品质和食具的洁净这些外在环境因素,而不强调人自身的身体状况,自然就不会去考虑改变“共食”的饮食习惯了。可是,这些西方关于身体与疾病的新知识和新观念的传入,却深刻而直观地反映出人与人在卫生健康问题上的身体关系,使得一部分民众开始反思自己的日常饮食实践。同时,在清末民初“中国传统的负面整体化”过程中,“共食”所依附的中国饮食也未幸免,一些接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中国革命激进人对中国的共食制饮食发起猛烈的批评。有些公共卫生学者更是将中国“大众杂坐,置食品于案之中央”的共食与欧美各国及日本那种“不论常餐盛宴,一切食品,人各一器”的分餐模式相提并论,认为中国饮食“争以箸就而攫之,夹涎入馔,不洁已甚”,从而提出“饮食革命论——废止筷碗共食、实行中菜西吃法”,每人两套餐具以共食,避免病从口入。于是,在这种强大的革命舆论话语主导之下,加之受到西餐的吸引,当时的中国社会开始出现一些调整饮食习惯的新现象。实际上,当时的广州人在吃宴席时创造了一种叫“每人每”的用餐模式,即每位食客“各肴馔一器”,但是价格十分昂贵。虽然这种安排只是为了“昭示敬礼之意,非为讲求卫生而设”,普及度有限,但是依稀也受到了西方分餐制的影响。可以说,新的现代卫生知识和西方餐饮模式逐渐改变了中国人的身体距离和人际接触方式,大家对日常的身体性互动变得很敏感,促使中国民众重新思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主义式的身体观被强化。

较为温和的学者如伍连德,他认为“最善之法,莫如分食”,但是考虑社会习俗和中国的烹饪方式,“分食制似不适宜”。于是他提出了一套名为“卫生餐台”的全新餐饮模式,即“法以厚圆木板一块,其底面之中央镶入一空圆铁柱,尖端向上,将此板置于转轴之上。则毫不费力,板可以随意转动。板上置大圆盘,羹肴陈列其中,每菜旁置公用箸匙一份,用以取菜至私用碗碟,而后入口”。这套办法只是改变了餐桌的形式,并且随菜碟增加一副“公筷”,简单合宜又不失中餐的乐趣,慢慢成为中餐馆和华人家庭喜欢使用的方式。有些地方的餐馆还开始了使用“一次性”筷子的做法,广受欢迎。

但是,某些人过分追求饮食环境的“卫生”程度,“卫生好洁,不与人共食,若赴宴,他人已下箸,则弗食之”,遭致周围朋友的反感,认为这种人“过于养其身,而忽于养其心”,出现了适得其反的结果,变成了一个缺乏礼数的不文明人。正如雷祥麟所言,这种现象不仅过于极端而显得自私自利、不近人情,造成人际之间的关系疏远和嫌弃,甚至过度地实践这种“反社会的习气”反而容易导致洁癖感,因疑心重而生病。

近代以来的“西风东渐”,使得中国饮食方式的选择不再只是遵从“礼制”教化的原则,更不仅仅是历史传统的一种日常习得。当时的中国人通过对西方现代化的整体性想象和憧憬,开始以一种现代“城市风景”的眼光来“发现”西方的“分餐制”饮食模式。但是就其背后的卫生观念而言,实际上更加强调个人对于公共卫生这一集体性事务的服从。虽然无论是从群体阶层还是地域空间来看,西餐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的普及程度确实是有限的,但是与之相随的“文明”与“卫生”的现代化思潮却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民国时期饮食风俗的变革讨论,从而掀起了近现代学者对中餐“共食制”的批判和反思。
三、集体生活中的分餐与共食
虽然民国期间批评“共食”的声音非常强大,同时工商业的发展产生了大批的职工,他们经常需要在单位里吃午餐,然而到了傍晚,职工们下班回家之后仍旧会与家人共食。临近解放前,有的职工公共食堂采取传统的共食制,每桌人数不定,在规定时间内随到随吃。有些地方为了加强工人的集体观念,职工公共食堂实施包饭制,即每人每日预先进行包饭,可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食量大小、胃口爱憎来填写一张饭牌,然后伙房按量做饭。下班后,每人即持牌前往食堂用餐。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最初几年,国家机关与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就餐的方式沿用解放区的供给制度,各机关自行办食堂,大家在日常工作期间会前往单位食堂就餐。1954年以后,国家开始实行工资制,但是公共食堂被保留,各机关单位、厂矿学校都建了食堂,作为对单位职工和师生的一种生活照顾。在这一时期,职工多是以粮票来支付饭钱,然后各自分餐而食,有时候还会在单位食堂买饭菜带回家,与家人一起合家同食,其乐融融。如果遇到加班,单位还给补误餐,一般是工人自己打饭,然后共食菜肴。

如果说,现代化进程中的职业变化和社会关系的个人化倾向,对中国当代的公共饮食方式变革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城市中的职工群体中形成了共食与分餐并存的饮食模式,那么50年代时兴起的“爱国卫生运动”则从科学、卫生的理性角度向普罗大众推广了分餐制。虽然中国医疗状况在民国时期已经得到了很多发展,但是整个中国的日常生活卫生环境仍然不佳,而且很多流行性疾病与季节气候变化关系密切,为了减少各种传染病的发病率,改善民众的身体健康状况,共产党政府开始向普通民众普及传染病防疫知识。时任华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殷希彭特别撰文《疾病的传染和预防》,其中就对饮食卫生进行了论述,特别还强调了“不要和传染病人同居共食”。实际上,当时有病人的家庭通常也会采用分餐制的方式来避免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传染。换言之,如果家庭成员身体都非常健康,实行共食制的饮食方式也并无不妥。

进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0年代初,受到当时国际外交环境的影响,中国国家政府在全国展开一场“爱国卫生运动”。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的“爱国卫生运动”主要任务是“抵御外国细菌战”和“除四害”,积极防治春季流行病和地方病,培养群众讲卫生的新习惯。一些城市的普通饭馆,尽管设备条件不是很好,但是也在“搞好卫生,保证顾客身体健康”的口号下,千方百计地讲究卫生。当多位顾客一起就餐时,饭馆除了为每位顾客准备自用的筷、匙外,还备有公筷和公匙,并为有病的顾客单独准备了餐具。某些农村公社还形成了“户户用公筷”的饮食新风气。在1958年,中国广大农村公社开始兴办公共食堂,一些公社甚至改变了进食的方式,实施分餐制和公筷制,并且注重餐具的消毒处理。公社还向社员宣传新的一套卫生习惯,每天刷牙,勤洗澡、勤换衣、勤晒被,饭前要洗手。这些配套措施的实行,客观上减少了各种疾病的发病率。而且,从五十年代初起,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爱国卫生运动,国家政府希望引导民众发扬自爱爱人的美德,把中国建设成“现代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的强国”。在集体主义生活日益高涨的年代里,“爱国卫生运动”经由党的情感动员,在全国各地不断地被宣传和推行。在公共食堂中就餐的民众非常多,为了预防“病从口入”,讲求卫生,很多地方政府于是在集体用饭时开始推行“公筷制”, 以“改变中国几千年来传统的用饭习惯”。这种新型模式虽然在1950年时已经有人提出,但是直到人民公社时期,才被视为“一件对人民健康极为有益的移风易俗的大事情”,得到了广东、四川、湖南、黑龙江、浙江等较多省市地区公共食堂的响应。

总而言之,无论是城市工人还是农村民众,无论是想努力建设新中国还是要“改造世界”,这一时期中国普通家庭开始由私人生活变为集体生活,由生产单位统一管理,不仅希望“帮助妇女从琐屑的家务下解放出来”,也十分强调“集体过生活,集体讲卫生”的观念,民众饮食的公共食堂化客观上促进民众对饮食卫生及消毒措施的了解与重视,有利于在集体生活中保障每个农民的身体健康,提高劳动的出勤率,保证日常生产的正常开展。与此同时,与公共食堂同时产生的“公筷制”也逐渐走入普通民众的饮食生活,成为一种自觉选择的生活习惯。此外,职工公共食堂虽然初衷是加强职工的集体主义观念,但是实际上却是推广了分餐制以及分配制度的个体性,对当代中国人社会关系的变革也存在影响。由此可见,虽然这场“移风易俗”的饮食生活变革并未完成“改造世界的伟大目标”,但也没有彻底“失败”。
四、“革除陋习”还是“保留传统”?
20世纪80年代初,以麦当劳和肯德基为代表的新式西方快餐与自助餐餐厅开始抢滩大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带来了新的就餐环境、新的装潢方式、新的饮食样式和新的服务模式。这种漂亮、干净、舒适的就餐方式,加之随取随用的便捷和快速,很快吸引了大量的中国民众,同时也形塑了新一代中国人时髦、平民、卫生与快捷的饮食观念。有鉴于西式餐饮企业在管理、经营模式上占据了极大优势,不少中国餐饮企业也开始模仿,投消费者所好,逐渐出现了蒸有味、好功夫、大家乐等实行单人点餐、分餐进食的中式快餐馆。无论是西式还是中式,快餐饮食的“个人套餐化”配餐模式无疑强化了饮食中的个体化色彩,自然也使分餐制得到更大的彰显。
如果说上述新式餐饮经营模式发生变化,使中国人的饮食风俗经由对西方饮食的想象而被动地发生变化,那么国家政府不断强调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性,特别是注重改善农村大众的饮食环境和饮食观念,并且普遍提倡一种节俭的饮食风气,强调国民的个人卫生意识,同样是影响深刻。70年代末,中国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新的话语模式——“改善社会风气”,并视其为当代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部分,逐渐形成新时期以学雷锋、树新风、“五讲四美”为核心的国家风俗观,以便促进城乡精神面貌和整个社会的风气改变。兴起自50年代的“爱国卫生运动”为了配合改善社会风气的新时期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目标,其核心价值则变成了“提高我国人民科学文化水平、实现四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反映人们道德风尚和精神面貌,关系中华民族兴旺发达、子孙后代健康的大事”,因此中央要求各相关单位要深入广泛地开展卫生宣传工作,“使爱清洁、讲卫生的新的道德风尚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蔚然成风”。
虽然改革开放后,大众一直在努力配合国家的政策宣传,希望建立卫生环保的生活环境,但是中国接连发生了两次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则促使中国人开始主动地变革和调适自身的饮食观念,不少人士站在现代的“卫生防疫”角度,抨击中国的共食制度,认为这是一种“陈旧陋俗”。首先是八十年代初,某些地方出现传染性疾病“肝炎”。经过建国后多方对“卫生”的宣传,大众其实对“病从口入”和“传染病”的认知已经加深,于是“改变共食为分食,移风易俗”来预防肝炎传染的倡议进入大众的话题。时任卫生部卫生防疫司的官员郭节一同样认为应该改变国人集餐的方式,过去中国人都是团团围坐、菜肴居中、各自伸筷、同食一盘,从卫生角度看,“是一种不良的吃饭习惯,必须加以改革”。因此,为了防止疾病传染,他倡议把吃饭方式由集餐制改为分餐制,各地不妨创造条件加以实施。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佟之复教授从专业角度提出肝炎可以通过消化道传播,因此提倡分餐,改变共食这一“不良的陋习“。针对中国饮食上的“不文明习俗”,一些饮食烹饪专家发出“积极改革我国筵席”的倡议,移风易俗,改变观念,普及饮食科学知识,“改变那种认为筵席的菜点越高档、剩得越多越能显示主人热情待客等陈旧观念”,同时“因地因人而宜,提倡公筷、公勺”。直到90年代,这场关于“分餐”与“共食”的讨论还尚未停息。相较于国家政府基于“分餐容易控制菜量,减少浪费,一人一份,卫生方便,不用互相礼让,有助缩短用餐时间,也便于餐厅人员实行规范化服务”的考虑,开始在“国宴”上实行分餐制,民众对这场讨论的回应则较为平淡,家庭饮食无论是日常三餐还是节俗宴客,仍然以共食制为主。
第二次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在2003年春季,一种新型的传染疾病“SARS”席卷了整个中国。一时之间,人人自危,大众“下馆子”的次数急剧减少。“分餐制”在这场时疫中再次成为一个流行话题。首先,餐饮业为了官方控制疫情和重新振作食客信心的需要,短时间内从卫生到服务都有了极大的改善,大众也尽量选择分餐制,使用公筷、公匙。其次,有些媒体甚至认为“非典”给中国带来七个转机,其中就包括改变国人“火锅式”的饮食陋习,推行分餐制,限定个人酒量与饭量,减少浪费。同时,中国饭店协会制定了《餐饮业分餐制设施条件与服务规范》,作为全国300多万家餐饮经营企业分餐制的操作指南,并且正式向国家质检总局申报为强制性国家标准。但是这种行为被大众视为激进的强制措施,而且选择的主动权在广大顾客而不在各家饭店手中,因此有人提倡从移风易俗的角度多做努力。
尽管经过二十多年的专家学者奔走呼告,期间经历了“肝炎”和“非典”两次大范围的社会疫情,但是大众对此仍然是应者寥寥,仅一些事业单位、集体性企业坚持了“分餐制”。支持者主要是站在公共卫生安全的角度来推广分餐制。反对者则主要强调中餐共食是一种“国粹”,体现中国团结和谐的气氛,分餐是“舶来品”,“不合中国国情”。诚如王力在《劝菜》中所言,因共食而“津液交流”的饮食场面确实令人心生不快,有违现代卫生要求,只是仅从“卫生健康”这一所谓的现代文明观念就否定中国的“共食制”固然有其科学理性的道理,但未免太过偏激,恐怕不尽然能解释时至今日“分餐制”为何仍然无法在中国普通家庭中普及的事实。更何况,在“非典”时期大家能自发地实行分餐制,一些公共场合的聚餐也会使用公筷、公勺,本身就反映出中国人实际上很重视饮食的公德,也明白“病从口入”的道理,并非真的以为“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大众对分餐这种“卫生的家庭饮食方式”并不太买账,而是以“传统”和“西化”的文化认同名义来抵制分餐制。实际上,相较于过去,中国的医疗水平大幅提高,加之民众自身的卫生观念也被强化,家庭内部的厨房烹饪环境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变,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病从口入”的风险性。而且,在家庭中实行“分餐制”既显得“生分”和疏远,又令人觉得麻烦,无论是风俗习惯上还是卫生健康角度,中餐的共食方式并未受到太大的冲击和民众的反对,只是相较于过去,西方新式餐饮模式的推广与普及,确实有限地提高了当代民众在公共聚餐时,甚至是家庭饮食中开始选择分餐的可能性。
五、结论
历经百年,中国普通民众的饮食风俗自觉不自觉地几经移易,“分食”与“共食”在中国仍然是高下难分,这充分显示了饮食文化作为一种社会风俗所具有的传习性、凝固性和变异性特征。纵观近现代以来中国饮食风俗的变迁过程,尽管影响进餐方式的因素纷繁复杂,但总体上看,无论是民国时期转动餐台的发明,还是建国后对“公筷制”的推行,或者是当代对“分餐制”的再次倡议,这些近代饮食风俗的改革与移易措施与古代的移风易俗思想在理念上存在着极大差异,如果说传统的饮食风俗观是以儒家礼仪为主体的传统道德伦理为理论根据的话,那么近现代以来兴起的饮食风俗变革已经开始以西方习俗为参照物,并且不断在反省与实践中形成一种自觉的现代化风俗观话语体系,影响着中国近现代以来的饮食风俗变迁。换言之,与其说这是一场中国文化遭遇西方文明冲击后中式饮食风俗的被迫改革,不如说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饮食文化所历经的一次主动的现代化本土尝试。在“卫生”“文明”与“独立”“个体化”的现代饮食消费观念与“分享”“平等”的传统人情社交需求之间不断地协调下,最终形成了今日“共食”与“分餐”并存、“中餐”与“西餐”兼容的中国式餐饮文化。
尽管中国人的私人生活在发生变革,民众的身体观随卫生观念的变化也在不断调适。诚如前文所述,中国人并非不重视饮食卫生问题。实质上,“共食制”不仅仅只是一种基于经济的考虑来合力分享丰富美食,更是一种“平等”姿态的体现,正是有这一层传统文化的人情底色,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共食制恐怕仍然符合多数普通民众的饮食就餐观念。在当代公共生活中,饮食风俗也将在现代卫生与身体观念的影响下,通过民众的传习与接受,不断潜移默化,约定俗成,从而形成一套契合当代中国人的饮食实践模式。
文章来源:《民俗研究》2015年第1期,注释与参考文献详见原刊。
作者简介:林海聪,中山大学中文系。
图片来源于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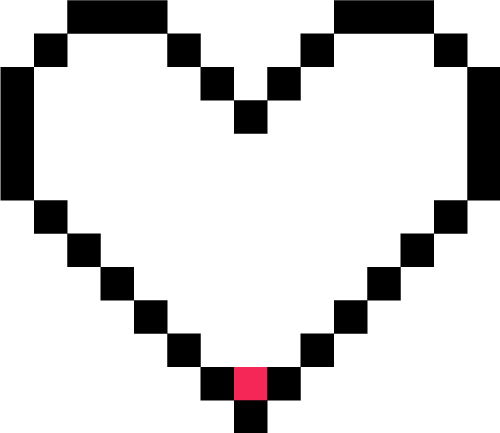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