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四部分类中的“故事”并不是一个文学概念,而是历史概念。明代以来,市民社会的发育壮大,民众精神生活的需求促成了“历史故事”向“文学故事”的转变。近代以来,传教士率先兴办儿童报刊,利用通俗白话故事进行宗教宣传,引起了爱国知识分子的警觉和重视。为了争夺文化市场,中国报刊纷纷以白话取代文言、故事取代小说,反复强化了故事作为一种叙事文类的公众印象。故事市场的充分发育引起了“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的高度重视,他们把它当作民俗文化的代表,从不同角度进入研究。周作人主张的童话研究与顾颉刚创立的故事研究范式之间的竞争,反映了同为进步知识分子的不同学术团队之间对于学术话语权的争夺。故事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现代学术,正是在这样一种正统文化与民间文化、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以及不同学术共同体之间的话语争夺中不断推进,逐渐建立起来的。
关键词
历史故事;白话故事;童话研究;故事研究;顾颉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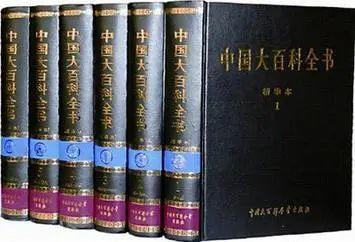
“民间故事”“故事研究” “故事学”都是现代学术的概念,我们很难在古代话语体系中找到对等含义的学术概念。为了辨析故事概念的转变,我们必须先确认一个参照坐标,也即现代学术对故事概念的定义。《中国大百科全书》对民间故事的解释是:“民间散体叙事文学的一种体裁。又称‘古话’、 ‘古经’、‘说古’、‘学古’、 ‘瞎话’等。民间故事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民间故事是泛指流传在民众中与民间韵文相对的民间散文叙事作品;狭义的民间故事指除神话、传说之外的,一系列具有神奇性幻想色彩或讽刺性奇巧特点很强的散文叙事作品。” 本文讨论中对“故事”一词如无限定或特别说明,均用其广义概念,泛指民间流传的口头散文叙事作品。
一、正统文人笔下的“故事”与“小说”
“故事”一词虽屡屡见载历代典籍,但在古籍中并不作为文类概念,多作先例、旧制、故业、历史事件解。以《史记》和《汉书》为例,(一)表示先例、旧制,如:“是时,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选名儒俊才置左右。”又:“(孝平帝)其出媵妾,皆归家得嫁,如孝文时故事。”颜师古注称:“故事者,言旧制如此也。”这是“二十四史”中“故事”一词最常见的用法。(二)表示故业,如:“及苏秦死,代乃求见燕王,欲袭故事。”苏代想承袭苏秦的事业。(三)表示历史事件,如:“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有人将述故事比之于《春秋》,说明故事就是记事,只不过《春秋》是记录,司马迁是整理。
总之,我们可以将这些典籍中的“故事”理解为一个历史概念,即“前人做过的事情”或“前人定下的先例、规矩”。颜师古引应劭注《汉书》“掌故”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者。”他自己也有进一步说明:“掌故,太史官属,主故事者。”也就是说,太史官中有掌故一职,专司故事,这跟我们今天用为文学概念的“故事”有本质差别。所以,《隋书·经籍志》将《汉武帝故事》等10种后缀为“故事”的图书均归入“史部·旧事篇”。《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则直接设有“故事类”,归在“乙部史录”麾下。
我们知道,指向现代广义故事概念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传承主体为“民间”;传承本体为“口头散文作品”。循着这两条途径,我们可以从古代话语体系中找到一个大致相近的概念,即“小说”或“笔记”。
较早对小说以界说者,是班固《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历代官修志书均沿袭之。此说基本符合广义的故事概念对于传承主体及传承本体的定义要求,所以鲁迅认为:“然稗官者,职惟采集而非创作,‘街谈巷语’自生于民间,固非一谁某之所独造也,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与传说。”用我们今天的话说,稗官即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者。而所谓的小说家齐谐、夷坚、虞初之流,也即当时著名的民间故事家。刘守华甚至直接把宋代笔记小说《夷坚志》称作“宋代的民间故事集成”。周楞伽也说:“小说,说之小者也。准此,则先秦诸子书中的神话、传说、寓言、故事,无一不是小说。”
从西汉直到清代,正统文人笔下的故事、小说两个概念的变化都不大,基本沿袭上面几种用法。比如清代钱大昕的《元史艺文志》、魏源的《元史新编》均设有“故事类”,依然将其置于“史类”“志”的大目之下。

近代丁传靖的《宋人轶事汇编》中设有故事类编,但他对“故事”的解释是:“事无主名,不能以人系者,辑为故事、杂事两门,统朝野记之。常然者入故事,偶然者入杂事。”说白了,故事就是尚未写入正史的潜规则、日常琐事。这算是传统故事观的一种解读。
二、明清白话小说中的“故事”
那么,老百姓口头文学中的“故事”概念该从哪里找呢?最好的办法是从明清白话小说中找,因为白话小说面向市民、面向市场,多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是文学大众化的文本体现。正如吴承学指出的:“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明清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联系最为紧密直接。……不同之处在于,晚明的变革只是中国传统内部的一次自我调整,而‘五四’则是一场思想文化的革命,其思想原动力主要来自近代西方。在思想上,大众化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征。‘五四’新文学所谓口语化、走向民间等思潮,就是在文学上的大众化表现。”

现存最早的话本小说《清平山堂话本》并没有出现文学意义上的故事概念。但是,到了冯梦龙的“三言”拟话本,故事开始脱离历史的窠臼,逐渐向文学靠拢。在最早成书的《喻世明言》中,故事尚是文学化的历史,如:“沈炼每日间与地方人等,讲论忠孝大节及古来忠臣义士的故事。”(《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如今在下说一节国朝的故事。”(《滕大尹鬼断家私》)“我今日说一节故事,乃是张道陵七试赵升。”(《张道陵七试赵升》)而在最晚成书的《醒世恒言》中,故事的内涵越发多样,虚构文学的意味更加浓烈,如:“方才说吕洞宾的故事,因为那僧人舍不得这一车子钱,把个活神仙,当面错过。”(《一文钱小隙造奇冤》)“若有别桩希奇故事,异样话文,再讲回出来。”(《徐老仆义愤成家》)“我又闻得一个故事。”(《大树坡义虎送亲》)在这里,既有“说故事”“讲故事”,也有“闻故事”,故事是作为一种“说”“讲”的文学形式被言说的。
但故事并不指称口头讲说的全部叙事文学,而是特指讲述“希奇事”的文学作品,所谓“世上希奇事不奇,流传故事果然奇,今朝说出希奇事,西方活佛笑嘻嘻”,指的就是故事的传奇性特征。最能体现明清以来民间文学故事观的白话小说,当属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
艾衲居士可能是明末清初的杭州遗民,其“闲话”即是故事。该书开篇即说,夏天的豆棚下,“那些人家或老或少,或男或女,或拿根凳子,或掇张椅子,或铺条凉席,随高逐低坐在下面,摇着扇子,乘着风凉。乡老们有说朝报的,有说新闻的,有说故事的”。在这里,故事与新闻并举,或许“旧事”的意味重一些。《红楼梦》第39回凤姐对刘姥姥说:“你住两天,把你们那里的新闻故事儿说些与我们老太太听听。”
对于听众来说,无论故事还是新闻,关键在于“异闻异见”,并不讲究其真实性。正如听众鼓励说故事的人:“如当日苏东坡学士,无事在家,逢人便要问些新闻,说些鬼话。也知是人说的谎话,他也当着谎话听人。不过养得自家心境灵变,其实不在人的说话也。”那讲故事的人也解释说:“在下幼年不曾读书,也是道听途说。远年故事,其间朝代、官衔、地名、称呼,不过随口揪着,只要一时大家耳朵里轰轰的好听,若比那寻了几个难字,一一盘驳乡馆先生,明日便不敢来奉教了。”这段解释,上升到故事理论的高度,就是普罗普的形态学观点:“(故事中)变换的是角色的名称(以及他们的物品),不变的是他们的行动或功能。……对于故事研究来说,重要的问题是故事中的人物做了什么,至于是谁做的,以及怎样做的,则不过是要附带研究一下的问题而已。”可见在明清时期的杭州,人们对故事的理解已经非常接近现代故事观念。
《豆棚闲话》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对话,指出了故事的口传特征、传奇性特征、变异性特征,以及职业故事人现编现创的创作特点等。比如,在第八则故事中,讲故事的少年解释其故事“我是听别人嘴里说来的,即有差错,你们只骂那人嚼蛆乱话罢了”,众人则解释“不管前朝后代,真的假的,只要说个热闹好听便了”。在少年的故事中,又出现一个名叫孔明的瞽目说书人,自称“品竹弹弦打鼓,说书唱曲皆能”,试演时,“孔明也就把当时编就的《李闯犯神京》的故事,说了一回。又把《半日天》的戏本,唱了一出”,这段描写说明,听众是认可现编现说故事的。
但小说毕竟是文人创作的,所以在这些白话小说中,正统文人的故事观与民间文学的故事观往往交替出现。正统文人的故事观将故事视作常态的、循例的事务,因此常常出现“虚应故事”(敷衍了事)的说法,如:“若官府不甚紧急,那比较也是虚应故事。”但在另一方面,作者又会依着民间故事观,将故事视作非常态的、例外的事务,因此又会出现“闹故事”的说法。如《红楼梦》第61回:“每日肥鸡大鸭子,将就些儿也罢了。吃腻了膈,天天又闹起故事来了。”第62回:“我说你太淘气了,足的淘出个故事来才罢。”
三、晚清报刊的汉译“故事”

从《豆棚闲话》可知,现代文学意义上的故事概念,至迟在明末已经在杭州一带成型,可是,与故事同义或近义的概念语词还有很多,如说话、轶事、异闻、奇谈、趣谈、传奇、古话、闲话、瞎话等,为什么这些语词没有成为通行的文类概念,只有故事一枝独秀,成为现代学术的研究对象?
故事成为通行文类概念,与外来宗教的传教策略有关。外来宗教传入中国,在传教策略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佛教进入中国的时候,大量借助变文、说唱等通俗文学进行宗教宣传。基督教进入中国之后,一样要向潜在的信众讲述一些通俗易懂、便于传播的宗教事迹。这些与神及其信徒相关的神异事迹,他们称为“故事”。
1875年,美国长老会牧师范约翰(T. M. W.Farnham)在上海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份儿童画报《小孩月报》,成为近代史上坚持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儿童读物。该刊文字浅近易读,内容丰富多彩,图文并茂,可谓老少咸宜,大别于晚清各文言报刊。其刊名刻意不用“儿童”而用“小孩”,已经明确地昭示其通俗化、大众化的民间风格。在选择Story的汉译词汇时,《小孩月报》选中了口头传统中的故事一词。他们将歌曲I Love To Tell TheStory译成《主的故事》:“我爱说主的故事,论人眼见之外,论我荣耀的牧师,论耶稣大慈爱,我狠爱说那故事,因我知道是真,凡言莫如此故事,能满足我的心。”
《小孩月报》创造了一种与“记”“传”“说”“论”“近闻”“笔记” “寓言” “问答”平行的“故事”文类,专门讲述基督信徒信教得福的神异事迹,如《祈祷有验故事》《美国小孩得救的故事》等,都放在头条位置刊发。《申报》将之誉为“启蒙第一报”:“沪上有西国范牧师创设《小孩月报》,记古今奇闻轶事,皆以劝善为本,而其文理甚浅,凡稍识之无者皆能入于目而会于心,且其中有字义所不能达之处,则更绘精细各图以明之,尤为小孩所喜悦,诚启蒙之第一报也。”
一旦确立了Story与故事之间的对译关系,天教系统在华影响最大的报纸《益闻录》《圣心报》等,也大量使用“某某故事”“某某的故事”作为神奇叙事的文章标题。如《圣心报》的《故事》,单讲一个中国的满洲小王,因为与汤若望交好,将汤若望赠送的宗教礼物贴身佩带在身上,结果在征战之时,小王连中三箭,直透内衣,但是身体却未伤分毫,自此笃信耶稣。范约翰创办的另一份影响巨大的《图画新报》,其中一个专栏名称就叫“祷告故事”。
晚清报刊无论是教会背景的,还是非教会背景,即使由中国文人编辑的白话报刊如《杭州白话报》《敝帚千金》等,这一时期大凡以“某某故事”为题的文章,多是中译的外国故事,而且热衷于相互转载,反复强化了故事作为一种叙事文类的公众印象。如《外国故事演义》系列、《讲波兰灭亡故事》系列、《三大陶工故事》系列(《绍兴白话报》,1900—1903)、《波兰的故事》系列(《杭州白话报》,1901)、《埃及故事》(《春江花月报》,1901)、《外国故事》系列(《童子世界》,1903)、《毕士马克故事》《爱国女子若安达克的故事》(《敝帚千金》,1903—1906)、《外国故事》系列(《童子世界》,1903)、《西事拾异:无穷故事》(《月月小说》,1907)等。就连1897年创刊的《蒙学报》,也已经意识到通俗的儿童教育对于救亡图存的重要意义,在其栏目中加设中西故事图说,如《母仪故事图说》《师范故事图说》等。
吴趼人1906年创办的《月月小说》,英文刊名叫The All-Story Monthly ,可见在这一时期“故事=Story=小说”,故事和小说的位置,正在发生微妙的转换。最有意思的是中国留日学生编发的《大陆报》,1902年至1903年连发了一系列“小说:故事”体的文章,如:《小说:一千一夜:渔翁故事》《小说:一千一夜:希腊王及医生杜笨故事》《小说:一千一夜:商人遇魔故事》等。孙毓修更是将童话、故事称作“儿童小说”:“儿童之爱听故事,自天性而然,诚知言哉。欧美人之研究此事者,知理想过高,卷帙过繁之说部书,不尽合儿童之程度也。乃推本其心理之所宜,而盛作儿童小说以迎之。说事虽多怪诞,而要轨于正,则使闻者不懈而几于道,其感人之速、行世之远,反倍于教科书。”
四、“童话研究”的提倡
《小孩月报》等教会杂志的盛行强烈地刺激着中国知识分子,争夺儿童,开启民智,成为晚清知识界的热门话题。1900年,“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与江南书局第一套儿童寓言故事书《中西异闻益智录》的出版,拉开了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大幕”。1901年至1903年相继创刊的《杭州白话报》《绍兴白话报》《中国白话报》,都非常注重白话故事对儿童的启蒙意义。晚清对于故事文类的倡导,起于传教士,盛于报章杂志,有识之士多是从教育一途着手,看重其与儿童教育的关系,认为儿童教育“最宜注意者,宜采用童话,不宜多用文言,俾儿童易于领悟。非然者,则诲者谆谆,听者藐藐”。
孙毓修1907年入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08年始主持编写《童话》丛书。他参照《泰西五十轶事》等西欧童话,编写《无猫国》《大拇指》等一百余种儿童读物,被誉为“中国童话的开山祖师”。
周作人认为“童话这个名称,据我所知,是从日本来的”。他受到孙毓修童话书的激发,写了《童话研究》和《童话略论》,提倡“童话研究,当以民俗学为据,探讨其本原,更益以儿童学,以定其应用之范围”。因文章对孙毓修有所批评,周作人担心商务印书馆不愿刊发,于是投给中华书局办的《中华教育界》,但还是被退稿了,可见当时人们还不能接受“童话有研究价值”的观念。后来因教育部编纂处要办一个杂志,周作人就把稿子投向这份寂寂无闻的新报刊。
周作人童话观与孙毓修童话观差得比较远,孙毓修的童话指的是单纯的儿童文学,而周作人的童话指的是狭义的民间故事,认为其读者(听众)也包括成年人。周作人将广义的故事分为三种,神话、世说、童话:“神话者元人之宗教;世说者其历史;而童话则其文学也。”这种划分,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神话、传说,以及狭义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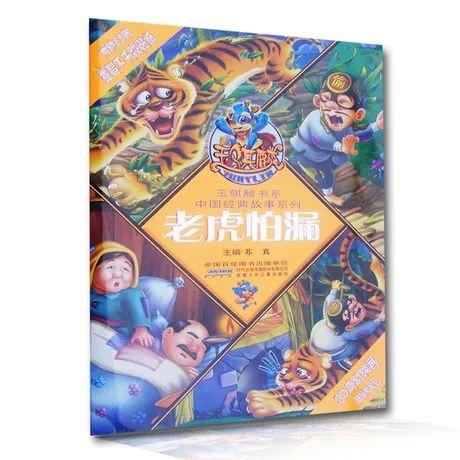


周作人认为童话反映了原始人的思维和习俗,是上古文化的遗留物,而儿童又与早期人类有心理上的相通之处:“童话作于洪古,及今读者,已昧其指归,而野人独得欣赏。……童话者,幼稚时代之文学,故原人所好,幼儿亦好之,以其思想感情,同其准也。”周作人以《蛇郎》和《老虎外婆》《老虎怕漏》等故事为例,就其中的神异母题与欧美、日本的同类故事进行比较,指出:“童话取材,大旨同一,而以山川风土国俗民情之异,乃令华朴自殊,各含其英,发为文学。”
周作人将童话分为两类,由传说转化而来的“纯正童话”(由原始思想转变而来的、解释历史文化遗留的),以及纯娱乐的“游戏童话”(含动植物故事、笑话、复叠故事)。他认为随时代和风俗变迁,今人以为诡异的故事母题,只有使用民俗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才能理解其真谛,“举凡神话、世说,以至童话,皆不外于用以表见元人之思想与其习俗者也”。周作人将民间童话称作天然童话、民族童话,与之相对,他将作家创作的童话称为人为童话、艺术童话,并且认为安徒生的童话写得最好。至于其功能,他认为虽然童话成人也爱看,但主要还是用于儿童教育。
《童话研究》纯粹基于人类学派的故事观虽然有些偏颇,但仍可称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第一篇故事学论文,万建中认为正是这篇论文“正式拉开了我国现代民间故事研究的帷幕”。可惜的是,论文在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社会反响,周作人意兴阑珊,“于是趁此收摊,沉默了有六七年”。但是,这些观点却触动了另外一位编辑家、民间文艺学家赵景深的注意。1922年,两人相约在《晨报附刊》连载《童话的讨论》。赵景深开篇就说:“就童话二字说来,许多人以为就是神仙故事,不过译的不甚恰当。”这段话正说明童话、故事作为一种报刊文类,在一般人心目中,是与译介文化紧密相关的。周作人则在回信中进一步解释说,“童话”一词,源自日本小说家山东京传的发明,“童话的训读是warabe no monogatari(日语:儿童物语),意云儿童的故事;但这只是语源上的原义,现在我们用在学术上却是变了原义,近于‘民间故事’——原始的小说的意思。童话的学术名,现在通用德文的Marchen这一个字,原意虽然近于英文的Wonder-tale(奇怪故事),但广义的童话并不限于奇怪”。
周作人心目中的“童话学”,方法论上用的是欧洲的人类学、民俗学方法,而研究对象却是由日本人限定的童话,目的是做中国故事研究。也就是说,周作人试图用欧洲的螺丝,配日本的螺帽,用于中国物事。这显然是世界上不曾存在的一种学问,它只是周作人的个人倡导,或者说个人理想。
五、中国“故事学”的建立
一门学问的创立,将起点划在概念的提出,以及倡导、呼吁,还是划在研究范式、示范文本的出现,体现着不同的学术史观。多数学术史家将故事学的创立划定在周作人《童话研究》的发表,而本文则将故事学的建立划定在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的发表。
故事学的兴起,无疑是“眼光向下的革命”的一部分。孙毓修、周作人将革命的目光投向了儿童,顾颉刚则将革命的目光投向了所有的普通民众。与多数知识分子不一样的是,周作人和顾颉刚都不是从“故事教育”的角度来关注故事,而是从“故事真相”的角度来关注故事,只不过两人分取了两条完全不同的求真途径,周作人取的是西方人类学派的路子,顾颉刚取的是自创的“历史演进法”。顾颉刚说:“民间故事无论哪一件,从来不曾在学术界上整个的露过脸;等到它在天日之下漏出一丝一发的时候,一般学者早已不当它是传说而错认为史实了。我们立志打倒这种学者的假史实,表彰民众的真传说;我们深信在这个目的之下一定可以开出一个新局面。”
我们无法确知顾颉刚是否读过周作人系列童话研究的论述,可以肯定的是,顾颉刚对周作人没有认同感,他曾经写文章公开讥讽“周不是一个办事的人” 。顾颉刚的故事研究,从文类的定名,到研究方法,以至对象范畴,完全无视周作人提倡的童话学,他另辟蹊径,开辟了一条纯中国式的“历史演进法”。1924年11月23日,顾颉刚在《歌谣周刊》发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刘半农大为感叹:“你用第一等史学家的眼光与手段来研究这故事;这故事是二千五百年来一个有价值的故事,你那文章也是二千五百年来一篇有价值的文章。” 随后,顾颉刚利用《歌谣周刊》的巨大影响力,展开了一系列讨论:“我们深信孟姜女的故事研究清楚时,别种故事的研究也都有了凭藉,我们现在尽出孟姜女专号,并不是心目中只有一个孟姜女,我们只是借了她的故事来打出一条故事研究的大道。”这段话中,顾颉刚开疆拓土,倡学立说的雄心昭然若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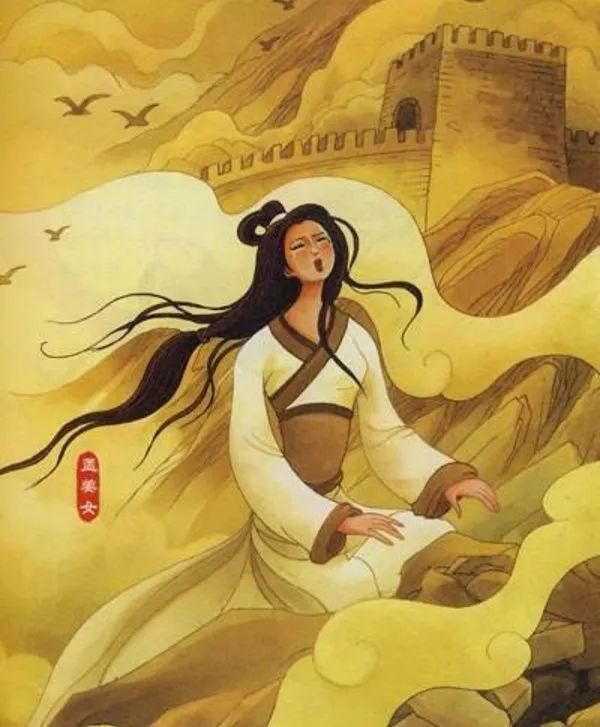
从顾颉刚的系列孟姜女故事研究及讨论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如下几点顾颉刚故事学的基本观点:(一)故事是不断变异的,它没有固定的体,故事的体就表现在前后左右的种种变化之上。(二)故事的变异是有规律可循的。(三)中国的古史(传说)是层累地造成的。(四)变动不居的故事中,也有不变的“中心点”。(五)故事中人物的角色是类型化的。(六)主流文化的话语霸权对于故事传播具有深刻影响。(七)故事传播的中心点会随着文化中心的迁流而迁流。(八)时势和风俗的变化影响着故事的变异。(九)民众的情感诉求推动着故事的变化发展。(十)情节的自我完善的需求推动着故事的丰富和发展。
顾颉刚的系列孟姜女故事研究,不仅奠定了故事学,也奠定了民俗学“变”(变异、变迁、转变)的研究范式。此后,模仿“变”的历史演进法以探讨故事变异、风俗变迁的论文成为民俗学的主流研究范式,“仅以1928年至1929年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为例,就有潘家洵的《观世音》,杨筠如的《春秋时代男女之风纪》《尧舜的传说》《姜姓的民族和姜太公的故事》,吕超如的《战国时代的风气》,余永梁的《西南民族起源的神话 ——盘瓠》,方书林的《孔子周游列国传说的演变》等等”。陈槃甚至说:“用了顾先生给我们辨伪史的工具——以故事传说的眼光来理解古史,于短期间写成这篇文字。若是这篇文字写得不好,这是我学力所限,但这个原则和工具是不会错误的。”
同一对象折射在执着于不同学术眼光的学者眼中,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提问方式和解题方式。作为经史学家的郑樵、顾炎武、姚际恒等古代学者,也都先后发现了孟姜女故事的种种变化,但是,他们以经史的眼光看故事,从故事的演变中发现这是一出“无稽之谈”;而顾颉刚以故事的眼光看故事,却从故事的演变中发现了“无稽的法则”,由此创立一门全新的学科。同样,周作人用了童话学的眼光,看到的故事都叫童话,而钟敬文用了故事学的眼光,看到的童话都叫故事,以至于把格林兄弟著名的《德国儿童与家庭童话集》都称作《民间故事集》。正是因为有了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学者们看待故事的眼光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从此有了中国故事学。
六、“故事研究”对“童话研究”的兼并
前面我们已经说到,无论故事还是童话,作为文类概念的出现,均与通俗文化的崛起、外来文化的介入、报刊杂志的盛行、启蒙教育的诉求、文化先驱的提炼与倡导密切相关。如果将故事视作所有“口头散文叙事作品”的总称,那么,用童话来指称狭义民间故事尤其是幻想故事,无疑会更加合适,可是,为什么现代民俗学者宁可采用广义故事、狭义故事的含混概念,也不采纳故事、童话的清晰概念呢?
采纳哪个名词作为学术定名,其实并不取决于名词的合理程度,而是取决于推广使用者的话语权。周作人想法多,声望高,但并不擅长主事,1913年的童话研究倡议没有得到理想的社会反响,他很快就泄气了,并没有持续投入这项工作,他对童话的界定也游移不定。比如赵景深说:“有些人把童话分为两类,神秘的称为童话,不神秘的称为故事,似乎郑振铎君是这样分法。”周作人回复说: “童话与故事的区别,我想不应以有无超自然的分子为定,最好便将故事去代表偏重人物的历史的传说,便是所谓Saga这一类的作品。……至于寓言与童话,因为形式上不同,似乎应当分离。动物故事原是儿童文学的一支,但是文章简短,只写动物界的殊性,没有社会的背景,因此民俗学家大抵把他分出,不称他作童话了。”文中多是我想、最好、所谓、似乎、大抵之类的不确定性表述,既没有对童话做明确限定,也没有出示可供模仿和操作的研究范式,也就占了个较早提倡的先机。
周作人涉猎广博,到处蜻蜓点水,他的确为童话研究写过不少文章,也有不少好的见地,但多是提倡式、评点式的,他不容易同意别人,自己又不从事实际操作,不同文章的观点还前后不大一致,童话研究事业后继无人是其必然命运。赵景深大概是周氏童话学最忠实的接力者,但他的童话学理念与周作人还是有些出入,况且赵景深自己也在童话学与故事学两可之间反复游移。
顾颉刚的做法完全不同,“孟姜女故事研究”根本就不做拖泥带水的概念辨析,开篇单刀直入:“孟姜女的故事,论其年代已经流传了二千五百年,按其地域几乎传遍了中国本部,实在是一个极有力的故事。”等他把故事的来龙去脉给厘清了,读者惊喜、叹服的同时,突然意识到“小小的一则民间故事,竟然可以做出这样的大文章来” ,一时好评如潮。顾颉刚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借着《歌谣周刊》的影响力,掀起一股孟姜女故事讨论热潮,吸引了大批追随者。顾颉刚自始至终都没有讨论孟姜女故事到底应该叫故事还是童话,抑或野史、传说、戏曲、宝卷。他只管领着大家往前走,并不在意走出来的路该叫什么路名。相比之下,周作人更像一个旁观的智者,指着一片荒野对路人说: “其实那边也可以去试试,兴许能闯出一条叫作童话研究的道路来。”
到了中山大学时期,顾颉刚更是借助其学术与行政的双重影响力,招兵买马,成立民俗学会、创办《民俗》周刊、出版“民俗学小丛书”,团结了一大批学术同道。“民俗学小丛书”第一本是杨成志、钟敬文翻译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共收录了70个故事类型。这些故事是最符合周作人童话理念的,而早年的杨成志、钟敬文都是周作人的粉丝,他们特地在第67—70型式的故事名称后面加注了“(重叠趣话)”,这正是周作人“游戏童话”中的一个类别,可是译者并没有将书名译为“童话型式”,而是译成“故事型式”。钟敬文、容肇祖、刘万章先后编辑的《民俗》周刊,大量刊载故事素材及故事研究的文章,甚至连童话一词都罕见提及,原因非常简单,编辑者都在顾颉刚的麾下,理所当然应该沿着顾颉刚开拓的学术大道前行。
钟敬文离开中山大学之后,虽然他的故事学思想逐渐丰富成熟,对于故事概念的内涵外延也有了新的设想,但他始终高举着故事研究的大旗。钟敬文在杭州发起成立的“中国民俗学会”也办了一份《民俗周刊》,发表了34则故事(幻想故事为主),多以“某某故事”为题,彻底抛弃了童话概念。在故事研究的强势话语中,作为周作人童话学最忠实的追随者,赵景深孤掌难鸣,也只能将童话研究纳入故事研究的旗帜下求其友声。1930年的“民俗学小丛书”中有赵景深的《民间故事丛话》,收录了他过去两年间的十篇故事学书评和笔记,其中就有《亚当氏的中国童话集》《白朗的中国童话集》《孙毓修的童话的来源》等多篇童话文论,尤其是《俄国民间故事研究》一文,题名“故事研究”,内文其实是对《俄国童话集》的类型比较,文章中交替使用了故事与童话两个概念。
小结:学术史的因果与逻辑
上述“故事”的故事,貌似各自独立,实则有其内在的发展理路与逻辑结构,相互之间构成了一种微妙的竞争关系。
(一)在正统文人的故事观与民间文学的故事观之间,正统文人对于故事内涵的坚持,体现了传统精英文化尊古守制、敬重传统、崇尚文字传承的特征,而自明末至清末的白话小说中所记录、摹状的,出自老百姓街谈巷议的,对于故事内涵的解读和阐释,则体现了民间话语生动活泼、与时俱进,不断适应民众精神生活需求的特征。正是后者,使故事作为通用文类成为可能。
(二)近代通俗报刊注重以民间故事开拓市场。西方传教士修建育婴堂,兴办白话报,用通俗易懂的故事点化和启蒙中国儿童,他们对于儿童生命价值和启蒙教育的重视,以及对白话故事教化功能的开掘,一方面让故事以读者喜闻乐见的面目成为报章杂志的常见文类;另一方面启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故事文类的高度重视。以1897年创刊的《蒙学报》为例,作为维新变法时期重要的儿童启蒙刊物,虽然还放不下文言叙事的臭架子,但也注意到了故事文类的作用,刊发了许多图文并茂的“师范故事图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其欲与西方传教士争夺儿童启蒙话语权的拳拳之心,彰明昭著。商务印书馆更是尤为重视儿童市场,他们另辟蹊径,以孙毓修为核心,编译了大量童话(包括故事、儿童小说),培育了一个巨大的故事市场。
(三)故事市场的发育必然导致故事研究的跟进。“五四”运动前夜,知识分子对于平民文化的关注已渐成燎原之势,周作人、赵景深对童话研究的提倡,与顾颉刚、钟敬文对故事研究的大力推广,都是这一趋势的必然响应。作为研究对象的童话或者故事,对于对象名称的隐形较量,则反映了同为进步知识分子的童话学团队与故事学团队之间对于学术话语权的争夺。
故事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现代学术,就是在这样一种正统文化与民间文化、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以及不同学术共同体之间的话语争夺中不断推进,逐渐建立起来的。正是不同文化层级之间的各种竞争,推动了文化的进步,也推动了学术的进步。
文章来源:《民族艺术》2020年第1期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