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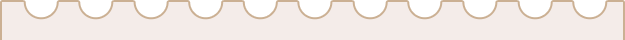
摘要:“民间宗教”是近代西方学术发展的产物,有其本来的学术语境和脉络。这一概念并不被它所描述的对象所使用,仅仅是一种学术语言的“建构”(construct)。它在东西方学术脉络中的演进,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信仰世界的研究范式。在跨越不同文化体系之后,“民间宗教”已经成为中国学术语言的一部分,但与此同时,它的基本内涵已经被改造的面目全非。它给中国学术界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迷惘。无论是偏向政治功能,还是偏向社会或文化功能,它一开始就被赋予了界定人群的功能,被理解为一种单一的意识形态或者社会阶层的身份认同。但实际上,“民间信仰”并不是单纯的“庶民信仰”,它是宗教教义的民间实践,是文本传统的草根体现,是精英解读在民间的倒影。在中国,所有宗教都在“间”,“民间”之外别无场域。
关键词:民间宗教 文化 思想史 海外中国学

“民间宗教 ”(popularreligion)或 “民间信仰 ” 概 念发源于西方近代学术。经过汉学家和历史学 家的改造,如今已变得面目全非。既有人用此概念专指不被政府承认的秘密教门(与官方相对 ), 也有人据此认为儒、释 、道之外的信仰和实践都 属民间宗教(与主流和正统相对 ),更有人强调 “民间宗教”是与文本传统不同的草根传统(与精英相对),等等 。鉴于此,本文将“民间宗教 ” 放在 “文化 ”的社会功能之下进行检讨,除了厘清它的学术发展史、考察西方学术变动对中国研究模式的影响外,同时也考察不同研究模式(国家/社会 、精英/大众 、中央/地方 、大传统/小传统 、文本传统/草根传统 )暗含之潜台词 ,进而重新审视 “民间宗教 ”。
一、民间宗教的学术脉络
在中国,虽然传统士人有排斥“淫祀”的文化倾向,但是“淫祀”的学术内涵和逻辑与现代学术话语“民间宗教”截然不同。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无论政府、士大夫还是宗教精英,都从未用过“民间宗教”这个名称来描述一般民众的信仰、仪式和象征体系。日本学者铃木岩弓认为,是姊崎正治(1873-1949)创造了“民间信仰”这一概念。朱海滨进而认为,“民间信仰”可能是直接由日本输入中国。然而事实上,姊崎正治的时代,日本也在西方学术的渗入和影响下发生着巨变;姊崎正治本人也是西方学术训练的产物。而且,在20世纪晚期之前,相关中文辞典中根本就没有“民间宗教”或者“民间信仰”这样的词条。即使是日本学者,也鲜有运用“民间宗教”概念来描述中国的信仰世界。大量地使用“民间/民族宗教”(popular/folk religion)概念,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学术界关于民间宗教的讨论,大多是在与西方学术界对话。
在西方学术界,“popular/folk religion”也不是从来就有的。以“民间宗教”(popular religion)对应“官方宗教”(official religion),并将其与不同社会阶层相联系(一般大众和制度性精英),是西方学术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研究框架。1757年,休谟(David Hume,1711-1776)提出了“大众/精英”(vulgar/literate)两分法。他认为,普通大众由于“自然的害怕”(natural fears)而信仰,但是知识精英从“真正的宗教”(true religion)中受到启示而信仰。彼得·布朗(Peter Brown)认为,休谟的“自然区分”至少在罗马晚期的历史中无法验证,真正把精英和大众区分开的是社会结构而不是“自然”。政治社会文化上的竞争导致了人群在宗教信仰上的区分。这样,文化区别最终在政治、社会那里找到了源头。
马克斯·韦伯用过很多词(比如,“Volksrehgwsitat”、“Massenreltgwn”和“Massenglaubens”)来描述民间宗教,这些词都能对应英语的“popular religion”。这些概念将民间宗教和特定的、在经济和社会结构中处于下风的大多数人联系在一起。但是,韦伯在研究早期以色列历史时也在思考,在特定的环境下,非特权阶层有没有可能和“官方宗教”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只要一种信仰或者实践体系在权力关系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它就会被描述成巫术和魔法之类的东西。权力在定义“民间宗教”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民间宗教”(popular religion)一词的出现,就是统治阶级把一种称作“民间宗教”的东西来定义。可见,这一概念一开始就跟人群界定联系在一起。
西方学者描述中国信仰世界的概念也是逐渐演进的。早期古典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Tylor,1832-1917)的《原始文化》(1871年)和弗雷泽(James G.Frazer,1854-1941)的《金枝》(1890年)将中国民间的信仰、仪式、象征等现象与原始文化列为同类。法国神父禄士遒(Henri Doré,1859-1931)在1912年所著的《中国民间崇拜》(Researches into Chinese Superstition)还依然用“迷信”(superstitions)形容中国的民间信仰。1915年,韦伯在《中国宗教》中也认为,中国本土的宗教只有儒家和道教,民间只有不属于宗教范畴的巫术和习俗。这些观点明显受到了古典宗教学的影响,认为中国民间信仰、仪式和象征虽然具有宗教现象的属性,但是与制度化的宗教不能等同待之,主张将它们与“多神信仰”、“万物有灵”、“迷信”、“巫术”等归为同类。
比“迷信”进了一步的是“教派”(sectarianism)。依据荷兰当局在印尼华人家中搜获的文书,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1840-1903)于1866年写成《天地会:中国和印度的秘密会社》,这是较早的研究中国秘密教门的著作,他用“会社”(secret society)来称呼自己研究的对象。1886年,博恒理(D.H.Pirter)的《山东秘密教派》和艾约瑟(Joseph Edkins)的《华北的教派》将原先被认为不属于宗教范畴的秘密教门,称为秘密宗教或者教派,这基本上就改变了之前不承认儒、释、道三教之外存在宗教信仰的观点。1903年,高延(J.J.M.de Groot,1854-1921)完成《中国的教派与宗教迫害》,也用“教派”(sectarianism)来称呼自己的研究对象。“教派”一词的频繁运用,表示这些外国观察者已经承认了中国民间信仰具有宗教的特征和属性,而不再仅仅是原始的“迷信”活动。
由于中国民间信仰的政治功能一开始就是西方汉学家们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在他们看来,民间宗教本质上是一种对抗正统政权的政治努力,宗教只是其外在形式,所以,在这种框架下,“民间宗教”便被改造成“秘密教门”或者“秘密宗教”,成为一种次级分类概念,不论是外延还是内涵,都无法与其本意相契合。
目前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以宋代为界,前后讨论的“民间宗教”内涵和外延都不相同。后者偏向于“秘密宗教”;而前者则更多地将民间信仰、仪式和象征看作是社会生活、文化体系的一部分,这一体系包括信仰(神、祖先、鬼)、仪式(祭祀、节庆、占卜等等)和象征(神系、符箓、对联、族谱等等)。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它不仅影响着一般民众的思维方式、生产实践、社会关系和政治行为,还与帝国上层建筑和象征体系的构造形成微妙的冲突和互补关系。
无论是偏向政治功能,还是偏向社会或文化功能,“民间宗教”作为一种研究模式进入中国,都强化了它的阶级属性。20世纪40年代,陈荣捷建议改变之前将中国人的宗教生活分为儒、释、道的做法,转而依据信众的社会成分,分为寻常百姓的层次和有知识者的层次。他把寻常百姓层次上的宗教称之为“民间宗教”。1956年,美国人类学者雷德斐(Robert Redfield)在《农村社会与文化》中提出“大传统”和“小传统”的概念,一时成为学者们分析文化结构的重要工具。他依然持知识精英的傲慢,认为“大传统”是由该文化中精英分子所创造的文化,是有意识、有传承的一种主动的文化传统;而“小传统”则是大多数民众所共同接受并保有的文化。这种视传统农业社会主要有两个阶层——“精英”与“大众”,或“统治”与“被统治”——所构成的观念,深刻地影响了学术研究。1961年,杨庆堃(1911-1999)将中国宗教区分为“制度化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与“普化宗教”(Diffused religion)两种。直到现在,这依然是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一个重要假设。
二、界定人群的“文化”:
阶级、革命、屈服与“民间宗教”
“民间宗教”研究范式的兴起,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革命理论对神学的解释密切相关。一种主流看法认为,民间宗教是被压迫阶级的文化表达方式,所以必须将之重新解读,以争取社会的公平正义。这种观点扎根于20世纪60年代左翼政治理论和社会运动实践中。
在中国,随着西方理论的大量输入,它颠覆性地重构了中国历史和文化。一方面,自秦朝往下的两千年历史被解释成“封建”的,类民间宗教的信仰和实践被斥为“封建迷信”,并将“封建迷信”描述为实现现代化的累赘;另一方面,革命理论也强调民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所以跟民众紧密相连的信仰和宗教实践又被赋予了朴素的革命意义,可以改造成革命和改革需要的文化。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相关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研究“封建迷信”和“现代理性”的关系,二是研究秘密教门与农民起义的关系。
中国传统话语中的“文化”与西方的“culture”都暗示了主流文化的霸权内涵。“文化”即“以文化成”,用我的“文”来转化你——对内教化百姓,对外则是“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西方的“文化”概念本身就暗含着现代化的目的论和西方对其他地区的优越感。它也是要“以文化成”,让你接受他们对历史和人类命运前途的解释,让你用他们的理论来匡正、清理本国的文化和传统。

把文化作为阶级或者人群的认同标志和象征符号的观念,是目前重要的研究理路。比如,柯律格(Craig Clunas)对明代的鉴赏把玩文化考察之后发现,这些看似无用之物却是文化精英建立和维持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艾尔曼(Benjamin Elman)关于科举的研究,就强调中国士人通过参加科举这种机制来建立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认同——考上考不上不重要,只要能参加科举,就已将自己与普通人区分开来。阿帕度莱(Arjun Appadurai)关于奢侈品的研究认为,特权阶层总是要冻结某些商品的流通(笔者按:比如,不得僭越的皇室用物、官员服装的不同颜色、特供商品等等),进而区隔出领导阶层与普通大众。争取放宽限制,扩大共享,往往成了政治斗争和社会变革的根源。同样的,作为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宗教既是人们想象人生与来世的解释体系,也是支配者用来创造社会秩序的手段。
凯瑟琳·贝尔(Catherine Bell)认为,从第一代汉学家开始,就专注于士大夫和普通大众的区分。比如,许理和(Erik Zürcher)就将佛教分为王室佛教、士大夫佛教和庶民佛教。在贝尔看来,这些区分都是将宗教视为不同“社会群体”(social groups)之间“界线”(boundaries)的标志。其基本前提就是认为文化具有阶级性或者具有垄断性,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文化,其文化标志着其“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许理和的研究影响很大,此后研究中国宗教信仰的学者,大多将民间信仰、仪式和象征作为某一社会人群的身份标志。比如,李四龙把佛教分为学理型佛教和民俗佛教。
在一些文化研究者看来,弱势文化存在一个“屈服”(subordination)的过程。就民间宗教而言,它到底是官方(精英、文本)意识形态的支持力量,还是民间象征抵抗的力量?屈顺天(James Watson)对天后的研究,证明了民间的方言传统可以被官方的大传统所吸收。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和他的学生丁荷生(Kenneth Dean)都认为,古典文本决定民间仪式。欧大年(Daniel L.Overmyer)、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和桑高仁(Steven Sangren)同样强调古典文本传统塑造或者影响了民间信仰。其实,早在19世纪,施古德就主张中国民间宗教是古典传统的衍生形式,民间文化(宗教)乃是精英文化(宗教)流传到民间后经过稀释、变质和庸俗化的结果。但这些观点也遭到了另一些学者的反对,他们认为,官方、精英、经典文化都来自生活,来自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实践。例如,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就认为,代表“精英文化”的《诗经》中有很多古代民间信仰的影子,古代民间宗教实际上是中国“精英文化”的根源,它起源于民间的生产和社区活动,官方、文本传统是它的“模仿”。而蔡彦仁认为葛兰言重建的《诗经》时代的民间文化只是出于他个人丰富的想象。葛希芝(Hill Gates)认为,官方文化无法完全控制通俗意识形态,比如在中国传统的官方意识形态中长期存在对交易和金钱意识的抑制,但是在民间宗教里“钱”的概念和象征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三、从“阶层”划分到“空间”划分:
“地方宗教”的兴起
新的概念的出现,往往不仅是表达方式的变化,还预示着学术潮流的兴替。20世纪70年代,威廉·克里思汀(William Christian)在研究西班牙宗教时,开始用“地方宗教”(local religion)代替“民间宗教”(popular religion)来描述他研究的对象。“地方宗教”比较好地避免了城市/乡村、知识阶层/普通大众的划分,将宗教现象在特定的区域、特定的时间描述出来,能够呈现出一个有传承的、统一的文化。克里思汀的研究影响深远,从一个特定的区域、特定的时间,依靠其本身的概念和材料来研究宗教现象,成为一种新的范式。从“民间宗教”转变到“地方宗教”,不但是西方“中国学”的一个转折,而且也是西方学术本身的一个发展趋势。
“地方宗教”研究模式的出发点是想回避“民间宗教”划分人群的倾向,将宗教现象放在特定时空内进行综合考察,是一种跨文化的尝试。不过,这种模式也创造了新的分隔,比如中央权威和地方认同的冲突。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在研究18世纪民间宗教时发现,文化精英和普通大众的关系不仅仅呈现为“宗教”(religion)对“魔法”(magic)的斗争,而且也表现为中央权威和地方权威的冲突。(34)西方的中国学者(主要是历史学家)们自80年代以来也逐渐倾向于把“民间宗教”放在国家权威、地方认同和社会需要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中进行考察,这成为当下民间宗教研究的主流。比如,玛丽·兰钦(Mary Rankin)强调政治权威和信仰的区隔,认定地方宗教活动为私,与精英所进行的官方及公共管理不同。万志英(R.von Glahn)强调中央政府对地方信仰的干预。屈顺天则强调中央政府和地方精英分子在地方信仰中共同发挥了作用。魏乐博(Robert Weller)相反,他强调地方宗教传统可以对抗政府的文化霸权,争取自己的利益。韩明士(Robert Hymes)通过研究江西抚州华盖山地方宗教传统发现,政府和地方精英们赞助地方神祇的动机截然不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也认为,当地方精英们的利益与政府一致时,他们非常乐意配合推广;但是当利益相左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支持未经许可的社区宗教传统。
地方宗教研究的兴起跟西方转向中国地方史研究相呼应。70年代以来,美国研究宋史的学者开始关注宋代的变化。郝若贝(Robert M.Hartwell)的研究为以后地方史研究崛起张本。韩明士(Robert Hymes)、包弼德(Petert Bol)等继之而起。在此稍后,中国学术界也逐渐开始强调民间信仰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比如,赵世瑜认为中国的地理区隔与地方传统两因素造成了民间信仰具有不同的内容和仪式活动,而民间信仰是地缘集团(如乡社城镇)、血缘集团(如家族宗族)、职业集团或性别集团强化凝聚力的重要途径。
其实,英文的“地方”(local)一词应有三重含义。一是地理概念,对应于“首都”(capital)。如果强调的是地理概念,那么京城本地的信仰,是不是地方信仰呢?二是政治概念,对应于“中央权威”(centeral authority)。三是文化概念,对应于“普遍性”(universal)或者“经典式”(classical)。那么,作为历史学家所描述的地方宗教,至少应从上述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四、穿越社会阶层的“文化”
精英/大众的两分法之所以容易被中国学者接受:一方面,是持传统历史观的学者强调知识精英对社会意识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致力于消除中国知识界的精英意识也强调普通大众的创造性和对文化的主导。不论是那一方面,都无疑接受了文化具有阶级属性的假设。1979年,人类学家弗雷德曼(M.Freedman)检讨了上述观点,认为宗教的基本社会功能在于提供一套可以超越阶级地位、经济利益和社会背景的信仰、仪式和符号,让社会的全体都能够接受。中国的农民文化与士人文化不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弗雷德曼对文化整体的强调,导致他认为存在着一种“中国宗教”。其实,弗雷德曼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知之甚少,而且也不存在一种“中国宗教”。但是,他关于精英文化与农民文化关系的论述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
在西方,“理性的宗教”(rational religion)和“魔法”(magic)被认为是两个相对的概念。彼得·布朗认为,中世纪的“魔法信仰”(magic beliefs)并不局限于没有文化的普通大众,阶级差别和教育差别并没有在宗教实践层面上有多大的差别反映。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指出,通俗信仰与上层阶级的信仰世界没有什么区别,公元4-5世纪的历史学家们从来不会把任何一种信仰定义为大众的文化或者精英的文化。凯克赫夫(Richard Kieckhefer)认为,“超自然”(supernatural)在中世纪生活中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文化因素,不论正统的教会还是普通的大众,相信“魔法”是完全“理性”的选择。因此,所谓民间信仰不应该与精英、有知识、正统截然割裂。
在过去十年,西方新一代学者开始不断质疑是否能够继续使用“民间宗教”这样的概念作为分析工具。他们认为,“民间宗教”不应该是固定的概念,而应该是在不断变化的,而且它取决于书写者自己的立场。宗教象征体系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受不同的群体解释和再解释。神学概念不断被发展、修正和舍弃。民间宗教存在于跟官方宗教的创造性紧张中,它们在信仰和实践上都有重叠的部分,是一个整体。玛丽安·鲍曼(Marion Bowman)认为,在所有的人类活动中,理论跟实践总是不能完全一致的,不可能期望人们对同一信仰系统产生同样的感受和理解。为了全面理解宗教,必须将普通人的思想和行为纳入考虑,而不是仅仅探讨理论层面的部分。就个人而言,宗教是接受的宗教传统和个人信仰系统的混合。正如廖咸惠所论,不能将传统的儒士和官僚对于神鬼的理论批判,致力于破除神灵的迷思,批评庶民对于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当成他们与民众信仰截然对立的证据。以梁启超为例,一方面批评鬼神信仰给中国社会造成极大的伤害,一方面自己却经常私下探问死去者的灵魂。
唐·约德(Don Yoder)将“folk religion”定义建立在德语词汇“religiose Volkskunde”的基础上,意为“宗教的通俗文化层面,或者是通俗文化的宗教层面”。“religiose Volkskunde”最早是由路德派神父保罗·鸠斯(Paul Drews,1858-1912)在1901年发明的,最初的意图是帮助年轻的神父们更加好地在农业地区传教:农业地区的基督教信仰,跟正规的官方版本具有巨大的差异。他通过创造这个概念试图“拉近宗教讲坛与听众信徒的距离”。尽管约德依然将民间宗教和官方宗教相对立,但是他开始强调其实民间宗教只是“跟正规的官方版本”存在差异而已。
近年来,西方汉学家逐渐形成共识,民间信仰并非是单纯的“庶民信仰”,在现实中,精英阶层也享有同样的信仰。比如,太史文(Stephen Teiser)在研究盂兰盆节时就发现,“地狱”和“救赎”的观念被一般人民、佛教徒及知识分子从不同的角度接受。在他看来,“文化”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意识形态或者社会阶层的身份认同。多样性和一致性同样是“文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其实,民间宗教与大众文化、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它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它是宗教教义在民间实践的结果,是精英解读在民间的倒影。正如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所论,民间宗教及其组织在区域内的存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作为一个为不同的社会阶层所共享的体系存在;另一方面,它在不同社会阶层的眼中具有不同的意义。例如,关帝的信仰不仅在一般乡民中存在,而且在国家的地方代理机构和绅士中流行。不同的集团对关帝有不同甚至对立的理解,但是这些集团用同一象征来追求各自的利益。
总之,“民间”一词既不涵盖“通俗”之意,又暗示与正统、官方对抗。中国到底有没有一种“正统”、“官方”的宗教都成问题。佛、道二教与后发概念“民间宗教”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作为“场域”的民间,似乎不为所谓“民间宗教”所垄断,一切的信仰、仪式、象征体系,都以“民间”为舞台,中国所有宗教都是“民间”的。“民间”之外的场域又是什么呢?区分场域对“民间宗教”的意义何在呢?实际上,经过汉学家和历史学家改造后的“民间宗教”这个概念过于宽泛,它无法成为令人满意的学术分析模式,以至于学者们尽量避免使用这个词汇,转而采用更加确定的比如节日、祭祀、神话、医疗、占卜等词汇。而且,尽量用描述对象自己的语言来描述历史也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准则,毕竟我们所描述的那个时代,有“佛教”、有“道教”,但是绝对没有“民间宗教”,“民间宗教”仅仅是学者们发明的一个帮助研究的框架。至少,这个框架只能在研究者所用材料严格分析的基础上才能理解,只能在认同“文化”可以穿越社会界线的情况下才能理解,只能在持续不断地分化和冲突过程中才能理解;特别重要的是,在研究中国宗教信仰时,需要“矫枉过正式”的去阶级化。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1年11期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