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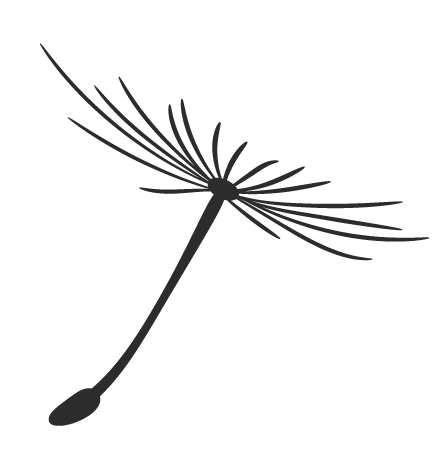

20世纪困扰人类的七大瘟疫
不可不说的环境因素
2009年3月底4月初在大洋彼岸发端的甲型H1N1流感,遍布了全球近40个国家和地区,还伴有持续蔓延的势头,这不禁让人感叹全球化在缩小了区域距离的同时,让传染病的流传也变得更加便利。其实,传染病的流传史一直都是和人类的交往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引发传染病的病原体随着人类活动而传播,又反过来影响到了人类的活动。这样,人类从分散到整体的全球史,同时也就成为病原体实现全球瘟疫“一体化”的历史。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种人、疫共生的全球史的演进历程,是与人类生存的大环境和小环境紧密相关的。其中大环境是指人类在大范围内的交往行为,它是关系到一般传染病能否从一个族群传播到另一个族群,并形成跨地区转移进而发展成为大规模烈性传染病——瘟疫的基本因素。小环境则指特定族群在特定地区的居住环境、生活方式和医疗条件等,它是关系到传染病最终是否可以发生,或者说病原体能否成功在人群之间传播的基本因素。
小环境的变迁与瘟疫的兴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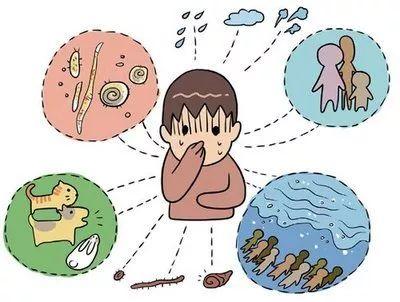
从人类的起源到约1万年以前,人们散居各地,谋生的手段主要是采集果实,间或以狩猎作为补充。英国学者庞廷(Clive Pontine)等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与动物、族群与族群之间的接触机会都比较少,故而传染病也较少发生。但大约从1万年前开始,人们逐渐定居下来,并实现了对多种动物的驯养,也使得后者身上的病原体成功侵入人体,其中一些从此还在人体内安家落户,成为典型的人类疾病。而对人类来说,几乎所有的传染病都源自动物携带的病原体。对此,美国学者戴蒙德(Jared Diamond)也指出,“人类疾病源自动物这一问题是构成人类历史最广泛模式的潜在原因,也是构成今天人类健康的某些最重要问题的潜在原因”。当年甲型H1N1流感的爆发,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人类在驯养动物的同时,也开垦耕地、种植作物,从而也拉开了人与病原体之间大规模生存博弈的序幕。从公元前5000年左右直到19世纪中叶,人类社会和病原体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且病原体似乎始终占据着上风。对于人类而言,小环境固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如居住条件不断改善、营养结构日趋丰富、医疗水平得以提高等,但医疗史学家们倾向于认为,这种改变并不能阻止病原体的侵袭,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会成为其滋生和散播的介质:人类大量聚集在狭小的空间内,并且这种空间往往人畜混杂,卫生境况糟糕。人们对传染病的医疗认识极其有限,有些应对措施如大规模的集会行为等很可能还会适得其反。
大环境促使全球瘟疫“一体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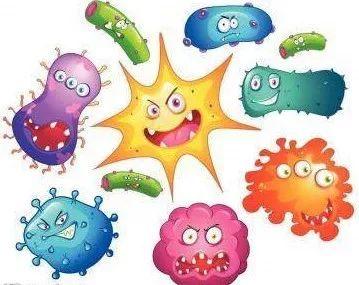
病原体之所以得以肆虐,还要归功于历史学家们普遍关注的大环境因素:大规模的对外作战是将地球变得越来越小的最主要方式,也是病原体开疆辟土的最佳途径。此外,不间断的土地垦殖使自然生态受到破坏,一些新兴的传染病也可能随之发作,而日益频繁的对外贸易也在瘟疫的流传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如法国史学家拉杜里所言,这些条件使得全球瘟疫“一体化”。
从大约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500年,是城邦、国家初步建立并彼此倾轧、建立地方霸权的时期,我们也在亚述和巴比伦的记载中发现了发热病、肺结核和鼠疫。从公元前500年左右开始,地区性的强国纷纷向周边地区开战,建立了第一批大帝国。病原体随之跨地区作业,如在罗马帝国东征西扩建立巨大版图的过程中,大瘟疫不可避免地数次爆发。在西罗马帝国的衰亡中,来自东方的匈奴人所携带的病原体或许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真正实现了瘟疫在欧亚大陆一体化还是在中世纪。14世纪的“黑死病”发源于中亚,然后随着蒙古铁骑和东西方商人的足迹传遍了欧洲,造成了欧洲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损失。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让人类在空间上基本完成了全球化之旅,而天花也成为病原体一统天下的代表。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病菌(还包括其他病原体)的印第安人触之即亡,总人口在一两个世纪内减少了95%。
近世环境变迁下的瘟疫图景
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和殖民主义的扩展,“最令人害怕、最引人注目的19世纪世界病”出现了,这便是霍乱。究其原因,从大环境上来说,殖民行为和民族冲突让区域间的交往变得更加复杂和紧密,城市化的进程则加速了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从小环境来说,工业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污染特别是河流污染,卫生条件变得更差了。这种局面让消化道病原体活跃异常,并最终发展成了世界性瘟疫。幸运的是,这些传染病引发了19世纪中叶开始的公共卫生变革。细菌学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医学思想上的革命,一种又一种病原体在显微镜下现身,人们逐渐掌握了传染病的传播机制,并有意采取措施控制。其中,大环境中的检疫制度与小环境中的隔离措施有力遏制了瘟疫的传播,而疫苗和抗生素的研发则为人类增加了一套“人造”免疫系统。
进入20世纪以来,在人类对大环境和小环境的干预中,更多的卫生因素被考虑进来。尽管随着交通工具不断地更新换代,地球逐渐“村庄化”,但人口的流动特别是长距离的流动却渐趋规范化,这使得大环境在加快了病原体传播速度的同时,却有效控制了它们的传播途径。而对于小环境来说,人们的居住环境更加整洁,卫生设施愈发健全,清除了许多病原地的聚集死角。随着这一系列公共卫生体制的不断健全,鼠疫、天花、霍乱等传统传染病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这绝不意味着人类对病原体的胜利。当人类的免疫系统和医疗水平可以有效控制传统病原体时,后者往往以变体的形式进行反击,如在1918—1919年间,被称为西班牙流感的世界性大瘟疫,导致了1500万到2000万人的死亡,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而这一瘟疫便是由特定恶性流感族群的演化所导致,这种演化后的流感病毒,正是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一种变体。另外,在1980年代才首次被确认的艾滋病今天已是世界公敌,据研究,其HIV病毒可能来自于非洲野猴。这不禁让人感叹,到底还有多少病原体,还将从动物身上袭击人类!
在大环境与小环境两方面努力

瘟疫史就是病原体与人之间的生存博弈史,人类的大、小环境的不良状态,使瘟疫的传播成为可能,而人类对大、小环境的改善又把瘟疫的生存范围压缩在了有限的范围之内,但瘟疫也在为谋取生存空间而不断产生新的变体。西班牙流感爆发90年后,我们又处在甲型H1N1流感等病毒变体的危险之下。一方面,我们不应该过于恐慌,因为西班牙流感的高死亡率要部分归因于当时小环境的不良影响,以及大环境中战乱所带来的交往混乱。而今天高水平的公共卫生体制和医疗救治水平,已经在控制瘟疫流传和救治患者方面初见成效。但另一方面,对全球瘟疫一体化历程的回顾警示我们,不可盲目乐观。要真正有效地控制瘟疫,减缓甚至阻断病原体的传播,就必须在大环境方面加强出入境检验和全球协作,并努力维护和平,避免战争之类非常规交往方式的出现。在小环境上,我们要继续改善民众的饮食、居住、医疗等条件,注意生活方式的文明化,特别是要努力弥补地区差异,减少瘟疫发源地的数量。唯有如此,我们才可以在面对病原体的进攻时,保持审慎的乐观。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年第7期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