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民俗学
[美]阿兰·邓迪斯
王曼利 译 张举文 校
21世纪初的民俗学状况不容乐观:全世界的民俗研究课程被废除或遭到了严重的削弱。阿兰·邓迪斯认为“宏大理论”创新的持续缺乏以及众多给这一领域带来坏名声的业余爱好者是导致民俗学学科衰落的原因。邓迪斯分析学员民俗学水平低下的原因有三方面:一是许多人只阅读坎贝尔的书而对民俗学的其他方面知之甚少,二是知识的缺失,三是民俗资料提供者的胁迫。尽管民俗学现状并不令人乐观,但波罗的海诸国的民俗学活动使他看到了民俗学的希望,民俗学并不是一门逐渐消失的学科。
【关键词】民俗学;衰落;宏大理论;坎贝尔
图1 :阿兰·邓迪斯像
21世纪之初的民俗学现状令人感到郁闷不安。全世界的民俗研究生课程被废除或遭到了严重的削弱,一度著名的哥本哈根大学学术课程不再存在,德国为了成为民族学中心而改变了民俗课程的称谓。甚至在赫尔辛基,这个民俗研究的真正麦加,赫尔辛基大学研究生课程的名称也做了改变。根据网页显示,民俗研究专业,连同民族学专业、文化人类学专业以及考古学专业一起,行政上隶属于文学院和文化研究学院。后一个称谓在我听来疑似文化研究,而从事文化研究的是想成为文化人类学家的文人。我不愿去考虑民俗学者与这样的追名逐利者为伍。而在美国这儿,情况更糟。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神话学和民俗学的博士课程被包含在世界艺术和文化这一类中,民俗博士学位成为舞蹈艺术专业扩展之后的几个学位之一。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民俗和民俗生活博士课程实质上已经崩溃,除非输入新的教师成员,否则这一情况将得不到改善。甚至连印第安纳大学,美国民俗学研究公认的堡垒和灯塔,也把民俗学与民族音乐学联系在一起看成是一个行政单元。结果,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民俗学本身不再拥有纯粹独立的博士课程,这种情况在我看来很糟糕。
有些人可能会以为这些行政转换只不过是你们中的那些认为“folklore”这一术语作为我们学科名称并不适合的人所引起的名称替换讨论的反映而已。瑞吉纳·本迪克斯(Regina Bendix)敏锐地观察到威廉姆·汤姆斯所杜撰的“folklore”这一术语本身也是一种名称替换(从拉丁文造词的“民间古俗”到盎格鲁-撒克逊语的“民俗”;1998:235),她的这一结论非常正确。但是,我相信她同时又犯了一个十分糟糕的错误,她认为造成该领域名誉不好的原因部分在于“folklore”这一术语被同时作为学科研究对象以及该学科的名称使用。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早有定论,19世纪的几个民俗学家已经对此做出了完美的解答,这其中包括莱因霍尔德·考尔夫(Reinhold Kohler),他用“folklore”(民俗)来指称学科研究的对象,用“folkloristics”(民俗学)来指称对于该学科对象的研究。“folkloristics”这一术语至少可以追溯到1880年。1996年,埃里克·芒特纳尔(Eric Montenyohl)告诉我们,“‘folkloristics’这一术语当然要比‘folklore’更为现代。关于该学科和学科对象之间的区别,以及各自的恰当术语在1980年进行了讨论。而在那之前,folklore既指对象也指研究该对象的学科——引起混淆的原因不止一个。”(1996:234)芒特纳尔大概是指布鲁斯·杰克森(Bruce Jackson)发表于1985年《美国民俗杂志》上的同样无知的文章,在那篇文章中杰克森抱怨“folkloristics”这一术语,并建议将其禁止,因为好像任何人都能够制定语言用法一样。杰克森引用了罗杰·亚伯拉罕(Roger Abraham)所说的是我创造了这个术语的玩笑话。我当然没有创造这个术语。1889年12月7日,美国民俗学者查尔斯.G.利兰(Charles G. Leland)(1834-1903),在新近成立的匈牙利民俗协会的致词中,谈到“民俗学的消逝”是历史上意义最为深远的发展之一(Leland,1890-1892)。如此看来,即使视野狭窄的美国民俗学者没有意识到,就像语言学是对于语言的研究那样,民俗学是对于民俗的研究,而且它已经存在了一个多世纪。尤里·沙科洛夫(Yuriy Sokolov)在最早出版于1938年的《俄国民俗》教科书中,认可了这种区别,并将书的第一章命名为“民俗性质和民俗学问题”。芭芭拉·科尔申布拉特—基布列特(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在同样是发表于《美国民俗杂志》(1985)上的一篇辩驳性文章《民俗学:一个不错的依地语词》中指出了沙科洛夫的这一用法。她也评论了阿克·哈尔特克兰兹(Ake Hultkrantz)在他重要的《普通人种学概念》(1960)中,将“folkoristik”作为“民俗科学”的同义词使用。因此,民俗和民俗学的区别,不是一个新的观念,在我主编的《民俗研究》(1965)的序文《什么是民俗》中,我尽可能清晰地对它做了陈述或“重申”。我很遗憾丹·本-阿默斯(Dan Ben-Amos)和艾利奥特·奥里恩(Elliott Oring)他们在《美国民俗杂志》1998年各自的论文中,对于该学科在其他方面进行了卓越、热烈的辩论,但都没有重申民俗学和民俗之间的重要区别。相反,我很高兴罗伯特·乔治(Robert Georges)和迈克尔·欧文·琼斯(Michael Owen Jones)把他们的实用教科书命名为《民俗学导论》(《Folkloristics:An Introduction》),并且他们在书的第一页就强调了“folklore”(民俗)和“folkloristics”(民俗学)的区别(1985)。简·哈罗德·布鲁范德(Jan Harold Brunvand)在他1968年出版的主流教科书《美国民俗研究》第一版中没有把这个术语包括在内,到了第二版本(1978),他决定把这个术语收录到这本书的第一页,此后的版本(1986,1998)凡涉及“民俗研究”都保留这种用法,但是他坚持在该术语上添加引号,这表明他并不是完全地接受了它。但是,我注意到在近来的学术界,“folklorisitics”(民俗学)这一术语越来越多地被人使用,我相信这是很好的预兆。
我并不建议把American Folklore Society名称改成Folkloristics Society of America。相反地,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是,确切地说是为什么民俗学、民俗学术研究这一成为每一个主要大学和学院所提供的课程一部分的学科,处在如此明显的衰落中。另一个令人遗憾的相关迹象是《南方民俗》杂志转换成了《南方民俗季刊》。这曾是美国主流民俗杂志,我希望我们南方众多的学院或者大学中某个有魄力的民俗学者能将这个杂志复兴。我认为衰落有其原因,我也同样认为衰落的一些责任要由美国民俗学会的全体成员(包括我在内)来承担。我猜想你们中的一些可能会认为我也许赞同发表于《通用语》(Lingua Franca)1997年10月号的那篇预言“民俗作为自治的学科可能注定消失”的令人极度沮丧的论文(Dorfman, 1997:8)。这篇宣布民俗学学科如同一个垂死的人的论文,因为其通俗文化标题“那就是所有的俗民!”借用《疯狂曲调》和《快乐旋律》中邦尼兔的惯语而更加令人觉得受侮辱。口吃的猪小弟说的这些话,意味着卡通的普及。但是,本质上将民俗领域与生动的卡通等同起来的这一时髦用语作为文章标题的用法那是很普遍的。我还不知道有哪位民俗学者写过表示反对或反驳的文字,尽管我努力地去寻找。我很抱歉地答复,《民俗学复活》没有在《通用语》上发表,尽管它确实公布于杂志的网站(www.temple.edu/isllc/newfolk/dundes2.html)上。在我的答复的最后一段写着:“当美国历史步入了多文化差异被歌颂的时刻,正好是文明的大学管理者鼓励这一可以一直追溯到赫德约翰与格林兄弟的国际学科的从业人员的时候。在认识民俗对于促进种族自豪的重要性方面,以及为发现世界观和价值的本土认知种类和模式提供宝贵的资料方面,这是一个先于其时代的学科。”《通用语》的确发表过一些表示反对的简短文字,这其中包括来自印第安纳大学的一篇标题为《民俗结束了吗》的文章,但是署名的是莉斯·洛克(Liz Locke)和其他80位研究生,而非印第安纳大学全体教员。无论是印第安纳大学机构还是美国民俗学会,都没有表示反对的文字。很显然,在我看来,当我们的学科受到侵犯时,学院和公共部门的民俗学者都不愿站出来进行捍卫。在这个时候,美国民俗学会的领导阶层到哪儿去了?这是不是正如谚语所说的“沉默即同意”?美国民俗学会是不是曾经认为或者现在仍认为作为学科的民俗是无生命力的?我可以顺便补充一下,《通用语》1991年创刊,2001年结束,但它的早夭毕竟只是《通用语》杂志的早夭,而非民俗的夭折。我很乐观地说,民俗研究已经成功地经受住了悲观的预言,并将继续走下去。
在我看来,大学中民俗学科衰落的首要理由是,被我们称为“宏大理论”创新的持续缺乏。按照《通用语》的说法,“民俗被认为是在理论化之内的”。艾利奥特·奥里恩,我们少数几个民俗理论家之一,在他的文章《关于美国民俗研究的未来:一个回答》中简洁地将其作为插入语:“民俗正好是阈限,因为它既没有理论也没有方法论来控制它的前景。”(1991:80)任何一个理论学科所具有的犀利必须建立在理论概念和方法概念上。民俗学固然已有一些,但是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在19世纪或20世纪初期创立的,直到现在既没有被取代也没有被补充。极为有意思的是,关于民俗的大多数宏大理论是由扶手椅子民俗学者或图书馆民俗学者而非田野工作者所提出。我想起詹姆斯·弗雷泽爵士交感巫术原理的形成或者麦克斯·缪勒对于太阳神话学的思索。甚至在20世纪,宏大理论也的确是来自于不具有田野工作者资格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相反,大多数田野工作者,在涉及当地的社区时,并不总是关心他们所搜集的材料的理论意义。
从历史的观点来说,民俗学学科来源于古物研究,或者是我所称为的对奇异的或者是古怪的东西的寻求。我在本国和海外的民俗中心访问时,时常会看到我命名为“蝴蝶收集”(butterfly collecting)的东西。民俗事象被看做是罕见的新奇事物,好比一个钉子钉住了它们并将之安放在用来展览的档案袋中,因此很难想象民俗事象永远是鲜活的(即,被表演的)。语境被忽视,只有文本被当地的收集者所珍视。因为这些本应该具有理论或方法观念的当地收集者并没有这样做,该领域的这一空缺留给了那些书斋式学者如弗雷泽来填补。而在美国,正是因为脱离实际的或是书斋式的学者的缺乏扩大了非理论空间。尽管我们图书馆资源丰富,信息技术处理大量数据库的能力无限,美国的民俗学者却没有对民俗理论和方法做出宝贵的贡献。几乎每一个应用于民俗学的可行的理论和方法概念都来自于欧洲。但是,我认为好的概念来自于哪儿这并不要紧。民俗学是一门并将永远是一门国际性学科。因此,我们很乐意使用法国民俗学者范·哲乃普(Arnold Van Gennep)的“过渡礼仪”(rites of passage)的概念,芬兰民俗学者卡尔·科隆(Kaarle Krohn)的“历史-地理方法”,或者瑞典的民俗学者卡尔·威廉·冯·赛多(Carl Wilhelm von Sydow)的“积极的传承者”和“地方类型”概念。但是所有这些概念都形成于19世纪末或者20世纪初。关于民俗的新的假定和推论又在哪儿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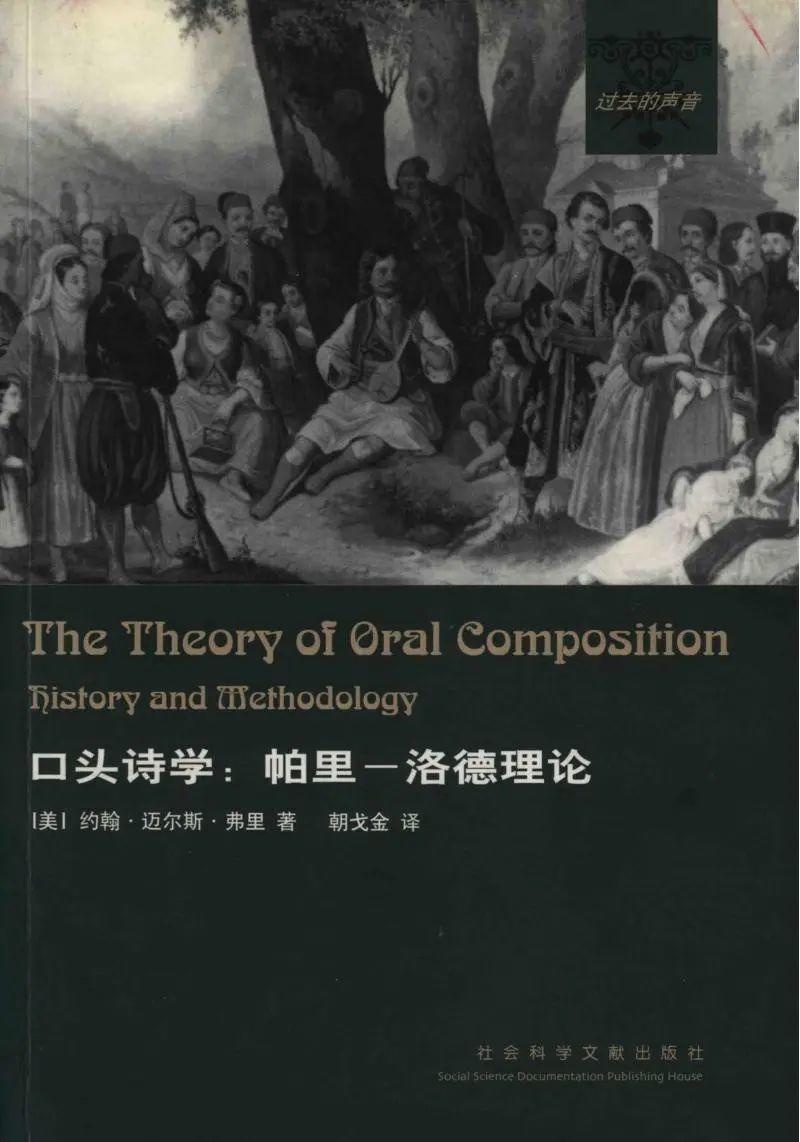
[美]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
现在,我可以想象你们中的一些民俗学者,特别是那些浸透着相当多的国家主义与自豪感的民俗学者正在对你们自己说:“等一下。美国人曾对理论民俗学做出过贡献。不是有女权主义吗?不是有表演理论吗?不是有口头程式理论吗?”尽管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和艾尔伯特·洛德(Albert Lord)因为发展了口头程式理论而受到赞扬,但约翰·弗里(John Foley)揭示了该理论来自于他们之前的欧洲学者(1988:7-15)。这种情况类似于弗朗西斯·查尔德(Francis Child)对于英格兰和苏格兰民歌的权威收集,毋庸置疑是效仿丹麦民俗学者斯文德·格朗德维格(Svend Grundtvig)的丹麦民歌的大规模处理或者斯蒂斯·汤普森(Stith Thompson)对于芬兰民俗学者安蒂·阿尔纳的故事类型索引的修订。美国民俗学者,很大程度上是追随者,而非引导者。我不得不承认我所陷入的这种范畴,是从俄国民俗学者弗拉基米尔·普罗普的《民间故事类型学》(1968)和奥地利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那儿得到的灵感。

[美]斯蒂·汤普森:《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
至于女权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所谓的“理论”究竟是什么呢?尽管以“女权主义理论”为题的书和文章很多,但是却找不到这种“理论”到底是什么的严肃阐述。社会中妇女的声音和角色受男性沙文主义和偏见的压制这种观念的确是真实的,但是那种真实性难道就能构成严格意义上的“理论”?“表演理论”又是什么?没有哪个民俗学者会否认只有当民俗被表演时它才存在,而民俗的表演包括参与者和观众,并且表演中的能力问题是被记录和分析的一个特征,但是表演理论中的“理论”在哪呢?我不认为所谓的女权主义理论和表演理论是“宏大理论”。正如我所关注的,它们只不过是“我们应该研究的被表演的民俗”、“我们应该对民俗学文本和语境中对于妇女的描述更加敏感”这样的自命不凡的说话方式。
真正宏大的理论能够使我们了解那些如果没有该理论就会像谜一般的资料。考虑从不在穿着的衣服上缝钮扣或者修补的这一犹太迷信,我们可能会观察到一些比较早的宏大理论继续在产生着洞察力。提供这一迷信的人,如果被询问,并不能够将这一信念下的可能的解释清楚明白地揭示出来。但是在弗雷泽顺势疗法巫术(homeopathic magic)法则的帮助下,我们能够相当轻松地解释这种风俗。唯一的一次当一件衣服穿着时被缝上钮扣是在尸体即将下葬的时候。因此,衣服在穿着时被缝上一颗掉落的扣子,或修补衣服撕破的地方是把穿这件衣服的人当做一个尸体,有效地表示或预示这个人可能很快就会死去。不用惊讶它被认为是这样一种禁忌。
关于水手民俗,我们知道在船板上吹口哨不吉利。我还记得我在美国海军服役时因为吹口哨被船长惩罚。为什么在船上禁止吹口哨?宏大理论再一次帮助了我们。根据“相似产生相似”这一弗雷泽顺势疗法巫术法则,哨声是暴风的模仿。恰好有一个民间隐喻“(吹口哨)招来风雨”。风无疑是航行时所必须的,但是太大的风则不是所愿望的,因为它可能会导致船只倾覆从而沉没。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曾经阐明过的宏大理论,能够继续产生洞察力。
正如你们中的许多人所知道的那样,我发现被认为是宏大理论的精神分析理论,使得我们彻底了解别的途径无法说明的民俗学材料。例如,有一个日本迷信,“怀孕的妇女不能打开烤箱门”。提供资料的人可能会说如果那样就会带来晦气。但是从烤箱和子宫的象征类同所获得的知识(甚至美国民俗中的习语所证明的怀孕妇女“在烤箱中有个小圆面包”),我们可以知道这是弗雷泽顺势疗法巫术的又一次应用。打开烤箱门会引起流产的发生。既然这样,我们不得不使用弗洛伊德和弗雷泽的理论来充分解释这个迷信。关键是大多数迷信的收集本,和多数的民俗——谚语或者民间故事——收集一样,无论什么都不提供解释。让我们再举一个运用精神分析理论来解释令人迷惑的民俗事象的例子。
从中世纪的西班牙到现代的拉丁美洲,为人所知的最流行的一首西班牙民谣是“戴尔尕迪纳”(Delgadina),它有500多个版本被发表。著名的西班牙民歌研究者雷蒙·曼南德兹·皮德尔(Ramon Menendez Pidal)说,这首西班牙民谣“凡是有西班牙语的地方就一定能找到它”(Herrera-Sobek,1986:91),并坚信“在西班牙和美洲,‘戴尔尕迪纳’毫无疑问是最广为人知的罗曼史”(1986:106)。民谣大意如此:“‘戴尔尕迪纳’讲述的是一个妇女反抗其父亲乱伦求爱的故事,为此,她被关了起来,并被喂以很咸的食物,但是却得不到水喝。”(Mariscal Hay,2002:20;Goldberg,2000:148,母题T411.1亲想与女儿发生性关系。被女儿拒绝)关于民谣的大量知识都倾向于把它作为父女乱伦,特别是对西班牙家庭结构中独裁父权极端厌恶的平实反映(Herrera-Sobek,1986),但是对于这首民谣为何会流行几百年而长盛不衰一直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戴尔尕迪纳是国王所生的三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在一些版本中她的穿着很性感,这其中包括“透视装”。这首民谣的许多版本中有关于谁应该为父亲想让戴尔尕迪纳成为自己的情妇这一企图受谴责的争论。通常是戴尔尕迪纳受到姐姐或者妈妈的谴责。其中有一段诗节,当戴尔尕迪纳徒劳地乞求妈妈给她一壶水喝时,她妈妈说:“走开戴尔尕迪纳,走开你这个邪恶的婊子/因为有你在,我当了七年冤屈的妻子。”在一个西班牙系犹太人的版本中(Aitken,1928:46),妈妈答复道:“自从有了你,犹太畜牲!自从有了你,残酷的野兽:因为你,这七年来我生活在不幸的婚姻中。”值得注意的是这首民谣是典型地由一个女人唱给另一个女人听的(Egan,1996)。因此,很明显这是一首女人的歌(Aitken,1928)。女儿幻想父亲跟她母亲在一起时并不幸福,而更喜欢和她在一起。正如艾特肯在她1928年的那篇文章中所表达的,女孩妒忌她的母亲,并且认为,“我与母亲比起来,我的父亲真的更喜欢我,他想让我越过我的姐姐,处于她的位置上。”(1928:48)
在类似的西尔瓦娜民谣中是这样安排的:母亲趁女儿睡觉的时候代替她去预先安排好的地方和国王父亲会见(Goldberg,2000:100,母题Q260.1)。我认为在这个版本中,有温迪·多尼格(Wendy Doniger)提到过的“睡眠把戏”(2000),我将它称做“投射反向”(projective inversion)(Dundes,1976、2002)。如果我们察觉到这首著名的民谣只是对俄拉克特洛厄故事的细微伪装,我们就能知道它表现了女儿的痴心妄想。她爱她的父亲,并希望代替她的母亲和父亲睡觉。这个被禁忌的愿望通过投影为父亲企图诱使他的女儿而得到转换。母亲替换了父亲床上的女儿是禁忌愿望的完美倒置。母亲替换了女儿,而不是女儿代替了她的妈妈,因而将女儿从禁忌的乱伦性行为中挽救了出来。明确涉及的女儿被喂盐的情节让我们想起了AT923,“爱如同盐”(李尔王情节的基础),同样牵涉国王父亲企图与他的女儿发生乱伦关系。这个情节也让人想起AT706,“没有手的少女”(Brewster,1972:11-12),它是以民谣形式出现的,同样被我理解为是投射反向的显著事例(Dundes,1987)。可能有人也会提到劳特的妻子这个十分明显是俄拉克特洛厄故事,在女儿们诱奸了她们酒醉的父亲后,她变成了盐。
不管是否同意这些解释,人们肯定能发现如果不求助于宏大理论,在这里,是指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理论以及我对投射反向概念的适度扩充,这些解释将是不可能存在的。就西班牙文化中父女乱伦投影长期流行的原因而言,值得记住的是天主教教义的中心情节包括上帝在没有征得处女的同意就使她怀了孕,又一个暗示着投射反向的俄拉克特洛厄幻想。简要地来概括:“我想诱奸我父亲但那是被禁止的,所以在投影中是我的父亲诱奸了我。相比较我母亲的惊恐,心理上的优势使得我并不内疚。这不是我的错,是我的父亲想要我。”天主教派中这个情节的流行也可以由《圣·戴夫娜传》来证明。在她母亲死后,她的父亲,一个名叫达蒙的爱尔兰异教徒酋长,想找一个女人来代替他的妻子,为此他寻遍了全世界,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直到有一天他回到家看到了和她的母亲一样美丽的女儿戴夫娜。他向女儿求爱,但是戴夫娜逃跑了。在比利时,他找到了戴夫娜,但是当她拒绝屈服时,他杀死了她。在结尾的分析中,女儿的死或者她把自淫的手切了下来的事实象征她最终因为自己最初的乱伦愿望而受到处罚。目前,无可否认,宏大理论的特定类型还没有被传统主流的民俗学者所广泛接受。但是我想指出的是,没有这个或其他的宏大理论,民俗文本将永远只是那种具有少量实质内容分析或者根本没有实质内容分析的文选。每一次当又一个非分析的民俗收集被发表的时候,民俗学者仅作为收集者、分类者和档案管理员的陈规又各自被强化了。
而这引起我对民俗学这门受敬重的学科衰落的第二个主要原因的关注。第一个原因,我在上文已谈到,是宏大理论的缺乏,第二个原因,我认为,是专业民俗学者在数量上远远不及给我们的领域带来坏名声的业余爱好者。2004年6月的第一个星期,我被邀请参加为纪念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诞辰一百周年而在亚特兰大召开的名为“神话历程”的会议。这次活动是由神话想象学院组织、约瑟夫·坎贝尔基金会和亚特兰大荣格协会支持,包括疆界(Borders)音像书店和音乐、抛物线杂志以及克里斯派·克莱米基金会在内的大量团体和企业赞助。尽管有许多座谈小组以及许多关于民俗的叙事(不只是神话),出席的专业民俗学者却不多。推荐者包括故事讲述者、艺术家、电影摄制者、荣格精神分析者,还有极少数自认为是民俗学者的人。在去亚特兰大之前,出于好奇我查询了一些我的小组讨论同伴和推荐者。我很震惊地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小学院里的教学人员,他们在名单上列的是民俗学教授和显然是讲授他们称做“民俗”课程的人。该课程是在文学作品中寻找荣格的原型,包括J.R.R.托尔金(J. R. R. Tolkien),或者探究坎贝尔的合成词“单一神话”(“monomyth”)的表现,“单一神话”这个术语与严格意义上的神话并无多大关联,更确切地说是基于传说和民间故事的结合。目前除了建立法西斯极权国家之外,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美国民俗学会阻止这样的“民俗学者”讲授他们所认为的“民俗”。罗伯特·乔治写了一篇文章,针对许多人在没有受过正规训练或对该学科做过研究的情况下就宣称自己为民俗学者表示反感(1991:3-4)。人们能够想象一个不曾受过物理学或数学正规训练的人声称自己为物理学者或数学家吗?乔治同样对许多被当作民俗学者训练的人隐蔽事实声称他们从属于别的学科的行为表示失望。此时,我忍不住想向你们提供关于某个民俗学者拒绝承认他的学科归属的最坏的例子。这件事情发生在1992年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对民俗深感兴趣的海地流亡总统吉恩—伯特兰·阿里斯泰德(Jean-Bertrand Aristide)被约定在校园内演讲。唐纳德·考森提诺(Donald Cosentino)那时是民俗和神话课程的主席。按照惯例在这种场合下,首先是高层官员在主席台上欢迎听众,然后把话筒交给考森提诺让他来介绍演讲者。而就在这之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大学副校长私下对考森提诺说:“我们这里来了一位州长。我呆会儿介绍你的时候会说你是英语专业而非民俗和神话专业的主席。以免自惹麻烦。”考森提诺按照指示,在介绍阿里斯泰德时没有表明自己是民俗和神话课程的主席。这件事让我感到愤怒的不是大学副校长令人不可容忍地侮辱我们的领域,而是考森提诺没有对此表示反抗,相反他怯懦地加以默许。我可以断然地说,如果我处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不在台上公然地抨击副校长,我也会把他私底下跟我说的话公布出来并自豪地宣布我的职位是民俗和神话主席。换句话说,我会设法使大学副校长感到困窘,而不是他令我和我的领域困窘。这是我们学术史上的一件真正可耻的事件,《通用语》杂志上提到的第一个要抨击的事件(Dorfman,1997)。
事实是我们似乎被伪装为民俗学者的非民俗学者的大众化作家所包围。假设一个人走进像巴诺(Barnes and Noble)或者疆界这样的商业书店查看“民俗和神话”类,他会发现什么呢?必然会有许多希腊神话选或者主要容纳希腊和罗马神话学词条的神话学词典,编者所重述的——“重述”一词为专业民俗学者所强烈谴责——特别是为儿童所修订的世界各地的故事卷。最后,至少有半数以上的书是约瑟夫·坎贝尔所编。我回想起几年前在伯克利的巴恩斯和诺贝尔书店发生的一件事。尽管我更喜欢二手书店,但我有时候也会为了知道是否有我所需要了解的新书而去逛逛商业书店。在那里,我发现自己找不到民俗和神话学类的书放置的地方。它显然是被移动了,因为书店经常改变书架和书类的安放位置。最后我让书店的一个职员指点我民俗和神话学类图书的位置。通常在这样的书店里,书类会被清楚地标明:宗教、社会学、自助等等。而民俗和神话学通常只简单地标注着大写的粗题字母“约瑟夫·坎贝尔”。令我感到震惊的是全部的民俗和神话学类都包含在坎贝尔的名字之下。我记得稍微能让我放宽心的是至少我的书没有一本放在那一类之中。我提及这件令人沮丧的事情的唯一目的是为了说明对于许多文化公众而言,民俗研究只意味着坎贝尔和他的著作。至今,专业民俗学者很少谈论坎贝尔编著的大量文集。我不知道在《美国民俗杂志》上是否曾有过对于他的任何一本书的评论。这是否就是“沉默即同意”的情况?相比较别的任何途径,更多的人很有可能是通过坎布尔的著作或者他在美国公众电视网上的一系列电视讲座从而认识和熟悉了民俗问题。但是我们的民俗学者却很少谈论或根本不提及他和他的理论。
我的论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新的宏大理论的缺乏,以及对于大量业余爱好者和那些成功宣称他们所占有的民俗领域是其封地的业余艺术爱好者所做的有效努力估算不足,导致了民俗学被公众理解为是一门薄弱学科,而这种理解不幸被学院和大学管理者过分频繁地使用。美国民俗学会从它诞生起,其目标一直是专业化民俗学学科。《美国民俗杂志》应该是表达新的理论和方法进步的主要论坛,而杂志的书评部分应该是对于那些分析民俗学资料的业余尝试的批评与反驳。我并不是谴责过去或者现在的《美国民俗杂志》编辑在这方面的不足。他们只能发表作为美国民俗学会成员的民俗学者的我们所提交的论文。因此我们必须接受对于我们学科状况的责备。相应地,要靠我们去履行对我们所深爱的领域的诺言,向所有相关的人证明,民俗学是一门有着自己有效理论和方法的世界级的全球性学科,我们不能因为大众化作家和业余爱好者的食言而遗弃我们的领域。伪民俗和民俗学主义到处大量存在,我们冒着被具有绝对数量的混合着创造性写作的民俗文选淹没的危险。
6月份在亚特兰大举行的神话历程的会议,极好地将网站和图形结合起来。屏幕上出现了一幅世界地图,人们可以点击不同的地区(民族),随之该地区/民族的神话就会伴随着洪亮的叙述而出现。多么令人印象深刻!而在屏幕底部还有各种各样的选项。其中一个选项是“写出你自己的神话”。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许多10岁和11岁的孩子接受了这个挑战,并将“他们自己的神话”用电子邮件发给了网站。令我恼火的是,当我给一群小学或者中学老师做了关于民俗的演讲之后,一位热情的老师随后说她充分认识到了神话的重要性,这也是为什么她鼓励她的二年级学生写神话作为一次练习的原因之所在。不用奇怪这些孩子长大后会对神话究竟是什么感到困惑,并成为我们都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神话英雄的坎贝尔这一论点的狂热者。
[美]约瑟夫·坎贝尔:《千面英雄》
很显然,迄今为止还没有民俗学者对坎贝尔做过任何评论,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评论一下坎贝尔。部分问题是因为坎贝尔并不真的知道什么是神话。他1949年发表的《千面英雄》所提供的大部分关于民间故事和传说的例子,也没有将神话与这两种类型真正区分开来。他的例子包括小红帽和豪猪型星星丈夫,但民俗学者并不将这两者归为神话。坎贝尔设法描绘了一种世界英雄模式,但是他并没有提到哈恩(J. G. Von. Hahn)在1876年区分被他命名为雅利安英雄驱逐和回归模式(Segal,1990:vii)特征所做的最初的先驱性讲话。坎贝尔也没有提到奥托·兰克(Otto Rank)最初发表于1909年开拓性的《英雄出生神话》,或者洛德·拉格伦(Lord Raglan)1934年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于《民俗》,不久又于1936年以书的形式出版的著名的英雄传纪模式(见Dundes,1965)。
让我们更多地谈论一下《千面英雄》,这是坎贝尔最初的更是其最知名的书。他是怎么想到这个易引起共鸣和让人印象深刻的名称的呢?1940年,坎贝尔遇到了一位虔诚的拉纳克利西纳(Rarnakrishna)信徒尼克兰娜达哲人(Swarni Nikhilananda)(Larsen and Larsen,1993:283)。在《千面英雄》中,坎贝尔引用了尼克兰娜达哲人对于拉纳克利西纳先生福音书的译文(Campbell,[1949]1956:115)。我们知道坎贝尔是因为拉纳克利西纳先生的著作而产生兴趣(Larsen and Larsen,1993:283-6)。在《印度文化遗产》第二卷,关于拉纳克利西纳先生百年纪念,尼克兰娜达哲人写了一篇长达176页的名为《拉纳克利西纳先生和精神复兴》的评论(1936:441-617)。我们知道坎贝尔阅读了1936年的论文,因为他在1960年的论文《作为玄学家的原始人》中做了引用。考虑一下尼克兰娜达论文中所提到的引自拉纳克利西纳的话:“被称为克利须那神的他也叫做湿婆神,此外也可以称做女神、耶稣和阿拉——一个有着一千个名字的罗摩……一个在不同的名字之下的实体”(1936)。我们知道坎贝尔是一个真正的如饥似渴的读者,也是一个善于吸收他所阅读的东西的大师。我们从未确切地知道,但是细节却与坎贝尔的题目有着奇异的类同。我们只是将“英雄”替换了“罗摩”,“面孔”替换了“名字”,从而得到了“一个有着一千张面孔的英雄”。注意,我这里所辩论的是灵感,而非剽窃。无论哪种情况,坎贝尔的名著都会被称为“规模浩大的引人入胜的英雄神话的研究”(Elfwood,1999:143)。但是坎贝尔分析的这个叙述并不是神话,而是民间故事和传说。
在他对于严格意义上是民间故事母题的“魔幻飞行”的讨论中,坎贝尔将詹森寻找金羊毛的故事也包括在内([1949]1956:203-4),但这与严格意义上的神话毫不搭界。更确切地说它是一个英雄传说,故事中没有提到世界和英雄的创造。由于坎贝尔对于“寻找”主题的持久兴趣,对于他频繁引用亚瑟王资料那就不足为怪了([1949]1956:300),这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论文所研究的课题(Larsen and Larsen,1993:75),包括所提及的圣杯的寻找。但是这样的亚瑟王故事明确地说是传说,而非神话。在坎贝尔《上帝的面具》四部曲中的第四卷《创造性神话》中,他重述了哥特弗雷德·范·斯特拉斯堡的特里斯坦(Gottfried von Strassburg’Tristan)以及乌尔弗雷姆·范·埃切恩巴奇的帕西发尔(Wolfram von Eschenbach’Parzifal)(亚瑟王传奇中寻找圣杯的英雄人物)的传说。重要而卓著的中世纪文学名著中,没有哪个通过民俗学想象的展开可以同时被认为是神话。坎贝尔认为霍尔弗雷德利用了“一个完全世俗的神话”(1968:476),但是神话是神圣的,而不是世俗的。这些文本最多可以被解释为文学传说。但是两者都明确包括与圣杯相关的寻求。坎贝尔也认为,托马斯·曼恩(Thomas Mann)和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是神话制造者。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创造性神话学》并不涉及专业意义上的“神话”。更确切地说,它是一卷宽泛意义上的文学批评。考虑到坎贝尔并不清楚什么是神话,不用奇怪他的无数追随者会同样感到困惑。这个不幸被许多作者就这一对象所共同使用的“神话”的宽泛定义,似乎证实了格雷格里·汉森(Gregory Hansen)关于民俗(包括神话)的定义伸展得如此之开,直到包括了万事万物的这一批评。一些神话书的作者包括神话标题之下的“B”电影和小说的作者。正如汉森所说的,“问题是如果现在万事万物都是‘民俗’,那么就无所谓‘民俗’了。”(1997:99)
坎贝尔将民俗学者范·哲乃普的通过仪式模式进行改编后应用到叙述中,这的确是极富洞察力的,但是普遍主义者建立在心理一致(psychic unity)——即,所有的人都拥有相同的神话结构——基础上的假定则是不正确的。在《创造性神话》怪异研究第四卷《上帝的面具》中,坎贝尔自己谈到了《英雄》:“在《千面英雄》中,我已经指出神话和神奇故事……属于我称为‘英雄冒险’的一般类型里,在经历了人类文字记录的历史后,本质形式没有发生改变。”(1968:480)
很长一段时间,神话的业余研究者都有一个普遍的幻想,即所有的人共享着同一个故事。很显然这是一种痴心妄想。坎贝尔提到把英雄模式作为一个普遍的单一神话,这个空洞的新造混合词是他从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Campbell,[1949]1956:30-35)中借鉴过来的。经验性事实从另一个方面提出了关于普遍性的问题。没有哪个单一的神话是普遍的,这个陈述与坎贝尔的观点背道而驰。他被邀请就代达罗斯(Daedalus)这个特定的问题写一篇论文专门收入1959年的《神话和神话创造》,该期刊还收录了摩萨·伊利亚达(Mircea Eliade)、克莱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和理查德·道尔逊的投稿。坎贝尔以他当时现成的《上帝的面具》系列中的绪论为基础,开始了他的《神话学的历史发展》的写作,“世界神话学的比较研究促使我们把人类的文化历史看做一个单元;因为我们发现像盗火、冥土、处女分娩、英雄复活的主题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分布,就像万花筒的原理,尽管主题并没有变化,但是似乎到处都有新的组合”。(1959:232)即使是刚起步的民俗研究者都会对这种论点感到怀疑。做出关于普遍性的权威声明很容易,但要想去证明它们却很难。以处女分娩为例。如果我们查询《母题索引》,我们会找到母题T547,处女分娩。关于这个母题只列了三处引文。一个提到了欧洲圣徒,另一个是古典希腊神话,还有一个是南美印第安人的资料。此外,我还不知道有没有非洲的处女分娩故事。在《母题索引》中也没有引证西伯利亚、波利尼西亚,或者是美拉尼西亚的故事。从原来的澳大利亚到新几内亚,我们记录了许多神话,但是很显然那里没有处女分娩的故事。因此我们能够接受坎贝尔单凭信仰所主张的处女分娩是全世界分布的吗?在《千面英雄》中,有整一章节都是关于处女分娩的([1949]1956:297-314),但是所引用的关于第一个男人与他的妻子们、与女儿们性交从而生出了孩子和动物的非洲文本,很难说是一个令人信服的处女分娩的例子。在他的普遍性的列表中,坎贝尔也提到了洪水。在我编辑的《洪水神话》中,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确定非洲沙哈拉地区本来就没有这个神话(1988)。
坎贝尔极为轻率地选用民俗资料来证明他所谓的英雄模式。例如,在名为“鲸腹”的章节中,坎贝尔引用了约拿故事,我确信那些西方种族中心主义的读者赞同将《旧约全书》中的这个叙事认为是该主题的理想范例(尽管就学术上而言该动物并非真的被看成是鲸)。坎贝尔接着引用了第二个说明性例子“一个被狼吞吃了的德国小女孩小红帽”([1949]1956:91)。该叙事当然不是神话而是一个民间故事,即阿尔纳—汤普森故事类型333,故事并不是关于男英雄的,而是讲述一个女孩成为了女英雄的故事。坎贝尔模式是平等地应用于女性还是仅就男性而言(cf. lefkowitz,1990:430)?这里所谓的吞食者不是一头鲸而是一只狼。但是,我们知道,更为重要的是,以女孩为中心的民间故事口头版本(相对于男性如查尔斯·皮劳尔特[Charles Perrault]以及格林兄弟所修订的文学版本而言),女孩并没有被狼所吞掉。相反她假装需要出来澄清而最终逃脱了。这样看来,因为小红帽是个女英雄而非男英雄,又因为她没有被狼吞掉(在韩国、日本和中国的版本中是老虎),所以该故事并非是证明“葬身鲸腹”这一神话模式全世界普遍存在的最好依据。
尽管缺少证据,坎贝尔似乎对于世界性民俗的存在毫不怀疑。在这方面,他倒退到了19世纪的心理一致说。大多数民俗学者同意相似物的出现归因于一元发生说和传播论而非多元发生说,但是这并非坎贝尔的立场。他的理论,如果我们也能如此称呼的话,主要建立在阿道夫·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毫无确实根据的“原初”(Elementargedanke)概念,或者是作为卡尔·荣格原型观念先驱的元素概念(elementary ideas)之上,两者都被坎贝尔不加批判地予以采纳(1972:44,1968:653;Campbell and Toms, 1990:68)。在他为盖泽·茹黑姆(Geza Ruheim)1951年纪念文集所写的《传记和神话:神话科学绪论》(Bios and Mythos:Prolegomena to a Science of Mythology)中,坎贝尔做了清晰的陈述:“然而,最为重要的是不忽略这样的事实,即神话原型(巴斯提安的元素概念)割断了文化领域之间的界线,它不再被限定于任何一个或者两个文化领域之中,而是在整体中被不同地表现。”(1951:333)坎贝尔最后,据他自己承认,相比较弗洛伊德他更喜欢荣格,尽管在《千面英雄》(Campbell and Toms, 1990:121)中,他运用了两人的概念,并且他似乎接受了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概念。“神话”,依照坎贝尔而言,“是集体无意识的表达”。但是,与荣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有时候的确接受这样的事实,即传播可以说明神话中跨文化相似的出现。(1990:123)
最令我感到烦恼的仍旧是坎贝尔坚持原型的存在。考虑一下《以神话为生》(Myths to Live By)里的这段话:“我的一生,作为神话学的研究者研究这些原型,我可以告诉你它们确实存在,并且全世界都相同。”(1972:216;原话为强调)荣格认为存在着与全人类所共有的个人无意识相对的被推测为集体一部分的全人类前文化土著形象,并且这些本能体现在梦中和民间叙述中。这些原型的数量很有限:伟大的母亲,智叟,儿童,四段式(fourness),等等。正如专业的民俗学者往往容易忽略坎贝尔并且未能对他的全部作品做出批评,同样的他们也未能对荣格及其原型概念进行批评。但是,在书店的那些名义上包含着民俗方面书籍的区域,我们发现了与坎贝尔的书几乎一样多的民俗学荣格精神分析理论研究。为什么没有民俗学者对于原型观念的批评?我认为相比较原型观念,业余爱好者所传播的个别观念更加不利于严肃的民俗研究。我发现它总是被无知的学者,以及那些无论何时我总有机会给他们做民俗公共演讲的大众所引用。除了精神一致以及普遍主义毫无根据的假设之外,原型问题,在荣格关于儿童原型的经典论文中已非常清楚,是这类简单证明的一种应用。引用荣格的话:
通常孩子是按照基督的样子被塑造的……有时,孩子出现在花瓶中,或者刚从金蛋中破壳而出,或者位于曼荼罗的中心。在梦中,他往往是以做梦人的儿子或者女儿,或者是一个少年男孩,或者是年轻女孩的形象出现,有时候似乎具有外国血统,是一个有着微暗肌肤的印度人或者中国人,或者看起来更符合宇宙法则,被星星环绕着或头戴布满星星的小皇冠,或者是国王的儿子或是有着恶魔品质的女巫的孩子。在“难以获得的财宝母题”的一个特殊例子中观察到,儿童母题变化多端,采用了所有的外形,例如宝石、珍珠、鲜花、圣餐杯、金蛋、金球等等。这些相似的形象可以彼此交换,并且几乎不受任何限制。(荣格,1958)
这种批评方法的问题是,在如此多的外观中如何确定其原型?当我们偶然遇到民间故事中的“金蛋”时,我们怎么知道这是儿童原型的表现?这里我们必须要想到荣格自己的方法格言:原型是难以定义的。我们只能渐近地或是略微地接近它。荣格反复重申这一点。因此,如果原型是不可知的,我们怎么知道它们?另外的理论难点是这些假定的原型依其申述是全人类的以及前文化的。因为它们是前文化的,所以它们只是在边缘受到了文化条件的影响。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了解到为什么那些主要研究什么是“文化”的文化人类学家,对于假定的前文化实体是否来自生物社会学或者荣格理论的这一学说并没有多大兴趣。附带地,我要责备一下弗洛伊德,部分是因为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原型存在的假定。弗洛伊德最严重的错误之一是他认为海克尔“个体发育重演了动物种类进化史”的生物学发现同样可以应用于精神产物。为了解释某一不断出现的白日梦的多种存在形式——例如,成人的诱惑,父母性交的观察,对于阉割的恐惧——他提出了以下的推断:
这些空想的需要和材料来源于何处?毫无疑问它们来自于本能;但仍需要被解释的是为什么得到相同满足的同一个幻想只要时机成熟就一定会产生。对此我有一个也许在你们看来相当大胆的答案。我认为这些原始的幻想,我喜欢这样称呼它们,毫无疑问和别的一些东西一样也是种族演化发展而来的天赋。利用这些天赋,个体超过了他自身经验而到达他自身经验根本还未发展到的原始经验。在我看来极有可能的是,现今所有被作为幻想讲述分析给我们听的事情——儿童的诱惑,通过观察父母性交而达到性兴奋的燃烧,对于阉割而非阉割本身的恐惧——曾在人类家庭的原始时期真实地发生过,幻想中的儿童只不过是用史前的事实来填补自身事实的缺口。(1916:370-1,1987)
这是一个明确的,尽管有点令人怀疑的陈述。如果个体在他或她的生活中没有象征或是幻想,那么象征和幻想将会通过重现动物种类演化的个体发育来提供。或许弗洛伊德运用这一原理最著名或是最声名狼藉的例子是《图腾和禁忌》中的结论。在承认仅仅是杀死父亲的想法就会引起儿子的罪恶后,弗洛伊德最后认为杀父行为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用原始游牧部落兄弟联合起来杀死他们的父亲来说明俄狄浦斯情结和图腾信仰与禁忌。按照弗洛伊德推测,这是因为原始人不同于现代人,他们并不羞怯内向,因此“想法直接转化为行动”。《图腾与禁忌》的最后一句话是弗洛伊德动物种类演化倾向的直接结果:“因为那个原因我认为我们可以很好地采用我们正在讨论的例子,虽然不能确保结论的绝对必然性,那就是‘太初有行’(the beginning was the deed)。”(1938:930)
弗洛伊德的演化遗传幻想明显可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相比较,其错误部分是由于他设法使心理学成为历史学。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整个理论基础本质上与19世纪的民俗理论,源于单线进化理论的遗留物学说是相同的。成人神经病症状本质上是幼年或童年早期所发生的创伤情况的遗留。为了了解或解释这种明显已失去理性的症状,分析家不得不通过自由联想和梦的满足从童年早期开始来推想这幅较完整的图画。很显然,这与安德鲁·兰描述的“民俗方法”相类似。兰在比较考古学和民俗时谈到,“这是一种研究民俗的形式,即收集和比较古老种族相似的非物质遗迹,遗留的迷信和故事,我们的时代而非它那时的观念。”([1884]2005:11)该理论基于19世纪儿童—原始人的等式。正如原始人经历了野蛮而进入文明一样,儿童经历了青春期而进入了成人期。为了了解成人民俗(即文明社会中的遗留物),我们需要找到存在于当今野蛮(或者原始)社会中的较完满的形式。用兰的话来讲,“这个方法是,当一个显然是不理性的且反常的风俗在任何一个国家被发现时,寻找一个有着相似习惯的国家,而在这个国家中该习惯不再是无理性与反常的,而是和处于该习惯中的人们的行为与观念相协调……于是,我们的方法是将文明种族表面上没有意义的风俗和习惯与未开化种族仍具有其意义的相似的风俗和习惯进行比较。”(1884:21)最后,兰总结道:“在一个文明种族中,民俗表现了文明是从野蛮观念发展而来。”(1884:25)弗洛伊德同样看到了个体发育与种族演化之间的相似点。他在约翰·伯克上尉所著的《各民族关于粪便的仪匦》(Scatalogic Rites of All Nations)一书的德文版序言中写道:“民俗科学走的是另外的道路,但是尽管如此它却得出了与心理分析研究相同的结果。它向我们展示了不同的人们如何并不完美地成功抑制他们的粪便倾向,不同文明水平的排泄物功能的处理如何接近人类生命的婴儿阶段。联系通俗习惯、神秘惯例、礼拜动作和治疗技术,它向我们揭示了习语中原始的根深蒂固的粪便嗜好症。”(1934:ix)这或许说明了弗洛伊德对于考古学的爱好,也展示了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学术范例,那就是重塑过去。一块碎片,就像迷信或是神经病症状那样,是过去的遗留物,但是遗留物可以帮助重建过去。
所有的这些并不是在为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观念做申辩,只不过是为了说明弗洛伊德的想法可能是这个神秘观念的直接或间接的来源之一。关于荣格的原型仍有另外的理论难点,涉及一些基督教内容的原型。我已经提到荣格明确论及基督徒与儿童原型相联系。然而,更令人烦恼的是,荣格提出耶稣基督是一个原型。在他的论文《唉翁》(Aion)中,荣格问道,“自我是耶稣的象征呢,还是耶稣是自我的象征?”他回答说:“在现在的研究中我确认是后者。我设法去展现传统的耶稣形象如何在它自身集中一个原型——自我原型的特征。”(1958:36)我并没有教荣格如何讲。他自己添加了一句斜体字纪录的话,“基督例证了自我原型”,并且用一个脚注邀请读者去“比较我在《心理方法或三位一体教条》中将基督作为原型的观察。如果我们还记得原型是被假定为全人类的,能够组成最异乎寻常的极端民族优越感的例子,而不提及自大和傲慢或者东方民族特征——即,假定所有的民族不论其文化和种族传统,在他们的意识中都有一个固定的原型的基督徒部分”。(1958:36)荣格说:“原始心理不会创造神话,而是体验神话。”(1958:117)这大概也可以应用到基督原型。事实上,正是因为荣格的基督教倾向,对于弗洛伊德而言,他是使精神分析更易被非犹太大众所接受的可能的继承者,但是作为民俗的形式,那种倾向延伸到神话并不仅仅是智力可以防御或维持的。
坎贝尔研究民俗的方法是以荣格精神分析作为基础,正因为如此,使得这种方法处于学术民俗学的范围之外。精神一致的普救说前提,结合原型是通过遗传得到的主张,给文化相对主义的影响和地方类型的形成留下了极小的空间。遗传问题是一个争议较多的问题。听听荣格自己怎么说的吧。在荣格1961年去世前不久,即1958年发表的《灵魂和象征》一书的前言中,他说了以下这些话:
精神并不像白纸状的心灵那样是天生的。如同身体一样它在确定之前有其个体明确性,即生物习性的形式。它们在不断重现的精神机能的模式中显得很明了。正如织布鸟能够将其鸟巢按照通常的形式准确无误地建造出来(作者评说:这种理论类型总是提及众所皆知的自然界的本能行为:没有谁去教鸟儿如何做巢,海狸如何做坝,从而通过错误的类推得到说服)。原型绝不是无用的古老的遗留物或遗迹。它们是引起神秘观念或主导陈述预先形成的活的实体……应该记住的是我的“原型”概念常常被误解为是一种哲学的推论(作者评说:请注意荣格如何澄清这种很显然的误解)。事实上,它们属于本能活动领域,按照那种理解它们表现出了精神行为的遗传形式。(1958:xv-xvi)
很难相信任何人可以接受这样一个神秘的概念作为民俗研究中可行的观念,但是坎贝尔如此做了。我们如何对待咖啡茶几上作摆设的书中充斥着所谓的原型形象?当然,从不同的文化中创造出母亲的形象是可能的,但是这构不成伟大母亲原型存在的证据——全部文化所拥有的母亲及其形象那么多,但是几乎没有相同的形象。甚至是耶稣基督和圣母玛利亚的形象在西方文化中也有着根本上的不同,代表性地具有画家或赞助人身体上的种族面貌特征。弗洛伊德在其《幻想的未来》(1928)所主张的婴儿的条件作用与人-神关系有着重要的联系,于是婴儿的条件作用按照文化的不同而不同时,人—神关系也会随之变化,因此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神话。恒定不变的不是原型,而是人类的关系。在所有的文化中都有父母-孩子关系,因此在全世界的民俗中都有父母-孩子之间的斗争。
1944年当坎贝尔为格林故事中的罗马万神殿写注释时,他做了准备性工作。他引用了故事类型、《母题索引》,以及那个时代的民俗学者的著述中所包含的学术建构。他甚至提到了历史—地理方法,又叫芬兰方法,因为这是民俗学者为追溯特定的民间叙事的发展和传播所使用的比较方法的首选形式,但是他在脚注中认为弗朗兹·博厄斯是这种方法的运用者(practitioner)。坎贝尔在他的哥伦比亚的岁月里,事实上与博厄斯在一起做过研究,无论如何,他应该知道博厄斯从未使用过这种芬兰方法。但是坎贝尔的“极少的学问”指出了我们的其中一个问题。民俗学者有些成功地宣扬了过去200年我们所做的努力的结果,于是别的学科的成员,在做了最低限度的阅读之后,相信他们有资格去权威地谈论民俗学问题。这个世界似乎充满了自称为“民俗专家”的人,有一些例如坎贝尔,被普通大众(以及公众电视,像坎贝尔这种情况)所接受。我无法告诉你有多少学者如同伯克利民俗课程的申请人那样,在他们的兴趣陈述中说他们阅读并喜爱坎贝尔的作品。我猜想,如果那样理解的话,我们欠他太多,因为他使得人们对我们的学科感兴趣。问题是如此多的人只阅读坎贝尔的书而对民俗学的其他方面知之甚少。
我认为,有另外两个因素导致了学员中民俗学的低水平:(1)早先知识的缺失;(2)民俗资料提供者的胁迫。早先知识缺失的事实或许部分归因于在全部领域知识的激增。维持全部的关于民俗学的写作以及无数的杂志和世界各地的专论丛书日益困难。虽然有参考书目、电脑数据库和搜索引擎的帮助,但是仍有太多的重复作业。资料检索的问题因为意图代表我们领域的业余爱好者的不断增多而更为恶化。他们对其学科问题的早期研究很无知。我已经提到坎贝尔没能涉及奥托·兰克和罗德·拉格伦早期对于英雄模式的描绘,另外还有无数这样的例子。
20世纪40年代中期,古典学者莱斯·卡彭特(Rhys Carpenter)在伯克利市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做了很有声望的萨瑟演讲(Sather Lectures),稍后以《荷马史诗中的民间故事、小说和传奇》(1946)为题发表。在那本书中,我们想至少会提到AT1137,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或者是奥德修斯肩上扛着桨,在内陆中寻找未知社区的母题(Hansen,1990,2002:371-8)。但是以上的这些我都没有找到。相反,我们发现了贫瘠的主张,即《奥德赛》包含了熊的儿子这个民间故事的结构,卡彭特的这一假设是在得知弗莱尔德瑞奇·潘泽(Friedrich Panzer)和其他人所主张的贝奥武甫(Beowulf)来自于那个故事类型的学识之后提出的。1910年我们有了《故事类型索引》,1932年又有了《母题索引》。但是不只是一个古典学者在1941年没有引用《奥德赛》中如此明显的民间故事元素,而且,更为恶劣的是,一个大出版社竟能够在没有让民间故事的专家做正式出版前的检查就出版了该书。我们仅仅将卡彭特的书与比尔·汉森最近发表的杰出的《阿里阿德涅的线团:古典文学中发现的世界故事指南》(2002)相比较,来看一个有着民俗知识的古典学者与一个真正的具有民俗学者资格的古典学者所做研究的差异。
让我们引用“知识的缺失”的另外一个例子。1955年,雷·威廉姆·弗朗兹(Ray William Frantz)完成了名为《民俗在马克·吐温创造性艺术中的地位》的伊利诺斯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这是关于吐温在他的代表性作品中对于民俗的兴趣和利用的众多研究中的一篇。弗朗兹在《民俗在越橘芬兰人中的功能》(1956)这篇论文中发表了他的一些见解。他的成果与维克多·劳斯·维斯特(Victor Royce West)在1930年所写的《马克·吐温著作中的民俗》极为类似,该论文是由1928年他在内布拉斯加州大学的硕士论文发展而来。这些和别的许多尝试论证吐温对于民俗明确兴趣的文章(cf. Jones,1984)只要简单地调查一下美国民俗学会早期成员就能得到肯定。在《美国民俗杂志》的第一期中,我们看到“美国民俗学会成员”列表中包括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S.L.克莱蒙斯(S. L. Clemens)。吐温不但是美国民俗学会的发起人,而且据杂志上的成员列表来看,他至少做了五年的会员。这意味着在最初的五年他被JAF所承认,我们可以在逻辑上设想他很好地阅读了其中的一些内容。无论如何,倘若事实是弗朗兹和其他的许多关注吐温对于民俗可能的兴趣的批评家没有谁提到他曾是AFS的成员,我们可以指出这个忽略是明显的“知识缺失”的例子。这种事实信息(factual information),如故事类型1137,波吕斐摩斯,对于任何一个真正的学者而言包含了可用的知识,作为专业的民俗学者,我们的部分任务是提醒我们的学者和同事记得这些知识的存在。我同样把芒滕岳尔认为“民俗学”是一个现代术语归于“知识缺失”。
但是如果“知识缺失”成为民俗学进步的障碍的话,那么我所说的“资料提供者的胁迫”也是一种障碍。两个民俗学者,都是我所景仰的大学者,他们发表的著述有着最高水平的学术特点,他们都提倡不要写任何可能会冒犯任何一个资料提供者的文章。这些伟大的民俗学者中有一个强调他的资料提供者是他的朋友,他绝不会去写一些在他们看来是侮辱的或攻击性的文字予以发表。他用或许是其代表作中的一句话来表示他的满足:“某一个问题解决了。我写了论文且没有失去朋友。”(Glassie,1982:33)我知道成功的田野作业中所达到的和谐,往往会产生牢固的、温暖的,虽然可能不是终身的友情。但是将论文和专论的草稿给予资料提供者,让他们具有否决权,或者,至少是审查的权力,我认为是不能接受的。民俗学,和所有的知识分支一样,不应该退化为通俗辩驳。如果医生因为曾经告诉一个患有严重疾病的人需要立即治疗而受到精神的谴责,那么会怎么样?这当然不是病人最为关注的。虽然没有必要去故意冒犯一个资料提供者,但是对从那个资料提供者身上得到的所有资料进行最好的和最有启蒙性的分析是必须的。如果民俗学者担心他们的资料提供者会说一些不喜欢的话,那么这个领域增多的只是民俗档案馆中堆积如山的未经分析的文本。
有时候,问题涉及的是更为严肃的伦理问题,正如第二位主要的民俗学者的情况。这个民俗学者收集了几十年的那瓦霍人的民俗,他在这方面的知识是如此的广泛,以至于被邀请作为唯一一位不是那瓦霍人的演讲者给纯粹是那瓦霍人的听众做系列演讲。这当然是对这位民俗学者崇高的致意。在对这些听众讲了科约特郊狼的故事之后,他被年长的歌手提出的问题给镇住了:“你有准备失去你家里的一员吗?”它揭示了这个民俗学者未曾意识到的科约特郊狼故事中的一层关于巫术崇拜的内涵,提问者设法警告这个民俗学者他的研究正处于潜在的危险领域的边缘。民俗学者把这个警告放在了心上。在一篇描述这件事情的文章中,他谈到:“正像一个民俗学者需要知道从哪里开始,也需要了解到哪里结束,我决定就此结束。”(Toelken,1987:400)他接着说:“确切地说,一提到科约特郊狼故事的讨论,正如所看到的那样,必然与不科学的以及没有学问有关,我要使自己避免这样的信息。确实,如果那样考虑的话,这是一篇非学术性的伪论文,关于我将不再利用过去25年记录下的文本的伪报道。”(1987,400)这个故事甚至更为恶劣。它使得某个人的田野资料研究自动停止,并以同类的东西毁坏那些资料。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民俗学者的主要资料提供者死了,他就遇到了问题。他知道那瓦霍人极力避免与死者的交互作用,这包括听已死去的人生前所录的声音。在询问了已故的资料提供者的寡妇之后,民俗学者把六十多小时的原始田野记录磁带(以及他在课堂上与讲座中使用过的拷贝)装入盒中寄给了寡妇,他知道她会把这些磁带销毁掉。在《美国民俗杂志》上发表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文中,他描述了自己是如何做出这个痛苦的决定的(1998)。我的观点是不止他丧失了学术界不可再复制的资料,而且那瓦霍人他们自己也因此失去了宝贵的资源。我们知道许多本土美国人很感激民俗学者和人类学家早先所做的保留他们部分文化的工作,因为这些文化在他们人口遭到大批杀害以及在与美国主流文化的适应中不幸消失了。这毫无疑问是资料提供者胁迫的极端例子,但是如果连我们最优秀的民俗学者都不敢分析他们的资料,或者更恶劣的是推动那些资料的毁坏,我实在为我们的民俗学领域捏了一把汗。如果资料被毁坏了或者如果因为我们担心冒犯一些资料提供者或是同事而不敢充分地分析它,这个领域就不可能向前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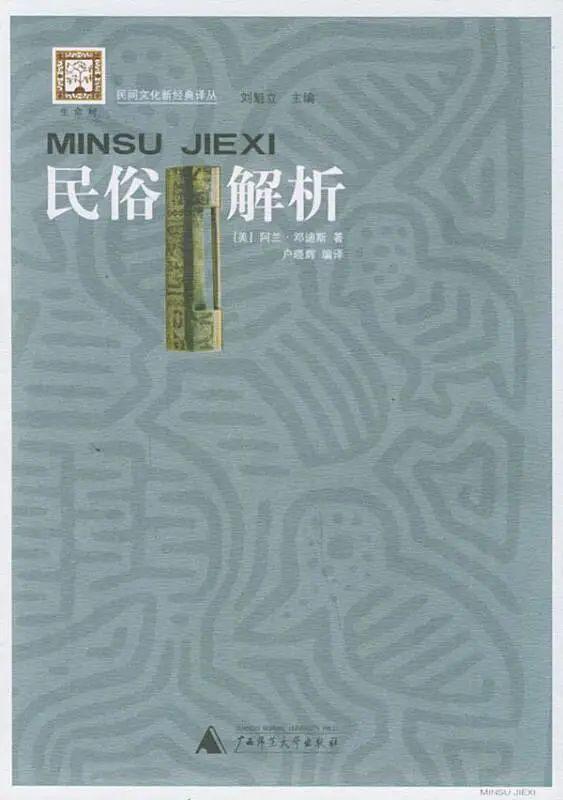
阿兰·邓迪斯:《民俗解析》
阿兰·邓迪斯:《世界民俗学》
我个人有几次应对胁迫的经历。第一次发生在1960年年末,我与别人合著完成了土耳其口头决斗的研究。意识到其中包含的一些资料在大多数美国中产阶级看来是淫秽的。我不知道向哪里递交这篇论文。最后我决定把它递交给《南方民俗季刊》,我写了一封信给有着印第安纳大学民俗博士学位的巴特勒·沃(Butler Waugh)编辑,解释说如果他不能同意发表这篇论文,我能表示理解。我很惊讶也很高兴地看到他在信中说他喜欢这篇论文并同意将其发表。这篇论文被接受后大概过了六个月,我意外地收到了爱德温·卡佩·柯克兰德(Edwin Capers Kirkland)的来信。此时,沃已经从佛罗里达大学转到了迈阿密的佛罗里达国际大学,柯克兰德是SFQ的临时代理编辑。这封信告诉我他非常遗憾,不能把我的那篇土耳其口头决斗的论文予以发表。所给的理由不是因为我的论点的中肯度或是资料报道的精确性,而是因为我的论文可能会冒犯佛罗里达大学的董事。我不认为这是这篇论文被拒的合理理由,特别是正式的编辑先前早已将其接受了。我给柯克兰德写了一封强硬的抗议信,并不是要求重新审议,而是抱怨这不是论文被拒的正当理由。美国民俗学会的一些年长的成员可能还记得这件事情,因为我的抗议还包括把我写的信的副本发给每一个主要的民俗学者,我知道我的目的是想让我的同行知道SFQ的承诺稍后可能会变得无效。不必说,我很痛恨这种没有胆量与骨气的编辑的决定,尽管我后来很高兴这篇有争议的论文在1970年的《美国民俗杂志》上发表了。
第二次受到胁迫或者审查是由于上一次我有机会在学会上演讲。这是1980年在匹兹堡举办的美国民俗学会年会上发表的主席演讲,距今已经20多年了。因为这类主席演讲在《美国民俗杂志》上是例行公事,我把最后的手稿交给编辑考虑。因为陈述非常长,他很恰当地把它转交给美国民俗学会的出版编辑。最后,我收到了一封拒绝信。拒绝的理由并不是因为贫乏的著述、不完善的论点或是不充分的资料,而是这份研究对于有着德裔美国人血统的美国民俗学会成员是一种侮辱。我发现这种推理是荒谬和无礼的,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有着部分德国人血统的美国人,但是我的确认识到了出版编辑的名字暗示了她自己是一个德裔美国人。我不知道这个编辑是否真的把它发出去做重新审查。这里的要点是,即使这个著作对德裔美国人而言真的是一种侮辱,也构不成不发表一篇做了充分调查的论文或专著的正当理由。正如你们大多数人所知道的,这篇文章直到1984年才发表。美国民俗学会的拒绝的确使得这篇文章延迟了四年才出版。
我也顺便说一下,事实上我的论文不止一次而是两次被不同的纪念文集所拒,理由是稿件将会得罪世界上特定部分的读者。匈牙利的奥图特(Ortutay)纪念文集,我递交了关于犹太人与波兰美国人的种族笑话的比较。最后,我被编辑告知在东方集团的成员中有一个不侮辱成员国同伴的协定。因此,发表任何取笑波兰人的笑话是与匈牙利的法律相违背的。然而,编辑说,如果我想修改我所递交的论文,关于犹太人的笑话仍然可以保留。考虑到我的论文的整体要点是比较两套陈规,我没有办法去掉全部的波兰笑话。当然,就个人而言,我对反犹太人的笑话被发表一点也没有问题的建议感到愤慨。我能够觉察到被纪念文集册拒绝不是简单寻常的事,而且我应付过两次。第二次是我的一篇关于东欧人政治笑话的论文被菲利克斯·奥纳斯(Felix Oinas)纪念文集所拒绝,因为怕得罪预期的苏联读者。这与我早期向《东欧季刊》递交的一篇关于罗马尼亚笑话论文的经历很相似。那个杂志的编辑承认他知道大多数笑话并知道它们是传统的,但是他因为担心这篇论文如果出现在杂志上,东欧将会取消订阅该杂志而拒绝了这篇论文。奥纳斯纪念文集的拒绝令我感到尤其伤心,因为作为他以前的学生,我非常爱戴已故的奥纳斯,我非常相信他个人会很高兴将我的论文收录其中。出于原则,我决定拒绝递交另一篇“非冒犯”的论文作为代替的邀请。
最近一次受到胁迫是关于我最新的一项研究成果,在这个研究中,我将民俗学的口头程式理论应用于可兰经。国内外的同行劝告我不要去做这项研究。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叮嘱我,这样做太不安全了。看了我已完成的用口头程式理论对于可兰经的研究(Dundes,2003),一位值得信赖的同行最终承认,我的分析当然是对的,但是从政治上而言这样做是不正确的。在伊斯兰世界里,将先前世俗材料分析中所使用的理论运用到可兰经的研究是一种亵渎神明的大胆行为,并且在西方,学者因为担心得罪阿拉伯世界的同行,所以一些理论上可以做的研究他们绝不会想去做。结果,无论是阿拉伯学者还是西方学者,都没有谁去做这方面的研究。审查是一回事,而自我审查在我看来则是学术怯懦的表现。相应地,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去反抗那些可能会导致自我审查的胁迫。在我的生涯中,我从没有过怕得罪资料提供者或是同行。这个被讨论的群体是由足球队员、德国人、还是是东正教犹太人组成,其实都一样。我的信条一直是:尽我可能去分析民俗,一切都必将迎刃而解。有一天当我开始担心我所做的分析可能会令人不愉快或者冒犯人,我知道那将是我的临终之时。
我希望这篇“阴暗和毁灭”的调查不会令较年轻的民俗学者感到气馁。是的,民俗课程的衰落令人不安,业余爱好者和大众化作家的侵犯需要被声讨,知识的缺失和资料提供者的胁迫需要被谴责,但是所有的这些并不让人困惑。世界上的民俗仍旧很多,收集和分析的挑战从未有如此激烈。当我的妻子卡罗琳和我在刚过去的夏天游览波罗的海诸国时,我看到了塔图的爱沙尼亚大学民俗学的巨大活力并深受鼓舞。我认为爱沙尼亚正慢慢地与他的邻国芬兰相匹敌,成为当今世界民俗学术的主要行动者。而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一样也是21世纪当代国际民俗学的积极参与者。我感到这些国家对于民俗的积极性和民俗学术的高水平非常令人鼓舞。在我刚出版的四卷本《概念:民俗》中,我毫不犹豫地利用了波罗的海诸国和芬兰较好的民俗知识。在地球的这些区域,民俗学当然没有死亡。
理查德·道尔逊在其杰作《美国民俗》中以这句话作为结束,“民俗已经逐渐消失的观念其本身就是一种民俗”。(1959:278)事实上我并不同意他在那句话的后面部分中使用或滥用“民俗”一词——沉湎于意指民俗是谬论或错误的过分流行的陈词滥调——但是我确实认为情感也许正好像适用于民俗那样适用于民俗学。芭芭拉·克什布赖特—吉姆布雷特(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我们民俗理论家小组的另一个人,似乎对道尔逊的观点有所共鸣,她在别的许多质疑我们学科名称的论文中说:“我们的学科是以正在消失的对象为基础的学科。”(1996:249)丹·本-阿默斯(Dan Ben-Amos),另一个主要的理论家,在他的一篇重要论文《语境中的民俗定义》中甚至更为悲观,当他回顾已经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发生的令人悲伤的预言时,他断言,“如果民俗研究最初的设想是以消失主题为其基础的,就没有办法阻止该学科步其后尘”。(1972:14)但是民俗没有消没,相反,由于凭借电子邮件和网络增强了传播,在现代社会中它仍充满活力地延续着。正如我所指出的,民俗学是一门逐渐消失的学科的观念当然也不是正确的。用马克·吐温这个美国民俗学会发起人的话来说,“民俗学灭亡的传言是非常言过其实的”。最后,让我们振臂高呼:民俗万岁!民俗学万岁!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民间文化论坛》2007年第3期
图片来源: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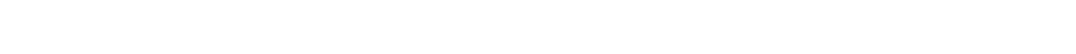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中国民俗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