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作者把相声的变迁放置到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进程中,以动态的视角来探究相声在“十七年”(1949-1966)期间的改进过程。形式与内容紧密相关,文艺工作者借用一定的民间的资源创造了一些固定的叙事类型,以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这篇文章选择了三种类型的相声:“文化反哺”型相声深受进化主义的影响;“浪子回头”型相声是为了通过对落后人物的批评,达到团结、教育人民的目的;而“见贤思齐”型相声则是为了在对比中凸显歌颂对象的高大形象,以此感染民众。作者通过考察研究,分析这几种相声的政治内涵与文化意义,探讨创作者如何通过对材料的组合以满足大众的欣赏趣味,制造出“寓教于乐”的相声。这种“寓教于乐”的新相声徘徊在国家与民众之间,在迎合政治宣传与满足民间趣味之间充满了张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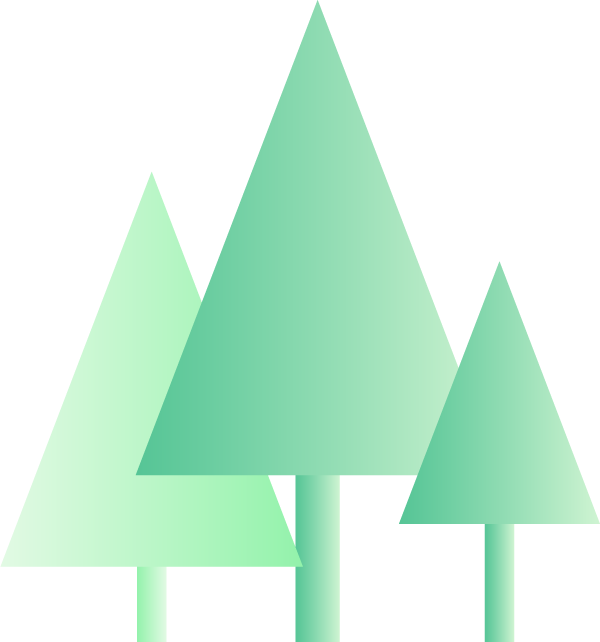
新中国成立后,相声获得了全国民众的喜爱。和老段子相比,新相声在表现新社会的新事物上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文艺工作者积极配合国家的政治任务,使新相声成为了政策推行与社会动员的有力工具。新相声的使命是“寓教于乐”,其创作需要突出思想性与知识性;另一方面,作为面向大众的娱乐,相声的宣传与教育又必须以大众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包袱”既需要给人民带来快乐,还要承载具体的教化意义和知识信息。一言以蔽之,新相声必须以“逗乐”的方式传达“说新唱新”的主旨。形式与内容紧密相关,为了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文艺工作者创造了一些固定的叙事类型,也借用了很多民间的资源。本文根据新相声常见的题材,选择其中的三种类型,分析它们的政治内涵与文化意义,并探讨创作者如何通过对材料的组合以满足大众的欣赏趣味,制造出“寓教于乐”的相声。
一、进化主义下的代际冲突:“文化反哺”型相声
在新相声中,有一类作品集中刻画了年轻人与老一辈的代际冲突,笔者将这一类型的作品称为“文化反哺”型相声,此处的“文化反哺”指年轻人以新思想来改造老一辈旧习惯、旧思想的行为。
这类作品的创作基础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信奉的进化主义,以及由此衍生的“弑父”型的文学作品。鸦片战争之后,现代中国的启蒙者普遍接受了社会进化的思想,这一思想也影响到了文学创作,“五四”时期出现了大量“弑父”型的作品,集中反映了新旧代际间的价值冲突。在作品中,受新思想影响的年轻一代往往将老一辈人作为封建统治的代表进行批判,巴金的《家》《春》《秋》“激流三部曲”、白薇的《打出幽灵塔》、洪灵菲的《流亡》是其中的典型。在延安的共产党人也继承了这一思想,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都描绘了追求进步的年轻人与封建父权之间的斗争,并以年轻人的胜利,向大众宣示了社会进步的必然。新中国成立后,在建设大同社会的追求中,“破旧立新”成为社会的共识。1957年,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对留学苏联的中国学生发表的青年人“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宏论,更是把“少年中国”的观念推向了极致。
新相声也承担起了“破旧立新”的任务,即通过表现年轻人的新气象,达到批判落后的旧观念的目的。如何用相声表现这一主题?“五四”时期“弑父”者决绝的抗争显然不适于喜剧题材,为了能用轻松、幽默的风格来表现新旧价值观之间的斗争,文艺工作者们创造了一个新的相声类型:“文化反哺”型。在“文化反哺”型相声中,年轻人代表新的观念,老年人则代表了旧的想法。新旧两代人因为价值观的不同展开争执,或许是关于是否要采取某种新的生活方式,或许是关于是否要采纳某种技术革新,总之争执的焦点在于是否接受新事物。在争执过程中,年轻人凭借自身的智慧与力量将老年人劝服,也将某种新观念灌输给了老一辈。
新旧价值观的冲突是制造笑料的基础,“文化反哺”型相声继承了“弑父”题材的新旧冲突模式,它的主线仍是新旧价值观之间的斗争。在作品中,年轻人仍是积极、进步的代言人,而老一辈则是保守、陈旧的象征。同时,为了适应喜剧风格,它又柔化了“弑父”主题中激烈的代际冲突,不同于《家》中的冲突产生于年轻一代与冷酷的族长之间,新相声的代际冲突一般发生在父子、婆媳、甥舅等亲密群体之间,矛盾也多发生在家庭场景中,并以生活化的方式表现出来;且不同于“弑父”主题多以悲剧收场(如《家》中的鸣凤投湖、觉慧出走),“文化反哺”型相声总是以年轻人的胜利结束。
在“十七年”的相声创作中,这类作品是极为多见的,如老舍在“大跃进”中创作的《试验田》(1958),作品描述了“大跃进”高潮中,发生在一个家庭里的矛盾冲突。作品中的“我”是一个落后的“老古董”,子女们积极响应总路线的号召,要建设全新的家庭,为了除旧布新,子女们把“我”作为了改造的“试验田”:他们提倡要节约,反对“我”在做客时送礼,提倡要讲卫生,反对“我”在屋里积攒废品等,为家庭带来了新的风气。而侯宝林、王决创作的《砍白菜》(1956)则宣传了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好处,作品讲述了“我舅舅”和同村社员之间因是否加入合作社产生的矛盾,“我舅舅”具有浓厚的小农意识,拒绝走集体化的道路,为此,“我”和其他社员用劳动成果,向他展示了集体化的优越性,使“我舅舅”改变了看法,加入了合作社。
在这些作品中,刘宝瑞、耿英、里果合作的《假灶王》(1963)是一篇较为成功的创作。作品的主题是反对封建迷信,提倡现代科学。故事发生在一个小农村,“我”是一个相信现代科学的青年,而“我妈”则是封建迷信的受害者,“我”和“我妈”为了家里是否该供灶王爷发生了争执。在作品中,母子之间集中的争执共三个回合,第一回合儿子生病,“我”请医生治好了儿子的病,而“我妈”则认为这是她请灶王爷“收魂”的结果,结果谁也没说服谁;第二回合,“我妈”坚持过年要祭灶,一定要“我”去买灶王像,“我”只好找了张印有猪八戒背媳妇儿的农历月份图应付老太太,但她浑然不觉,一直虔诚祭拜;第三回合,村里闹虫灾,“我妈”求灶王爷显灵除灾却没效果,最后还是由政府派飞机撒药才消灭了灾害。最后,在我的劝说下,“我妈”认识到了迷信的害处,要撕了灶王像,才发现自己一直拜的是猪八戒。作品在轻松喜悦的气氛中结束。整个作品喜庆诙谐,非常适合节庆期间播出。1963年底作品面世后,由广播说唱团的刘宝瑞、李文华排演录制,交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1964年春节播出。
以“我”和“我妈”就新年是否还要供灶王爷的一段争执为例:
甲:那年到腊月二十九了,我说:“妈,咱们都是人民公社的社员了,今年可别供灶王爷了,供那玩意儿不但不灵,还让人笑话。”
乙:对。
甲:我妈说:“笑话?谁笑话呀?不供灶王爷那才有人笑话哪。叫人家说:过几年好日子了,连灶王爷都忘了!”
乙:嗐,这关灶王爷什么事呀!
甲:是呀,我爱人也说:“妈,过好日子,多亏共产党领导的好,灶王爷什么也不是!”
乙:这是真话。
甲:我妈说:“呦!你们这年轻人啊,咋这么没大没小的,连灶王爷都敢骂呀,灶王爷是一家之主,比我还大一辈呢!”
乙:嗐!
在这段争执中,“我妈”代表了落后的迷信思想,而“我”和“我爱人”则代表了进步、科学的力量。在反驳我们时,“我妈”使用了两种权威话语:家庭权威和传统信仰权威,“年轻人”“没大没小”这些训斥,是为了凸显她在家庭中的权威,而“灶王爷是一家之主”则是为了凸显传统信仰的权威性。在新社会里,这两种话语是“落后”的代名词,因而,“我妈”的话也就是落后思想的体现。在劝“我妈”时,“我们”采用了大量现代话语,“我”点明了“社员”的现代身份,劝勉“我妈”要选择符合现代身份的信仰,并用“让人笑话”,暗示了反迷信的观念不仅是年轻人的想法,而且已经成为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我爱人”则通过对“过好日子”的强调,暗示现代的富足生活是应该远离迷信的,并将生活的改善归功于党的领导,劝说“我妈”应该和党的信仰保持一致。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代表了社会主义新人的精神面貌、现代社会的理性价值以及社会的普遍舆论,显然,这些话语在新社会中代表了“进步”。
“我”和“我妈”三个回合的交手,都体现了“落后”与“进步”的争执,“我”代表的进步力量积极出击,步步为营,而“我妈”代表的落后思想则左支右绌,强词夺理。几次冲突既制造了“包袱”,也宣示了年轻的进步思想战胜老旧的落后观念的必然。以村里闹虫灾以后的家庭冲突为例:
甲:哪呀,她跪在地上给灶王爷磕头
乙:那没用!
甲:还跟我说:“虫子是虫王爷撒的,越抓越多,虫王也不往回收多咋也不能光。”
乙:真是迷信!
甲:“那虫子就算归虫王爷管,你给灶王爷磕什么头啊?”
乙:是呀!
甲:我妈说:“你咋这么糊涂啊,灶王爷跟虫王爷都是同事,能没点交情吗?”
乙:这都哪的事呀?
甲:“灶王爷是咱们一家之主,年年吃咱们灶糖,喝咱们的面汤,到这时候他还不给咱说句好话?他在虫王爷面前给咱们讲个情,虫王爷一高兴,把虫子就收回去了!”
乙:好嘛,这算迷了心窍了!
甲:我怎么劝她,她也不听,跪在地上一边磕头一边嘟囔:“灶王爷呀,你在虫王爷面前多说几句好话,要能保佑我们这一方,早点把虫子全收回去,到秋后大丰收,我买个八斤的大猪头给你上供……”
整部作品的矛盾冲突是在现代人的理性观念与落后的民间信仰之间展开的,由于冲突双方的关系是母与子,亲昵关系使矛盾冲突以家庭轻喜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到最后,矛盾以年轻人顺利完成“文化反哺”,老年人诚心接受新观念的方式解决。在代表了现代化的灭虫飞机的轰鸣声中,“我妈”认识到了封建迷信的虚妄,表示以后要放弃迷信,相信科学。
“文化反哺”型相声是以对某种规范的调笑来制造“包袱”的,只是这里的规范已经替换成了昔日落后的规矩、老一辈人固守的陈旧观念,而作品正是通过年轻一辈人对这种规范的逾越来制造“包袱”的,在最后,老一辈人也打破了既定的旧规范,接受了年轻人的反哺。

二、“寓教于讽”:“浪子回头”型相声
在“十七年”里,文艺工作者创作了大量的讽刺相声,对落后小人物的善意讽刺是讽刺相声中的大宗,这里将这类作品称为“浪子回头”型相声。
就新中国成立前十年的相声创作而言,讽刺占了相当多的数量,文艺工作者围绕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展开了对落后行为与人物的批评。在当时的语境中特别强调讽刺的传统,蕴含了知识分子希望借助文学干预社会的理想。他们对讽刺的重视,实则是对现实主义文学针砭时弊传统的继承与强调,希望用讽刺来鞭挞丑恶、警醒世人,推动社会进步。在为讽刺相声《买猴》辩护时,老舍便指出:当时讽刺的缺点“不在他们讽刺得太过火,而在讽刺得不够深刻,不够大胆”。
但是,作为一种批评性的修辞,“讽刺总是敏锐地意识到事物怎么样与事物应该怎么样之间的差距”。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里,讽刺的对象与讽刺者的立场显得极为重要。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主席将社会矛盾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并指出:“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应该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应以“团结—批评—团结”的形式处理。因此,相声对落后人物的讽刺,就需要遵循内部批评的原则,仍把被讽刺的对象当做人民来对待,采取善意的、内部讽刺的方法,并须注重讽刺的“政策性”和“分寸感”。通过讽刺来改掉落后人物身上的种种毛病,完成对他们思想的启蒙、身份的净化。毕竟,内部讽刺仍是为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使犯错误的同志回到正道上是内部讽刺的主旨。
新相声也需要遵循这一原则,正如学者罗常培所说:在创作讽刺作品时:“咱们必须认清楚敌人或朋友才不至于出偏差。对于咱们的朋友犯点儿小错误,应当含而不露的讽劝,希望说服他们觉悟悔改。”。本着这一原则,在批评落后的小人物时,文艺工作者们创作了“浪子回头”型相声。
在这些作品中,“捧哏”与“逗哏”一般有固定的角色分工。“逗哏”多站在反面人物一方,“捧哏”则站在观众的立场上扮演劝说者。主人公往往是一个思想落后、行为可笑的小人物,“捧哏”则竭力教育他,劝他改变错误的观点,捧逗之间的争论贯穿整个叙事。在作品的开头,反面人物就表现出对现存某一社会规范的不满或认识不足,他自以为是,坚持自己错误的观点,而劝说者则苦心规劝。接下来,反面人物坚持己见,“拿着不是当是说”,讲述其各种不满/认识不足造成的表现,借助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悖反制造笑料,“捧哏”则逐一反驳纠正。然而,反面人物发现他的一套错误观点在现实社会中到处碰壁,获得惨痛教训(如个人形象受损、或触犯社会法规,或被代表社会主流价值的众人孤立),规劝者借此进行教育,解释反面人物的错误所在,进而宣讲正面的社会价值。最后,反面人物不得不在教训面前承认错误,认同了社会的主流价值。
在“十七年”的内部讽刺作品中,“浪子回头”型的相声占了绝大多数。如刘宝瑞的《吃饭我掏钱》(1955)以宣传反浪费为主旨,作品刻画了一个浪费成性的小人物——“我”的可笑行径,在食堂吃饭时老是浪费,如吃不完的馒头就扔了,吃包子只吃馅儿不吃皮儿等。“逗哏”则劝说我要爱惜劳动果实,并将农民生产粮食的过程细致告诉“我”,在他的劝说下,“我”幡然悔悟,表示以后一定要爱惜粮食。而常宝华的《水兵破迷信》(1958)则讽刺了迷信书本、迷信外国的知识分子,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在美国学过造船的科学家,上级派他去给造船的水兵帮忙,他扛着一箱关于造船知识的书到了现场,以专业知识颐指气使,结果却一无所获,反倒是水兵们以实践精神造出了船只,让他自惭形秽。
最为典型地体现了“浪子回头”主题的,是交警郎德沣等人创作、侯宝林改编的《夜行记》(1955),作品刻画了“我”——一个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的经历与遭遇,“我”受不了社会规范的约束,走路不走人行横道,坐公交车不爱排队,在车上还抽烟、吃栗子,遭到了大家的批评。于是,“我”赌气不再坐车,花低价买了一辆“除了铃不响其它哪儿都响”的自行车,“我”骑车时乱闯红灯,与机动车辆赛跑,碰撞了老年人不但不道歉反而自以为得意。最后,在飞车乱窜中,“我”掉进了地沟里。
作品从“垫话”开始就渲染“我”不守规矩的形象:
甲:爱听是爱听啊,可剧场里这限制受不了哇。
乙:剧场里边儿有什么限制呀?
甲:头样儿,不让抽烟我就受不了。
乙:噢,您说这剧场里边儿不让抽烟哪?…… 这对呀。…… 你想啊,台下观众好几百位,要全都抽烟,大家一齐熏,这台上演员受得了吗?
甲:那是这么说呀,台下人多,台上人少,应该少数服从多数嘛。
乙:这不行,这公共秩序,大家都得遵守。
甲:这还可以,还不让乐!您想,听相声不让乐,受得了吗?
乙:不让乐?……哪有这个事呀?
甲:你那儿刚一乐,后边那儿:“嘘!”这……这什么意思啊?
乙:噢,当然,他打“嘘”不完全对。
甲:是啊。
乙:他是怕后边儿的词儿呀,听不见。
甲:所以这受限制啊。
乙:这不叫受限制
在上述引文中,“逗”与“捧”之间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念,“捧哏”代表的是遵守秩序的正确观念,而“逗哏”则代表了对秩序的逾越与破坏。“我”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认为剧场中不让抽烟、不让乐的公共秩序对自己造成了约束,在这里,“我”冒犯了社会的公共秩序,以无理取闹的方式制造“包袱”。无论是对“少数服从多数”的歪解,还是对“受限制”的抱怨,都构成了落后人物对社会公共秩序的冒犯。而“捧哏”则负担起了教育民众的作用,他站在观众和社会秩序的立场上,对“我”每一处错误的想法进行纠正与规劝,并正面教育“我”“公共秩序,大家都得遵守”。以“我”在公交上的表现为例:
甲:我一瞧,我头一个上,刚一迈腿儿,卖票儿的把我拦住了。
乙:怎么啦?
甲:“同志,把烟卷儿掐喽!”
乙:车里头不能抽烟嘛。
甲:嘿,得亏我买栗子啦。
乙:哎,不行,车里头不能吃带皮的。
甲:这也不行?
乙:嗯,不行!
甲:你让他站住,我下去!
乙:那没到站哪!
甲:你说这不是生气吗?这不是受限制吗?
乙:这不叫受限制。
甲:我纳着气儿,好容易到车站啦……
乙:嗯。
甲:下车的时候儿,他还跟我要票呢。
乙:多新鲜啦!
甲:“票给你!撕半张儿报销!”
乙:你还报销呢?
甲:哪儿报销去,我就为让他费点儿事。
乙:这什么行为!
在这里,规劝者和售票员一起站在社会主流观念的立场上,对“我”种种的不靠谱行为提出批评和劝告,几乎是一句一劝。这种设置印证了侯宝林所说的:作品如要致力于提高作品的思想性与教育意义,这就“要求‘捧哏’演员站在先进的立场,对叙述人所叙述的故事加以评论”。
为了达到团结落后人物的目的,在作品中,主人公的落后毛病不能是政治、阶级上大是大非的问题,只能是一些个人认识和品行上的小瑕疵,如浪费、食洋不化、自由散漫等。在《夜行记》中,“我”所犯的错误是不遵守公共秩序,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中极轻微的表现,在此基础上,小人物对主流秩序的逾越,既不会像何迟的名作《买猴儿》那样踩到讽刺的红线,又能够造成充足的“包袱”。整段节目的矛盾冲突就是在“逗哏”对主流秩序的逾越和“捧哏”对“我”的劝说中展开,“逗哏”的逾越制造了笑料,而“捧哏”的规劝则传达了正确的价值观,起到了教育民众的作用,从而达到了“寓教于讽”的效果。作品末尾虽然没有直接描绘“我”幡然悔改的场景,但从“掉沟里了”的情节设置上,我们不难推测:自食其果的“我”将会认同社会主流秩序。

侯宝林和郭启儒基层演出
三、“寓教于比”:“见贤思齐”型相声
“十七年”相声创作的一大特点,是出现了一批宣传新人新事的歌颂型新相声。为了制造“包袱”,歌颂相声经常以次要人物对主要人物的陪衬,来凸显主人公的光辉形象与高尚品德,我们将这类作品称为“见贤思齐”型相声。
歌颂相声的崛起,是由新中国的社会成就与阶级构成的变化决定的,本着“说新唱新”的原则,文艺需要去刻画已成为社会主流的“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新的道德风尚”。并通过对先进人物的塑造来感染、教育民众。然而,歌颂是一种正面题材,如何在歌颂先进人物时安排笑料呢?无疑,作品中的主人公是被赞扬的对象,是不能随意打趣、调侃的。正如李文山所说:
一般这种歌颂性的段子,主题严肃,找“包袱”只能从对象以外找,只能是“外插花”的“包袱”。你真正顺着主题延伸下来的“包袱”少。而且你题外“包袱”啊,写完了还得赶紧拽回来。
为了平衡歌颂主题与笑料安排之间的矛盾,文艺工作者们展开了讨论。有论者指出:如果相声能够“用谐趣的手法,来表现先进人物在前进过程中的不调和的东西,就能产生更大的教育力量”。
受这种观念的启发,创作者们采用了对比的手法,在作品中设置了一组主、次人物,通过两人的对比进行叙事,正面人物严格要求自己,处处进步,次要人物则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落后,在对比中,主要人物的美好品德得以弘扬,最后,次要人物也认识到了自己的差距,表示要“见贤思齐”,向主要人物学习。
不少歌颂型相声采取了这一叙事模式,如夏雨田的《女队长》(1964)描绘了“我”和“我爱人”——村里公社的女队长之间的矛盾,“我爱人”是一个无私、勤快的女队长,处处为集体着想,而“我”则有自私的毛病,总是想着过两口人的小日子,“我爱人”把我想买收音机的钱拿去为公社购买农业器械,还把自己的新草帽给了别的社员用,我相当不高兴,和她发生了各种摩擦。最后,在她无私行为的影响下,“我”逐渐改变了自私、个人主义的想法。马季的《画像》(1963)则歌颂了山东文登劳模张富贵爱劳动的美好品质,作品描写了“我”(画家)要为劳模张富贵画像,千方百计要让张富贵闲下来给我做模特,而他则闲不住,最后,在他的影响下,我也投入到了劳动中。
最为典型的作品是在解放军第三届文艺会演上一炮打响的《好连长》(1964),这是一段军事题材的相声。作品由庞秀山创作,朱光斗、于连仲改编,歌颂了一个既爱护士兵、又严格要求下属的连长,作者同时刻画了“我”——一个入伍不久的新兵,性格略显冒失,并有一定的名利思想,不安于步兵的岗位,想当技术兵,连长以“爱字出发、严字要求、变字看人、帮字入手、好字落实”的带兵方针关怀“我”,逐渐扭转了“我”浮躁、不踏实的性格。纵览全篇,几乎所有的“包袱”都出在“我”身上。以连长对“我”严格要求的情节为例:
甲:……有回演习班进攻,因为我手榴弹没扔好,连长在队前点我的名。
乙:准是你扔的不远。
甲:不是。……我没拉弦就扔出去啦!
乙:嗐!那不成了甩棒槌啦!
甲:我就是拉了弦,那手榴弹也响不了。
乙:手榴弹受潮?
甲:里边没药。
乙:没药哇?
甲:教练弹!
乙:那是没药!
甲:手榴弹是假的,演习也是假的,你说何必那么认真哪!连长批评我缺乏实战观念,没有树立训练为了打仗的思想。当时非叫我重来一遍。……重来就重来吧。这回我使足了劲,来了个五十米跃进,等接近敌人前沿的时候,我掏出手榴弹,做了个拉弦的动作就扔出去啦!
乙:连长满意啦。
甲:不行,还得重来。
乙:你不是拉弦啦吗?
甲:弦是拉啦,我回臂的时候使劲过猛,把手榴弹甩到后头去啦!
在引文中,“逗哏”一人分饰主、次两角,以主要人物连长对次要人物“我”的帮助为主线组织叙事。连长是要歌颂的对象,他的形象是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没有丝毫可笑之处,在引文中,他甚至是以第三人称叙事出现的,没有直接发声。相比之下,“我”的形象则更加生动:“我”略带小毛病:办事不认真,但又赤诚可爱,在连长的要求下,“我”做出了“没拉弦”与“甩后头”的动作,既塑造了“我”冒失、不认真的形象,也反衬出了连长的严格要求。在这里,“包袱”的组织是通过“我”对连长模范标准的逾越产生的。通过“我”和他的对比,连长的种种美德得到了展示,而我与他的道德差距,不但是作品“包袱”的主要来源,又从侧面反衬了连长的严格要求和优良品格,从而达到了“寓教于比”的效果。
“见贤思齐”型相声带有浓厚的道德教化色彩,在轻喜的风格中,把先进人物的思想传达给了受众。在评论《好连长》等曲艺作品时,当时的文艺评论家们就指出:“这些曲艺佳作的思想性好,形式新颖,风格更高,集中反映了部队曲艺工作者近年来‘说新唱新’的成就,达到了一段曲艺节目就是一堂政治课”的教育效果。
与其他“见贤思齐”型相声一样,《好连长》以我的转变结尾:连长接连和“我”谈了九次话,使我彻底改变了原先好高骛远、办事不认真等坏毛病,最后,“我”表示要安心于步兵的本职工作,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努力完成革命任务:
甲:……这是连长那颗热爱战士的心,换得了我对革命诚实的心。另外,他也特别重视调查研究。在连长和全连同志的帮助下,现在我已经加入共青团啦!
乙:好哇!
甲:“好字落实”嘛!
乙:这就叫“好字落实”?
甲:对啦,好字是连长检验他一切工作的标准,是爱、严、变、帮四个字的最终目的。现在我已经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连长要我继续努力,好上加好!
乙:我问你,现在你真的愿意当步兵啦?
甲:只要是干革命,叫我当什么兵我都干。
乙:问题解决得彻底。
甲:不过就有一种兵致死我也不当。
乙:什么兵?
甲:逃兵。
乙:那……是不能当!
我们可以把上述这三种题材认为是文艺工作者兼顾“说新唱新”的政治要求与相声文体特征的产物,是文艺工作者在政治规约下,发挥创造性智慧,使作品既符合教化主旨,也产生娱乐效应的结果。通过对正面人物的弘扬,新相声完成了“说新唱新”的任务,而借助对落后人物的揶揄和嘲讽,作品又产生了娱乐效果。可见,“寓教于乐”既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技术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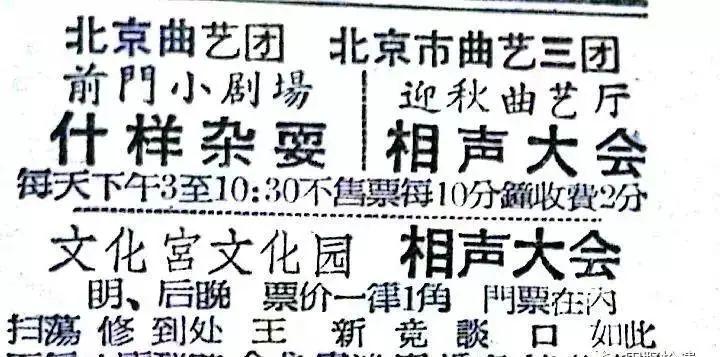
北京曲艺团刊登于1958年6月2日《北京晚报》演出广告
四、政治宣传、民间趣味与文体之间的张力
为了表现新时代的新精神,文艺工作者赋予了新相声全新的题材,这些作品在政治上表现出了全新的内容:“文化反哺”型相声深受进化主义的影响;“浪子回头”型相声是为了通过对落后人物的批评,达到团结、教育人民的目的;而“见贤思齐”型相声则是为了在对比中凸显歌颂对象的高大形象,以此感染民众。那些积极进取的青年人、幡然悔悟的小人物,乃至“高大全”的英雄人物,都是新社会的产物,在旧相声中是看不到的。
为了达到“寓教于乐”的社会效应,新相声吸取了大量民间的喜剧性因素,并为其灌注进了新的内容。纵观“十七年”那些比较优秀的新相声,在歌颂或讽刺的时代主题下往往都具有来自民间的叙事原型,常宝华的相声《水兵破迷信》讽刺了只会死读书的知识分子,其原型来自《抬杠铺》《孔子求教杜三娘》等充满反智色彩的民间故事;在夏雨田的《女队长》中我们不难发现《杨门女将》的影子;而讽刺小知识分子婚姻观的《离婚前奏曲》则与揭露了读书人喜新厌旧的《铡美案》如出一辙。
在这些作品中,无论是落后于时代的老一辈,还是言行不靠谱的小人物,都让我们联想起那些民间戏曲中的丑角,让人想起赵树理笔下的“三仙姑”“二诸葛”,这些人物有小毛病,但又不失可爱。他们之所以迷人,说到底是因为和“巧女”故事一样,充满了民间的趣味。
得益于这些民间因素的润滑,原本以教化民众为己任的相声不再显得枯燥乏味,那些符号化的、作为政治图解的正面人物才不至于让人感到厌倦。民间趣味既满足了民众在通俗文艺欣赏中形成的趣味定势,也响应了国家对人民文艺的推崇。在论述“十七年”期间的文艺作品时,陈思和也认为:
(“十七年”的文艺作品)往往由两个文本结构组成,显形文本结构通常由国家意志下的共名所决定,而隐形文本结构则受到民间文化形态的制约,决定着作品的艺术立场与趣味。以电影《李双双》的故事为例,从其显形文本结构来说,是一个歌颂大跃进运动的政治宣传品,但其隐形文本结构则体现了传统喜剧“二人转”的男女调情模式,有意思的是,其后者实际上冲淡了前者的政治说教,使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时代而获得民间艺术的审美价值。
在新相声的个案中,官方话语与民间资源之间并不是一种单向的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与其说是政治宣传在利用民间资源,不如说启蒙话语要想获得普通民众的青睐,就需要凭借、倚重民间的趣味与形式。可见,民间文化并不是与现代文明、主流政治完全对立的存在,相反,它们展开了互相博弈与协作。在这一过程中,相声的创作不仅需要顾及政治宣传话语,还需要兼顾传统的欣赏方式与民间的伦理价值。所以,新相声尽管与政治有着紧密的关系,但仍是一个充满多种话语的文化载体:国家意志、启蒙话语、民间资源互相交织,互相借重,从而使来自民间的艺术获得了在新时代的合法性,维系了民族的主体意识。
文体与题材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文体特性决定了新相声的表现内容——优秀的新相声仍需要遵循相声一般的文体特征:即通过对某种秩序的逾越来制造“包袱”(参见本书第一章)。在我们分析的三个相声类型中,对秩序的逾越与颠覆仍然存在,只是秩序已经被替换成了某种落后人物过时的观念与做法,这种逾越多数是通过正面人物与落后人物之间呈现出的进取/先进/与落后/陈旧之间的冲突完成的。通过“捧哏”的正面引导,“逗哏”的反面推动,编演者建构了他们心目中的理想观众——一群具备现代社会的种种优秀素养:热爱国家、不浪费、办事认真、遵守秩序——的模范民众。
而吊诡之处在于,这种文体特征与民间趣味一旦结合起来,往往会左右大众对相声的观赏侧重,甚至阻碍相声教化主题的顺利达成。深究这些作品中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创作可以发现,无论是歌颂相声,还是讽刺相声,新相声“包袱”的组织多是由“小人物”——讽刺相声中的落后者,或歌颂相声中的次要人物——完成的,所有的笑料都集中在反面人物或落后人物的身上。因此,作品中那些有小毛小病的小人物与反面人物反而显得生动精彩,而那些正面人物却相对无趣。究其原因,是因为小人物对主流秩序的逾越,在无形中体现了民众人性深处追求自由的需求。显然,在演出这些相声时,编演者和观众之间总是会产生交流与理解上的错位,观众是站在小人物的一方来解读作品的。
在评论新相声的创作时,美国学者林培瑞(Perry Link)敏锐地发现:在观赏《夜行记》的过程中,观众更多感受到的是一种“闹剧化”的体验,他们不是在笑小人物,而是“在和越轨的小人物一起笑”。人们之所以记住《夜行记》,正是得益于小人物那一连串骑破车、闯红灯、把老头撞进药铺、和汽车比快慢的荒诞举动,从这个角度说,草根相声的越轨性与狂欢性其实是通过新相声中小人物的落后行为得到了改头换面的保存。1960年,北京曲艺团创作了歌颂毛泽东战略思想的新相声《牵牛记》,描写了1947年刘邓大军智斗国民党第五兵团的故事,歌颂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为了表现我军的英勇威武,作品对国民党军队涣散的军纪、萎靡的士气,以及败军后的惨状做了浓墨重彩的描绘。作品发表后,有观众来信表示:“我觉得这段相声对敌人的描写,给人印象很深。相对的,对于我军则刻画得不够生动,缺乏鲜明的形象。”这一反馈足以证明我们的论断。尤其在政治空气相对紧张的时期,在《画像》《好连长》这样的段子中,性格有缺点的人物一下子抓住了观众们的心,反而使高大全的正面人物黯然失色。这些小人物之所以让人难忘,正是因为它们往往保留了大量直达人性深处的喜剧化元素。
在“说新唱新”的号召下,新相声的题材也呈现出了鲜明的类型化倾向。受限于艺术的特性,相声不能表现过于严肃的社会问题,受限于社会言论的尺度,相声也不能触及过于阴暗的社会现象。在这些作品里,我们一般看不到十恶不赦的反面人物,也看不到激烈决绝的情感冲突,而是以刻划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与矛盾为主,有着浓厚的生活情趣,而其中的矛盾也往往以误会、巧合、小人物的白日梦、情侣间的赌气等无伤大雅的手法产生,且必然以皆大欢喜的和解结尾。对新人新事的歌颂,以及对落后人物的善意规劝因此便成为了新相声中的大宗。新相声之所以常常被人赞誉为“清新”,正是因为这些作品常常以社会主义轻喜剧的形式来组织笑料、制造谐趣。
然而,“十七年”社会政治语境是多变的,像何迟的《买猴儿》那种从“香花”变成“毒草”的作品不在少数。创作者需要在多变的政治环境中保护自己,“随大流”与“跟风”就成为了相声创作的必然,新相声的主题也就难免沦于模式化、同一化。本文分析的三种模式既能符合政治要求,也顾及了娱乐效果,因此引起众人争相效仿,乃至被滥用。在1957年的“鸣放”中,北京曲艺团的相声演员张善曾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新相声对“浪子回头”型主题的滥用:
据老艺人讲相声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说是八种,有的说十种,其说不一。可是现在的创作却只是一种,那就是故事性的相声,开始就都是甲对某些事件生气,乙给解释,再不就是甲说些没头没脑、不着边际的话,乙给纠正,集中落后现象于一身,然后转变,鞠躬下台了事。但后来又不写转变了,如一个相声内容是防火,某人屡次由于不重视防火、惹起火警,相声中是处理某人认识了错误,转变了事,但公安局有人却对这个相声提出了意见,说这样处理是有错误的,按这情节非送法院不可!我们也只好改成送法院了。
显然,这种脱离生活、形态雷同的相声是政治过分干预艺术产生的后果。“寓教于乐”的新相声徘徊在国家与民众之间,在迎合政治宣传与满足民间趣味之间充满了张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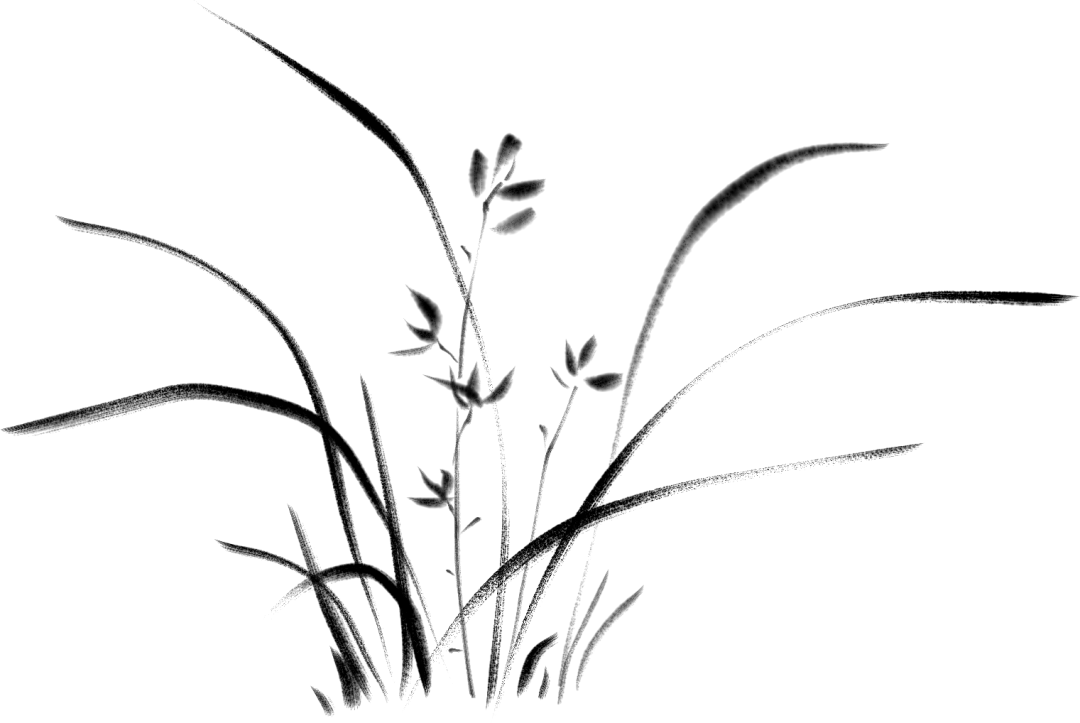
本文节选自《文体的社会建构:以“十七年”(1949-1966)的相声为考察对象》一书,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田野拾遗” 2018-10-10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