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自20世纪初期开始,神话等民间文学资源的现代价值就引起了关注,其经由文学“发酵”,逐渐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儿童文学在“幻想性”与“民间性”的交叠中,成为实现神话等民间文学资源现代转化的关键路径之一。本文通过梳理葛翠琳1949—1966年的儿童文学作品,探讨神话如何在与主流话语的“耦合”中象征性地转换为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及本土现代性的建构力量。另外,这一时期葛翠琳的儿童文学创作不仅体现了对人民文艺精神内核的承继和审美理想的不懈追求,亦彰显出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关键词:神话;民间文学资源;葛翠琳;文化转型;儿童文学

一
20世纪初期,随着对现代启蒙及人之个性的重视,引起了文学观念及文学研究格局的变革。从1918年北京大学歌谣征集活动开始,对“有关一地方、一社会或一时代之人情风俗政教沿革”的自觉认识激发了对神话资源进行再发掘与再阐释。神话资源在儿童教育方面的价值问题引发了许多讨论。如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中重提他于1913年至1914年所写的《童话略论》《童话研究》《古童话释义》和《儿歌之研究》等文章中表达的“儿童本位思想”。他认为“就‘文学’这方面来说,儿童所需要的是文学,并不是商人杜撰的各种文章”,其中的“文学”指的是“儿童的文学”——如童话、小说、故事、儿歌等。这一时期,梁启超、包天笑、林纾等人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被重译,而围绕童话中“神话与传说材料”的定义、“幻想性”及其与儿童心理契合与否的讨论陆续展开。其中,赵景深认为童话中的神仙妖怪的故事,由于不含有“宗教的教训”,有别于“说教的神话”,因此他主张把童话的内容,合于教育原则的传说物话等划为“教育童话”:
凡童话都是文学:民间的童话是原始的文学,文学的童话自然是文学的正宗;而教育的童话又是从二者中取出的……
所谓“合于教育原则”,即对原先“不符合儿童身心”的部分做了“汰洗”,但是依旧保留“神仙故事和物话的神秘性”。赵景深强调:童话这件东西,实在是一件快乐儿童的人生叙述,含有神秘的而不恐怖的分子的文学,质料依旧是神话和传说的材料,不过严肃和敬畏的分子是没有了。
1931年,湖南省主席何键下令禁止“鸟言兽语”的童话书刊发行,并呈请南京教育部通令全国查禁。1931年,尚仲衣发表《关于“鸟言兽语”的讨论:选择儿童读物的标准》和《儿童读物与鸟言兽语的讨论:再论儿童读物》,掀起了关于“鸟言兽语”问题的讨论。时任中华儿童教育社社长的陈鹤琴在《“鸟言兽语的读物”应当打破吗?》中认为“年幼的小孩子是很喜欢听鸟言兽语的故事”,“他看的时候,只觉得他们好玩而并不是真的相信的。”他基本沿袭了周作人对待神话的态度,肯定了“鸟言兽语”的存在价值。1936年,叶圣陶发表童话《“鸟言兽语”》,用“鸟言兽语”的童话形式来探讨“鸟言兽语”这一问题,具有一定的反讽意味。
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儿童”必然要被纳入到民族国家共同体中。“儿童本位教育”被“民族国家本位教育”所取代,童话中“神话和传说的材料”对儿童的教育意义逐渐凸显——在儿童与社会间搭建桥梁,以满足国家社会的现实需要,同时也需要照顾到儿童心理与生理的发展。1949年以后,由于新的文艺体制建构的需要,同时也受到苏联教育理念的影响,围绕神话资源现代转换的话语实践成为儿童文学创作的坚实基础。另外,新中国初期的文艺研究抛弃了西方文明论,将神话等民间文学资源作为“新的文学话语的接驳场域与动力源”;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作家主体成长的过程,“群众”这一角色作为作家“自我”认知和转变的“他者”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
二
自“五四”时期,学人就开始关注对神话等民间文学资源“现代性”的探讨;他们通过对那些来自历史的,逐渐被遗忘的、零散的神话等民间文学的变形、裁剪、转换,使其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拥有新的意义,焕发新的生机。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下简称“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预演和实践了“新的人民的文艺”。1952年年底,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应约在苏联的《旗帜》上发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一文,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历史性”及“批判性”。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主义文艺自身的发展规律提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的神话资源由简单的“汲取”和“引用”向“创造性转化”发展。

葛翠琳的儿童文学创作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下展开。葛翠琳,我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1930年2月她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前葛庄村,自1949年开始进行儿童文学创作,先后出版《野葡萄》《巧媳妇》《采药姑娘》《金花路》等童话集。葛翠琳于1948年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青年先锋队(CY),在校期间,她主修社会服务科,当时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课的雷洁琼与葛翠琳之间师生关系密切。葛翠琳在访谈中回忆起那段时光总说:
那时候师生关系很密切。学生可以随时去教授家里请教问题。……那时候师生关系很自然,很亲切的。没有那种市侩的东西。
在葛翠琳未入学之前,雷洁琼就对“儿童福利”这一社会服务问题极为关注。1947年,雷洁琼受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委托,开设“儿童福利”课程,并组织社会系、家政系、教育系、心理系学生在海淀成立儿童福利站,为海淀镇附近儿童提供救济、福利等服务工作。燕京大学迁往成都后,其社会学系把重点放在少数民族、边疆、宗教、农村和社会服务等研究上,推进社会学的中国化。
葛翠琳也多次提及自己在“渤海边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度过的童年:
从学习讲话开始,就听着祖母摇着纺车讲述动人的传说——
狐仙、狼外婆的故事,喜鹊、布谷鸟的传说;
人参、何首乌的故事,花仙、槐树精的传说;
花木兰从军、昭君出塞,杨门女将、十二寡妇征西;
牛郎织女七月七鹊桥相会,梁祝化蝶,孟姜女哭倒长城……
上述的学习与成长经历,为她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展多民族视野下的儿童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9年毕业后,葛翠琳被分配到北京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参与筹办“第一次文代会”。1949年10月1日,她参加新中国成立庆典时,遇到北京市委宣传部第一任部长李乐光,他对葛翠琳表示:希望她能用手中之笔“为孩子们写书”。1950年,她在北京市文联任老舍业务秘书兼北京市文联儿童文学组组长。其后,她在与老舍、冰心等人交往中深受感染,决心“寻找新的起点”,创作“内心深处流淌真情的作品”。

这一时期国家对儿童教育问题极为重视,1955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社论,强调“优良的少年儿童读物”在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方面的重要作用。同年《中国作协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下达后,叶圣陶发表《响应号召》,冰心发表《“一人一篇”》。郭沫若、魏金枝、靳以、周而复、周波、马烽、康濯、臧克家、田间、李季、阮竞章、袁水拍、贺敬之、袁静、刘知侠等也都制定规划为少年儿童创作,对“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这一需要儿童文学密切配合基础阶段教育的要求表示理解与支持。
以老舍创作的儿童剧《青蛙骑手》为例,从附在文后的《〈青蛙骑手〉的一些说明》可知,此剧系根据萧崇素整理的《青蛙骑手》改编而成,作品传达的基本文化信息和核心主题与以“青蛙”“蟾蜍”“癞蛤蟆”为母题的英雄神话极为相似;如流传在白马藏人中的《月月》《白马少爷》《阿尼泽搜毕记》等;流传于西南一带的黎、壮、苗、羌、彝等少数民族中的《蛙郎的故事》《青蛙女婿》《蟾蜍儿》《蟾蜍皇帝》《蛤蟆驸马》等,流传于四川凉山的《司惹巴洪》《天神的哑水》《勒俄特依》等。在老舍的创作中,保留了神话的重要母题及角色设置,同时树立起惩恶扬善、反抗压迫的主题,加深了作品的思想性与现实性。“头人”象征封建统治阶级,他对于“青蛙”的忌惮与迫害说明了在统治者残酷压迫下绝不允许“异端”的出现,“头人”与“青蛙”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头人畏惧于青蛙“遇见耕田的老夫妇,或是山中放牛的小娃娃”时,“世人不应分贫富,百姓不受官欺压”“修一条大道通北京,来来往往,汉藏成一家”的言论;对青蛙能使得“天旋地转”的哭笑无可奈何;在“撕碎蛙皮冻死青蛙”的计谋落空之后,头人只能默默退入院中,留下狂欢的“群众”。老舍作品中对神话的“改编”侧重的是“对现实的重新认识”,从而“唤起面对现实的革命主义态度,唤起一种能够改变世界的态度”。为了用新的意识形态来“整理和改造”神话等民间文学资源,“规范人们对历史现实的想象方式,再造民众的社会生活秩序和伦理道德观念”,老舍不仅将“三姐”的身份改为“头人的义女”,而且将蛙皮改为被头人劫走,增强其阶级冲突。但当时的学人已经注意到,倘若否定和忽视民间文学“幻想性”的基本特征,将会造成文学传统与话语实践的深层断裂,如李岳南、刘守华围绕《牛郎织女》改编的讨论以及当时杨绍萱与艾青对《牛郎织女》戏曲改编的争论等。
三
葛翠琳在创作中注重对民间文艺话语的运用,并尽力发挥这一优势。在《野葡萄》《少女与蛇郎》《片片红叶是凭证》《悲苦的钟声》《沉默的证人》《蝎子尾巴》《金饽饽》《秀才和鞋匠》等作品中,她运用“宇宙起源”“人类起源”“文化起源”“动植物起源”等神话母题,象征性地再现了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演变轨迹。文本中由神话意象、神话思维等连缀而成的超越现实的叙述,消弭了阶级观念、革命叙事与民间信仰在话语实践中“先在”的距离感,在葆有神话“神圣性”的基础上,“潜移默化地影响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化解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暧昧与混乱”。

葛翠琳将童年记忆中关于“狐仙”“狼外婆”“花仙”“槐树精”“牛郎织女”的美丽幻想与现实世界相结合,沉淀为她1949—1966年儿童文学作品的特殊印迹。她将具有“时代性”的、对现实的思考熔铸到个人的写作实践中,对富于想象力和诗性智慧的神话资源的“创造性转换”,在一定意义上消解了“工匠式镶嵌”的儿童文学创作对现实生活的遮蔽。1953年发表在《少年文艺》上的《少女与蛇郎》开启了葛翠琳儿童文学创作之路。此后她又陆续创作了《雪梨树》《巧媳妇》《爱作诗的长工》《野葡萄》《采药女》《种花老人》《雪娘》《泪潭》《悲苦的钟声》《金花路》等脍炙人口的作品。除此之外,她还广泛涉猎小说、散文、诗歌、电影剧本等的创作。
这些受到“民间口头文学的乳汁滋养”的作品,通过对神话等民间文学资源的“复现”与“重构”,以“儿童”之名将其象征性地转换为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及本土现代性的建构力量;而由“人民和他们的口头创作”所抚育的儿童文学作品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与“主流话语的宣传诉求密切耦合”的在地化知识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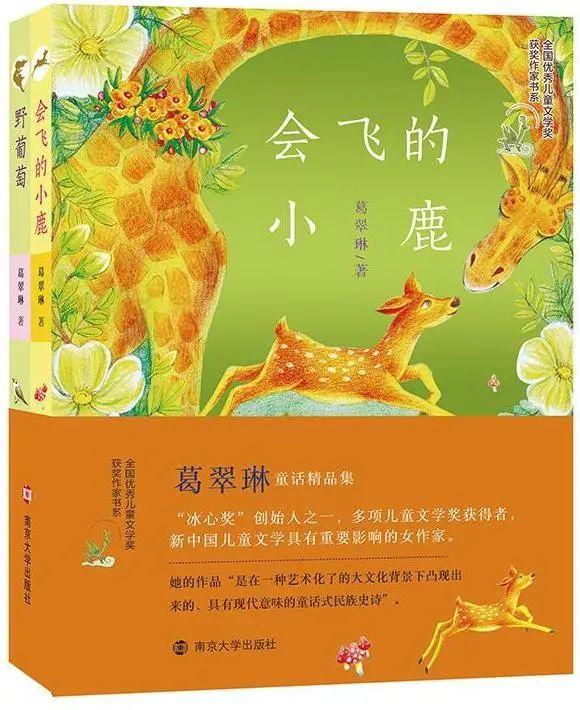
以《少女与蛇郎》为例,这一文本中所包含的兽婚、变形、季女胜利等情节,早在20世纪20年代,署名为“林兰”(或作“林兰女士”)者出版的《渔夫的情人》(民间童话集之二)中《菜花蛇的故事》就有类似情节,并且在文末还附有林兰与周作人《关于菜花蛇的通信》,其间忆及童年时母亲在“雨窗灯影”之下,怯弱的身影,和缓的声调,在叙述这些故事时,心中充满了“说不出的甜蜜和神秘的感想”。但葛翠琳的童话《少女与蛇郎》中对“从前的文本和习俗在文本生产中的表达方式”的再造或改变,“反映了实际,表现了各种社会关系、社会斗争的观念,反映了人民的思想和期望”,赋予神话资源以全新的社会功能。比如蛇郎和少女成婚后,依旧需要从事整理花木的工作,正是因为他们勤劳肯干,才能过着美满富足的生活,由此引发了少女后娘的嫉恨。林兰女士的《菜花蛇的故事》保留了这一神话传说在中国现代社会历史时期的流传形态;葛翠琳的《少女与蛇郎》则对原先神话中意义芜杂、稍显暧昧的部分做了“选择”,冲淡其中的“爱情”表达,而着重突出“劳动”“反封建”“善恶有报”等主题。在这里,民间文艺与主流意识形态实现了一定意义上的话语整合,神话资源被注人了“全新的革命意涵”。《野葡萄》中的“白鹅女”也一样,她苦苦找寻的“果皮像珍珠一样透明,叶子像翡翠一样闪耀”的野葡萄,具有治愈眼疾的神异功能。在找到野葡萄后,她拒绝了山神“石头老人”提出的为其看守宝石,“舒舒服服地吃、玩”的诱惑,一心想将光明带给以“磨坊做工的瞎老头”“吹笛子的盲艺人”为代表的“劳苦大众”。

此外,这些作品反映了大众集体诉求,无论《采药女》中“巧姑娘”因不堪忍受国王的奴役,与国王、法师代表的封建势力抗争,用自己高超的医术和神力帮助人们过上幸福的生活;还是《雪娘》中“雪娘”出于对“人类温暖的心”的向往,不惜违抗天地间的秩序制造者——“神娘”(与《牛郎织女》中王母娘娘的角色类似)的命令,跌落凡间,历经人世间的艰难困苦;这些皆隐喻了反封建的政治指向;以《雪娘》为例,在“雪娘”由神到人的身份转变中,她对人世间的向往体现了传统农业社会中“男耕女织”的社会理想和“五四”时期的“追求自由平等,提倡个性解放”的启蒙精神。在神话等民间文学资源的现代转化及话语重塑中,原初的诸多象征意义被层层剥离,被置换为与时代“共名”的表述与文化蕴涵。在这个“仙女凡夫”的故事中,“丈夫”这一角色是缺席的,承诺“儿子诞生就会回来”的丈夫在出门寻找幸福生活之后,始终没有再回来。“雪娘”一人独自承担起生活的重担。这种情节上的设置与1949年之后中国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婚姻家庭诸方面地位的变化密切相关。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阶级话语”常常在文本中占主导,但是民间话语依旧凭借自身鲜活的“幻想”溢出主流话语的边界。比如故事中的“天地秩序制造者”——“神娘”与“雪娘”之间的关系虽然渗透着阶级话语,但并不像“反封建主题”确立后的《牛郎织女》故事中王母和织女之间尖锐的阶级矛盾。随着“白雪仙女”凭借自身努力克服一道道难关,“神娘”由一个冷酷残忍的迫害者(神——统治者)逐渐变为温和善良的慈母(人——普通女性)。
神话等民间文学资源充满“幻想性”的话语表述及审美趣味,为20世纪50年代的儿童文学创作建构了灵活、弹性的话语空间;而正是由于社会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参与,将“时代感”注入了童话之中,其现实精神和价值状态才得以强化。1951年7月《新湖南报》发起的关于“李四喜思想”的讨论以及20世纪50年代在农村进行的扫盲运动、识字运动等,其中所涉及的农民自身的思想教育和身份变迁问题在葛翠琳的儿童文学创作中均有所体现。如《我比她还强》中喜欢逞能的李贵媳妇学“巧媳妇”招待朋友,反而弄巧成拙的趣事;《巧嘴儿》中的“眼里眯不进灰尘,手里溜不掉绣花针”的大媳妇被老师傅作弄,五年没有张嘴说话,最后感受到劳动的快乐——“自己烧的饭特别好吃,自己烧的炕特别暖”。《秀才和鞋匠》中的老婆婆和补鞋匠对只知道“皇帝”和“墨水”的秀才的嘲讽:
最穷穷不过只有一张口,最富富不过一双万能手,最黑黑不过大官财主的心,最白白不过庄稼汉里的明白人。

在葆有民间文学“幻想性”的基础上,葛翠琳的儿童文学创作摆脱了民间文学资源“言说状态”的当下性限制,在现代转换的话语实践中凸显其“人民性”与“时代性”。“从原初自发的民间的口头文化或炉边文化形态,推进到近代自觉的、经典的印刷文化形态”,呈现出时代“共名”之下作家主观价值体系的重构。如其主人公作为利用传统民间文学资源塑造出的“新”民,大官、王爷、皇帝均为封建势力的代表,天、地、人之间的斗争反映的是劳动人民对封建势力的反抗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经过“现代”阐释的神话等民间文学资源,“对于儿童个性的全面发展,使儿童更好地理解各种生活现象和人的关系,对于强固儿童的创造力与主动性,对于儿童道德的高尚化,有着头等重要意义……”葛翠琳在其童话作品中所构建的神话世界,既是对现实语境下人类的生存状况的神话构拟;也是在真实与想象的互动中对人类“生活世界”的神话类比和象征。其历史发生机制和现实生成逻辑之间的张力关系传递出特殊的文化蕴意与政治喻示,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在儿童文学领域中关于社会、思想、文化变革的话语实践。神话等民间文学资源为葛翠琳的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稳定的叙事话语,她在保留基本情节脉络的前提下,对人物、地域、风俗进行了置换与删减,赋予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以全新的意蕴;这也就更适应新中国儿童文学的教育要求。
总之,这一时期葛翠琳等人的儿童文学创作,在兼顾民间文学的“幻想性”与“民间性”的同时,又将其置于“开放性”的结构体系中。与民间文学母题、意象及思维相关的“话语实践”逐步成为创作的核心,“选择性改编”后的神话等民间文学资源在一个又一个语境中被重复,其文化内涵处于不断被修改和再生产的动态过程。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文章来源:《文化遗产》2021年第2期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