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击上方“民俗学论坛”可订阅哦!

赵宗福,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青海师范大学民俗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青海民俗志》于2015 年秋由青海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立项, 委托青海省民俗学会承担编撰。2016 年3 月初正式启动编撰。30位民俗学及相关专业训练的学者,历经五年通力合作,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
全志将近150万字,分为8编27章以及综述、附录等,以物质生产民俗、物质生活民俗、精神民俗、社会组织民俗、社会生活民俗、口承民俗、特色民俗、机构与人物、民俗文献为主体框架,按照地方志的体例格式,对青海民俗文化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忠实记录与深度描述。
立项之初,我们就如何完成好这部民俗志,进行过思考研究。考量海内外已有民俗志的体例、质量和体量后,我认为“拒绝一般化”和领先地方民俗学,应该是编写我们的质量追求,接着明确了具体的编撰思想。即坚持正确的文化引领方向,准确把握和再现青海多民族民俗文化,并在现行的地方志体例与民俗志学科理论方法有机结合方面做出新的探索,以现行地方志形式为志书载体,以民俗学话语体系为表述核心,灵活运用民俗志的深描理论方法和标志性文化理论,突出青海多民族民俗文化特色,形成有学术品质、有青海特色、国内同类著作中质量上乘的民俗志书。之后连续不断的文献爬梳、田野调查和研究、撰写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了这样的编撰思想。
地方民俗志的书写是中国民俗文化书写的传统之一。自从南北朝时期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以来,这方面的著作层出不穷,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地方民俗志的书写更是数不胜数。青海地区也不例外,各种“风俗志”应时而出,其中朱世奎的《青海风俗志》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但就整体而言,往往缺乏学理性,或缺乏深入科学的田野调查,缺乏民俗学理论的学术统领,或缺乏先进文化思想的观照,《青海民俗志》如何避免这些问题,真正实现既定的学术目标,是值得思考探索的。
首先在架构上,基本遵循普通地方志结构格式的基础上,严格按照民俗文化的特性进行架构和书写,不为形式而形式,而是形式服从于内容,使之成为真正有特色的“青海”的《民俗志》。志书专门设置了“特色民族民俗”篇章,专节完整地描写了《格萨尔》、黄南六月会、土族纳顿、花儿与花儿会、青海湖祭海、赛马会、撒拉族“骆驼戏”、回族宴席曲、蒙古族那达慕、河湟社火、塔尔寺酥油花、昆仑神话等11个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事象,从而保证了标志性文化书写的系统性。

其次在内容上,以团队田野所得的第一手材料,使志书内容丰满和鲜活起来,血肉相融,富有立体感。所谓田野作业,并非是简单的搜集资料途径,而是在把一种民俗文化放置在具体可感的时空中去考察的研究方法。在特有的时空中科学观察和记录,并从主客位两方面予以文化互读,进而准确把握文化的表征与本质,才有可能进行科学的“深描”。也只有在具体时空中的“深描”,才会使书写生动而准确。本志所写民俗事象都是根据编撰者在多年来扎实、科学的田野作业和综合研究所得,并予以细腻和完整的描写,既避免蜻蜓点水式的简单罗列,又避免枯燥乏味的概念背景介绍,从而增强志书科学性和立体性、时空感。
再次是志书独特的并列式中呈现学术性。民俗的并列式书写是为了归类分项,眉目清晰,但又容易把整体文化分割得支离破碎,这就需要统筹规划,并列书写中充分考虑一种具体文化事象的网络弥散性,尤其是核心民俗对其它民俗文化的统领性,彼此之间照应,使各篇章具有一脉相承的文化观照。所以把并列式看做是一种更高程度上的混合式,是一种学者缜密思考的书写。
又次是编撰风格上力求统一的科学表述。民俗志书写需要有学术共同体的表达方式。根据学界的定义,所谓“学术共同体,具有相同或相近的价值取向、文化生活、内在精神和具有特殊专业技能的人,为了共同的价值理念或兴趣目标,并且遵循一定的行为规范而构成的一个群体。”(布朗《科学的自治》) 而作为民俗志的众多编撰者,要有相同或相近专业训练,有共同的学术话语,熟悉民俗文化学的基本原理,自觉遵循民俗志书写的学术规范和学术伦理,并具有良好的团队协作意识。这就是本志书在启动之前精心选择和组建编撰团队的根本原因。
最后是作为新时代的民俗志,需要以先进理念贯穿全志。青海高原民俗文化传承悠久,自然会有一些事象已不符合社会主义新时期主流文化的要求,如何既客观又科学地记述这些民俗现象,值得谨慎把握。同时,在今天编撰一部大部头的民俗志,应有服务于地方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这就是“存史、资政、育人”。通过一部民俗志,全面系统科学地记述保存民俗文化,生动彰显弘扬高原民族优秀文化,凸显多民族文化的共生共荣,服务于青海当下和未来的文化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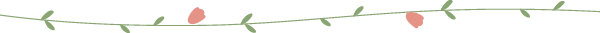
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图片来源:网络
免责声明: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与本号无关。
版权声明:如需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并保留二维码。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民俗学论坛

